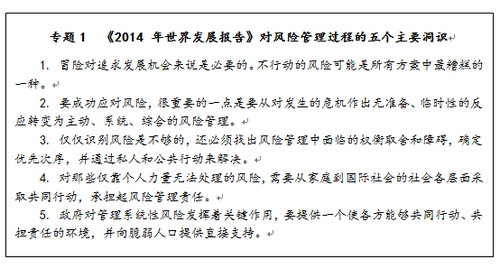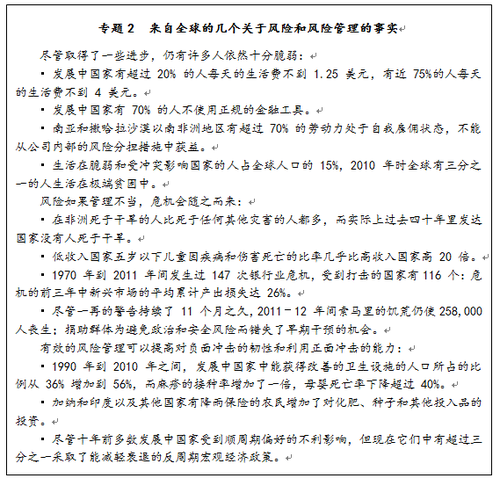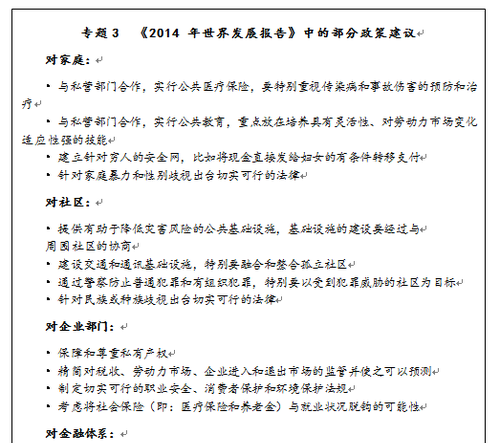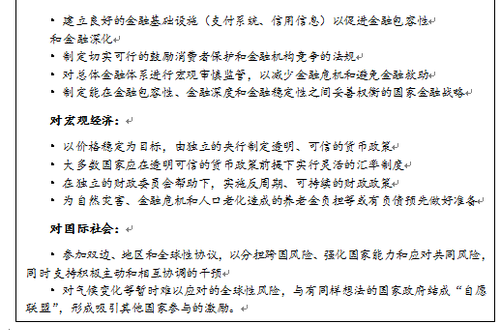2013年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三期
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企业:在差异中了解和学习
Janelle A. Kerlin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企业都同时得到了扩展。然而,关于美国和欧洲社会企业概念比较和对比的研究成果很少,这导致了有关这个论题的交流困难,也错过了学习和总结国外经验的机会。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本文通过两个地区研究文献的全面回顾以及与在大西洋两岸的社会企业研究人员的讨论,比较和对比了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企业。论文概述了美国与欧洲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所使用的社会企业概念,指明了促进和塑造不同社会企业概念的历史因素,强调了其运行的不同制度和法律环境。通过指明美国人和欧洲人相互学习彼此社会企业的经验这一事实,本文得出了结论。
导言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企业运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将之广义地界定为使用非政府和市场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在这两个地区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融资和社会倡议的方法。然而,尽管其发展趋势和终极目标十分相似,但差异仍然存在于社会企业的有关概念中,包括侧重点和谨慎的结果(Discreet outcomes)。这些差异来源于塑造和强化各地区社会企业运动的对比力量。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研究发现,虽然社会企业的涵义往往在区域层面存在差异,然而更广泛的分歧存在于这两个区域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使用、环境和政策上。
社会企业涵义的对比
美国
在美国,社会企业概念的界定通常比其他地方更广泛地聚焦于对企业创收的追求。即使考虑到美国研究者和从业者对社会企业的概念区分,这仍然是一个事实。在美国学术界,社会企业被理解为包括这些组织:从事有益于社会活动的(企业慈善事业或企业社会责任)、利益导向的公司,融合利润目标与社会目标双重目标的公司,以及致力于任务支持的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目标导向的组织)。对于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组织,任务支持型的商业活动可能只包括创收,它在非营利组织或者同时创造收入和提供项目的活动中支持其他项目,以此来满足任务目标如残疾人庇护工厂(Young,2001;2003a)。社会企业致力于非营利活动可能会采取一系列不同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内商业企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子公司、包括事业关联营销的商业合营公司。这一宽泛的定义与美国的一流大学商学院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一致的(Dees,1994;Dees,1996;Dees,1998)。它包括哈佛商学院的社会企业倡议,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社会企业家创业精神发展中心,以及哥伦比亚商学院研究倡议社会企业家精神中所使用的定义。这个定义也被许多社会企业咨询公司使用,他们建议非营利组织要和营利组织一样立足于社会企业的发展,这包括社会财富企业、社会企业集团、欧瑞格社会企业合作伙伴。
然而,在学术界和咨询公司之外,美国的“社会企业”的大部分实践仍然集中在创收上,尤其是通过非营利组织(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国税局注册为501(c)(3)的免税组织)。例如,社会企业杂志在线将社会企业界定为:“承担起以增加收入、创造就业项目活动为宗旨的个人社会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联合体”。社会企业联盟,一个全国成员组织,将社会企业更狭隘地界定为:“任何收入业务或非营利组织支持其慈善使命而采取的创造收入的策略。”此外,基金会赞助的社会企业项目往往更关注非营利的一面,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投资基金倡议,由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推进的社会变革报告,戴维、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资助的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项目(一个罗伯茨基金会的慈善项目),以及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委托的非营利创业报告等。也有一些商业学校和社会企业顾问,只关注非营利。在某些圈子里,由于商业导向的慈善活动这一术语的使用,社会企业的非营利类型就是用这些术语加以区分的:非营利社会企业,非营利企业,非营利合资企业,进取型非营利组织。
西欧
在西欧,社会企业的概念大致是使用相同的分类来归纳提取出来的,但在两种形式的思潮内部有差别,在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区别不大。一种学派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为这些力求提高生产活动社会影响的公司所持续推动。在这方面,研究文献往往强调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是按照商业培育的方式发展的(Grenier,2003),它主要通过非营利组织,也可以通过营利部门得到发展(Nicholls,2005)。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想法至少部分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有关。
另一种学派把分析限定在属于第三部门的社会企业领域,包括社会合作社(Nyssens和Kerlin,2005)。对社会企业的这种理解是由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开发的,他们与欧洲社会企业的兴起(简称EMES)研究网络相协作。在其他方面,这项研究试图建立社会企业的“理想类型”,认为社会企业不一定秉承“理想类型”的特点,然而这些“理想类型”的特点依然属于社会企业的范畴。根据欧洲社会企业兴起的研究,社会企业“理想类型”的特点包括:
1.连续的产品生产和(或)销售服务;
2.高度自治;
3.显著的经济风险水平;
4.最低报酬的工作;
5.造福社区的明确目标;
6.由公民群体发起的创意;
7.不是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
8.参与性,包括受活动影响的人;
9.有限的利润分配(Defourny,2001)。
对美国和欧洲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比较发现,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不允许任何利润分配,而欧洲的定义则允许,这至少主要归因于欧洲的定义中包含了合作的含义。同时,社会企业在欧洲被视为归属“社会经济”,社会效益是其主要驱动力。事实上,社会经济的主要组织包括合作社、共同组织、协会和基金会(OCED,2003)。在美国,没有社会经济的概念,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经常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中运作。
在西欧,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的关注刚刚概述的两种思潮,相关术语有时会与一组特定的服务相关联。在英国,中央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门(DTI)将社会企业界定为:“社会企业主要的社会目标是其盈余主要在商业或社会中进行再投资,而不是为实现股东和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所驱动”(DTI,2004)。同样,在英国,西米德兰地区社会经济伙伴关系(WMSEP)将社会企业界定为:“一个组织的集合名词,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和社区价值所驱动,旨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框架内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运转,即帮助社区也保持可行的业务”(WMSEP,2004)。
在比利时,如同一些欧洲国家,社会企业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一般来讲是服务组织,开展商业活动。第二层含义是指那些合作社或协会,其目标主要在于激励“针对那些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职业群体”(Defourny和Nyssens,2001)。第二层含义源于特定的社会服务需要,社会企业在欧洲的发展导致它们与就业创造计划密切相关。这种常见的定义与一个社会目标组织的美国学术概念高度一致,这些组织为参与者制定计划,包括能同时创造收入的活动。在欧洲,社会企业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员工发展信托、社会公司、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社区商业等(OECD,2003)。
正如欧洲社会企业兴起的定义中所隐含的,通常认为,欧洲的社会企业与美国不同,它涉及项目受益人的工作和参与性贡献。例如,合作社通常被理解为社会企业的基本类型,合作社的加入似乎影响了社会企业定义的总体方向。欧盟的定义强调参与,还把概念内涵拓展到社会企业的管理上。管理机构是由一个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可能包括受益人、员工、志愿者、公共当局、捐助者等。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采用正规的民主管理风格,但这并不是美国社会企业所需(Defourny,2001)。事实上,Young和Salamon指出,“在欧洲,社会企业的概念更多地集中在一个组织的管理方式上及其目的上,而不是它是否严格坚持正式的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约束”(Young和Salamon,2002;也参见Borzaga和Santuari,1998)。多方利益相关者群体,作为一种独特的合作形式,在欧洲越来越受欢迎,甚至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法律认可(Levi,2003;Lindsay等,2003;Münkner,2003)。在意大利,1991年的法律第381条规定,社会合作具有三个主要类别的分享者或利益相关者:贷款或融资成员(65%)、受益人/用户成员(5%),志愿者成员(20%)(Thomas,2004)。法国最近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多方利益相关者策略的合作社利益体(Lindsay和Hems,2004)。
对美国和欧洲社会企业的定义进行比较表明,社会企业这个词在两个地区似乎已被界定为略有不同的事物。在欧洲,除了英国,社会企业通常意味着社会合作社或协会,其成立是为在一个参与性框架内提供就业或特定保健服务。在美国,社会企业通常指任何类型的从事创造收入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尽管美国有许多与欧洲社会合作社相类似的工人合作社,但这些实体却未被纳入美国社会企业的定义中。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国际组织被夹在中间,因为它们在大西洋两岸的使用中要么采用美国社会企业的定义,要么采用欧洲社会企业的定义,而不是这两类定义的综合。例如,偏向欧洲多一些的定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社会企业界定为“符合公共利益的、在企业战略的组织框架下开展的私人活动,但其主要目标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并且有能力用创新方法解决社会排斥和失业问题”(OECD,1998)。相比之下,美国对口国际的报告概述了乌克兰社会企业发展的经验(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1997—2002年投资的项目),将社会企业界定为“非营利企业或创收活动的通用术语,其创建在于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参照财政底线进行运作”(Alter,2002)。
促进和塑造社会企业的历史因素
美国
在西欧和美国所发展的社会企业概念中,对其界定的差异源自不同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历史因素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更多地关注创收,而在欧洲,创收活动则与项目受益人的工作或参与活动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当宗教和社区团体举行义卖和出售自制的产品来增加自愿捐款时,非营利组织利用商业活动来支持相关的使命,这些活动已经从国家的基层开始实践了(Crimmins和Keil,1983)。然而,社会企业这个词首次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将非营利组织的一些商业活动确定为贫困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Alter,2002)
在美国,当非营利组织所依赖的政府资助受到削减后,社会企业作为一个被界定的概念开始扩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计划开始,联邦政府在扶贫工程、教育、卫生保健、社区发展、环境和艺术方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这些资金通过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运作来推动社会企业组织的拓展与创新,而不是创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Hodgkinson等,1992;Salamon,1995;Young,2003b)。受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低迷的影响,80年代福利紧缩,联邦资金大规模的削减,并导致了在医疗保健领域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减少了大约380亿美元(Salamon,1997)。非营利组织开始利用社会企业来填补政府支出极大削减后留下的空白,来扩展非营利性商业活动的作用(Crimmins和Keil,1983;Eikenberry和Kluver,2004;Young,2003b)。正如Salamon所说,在1977到1989年间,社会服务组织将近40%的收入增长来自收费和其他商业来源”(Salamon,1993)。随着这种情况的扩展,社会企业这一术语开始呈现更广泛的意义,几乎任何类型的商业活动都在追求社会目标。因此,在美国,至少在最初阶段,现有的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把社会企业活动作为一种为投资于服务提供的方式,其结果是社会企业往往是独立的,它通常在活动之外支持更为广泛的社会服务。
来自于城市研究所国家慈善中心的数据表明,在美国,社会企业在持续增长。运用财务信息的数据库对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进行了20年(1982—2002)的追踪研究,这些非营利组织拥有25000美元,并超过美国国税局的收入档案。商业收入包括项目服务收入(服务费),销售商品的净收入,特殊事件和活动的净收入,以及会员的会费和评估会员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的评估费。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年间,商业收入不仅一直是收入的最大贡献者,而且也获得了大幅增长。从1982年到2002年,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收入增加了219%,私人捐款增加了197%,政府拨款增加了169%。最重要的是,它也成长为总收入的一部分。1982年,商业收入占非营利收入的48.1%,但是到了2002年则占到57.6%。同时,私人捐款所占比例却只从19.9%增加到22.2%,政府拨款从17.0%增至17.2%。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收入的变化趋势可能会由于非营利界别分组而有很大差异。例如,在相同的时期内,艺术和文化的非营利组织见证了私人捐款的增加,它远远超过了政府拨款和商业收入的增加(Kerlin和Pollak,2006)。
西欧
在西欧,社会企业向现代的发展趋势比美国稍微晚一些,它主要集中在第三部门的服务和创收多样化的同时发展。伴随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许多欧洲福利国家出现了危机。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许多欧盟国家经历了失业率从3%上升到4%甚至高达1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的12%和日本的15%相比,欧洲失业人口中超过40%都是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一年)(Defourny等,2001,p.5)。其中预算约束是主要原因,但这场危机也与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关(Borzaga和Defourny,2001;Borzaga和Santuari,2003;Spear等,2001)。由于失业政策尤其是长期失业政策(包括贫困群体和低技能群体)被证明是无效的,失业人口聚集地区政府的合法性遭到极大削弱(Borzaga和Defourny,2001)。
以分权、私有化和减少服务为特征的福利国家的紧缩也紧随其后。作为福利紧缩和失业人口增加的结果,公共政策方案相当缺乏,大量的社会服务需求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第三部门的新型社会企业,开始应对这些不断涌现的需求,包括解决日益边缘化群体的住房问题,提供儿童保育服务以满足由于社会经济变化所产生的新需求,为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老龄化提供新服务,城市重建计划,长期失业人员就业计划等等。在欧洲,大多数创新性的社会企业由民间社会行动者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这些民间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工作者、联合的激进分子和更传统的第三部门组织代表,有时还包括被排斥的工人们(Nyssens和Kerlin,2005)。
因此,在欧洲,由社会企业支持的各种服务比较少(相比于美国社会企业活动支持的宽广范围),因为欧洲的社会企业倾向于处理福利国家已经退出或不能满足需求(即长期失业者就业计划和个人社会服务)的特殊领域。当然,社会企业满足特定服务需求的程度会因福利国家和每个欧洲国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社会企业的法律环境
在美国和西欧,社会企业的法律环境反映了政府介入问题的差别。美国的非营利组织(501(c)(3))与欧洲的协会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验证。
美国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将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税收(UBIT)宽泛地定义为与一个组织免税目标无关的非营利收入所得税(Cordes和Weisbrod,1998)。特别是,美国国税局(简称IRS)将无关的业务所得税定义为“从一项贸易或业务中定期获得的收入,它实质上与具有免税目的或功能的组织活动无关,除非组织需要从这个活动中获得利润”(美国国税局,2004)。州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已经为非营利组织创造了类似的无关的企业所得税。
尽管不同层次的美国政府试图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活动,评论家仍然指出,“在实践中,联邦、州、地方税务部门区分应税和免税的商业活动被证明是具有行政障碍的”(Cordes和Weisbrod,1998,p.85;see还有Simon,1987)。这种情况使得非营利组织谨慎从事某些类型的创收活动,因为他们担心会削弱他们的慈善的免税地位。另一方面,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声称非营利企业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并不总是对同样的服务和产品缴税,而营利性组织则需要缴税(Crimmins和Keil,1983;Leavins和Wadhwa,1998)。在美国,过去50年来,几乎没有出台新政策以适应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企业的商业活动。
西欧
在西欧,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在一个非营利性的协会或合作社的法律形式下运作。在那些国家里,社会企业是以协会的名义建立的,法律意义上的协会被允许在开放的市场上享有销售货物和提供服务的自由。像在瑞典、芬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里,协会更多地被限于这方面,社会企业往往建立在合作社的法律形式之下(Borzaga和Defourny,2001)。因此,与美国不同,具有社会和就业目标的合作社也被视为社会企业。以就业为中心的合作社是一类特殊的社会企业,它被称为“社会企业的工作整合”(简称WISE)。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残疾人或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的社会和职业的融合,同时在企业内部或一个固定的雇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跟踪或持续融合的培训”(Spear和Bidet,2004,p.8)。Borzaga和Defourny(2001)指出协会和合作社可能会融合,因为协会采用了更多的创业活动和合作社向非会员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
不像在美国,社会企业的法律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在一些西欧国家得到发展,特别是在那些对社团开展业务活动有限制的国家(CEC,2001)。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社会福利服务的创业和业务支持,提高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同时促使各种利益相关者(员工、志愿工作者、目标群体、自治市或区的政府当局)参与到生产过程中”(CEC,2001)。
正如已经提到的,意大利在1991年第一个引入“A型和B型社会合作社”立法,多年来它已经成功地增加了许多这类组织。比利时在1995年为“具有社会目标的公司”提出立法,葡萄牙在1998年创立了“社会团结合作”,希腊1999年建立了“社会合作有限责任”(Defourny,2001)。法国在2001年引入了集体利益合作社协会。这项立法由欧洲委员会的Digestus项目所支持,这个项目开始于1998年10月,它提议成员国改变法律,以沿着意大利合作企业的模式以实现促进社会企业的目标(Lindsayet等,2003)。由于强调创业行为,新的法律实体倾向于采取合作形式(Borzaga和Defourny,2001)。在欧洲,社会企业最新的组织形式是“社区利益公司”,它是英国在2005年提出的。
社会企业的制度环境
美国
在美国和西欧,社会企业的制度环境往往反映了美国以私人/商业为中心,欧洲以政府/社会服务为中心。在美国,制度支持环境主要由私人组织组成,这些组织为社会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教育、培训、研究和咨询服务。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美国社会企业战略发展最大的外部金融支持和其他支持来自私人基金会,而不是政府(Paton,2003)。
社会企业的战略发展
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私人基金会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组织。一些基金会关注社会企业的基本信息收集和网络创建(凯洛格基金会,考夫曼基金会,苏德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另一些基金会则把支持转向社会企业的起始阶段(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社会企业业务竞争(高盛基金会,皮氏慈善基金会),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集中的教育计划和(或)资助来支持私人社会企业家,其中有些教育计划和资助是国际性的(理查德·卡普兰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绿色回声组织,阿育王基金会,施瓦布基金会)。
得到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是所谓的社会企业的加速器。虽然数量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是匹兹堡的宾夕法尼亚社会企业加速器。起初,它是由两大基金会投资创办来支持新兴非营利企业在匹兹堡地区的发展,而这对非营利组织来说没有任何成本。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小型投资组合来说,它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种子资金、商业工具和与社区中关键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等服务,其中社区中关键利益相关者有服务提供者、资助方、企业、公共机构和大学课程。不同背景的员工和咨询委员会成员帮助促进社区联系(匹兹堡社会企业加速器,2006)。由于那些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愿意付费,大量的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运营和业务方面协助社会企业。
对社会企业一些有限的大部分是间接的政府支持,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三个层次都存在。例如,尽管由不同级别的政府发起的社区发展计划并不直接针对社会企业发展本身,但他们可以提供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直接支持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子是,由华盛顿西雅图支持的1998-2001年社会企业创新计划。它经常联合各基金会来赞助诸如非营利组织创业培训,以及作为美国第一个社会企业博览会等实例的西雅图社会企业博览会。社会企业博览会促进了西雅图社会投资论坛的发展,该市资助了其前两年。其后年度论坛的资金交由盖茨基金会接管(Pomerantz,2003)。
一些州和联邦也有预留方案,这些方案主要雇佣残疾人开展社会企业社区康复计划。27个州留出资金用于从康复计划中购买州所用的物资和服务。例如,华盛顿的康复计划向州出售了价值约300万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一个存在于联邦政府层面的类似的计划由华格纳-欧德法建立。强制性联邦采购计划“通过策划政府购买产品和服务为超过36000位美国盲人或其他严重残疾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产品和服务是非营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雇佣这些残疾人来提供的”(Pomerantz,2003)。
社会企业研究
在美国有关机构支持的社会企业研究方面,商学院对社会企业进行了与社会科学院系一样多的研究。商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用知识上,这些知识是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经理们开展社会企业活动所需要的(Boschee,1998,2001;Brinckerhoff,2000;Dees等,2001;Emerson和Twersky,1996;Paton,2003;等等)。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根据主题采用更为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书籍和文章(Ben-Ner和Gui,1993;Hansmann,1980;Rose-Ackerman,1986;Weisbrod,1988;Young,1983)。
会员协会
最近,在美国,围绕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的理念已经形成了会员组织。成长最快的一个组织是社会企业联盟,它自我界定为“领导创建社会企业运动的会员组织”,其目标是“动员非营利组织和资助者团体来推进创收策略”(社会企业联盟,2004)。它是由社会从业人员来运营。该联盟是2002年两个团体合并的结果:全国性社会企业家集会(成立于1998)和思迁公司(成立于2000)。这些团体的根基是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除其他之外还包括凯洛格基金会,考夫曼基金会,绿色回声基金会和诺斯兰研究所(福特基金会)(社会企业联盟,2004)。
西欧
社会企业的战略发展
在西欧,社会企业战略支持的制度环境更多地与政府和欧盟的支持联系在一起。尽管第一批欧洲社会企业的出现没有任何特定的公众支持,但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特定公共计划在许多国家的发展。政府支持包括上面所说的新立法以及特定公共单位和计划的协调和政策工作。
在英国,后者的一个例子是中央政府的贸易工业部,它有一个社会企业单位负责实施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即“社会企业:成功的策略”。它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工业部、区域发展机构、政府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社会企业的支持环境。该单位还为社会企业制定了税收,提出了行政监管的建议,支持了该地区公共和私人的培训与研究(贸易工业部,2004)。
在爱尔兰,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支持社会企业,并把它作为降低失业率的一种方式。国家社区企业项目,建立于1983年,“提供资助性的培训项目,推进为社区团体提供发展资助和商业支持”(O´Hara,2001)。在芬兰,劳工部曾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合作社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来拓展有关如何建立合作社的材料和报告(Pättiniemi,2001)。
然而,大部分的政府支持,在公共政策和融资方面(除意大利的“A”型社会合作外),仅仅关注前面提到的社会企业的工作整合(WISE)。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当局对社会企业整合的法律认可是通过工作上确实允许更加稳定的获得公共补贴来实现的,但是这是一个有针对性而有限的方式。通常只有临时补贴才允许提倡,并弥补“临时丧失了就业能力”的工人(如由于在长期远离劳动力市场后导致技能退化,他们很难再找到工作)(Nyssens和Kerlin。2005)。
在推动社会企业的研究和项目支持方面,欧盟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它把社会企业看做是一种可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就业和生活质量问题的业务模式(Thomas,2004)。1996-1999年,欧盟委员会研究总司资助了社会企业兴起计划的欧洲项目,它调查了所有15个国家而不是欧盟一部分的社会企业。该委员会还资助了后续的PERSE(在工作整合领域的社会企业的社会经济计划)项目,该项目在2001-2004年欧盟的11个国家中进行。欧盟委员会企业总司支持了社会经济企业,如自1989以来的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它目前的重点是“企业方面”。它支持研究,帮助起草欧盟法规,与组织进行协商,并为成员国制定法规的政府官员取得联系(欧盟,2004)。
欧盟为各成员国的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欧盟在这一地区特别活跃。1992年初,爱尔兰已从欧盟结构基金得到全面资助,“来支持地方发展与企业创新,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和社区的整体发展”(O´Hara,2001,p.156)。针对农村发展的欧洲领导人项目也提供了类似的帮助。其他的欧盟创新计划在爱尔兰为当地的社会企业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帮助,这些企业有INTEREG,NOW,INTEGRA和URBAN。如O´Hara总结的,“针对当地发展的这些支持为新型社会企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通过参与这样的项目也为现有企业提供了机会以扩展或巩固他们的活动(O´Hara,2001,p.156)。
社会企业研究
在西欧,社会企业研究几乎完全在社会科学院系进行,尽管一些商学院已经开始探索这个主题。研究和教学聚焦于合作社,互助协会,以及独立于营利部门的社会经济运作的协会。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些组织的技能匮乏的工作整合和护理服务所带来的贡献上。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欧盟国家对欧洲社会企业兴起的研究网络的工作中,欧洲更加一致的努力对社会企业进行统一的定义和研究(Defourny,2001)。目前的研究包括社会企业研究理论方法的发展——这项工作经常利用经济理论(Bacchiega和Borzaga,2001;Badelt,1997;Laville和Nyssens,2001;Sacconi和Grimalda,2001),有时也会用一些社会理论(Evers,2001)。
会员协会
社会企业的会员组织在欧洲是一个新现象。英国社区行动网络创建于1998年,它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会员协会,大致相当于美国社会企业联盟。它宽泛地定位于提升社会企业家的精神,尤其是促进在非营利组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思想交流。这个网络声明说,“我们主要关注社会创业方针的实际传递,同时在方法及该方法对社会重建的重要性两方面继续刺激政府、公众与个人进行思考。”(社区行动网络,2004)。
问题及挑战
美国
在美国,尽管社会企业发展良好,但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包括特定群体的排斥,市民社会的弱化以及政府的缺失。对于第一个问题,特定类型的社会企业在进一步加强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上,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例如,社会企业通过有偿服务策略获得收益是社会企业活动的一种通常形式。但一旦该策略被使用到无偿社会服务中,由于难以支付服务费用,许多贫困的潜在受益人将自动被排除在享受服务范围内(Salamon,1993)。另外,当营利活动损害服务质量时,脆弱群体或将被排除在外,而服务质量是非营利机构的重心,更糟糕的可能是一些营利活动因有利可图更受欢迎(Dees,1998;Eikenberry和Kluver,2003;Weisbrod,1998;2004)。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参与市场活动的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注重迎合个体客户的需求,而不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服务于邻里或社区(Alexande等,1999)。由于营利组织提供类似服务,非营利组织面临着新的竞争,而且这种情况日益恶化(Young和Salamon,2002)。
美国的观察家担忧,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市场化将使市民社会面临危险(Alexander等,1999;Eikenberry和Kluver,2003)。非营利组织对市民社会的有益之处之一是,非营利组织可以强化社会资本。对提供服务的底线的关注或将导致非营利组织强化社会资本的效率降低,例如经营志愿者项目。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企业化也可能导致这些组织意识到他们无需依赖股东及其网络,例如私人捐赠者,组织成员,社区志愿者及其他社区组织,这最终导致提升社会资本机会的错失(Aspen Institute,2001;Eikenberry和Kluver,2003)。最后,非营利组织对市场策略的关注,或将导致组织成员由与社区密切相连变为与市场交易密切相连(Backman和Smith,2000)。
鉴于以上几点,美国面临的其它挑战还包括致力于营利活动的非营利机构的清晰的法律定义。事实上,当前与欧洲的对比表明美国相对缺乏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参与,这预示着这个领域可能是需要改进的。
西欧
西欧社会企业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及挑战,这主要因为社会企业的运行方式大不相同。观察家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社会企业提供的服务范围很窄。与工作整合以及社会服务相关联(通常作为政府在特定领域政策失败的替代品),社会企业未被充分发挥其作为支撑第三方活动的可用策略的作用(Borzaga和Defourny,2001)。它的促成因素和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与美国相比,西欧实际参与的社会企业类型有限(在美国,特定含义的社会企业包括与营利组织之间的非营利伙伴关系的活动,事业关联营销,以及任务相关产品的销售)。
与美国一样,大量西欧国家也缺乏对社会企业法律框架内的清晰界定。Borzaga和Defourny(2001)呼吁政府出台对社会企业给予充分的法律认证和规定的相应政策,以及考虑具有应对失业、社会排斥和提供更广泛服务的社会政策。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修改法律以满足这些需求。Borzaga和Defourny还呼吁,当地政府通过在特定区域限制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合作,来增加对社会企业产品及服务的需求。
结论:相互学习
下表提供了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差异的比较的概况。社会企业的比较表明,美国社会企业面临困境的地方,欧洲发展良好,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一方面,美国可以向西欧借鉴对社会企业的政府参与,组织管理。另一方面,美国在如何利用社会企业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如何扩展社会企业类型,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利用政府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合约等方面,为欧洲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企业比较概况表
|
国家 比较项 |
美国 |
欧洲 |
|
重点 |
收入 |
社会效益 |
|
一般的组织类型 |
非营利组织(501(c)(3)) |
协会/合作社 |
|
关注点 |
所有非营利活动 |
人类服务 |
|
社会企业类型 |
很多 |
很少 |
|
受益者参与度 |
有限 |
普遍 |
|
战略发展 |
基金会 |
政府/欧盟 |
|
大学研究 |
贸易和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 |
|
环境 |
市场经济 |
社会经济 |
|
法律框架 |
缺失 |
不发达但不断提高 |
特别是,美国可以向西欧借鉴社会企业活动中有关项目受益者参与的实践。可以通过合作或直接参与到效益生产过程中使受益者参与其中。但一些社会企业没有必要受益者参与其中,例如付费服务;更加协调的社会企业活动有可能使受益者参与其中,尤其是某个组织已经参与到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以营利。这种过渡可以提供有利的工作经验并对项目受益者进行培训。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最贫穷的群体参与进来,这样就可以简单地解决美国社会企业所面临的排斥问题。
美国还可以向西欧借鉴社会企业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多股东模式及民主管理模式。欧洲社会企业的理事会有多位股东组成,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建立市民社会,加强民主。随着社会企业在美国的扩张及其对市场化和市民社会弱化的贡献,可以通过将社区内的个体联合起来的方式,使多位股东管理社会资产。民主管理模式加强了各个层面的民主实践。
西欧还提供了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如何建立一个适合社会企业创新及发展的环境。通过比较揭示了,在美国,基金会是支撑社会企业的主要力量,特定的经济、法律及管理边界限制了建立有利于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另一方面,西欧也可以从美国获益良多。历史因素限定了欧洲社会企业的出现,导致欧洲的社会企业的关注重点仅局限在工作整合与个人的社会服务上。在美国,社会企业活动范围很广,包括社会服务之外的非营利活动(例如环境保护)。欧洲人对扩大社会企业的服务范围很感兴趣,他们可以从美国的工作模式中获益。
与之相似的是,欧洲人可以向美国人学习社会企业的不同形式,以拓展其创收活动。根据欧洲扩大其社会企业涵义的意愿大小,美国人可以提供多种非营利策略范例,例如任务相关产品的销售,事业关联营销(营利产品的联合品牌),与营利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与其他非营利机构一起建立营利分支机构(Sealey等,2000)。
最后,尽管美国政府基本不参与社会企业,但欧洲政府不愿涉及的一个领域美国政府确实参与其中了(少部分除外),即政府为社会企业产品签订的合约(Borzaga和Defourny,2001)。美国联邦政府在通过由3.6万名分布各地的员工生产的产品采购所获得的补贴基金上,为社会企业产品创造需求提供了一个案例。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政府都操控着相当的补贴项目。欧洲可以通过鼓励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类似的支持管理方式,来加强现有的社会企业的运转。
论文信息:Janelle A. Kerlin.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Voluntas (2006) 17:247–263.
·减贫报告·
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
《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
世界银行
前言
最近几年里,世界遭受了诸多危机。金融和经济动荡带来的收入下降、就业减少和社会稳定性丧失扰乱了世界经济。剧烈的自然灾害摧毁了从海地到日本的一个个社区,造成了生命和经济损失。对全球变暖的忧虑不断增加,同样不断增加的还有对致命传染病传播的担忧。
在全球旅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相同的关切:我们怎样才能变得对这类风险更具韧性?《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WDR 2014)有助于回答这个急迫的问题。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如果不冒必要的风险则可能错失发展机会。追求机会就需要冒险,但许多人,特别是穷人,常常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不好的结果。不能采取行动会让人们陷于贫困,使他们容易遭受不利冲击的影响,甚至降低他们追求那些会改善他们福祉机会的能力。
缺乏适当管理风险的能力会导致危机和错失机会,这对达成世界银行集团的两个主要目标——到2030年时终结极端贫困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底层40%的人口共享繁荣——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因此,有效地管理风险对世界银行的使命而言绝对是核心问题。《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工具——它能拯救生命,避免经济震荡,并帮助人们构建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
这个报告呼吁个人和机构不要再做“危机斗士”,而是成为“具有主动性和系统性的风险管理者”。有大量证据表明认识危机并为危机做好准备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表现的具有韧性,这是因为之前它们对自己的宏观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
通过建立对风险的韧性来保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是实现繁荣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同自然灾害、流行病、金融危机、社区范围的犯罪浪潮搏斗的人,还是要应对家庭主要供养者罹患重病的人,情况都是如此。风险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通过采取包括结构性政策措施、以社区为基础的防范、保险、教育、培训和有效监管在内的平衡的方式,人和机构可以建立对风险的韧性。国家已经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管理风险,但到目前为止,与发展中国家风险管理相关的研究还未能合成一个单一的、易于获得且内容翔实的资源。
这本《世界发展报告》旨在填补这个空白,对于使风险管理成为发展日程的主流和帮助国家与社区加强它们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它可以发挥有价值的指导作用。本报告还为世行改变面对自身业务风险的方式提供重要的见解。世界银行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转型,这就要求转变关于风险的机构文化,使之从极力避免风险转向有根据地冒险。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提醒大家: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根本不冒险,对此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的希望是《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能带来这样的风险管理政策:它能让我们在将未来发生危机的危险降到最低的同时抓住每个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将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人人都渴望的世界:一个摆脱了贫困,大家共享繁荣的世界。
风险管理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工具
过去25年里世界各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很多变化是朝着好的方向。很多国家走上了国际融合、经济改革、技术现代化和民主参与的道路。它们的经济在增长,人民在摆脱贫困,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家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使数亿人受益。随着世界的变化,各种机会也不断涌现。然而,伴随着这些机会也出现了许多旧的和新的风险——从失业、犯罪和疾病到金融风暴、社会动荡和环境损害等各种可能性。如果置之不理,这些风险就可能转变成危机,逆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并危及造就这些成果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风险管理不当的后果可能是生命、财产、信任和社会稳定遭到摧毁,而常常是贫困人群受到的打击最大。
《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解决办法不是为了避免风险而拒绝变化,而是要为变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和风险做好准备。负责、有效地管理风险可以拯救生命、避免经济受到损害、防止发展遭遇挫折,同时还能释放机会。这样做还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安全和保障以及发展的途径(专题1)。
有效的风险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风险管理就是直面风险、进行风险准备并应对风险的过程,其目标有两个:形成韧性,韧性是人、社会和国家从负面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实现繁荣,这来自对能释放发展机会的正面冲击的成功管理。风险准备由三种可以提前采取的行动构成:获取知识,即了解各种冲击、内部和外部条件及潜在的结果,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建立保护,即降低损失的概率和规模,提高收益的概率和规模;获得保险,即将资源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好的自然状态与差的自然状态之间进行转移。而一旦风险(或机会)成为现实,人们将采取行动应对发生的情况,即从损失中恢复,并尽可能扩大收益。有力的风险管理战略应包含所有这些元素,它们互相作用并彼此补充,比如,更多的知识可能导致资源在保险和保护之间得到更高效的配置。同样,更好的保险和保护可以降低风险应对的难度和成本。
风险准备的收益大于其成本
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产生的危机和损失代价很高,但为进行更充分的风险准备而采取的措施也有很高的成本,因此,进行风险准备是否物有所值?证据表明,收益会大于成本,有时甚至会远远大于成本。比如,旨在减少营养不良及相关健康风险的矿物质补充剂带来的收益至少比成本大15倍。
风险管理还要求对不同的风险及对每种风险进行准备的相对必要性做出评估。鉴于有限的资源,确定重点和作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比如,一个容易受到暴雨困扰,同时还面临国际金融冲击风险的小国,就必须要决定花多少资金来防范洪水和储备多少资金以减缓金融动荡的影响。
要考虑的不仅是各种权衡取舍,还有各种协同作用。“双赢”的局面可以降低风险(损失的概率)和增加可能的收益。典型的例子是对营养和预防医疗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有秩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种协同作用非常普遍,应该受到重视,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毫无成本或者容易实施。
个人和社会进行管理风险的难处
如果风险管理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具有成本效益,那么为什么个人和社会不能更好地管理风险?尽管每个实例的具体答案都不同,但这个问题总是与个人和社会所面临的障碍与制约因素有关,包括缺乏资源和信息、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失败、缺少市场和公共产品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外部性。这种现实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仅仅识别风险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出风险管理中面临的障碍,确定优先次序,并通过私人和公共行动来解决。
整体性的风险管理方式
虽然个人自身的努力对管理风险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支持,他们能取得的成功将是有限的(专题2)。大多数个人本来就不具备应对大的冲击(比如一家之主病倒)、系统性冲击(比如自然灾害或金融危机)或多重冲击(比如干旱之后又发生食品价格震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家庭到国际社会的社会各层面采取共同行动,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这些社会和经济体系可以用不同但互为补充的方式支持人们的风险管理。
·家庭是提供支持、共享资源、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脆弱的成员)并使他们可以对未来投资的主要单位。
•社区提供非正式的保险和保护网络,帮助人们处理个体风险,并整合资源来应付共同面临的风险。
•企业有助于吸收风险和对风险所包含的机会加以利用、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促进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
•金融体系可以在负责任地管理自身风险的同时提供有用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储蓄、保险和信贷。
•国家具有管理国家和地区层面系统性风险的地位,可以为其他系统的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并对脆弱的人群提供直接支持。这些作用可以通过社会保护(保险和救助)、公共产品(国防、基础设施、法律和秩序)和公共政策(监管、宏观经济管理)来实现。
•国际社会可以提供专业知识,推动政策协调,并汇集资源用于应对那些超出一国能力或跨越国家和代际界限的风险。
这些体系相互作用,常常互为补充,有时会彼此替代发挥风险管理的作用,比如,企业依赖宏观经济的稳定、公共服务和金融产品保持活力和持续为人们提供收入和就业。金融体系可以提供保险、储蓄和信贷,但前提是有足够多的家庭和企业使用这些服务,而且经济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通常,只有具备法治和合理的监管框架等必要的公共服务,市场才能越来越多地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和资源。
使风险管理成为发展日程的主流
《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了在社会不同层面改善风险管理的数十个具体政策建议。然而,它给出的首要建议就是应该以积极、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实施这些建议以取得最佳效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报告主张各国建立国家风险理事会,它能有助于使风险管理成为发展日程的主流。这个理事会可以是一个新的机构或者由现有机构改革而成:最重要的是方式的改变——一种向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进行协调、系统的风险评估过渡的方式。实施这些建议要求政府大幅改变制定和实施其整体规划的方式,将变化和不确定性视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性。
改善风险管理公共行动的五个原则
《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析说明,要改善对风险管理至关重要的社会保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有几项关键原则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好的指导。下面讨论的这五项原则是从世界各国的最佳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适用于各种风险和各类国家。但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应当符合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虽然乍看上去这些原则没有什么争议,但实际应用起来却可能引起紧张和矛盾,使它们的贯彻遇到挑战。
1.不要引发不确定性或不必要的风险
国家应该力求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或者至少不要使之恶化。政府为什么或者怎么会加剧风险和不确定性呢?首先,它可能延续歧视某些群体(比如妇女或某些种族群体)的社会规范,使他们更加脆弱。第二,它可能优待政治上支持自己的群体而牺牲其他人的合法利益。第三,内部碎片化和缺乏组织协调的政府可能采取自相矛盾的政策或者不能有效执行政策。最后,在面对难题时,政府可能被意识形态、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简单的绝望所左右,而不是依靠建立在良好证据和分析基础上的措施。
2.向人们和机构提供正确的激励,促使他们在不将风险或损失转嫁他人的前提下进行自己的风险规划和准备
正确的激励对于避免发生一部分人获益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情况至关重要。应该避免救助,但如果不得不进行救助,那么救助方案的设计要避免提供不当激励。在2000–01年的银行业危机后土耳其的作法(特别是土耳其银行监管机构的坚定立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社会保障可能因为不鼓励自立以及给国家造成不可持续的负担受到批评。直接将对人们的激励考虑在内的设计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设计良好的安全网——如孟加拉、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或工作福利项目——改善了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创业方面的做法,同时又保持了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人们对于个人和社会责任思维模式的两个转变对有效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那就是从依赖到自立,从孤立到合作。提供正确的激励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帮助。
3.对风险管理采取长期视角,建立超越政治周期的制度机制
诱导国家保持长期视角,不为公共意见或政治联盟的反复无常所动需要制度机制,比如,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必须以连续的、可持续的资金为基础才能取得成功。泰国和土耳其近来向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过渡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金融体系必须在包容性和稳定性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在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财政部和私营部门互相配合制定针对金融部门的长期战略。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要求采取长期的视角。就这一点而言,智利、哥伦比亚和挪威一直以长期预算平衡为目标。
4.通过清晰、可预见的制度框架提高灵活性
适应新环境的灵活性对加强韧性、抓住机会而言非常必要。典型的例子包括家庭为应对变化的经济形势而搬迁以及企业面对技术和需求冲击进行创新。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保持合理、透明、可预见的制度结构的同时提高灵活性。就企业来说,丹麦的“灵活安全”模式就提供了这样的平衡,将市场灵活性与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和再就业政策结合起来。就宏观经济来说,具有浮动汇率的通胀目标制提供了灵活且制度上健全合理的货币政策的良好范例。
5.在鼓励自力更生、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脆弱人群
对于仍极易受冲击影响的家庭,国家可以提供安全网。只要支持明确地以脆弱人口为对象,并且以鼓励劳动为目标进行设计,即使是低收入国家也可以提供安全网。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体系”为数百万家庭提供了粮食保障,同时对社区资产进行了投资。国际社会也可以向脆弱人口提供资源和专业知识。尽管受到许多诟病,在可靠的当地机构的协调配合下提供的海外援助却一直十分成功,2004年海啸后的印尼就是这种情况。通过促进持续的增长,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脆弱性并有助于消除极端贫困。
简短结语
如果个人和家庭可以针对现代生活的风险和机会作出规划和准备,他们的命运就可以有所改善。如果社区和国家可以共同承担风险管理的长期责任,它们的命运也会有所改善。
来源:世界银行。
·书籍推荐·
评《饥饿与公共行为》和《贫困与饥荒》
陈国富 卿志琼
曾经以为,中国经济学家今天的使命就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弘扬“主旋律”,而对于在这一浪潮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则可将其划归为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对象,他们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存在;曾经以为,二十世纪那场在中国持续了三年并夺去成千上万生命的饥荒与经济学家无关,因为那是一场“自然灾害”,既然是“天灾”,经济学家就无须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曾经以为,中国目前尚有几千万人遭受饥饿的折磨肯定是由于耕地撂荒、粮食减产所致,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呼吁保护耕地并做一些有限的捐献而已。但是,当读完阿玛蒂亚·森(Sen)所著的《贫困与饥荒》和《饥饿与公共行为》之后,立刻令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并自以为可以置身局外的经济学工作者羞愧万分。
这种羞愧首先源于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历史意识的丧失。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凸显“形式化”的特征。形式化倾向使经济学家逐渐远离社会现实,他们倾向于只重视分析技术,而忽略其假设的现实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也习染了这种形式主义的传统。一些经济学家满足于在狭窄的领域做“专家”,以适应经济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要求。但是,“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萨义德语),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淹没了。
就饥饿和饥荒的研究而言,中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真切的现实素材,但奇怪的是,专门从事这一研究并有建树的中国学者少之又少。在有关二十世纪那场旷古至今的大饥荒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出几份出自大陆经济学家之手,哪怕是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系统记录。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中,有关那场饥荒的记忆逐渐淡去,人们有意不再提它,好让它尽快成为过去,永远不再出现。但是,这种有意遮蔽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不对造成饥荒的原因做深刻的学理研究,我们就找不到防范的措施,饥荒就随时可能再次袭来。因此,无论如何,“忘却”不是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的有效办法。
相比之下,身居主流经济学大本营的阿玛蒂亚·森,却一直秉怀历史意识,顽强地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森后来回忆道,自己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投入福利经济学,与他童年的饥饿经历有关。一九四三年,森九岁的时候,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在饥荒中死去。森亲眼目睹了饥荒所造的惨状,“成群结队的人在寻找粮食”,“数千饥饿的乞丐充斥街头”,“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未被处理的死尸”……(《贫困与饥荒》,74页)。后来他负笈英伦学习经济学,但经济学中那些华丽的模型似乎冲不淡他儿时饥饿的记忆,他决定研究饥饿和贫困。当时,他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告诫他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那些“道德垃圾”,但森的道德情怀还是促使他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方向前行,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做出了多项关键性的贡献,这些问题包括福利的定义与社会选择、贫困的度量与收入分配、饥民的救助和权利促进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人类应对饥饿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
在研究视野和理论的解释力方面,阿玛蒂亚·森同样让中国同行感到羞愧。研究饥饿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七九八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传统的研究视角则侧重于食物的供应方面,通常只考察食物总量和人均食物量等指标,因此,饥荒通常被认为是粮食供给下降(即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引起的。这样一来,饥饿就常常被归咎于“自然灾害”,提高粮食产量和发展农业就成了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政策主张。
但是,阿玛蒂亚·森发现,在二十世纪,印度、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国在人均可得食物大量增长时期,饥荒还是无情地发生了。并且,在饥荒蔓延的时期,不少受灾国家和地区还在出口粮食。许多人竟然在盛满粮食的仓库旁被饿死!这些发现让他确信,FAD派观点对饥饿的解释存在误导,“它不能告诉我们在粮食供给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饥饿为何发生;也不能告诉我们即使伴随着粮食供给减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人啼饥号寒,而另一些人却脑满肠肥”。一些人挨饿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控制了现有的粮食?通过对这些问题连续性追问,他们形成了一种更有一般性、也更具解释力的方法——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这是一种透过经济现象,深入到社会、政治和法律层面去探究饥饿原因的方法。
与传统的FAD方法比较,权利方法在饥饿原因的分析方面远为深刻,提出的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的措施也更为根本。
在造成饥饿的原因分析上,权利方法实际上做了两个方面的跨越:一是从强调食物供给转为强调食物权利;二是进一步从强调食物权利过渡到强调非食物权利。
“对饥饿者来说,食物总量是一个太过遥远的变量”(《贫困与饥荒》,154页)。因此,一个人是否挨饿不是由这个国家(地区)的食物总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个人所控制的食物数量决定的,而他能控制的食物数量是由他能够利用的获取食物的渠道以及他可选择的商品束的集合决定的,即他在控制食物方面的权利决定的。一个人对食物所能实施的控制权利又是由一系列法律和经济因素决定的,即使在食物总量和人均食物量大量增长的条件下,那些失去食物控制权的人群仍然会成为“饥民”。基于这种发现,作者将饥饿归结于“权利的丧失”,是一个人“失去了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的权利的结果”。因此,从其本性上说,饥饿是“权利的失败”,它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饥饿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因此,权利方法重视的是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这种权利是由他初始的财产禀赋和他能够利用的贸易机会决定的。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一个人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失去控制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能力。例如,“权利的丧失”可能由于他的禀赋下降(如土地的转让,或因不健康而失去劳动能力),也可能因为他在“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上发生了不利变化(失业、工资的下降、食物价格的上涨、他所出售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下跌等)。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一般来说,食物供给的减少,会通过价格上涨,对一个人交换权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使他面临饥饿的威胁。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
但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完全可以是食物供给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商人的勾结行为会妨碍食物从低价地区向高价地区的预期流动。商人的共同利益常常导致对市场的分割,并且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希望通过限制贸易来阻止遭受饥荒地区价格的缓和”(《饥饿与公共行为》,96页)。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仅有食物权利还不足以消除饥饿引起的人口死亡。因为,“即使在饥荒时,绝大部分死去的人都是被各种疾病杀死的,而非直接被饿死”。因此,要消除饥饿带来的生病与死亡,只关注获取食物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保全性命不仅依赖于直接的食物供给,更依赖于对疾病的有效预防,而后者依赖于每个人从非食物事项——如医疗照顾、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设施、纯净水的供应、传染病的控制等方面获得的服务。正是这些非食物权利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生活质量的分布。例如,斯里兰卡和不丹人均卡路里的消费值相差无几(分别为2385和2572),但两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却相差悬殊,前者为七十岁,后者仅有四十四岁。作者将这种差别归结为国民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的不公平分配。在斯里兰卡,93%的人口可以获得公共卫生服务,而不丹的这一数字只有19%(《饥饿与公共行为》,186页)。
在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方面,权利方法提出了更为根本也更值得期待的措施:权利保障和权利促进。措施的有效性与原因分析的准确性直接相关。由于将饥饿视为权利的丧失,也就指明了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的方法。这种方法促使我们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保障或促进公民权利的方式,包括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法律框架的改革。
权利保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弱势群体不致面临支配食物及其他必需品能力的崩溃。可能的威胁不仅来自生产的失败,而且也来自获取基本必需品的机会的恶化(由于失业或贸易条件的恶化)。这里必须着重关注那些挣扎在饥饿边缘人群的经济状况,因为轻微的市场波动就足以将他们推向饥饿的深渊。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为失业者、老年人和赤贫者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可以让他们避免因丧失食物权利而失去生命。
但是,比较而言,权利促进更为根本。它不仅要求扩展人们通过就业与生产来获得的生存手段(食物),通过普遍增加收入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要求扩大某些关键性的非食物投入——如卫生保健、基础教育、干净的饮用水或公共卫生设施等。
在广义上,预防饥饿依赖于非食物权利的促进。因为一个人食物权利(即人们对食物的支配)的实现其实高度依赖于非食物权利。一个人要过健康的生活,不仅需要食物,而且需要卫生保健与医疗护理。因为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寄生虫和其他疾病对健康的损害是致命的。此外,基础教育对消除营养不良以及预防发病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在饥饿的境况下,需要关注的是人们过营养充分的生活能力,而不是他们食物摄取的数量。”(《饥饿与公共行为》,269页)如果有关营养和健康的信息缺乏,就会削弱人们从某一食物和卫生保健权利中所获取的能力。而教育不仅有助于人们在更多知识的指导下去购买食物与药品,而且广泛的基础教育还能引导他们更好地利用公共卫生服务,并能产生更有效地提供这类服务的政治要求。再者,受过教育的民众更容易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中——部分通过有报酬的就业而扩大——从而使发展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食品供给与非食品供应所依赖的机制是不同的。一般地说,食物可以在市场上购得(即使受到津贴、定量配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食物供给较多地依赖市场机制。但在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卫生服务和控制传染病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加直接和迅速,因此,在教育、医疗以及相关设施等方面,更经常地——以更好的理由——须由国家来提供。如果说“市场失灵”有可能使民众失去食物权利,那么“政府失灵”则必然使数量众多的民众丧失非食物权利。因此,饥饿实际上是由于“公共行为”的失调造成的。
但阿玛蒂亚·森强调指出,这里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国家为公众做了什么,而且包括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后者不仅包括社会机构所做的直接有益的贡献,还包括压力集团和政治活动家的行为。在治理饥饿的公共行为中,公众不应仅仅视为被关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种“动因”,是一种能改变社会的力量。从对“公共行为”的这一理解中,我们可以导出权利方法所蕴含的道德意义。饥饿的生理感受是个体性的,但权利的本质却是社会性的。因此,一个人挨饿表面上是他可支配食物的缺乏,但造成这一缺乏的原因则是社会(公众)剥夺了这个人的食物权利。借助于权利的范畴,阿玛蒂亚·森将社会中所有机构和个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个人挨饿表明他权利的丧失,但在保障这个人权利的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可能由于行为不当而促成了这一局面,因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挨饿,所有人都要在道德法庭上接受拷问。
《贫困与饥荒》,阿玛蒂亚·森著,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19.00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版,35.00元。
来源:《读书》2009年第6期。
社会企业与竞争逻辑难题:
公平贸易和社会责任投资行业中的利润与亲社会使命
Curtis Child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摘要
近几十年,我们见证了积极追求社会与经济目标双赢的社会企业的不断壮大与发展。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提出如下问题:这些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同时兼顾亲社会与利润追求双重目标?它们又是怎样(以及更好地)践行亲社会义务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属于社会企业研究的前沿课题,同时也涉及到组织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内的研究主题。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对两个行业的调查——公平贸易行业和社会责任投资行业。我与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平贸易从业人员进行了66次会谈,邀请了来自48个商业领域的专家,同时对行业会议进行了观察和非正式访谈,以使得调查更富有成效。
关于社会企业,我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其一,从业人员们经常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谈论社会企业,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有疑问的事情。我认为,他们持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这个论述已经内在的设计出解决社会企业的固有矛盾以及为一系列相关企业活动辩护的内容。其二,我认为市场力量中有两个主要的“支柱”在迫使着企业对它们的社会责任给予充足的关注。这些支柱来源于正规形式,我称之为情感控制。行业组织在情感控制的依赖程度上的差异,已经在塑造它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方式上产生了作用。从理论上讲,这项研究比组织社会学更胜一筹,后者探讨制度逻辑是否具有竞争性和亲和性,而此调查关注的是结论和表象的依存关系。在公平贸易和社会责任投资行业中,与组织实践相冲突的制度逻辑在本文的论述中变得更加缓和。本文还通过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化工程给予关注,即通过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去商品化的社会行动者,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学术发展。本文不仅仅要强调它们之间可能潜藏的矛盾,也要探讨它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引言
近几十年来,积极追求市场导向与亲社会目标双赢的企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常规现象。先前的观点认为,以直接而明确的方式同时创造社会与经济价值是可行的。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非营利性企业,遵循双方或三方底线原则运行的商业组织,以及创造性的将营利与非营利模式融为一体的替代性企业,都属于“社会企业”的范畴。实例不胜枚举——小额信贷机构、公平贸易组织、社会责任投资公司、非营利性企业以及社会公益性企业——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都有一个组织管理层、追逐利润的资本动力以及增进人类发展的慈善兴趣。实际上,正是这些核心的特征——这些看起来似乎具有逻辑矛盾的理念可以相互兼容——使得亲社会的、追逐利益的公司或以市场为导向的慈善机构看起来荒谬却极具吸引力。鉴于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对它们的认识也是肤浅而片面的,这一矛盾并不足为奇。对此论题感兴趣的学者们在评估该项研究时缺乏证据支持和理论见识。
本文从两个主要问题的提出入手来阐明关于社会企业的学术观点:
1.企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兼顾亲社会与利润追求双重目标?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存在吗?或者说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目标吗?
2.如果亲社会与利润追求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存在,社会企业又是如何实现的?参照营利性企业所面临的巨大市场压力,这些社会企业又是如何(以及更好地)维持它们的亲社会义务的?
下面的章节通过对公平贸易和社会责任投资行业展开分析来回答以上问题。本论文在处理大量调查案例中有所获益,并涉及到了两个更为泛化的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1.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是如何变得彼此兼容的?
2.这些社会化工程——即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反商品化的社会行动者而做的努力——如果将他们定位于市场部门又会如何?所做的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一点,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从宏观上描述发展趋势(如Cooney and Shanks,2010),为社会企业的扩展做辩护(如Yunus,2008;Yunus and Weber,2010),以及考虑其法律后果(如Taylor,2010)。上述问题将社会企业视为一种注定(或可能无法)要完成的、潜在的问题追求,从而使社会企业问题复杂化了。阐明为什么它是有问题的,它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的,都是该项目的核心和实质目标。
从理论上讲,这些问题(以及随后的解答)都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的一些实例特别地受到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关注。虽然在上面我已经大致阐明了本文的中心主题,但是我的研究是如何与这些学科相联系的将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探讨。然后,我将简要介绍公平贸易和社会责任投资,并简要概述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论。
结论
本论文旨在探讨社会企业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同时达致利润中心与亲社会双重目标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社会企业的案例来探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经济社会学中更为广泛的话题。以上的章节都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文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对公平贸易从业人员以及社会责任投资专家的访谈,同时也参考了观察数据和间接的历史资料。在结论部分,我回顾了引言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并结合先前的分析来总结关于这四个问题的答案。
·企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兼顾亲社会与利润追求双重目标?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存在吗?或者说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目标吗?
资本主义和慈善事业分别代表着一种差异性的制度逻辑——自利性的利润资本积累(Swedberg,2005)与人类关怀的导向(Payton and Moody,2008)。历史上,慈善事业、资本主义实践与制度之间曾以一种复杂的,经常矛盾性的状态共存。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冲突:如果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对利润的合理化,以及自利性需求(Jones,1986;Kinsley,2008;Swedberg,2005),那么慈善事业会被定义为经济非理性的,以及对社会利益的自我否定性追求(Payton和Moody,2008;cf. Ilchman、Katz和Queen,1998)。对待两种传统的双重化态度已经在当前经济时代中的社会和合法组织中广泛的体现出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部门——这一点从根本上塑造着组织行为,这一组织行为对于在美国文化历史上盛行的慈善事业与资本主义二分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对这些影响深远的传统进行研究之外,本文在探讨社会企业时,试图将专属于慈善事业的亲社会目标与主要和资本主义相关联的利润目标相融合。同时,根据社会企业的从业者所言,他们并不质疑社会企业自身所做的努力。毫无疑问,开创一项成功的事业,保持强盛的竞争力,管理好复杂的供货链条,以及吸引一个固定规模的消费者群体,可能是极富挑战性的。但是这些难题当然并不仅仅专属于社会企业。尽管通过运用历史和法律上认为二者相悖的二分法对其相互矛盾的目标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但在被调查者中,很少有人宣称社会企业是先天不足、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吃惊。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亲社会与利润追求两个目标是相悖的,社会企业又是如何实现的?参照营利性企业所面临的巨大市场压力,这些社会企业又是如何(以及更好地)维持它们的亲社会义务的?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尽管我们研究的组织都受到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并且在第二章中讨论的话语资源可能使得从业人员以一种辩护的方式去维护市场,社会企业仍旧做出了与其经济利益相左的决定。尽管其他导向的行为有时会营造一种市场优势,并被认为对商业有所裨益,一些决定仍旧在经济利益不明确或不存在时做出。
·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是如何变得彼此兼容的?
在引言中,我已经指出,本研究不仅仅描述了社会企业案例,而且也探讨了可广泛应用于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中相关主题的社会企业案例。探讨不同的制度逻辑如何相兼容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一。参照组织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我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两种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的产物。在这一界定中,制度逻辑被定义为引导和推动行为的特定信念与假设体系(Scott,2004)。它们提供了个人和组织可以依靠的理所当然的规则和意义,同时它们也成为过去三十年来受学术界相当多关注的对象。
我认为,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找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观点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观点有时被相同的作者或者持相同理论观点的学者采纳。一方面,学者将制度逻辑定性为一种可以被战略企业家创造性运用的资源。这是一种强调制度逻辑灵活性的观点。比如Binder(2007)注意到,在现实环境中的带着过去间接经验的人们把他们和来自其他领域的制度逻辑相结合,从中选取对他们有用的部分来满足他们的需求。Thornton(2005)写道,“制度化的企业家关注的是一个部门和实验中的文化元素模块怎样以一种混合的方式进行分解与重组”。Kraatz和Block(2008)尽管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也宣称他们“找不到能断定一个组织不能实现大众需求,体现大众价值(或者逻辑)以及成功地获得源自制度性的大众认同的理由”。
·这些社会化工程——即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反商品化的社会行动者而做的努力——如果将他们定位于市场部门又会如何?所做的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方案也涉及到了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相关主题。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论著中找到三个相关的观点:(1)经济和社会是紧密交织的(Granovetter,1985;Granovetter和Swedberg,2001);(2)两种行为:脱离社会生活的经济活动(在经济社会学家的案例中)或允许市场资本轻视个人的价值和人际关系,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Marx和Engels,1978;Polanyi,2001);(3)嵌入的经济行为(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下)或者将去商品化再次嵌入商品化了的社会关系中,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简而言之,这些文献可以看作是,对忽视社会因素而导致一个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呈现的负面的社会后果进行学术探讨的努力。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现实的问题。当人们将社会问题完全降罪于资本主义制度时,学者们也不会坐视不管。学者们记录了主要来自于市民社会的以反压力形式存在的对国家行动者的抵制。
社会企业在尝试解决资本主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方面的独到之处在于,这些努力是在市场部门中进行的。对于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而言,他们没有从典型意义上去阐述嵌入式经济行为,即传统的商业活动是由包含着个人关系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与此相反,这些组织的建立可以将社会意义嵌入它们的支持者所认为的传统的、商业化的或者社会剥夺性的行为模式中。对社会企业和纯营利性企业而言,将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和意义紧密结合并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未来,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建立在将这些结论置于新的背景或结合不同的方法的基础上。关于对情感控制后果的学术研究,进一步的工作可能会通过加强组织层面的对比而大有进展。鉴于第四章中所阐述的原因,本研究方案主要依靠于产业对比,从组织层面收集的有效数据也会对研究有所裨益。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纳我上面提出的观点(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并做进一步的仔细研究。寻找有争议的案例恐怕是一条简单的研究路径,比如情感控制很强但是我所界定的促进因素并不存在,或者相反,实现条件存在但情感控制并不存在(或微弱)的案例。同时要研究那些有助于我们能对情感控制如何生效进行更加精确论述的案例。
在案例研究之外,通过对咖啡贸易进口商进行访谈调查,或许也可以进一步验证这些观点。把每英镑咖啡价格作为因变量,然后控制对咖啡价格影响大的咖啡质量及其它因素,我们可能会认为上文所探讨的高层次的组织——诸如这些经常与农民接触并作出情感回应的组织——更有可能会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咖啡。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会以一种比市场需求更为慷慨的方式对待农民。此外,一直关注一个或若干进口商如何从传统的进口方式转换为公平贸易,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正如刚才所描述的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公平贸易环境中的进口商的经验是如何区别于传统渠道中的进口商的,以及这些不同的经验是否能转换为不同的组织实践活动。最后,比较中央银行与地方银行(或者信用社)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以及理解与社会责任投资相近的企业是如何有机运转的,都是非常有趣的。基于以上的观点,有人可能会认为,相比于与任何一个社区不存在紧密利益的中央银行而言,地方银行会以更为积极,热情的态度服务于客户。
对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亲社会工程的进一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研究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对其感兴趣的学者是否有一个能客观理性的评估其发展的学术组织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社会企业的论著都是有所增益的,也是丰厚的。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有其地位和价值。但是,在试图了解社会工程如何运行以及它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否正当时上,学者即便不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辨别力也是必要的。
论著信息:Curtis Child,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 problem of competing logics:Profits and prosocial missions in the fair trad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industries,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2011.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华中师范大学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何晓军 王小林
本期编译: 李海金
责任编辑: 张德亮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84419641
传真:010-84419658
电子邮箱:zhangdeliang@iprcc.org.cn
网址:www.iprcc.org.cn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
地址:北京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86-10-84419655 传真:+86-10-84419658(电子地图)
版权所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京ICP备202003919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