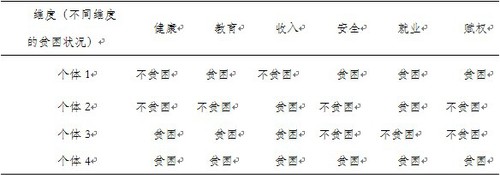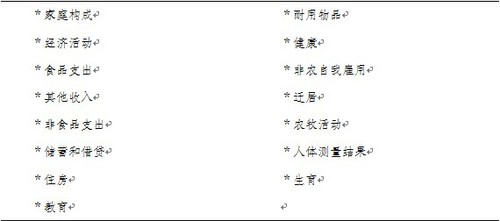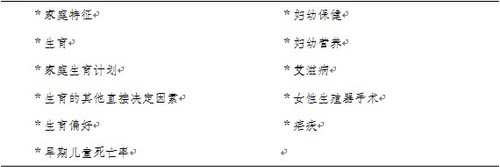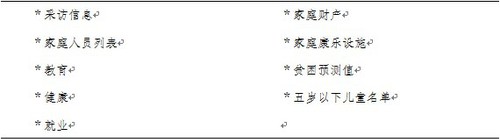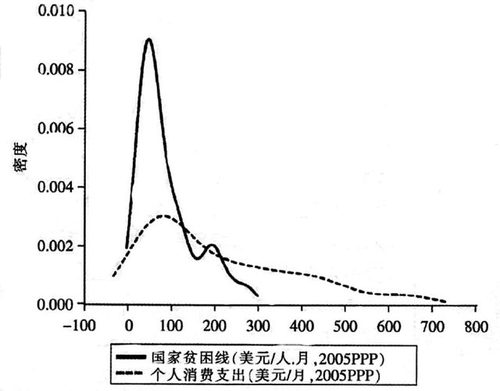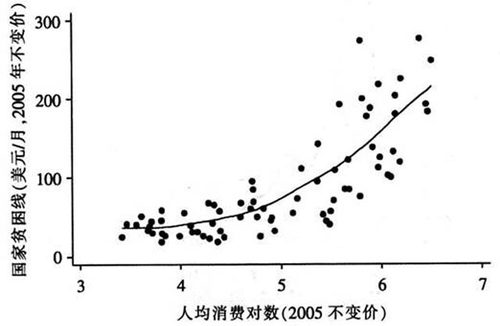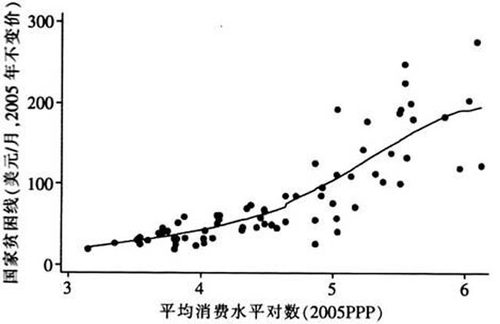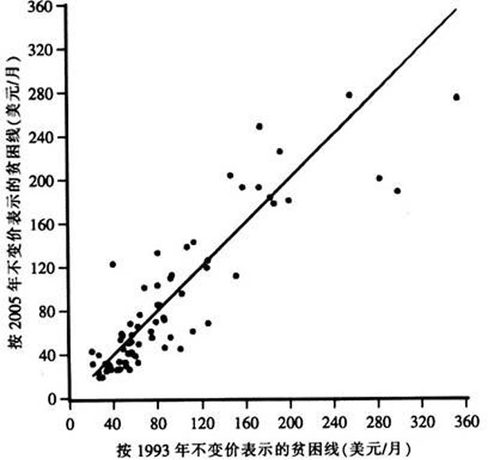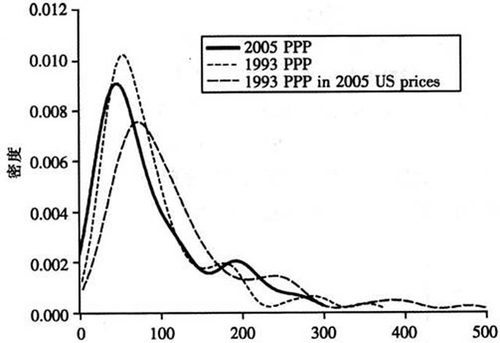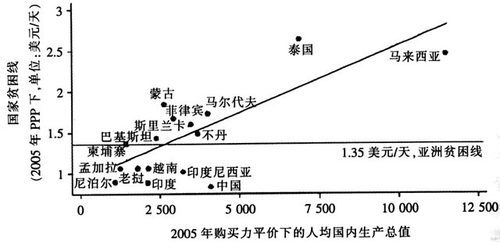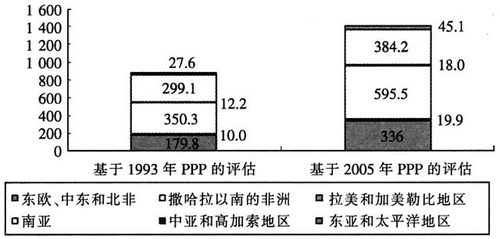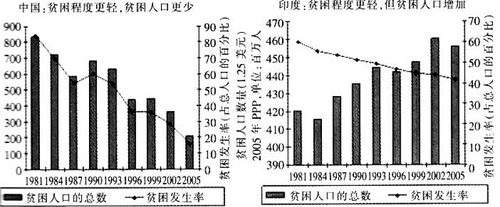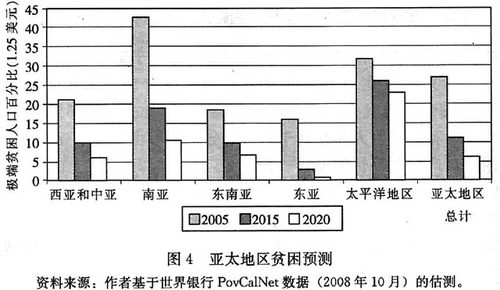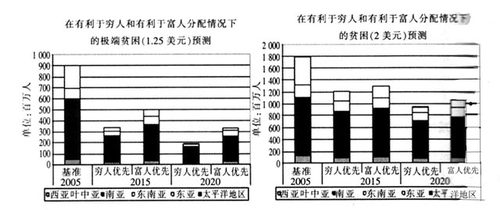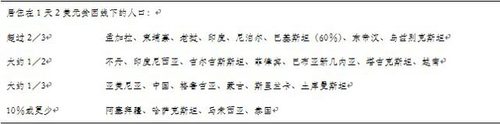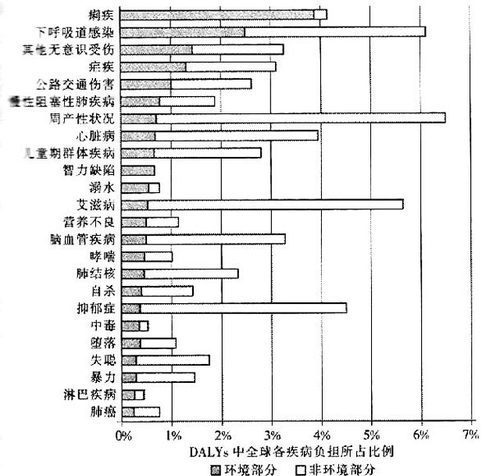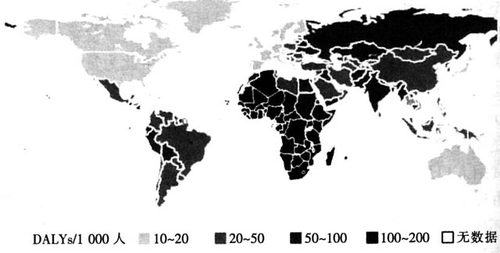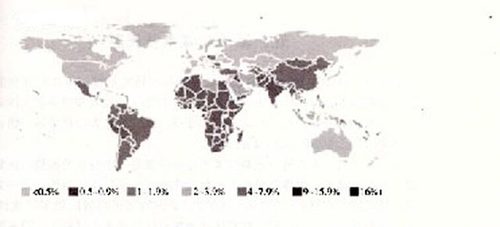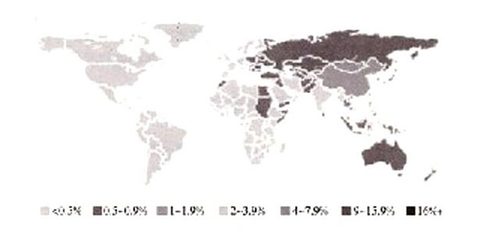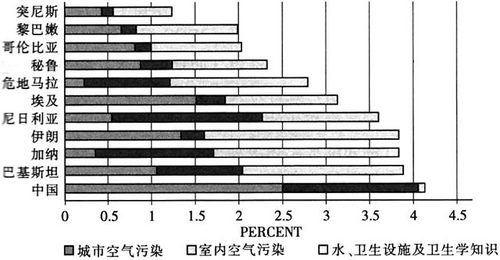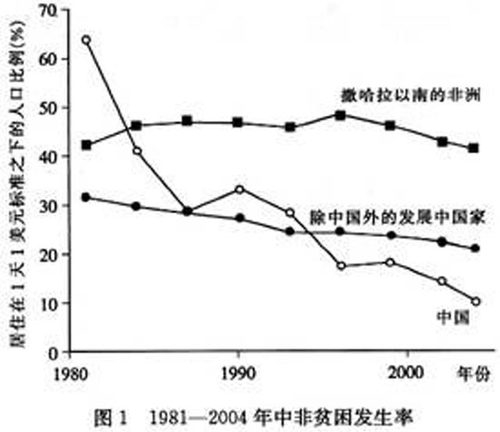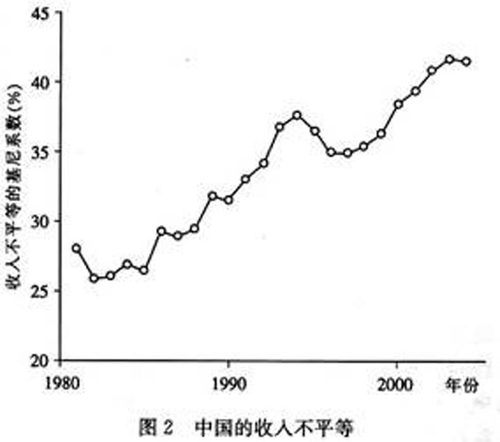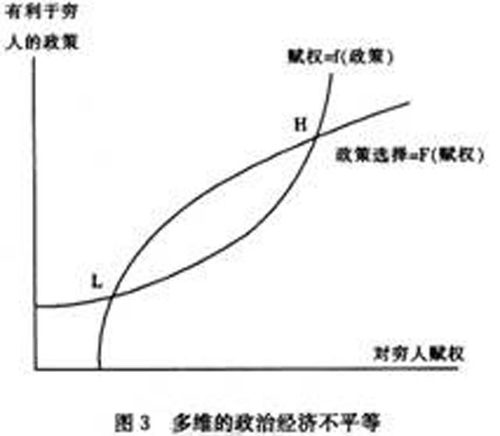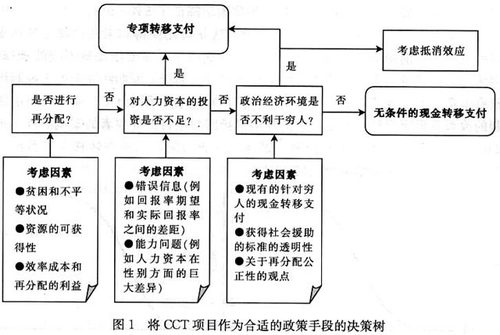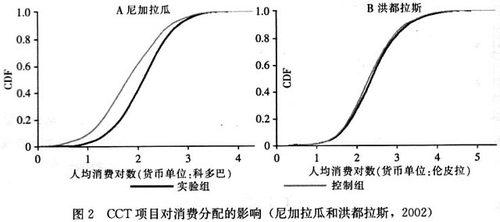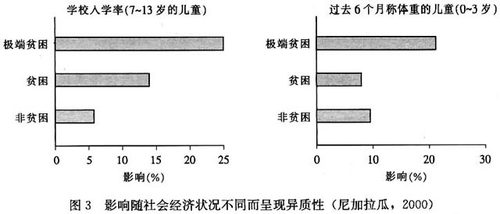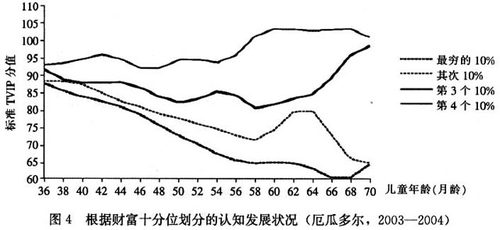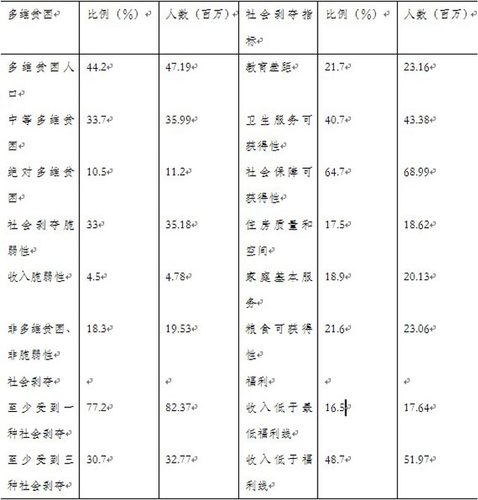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0
第一部分
贫困理论和贫困测量
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
(Sabina Alkire&Moizza Binat Sarwar,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
一、 引言
本文研究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及国际机构广泛关注并逐步采用的贫困和福利多维测量方法,指出了多维测量贫困仍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并描述了不同政策环境下的测量方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减贫成为全球共同的任务,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出现了使用主流的多维测量贫困和福利的方法的高潮。不仅在学术文献中出现这种趋势,在政策领域,关注多维贫困测量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尤以萨科奇委员会下辖的生活质量小组——经济业绩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CMEPSP)为代表。经合组织的社会项目测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关注项目测量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机构、智囊团、学术团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这种关注证明含义更加广泛的人类进步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具吸引力。在国际机构中,世界银行自1997年以来就已将贫困视为多元现象,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已开始磋商2010年报告反思人类的发展,将以多维测量方法补充人类发展指数(HDI)。
发展多维框架的推力来自于各个方面,这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稳定性。Sen、Fogel和其他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对广泛的需求给出了一个规范性的解释,然而Inglehart、Kahnemann、Layard和其他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基于收入的发展缺乏满意度。同时,实证研究已经把基于收入的测量方法应用范围和限制进行了分类,也指出人类行为偏好基本假设方面的缺陷。实际上,相关数据来源有了很大扩展,计算机设备的改进为更好地进行多维分析提供了条件。就政策空间而言,2000年发起的千年发展目标关注到的人类苦难和成就的8个方面已成为许多国家正在进行运动的基础。2009年9月15日以后,国家和国际领域关注贫困和福利多维测量方法将增多,因为经济衰退期或许提供一个关注福利测量的政治刺激。
不管各种行为出于何种动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在实施贫困和福利多维测量方法时,任何行为都将面临下列相似的问题和困难:选择分析单位;选择分析顺序;选择维度;选择维度的变量/指标;选择指标的终止点;选择指标的权重;若每个维度多于一个指标,则聚类;选择跨维度权重;选择方法;集合方法-跨维度,并尽可能在统一维度内;不平等或分配权重的合并。
传统贫困或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通常是基于家庭净货币收入或者家庭消费。对贫困而言,如果他们的收入低于贫困线,传统的方法将定义这个人为贫困。贫困线可以是主观的、客观的、或者混合的。一个国家贫困线确定方法通常有:食物、消费篮,或平均数的百分比,或总收入分配的中位数。除了收入以外,其他对贫困的货币测量方法包括消费支出和储蓄。也就是说,传统的测量方法根据人们的总收入或总消费考虑个人或国家的生活质量。
多维度的方法是从传统的单维度方法中脱离出来,这种方法反对一维测量。使用单一指标的困难包括人们对收人多大程度上转变成效用的争论:收入转换成效用时人和环境的异质性,公共部门的作用和贡献,政治的局限性和市场不完善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重点关注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应把社会福利的范围扩展到经济之外。
20世纪60年代,欧洲出现了发展社会指标的运动,从衡量收入的平均值转为衡量经济活动的结果。阿特金森等人(2002)把欧洲成员国最常用的社会指标按照金融、教育、就业、卫生、社会参与和住房等7个维度进行分类。欧盟委员会的工作加强了向社会指标发展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国际组织为社会指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关于方法和结果的辩论中,阿玛蒂亚森(1992,1996,1999)的能力方法论占据了主导地位。森提出,人类的福祉应该通过直接观察人的能力,人们能做什么和做成什么进行衡量,这些构成发展的结果。这种人们内在价值被定义为自由。因此,他们不能被外部的力量强加。能力方法是一种多维度的测量贫困和社会福利的方法,该方法不仅描述经济和社会部门引起的贫困和生活社会变化,而且全面描绘了人们自由价值享有和缺乏的状况。虽然森的能力方法关注发展的结果,但是人们也非常关心识别方法的效率问题。森(1999)已确定五个有关自由衡量的工具,都与经济发展成就紧密相关:政治自由,经济设施,社会机会,透明性和安全性。能力方法在关注人类发展结果方面极具吸引力,并且是开放和灵活的,包括社会福利方面测量维度,如何选择,每个维度相对权重,识别贫困的最终截断点。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其他机构被鼓励制定多方面的措施,以适应其特定的目的和能力。通过研究不同国家发展的多维测量方法的案例,本文将探讨取得一致性的重要问题,以及仍待解决的多维测量的关键问题。
二、 贫困多维测量的发展简史
本节将评述过去实施的多维方法的类型,并指出实践中主要面临的挑战。
本节讨论的方法多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并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主要讨论以下5个指标:
1.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用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该指标通过三个统计数字的均值合成而得(基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这些统计数字在0~100的范围内加权而得。
2. 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用于对国家排名。该指数作为三个领域[平均寿命(健康)、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教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的加权组合来测量生活质量。
3. 基本需求方式(BNA)。基本需求方式扩大了衡量贫困的需求,但是这种方法没有说明如何选择及如何赋权。
4. 农村综合发展(IRD)。这种方法关注中小规模农户,目的是通过实施一整套的干预措施使他们超越生存农业。
5. 综合发展项目/计划。综合发展项目主要是一个基于区域的方法,该方法被实施到分散决策——为了减少贫困按照当地水平制定决策和支出。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是由Morris在1979年提出的,包括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这种方法把复合指数的指标赋予同等权重,它假设定义中的指标在是同等重要的。
物质生活指数在概念和方法上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人们的福利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它们不能在道义上和逻辑上互换,所以,不能用单一指标衡量。物质生活指数也因为它的有限测量维度而受批评,它过分强调健康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指标使用的巨大障碍是获取非收入所得的数据,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比较。
人类发展指数(HDI)
最有名的贫困多维测量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1990年,UNDP在发布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时介绍了HDI,HDI提供了从社会福利到经济指标国家层面的数据,指标由三个维度组成: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指标也是等权重,HDI被认为是能力和贫困基本需求的早期代表。因参与式发展强调地方人员参与项目的整个过程,也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资金,这种简略多层面的举措必然是不完整的。
多维方法的发展历史出现了很多社区发展和参与方式的重要概念: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性别平等、女权、小额信贷、社会保护和安全网等,表明经历了多种发展方式,测量方法已经有意识地聚集到多维测量。
三、 案例研究
本部分介绍了7个国家案例,这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在近期采用了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方法。本节将介绍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对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方法,在关键领域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在设计和执行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时的普遍矛盾,以及在测量中还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案例的选择有两个标准,即(1)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从而能全面地反映多维测量方法在不同经济实力的国家的设计、实施和执行情况;(2)多维测量方法处于不同发展和利用阶段的国家,以展现过去或现在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推进贫困的多维测量。
每个案例研究的结构如下:首先,对多维贫困衡量的历史进行简单介绍,重点是强调各个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指示和行动。然后,对已经开始实施的多维测量的细节进行讨论,当前刚开始制定测量方法的案例则不予讨论。测量维度和指标的细节,实施方法和结果的运用,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
墨西哥
2000年,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所有由联邦执行部管理的项目都需要年度评估,从而保证公共项目的负责性。2001年,规划和社会评价部被任命执行这一目标。同年,规划和社会评价部成立了“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这一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定该国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根据他们的方法,2002年规划和社会评价部第一次公布了对2000年贫困的官方测量,该测量方法建立在三个贫困概念上:食物贫困、能力贫困和财产贫困,使用非等量化收入,把家庭作为调查单位,把支出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以此方法为基础,2002、2004、2005、2006年的改进方法也被公布。2006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社会发展总法》,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系统来设计、监督和监测社会政策和项目。2006年,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成立,理事会有两个主要任务:(1)评估社会政策和项目;(2)衡量全国、州、市的多维贫困状况。根据第36条条令,社会评价规划部有权利和义务制定一个标准从多角度定义、识别和衡量贫困。在联邦和州一级,贫困测量至少两年评价一次,在市一级至少5年评价一次。
新的法律层面多维贫困衡量必须包括收入贫困,以及其他七个方面,其中一些是社会权利: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服务,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2007年和2008年,墨西哥政府委托了国内和国际的专家对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进行了改进。
菲律宾
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政府把消除贫困作为社会改革议程的一部分,采取步骤监测和追踪贫困。因为搜集资料的困难和财政资金的限制,于是诞生了基于社区的系统,该项目收集了最小单位的14个核心地方贫困指标。执行社区监测系统的费用全部由地方政府资助,2005年,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开始对社区监测系统作出一些贡献,当地人民自己收集和处理数据。社区系统以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监督者,可灵活纳入地方治理的具体指标。贫困测量的核心指标有以下8个维度:健康、营养、住房、水和卫生、基础教育、收入、就业、和平与秩序。地方政府机构可以增加其他指标或使用代理指标,以监测地区的具体问题。核心指标主要如下:
(1)O~5岁儿童死亡率。
(2)孕妇死亡率。
(3)0~5岁儿童营养不良率。
(4)住在临时房的家庭比率。
(5)居住寮屋的居民比率。
(6)没有安全饮水的家庭所占比率。
(7)没有卫生厕所的家庭比率。
(8) 6~12岁儿童小学失学率。
(9) 13~16岁少年中学失学率。
(10)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比率。
(11)收入低于生存线的家庭比率。
(12)粮食短缺的家庭比率。
(13)失业人口比率。
(14)犯罪受害者的人口比率。
印度
印度有两个贫困测量的相关活动:一是识别贫困家庭,为了瞄准政府服务;另一个和2008年8月新宣布的“多维贫困指标”相关。自1992年以来,—个识别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活动每5年进行一次,由州政府和地区管理者负责,目的是识别和瞄准在各部委各种项目下的贫困家庭。1977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全国范围的人均消费贫困线,农村人均消费2400千卡的热量,达不到这个消费的人称为贫困人口。1992年,开始收集全印度的收入数据来制定收入贫困线,这个贫困线对于农村太高了。更重要的是,1997年使用了支出和多重标准的贫困线代替了单一的收入贫困线,批评家认为这种方法太严格了。而且,贫困线标准在全国不统一,各州之间很难比较。最终,在5年之内都没有任何可行措施将新的家庭添加到贫困线下的名单中。
第十届贫困线调查组为了改进识别贫困的方法,组建了由行政人员、学者、各邦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专家小组提出了若干建议改善贫困线,并指导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最终,印度在2002年以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取代了收入贫困测量方法。
识别印度农村贫困家庭,主要调查13个方面的贫困信息:
Ql:你有多少土地?
Q2:你的住房结构?
Q3:你有多少衣服?
Q4:你每天吃多少食物?
Q5:去浴室的便利性
Q6:自产的消费品
Q7:家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
Q8:在家庭中的劳动地位
Q9:生活状况
Ql0:家庭中小孩的状况(上学或工作)
Q11:你借了什么类型的贷款?
Q12:家庭迁移
Q13:你想从政府得到什么帮助?
这些问题有5类答案,13个问题同等重要,得分0~4,最大得52分,通过总分来确定家庭是否贫困,贫困家庭能得到一个“贫困家庭”卡,政府给予他们一些免费服务。
这次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受到怀疑。2008年8月,在印度第二次多维贫困测量的倡议下,计划委员会主席Ahlewalia宣布将对普查数据进行补充,建立一个贫困线补充参照指标。
不丹
1972年,不丹宣布打算衡量国民幸福总值,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幸福的概念基于四大方面:(1)促进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2)保护和提升文化价值;(3)保护自然环境;(4)促进善政。2008年,全国范围的国民幸福总值的数据调查工作开始。
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由不丹研究中心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合作设计,2008年11月26日公布。构造的国民幸福总值包括72个指标,9个方面的内容。每个指标都设置一个“有效”线,和贫困线类似,能区分哪些人已经得到了幸福,哪些人没有。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是对12个地区560个受访者调查的基础上设计的,不能全面反映全国水平。在今后几年中,该指标可能要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指数在某些领域的准确性,但9个方面将保持不变。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政府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提高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在过去,玻利维亚用收入,以及多方面的方法衡量基本需求。
衡量基本需求有以下四个阶段:
1. 评估家庭的基本需求:住房,基本服务,教育水平和健康服务。
2. 制定基本需要时把每一个变量标准降到最低。
3. 每个级别都有一个评估值,根据其距离平均值和缺口指数计算每个变量。
4. 用简单的权重计算四个标准的总得分,从而得出整体基本需求指数。
“过上幸福生活”用于贫困测量的目的不同于人类发展指数,它包括了遭受贫困人口的世界观。玻利维亚政府正在研究调查问题,并借此制定一些与过上幸福生活有关的政策。这项工作的基础在于玻利维亚的贫困数据以及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补充指标,这些都将汇总到福斯特多维贫困衡量中。多维衡量指标弥补了遗漏指标,还将有助于引出贫困地区用货币无法衡量的价值信息。
英国和南非
英国和南非的案例在贫困模式方面具有相似性,该模式如下:
贫困具有多重性,体现为多种剥夺的模式,不同剥夺维度具有不同的可识为缺乏数据,HDI对人类福利的概念定义过窄。有人批评这个指标没有关注政治和文明、不平等、权利等,还有数据获得和国家比较方面的缺陷。
相关的多维测量是人类贫困指标,该指标包括三个维度:寿命、知识、体面的生活。利用综合数据,生活水平的指标是把不能使用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卫生服务,以及中度或重度体重不足的5岁以下儿童加总,然后再除以指标数。
基本需求方式(BNA)
基本需求方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大背景下,货币增长——经济和收入伴随着涓流效应带来了人类福利的提升。基本需求方式促进了瞄准人类基本需求的政策出台。在基础层次,基本需求方式包括最小物质需求满意度,如食物消费、住房、公共交通、健康、教育等。对基本需求方式的批评主要是概念性的:
·基本需求难以量化,改进收入不平等和减少储蓄在贸易上都是无效的。
·BNA把人类本性、全球变化、发展的线性模式都纳入了基本假设。
·一些BNA过于关注资源和输入,忽略了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
·不能清晰地看出基本需求方式如何包括参与和自由。
农村综合发展
农村综合发展指标由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捐赠者的增多在70年代开始流行。农村综合指标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强调地方参与和社区所有,经济增长不必直接受益穷人,它和发展的目标有不同之处,但也有关联。
农村综合发展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是规模是其成功的障碍。世界各地农村综合发展的主要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美国国际发展署,2005):
·农村综合发展往往变成供给驱动型。
·农村发展项目为了提高效率,绕开政府机构,忽视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很少有互动、评估、训练和资本管理机构,一旦经营出现分歧,项目就无法继续。
·项目允许州政府干预整个过程,但避开了最主要的土地分配问题,从而使家长式关系出现阻碍活动的可持续性。
整体推进项目和参与式发展
整体推进项目和参与式发展都是发展中国家以地域为基础的主要发展模式,整体推进项目是南非政府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关键的减贫工具,现在仍在使用。
别和测量的方法,多重贫困是基于把可识别的贫困和可测量贫困相分离。经历过贫困的人对于这个地区的整体,可能在某些特殊角度增加了贫困程度。衡量贫困的不同剥夺方面,才能理解贫困的多重性。
英国
在英国,测量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地域差异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欧盟的“社会排斥”概念。2000年,英国逐步制定了多重贫困指标,作为反对社会排斥成果的一部分,一些资金资助计划开始瞄准英格兰最贫困的地方。2000年,美国政府制定了贫困指标,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进行了改进。目前,2007年贫困指标在小部分地区作为政府官方的多重贫困测量指标。使用普查数据和政府的数据去考察地区间贫困差异,从而提供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政府服务。该综合指标的指数包括经济、社会、住房问题。2007年的多重贫困指标是建立在小范围内的低产出地区。还有两个补充指标,影响儿童的收入剥夺和影响老人的收入剥夺,这些都是收入剥夺域的子集。
多重剥夺的模式是对2007年多重贫困模式的改进,多重贫困指标有7类37个不同的指标组成。不同区域加权后作为2007年的贫困指标,每个地区的指标都是既定的技术标准,这些指标是:为特定地区特定目的专门设置;衡量贫困的主要特征;最新的;定期更新;满意度稳健;在整个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可行。
南非
南非的国家统计局负责收集全国的官方统计数据。统计局的社会人口分析司负责分析全国和地方的贫困、社会趋势。南非统计局定期对住户进行调查,从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主要调查多维贫困的六个方面:教育、健康、工作或失业、由家庭承担的非酬劳旅行、住房和服务的可得性。南非的宪法要求财政资金要根据各省贫困状况公平地分配。
从2000年开始,南非统计局开始和国际组织共同进行贫困统计。2000年,南非统计局有两个识别指标:住房结构指标和居住环境指标。然而,他们没有具体阐明任何一个多重贫困模型,也没有给予服务可得性更大的权重。另外,因为调查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对小地方缺乏针对性。
不过,最近南非统计局联合南非社会政策分析中心和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对各省设计了指标,每个地区的相对贫困状况通过得分计算出来。省级多重贫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可分割的贫困测量基础上的,允许不同层面的贫困单独地测量,然后加总。贫困识别从5个方面:收入和物质上的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教育和生活贫困、环境贫困。
当前阶段,每个省级贫困指标提供了省级贫困的相对水平,但不能实现省间的相互比较。
四、 共同主题
从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出非货币的综合测量法正在兴起。本节将讨论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需要多维贫困测量,多维测量方法运用的结果是:
1. 动机。在案例研究国家选择多维贫困测量最普通的动机是什么?考察选择方法的选择是政治的选择,政策资助的结果,还是过去研究和经验的结果。
2. 选择维度和指标。案例选择的维度和指标是由每个国家选择的,讨论有技术含量的实践或者是“价值判断”的实践结果。
3. 支持和协调。选择的案例都是高度国际化的,分析国家资源在支持多维测量上的作用。
4. 随时间的变化。考察一些国家如何参与到多维贫困测量中,以及怎样处理相似的问题。
5. 基准的设定。国家识别贫困的不同方法。
6. 总体指标。构建一个综合指数考察不同的衡量指标的优缺点。
7. 使用过程和结果。此部分考察不同的衡量方法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被应用的,怎样收集结果,怎样把结果应用到政策中。
8. 公共讨论。研究在发展多维测量过程中,公众参与、公开辩论的程度,以及他们在不同条件发挥作用的程度。
动机
采用多维测量的动机需要从法律和政治方面进行讨论,南非和玻利维亚是为了减少不平等现象,英国和印度是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在英国和印度的案例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政策干预的贫困家庭数量。在四个国家中,开展多维贫困衡量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准确识别贫困水平,从而把资源有效地转移到最贫困地区和最贫困人口。
菲律宾和墨西哥需要公开监测和评估政策的影响,菲律宾社区监测系统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给政策制定者和项目执行者提供目标和信息。跟踪和监测是墨西哥多维贫困监测的目标,2006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社会发展总法》,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系统来设计、监测和评估社会政策和项目,该法条款规定,政府有义务制定衡量贫困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从而定义、识别和衡量联邦、州和地方的贫困程度。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的出现拒绝了货币价值对社会福利的衡量,并且把人们的价值观传到了政策优先权。如玻利维亚也或多或少选择了多维测量,因为能够更好地捕捉多样化的内在兴趣。
指标选择
指标的选择都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在某些案例中也有新的调查。菲律宾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大量采用村庄社区设计、调查和分析的贫困数据。墨西哥和波利维亚,多维贫困测量处于发展阶段,现在它能够解释社区参与缺乏的问题。其他三个国家对非传统的测量感兴趣。
在墨西哥、印度、英国和南非,由学术专家、有过调查经验的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来选择指标。在墨西哥,物质需求非常少,对热量和其他物质的需求量就是从早期的研究中获得的,然后用Ravallion的食物篮法选择食物篮的商品。在印度,专家收集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据,然后请教政府人员、中央政府的同级部委,再给出他们的意见。
在英国,贫困的衡量是采用学术回顾,协商确定的,每个地区指标采用各种技术指标组成,包括集合和模型,并通过标准的技术选择,他们应该是:为了特定目标在特定地域;衡量贫困的主要特征是最新的;可定期更新;在整个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可行。
在南非,利用现有数据,有关贫困和生活质量的研究,选择5令主要的贫困测量指标。
不丹的贫困指标选择是由四个主要方面组成:(1)促进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2)保护和提升文化价值;(3)保护自然环境;(4)促进善政。选择9个维度,相同权重的指标。
玻利维亚的衡量单位和指标正在进行调查工作。这两个指标和措施将在接下来的数月中被丰富。
在菲律宾,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成功地运用于测量地方贫困,这是一个由13个核心指标组成的数据收集系统。社区监测系统在设计、收集、监测和执行都是由菲律宾的一群前沿研究者负责。这个系统还通过与地方政府、社区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不断磋商改进。
在数据收集阶段,数据是由经过训练的社区成员、地方政府官员收集和分析的,主要的目的是减少贫困,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好处,如增加性别平等、对危机早期预警。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调查的目的,社区成员在数据调查、分析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每个住户的信息收集后,在村级汇总,然后返回数据以供调查和讨论,这为积极参与贫困分析提供了适当的干预措施。社区贫困监测系统现在进行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加强对暴力、赋权及其他方面的考核。
支持与合作
由国际机构参与构建和实施的多维贫困测量案例特点多种多样,但几乎包含所有情况。在菲律宾,国家、地方政府、捐赠者、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到这场规模宏大的社区贫困监测系统中。在不丹,城市研究中心是固定的组织,但政府管辖的城市服务机构掌握国民幸福总值的衡量。随着政策和项目的发展,政策和国民幸福总值会结合得更紧密,社区贫困监测与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倡议机构联合研究衡量指标。玻利维亚有一个固定的城市服务机构,负责搜集贫困数据和衡量人民幸福状况,这样可保证多维贫困的可持续性,不会随政府变更而改变。在南非,由于政府、学术研究机构的参与,省级多维贫困指标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成果。在印度,贫困家庭仅仅是各州制定的州贫困概念,新的多维贫困指标由计划委员下属小组正在制定。在菲律宾,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正在试验阶段,然而,因为项目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地方所有权,研发中心仅限于社区贫困监测系统的进一步试验、提供技术指导、建设可持续的能力,省、市、村级政府为本地的社区监测系统执行提供资金。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有三种类型的国际社区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具有可支持性和可持续性:
1. 州联合研究机构型,研究机构拥有的技术和学术专家对贫困指标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建议。
2. 仿效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模式来资助当地的试点方案,在当地村庄选择最适合本地情况指标试验社区贫困监测系统,然后用试验识别社区贫困系统的出现的问题以及克服困难。
3. 在国际论坛上传播有关多维贫困的成功、使用、不同设计方案的局限和失败经验、实施和具体运用方法等。
最新变化及趋势
2001年,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把FGT贫困指标制度化,调查家庭支出。社会政策评估委员会现在已经代替社区,正在改进FGT指标,开发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印度已经改进了1977年制定的农村居民2 400千卡热量这一贫困线,2002年,建立了以13个核心维度的家庭贫困线,那些贫困指标在2008-2009正在修改。
英国2007年和2004年的主要方法的指标保持相似性,只及时修改一些有变化的指标,某些领域已被新的指标替代,尤其在收入方面。同时,南非测量焦点从质量转到了规模,从测量地区贫困总体贫困,继省级多维贫困的研究后,现在正在开发多维贫困国家指标体系。
建立标准
英国和南非采用贫困排序的方法衡量贫困。在英国,按照2007多维贫困指标,低超级收入区排第一,排32 482位的是最富裕区。在南非,省级多维贫困指标提供了一个从最富到最穷的排序标准。
然而,墨西哥和印度建立了识别贫困的门槛值,在本文中提到,委员会使
FGT指标制度化,使用非等效收入,以家庭为收入单位,主要调查支出数据,定义三个相关的贫困线,这是墨西哥考察人类贫困问题的起点,从经济和社会权利角度考察多维贫困标准化问题。然而,印度贫困测量方法至今仍没有标准化,它仍在使用有明显缺陷的标准化的方法。
在菲律宾,社区监测系统复合指标包括14个核心指标,指标衡量家庭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如健康、营养等。社区监测系统在资产、社会经济、民主和空间属性方面可用来衡量收入或者贫困。
如前所述,玻利维亚和不丹正在开发多维贫困,但是标准方面有特殊之处。
总体方法
在案例研究的国家中,都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合成一整套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在墨西哥,不同的政府,平行地参与到贫困和剥夺的测量中,然而,在不同水平上的整体贫困测量方面仍有不同的方法,墨西哥现在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方法,13个参数得分从0到4,总分最大值是52,贫困线通过这个总分制定。菲律宾社区监测系统包括14个核心指标,衡量未满足4项社区监测系统综合指数指标的住户数量,这4项综合指数指标是根据核心指标详细说明简化得出,能使目标瞄准更便利。
在英国,指标由七个不同纬度的贫困指标组成区域指标,区域指标组成了整体指标,指标权重设定建立在理论、学术研究和前期指标研究工作基础上。南非多重贫困指标得分是由权重组合而成的,通过指数变换,多重贫困指标得分越高的,贫困程度越严重。得分是通过简单比率计算得出的:人们在特定域的一个或者多个指标经历贫困的比例,单个指标没有设专门的权重。玻利维亚正在开发整体指标。
使用和结果
墨西哥、玻利维亚、不丹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多维指标。南非已经开发了省级水平的多维测量方法,称2001省级多维贫困指标。印度的贫困线以下人口调查是用来识别贫困户,用于选择那些能接受政府服务的家庭。
在菲律宾,社区监测系统收集核心指标的住户数据,这些数据通过住户调查或者小组讨论得出。这个系统是由省、村政府提供资金,社区搜集数据,个人处理和分析数据。通过每个家庭收集信息,然后在村汇总,最后汇总到上一级政府。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再返回给社区确认和讨论,这个阶段允许地方政府对数据干预,这种干预也是资源分配。数据用于分析年度发展计划和社会经济概况,也用来识别减贫项目受益人。
在英国,2007英国贫困指标产生的排序用于决定分配给地方政府货币数量,工作邻里基金大约每年分配0.5亿英镑,也用于瞄准以面积社区为基础的地区干预,指标还用于主要政府和非政府的筹资方式。
公开辩论
公共辩论一般只限于在国家范围进行磋商,在学术领域很少有超越专家小组的。在英国,指标是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志愿者组织广泛讨论的结果,技术工作是由学术小组承担的。一旦贫困指标投入使用,政府就把它用于瞄准资助计划识别地区。
在南非,讨论仅限于研究中心的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在印度,专家委员会推选了13个核心指标,这13个指标用于改进识别贫困家庭的方法,为第十个五年计划服务。专家委员会也咨询州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央政府的同级部委也给出他们的看法。2006年9月完成了调查,同时,提出的意见被采纳,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可以免费享受社会服务。州政府可以自由地通过本州的任何项目提出的贫困标准。
在不丹,试验调查试着为了穷人把公众的意见加到指标中。而在玻利维亚,“过得很好”的概念是由政府和国家发展计划部解释和介绍,由于玻利维亚仍处于调查阶段,不可能说公众讨论已经参与到计划设计和执行中。菲律宾地方调查员也是数据收集者,系统灵活地把敏感指标纳入,菲律宾成功地把反贫困计划下放,这是典型的在地方构建和交付反贫计划。
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案例的调查,了解了多维贫困测量问题正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着。当前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不同于以前的贫困测量方法,当前方法更强调不同国家的贫困环境。在上述讨论的案例中,政府试图使用不同的方法设计和收集数据,从而把更广阔意义的贫困和福利测量纳入。尽管大多数国家都还处于设计和实验初期阶段。菲律宾的情况表明,这种方法和政策联系非常紧密,可以反馈给当地政府,积极干预。英国也宣称其有效的政策瞄准是多维测量的结果。此外,菲律宾和玻利维亚的案例突出了不同国际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案例研究中讨论了贫困测量的各种发展层次,在多元经济环境下,正朝着多维贫困测量的方向迈进,国际社会对支持多维方法测量贫困和福利起了重要作用。
贫困数据缺失维度导论
(Sabina Alkire,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行动中心)
本文旨在考察贫困数据的“缺失维度”——那些对穷人很重要但我们不掌握具体情况或者没有数据的维度。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界定为拓展人们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各种自由的过程。尽管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有人们最熟知的收入、寿命和教育等指标,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价值及与之对应的多维度的贫困并不仅局限于这些领域。为了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我们有时需要利用个体以及家庭层面的数据来对多维贫困做实证研究。多维贫困国际分析的一个致命障碍是我们很少能获得国家或个体层面高质量的核心领域的指标,这些领域不仅对穷人很重要,而且还具有潜在的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一、 引言
人类发展是扩展人们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自由的过程。然而,创建推动人类繁荣进步的各种机制需要有与珍贵的自由有关的各类信息,它可被用来监测自由的拓展以及进行实践研究,如那些涉及各种自由相互性或实施各类干预措施的次序的问题。
对人类发展最广为人知的衡量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包含了收入、寿命和教育三个维度。然而,人们同样也认为,人类发展的范畴超越了这三个领域。多维贫困研究确定了许多与贫困相关的维度和衡量指标。本文将提出这样的认识:缺乏一些关键领域高质量的可进行国际比较的个体/家庭数据将会成为人类发展及多维贫困研究的瓶颈制约因素。特别是,在标准调查工具中加入一些关于就业质量、赋权、安全、体面出门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福利的简单的数据模块可能会很有用。
这些问题曾在2007年5月29-30日于牛津大学和2007年11月3-4日于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启动研讨会上进行过讨论。在牛津题为“贫困数据缺失维度”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一个更为宽泛的研究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工作进行了讨论,该研究计划寻求构造一个基于能力理论及其相关问题之上的多维减贫框架。
该研讨会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来衡量能力理论提出的内容更为丰富的多维贫困与剥夺?
(2)何种反映缺失维度的指标与问卷问题能显示那些需要进行跨国比较的研究性与政策性问题?
(3)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初步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确定了五个数据不够充分的领域:
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其核心是就业质量(Lugo,2007)。
赋权,或主体性:一个人实现其所追求或有理由追求的目标的能力(Ibrahim和Alkire,2007)。
安全,主要关注财产和人身不受侵犯(Diprose,2007)。
体面出门的能力,强调尊严、尊重以及免受侮辱的重要性(Zavaleta,2007)。
心理和主观福利,强调价值及其决定因素和满意感(Samman, 2007)。
前四个领域是贫困的维度。我们并未严格地将心理和主观福利视作贫困的维度,因为关于人们缺乏这一维度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贫困及其与政策的相关性还存在疑问。但同时,心理和主观福利的确似乎又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成为一个数据缺失的维度。参会者认为这五个领域是人们解决相关问题的合适的考察对象。会议集中讨论了什么指标和问卷问题能最好地衡量这几个维度以及在探索规范数据收集附加价值及其合适时机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
本文将展示考察数据缺失问题以及拓展调查问卷问题范围的逻辑依据,这些调查问卷问题将被列入可进行国际比较的国别性家庭与个人调查当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的需求特别强烈,因为这些国家贫困且数据更少。其后,我们会说明选择上文提到的五个维度的理由,也会介绍关于这些维度的五篇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给出了相应的调查问题和指标,同时也会确定可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与政策议题。
二、 缺失的数据
如果我们把发展理解成人们珍视或有理有珍视的自由的扩展过程(Sen,1990),那么衡量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要用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之间一致并可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衡量。比如人类发展指数考虑了教育、寿命以及收入因素,但大多数学者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森(2004)在一本书中写道:“比起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一种对发展的衡量是非常成功的。它没有仅仅关注经济财富(而这是GNP所显示的),而是以三个组成部分(即基础教育指数、预期寿命指数和收入指数)为基础。在衡量发展的过程方面,人类发展指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实证研究视野。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发展指标。”
在最近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中,拉尼斯等人(Ranis等,2006)指出:人类发展指数与一系列重要生命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些重要维度包括:精神福利、赋权、政治自由、社会和社区关系、不平等、工作条件、休闲、政治、经济稳定以及环境。基于该项研究,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将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测度扩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维度会显著改变人们测度和评估一国发展成就的方式,但目前这些拓展维度的数据要么不存在,要么很不完全,而且仅覆盖了少数样本国。
为什么提出一小组重要但不是标准的人类发展维度指标呢?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
首先,与以前任何一个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对这些数据的拥有量更大,在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我们难以全部进行分析的程度。这些数据指标源于家庭调查、社区调查、普查以及人口与社会调查。对于非标准指标,我们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来选择技术上精确且又可在多种文化间进行比较的指标。
第二,许多人已经采取行动正在探索衡量这五个领域的能力与机能以及构建国家和地区衡量框架的途径。比如,“非正规就业中的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项目已经开发出了包括非正规工作在内的就业衡量工具。艾尔索普(Alsop)、纳拉扬(Narayan)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赋权指标的开发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欧盟国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以及经合组织有关机构和其他一些组织在构建能力理论框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此外,致力于开发能力衡量方法的学者们也正在利用微观及原始数据来组织调查和开展研究。最后,社区监测系统也在整合并考察与能力及机能有关的缺失指标。本项旨在为国际数据收集确定人类发展衡量所缺失的关键指标的研究利用了上述行动的成果并尽可能地支持这些行动。
第三,这些维度可能是人类发展其他维度的重要触发器,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因为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都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维度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例如,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国家是一些正在经受或出现暴力冲突的国家。人们已经反复指出赋权是消除贫困的一个重要工具;消除针对特定等级、年龄、宗教、种族人群或者其他一些人群的社会排斥似乎已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减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四,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这些缺失的维度可被证明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选择它们进行分析很重要。此外,如果这些数据能够首先进行不同维度加总之后再进行不同个体加总的话,多维贫困测量能够更好地澄清一些特定问题,如极端贫困的瞄准与分布。对人类发展指数而言,其数据就可以对每一领域所有个体进行加总。如果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从同一个调查或若干个在个体层面能匹配的调查中获得,这种方式就会显现出明显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表1左边三列列出了4个个体一般可获得的数据(黑体),右边三列给出了只有在三个维度被放在调查中考察之后才能获得的数据。如果对每个贫困维度都有确定的贫困线或贫困段,我们就可以确定每个人在每个领域是否贫困。首先来看左侧三列,我们会发现个体1和个体2在三个维度中仅有—个维度贫困,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那么他们的贫困程度是相同的:个体3和个体4在三个维度都贫困,所以他们贫困的程度相同,且他们比个体1和个体2更贫困。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右侧三列的数据,这四个个体的贫困排名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个体4将是最贫困的人,其次为个体1。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则每个个体的贫困状况将会因权重不同而不同。即使存在关联性,确定被研究个体与家庭贫困的性质与程度对政策目标的制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调查的匹配一致性在伦理上和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重点关注那些可以加入到现存调查中的新拓展维度的数据模块。
表1 不同贫困维度的个体数据
三、 数据来源
千年发展目标行动已明确提出并倡导收集国际数据,并发布了49个指标。这些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发展的研究,值得赞扬。千年发展目标无疑充当了—个跳板,显著地推动并拓展了福利的一些关键维度的数据收集、整理以及发布,这些维度包括教育、健康、营养和性别等。但是,它仍然处在人类发展的一些特定基础性领域,可进行国际比较的个体与家庭数据依然缺乏。虽然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很重要,但它并没有涵盖所有人类发展的基础性维度,也由于此,同样也没有涵盖人类安全和人权的基础性维度。200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但它也同时承认人类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很重要,如远离暴力。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等人题为《穷人的呼声》的研究发现:穷人同样珍视就业、安全、尊严、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以及和平安宁。阿玛蒂亚·森反复提及自由和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经常在赋权的议题下被讨论。像《穷人的呼声》一样,他也讨论人们体面出门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当前关于社会排斥与包容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维度。关于那些以前缺乏数据但现在可以获得数据的重要维度,许多其他作者也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数据方面的约束极大地影响了研究者从实证角度对人类发展进行研究的能力。因此,寻求开发缺失数据的努力可被看作一种投资,使我们在未来具有开展良好的多维贫困研究的能力。
在目前收集相关数据的各种工具中,四种著名的调查已经被有关国家应用到了收集和报告关于多维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的数据及成果当中,它们分别是:世界银行生计标准和衡量调查(LSMS)、世界银行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人口和卫生调查(DHS)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多重指标集束调查(MICS)。在上述这些调查中,我们所提到的维度严重缺乏,尽管一些国家采用了与之有关的一些问卷问题。
1980年,世界银行启动生计标准和衡量研究(LSMS)开发相关政策数据,展示失业、收入贫困以及低教育卫生水平等的决定因素。LSMS的目标是使有关国家能够改善数据的质量,强化统计研究机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并使数据得以公开。LSMS家庭问卷包括以下单元(表2):
表2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作为一个模块被包含在LSMS中,但是一些国家已经修正了LSMS,使其包括了非正规就业和主观福利等问题。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人口和卫生调查(DHS)是全国性的大型代表性人口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关于健康、营养和人口指标的信息,具体的变量包括(表3):
表3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模块被包含在DHS中。但是一些国家的DHS已经添加了一些关于缺失维度的特殊问题,比如家庭决策或性暴力。
世界银行的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调查被设计用来快速生成标准化的社会福利指标。CWIQ问卷一般由四页正反两面的纸构成,做完一份这样的问卷大约需要20分钟。其内容主要包括(表4):
表4
CWIQ包括了一些可以提供非正规就业基本信息的问题,但是它不能收集到完全的信息,也不能解决关于其他四个缺失维度的问题。
最后,MICS提供了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数据,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儿童福利的数据。比如,MICS调查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能够对某些千年发展目标进行监测,这些目标与以下问题相关:儿童营养不良、免疫接种、婴儿、五岁以下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安全饮用水及卫生可及性、孕妇艾滋病感染率、儿童入学和结业比例等。虽然一些国家也已经引入了相关特定问卷问题,但总的来说,MICS没有包含我们所提出的五个缺失维度。
除了以上这些调查工具外,每个研究者都还会考虑进行其他一些调查,比如地区动态调查、欧洲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以及诸如犯罪和受害调查之类的特殊调查。在各类国家综合性多主题家庭调查中,我们所提出的维度通常也没有被包括在内。即使出现在调查中,这些维度也很难被发现且经常只有很少的信息。由于内嵌于家庭调查数据库中的搜索功能和标准的多主题调查搜索引擎还不允许对这五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搜索,相关研究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四、 指标选择的根据
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收集方法在不同的层次上(比如调查、参与式测验、管理记录、人口普查)生成。本研讨会所有论文都集中关注了一种数据收集方法,即国际可比并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个体与家庭调查(下面简称为家庭调查)。这些调查有许多优点,它主要强调: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对已收集数据(特别是与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数据)和新建议维度数据比较的可能性以及为政策分析直接提供数据的能力。家庭调查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以及主观数据与客观数据。在这里,我们对使用这些调查收集所有类型的数据不做限制,因为他们包含了缺失的维度。虽然如此,这些方法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局限性:从设计上,家庭调查忽略了其他层次的分析,比如包括像户内和社区因素以及制度、国家或全球因素等对人类福利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家庭调查处在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前沿地位,但很明显它们只提供了一个层面的信息。
下面提出的一些标准被本项目中所有有关人员采用来选择个体与家庭调查的合适指标。第一,该指标必须具有国际可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缺失维度的可比指标信息非常稀缺。第二,这些指标不仅要被用来测度我们所提出维度的工具性价值,而且还要被用来衡量其内在性价值。第三,我们要求所选择的指标要能反映每个维度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变化。第四,我们在选择某个指标时必须要考虑该指标以往被利用的状况,也就是说该指标以往被选用并且被认为能恰当实现研究目的的频次。感知性指标在以往的国别典型调查中并不被经常使用,但它在对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心理测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如此,尤其在贫困国家的背景下,这些指标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五、 缺失的维度
在明确获取额外数据的需求和提出相应收集方法之后,我们选定了一些受穷人珍视以及具有政策相关性的特定维度。在这里,我们要阐述一下选择这五个维度的内在依据。这些维度被人们认为属于人权的范畴,在《穷人的呼声》系列研究中被加以界定,而且还被罗尔斯的政治理论以及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研究人类安全的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维度包括:就业(重点关注就业的质量)、赋权、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福利。此外,在确定这些维度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代表这些维度核心要素的可操作的具体的指标与问卷问题。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要为每个维度设计出一个包括5~8个指标的列表,并构成—个模块加入到用来培训调查员的标准调查表中。这些模块会依次出现在下面的论述中。每个维度将被依次讨论。
就业质量
就业并不是一个关于福利的新维度,但它在人类发展和减贫政策中有时会被忘记,或者至少没有被充分考虑。对世界上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很多,但一般来说,一份体面而又报酬不菲的工作总是与不贫困有密切的联系。除此以外,就业还会给人带来自尊感和成就感:就业作为个体福利的一个基本因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有的就业数据大多关注正规就业,而忽视了穷人的就业以及就业的潜在意义。卢戈(Lugo) (2007)从全球层面提出了五个就业指标来弥补这一不足。其中有四个指标与就业质量有关,包括非正规就业、自我雇佣收入、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就业不足与过度就业。最后一个指标与数量有关,它试图确定失意性失业的水平,即那些愿意工作但没有找工作的人。
主体性和赋权
主体性被定义为:“一个人在追求他/她认为重要的目的或价值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去做或实现的事情”(Sen,1985b:206),更简单地可定义为:“既可以行动又可以做出改变的人”(Sen,1999:19)。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反面是那些被强制、压迫或消极被动的人。主体性及其扩展(赋权)由于对贫困社区具有工具性和内在性重要价值而被再次确定为一个变量。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易卜拉辛和阿尔基尔(Ibrahim和Alkire)(2007)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体或集体主体性的简短的指标列表。简单地说,他们使用“决策(decision-mak-ing)”问题来确定控制感,即在家庭生活中谁在做决策以及受访者能否做决策。为了衡量人们感到自己被强制及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的程度,本文提出了心理自主性的衡量指标,这曾在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最近在贫困社区进行过检测。其他问题考察了个体或社区层面个人感觉有能力做出改变的程度。
安全
在后冷战时代,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不再是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冲突,而是各国内部个体、团体以及国家行为人所造成的侵犯(Hegre等,2001;Sen;2006;人类安全会议,2003)。这些侵犯抵消了在诸如教育、健康、就业、收入增长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成果。除此之外,这些侵犯还阻碍了人类安全生活的自由,使贫困陷阱在很多地方持续存在。但是,侵犯并不是人类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大多数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贫困的人群能够和平共处。人们需要开发关于人身和财产侵犯的可靠且可比的数据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迪普罗斯(Diprose)(2007)提出了一系列问卷问题来衡量由冲突和犯罪引起的侵犯,这两类侵犯在各类调查工具中并未组合在一起。迪普罗斯的这篇文章试图确定由犯罪和冲突这两类来源引超的人身和财产侵犯的发生率和频率以及现在和未来对安全威胁的感知。
可以体面出门的能力
羞耻(shame)和受辱(humiliation)对我们理解贫困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些维度的国际可比数据仍然缺失。基于相关领域已有的指标,扎维莱根(Zavaleta)(2007)提出了八个指标来衡量与羞耻和受辱有关的各种特定问题。衡量羞耻的指标选自研究因艾滋病而受辱的文献、关于歧视问题的文献以及心理学研究使用的工具。第一个指标与因为贫困而感到羞耻有关,或称为贫困的羞耻感。第二个指标是羞耻倾向,即受到特定负面事件影响时个体显现羞耻情绪的倾向(Tangney和Dearing,2002;2003)。羞耻倾向与贫困具有特别的相关性,因为它会影响社会关系、自尊以及可以无羞耻出门的能力,这些都是能力贫困的问题。外在受辱的问题核心是受到尊重、不公平对待、歧视以及个人背景阻碍其行动的感知;内在受辱的问题旨在衡量个体累积受辱的水平。
心理和主观福利
我们最后考虑的维度是心理和主观上的福利状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内在性价值。它们是我们所建议的其他维度的一个核心影响因素及最终结果。此外,它们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价值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野,尤其其作为非物质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对于心理福利,萨曼(Samman)(2007)提出了一种双向嵌入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1)问卷回答者根据自身独特的潜能来回答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2)问卷回答者实现理想的能力。为了开发这些概念,她利用了斯蒂格的生命意义问卷(Steger等,2006)以及德西和瑞安关于确定和追求目标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反过来可以预示出最优机能)的衡量方法(Ryan和Deci,2000,2001)。这些需要是自主(autonomy)、胜任(competence)和相互关联性(relatedness)。对于主观福利的考察,她分别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了衡量。对满意度的衡量考虑了生活的整体以及其几个特定领域,这些特定领域被认为很重要,即物质福利(食物、收入、住房)、健康、工作、人身安全、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教育、邻里关系、有效帮助别人的能力以及来自精神/宗教/思想信仰的福利。
六、 后续行动
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中心工作论文1到5提出了许多代表缺失维度的指标和问卷问题,在研讨会上这些指标和问卷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得以进—步改进。但是,这些文章仅代表整个进程的第一阶段,该进程将对这些指标和问卷问题进行考察和检验,研究它们的附加值和效用,并呼吁将它们纳入不同数据收集工具。所有与会人员的评论以及格莱斯·贝蒂亚科(Grace Bediako,联合国社会与住房统计处处长)、弗兰克斯·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mingnon,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和斯蒂芬·克拉森(Stephan Klasen)等人的讨论发言非常重要,通过对把我们所提出的模块加入现有数据收集工具以及未来对这些数据的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促进了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中心未来行动方案的构建与完善。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尝试的局限。最终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衡量贫困,而是要构造一个新的研究与政策框架来帮助实现持久的减贫。家庭调查似乎是—种收集所需数据的最有效的方法,但它存在许多局限:它忽视了家庭内部的问题而且成本很高。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需要确定只通过几个问卷问题能否足以衡量我们所建议纳入的那些复杂维度。不过,我们坚信从这项行动中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将会远大于其本身存在的不足。
“摆脱贫困”研究:一个综述
(Deepa Narayan,Lant Pritchett和Soumya Kapoor,世界银行)
原则和方法
“摆脱贫困”研究是早先“穷人的呼声”系列研究(Narayan等,2000;2001;2002)一个后续研究项目。旨在自下而上探索穷人摆脱贫困的途径。
人们的呼声、地方状况与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本项研究整体上遵循了三个指导原则:第一,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生活,穷人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对数以千计的农村社区居民进行了访谈,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基本看法,这种方法并非漫无边际。我们也充分地了解,这些主观信息,特别是关于以往生活的主观信息,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而失真。包括回忆出错(Gibbs,Lindner和Fischer,1986; Withey,1954)、每个人叙述生活经历的方式(Tilly,2006;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研究方法和访谈所提问题对访谈回答的影响(Krueger和Schkade,2007,Kahneman和Krueger,2006)、社会环境与权力结构(Chambers,2002)以及一些一般性的误差等。此外,贫困研究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贫困人口和社区可能会出于获得资金或项目的考虑而给出“合适”的答案。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也无法摆脱这些问题的影响。同时,我们认为个体叙述自身经历的方式与其利益诉求密切相关。此外,我们也认为应该采取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即使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视角来审视某一种现象。本项研究是要补充而非替代人们关于贫困问题研究正在采用的诸多定性和定量方法。
第二个指导原则是地方社会经济背景十分重要。据此,我们将个体或农户置于特定社区背景下进行研究,而不像典型贫困调查那样仅关注个体或农户的特征。我们特别关注了规范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的规则与期望。
第三,我们考察了贫困随时间发生的动态变化。大多数研究只考察了某些个体在某一固定时间的状况,而我们则是要深度了解人们摆脱或者陷入贫困的过程。
什么是贫困?谁是穷人?
如果一个人要了解穷人的生活及其脱贫的方式,首先要对贫困进行定义和衡量:当世界银行探讨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时,他们对对贫困进行了定义:当各国首脑齐聚联合国誓言消除贫困时,同样也给贫困做出了定义。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对贫困进行定义,而让当地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去定义贫困。
生活阶梯
我们采用了一种叫做生活阶梯的工具来让社区居民自己界定贫困和富有,并确定在社区中谁应算是穷人。一个典型的生活阶梯讨论小组有6~15个成员,他们都是根据研究特殊的要求选出来的,代表社区内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团体。一般来讲,每组的讨论会持续2~4个小时,如果可能的话,这种讨论会按照男女分组来进行。
小组讨论开始会进行一个初步分析,即提出促进和阻碍本社区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参与者们再构建一个生计状况阶梯,最低一阶代表社区内最为贫穷或生存状况最糟的人群,最高一阶代表最为富有或生活良好的人群。再后,参与者会讨论和描述阶梯中每一层阶家庭的特征以及家庭在阶梯结构中上升或下降的典型方式。
然后,讨论小组要将社区内150个家庭按照阶梯台阶进行排序。他们会确定每一个家庭初始(约10年前,1995年左右)和当前(2005年)的位置。在排完序后,我们会得到一个社区居民在阶梯上流动的矩阵图,显示每个家庭过去十年在阶梯中向上、向下或保持不变的状况。
完成家庭排序后,讨论小组将确定一个社区贫困线。这个社区贫困线位于生活阶梯的两个层阶之间:低于贫困线各台阶家庭被认为是贫困的,而高于贫困线各台阶家庭则是非贫困的。由于不同的讨论小组所建构的阶梯层数不同(通常是4~6层),他们可根据自己所在社区的实际情况来划定贫困线。
绘制社区流动矩阵使我们能够对社区内家庭按其在研究期内具有或缺乏贫困流动性而进行分类。所有家庭在阶梯中的位置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也可能保持不变。那些位置发生变动的家庭可能会越过贫困线,也可能不会。在本文中,我们确定四种流动类型:
·脱离贫困家庭:1995年贫困但在2005年脱贫的家庭;
·长期贫困家庭:1995年贫困,而在2005年依旧贫困的家庭;
·从不贫困家庭:1995年属于非贫困者,2005年依旧非贫困的家庭;
·陷入贫困家庭:1995年属于非贫困但在2005年陷入贫困的家庭。
据此,在本项研究中,“穷人”和“贫困”两词指的是讨论小组所建生活阶梯认定的贫困家庭。每个讨论小组的定义都未做改动。流动状况既非外部专家指定,也非家庭自行评定。
主要发现
本项研究共有7个主要发现,下文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这些发现与我们将流动界定为如下两个概念发生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有关:穷人为脱贫而采取的行动和他们可采取这些行动的机会,二者都会得益或受阻于地方层面各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穷人并没有陷入某种所谓的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贫困和“穷人”的问题时形成了三种观念。前两种观念可追溯到工业革命,当时,在英国的城市中涌现出大量穷人。维多利亚女王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存在性格缺陷且道德败坏。因此,施与救济加上教化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合适办法。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导致贫困,只有改变制度,才能使穷人脱贫。照此逻辑判断,贫困是穷人的宿命,他们自身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尽管这两种世界观差别很大,但都否定了穷人自身的作用。
上世纪,美国人类学家Oscar Lewis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1959,1966)。他将“贫困文化”定义为一个包含众多特征的复杂概念:离群、消极、懒惰、无能、没有价值、缺乏抱负,更不用说吸毒、酗酒和犯罪。他认为这些文化缺陷会在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他的观点引发了争论,并促成了美国有关福利政策的出台。至今,关于穷人仍然有一个饱受诟病却根深蒂固的认识,即穷人不能因为自身的窘境抱怨任何人。直到最近,学者Charles Karelis(2007)还使用文化因素对美国及全球贫困的顽固性进行了解释。
在我们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穷人陷入某种贫困文化的证据。即使在马拉维这样极端贫困的国家或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这些饱受社会冲突摧残国家的社区,穷人也很少丧失信心。反而是,他们会努力行动,一般做一些小生意,来保障自身的生存并实现发展。其中,有一些也确实脱了贫。在每一个国家,当我们让那些“脱离贫困家庭”列举其脱贫的三个最主要原因时,他们的回答中提到最频繁的是人们在寻找就业机会和开办生意方面的努力。当我们考察“长期贫困家庭”出现改善现象的原因时,所得到的回答基本相似。这一结果与懒惰、消极和犯罪的文化相去甚远。
即使那些未能成功脱贫的人也还在不断地努力。在印度,我们对2700个家庭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长期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一样采取了同样多的行动,尽管他们仍深陷贫困。鲜有证据表明,贫困者是因为懒惰、酗酒、不愿工作和储蓄而陷入贫困。恰恰相反,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强调努力工作以及拥有能承担繁重工作的健康身体的重要性。乌干达Bufkaro一个男子讨论小组的发言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穷人的资本就是他们的体力,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
穷人不是圣人。我们确实发现,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受冲突影响最重的国家,都有少数社区存在一些深受酗酒、吸毒、家庭破碎和绝望情绪困扰的贫困家庭。不过,这些严重的问题只影响了一小部分穷人。在小组讨论中,很少有人将赌博、酗酒和吸毒列为其陷入贫困的原因。反而是国家和地方经济萎缩、疾病和死亡以及家庭支出等因素被列为其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穷人并不缺乏信心,尽管信心只会在脱贫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加强。即使在充满冲突的动荡环境中,人们仍能保持勇气和坚韧并充满理想。32岁的Pedro生活在哥伦比亚圣帝马拉一个犯罪率很高的村庄,他说:“我很有信心,因为我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愿意克服一切艰难努力进步。”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需要自信和行动。事实上,我们发现78%的受访家庭都相信他们的子女在将来会生活得更好。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孟加拉、塞内加尔以及阿富汗这些低收入国家,超过90%以上的家庭都对他们子女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显然,绝大多数贫困的父母并未将贫穷的悲观情绪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这些发现对制定减贫战略有三个重要启示。一些国家存在大面积贫困——此如,赞比亚超过6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马拉维一半人口是贫困人口,印度则是1/3——并非是由于大量人口行为不善而导致的。慈善或其他外部施舍的项目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缓解少数人的痛苦,但根本不足以使整个国家或社区摆脱贫困。
减贫组织所采用的主要诊断工具——贫困衡量一般会对最底层1/5穷人的特征进行测量并分析其与富人出现差别的原因。这种做法暗含着一个假设,即穷人所具有的特征是导致贫困出现的问题所在。可事实上,人们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穷人采取行动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探索拓展当地经济机会的途径。
在经济低迷且贫困面很大的时候,人人都能受益的再分配项目可能会有助于穷人脱贫。不过,这些项目很少能赋予穷人降低脆弱性所需要的永久性资产:它们提供的资源通常非常有限而且很少能分配到每一个人。在马拉维,一个讨论小组曾提及该村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这个项目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为在整个社区中只选择了两个人……它不应该是有选择性的……你只惠及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能够改善整个社区?”
这样的项目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减贫。社会保护项目应分配足够的资源,以使穷人能够渡过危机并获得资产进而摆脱贫困。此外,这些项目的关注点应该转移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拓展发展机会、提供生产技能上来,从而使穷人的努力真正发挥作用并摆脱疾病的困扰。
贫困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
穷人是左撇子或患感冒的几率比富人更大吗?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疯狂,但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揭示了人类本身属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方面是一些稳定的、永久的特征,如生理性别、成年身高或左撇子。这些特征是我们个体身份的一部分,尽管并不总是如此。另一个方面则是一些人们所经历的短期的、偶然的情形或状态,如穿一件红衬衫或患感冒。它们持续时间或长或短,并不会永久存在,也不能用来界定他们的身份。
目前,有成百上千个机构在寻求解决贫困的办法。“穷人”被提得越来越多。谁是“穷人”?这些“穷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全球化将怎样影响“穷人”?然而,“穷人”这个词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它把那些除了经历过短暂贫困之外毫无其他任何共同点的个体凑在了一起。
本质上,以部分拥有特定经历人群的特征为基础进行实证分类并没有错误。比如,统计学家可以确定某个家庭调查在特定时间点的怀孕人群。这一人群,“怀孕者”,与其他人群具有一些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她们都是女性,处于一定的年龄范围),同样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同的社会特征和行为方式(已经结婚或有性伴侣,有性行为)。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怀孕者”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稳定的集合。我们都承认怀孕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状态,是个体在人生特定时期的经历和状态。
在对本研究中社区流动矩阵和受访者生活经历进行定性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可以大胆地说,贫困并不是“穷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对少数人来说,“穷人”是一个稳定的先赋性身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贫困只是一种“状态”。总体上说,贫困并不是一个家庭的永久特征,而只是一种状态,是家庭经历的一部分。
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我们的分析得出三个关键的认识,它们都认定贫困是一种经历:第一,在我们所研究的社区中,人们并没有将贫困视为一种身份,第二在生活阶梯中,很多农户的贫困状态都发生了或改善或恶化的变化。第三,我们的分析有很强的区位效应,即人们所在的社区对研究的结果影响最大。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社区中的穷人或其他人将贫困视为一种身份。在上文所描述的生活阶梯中,刚刚脱离贫困线与即将越过贫困线的两类家庭的共性要多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样的结果与贫困是一种身份的观念相矛盾。进一步歩,如果贫困是社会的一个身份特征的话,无论是自我归类还是社会强加,人们就不会讨论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的问题了。然而,当我们提出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小组,包括残疾人,都强调个人努力、自力更生的进取心。这些都是摆脱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身份特征的途径。在讲述生活经历的过程中,被调查者清晰地指出其处于贫困状态的时期长短,但他们强调贫困只是一种需要改变的状态,而不是永久的宿命。
如果“人”陷入贫困是因为一些稳定的、持久的特征(如文盲),那么在这些特征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看到积极的变化。然而,我们的证据表明,农村访谈社区陷入贫困的人们有一个显著改善的趋势,这并不是说不存在“贫困陷阱”,只是表明大多数穷人可能并非由于其自身的特征而陷入贫困陷阱。在典型调查地区,初始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几乎有一半在生活阶梯中至少上升了一个台阶,平均约有25%的家庭实现了脱贫。
对任意时间点上贫困水平净恶化或净改善的统计隐藏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效应:脱离贫困和陷入贫困。要获得贫困净缓减的实际数据,我们必须要测算出在既定时期内脱离贫困人口多于陷入贫困人口的规模。例如,马拉维样本社区贫困净变化的边际增长不到1%。然而,这一停滞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如做更进一步的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生活阶梯测验中所有马拉维的农户有200.2%已经摆脱了贫困,同时有近10.6%的农户却陷入了贫困,返贫的规模抵消了脱贫的成效。
在所有被研究的地区中,我们的证据表明脱贫和陷入贫困的流动性都很高。在一些典型的研究地区,脱贫和陷入贫困的规模是净脱贫规模的三倍。这种流动特征对政策制定至关重要。如果“穷人”是个固定的群体,那么他们就能够通过专门转移支付项目被加以识别和扶持。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上升和下降,就需要解决大量人口的脆弱性。在经济困难国家,减贫战略必须要帮助穷人构建永久性的资产和生计方法,来帮助他们应对生活环境的动荡。
没有人会怀疑居住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能增加人们脱贫的机会。然而国家层面绝对贫困的缓减往往会掩盖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的数据表明,地方的社会经济条件对贫困的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发现可支持这一结论:第一,我们发现村与村之间在发展水平和脱贫状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社区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而有些社区几乎没有人实现脱贫;第二,地方层面的差异很大。对样本社区简单的方差分析表明,穷人向上移动的变差只有25%可归因于研究地区或国家的差异,其他75%则是由一国内部社区的差异所造成的。在社区效应如此强的情况下,贫困显然不只是个体特征的问题。
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都会对社区流动(指脱贫或返贫)产生影响。有利于脱贫的积极因素包括整体经济繁荣(尤其有利于找工作)、村庄市场建设以及靠近城市和道路等。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也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另外,流动的发生也会受制于村内贫困人口比例过大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会造成人们参与市场交易、利用公共设施以及享受社会服务的不公平)。集体行动倾向也对流动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并不明显。我们的证据表明,在社会高度分化的社区(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穷人因为贫困而被排除在富人的网络之外,只能相互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困难和维持生存,这是一个消极的兆头。
综合来讲,我们的发现否定了贫困是一个人永久或半永久特征的观点。如果人们是因为一些固定特征而陷入贫困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么多脱贫的案例,也不可能观察到家庭如此大幅度地向上或向下移动。最后,如果脱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个体行为或是国家层次的现象的话,村级差异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寻找解决问题之道要深入一国内部,聚焦于社区。关注的重点应转
向通过修路、发展市场、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心以及消除社会不平等(包括将穷人组织起来)等方式促进社区发展进而改善穷人发展的环境上来。贫困监测和减贫效果评估工具应考虑各种地方层面促进社区发展的各种背景和条件因素。它们应要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贫困是一种暂时状态,那么什么因素才能决定一个家庭是否脱贫?
总之,正如我们在坦桑尼亚卡盖拉的研究所显示,现有的经济模型对陷入贫困的预测要比对脱离贫困的预测更加有效。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深入探究地方发展的过程并将个体置于地方社会经济背景下来更好地解释哪些人最终实现了脱贫及其脱贫的途径。我们的分析是根据考察穷人的行动与地方社会经济状况所提供机会的关联这一概念框架进行的。我们研究的是社会分层影响单个穷人或组成集体获取经济政治机会的程度。
内在力量有助于人们改善生活
研究中我们与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进行了交谈,发现人们反复提及内在力量和信心,作为脱贫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在取得一些成效时,穷人的自信心会迅速增强。实际上,在自信心和内在力量方面,穷人与富人并无区别。
在家庭访谈中,我们让被调查者用力量和权利十级阶梯对自身进行排序,并表示他们完全没有力量,10表示他们力量很强且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将这一测度指标作为自信心的代理变量,将10级当中上面7级定为感觉到有力量,将下面3级定为感觉到没有力量。
据此分析,得出三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形。第一种:那些10年前并不贫困而现在在陷入贫困的人感觉到没有自信且没有力量。这些人中,仅有33%的人认为自己有力量,而在长期贫困家庭,这一比例为43%。
第二种:虽然平均来讲,长期贫困家庭的力量感要低于脱贫家庭和非贫困家庭,但他们仍有近一半家庭认为自己有力量。这一结果使得“穷人”天生缺乏信心的论调难以成立。
第三种:自信感在不断变化且与经历有关。这是我们对比人们十年前和目前排序的结果后发现的。十年前,当他们还没有陷入贫困时,有将近60%的陷入贫困家庭认为自己有力量;而现在,该数字下降到33%。与此相反,十年前那些即将脱贫家庭只有42%认为他们有力量,那时他们尚处于贫困状态,现在当他们摆脱贫困后,这一比例上升到74%。这表明,境况变差的人会因为经历了坠入低谷的过程而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而穷人会因为境况得到了改善而重拾信心。穷人和富人之间在自信心方面并无天生差异,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环境使然。在Uttar Pradesh的Boodanpur,一个男子讨论组证实了这种脱贫的良性循环:“摆脱贫困后,由于人际关系的逐步改善,人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强。有一句俗话说得好:饿鬼只能招来更多的干旱,‘没人欢迎:富人无论在何处,皆受欢迎。”
自信心和个体能动性在脱离贫困中十分重要。我们的这一判断来自于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对家庭脱离贫困过程的测度建立在社区而非家庭对自身所处状态排序的基础之上。这减弱了我们对受访者关于自身脱贫和陷入贫困状况的判断和其对其他一系列因素的感受进行回归处理时出现的潜在偏差。同时,我们把人们在力量方面的自我排序和对日常生活决策的控制程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关于力量和控制程度的衡量指标。我们没有发现因果关系,因而,我们转向了对受访者关于自身生活经历介绍的考察.这些介绍反映了受访者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最近十年。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一些国家,受访者关于自身力量程度的排序和贫困状况的变化高度相关,甚至是在控制了22个或更多其他社区与家庭变量包括教育和资产之后也是如此。在印度Uttar Pradesh邦和Assam邦以及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与乌干达,相关性都很高且为正。比如在孟加拉,个体控制力每上升2个单位,减贫的可能性就提高15%。我们还发现,在15个有定量数据的研究地区中,有10个地区,另一个心理变量,即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呈现出更强且更为稳定的正相关。在西孟加拉,对未来的期望每上升2个单位,脱离贫困的可能性就提高35%。
马拉维Guluteza的一个名为Milward的长期贫困者强调了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我已经努力了很多年,终于挺过来了。这令我信心大增,现在我不用依靠任何人了。无论家里遇到什么事,我都会和我的妻子一起努力解决。我还觉得,我妻子和我一起奋斗,增强了我的信心。”由于Milward在社区内的地位不断提高,且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其自信心也相应地有了进一步的增强。最近,Milward被推举为村里的族长。“我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人们像我一样拥有信心。而且我一直在自问我怎样做才能让大家觉得我已经担负起了应尽的职责?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获得更多的勇气。”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穷人虽然有时会将贫困比喻为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透不过气来的巨蟒,但同时又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哥伦比亚LosRincones 60岁的老人Gudelia说:“我们要乐观,这是我们渡过难关的法宝。”
然而,穷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所拥有的影响力也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却大多接受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各国访谈者对于不公平现象通常的比喻是:“看看我的手,手指一样长吗?当然不,总有一个比其他的长。”
贫困的父母总是自己承受恐惧,大多数不会将其传给儿女。在与年轻人探讨志向的问题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沿袭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具有比父母更宏大的理想——做生意、当律师或医生、拥有工资性就业岗位、使自己的农场现代化以及在社区内争取平等的权利。
不同的资产和能力都可能会促进或阻碍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健康危机,它会导致收入降低、产生额外开支,有时还会造成家庭主劳力的死亡。所以,并不奇怪的是,控制感越强,健康意外发生的频率就越低。家庭资产就越多,户主受教育程度就越高。在力量和权利阶梯中处于高位的人,也更可能参与政治活动,如通过求助当地的政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我们在个人能动性上的结论对如何实现发展也很重要。发展干预应尊重和增强人们对于自身和家庭的信心,而不是相反。参与式和由社区主导的方式能够强化人们的能动性。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也可通过加强贫困妇女组织的投资来部分地加以解决。有助于增加人们物质资产特别是永久性住房的措施也能强化人们的自信心并为他们建立发展的经济基础。此外,防止和缓减健康危机冲击的战略也同样重要。最后,将穷人的努力转化为市场经营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相信自我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但不能解决穷人缺乏经济机会的问题。机会缺乏会使穷人的努力无用武之地。向穷人释放机会需要对三种基本的制度进行改革:市场、地方民主和穷人自己的组织。
机会平等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与富人拥有众多选择不同,穷人可利用的资源寥寥无几。我们对社区内穷人和富人可利用的选项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大多数地区,即使是地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机会公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在坦桑尼亚咖啡种植区Ngimyoni,经销商们经常在咖啡收购称重时欺骗贫困的生产者。这种伎俩甚至有一个专用称谓——masomba,意即使咖啡像向日葵花一样轻飘飘。于是,小农出售超过60千克的咖啡可能只获得大约50千克的报酬。由于收入微薄,他们常常会向社区内的富人借钱,但这时他们可能他会受到欺压。在放款之前,放贷人可能会迫使小农签署一份协议,声称其借了高于实际金额两倍的钱。
在所有调查地区,贫困的农民都说自己出售咖啡或香蕉时根本无力与大买主讨价还价。由于急需现金,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低廉的价格,或遭受放贷人的剥削。马拉维Bamlozi的农民说,“小农最容易遭受打击。在遇到饥荒时,他们很快就会耗尽微薄的资产。”
对穷人而言,其经营环境与大企业截然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应推行自下而上的自由化,包括废除限制性的政府管制、扩展市场通道(特别是通过建设道路、桥梁和通讯设施)以及为穷人参与市场经营创造更加公平的条件。穷人的经济组织与商业经营技能培训非常重要,能帮助他们克服规模经济难题并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当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时,无论是通过修路、提高市场自由化程度还是引入新的经济作物,仍需要近两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社会结构的转变。在此期间,机会公平度可能会不断提高,不同阶层、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显著的转变。但最终,新的精英团体也会出现,而且新的脱贫与致贫循环也随之开启。
有效的基层民主有助于减贫
基层民主运作漏洞百出,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尽管问题很多,但大多数穷人依然很看重民主,他们将民主等同于自由地投票、思考、说话、行动、抗议和工作。菲律宾San Dogon 一个讨论组中的妇女说“民主和自由是一体的”,“如果没有民主,我们就无法体验自由。”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地方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民主的效率。我们发现,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的确,在我们的研究中,基层民主差异的93%可通过国内差异来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基层政治对穷人脱贫的努力有多么的重要。
理论上,能有效做出反应的地方政府在提供脱贫机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通过两个渠道提供脱贫机会:一个是促进社区整体发展,另一个是向单个个体提供帮助。它们能够提供良好的社区服务,如卫生、教育、法律法规等,这些有利于改善生计并鼓励穷人努力脱贫。地方官员还会向家庭分发政府的援助,如食物、农业生产资料、住房以及土地。此外,政府还能通过农业推广以及非农培训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
我们对民主实践能否产生上述良好效果进行了考察,想要知道地方民主与减贫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证据表明有效的地方民主可能有助于脱贫。我们发现,实际上,更有效的地方政府能更好地提供清洁水、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且,在这些社区,教育和卫生服务的质量得到了更大的改善,道路更加便捷,社区也更加安全。此外,腐败现象也少得多。然而,地方民主与个体脱贫之间的相关性相对比较复杂:在南亚一些地方,呈现出强正相关,而在另一些冲突不断的地方则呈负相关。
贫穷国家政府的惠民措施十分有限,加之精英的掠夺,穷人得到的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发展成了零和博弈:如果我赢了,你就要输。由此看来,穷人为了有限的资源竞争得你死我活就不足为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都可证明这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能够促进地方民主的方式很多。在我们所调查的社区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地方政府正变得越来越有效,说明转变是有可能的。转变的机制有推举优秀的领导、开展自由公平的选举、公开信息(特别是地方政务信息)、鼓励民众参与以及通过穷人的组织施加压力等。地方领导在拓展经济机会和实现经济自由化方面尤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结论最重要的启示是,减贫战略不能忽视地方政治,否则就会损害穷人的利益。要了解民主,就必须要关注地方层面的问题。通过建立自助性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哪怕其成员是文盲)来提出诉求,能够使地方政府官员更负责任。地方层面信息的公开,特别是有关地方官员和政务的信息,是使民主惠及大众的关键所在。
集体行动能够帮助穷人应对危机,但却难以实现致富
社区中的穷人常常会组合在一起统筹安排他们的劳力、资金或技术,但统筹的资源一般都很微薄。这种集体行动存在一个矛盾,即它能够使穷人维持生活并生存下来,却无法帮助他们实现脱贫。即使它能使成千上万的穷人通过组织起来实现互助,由于这些组织十分分散,没有实现有机的整合,还是不能形成规模优势。
讽刺的是,穷人的集体行动会使社会整体真正受益。在微小组织中的协作,加强了团结、信任、社会凝聚力并使人们获得了对比家庭更大单元的社会归属感。这培养了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对于建立运行良好、稳定且具有凝聚力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起点。
在被研究的各个地区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型的自发性的组织,它们虽然有利于穷人,却没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穷人的组织都缺乏资金、资产、教育以及市场经营技能,而且与富人和当权者的关联较少。当穷人仅将自身组合起来时,可利用的也只是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源。穷人们对这些制约因素也清楚,也承认“一个饥饿的人很难养活另一个饥饿的人”。挑战在于如何拓展地方这种互助的传统,从而使他们打破社会界限并与那些能带来新资源、新理念和新技术的人群建立联系。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在实践中,绝大多数人都依赖离他们最近的组织体:家庭。在印度2700个受访者的生活经历中,家庭是人们提及最多的积累资产能够依赖的组织体。人们认为从家庭中获得帮助要比从类似政府这样的公共机构、民间组织以及私人部门更为重要。所有四类家庭群体——脱贫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家庭、长期贫困家庭和从未贫困家庭都是如此。
鉴于这种依赖亲属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对成功家庭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他类型组织(从小组到合作社再到穷人组建的股份公司)利用这些特征的途径。我们选取几个取得大范围成效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如孟加拉格莱美银行、印度安得拉邦妇女自助运动以及印尼社区发展项目(在半数以上的村庄实施)。
很少有人提及非政府组织能帮助穷人脱贫,它所提供的帮助在人们所提到的所有促进脱贫的因素中仅占0.3%。但这并不能说明非政府组织没有去做事情,只能说它们的工作只影响了一小部分穷人或它们对脱贫没有直接的效应。穷人的集体行动具有通过将贫困的生产者与市场联系起来并帮助他们占据价值链高端从而改善生活境况的潜能。但是,建立这种组织需要时间和金钱,且不会立竿见影,从而导致出现普遍的投资失败现象。在思想和实践上进行这样的转变很不容易。需要了解地方实际和整合社区力量办法的人与那些拥有资本、商业技能和市场通道的人组合起来。只要这两类组织——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穷人就会始终被排除在市场之外,重要的创新,如建立穷人的企业以及改造主流商业模式进而更加公平地获取收益就不会出现。
减贫应吸取穷人的经验
总的来讲,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从事按日计酬工作、耕种小块土地或经营小生意的妇女、男子和年轻人,都不缺乏努力工作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他们中有些人成功了,但有些人却没有。然而,绝大多数深陷贫困的人们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仍然对自己和子女未来更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我们的研究对象都否定了那些把“穷人”看作一个无法实现自助的群体的认识。穷人并非都是懒鬼、酒鬼或笨蛋,他们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并且尽力抓住出现的每一次机会。事实上,本项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并不存在“穷人”这样一个固定的群体。贫困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永久的身份。
鉴于现有减贫措施的不足,在我们结论性的反思中,我们提出了在今后减贫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这些原则源于成千上万接受过我们访谈的穷人自己提出的经验。
第一个原则是所有的行动都应旨在扩大穷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空间。穷人有需求,但是仅仅强调他们的需求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愿望、梦想、志向和技能,也即剥夺了他们自助的能力。穷人的能动性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通过穷人的组织)都十分重要,当穷人的组织形成规模并与市场和公共部门实现对接时,穷人就会成为做出对其生活有影响决策的重要一方。
在所有研究地区,我们都被穷人始终对市场所抱有的信心所打动。尽管进入市场有重重阻碍,他们仍然相信市场将会发挥作用,并希望能够公平地进行交易。由此,第二个原则就是所有的行动应寻求改善市场运行机制,让穷人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几个关键的措施:拓展穷人的生计并将其有机地整合起来;加强交通、通信、电力和灌溉设建设使其与市场联结起来;降低获取生产性贷款的难度;提供市场信息、经营技巧和技能使穷人进入主流市场。
同样地,穷人也仍然相信政府以及地方民主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并希望参与其中。自由和民主都具有天然的重要价值。因此,第三个原则就是运作良好的基层民主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我们看到过很多地方民主失效的案例,地方层面常常由于权力的滥用、腐败的蔓延而沦为零和竞争,一些人的机会必然会成为另一些人的阻碍。但是如果有优秀的领导、公平的选举、公开的信息。民众参与和集体行动,就能够使穷人有能力要求地方领导更好地履行职责。 从而促进自下而上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发展。
概念框架
我们的研究从几个泛泛的问题开始:是什么原因导致社区中的一些穷人脱离贫困,其他人却仍然深陷贫困之中?社会关系在脱贫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心理因素和个人能动性到底有多重要?地方民主是否能带来不同的效果?
减贫源泉来自于数以亿计的人们及其家庭为改善生活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种植新的作物、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进入新的市场、创办自己的企业、获得就业机会或是外出务工等等。他们采取这些行动源于他们的自信能动性、抱负和力量——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也知道自己有能力取得成功。
这种努力也体现在集体行动中,从集中劳力和储蓄共同参与市场销售到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合作社。穷人和富人都可以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组织与网络来协调行动,但通常都是与自己人合作,即穷人与穷人,富人与富人。有时,穷人和富人的利益也会一致,因为他们要解决涉及社区整体利益的问题。而在有些时候,他们会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和利益而展开竞争,穷人的集体行动可能会遇到富人的压制。
现实中,大多数地区都存在阶层、种族、性别、宗教或财富分化的现象。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也会出现同样的分化,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产生“持久的不平等”(Tilly,1999)。在所有研究地区中以及所有研究主题上,我们都发现社会分层是影响人们行动与机会的一个制约因素。
经济行动,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能否改善人们的境遇取决于可利用的机会是否存在并能否抓住它。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整体的繁荣对减贫的进程影响巨大。然而,我们研究的首先不是国家政策与贫困的关系,我们仅关注地方层面。在地方层面(小到村),各种各样的机会是如何影响贫困变迁的?经济机会的公平性——即所有的人是否都能够有效地参与经济竞争——在地方层面进而到国家层面是如何影响减贫的?
在政治领域也一样,人们也会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参与其中。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地方。只有参与到一个开放竞争的基层政治进程中,才能获得并影响政府的服务与支持。穷人个体可通过选举参与其中,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表达共同诉求方面很重要)也是成功参与的关键,对边缘化的群体来说尤为如此。进一步说,政治机会的分布格局对基层政治促进或阻碍穷人改善自身状况影响很大。我们关心的是选举责任的效力、政治庇护主义的存在以及参与公共决策机会的公平程度。在参与公共决策机会的公平程度方面,对妇女的歧视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指标。
当然,在现实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且相互交叉的。政治权力可能会阻碍或拓展经济机会,而经济成就也能增强权力并影响政治。
穷人从未放弃,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与各种企业、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以及相关的公民与政府——与我们一道协同努力来促进自身及社区的发展。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与他们一道再次努力呢?
脱离贫困陷阱:2008/2009年度长期贫困报告综述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过去5年间,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陷入长期贫困的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地增加。大约3.2亿到4.43亿人仍然被持续多年甚至终其一生的长期贫困所困。他们的后代如果能够长大成人,多半会继承这种长期贫困。许多长期贫困人口会因一些易于防治的疾病而过早地死去。对于陷入长期贫困的人们来说,贫困不仅仅是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还包括许多方面面临的现实困难——饥饿、营养不良、饮用水不安全、基本卫生服务缺乏、社会歧视、人身安全无保障以及社会排斥。不管用何种方式来阐释长期贫困问题,如生活困苦、脆弱性突出、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权无保障以及身份低微等,有一点很清楚,普遍的长期贫困存在于一个具备消除长期贫困所需知识和资源的世界。
本报告认为,消除长期贫困是目前全球范围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具有基本的道德意识的话,就肯定会认为长期贫困人口应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为之付出努力。如果我们想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应将解决长期贫困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解决这一问题也有现实的需要,即如果我们越早地消除长期贫困,我们付出的成本就会越低,而获得的成效却会越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缓减长期贫困能给公众带来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公共卫生改善等方面的收益。
长期贫困人口有时难以识别,他们多数都是“工作中的穷人”,只有少数无法进入劳动市场。具体来讲,他们包括:(1)受到歧视的人群;(2)社会边缘人群;(3)特定种族、宗教和阶层人群及土著居民;(4)移民和包身工;(5)难民及无处安身人员;(6)残疾人;(7)病人;(8)年轻人及老年人。在很多情况下,贫困的妇女和女孩最有可能陷入终生贫困。尽管各类人群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仍可确定导致长期贫困的5个重要因素:
1. 不安全。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通常没有保障,资产不足和权利缺失使其难以抵御外部冲击和生活重压。其应对之策常常是以牺牲长期发展——如资产积累或子女教育——的代价来换取短暂的生存。
2. 公民权利缺失。长期贫困人口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出头。他们所在的社会及承担社会管理职责的政府通常会忽视他们的基本需求与权利。
3. 空间条件差。地处边远、特定自然资源条件限制、政治排斥和经济融合弱是造成一国内部空间贫困的主要因素。有时候,整个国家的空间条件可能都很差(我们称之为长期贫困国家)。许多城市地区虽然拥有潜在的空间优势,但由于公共服务缺乏、犯罪率高、生存条件差而依然处于极端窘迫的境地。
4. 社会歧视。受阶级、阶层、性别、宗教、种族、年龄等因素制约,长期贫困人口的社会关系——权力、外部资助、竞争、合作和支持——一般会使他们陷入被剥夺的境地或无法获得公共和私人产品与服务。
5. 就业机会缺乏。在那些经济增长水平低以及增长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地方,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而且人们更容易受到剥削。这些工作机会仅能维持日常的生存,无法提供资产积累和子女教育所需的条件。
对应这5个因素,本报告给出了5种应对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与导致长期贫困的因素并非一一对应,而是通过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政策框架来消除导致长期贫困产生的各种涉及多个方面且相互交叠的因素。
人们应当优先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政策领域采取措施,它们在长期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首当其冲的作用。与之相辅,实施消除歧视、赋权于妇女、构建个人和集体资产以及鼓励城市化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将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就会直接缓减长期贫困并形成一个持续努力消除长期贫困的公平的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这些社会契约能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合理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在这份全球报告中,我们努力提出一些能在许多国家发挥实效的政策建议。然而,正如本报告所示,消除长期贫困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措施。尽管本报告纳入许多案例研究来介绍特定国家的状况,但我们仍然使用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对不同国家进行了划分。通过对131个非经合组织国家进行聚类分析,我们确定了4种类型的国家集群:
·长期贫困的国家
·部分长期贫困的国家
·部分持续改善的国家
·持续改善的国家
尽管各类国家减贫模式所产生的效应好坏兼有,但显而易见的是,东亚、东南亚、中东、北非、中南美局部地区在消除长期贫困方面起步或初见成效的进程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突出一些。
在所有样本国家中,长期贫困国家儿童死亡的比重(36%)、婴儿死亡的比重(30%)和一天一美元贫困人口的比重(17%)相对于其总人口所占的比重(10%)要高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
相反,在持续改善的国家中,儿童死亡比重(6%)、婴儿死亡比重(11%)和一天1美元贫困人口比重(22%)要比其总人口的比重(33%)要低得多,并且一直在下降。此外,国别轨迹分析显示,长期贫困国家的数量正在增加,而持续改善国家的数量则在减少。
对长期贫困国家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一些国家已深陷“贫困陷阱”。超过80%的长期贫困人口生活在完全和部分长期贫困的国家,如果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外,这一比例将上升到90%以上。我们认为,长期贫困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框架来使自己摆脱困境。
政策和政治挑战
要满足长期贫困人口的需求和权利,需要采取两种互相联系但形式完全不同的政策措施。就短期而言,为使长期贫困人口及其子女的生存得到保障并使即期发展前景得到改善,需要采取实质行动满足其最紧迫的需求并为其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在政策上做出调整,筹集额外资源并有效地为其提供各类服务。就长期而言,要改进社会和政治制度,给予长期贫困人口发言的机会并支持他们的要求,这需要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这一过程比较复杂,本报告把它称为在国家层面上培育公正的社会契约,并辅之以国际层面的相应转变,即从向远方的陌生人慈善捐款转变为替穷人争取公民权利。
采取实质行动有效缓减长期贫困的需求对当前的主流政策及决定减贫与资源配置优先顺序的国内外政治秩序都构成了挑战。要使长期贫困人口得到帮助,所采取的政策要超越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并直接向本报告所界定的导致长期贫困的5个因素发起挑战。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解决不安全和公民权利缺失问题的现代政策,并将解决其他三个长期贫困诱因——空间条件差、社会歧视和就业机会不足——纳入主流政策体系当中。
减贫战略体系(减贫战略体系在本报告中系一专有名词,英文表述为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简称PRSs)是能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已在使政策决策向实证(evidence-based)方式转变并更加注重对贫困的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一项对最近10个减贫战略体系(PRSs)的分析显示,总体而言,长期贫困人口仍然不为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们所重视。减贫战略体系(PRSs)中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长期贫困人口有益,然而,鲜有证据表明实施这些战略体系时曾对持久贫困进行过特定的分析或选择实施了专门关注长期贫困人口的政策。尽管社会保护在一些减贫战略体系(PRSs)中被列入日程,但如何使他们惠及长期贫困人口却还并未确定。实现公正和赋予长期贫困人口公民权并未包括在减贫战略体系(PRSs)当中,反歧视和性别赋权也仍是边缘议题,而且奇怪的是,城市化和迁移也很少提及。
虽然政策选择很重要,但资源配置和实施效率是决定政策是否发挥减贫效应的决定因素。这些都与支配公共政策及管理的政治体系有关。减贫战略体系(PRSs)应该是一个动员民众支持穷人和建立更公平社会契约的工具,然而,时至今日这仍未成为现实。在大多数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减贫战略体系(PRSs) 一般都被视为施惠者创造的产物。第三代减贫战略体系(PRSs)一定要被当成国家政治工程来看待,它要向社会大众开放正规的政治决策过程和非正规的空间及网络。
有争议的是,本报告发现那些对长期贫困做出最有效反应国家,往往缺乏开放的政治体系,例如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越南。这表明在那些实施“精英工程(elite project)”推动国家建设的国家里,建立公民与国家之间社会契约的需要得到了认可,使长期贫困更可能被提上政策议程。长期贫困人口并非简单地要求“获得好的政策”,还需要“使政策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人们要思考民主、选举和分权等现代意识之外的问题。
把社会保障放在优先位置
本报告重申和扩展了2004/2005年度长期贫困报告的结论。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助,在消除长期贫困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帮助穷人抵御各类冲击以及消除他们严重的脆弱性来解决无保障的问题,帮助他们保存和积累资产从而使其改善生计并提高生产力,同时,通过夯实穷人长期的生计基础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尽管私人部门、非正式部门和公共部门都能够提供社会保障,但由公共部门提供社会保障应予以优先考虑。原因有四: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传统的社会保护方式正在逐步弱化;
·新的私人社会保护来源,如外出就业汇款,很少能惠及长期贫困人口:
·在长期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事实上不存在私人保险市场;而在其他地区,这种私人保险市场也太过昂贵,长期贫困人口负担不起;
·全球化使最穷的人口面临着新的更大的风险——金融危机、经济重组、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全球变暖。
近些年来,指导设计社会保障政策的知识基础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通过系统性的监测和评估来建立这一基础至关重要。尽管这一知识基础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但对长期贫困人口而言,有两点尤为重要:
· 家庭而非个人应该被作为主要的瞄准单元;
·收入转移支付可以与其他形式的支持(儿童医疗服务、营养套餐、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资产转移)结合在一起来解决多元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
大量证据表明,社会保障是一个缓减贫困和长期贫困划算的方法,对国家而言能够负担得起,甚至在相对贫困的国家也能大规模地推广。有一些案例研究曾介绍过社会保障推动大规模减贫的更加广泛的方法。例如,在乌干达,社会保护正在培育和加强社会契约。
然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不仅需要良好的技术分析,也需要获取政治支持保证其得以启动、实施并顺利筹集资金。在许多国家,社会保护政策都是由主导性政党引入的,而非民间组织游说动员的结果。社会保障项目通常被看作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非捐助人对减贫的关心。这样,向政党及其“执行机构”提供合理的技术建议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行动,而且,这还需要与对国家发展目标的讨论相结合。通常,人们认为经济精英和中产阶级会反对社会保护,因为他们害怕产生依赖性和增税。然而,本报告所考察的大多数干预措施在开始阶段都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甚至随时间的推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政治支持。
目前,我们所具备的知识条件已足以起草2010年全球社会保护战略,争取实现到2025年完全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经济增长与长期贫困
关于长期贫困人口如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问题,目前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长期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很有限。他们常常居住在农业发展潜力很低且远离市场的地区。由于交通条件差,通信设施不完备,他们被完全排除在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之外。即便他们有机会进入国内或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也少得可怜。很多长期贫困人口以不稳定、低报酬、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为生,改善的希望很渺茫。他们努力工作,但由于受教育水平很低,资产严重不足,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有限,导致无法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极端的条件限制,经济增长能够改长期贫困人口生活的程度差强人意。
本报告总结了通过改变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缓减长期贫困效应的三个主要领域:农业、城市化和社会保障。 在有效提高农业减贫贡献度方面,本报告提出了3项措施:
·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基础设施能“增厚”地方市场,使地主、商人和雇主无法再将他们的价格强加给当地的劳工、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还能提高食品安全的保障程度,并降低他们外出寻找工作机会的成本。
·教育。它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改善那些在城市地区获得就业机会的外出务工人员的生计(并向家中汇款)。
·信息。一般来讲,长期贫困人口缺乏获得如就业机会、要素和产品价格以及新技术等方面重要信息的渠道。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是农业推广。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需要发动私人、公共和非政府机构的力量来来改善最贫困人口获取信息的渠道。
第二个核心是城市化。本报告认为,城市化不仅需要在政策上做出调整,还需要政策制定者们改变他们的思维逻辑框架。决策者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更激进且与时俱进的国家城市规划战略,而非将城市地区看作是通过各种有规划的控制措施(很少实施)来管理的分散的单元集合。这一战略将把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贫困地区与城市联系起来,促进贫困地区城市和乡镇的发展,解决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歧视问题。
第三个政策焦点是社会保障。在家庭层面,社会保障不仅能够帮助长期贫困人口改善消费,还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资产拥有量。在“落后地区”,社会保障资源的流入能够刺激地方市场,推动经济繁荣。
实施这些政策会面临诸多挑战——要在从其他项目抽调资源及筹集额外资源上做出抉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考虑短期的成本和收益,但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增长会带来飞速的社会变化,特别是通过城市化和迁移,而这些变化将会对长期贫困人口产生影响。同样,城市化和增长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可能会破坏一些人的生计并加剧经济不平等,从而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因此,这一方面的政策需要考虑对这些有害影响的管理和控制。
社会转型
社会秩序例如阶级、阶层和性别关系对长期贫困人口的生计、福祉和意愿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秩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当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比以往变化得更快,不过,所有国家最终不太可能变成完全一样。现有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导致长期贫困形成的三个方面的因素,使穷人永远是穷人:社会歧视、有限的公民权和不利的就业机会。
在减贫战略体系(PRSs)和类似的政策文件中一般很少提到推动积极的社会转型,但是,它是解决长期贫困问题的核心环节。长期贫困人口不仅需要“好的政策”,更需要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权利、表达意愿的社会。本报告提出了三个社会优先目标:性别平等、社会包容和能力增强。在促使这些目标实现的过程中,5个方面有效的政策要引起重视:
·初级以上教育;
·生殖健康服务;
·迁移与城市化;
·为社会活动创造支持性环境。
有一些实践案例指出了实施这些政策来帮助长期贫困人口获取权利并提高能力的具体途径,包括为在校儿童提供食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将转移就业纳入减贫战略体系(PRSs)、设置就业岗位储备(印度)和建立拾荒人合作社(亚洲及拉美)等。虽然推动社会转型可能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但这些事例表明,创新性的项目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消除暴力冲突,构建社会契约
暴力对所有国家的穷人来说都是有害的,在长期贫困国家尤为突出。贫困可能是诱导暴力产生——从犯罪到战争——的一个原因。不公正可能导致战争,但只在涉及商业投机时才会驱动战争的发生。同时,商业有时候也是内战的根源,特别是在矿产资源能够获得暴利的情况下。因此,消除战争与打击那些通过暴力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团伙有关。然而,就算这些“坏家伙”被铲除,也不一定就能换来和平。
降低政府脆弱性进而减少暴力和冲突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并维护一个社会契约,在这一契约下,政府采取行动——建立法律和秩序、提供服务和建设基础设施——降低民众的风险,民众则不断强化其对政府的义务(如愿意缴税支持政府各种行为的资金需求)。社会契约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确立了互相承担义务的框架,为个人通过纳税贡献自己的金钱来推进国家建设奠定基础。这样,国家就成为一个能切实帮助穷人的机构,而非一个抽象的实体。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特殊的财政制度来关注穷人及其需求。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契约就能与人们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诉求有机结合。
从历史上看,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契约存在诸多不同的模式,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有一个有效的包括税收创造在内的公共财政体系。这一点在脆弱国家尤其重要:新的领导者需要一个好的执政起点,就会实施一些“快速见效的政策”。这些政策大多与直接消除长期贫困领域的问题相关——如加强边远地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法律和秩序、提供各类服务和建设基础设施来降低人们的风险则是下一步的打算。这就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起了相互承担义务的责任机制并为个人愿意通过纳税贡献金钱支持国家建设创造了条件。此即为创建公民权的真正基础。
消除长期贫困
如果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够做出必要的政治承诺并相应地投入资源的话,在2025年前消除长期贫困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对于一些长期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一目标看起来似乎过于雄心勃勃,不过,退而求其次,就几个稳定且相对富裕但长期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孟加拉、中国、印度),在未来几年会见到比较快的成效。
虽然各国在实施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时要因地制宜,但目前有证据显示。各国及国际组织应首先在下述5个政策方面有所行动:
·社会保护:政府提供社会保护特别是社会救助,能够显著地降低长期贫困人口的不安全程度,并增加其融入经济增长进程的机会。
·为难以惠及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和初级以上教育可以打破贫困的代际转移,并对长期贫困家庭的发展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构建个人和集体资产:拥有资产能够增强长期贫困人口的个人(和集体)能力,一个家庭持有的精神、物质和社会资产越多,它在社会网络、交易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就越高。
·反歧视和性别赋权:消除社会歧视能够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契约并增加长期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
·城市化和迁移:在农村地区,长期贫困仍然非常普遍,在城市地区,长期贫困可能会更严重。因为这些长期贫困人口没能从城市化中获益,无法通过移民获得工作机会。长期贫困人口需要通过教育和反歧视来获得迁移的机会。人们需要采取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发掘城市增长的利益点,并允许农村贫困移入者获得一部分城市生产的收益。
为消除长期贫困,我们还需要调整国际上主导性的减贫模式——减贫战略体系(PRSs)和千年发展目标。
减贫战略体系(PRSs):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是需要:
·提供不同类型穷人更多的信息,并对各国长期贫困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由施惠者出台的政策文件转变为融入国家社会发展战略框架的重要行动指南;
·超越政策制定,根据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要求,来引导社会和政治变革。
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在2015年的时限上进一步拓展,充分整合各种力量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消除长期贫困的战略目标框架。这就要求:
·设立到2025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设立到2020年为所有穷人和脆弱群体提供基本社会保护服务的目标;
·设立到2020年普及初级以上教育的目标。
本报告对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不过,政策的改变一定要注意长期贫困人口在解决自身贫困方面的主体地位。今天,虽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长期贫困问题的存在,然而,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大众仍将他们视为具有依赖性且被动等待救助的群体。大多数长期贫困人口都在努力地工作来改善他们自身的生计及子女的未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他们别无选择。他们需要真正的承诺,辅之以具体的行动和资源投入,来支持他们的努力,使他们克服摆脱贫困、获得公民权利的障碍。
“1天1美元”贫困线的修订
(Martin Ravallion,陈少华,Prem Sangraula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
本文对1990年提出的用于衡量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绝对贫困水平的“1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做了首次重大的更新。我们发现在一系列新的国家贫困线中,仅仅当人均消费水平高于“1天2美元”时(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才会出现显著的经济梯度变化。我们建议将人均“1天1.25美元”作为新的国际贫困线。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问题比曾经预想的更严重。作者认为,相对贫困必定会在“1天1.25美元”以下出现。当平均消费水平超过2美元/天时,相对贫困的变化斜率为1/3。
一、 引言
大量的贫困测量文献认为,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对贫困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通常穷人认为的消费临界水平是指足以能够摆脱贫困的水平,而富人所认为的消费临界水平是足以避免成为穷人的水平,因此,穷人的消费临界水平很可能会低于富人所认定的水平。
在定义贫困的众多标准中,经济梯度能否用来反映国家之间以及特定国家内部的贫困状况呢?Ravallion,Datt和van de Walle(缩写为RDV)(1991)研究了当平均消费水平和贫困线都按照共同的购买力平价(PPP)(即货币转换率,目的是确保对商品的共同购买力)折算后,贫困线如何随着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通常偏低,而且很少或根本没有显示出经济梯度。然而,RDV还发现,当超过消费临界水平后,国家贫困线随着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急剧上升,富裕国家的弹性趋于1。因此可以认为绝对贫困(即贫困线的真实价值不变)与贫困国家更相关,而富裕国家表现更突出的是相对贫穷(即贫困线与收入中位数成比例)。
国家贫困线为什么有这种经济梯度呢?贫困线通常关注的是营养需求,而穷人和富人的营养需求往往很相似。因此,营养需求不是用来解释贫富差距的原因。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如果某人不是穷人),他的(传统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求观念就会相应发生变化,人们希望能够消费价格更高的食物(更多的肉类和蔬菜,更优质的粮食作物),有更标准化的饮食,有更好的衣食住行。从这个观点来看,贫困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概念,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能够摆脱贫困的消费需求取决于该社会中人们普通的消费水平。
那么我们应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的整体贫困程度呢?有人可能会利用每个国家都普遍贫困线(或特定国家人们所期望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衡量,但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具有相同消费水平的人之间的贫困差异。同时,将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一视同仁,还可能会分散扶贫最应该优先关注的内容,即提高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而且,福利经济学所普遍假设的个人福利取决于其自身消费水平也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绝对贫困线应该如何制家呢?在RDV之前,用于测量全球贫困的绝对贫困线已经有很多随意的制定办法。
受这些方法的激励,RDV和世界银行(1990)认为,应该按照最贫困国家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全球贫困。以RDV原先设定的国家贫困线为基础(Chen和Ravallion,2001),采用RDV和世行提出的新方法,使用每月32.74美元或每天1.08美元(按1993年的PPP)的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对贫困程度做了最新估计。根据该标准,2004年发展中国家约有1/5(约10亿)的人是贫困人口(Chen和Ravallion,2007)。
这显然是衡量全球贫困的一个保守估计数。人们几乎不能相信,按照最贫困国家的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世界上的)并不是事实上的穷人。这也就是说,除了为世界上最贫困人口而设定的贫困线外,并没有设定一条较高的贫困线,另一种情况是,假设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的生活水平来制定贫困线,那么这样的标准对于(可能)拥有95%以上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美国的生活标准对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如果有人认为应该用福利维度以及福利的相对剥夺来衡量贫困,那么相对贫困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Chen和Ravallion (2001,2004)提出了相对贫困测量的一些估计,如果一个人满足“1天1美元”的绝对消费标准,并且假设该国居民中超过1/3的人其平均消费标准也是“1天1美元”,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穷人,其中“1/3”这个系数完全符合RDV设定的贫困线数据(Chen,Ravallion,2001)。但是请注意,即使采用这种方法测量贫困,“1天1美元”线的准确定位也必定低于相对贫困线。
本文运用大量的新数据,来重新思考国际贫困线的设定问题。这些数据有两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2005年的全球国际比较项目(ICP)(World Bank,2008a),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新数据,该轮ICP数据收集(开始于1968年)是最耗时耗力的,同时也被期待数据质量能有大幅的提高。第二个来源是基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为本报告编写)得到的新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自199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借鉴了大量的特定国家贫困研究的数据,而这些贫困研究是自1990年以来在世行的ICP指导下已经开展的研究。
二、 社会主观贫困线
回顾文献,有关福利和贫困测量已经公式化为一个观点,即“社会主观贫困线”(SSPL)。SSPL是指如果某人的收入水平高于特定社会中假定的那个点,那么这个人就不认为自己是穷人;相反,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那个点,这个人就认为自己是穷人,这个点就是社会主观贫困线。SSPL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一个人对贫困的理解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生活水平,大量证据都显示出与该前提相一致。
SSPL也可以被假设为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下,社会对个体贫困认识的影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个体所处的环境会影响个体对福祉的看法,而许多文献仅(明确或不明确地)关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存在贫困的社会影响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家贫困线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就是社会主观贫困线(SSPL)。在更多情况下,贫困线是根据一系列的基本消费需求费用来估算,通常是以能够满足身体健康为标准的营养需求来估算。然而,在贫困实际测量中,选择贫困线参数的范围很广,而最终选定的贫困线很可能是社会认可的贫困线。事实上,如果任何国家的贫困线与SSPL间存在重大的分歧,那么该贫困线也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在制定客观贫困线时,最基础的概念就是SSPL。
我们假定,某国的贫困线就是该国的SSPL,每个人又都有一个基于其自身消费和收入水平(y)设定的个体贫困线(z),这种联系仅限定于特定国家。更普遍的是,我们假定z和y的函数形式仅限定于某一特定国家。我们更进一步假设,个体贫困线(z)和消费或收入水平(y)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国的整体平均消费水平(C),指标C可以用来描述个人主观贫困线的社会影响。我们用下列函数表示指标间的这种关系:
Z=φ(y,C)当y∈[ymin,ymax] (1)
为了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贫困线,我们对函数φ做以下三点假设。
(1)函数对于个体消费或收入y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是连续可微的,并且,消费或收入Y是严格增加和连续的,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是非下降的;(2)最穷的人认为自己是穷人(φ(ymin,C)>O),而最富裕的人认为自己不是穷人(φ(ymax,C)<ymax;(3)随着个体收入的增加,主观贫困的差距在缩小,即φ,(y,C) <1。这些假设意味着(根据中值定理)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SSPL(Z),可用明确的点来表示:
2=φ(Z,C)=f(C)
公式(2)表示社会主观贫困线z是个体贫困线(z)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的函数。
一个特例 :假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当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高于消费临界水平C*, 即当C>C*时,随着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的提高,个体主观贫困线Z(=φ(y,C))是严格上升的。当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低于消费临界水平C*时,即C≤C*时,个体主观贫困线Z取决于个体收入y,即C=φ(y,C)=φ(Y)。只有当社会平均消费水平C高于消费临界水平C*时,个人主观贫困才会影响。也就是说,非常贫困的国家生活水平通常很低,很少有人会有相对贫困的感觉。那么很显然,社会主观贫困线(SSPL)与平均消费水平(C)的总体联系可表示为当平均消费水平C低于消费临界水平C*时,即C≤C* ,(C)=O,表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是一个常数。在消费临界点所表示的社会主观贫困线Z*[Z*=f(C*)]必定低于国家贫困线。
三、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贫困线
RDV收集的国家贫困线包含33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了专门的、具体国家的、大多数的贫困研究成果,时间跨度为1980-1990年,显然,现在看来这组数据比较陈旧。
自RDV以来,借助世行的国家“贫困评估(PA’s)”项目,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越来越多,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了“贫困评估”(尽管在1990年可利用的PA’s还是非常少)。许多核心报告都出于国别的世行分析项目,每一份报告都描述了该国的贫困程度及贫困原因。特定国家的“贫困评估”是在与该国政府协商后开展,其中许多“贫困评估”都由政府来做。许多低收入国家也从事“减贫战略文件(PRSP)”的工作。尽管能够得到一些项目捐助者的资金支持,PRSP实际上是由政府来承担。“贫困评估”或“减贫战略文书”中大部分工作都包括贫困测量方面(包括贫困状况)。PA和PRSP通常都将会描述在每一个国家中贫困的含义(贫困状况、总的贫困统计以及随着时间变化两者的变化情况)。显然,“贫困评估”和“减贫战略文书”是取得有关发展中国家公认的贫困线信息的重要来源。
本文所用的88个国家贫困线的数据来源于最近出版的PA、PRSP以及其他资料中涵盖1990-2005年的数据。每一个贫困线给出的价格为特定调查年份的价格(用于贫困测量的计算),大约3/4的样本观测值来源于同一项调查。在其他情况下,如印度,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原有的国家贫困线进行了更新。
由于PA是世行的一个报告,因此会引发两个问题。首先,这些国家的贫困线可能会被猜测为是表面贫困线,而不是被每一个国家所接受的贫困线,因此引发对SSPL的质疑。然而,在制定PA的过程中需要(大范围地)与政府协商,当然包括关于制定最适合贫困线的讨论。因此,与RDV相比,新一套的贫困线更有理由被认为是国家贫困线,而RDV的贫困线大部分是用于学术研究。
第二,世界银行和减贫战略文件所使用的贫困线可能是偏向于世行的国标贫困线,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PA(和减贫战略文件中)的贫困线通常既有预先存在的国家贫困线也有派生贫困线,而这两种贫困线并没有明显地标明来源于世行“1天1美元”的贫困线,它们仅是适合特定国家的贫困线。80%的情况下,贫困线的设定使用“基本需求费用(cost of basic needs)”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食品贫困线是指消费一定食物量的支出,这里特指的是具体国家(或地区)所约定的食物能量需求量,常用每人每天2100千卡热量表示。同时还要加上“非食物支出”,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贫困人口的非食物支出而言,他们的食物支出(或有时是全部支出)近似于食品贫困线。这是制定贫困线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部分。尽管约定的食物能量需求很相似,但是有许多种食物可产生相同的食物能量,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表现出一些食物比另一些食物更受欢迎。对充足的非食品支出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在对贫困线参数设定的判断上,也可能反映了每一个国家对贫困含义的普遍观念。
我们使用2005年全球国际比较项目(ICP)中的家庭消费(PPP)将这些国家贫困线转换为当前的货币。2005年的ICP显然是对不同国家生活成本如何变化的最全面的评估。ICP收集的是特定区域中600~100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将146个国家(包括OECD国家)根据155个具有可比性的“基本项目(basic headings)”进行分组,价格来源于每个国家中的大量样本店铺的价格。根据2005年的ICP,将世界划分为6大区域,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产品清单,所有区域都参与了该项目,但拉丁美洲的参与率较低。
2005年的ICP比1993年的ICP有明显改善(1993年的数据用于全球贫困测量),主要体现在:参与价格调查的国家更多(2005年为146个,1993年为117个),调查方法更科学。新方法已经用于政府补偿和住房的测量中,该调整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生产率较低的公共部门中的工人(降低了公共管理、教育和卫生部门中服务的估算值),许多国家都进行了环比(通过全球价格与地区PPP估计相联系)。此外,2005年的数据是建立在更严格的监督、更准确的计算方法之上的,在ICP价格调查中,对于具有国际可比性商品质量标准的认定上采用了更加严格的规程。除此以外,用ICP数据(世行,2008a)对PPP的计算也采用了标准的方法,同过去一样,世行采用了双边费希尔价格指数的多边延伸。
每个国家都采用世行(2008a)的个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将国家贫困线转换为2005年的价格,88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不能用2005年的PPP进行调整(主要由于拉美的ICP的覆盖范围很低),其中一个国家(津巴布韦)的数据被认为不可靠。考虑到PPP的缺失和其他一些数据问题,我们得到了75条贫困线。图l列出了贫困线的密度函数(采用标准的kernel函数),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国家贫困线在每月19.05~275.71美元之间,贫困线平均数为87.59美元/月,贫困线中位数为60.81美元/月。

图1 74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线密度
尽管ICP是为了测量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商品价格,但事实并非如此。抽样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国家调查范围仅限定在城市地区。例如,在中国仅调查了11个城市,尽管样本也包括城市周边的一些农村地区,但这些地区并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的情况(Chen和Ravallion,2008a)。基于ICP样本信息,我们将下列国家2005年的消费购买力平价作为城市的购买力平价: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柬埔寨,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基斯坦,秘鲁,泰国和乌拉圭。因此,这些国家的贫困线是城市贫困线。
我们遵循RDV的原则,采用国民核算账户(NAS)中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PCE)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措施(更准确地说,我们采用“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个人消费支出(PCE)的样本均值为209.40美元/月(6.89美元/天,2005年不变价)。样本中有15个国家的PCE低于60美元/月,或2美元/天;最贫困国家是马拉维,人均PCE仅为1.03美元/天。图1也显示出人均PCE的密度函数,中间部分显示的不太分散,但是当分配越不公平时,PCE也变得越分散。
在国民核算账户中,可用相关调查的家庭平均消费或家庭平均收入来替换PCE。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贫困线的计算来源于同一项调查,所以国家贫困线和平均值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太真实,’但它们有共同的测量误差。例如,我们来看设定国家贫困线最流行的方法,其中食物支出根据国家(或某一地区)预先的设定值,而对非食物支出的补贴则是依据恩格尔系数。在调查中,非食物支出的低估将改变恩格尔系数并且使贫困线自动向下调整。测量误差将在贫困线和均值间产生一个正向相关关系。只要国民核算账户的测量误差独立于调查的其他变量,PCE将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然而,我们也要用替代的调查方法来做敏感性检验。

图2 比照平均消费水平的国家贫困线散点图
图2是根据调查年份的对数PCE绘制出的贫困线。图2表明,一旦平均消费水平高于某一临界点,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梯度。同时,也根据平均消费对数显示出国家贫困线的非线性回归。
对应于图2,图3使用调查的平均消费水平代替PCE,所用模式也类似于图2,但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贫困线弹性稍高,为0.804(t= 15.97)。

图3 比照调查均值的国家贫困线散点图
因此,PDV利用先前汇编的国家贫困线数据所作的模型类似图2,随着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贫困线也在上升,但初始弹性较低。因此,贫困国家主要关注绝对贫困问题,而高消费水平国家关注的是相对贫困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弹性到底多高才算是发展中国家。
由于存在食品和非食品需求,因此贫困线中的经济梯度是一个集合体,尽管我们只能用样本贫困线来量化该分差。通过将28个样本国家中的食品部分和非食品部分分离,我们得到了完整的数据。在贫困线中,食品所占平均份额为0.564(0.260~0.794之间)。我们发现,贫困线中食品在平均消费水平中的弹性是0.471(t=9.55),几乎是非食品的1/2,非食品的弹性是0.910(t=8.97)。
因此,尽管经济梯度中食品部分也占一定比例,但是在图2中表明,国家贫困线所显示的经济梯度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非食品部分(占全部弹性的60%左右)。贫困线的社会影响更多地是由非食品需求决定,而不是食品需求。
四、 国际贫困线的设定
利用新汇编的数据,我们来重新思考曾代表许多发展中国家“1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探索出与这些新数据相一致的一条新的国际贫困线。
所有样本国家(样本数n=75)的中位数贫困线是60.81美元/月,相当于每天2美元,而平均贫困线则高达2.90美元/天。图2显示的经济梯度意味着平均贫困线远远高于那些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
马拉维的贫困线(样本中最低人均消费支出)是26.11美元/月。然而正像样本中许多特殊点一样,这可能是由于较大的测量误差和国家特定误差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图2中所显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低PCE水平下变动较平缓,但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动。毫无疑问,所用数据以及制定国家贫困线所使用方法的不同是其主要原因:不同国家如何设定贫困线,存在着测量误差和选用方法的差异,这些可以被作为从福利映射到收入方面时的干扰项。在正常的经济测量中,自然会得出一些普遍观点。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的期望值,反映贫困线如何随着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动而变动。
我们所选的参照组是样本国家中人均PCE小于60美元/月的国家,包括马拉维,马里,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尼日尔,乌干达,冈比亚,卢旺达,几内亚比绍,坦桑尼亚,塔吉克斯坦,莫桑比克,乍得,尼泊尔和加纳,这些国家的PCE的变动范围从31.34美元/月到56.90美元/月,平均PCE为42.26美元/月(或1.40美元/天),PCE中位数为41.33美元/月,平均贫困线为37.98美元/月或每天1.25美元(中位数是38.51美元/月)。
在参照组中,1.25美元贫困线的变化非常稳健。如果仅关注一个国家而不是最贫困的10个国家,那么平均贫困线是37.27美元(1.22美元/天);如果关注最贫困的20个国家,那么平均贫困线是38.33美元(1.26美元/天)。不过,这些是非连续性的参照组。相反,如果我们重点关注贫困线按“当前货币”表示的、来源于相同的调查(而不是对较早的仅用来防止通货膨胀的贫困线进行升级)则平均贫困线仅上升至38.89美元/月(样本数n=11)。如果我们关注按当前货币表示的最贫困的10个国家的贫困线,那么平均贫困线为37.22美元/月。
为了使贫困线测量更完美,我们也提出建立相对贫困线,假定为每天1.25美元,当超过消费临界水平后,相对贫困线以1:3的梯度迅速上升。较低的1.25美元仅对15个最贫困国家有约束力,而贫困线迅速上升的点则为平均消费水平为1.95美元/天。该相对贫困线与图2(r=0.994)的拟合值以及与国家贫困线的数据(r=0.863)有很高的相关性。
五、 与过去的贫困线进行对比
绝对贫困线
由于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设定国家贫困线时所用数据及方法也在变化,新设定的贫困线与过去的国际贫困线相比较复杂。然而,为最贫困国家设定贫困线已经有很多实践。根据Penn World Tables(1985年PPP)。RDV使用了2条贫困线:其中之一是最贫困国家每周23美元的预测贫困线。用一条是通过分析6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泊尔,肯尼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而得到的较高的每月31美元的贫困线,该贫困线能够代表低数人国家的水平。用1993年的PPP,Chen和Ravallion(2001)用RDV数据中显示的10条贫困线的中位数得到了32.74美元/月或1.08美元/天的贫困线,结果显示与预测的贫困线非常相似(1.05美元/天)。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最具可比性的估计数是最贫困国家的贫困预测线。平均消费干净函数贫困线的对数回归值类似于Chen和Ravallion(2001)所做的33.76美元或1.11美元/天(2005年不变价)。正如上面所述,更稳健的一值是基于非参数回归所做的估计值,为37.16美元/月或1.22美元/天。因此,如前所述,15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为1.25美元/天。
很明显,新的国际贫困线1.25美元/天比以前的贫困线所代表的美元价值因此,按照1993年的美元价值折算,1.25美元/天仅相当于0.92美元/天,比Chen和Ravallion(2001,2004)所做的1.08美元/天(1993年PPP)低于1.25美元/天的贫困线相当于1996年的1.00美元/天。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仅仅对1993的贫困线按照美元通货膨胀进行调整,那么我们将得到的贫困线是1.45美元/天(2005 PPP),而Chen和Ravallion(2001)历估计的贫困国家的贫困线“1.05美元/天”按照2005不变价将调整为1.42美元/天,这些贫困线显然高于我们所估计的1.25美元/天的标准。
图4 国家贫困线按不变价修订
如果将一个特定的国家贫困线按照1993和2005的美元价值转换,我们就会看到PPP的巨大变化,72个国家的比较结果见图4。平均贫困线(1993年不变价格)是91.25美元(而2005 PPP的为87.59美元),贫困线中位数是66.70美元(2005 PPP的为60.81美元)。从图4中需要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的ICP往往意味着最贫困国家贫困线的美元价值下降更多(按比例计算)。这可从图5可选的PPP国家贫困线的密度函数清楚地反映出来(图中给出的是在1993、2005不变价格计算出的国家贫困线,并且按照美元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根据人均消费水平计算的15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线是44.19美元(1993不变价格),按照2005不变价格计算的平均贫困线是37.98美元。这可以被认为是2005年的ICP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PPP,而使得贫困线下降。

图5 国家贫困线密度(1993、2005年不变价)
为什么2005年的平均贫困线与1993年的相比要远远低于按照通货膨胀去行调整后的贫困线,原因有许多种,我们不能排除通货膨胀率误差的可能性,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由于1993年的PPP。1993年的ICP价格调查,界定可比较品时采用的标准较低,可以很容易地提高1993年的PPP。
相对贫困线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还用新的相对贫困线与Chen和Ravallion(2001-2004)的贫困线进行了比较,按照Atkinson和Bourguignon c2001)的观点,非贫困者必须既有一个绝对的最低收入,但又不是相对贫困的,这表示其收入要高于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k)。Chen和Ravallion选择贫困线等于1.08美元/天并且k=l/3作为非贫困者的界限,这与RDV设定的贫困线(1993PPP) 非常吻合
有关该贫困线,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相对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的弹性从来不可能为“1”(低于1.95美元/天时弹性为零,并且当平均消费水平C等于无穷大时弹性才趋于1)。这样我们所计算的相对贫困线就避免了过去设定和固定比例贫困线的一些异常现象。第二,Chen和Ravallion在设定相对贫困线时的消费水平略高于我们设定新贫困线的消费水平。Chen-Ravallion设定于相对贫困线是在消费水平为3.24美元/天(1993PPP)的节点处,而我们所建议的相对贫困线与消费水平的节点为1.95美元/天(2005PPP)。如果我们选择1.25美元/天与消费水平的1/3中的最大值作为相对贫困线(2005ppp),那么链接点将是3.75美元/天而不是1.95美元/天。个人消费支出在1.95美元/天与3.75美元/天之间的包括18个国家,这18个国家不再受绝对贫困线的约束。另外,如果我们使用1.20美元/天和消费水平的1/3中的最大值为相对贫困线(假定1.20美元/天是我们按照2005不变价格估计的平均贫困线,对应与1993年不变价格的1.08美元/天),那么我们发现其中的16个国家不享受绝对贫困线的约束。
根据新数据我们所做的国家贫困线认为,与RDV的研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相对贫困。这反映出我们早先发现的贫困线与样本国家平均消费水平之间的整体弹性很大,略小于1,类似于过去对发达国家所做的一些估计数。
六、 结论
原来设定“1天1美元”贫困线的目的是评估世界整体的贫困状况,采用最贫困国家中贫困的标准进行测量。我们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线进行了修订,利用了特定国家所做的世行“贫困评估”和“减贫战略文件(PRSP)”中的资料。将这些国家的贫困线采用一套新设定的消费购买力平价将国家贫困线转换为统一的货币单位,来源于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ICP)所做的价格调查。
我们发现,当平均消费水平高于临界消费水平时,不同国家的国家贫困线都趋于上升,但是,当平均消费水平低于临界消费水平时,贫困线的变化较平缓。这种模式符合我们将国家贫困线作为“社会主观贫困线(social subjectivepuverty line)”的解释,即如果某人的收入水平高于特定社会中假定的那个点,那么这个人就不认为自己是穷人;相反,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那个点,这个人就认为自己是穷人,这个点就是社会主观贫困线。
我们发现,2005年ICP价格调查结果显示了最贫穷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要向上修正。因此,简单地根据美元的通货膨胀水平向上调整旧的国际贫困线要远高于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而计算出的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为了与贫困国家的贫困线相一致,以真实美元价值表示的国际贫困线必须要根据较贫困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向下调整。我们建议根据2005年不变价格来设定“1天1.25美元”的一条新的国际贫困线(相当于1996年不变价的“1天1美元”的标准),该贫困线是15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人均消费水平线。总的来说,全球贫困线将趋于上升,因为购买力平价较大的比例调整主要是针对较贫困国家而言。
研究结果表明,与20年前相比,对相对贫困的关注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随着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贫困线也在提高,这些国家开始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在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的总弹性为0.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提出了相对贫困线,与国家贫困线的数据一致。相对贫困线最低值设定为1.25美元/天,该贫困线适用于上述参照组,但是后来根据1/3梯度的平均消费水平做了相应的提升,这与我们设定的国家贫困线数据非常吻合。
在Chen和Ravallion (2008b)的研究中,1981-2005年新贫困线测量涵盖了116个国家的675次调查,本文采用的是“1天1.25美元”(2005年不变价格)的新贫困线,在其他方面使用了类似的估算方法,如Chen和Ravallion(2001,2004)概述中所提到的。Chen和Ravallion也测试了选择贫困线定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并且提出了贫困线的估计值在1.00~2.50美元/天。
世界银行新贫困数据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启示
(Armin Bauer,Rana Hasan,Rhoda Magsombol,Guanghua Wan)
一、 引言
2008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新的世界及地区贫困评估报告。随后在2008年10月14日又发布了国别贫困评估报告。新的数据显示贫困人口较先前的估计有所增加。基于亚洲开发银行从25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人口的95.3%)获得的新数据显示:2005年有9.03亿人(占这25个国家人口的27%)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比早前估计的6.64亿人(20%)要高出大约1/3。此外,该地区大约9亿人属于中等贫困,也就是说这个地区超过一半的人口(即18.03亿人,精确地说是54%)生活在极端贫困或中等贫困中。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并非由于使用了更高的贫困线,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这是亚洲开发银行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新的贫困数据表明该地区想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未免言之过早。有趣的是,许多政府似乎都接受了新贫困数据的隐含意义,即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解决贫困和脆弱性问题。
那么,对亚洲开发银行新的“2020年战略”及其共享式增长的策略的意义何在呢?
二、 何种贫困线适合于国际贫困比较?
采用国家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
事实上,所有的发展中成员国都设立了自己的贫困线,贫困线反映了维持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所需的食品和非食品成本。可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最低生活标准依国家不同而不同。特别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中所包括的非食品产品和服务就越多,且越重要。因此,富裕国家的国家贫困线要高一些(见图1)。
结果是,基于国家贫困线的贫困评估虽然对于讨论该国问题来说很重要,却不能为地区的国别比较提供基础。对贫困进行国际比较,需要一个通用的生活标准来区分所有国家的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换句话说,选择的贫困线必须能够代表所比较的各国的生活标准,并且是一个恒定的临界值。这一贫困线即为国际贫困线。

图1 亚洲的国家贫困线:富裕国家的国家贫困线更高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08。
“1天1美元”贫困线
应该如何设立国际贫困线呢?1990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者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声称低收入国家的国家贫困线为全球和国别的极端贫困比较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基于33个样本国的国家贫困线,他们发现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能够代表10个低收入国家的国家贫困线,从而提议将之作为对极端贫困进行国际比较的通用基准。随后,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中首次采用并介绍了“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
1天1美元的贫困线是否定期更新
世界银行的研究者们对1天1美元的贫困线曾进行了几次更新。2000年他们依据1993年的价格,将极端贫困的国际贫困线更新为1天1.08美元。然而“1天1美元”这一由许多分析家得出的官方辞令仍然得以保留。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在2008年的3月,即依据2005年的价格将国际贫困线提高到1天1.25美元。
为什么1天1美元和1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本质上是一致的?
提高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会造成一种提高“门槛”的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更新都是基于最初的原则:1天1美元的贫困线是用来代表贫困国家的国家贫困线的。诚然,实践这一原则的程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获得发展中国家贫困线更好的数据来作为设立国际贫困线的起点。2000年的贫困评估是基于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PPP)比率,2008年的更新则是基于能够得到的最新的2005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比较数据。
(如果贫困线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为什么贫困评估的结果却显示贫困人口正在越来越多?
主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成本较先前评估显示的有所提高。因此,1美元能够购买的食品和非食品的消费量在减少。这也是亚洲开发银行积极参与的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特别是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成本比1993年国际比较项目所显示的结果要高。在参加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的146个经济实体中,中国属首次参加,而印度距上次参加也已经过了20年。
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成本?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亚太地区的协调机构,与23个国家的国家统计机构一起搜集并比较了1 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其中大约650种是家庭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产品的价格被用来计算家庭消费“购买力平份”(简称消费PPP)。消费购买力平价使我们能够在国家间对生活成本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从而在评估贫困的国际比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菲律宾为例,说明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的重要性
以2005年价格1天1.25美元贫困线为例,要计算在菲律宾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就需要将1.25美元转换成菲律宾比索,然后利用菲律宾2005年的家庭支出调查数据得出贫困人口的数量。与通常所想不同的是,美元转换成比索的过程充满了玄机,我们可能觉得使用市场汇率(计算)是很正常的,如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在2005年,货币市场上55.09比索能够交换到1美元,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普通家庭消费产品方面,美国的1美元和菲律宾的55.09比索具有相同的购买力。,由于受到国家间贸易程度、投资流、外汇投机以及官方储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汇率可能并不是反映不同货币在一个国家家庭消费物品和服务购买力的好的指标。事实上,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发现在家庭消费方面,美国的1美元与菲律宾的24.18比索具有相同的购买力。因此,在计算2005年菲律宾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时,应采用24.18而非55.09作为乘数来将1.25美元折算成比索。从而,对于菲律宾来说,2005年的国际贫困线就是1天30.23比索。基于这一国际贫困线,任何每日支出在30.23比索以下的人都被应该被划分为贫困人口。
对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更新的批评
世界银行的贫困评估,已经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正确的标准:1美元或1.25美元的贫困线都受到质疑,人们认为它们所代表的生活标准要么过高,要么过低,而没有理由不考虑其他的国际贫困线。1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代表了世界15个最穷的国家极端贫困状况,而许多亚洲国家都使用高于1.25美元的贫困线。事实上,正如亚洲开发银行2008 年的重要指标所透露的,在1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国家贫困线的均值是1天1.35美元,这些国家在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在4 000美元左右。因此很容易会想到以2美元(在2005年价格水平下)作为新的临界值。我们认为1天2美元的贫困线代表中等贫困。正如Chen和Ravallion指出的,1天2美元的标准能够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值。需要说明的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所使用的贫困线都已经远高于1天2美元。
穷人的能力:有人认为世行制定贫困线的方法过于武断。他们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国际贫困线首先应以“国际公认的单个个体具有确保自身不贫困的收人能力”为基础(Reddy,2004)。由此,对贫困进行国际可比性估测需要在每个国家确定单个个体具有公认收入能力/物品及服务篮所需的特定资源。然而,国际社会关于标准的贫困线并未取得共识,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各自的国家贫困线。人们在确定怎样才算是穷人这样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按照Kakwani(2007)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采取某种意义上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妥协。根据人类的一个基本需求就是获得充足的营养这一判断,Kakwani以确保充足卡路里摄入量的食物需求标准为基础来计算国际贫困线。
穷人的购买力平价:另一种批评与将国际贫困线转换为国别货币时所使用的购买力平价有关。特别是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标准,它以对各国国民账户家庭消费总量比较而得出的购买力平价为基础,即基于全体大众而非穷人的消费。这意味着购买力平价会受到极端贫困人口难以消费的那些商品的影响——例如摩托车和高级衬衣。此外,购买力平价也可能对某种特定的产品赋予了不合适的权重。例如,既然在穷人的总支出中食品支出占相当大的比例(通常比大众平均水平要高15%~20%),在进行贫困评估时,食品的价格就应当在购买力平价的结构中占有更高的权重。如亚洲开发银行在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中证明的一样,以穷人的消费模式为基础计算购买力平价并进行国际比较和贫困估测是完全可行的。此外,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还表明,与标准消费购买力平价相比,采用贫困人群购买力平价对本区域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亚洲开发银行的方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即在下一轮的项目中,预计在2011年展开,要收集穷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计算贫困人群的购买力平价。
三、 数据显示的结果
全球贫困人口增加
世界银行新的数据显示,贫困人口比之前预想的要多得多。据该估计,2005年全球贫困人口由之前所估计(基于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的8.7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6.1%)上升到14亿(25.7%)。以2美元的贫困线为基准,则有超过26亿人(接近发展中国家人口总和的一半)属于贫困人口。超过2/3的贫困人口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所服务的亚太地区。

图2 两次贫困评估的比较
资料来源:Chen和Ravallion,2008,PovCalnet。
大约1/3的亚洲人口属于极端贫困,而采用中等贫困线,这一比例则接近2/3
新的评估显示在亚太地区贫困人口从6.64亿(占所调查的25个亚太国家总人口的19.9%)增加到了9.03亿(占该区域总人口的27%)。另外,如果使用2美元的贫困线,则有8.99亿人属于中等贫困。这样的话,这一地区就有18.03亿,即总人口的54%属于贫困人口。在那些减贫较为成功的地区倒如东南亚,贫困发生率也比上次预测的要高(贫困率为17%,上次预测仅为10%)。
虽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增加,但减贫成就仍然显著
虽然新的数据显示贫困发生率更高,但减贫成就仍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中尤以中国为最。新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1981年的52%(19亿)减少到2005年的26%(14亿)。在亚太地区,极端贫困人口(1.25美元)从1990年的14.16亿(调查人口的52.3%)减少到9.03亿(27.1%)。
然而,全世界在减少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上并未取得成功。1981-2005年,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在此期间,中等贫困人口数量(即生活在1.25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人口)甚至增加了1倍,从6亿增加到了12亿。
亚太地区情况要好一些,2005年有18.03亿人(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54.O%)生活在1天2美元的标准线以下,比1980年(20.21亿)和1990年(21.49亿,占总人口的79.4%)要少大约2亿。很明显,在这一地区,增长分配和其他因素对于贫困的影响仍然有限,针对贫困的斗争远未结束。
只有少数亚洲国家能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收入贫困减半)
全球减贫的成就主要是由中国推动的,如果没有中国的努力,千年发展目标1(在1990-2015年间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减半)不可能实现。以1.25美元贫困线计算,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在1981-2005年间贫困率从40%下降到29%,这仍不足以减少整个世界的贫困人口数量。预测显示,只有东亚地区有能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即在1990-2015年间将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减半。这一地区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土库曼斯坦和越南。然而,如果将人口增长考虑进来,印度等无法将贫困发生率减少一半。此外,大多数国家的减贫成就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非21世纪,这要归功于当时亚太地区非常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东亚是减贫最为成功的地区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区域划分中,东亚地区仅包括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蒙古。在1981年,这里曾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如今这里的减贫成就最为显著:在25年的时间里,中国将生活在1.25美元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从1.25亿(84.O%)减少到2.08亿(15.9%)。虽然中国减贫的道路不太平坦,但中等贫困人口(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的数量仍然减少到36.3%(4.75亿)。此外有趣的是,从1980-2005年,在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贫困率也从44.5%持续下降到了1.7%。
东南亚在解决贫困脆弱性方面仍有欠缺
在1980-2005年间,这一地区成功地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1.93亿减少到0.93亿。然而,贫困的脆弱性问题却没得到可持续的解决。这表明不平等程度显著升高,减贫和社会发展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共享性。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分别将其生活在1.25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从71.5%和90.4%减少到21.4%和22.8%,而菲律宾仅从31.4%减少到了22.6%。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极端贫困人口,两国总人口中分别只有0.4%和0.5%属于极端贫困。对于这两个国家,2美元的贫困线更为实际:马来西亚的贫困脆弱型人口(2美元)从1990年的11.1%下降到2005年的7.8%,泰国则从30.5%(1990)和44%(1980)下降到11.5% (2005)。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在共享性方面仍然有限:2005年,印度尼西亚仍有53.8%的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标准之下,这一比例在菲律宾是45.0%,在越南是50.5%。
南亚仍然是最穷的地区
南亚的贫困现象仍然严重,总人口的42.5%属于极端贫困(旧的估计为30%),75.6%属于脆弱人群或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中。南亚的贫困程度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更为严重,不仅在于绝对数字更高,而且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更大。亚洲其他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于1981-2005年期间都在下降的同时,南亚却在增加,极端贫困人口(1.25美元)从4.7亿增加到了5.5亿,脆弱人口(2美元)从7.09亿增加到了9.78亿。在绝对数方面,孟加拉(生活在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1980年的0.4亿增加到2005年的0.77亿)、印度(从4.2亿增加到4.56亿)和尼泊尔(从0.12亿增加到0.15亿)贫困人口的增加尤为显著。南亚地区唯一成功的国家是斯里兰卡,贫困人口数量从470万下降到200万;在百分比方面,所有国家都呈下降趋势,只有孟加拉国例外,该国2005年生活在每天1.25美元以下人口的比例仍超过50%,高于1980年的44%。基于2005年购买力平价的新的数据与基于1993年购买力平价所做的估测有着本质的不同:(新数据显示该地区)贫困发生率都在上升,特别是孟加拉国(从30.3%到50.5%)、尼泊尔(从23.8%到54.7%)和斯里兰卡(从1%到10%)。根据新购买力平价估计的结果显示,印度贫困人口数量从3.36亿(总人口的30.7%)增加到4.56亿(41.6%),农村贫困发生率上升为43.83%(3.43亿),城市贫困发生率增至36.2%(1.13亿)。
中亚和西亚在倒退
在苏联解体前,中亚共和国和高加索国家基本上没有极端贫困现象是,1996~1999年,高加索国家的贫困率突升至15%,而中亚增幅更大,增至35%~40%。直到2005年,各国极端贫困现象才有所减缓,但情况各有不同:目前,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贫困发生率在1%~5%之间,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在12%~13%之间,而3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1%~39%之间。对这一地区情况相对较好的国家来说,可以使用2美元贫困线:除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只有1%~10%的人口收入低于2美元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这一比例大约为1/3,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略高于50%,乌兹别克斯坦则有70%的人生活在2美元以下。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区域划分中,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属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巴基斯坦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可能不为人知的成功,该国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22.6%。但是,如果采用1天2美元的标准,巴基斯坦则没有那么成功。2005年,巴基斯坦仍有60.3%的人生活在此标准以下,这一比例在1981年为91%。世界银行没有提供关于阿富汗的数据,但据估计,该国极端贫困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2%,中等贫困人口的比例可能超过了85%。
太平洋地区
世界银行的新数据仅仅提供了15个太平洋国家中2个国家的信息,即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77%。从1981-200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极端贫困(1.25美元)人口的比例保持在29%左右,脆弱人口(2美元)约为51%。东帝汶极端贫困人口和脆弱人口的比例分别从82%和93%下降到了44%和70%。除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外的多数太平洋国家都采用生活标准指标来测量贫困。专家估计,按约1天1.5美元的标准计算,该地区收入贫困发生率约在15%~30%之间。
一些国家虽然贫困率在下降,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在增加
在1981-2005年间,整个亚太地区成功地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第一部分贫困理论和贫困测量15.72亿减少到9.03亿,但若除去中国,成就会大打折扣——除去中国,亚太地区的贫困人口仅比25年前减少0.4亿。对于像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这样的国家来说,虽然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贫困人口的数量却在增加或维持不变。一项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比较显示(图3),尽管印度的贫困率从60%下降到42%,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却从4.2亿增加到了4.56亿。而中国则在降低贫困人口比例(从14%到16%)的同时,也削减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81年的8.35亿到2005年的2.08亿)。

图3 绝对数与百分率的对比: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2008年10月)的估计。
贫困和食品价格上涨
由于调查数据获得的滞后,这次评估不能将2005年以来食品和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对贫困的影响考虑在内。如果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亚太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可能会更高。最近的模拟实验显示,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通货膨胀的趋势可能会使贫困率升高3到5个百分点。这些地区的政府正在采取价格补贴以及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等措施来缓减这一压力,然而新的数据显示:整个地区的贫困率将可能增加。
四、 展望2020年
估测贫困未来变化趋势的重要性
预测未来总是存在风险。然而,预测贫困趋势对亚太地区的政策设计至关重要。例如,气候变化是导致干旱和沿海地区贫困加剧的一个主要因素。更一般性的,对贫困发生率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下面,我们将预测发展中的亚洲2015年和2020年的贫困状况。
增长预测
以2005年的情况对2015年和2020年的贫困进行估测,需要我们对202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如何转化为不同家庭人均消费的增长进行预测。我们考虑了如下几种情形:对于经济增长,我们假设,每个国家2008—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以该国过去5年,即2003-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幅75%的速度持续增长。这里有5个国家例外,它们由此得出的经济增长速度出奇的高(超过8%),或是出奇的低(低于2%)。除了它们以外我们计算得出的增长率与这些国家过去17年的平均增长率非常一致。接下来,通过将前者下调,我们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化为人均家庭支出增长,得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时调查所得人均支出均值增加0.6%的实证结果。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得到2005-2015/2020年家庭平均支出的估计值。
“ 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的分配方式假定
在预测贫困之前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即2020年的平均家庭支出在家庭之间如何分配。
由于一国内部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即使在确定增长率以后仍然无法预知2020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一种不可知的方法分别考虑人均支出分配的三种情形。第一种,假设2005—2015/2020年的收入分配情形不变(或更精确地,从可获得的家庭调查数据最近一年到2015/2020年)。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相对于2005年的基线来说是“分配中立”的。第二种情形是假设分配将更有利于穷人,即将中间40%人群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幅确定为经济增长均值,最穷40%人口人均消费增长比平均增长值快5%,而最富有20%人口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则比平均值小。我们认为这一情形下的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第三种情形是最富有20%人口消费支出增长比总增长率要快5%,中间40%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持平,最穷40%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则要慢一些。我们称这种经济增长是“有利于富人”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的分配方式之间蕴含的基尼系数差异平均值在3%左右。
到2020年,除非增长更具共享性,否则亚太地区将无法完全摆脱极端贫困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将带来最低的贫困率,有利于富人的增长将带来最高托贫困率。除东亚(在中国的驱动下)外,在有利于富人的模式下,到2020年,极端贫困的发生率预期仍将保持接近两位数(8.6%)。在贫困人口数量方面,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的分配情形将使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产生1.5亿的差异(即1.88亿和3.24亿)。在南亚,据预测从2008—2020年,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的增长路径会使1.25美元标准下贫困发生率产生5.5%的差距。对于中国来说,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将决定其是否能够完全消除极端贫困,还是继续遗留1 700万的极端贫困。
到2020年,因贫困而导致的脆弱性仍然是重大的发展挑战
即使在有利于穷人的最好的分配情形下,亚洲发展中国家仍然会有9.43亿贫困人口。当然,与2005年亚太地区有54%的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状况相比,这还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仍会有1/4的亚洲人生活在贫困中。
减贫不会自动实现——不能指望涓流效应,应当推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
虽然在预测这些数据时所使用的方法会被批评为过于简单,但它仍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提示,那就是尽管保持经济增长对于减贫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更具共享性增长的政策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实施更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政策。图5是在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情形下对贫困所做估测的示意图,该图显示分配方式对解决极端贫困来说尤为重要,尽管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对于解决脆弱性和中等贫困(2美元)来说可能更为重要。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表明,人口政策是减贫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其他一些政策如区域瞄准亦然。只有低收入的群体能够从社会财富(收入以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中获益,增长和社会发展才是共享式的。另外,共享式增长也要求公平分配增长的收益。因此,对于那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1天2美元贫困线是一个衡量其国家共享性程度的绝佳指标。减贫的进展不仅需要百分比的变化,更需要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从这个观点来看,亚太地区通过共享式政策而取得更大的减贫成效还具有很大的空间,因为目前该地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推动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即使它们不足1/3的人口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每天每人必须品花费超过2美元(如表1)。


图4 亚太地区贫困预测
图5 在有利于穷人和有利于富人情况下的穷困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2008年10月)的估测
表1 共享式增长:哪个国家的效果更大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PovCaINet数据分析。
五、 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启示
减贫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超过1/4(不少于1/5)的亚洲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1.25美元)中,超过一半的人属于中等贫困(2美元)。世界银行更新的数据显示千年发展目标(将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在许多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减贫对于亚洲各国政府来说仍然是巨大的挑战。随着在移民、老龄化、气候变化、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等方面新的发展问题的出现以及城市化、发展缓慢和世界经济开始衰退等因素影响,亚洲各国在对抗贫困方面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2020战略需要在减贫和共享式增长方面设定可行的目标
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将减贫确立为其机构业务的首要目标。2008年5月发布的亚洲开发银行第二个长期战略框架(2008—2020)(简称2020战略)确定减贫仍然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与新千年开始时不同,目前亚洲开发银行的业务及研究工作对直接减贫成效的关注有所下降,而且,对干预政策间接效益的精确监测和分析也有所削弱。作为地区性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需要找到新的途径,以更有效的方式促使伙伴国关注减贫和共享式增长。2020战略是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然而,将亚洲开发银行的投资、知识和政策与提高地区增长共享性程度联系起来的战略方向仍未成型。本地区各国正在不断地加强穷人居住区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更为综合的健康和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生计问题和气候相关的脆弱性;改造住房和贫民窟,并在具有增长潜力的农村地区发展小城镇;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政府与私人部门一起建立新的劳动力市场并配套实施培训和促进就业项目,为社会贫困阶层创造增收机会。亚洲开发银行应将业务和理论支持投入到伙伴国那些有利于穷人的投资及能力建设上。
采用新的贫困数据
亚洲开发银行通过2020战略更新其参与亚洲减贫和共享式增长进程模式的第一步将是在该地区采用新的比以前估计高很多的贫困数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亚洲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被世界银行纳入15个最贫困国家的行列当中。采用世行的方法对亚洲地区进行处理后,我们提出了亚太地区一个更高的贫困标准,1.35美元,于此相对,关于贫困得各种估测数据也会提高。此外,这一地区很多国家的贫困县都高于1.25美元。尽管在进行全球和地区比较时,我们建议采用这一标准来进行国家层面的讨论,但我们仍然建议使用伙伴国各自的贫困线并展示各国贫困线的等值折算因子以及根据国际贫困线(1.25美元)计算出来的贫困发生率。
转而使用1天2美元贫困线
超过一半的亚洲人口生活在1天2美元的标准以下。2美元贫困线是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均值。亚洲新兴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已经采用了接近或高于1天2美元的贫困线。2020战略也采用了1天2美元的标准,比1999年减贫战略更进了一步。2020战力使亚洲开发银行在推动减贫和实现共享增长方面的工作领域大为拓展,这意味着除了区域持续增长外,亚行将通过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机会参与增长和通过为那些被增长过程中落下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亚洲开发银行希望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减少本地区的极端贫困(1.25美元)和中等贫困(2美元)。
通过提高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社会排斥
贫困具有多维度性。1天1.25美元贫困线不能完全反映亚洲大多数穷人的生存状态。除了采用1天2美元贫困线外,亚洲开发银行可能会针对社会和环境贫困制定一系列指标,确保全体人民能够体面地生活。这些指标与千年发展目标更为一致。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7(环境千年目标),需要做进一步的提炼,以更好地从贫困的空间维度来反映环境贫困。
亚洲开发银行的成果框架也需要增加指标来进一步完善,以显示其对伙伴国收入贫困、社会贫困、社会包容和保护以及穷人的环境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考虑穷人的购买力平价
对各国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的方法也需要通过使用反映穷人消费蓝(数量、质量和产品选项)而非社会平均水平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作为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的一部分,亚洲开发银行已对16个亚洲国家进行了类似的处理。亚行——通过其经济研究部——希望其合作伙伴(特别是世行)在2011年对购买力平价进行更新时,采用穷人的购买力平价来测算本地区的贫困。
在确定具备实现有利于穷人增长潜力的地区时,加入地理维度的考量
穷人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其中有些地区具备实现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潜力,有些则不具备。亚洲贫困的另一个维度是移民,即穷人迁移到他们认为能够增加其收入的地区,通常是城市。我们建议将空间维度引入对贫困的研究,而不仅是城乡分割。亚洲开发银行在国家战略形成的过程中,希望能加强对项目合适地点的分析,并建议项目设计方向能够更多地倾向于贫困地区以及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例如,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投向穷人迁移到贫民窟之前的地区可能不会对贫困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针对贫民窟的更广泛的投资(要最大限度地进行住房建设、贫民窟改造以及城市规划,而非仅局限于提供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可能会更有效。
为穷人建立更好的环境
将地理维度引入共享式增长,可能会促进亚洲开发银行在环境领域的工作,而环境是2020战略5个核心的领域之一:亚洲开发银行将以影响低收入群体福祉的居住地为基础对贫困和脆弱性进行研究,来加强其“环境贫困”领域的工作力度。据此,贫困人口可能被按照居住在有利于穷人增长潜力和不具有共享式增长潜力的地区划分为两类。后者可能包括:(1)干旱地区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干旱和沙漠地区);(2)泛洪区的贫困人口(居住在频繁遭受洪灾侵袭的地区);(3)高山区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边远高地或山区);(4)沿海的贫困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依靠海洋资源生活); (5)贫民窟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劣质房屋内,受城市污染侵袭)。
尽管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地区,缺少收入机会仍然是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改善穷人环境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强。亚太地区在减少收入和社会贫困方面可能仍会不断取得进展。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当中,环境致贫将跃升为首要影响因素。据估计到2020年,大约70%(这一比例在今天是53%)的极端贫困人口和62%的中等贫困人口将居住在环境是致贫首要因素的地区。气候变化会加剧贫困,特别是在干旱地区和易受灾害侵袭的地区,而全球化因素(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以及移民)将加剧贫民窟的贫困。目前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仍然集中在环境领域,导致了对那些二氧化碳排放量高的大国和新兴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来阻止气候变化,然而,这些支持对减贫没有多大效果。在环境是致贫主因的地区,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在干旱地区、高山地区、沿海地区、泛洪去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而非遏制气候变化)项目,使增长和社会发展更具共享性。
此外,投资应更多地流向城市交通管理、住房以及改善低成本、近距离运输系统等方面,以解决贫民窟贫困人口面临的健康和拥挤问题,而不是针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援建公共交通设施。
制定减贫业务规划
2008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启动了新的2008-2020长期战略框架。之前,在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曾对1999《减贫战略》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以此为基础,亚行确定了其主要的发展目标。随后在第一个长期战略框架(2001年)中确立了实施减贫战略的具体执行计划。2008年5月启动的《2020战略》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整体规划文本,其中减贫战略/环境减贫战略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但是需要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二个长期战略框架一一即2020战略中进行重新阐释。
这一文件重申减贫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战略目标,并将其努力的方向重新集中到3个战略领域:(1)使本地区的增长和社会发展更具共享性(通过解决地区差异、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动员私人部门参与以及通过教育来提高人的能力等方式和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保障等手段);(2)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通过遏制气候变化、使用更为环境友好的技术、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和增强环境承载力等方式);(3)促进地区融合和合作。2020战略为增长、环境和区域合作设立了清晰的战略和投资指南,但是在如何促进共享性方面显得较为不足。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的减贫战略需要与2020战略相衔接,那就是阐述亚洲开发银行如何更为有效地使本地区实现共享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从而解决脆弱性和1天2美元贫困。
关注实施而非政策本身
改进后的减贫战略强调了调整政策研究与实施机制的需要。从21世纪早期开始,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大多数成员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运行良好的减贫战略。因此,是时候开始关注政策实施而非政策本身了。为此,亚洲开发银行更需要监测自身对于减贫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加入到成员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形成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曾引人事前影响评估工具,对所有投资项目都经过强制性的贫困和社会影响评估。然而,这种贫困和社会影响报告的质量常常受到质疑,而且并不总是被实施。新财务模型的引入以及对项目支持的强调使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在部门层次上应用有效的发展影响分析工具。《2020战略》中促进减贫的政策,将在项目和部门层次上,显著加强分析能力建设和对减贫效果的评估。
第二部分
环境、气候与贫困
环境健康为什么对减贫很重要*
(贫困一环境合作项目组)
环境健康主要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有关。2004年在哥伦比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低收入家庭把环境健康作为他们最优先考虑的环境问题,而高收入家庭中该比例仅为30%。这项调查还发现,低收人群体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往往更多地集中于洁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资源,这表明环境健康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被处于优先级考虑的范畴之内(World Bank,2006c)。
由Globe Scan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贫困国家的公众认为“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是指与环境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包括饮用水短缺。空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水质污染以及自然资源枯竭。相反,高GDP国家的公众认为雨林和荒野的消失、水污染以及自然资源损耗是最严重的环境问题(Miller,2004)。 而在哥伦比亚调查发现,高、低收入群体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有相似的反应(World Bank,2006c),穷人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是空气污染(74%),富人关注的是全球资源管理的落后(78%)。环境健康很显然是和最贫困、最脆弱的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们越来越关心全球性问题(加气候变化)会对当地造成什么样后果这样的大背景下,将环境卫生和减贫综合在一起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像气候变化这样的新出现的问题将为减贫带来挑战。极端气候(如热浪,干旱)的影响范围、发生频率、发生强度以及持续时间都将加剧一些国家的水资源短缺;也会对公众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尤其会影响到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并且也会对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严重影响到穷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
一、 读者群与目标
本报告是一些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通过环境健康的改善,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本报告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同时也面向发展机构构的工作人员和机构顾问。
该报告的主要目标包括:
尽管一些国家在努力强调环境健康对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将和贫困人口密切相关的环境健康问题置于国家发展议程中时,取得的成功仍很有限,本报告试图阐明这个情况。
本报告就如何提升环境健康问题对于贫困人口重要性的认识,并且把贫困人口更成功地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战略和计划中,开展合作以支持这些战略和计划的落实这两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二、 环境健康为什么是重要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都表明,应对环境健康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80多个重大疾病损伤中,环境风险因素占据着一席之地(Prüss—üstün和Corvalan,2006)。发展中国家承担着大部分的、由环境变化导致的疾病负担,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均健康寿命减少的年数是发达国家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都表明,应对环境健康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80多个重大疾病损伤中,环境风险因素占据着一席之地(Prüss—üstün和Corvalan,2006)。发展中国家承担着大部分的、由环境变化导致的疾病负担,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均健康寿命减少的年数是发达国家的
* 节选自《环境、健康及贫困-将环境健康至于国家发展规划当中》一文。
15倍(Prüss - üstün和Corvalan,2006)。环境变化是导致腹泻、呼吸道感染、其他意外伤害、疟疾病等疾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图1)。此外,Prüss - üstün和Corvalan(2006)估计,全球24%的疾病、23%的死亡人数都归因于环境因素,这些都可以通过环境改造(如提供安全饮用水、改善的卫生设施以及普及的卫生学只是)而得到预防。
全球现有的证据表明,缺乏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室内空气污染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两个主要风险因素,而受这两个风险因素影响的又主要是 贫困家庭的儿童和妇女。通过对死亡人数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Ys)的测量。环境对男性和女性健康风险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突出表明,贫困国家需要制定和实施环境健康干预措施,以改善安全饮用水的获得,提供充足的卫生设施,改善室内外的空气质量。
全球有11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26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水和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仍然很高(WHO/UNICEF,2005)。每年由污染水和恶劣卫生条件引发的腹泻病例达54亿例,死亡人数160万,其中大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Hutton和Haller,2004)。存活于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社区中的肠道蠕虫,已经使20亿人受到了感染。根据感染严重程度不同,肠道蠕虫疾病可能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生长迟缓以及学习成绩下降率(kbqv等,2004)。大约有600万人因沙眼失明,而该种疾病是由于缺乏水以及不良的卫生习惯造成的。另有2亿人感染了血吸虫病,20万人承受着严重的痛苦和疾病后果(UNICEF,2006),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中处于城市贫民窟、郊区或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

图1 与环境最相关的疾病
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虽不及公共污染严重,但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病例超过了150万,占到全球死亡病例的2.7%(kbq,2006)。在发展中国家,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和使用天然污染—“生物量”做饭。据估计,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使用固体燃料(生物质和煤)做饭和取暖,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Rehfuess等,2006)。由恶劣环境造成的健康负担使大多数脆弱性穷人受到了影响,其中主要是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妇女、残疾人和老年人。一半以上的死亡病例是室内使用固体燃料家庭中的5岁以下儿童(Smith等,2004)。在21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地区中5%以上的疾病负担是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在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中国、刚果、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在内的11个国家,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20万之多(WHO,2007b)。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受到室外空气污染,而妇女面临更多的是室内空气污染,因为传统上妇女在室内待的时间更多,靠近火炉。迄今为止,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最大的疾病负担落在5岁以下的儿童群体中(Smith等,2004),当面临2004)风险因素时,这些儿童更容易受到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Ezzanti等,2004)。
三、 环境健康和营养不良之间的联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与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营养不良不仅是由于食物摄入不足所致,更多情况是由恶劣的卫生条件和重复感染造成的(World Bank,2006d)。环境健康风险诸如不充足的水资源、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不良的卫生习惯,都会通过腹泻病和(间接的)营养不良影响儿童的健健康,而这又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认知学习和生产能力。
人口密集、营养不良比率较高的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假设环境健康、营养不良、疾病之间存在联系,世卫组织在2007年重新计算的疾病负担评估认为,疾病负担还需要考虑到与不充足的水源、不充足的卫生设施供给以及不良的卫生习惯相关的间接(通过营养不良导致的)健康风险因素的影响(Fewtrell和Pruss - ustun等,2007),世卫组织估计,当考虑到与营养不良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时,近7%的疾病负担是由于供水不足、不足的卫生设施供给以及不良的卫生习惯造成的(Fewtrell等,2007)。以该分析为基础建立的即将开展的研究将在国家一级范围内评估环境卫生风险(包括那些由营养不良导致)的经济成本。环境健康kbq营养不良间的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儿童生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World Bank 2008)。
四、 环境健康与贫困
本节首先探讨了贫困的概念,然后分析了贫困与环境健康的相关性,在最贫困国家,由环境因素诱发的疾病负担所占比例最大,同时,在这些国家中,最贫困人口所占比率又最高。以先前的减贫与环境研究中的“贫困与环境kbq(PEP)”(DFID,EC,UNDP and World Bank 2002 and ADB,CIDA,DANIM kbq,GTZ,Irish Aid,IUCN,SEI,Sida,SIWI,SDC,UNDP9 UNEP,and WHO,2006)为基础,本文假定贫穷应被视为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过程,环境健康有助于减少不同维度的贫困。联合国(2005)指出,“极端贫困包含诸如收入贫穷、饥饿、疾病、缺乏适当住房、社会排斥等多个维度,而提升性别平等、教育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涉及基本的人权,即地球上每个人都有健康的权利”。PEP减贫战略框架(DFID,EC,UNDP,and World Bank,2002)是基于在任可减贫战略都需要探讨的以下四个关键因素:
提高生活的安全性:是指贫困人口利用其资产和自身能力,使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降低健康风险:降低贫困人口、最脆弱人群(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陷入不同程度的疾病、残疾、营养不良以及过早死亡的风险。
降低脆弱性:降低来自于环境、经济和政治风险的威胁,包括突发性和长期性的不利趋势的影响。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减贫来说,提高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特别是由此为贫困人口创造新机会的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Cairncross和Kolsky(2003)强调了为什么环境健康对于贫困人口以及减kbq影响是重要的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贫困人口生活的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环境条件。
·由环境导致的疾病负担大部分会落在贫困人口身上。穷人更脆弱、更容易遭受环境疾病的威胁,他们对疾病感染的抵抗力较低,对环境健康的干预会降低健康风险。
·穷人往往对环境卫生服务支付的费用比例更高。在低收入地区,许多人是从水供应商处购买水,而水供应商卖给他们的水价往往要比官方为有住所的居民提供的水价高出10~20倍。有更多收入的人能够更好地获得水资源,从而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安全性。
·疾病是造成贫困的原因。当穷人生病时,他们失去了收入,甚至失去了工作,患有肠道寄生虫病的儿童可能会在其生长过程中及智力表现方面受到抑制。改善环境卫生可以减少穷人的脆弱性。例如,良好的卫生环境和适当的卫生设施是降低感染艾滋病几率的关键,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的卫生设施和良好的卫生条件也有助于减少艾滋病携带者的家庭成员的负担。
·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可带来更多的健康收益。主要收益往往包括:(1)节省时间;(2)较低的生活费用;(3)逐渐提高的性别平等(安全和尊严);(4)通过服务供给增加了生活便利性(循环利用,修建厕所等);以及(5)降低了日常生活的负担。这些好处会更好地促进健康,也会间接地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从区域来看,环境卫生影响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大部分贫困人口。如图2所示,用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Ys)测量,这些地区中最贫困的国家承受的环境疾病负担最高(也可参见图3)。2002年,仅占全球人口1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DALYs疾病负担的比例却是24%,占全世界由环境导致的疾病负担的29% (Pruss - ustun和Corvalan,2006)。5岁以下儿环境危害的影响最大,最有可能感染由环境引发的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环境健康问题尤为严重,儿童营养不良现象非常普遍。低收入国家中,超过1.47亿的5岁以下儿童长期营养不良或发育迟缓,超过1.2%亿的儿童其体重低于正常水平(World Bank 2006d,Svedberg 2006, Fewtrel等,2007)。

图2 环境疾病负担(每千人中的DALYs)
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贫困与环境关系(PEN)”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贫困和环境问题是两大类问题(即环境卫生和自然资源使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World Bank,2006)。影响环境健康最重要的方面包括:由于农村和城市地区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城市、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工业活动造成的水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尤其是在老挝和柬埔寨高原地区;以及在农业中使用杀虫剂造成的危害(World Bank,2006)。这项研究的另一项主要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当穷人意识到了污染会导致贫困,但他们的社区也没有能力或缺乏地方制度来获得服务或尽量减少风险。
A.不安全饮用水

B.固体燃料产生的室内烟雾

C.城市空气污染

图3 儿童期及孕期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负担(所选疾病的DALYs所占比例)
五、 城市和城市贫民窟
据估计,到2030年贫困国家的城市化每年将增加超过6 000万新的城镇居民。据联合国估计,未来人口增长几乎全部都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中。今天拥有最多农村人口的亚洲和非洲,预计城市人口将增加一倍,即从2000年的17亿增加到2030年的34亿。
贫困、环境、人口健康重叠交叉的地理位置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例如在贫民窟。不久的将来,世界上城市人口数量将首次与农村人口相等,其中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Lee,2007)。亚洲的贫民窟居民最多,达到5.81亿人,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居民所占比例最大(约占城市居民的71%)(联合国人居署2006)。居住在贫民窟中的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着多种环境健康风险,包括空气不畅通和低效率的炉灶,水和卫生设施的缺乏,劣质的住房结构和房屋建筑,室内的泥地面,拥挤,较差的、不足的和不安全的运输工具(Parkinson,2007)。
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城市贫民窟的无节制增加正在为城市贫困人口创造着一个双重的环境健康负担。这些贫困人口不仅要承受室内空气污染、拥挤、较差的水和卫生设施(通常与农村人口相挂钩)的风险,而且还要承担与运输和工业污染(Satterthwaite,2007)相关的观代化的风险。在世界一些地区,疟疾(和登革热)愈加成为一个城市问题(Breman等,2004),而这又由于气候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Campbell-Lendrum等,2007)。
环境健康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密集的城市人口对于各种服务的提供是一个机遇,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服务的成本效益以及快速提供服务的方式。相反,无视越来越多的、环境条件较差的、几乎无法获得任何环境服务的贫民窟的存在,会破坏城市政府努力提供的健康环境和改善卫生的成就。
六、 环境健康和经济增长
要使贫困得到减少、福利得到改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全部有利的影响,减少不公平是必不可少的(WorldBank,2006b)。通过投资和其他方式降低环境风险,能够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健康水平,并且有助于缓解不平等。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人们的生产力和生产绩效是息息相关的,而生产率往往受制于恶劣的环境卫生条件,而恶劣的环境卫生又会导致疾病,并因此使人们失去了收入,增加了医疗费用。这种由恶劣环境导致的健康问题给社会增加的经济负担可以用一国GDP的一定比例进行量化(图4)。例如,哥伦比亚每年由环境破坏发生的费用(包括水、卫生设施和卫生知识的缺乏,城市空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农业土地退化,自然灾害)超过了GDP的3.7%(WorldBank,2006c)。导致这一费用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供水、卫生设施以及卫生知识的不足,二是室内外的空气污染。同样,在印度和中国,仅由空气污染引发的死亡率和发病率造成的损失每年就占到GDP的2%~3%。图4表明,环境退化威胁着经济增长,而由环境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4%,这些费用绝大部分都由穷人负担。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事例中,把与环境健康和营养不良相联系而造成的影响进一步计算在内的话,这些损失的费用大幅增加至GDP的近9%(World Bank,2008)。

图4 与恶劣的环境卫生相关的经济负担(占GDP的比重)
疾病和不健康都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影响一个国家就业人口的生产力。据统计,在疟疾高流行国家,每年可导致经济增长下降1%似上(World Bankkanbuqing)。此外,对传染病的认知风险已经对投资、贸易以及种植作物的选择显示出负面影响。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减慢,也会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差距(Teklehaimanot等,2005)。
恶劣的环境卫生也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本的赤字,影响当前和未来的生产力。占全球环境疾病负担40%以上的5岁以下儿童,他们的认知和学习尤其会受到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据估计有2亿名5岁以下儿童,由于贫困、恶劣的环境卫生、照顾不周等原因,在认知发展方面难以达到他们应有的潜能。此外,重复疾病也伴随着对认知的影响,导致了适龄学童较低的学习成绩kanbuqing等,2006)。联合国营养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也证明了铁缺乏、kanbuqing缺乏、寄生虫疾病与较差的学习成绩之间的联系(Hunt和Peralta,2003)。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教育水平的儿童,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工作效率,并且也是代际间贫困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Grantham-McGregor等,2007)。
健康人群是有较高生产力的人群。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较高生产力的劳动力,打破贫穷循环必不可少的经济增长也将无法实现。改善环境健康将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和可信赖的经济增长。这部分内容将在后面章节中探讨。
七、 气候变化以及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最贫困的国家往往也最容易受到区域和全球环境退化的威胁。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2007)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未来气候变化会影响到以下各个方面:包括淡水供应、农作物生产力、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海平面上升以及健康等。具体来说,IPCC报告指出,由于贫困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低,对气候敏感资源(如食物和水)的依赖,他们对气候变化尤其脆弱。该报告还指出,数百万人的健康状况,特别是那些低适应能力的人群,将更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将表现为死亡人数、疾病,受极端气候变化伤害(例如洪水、热浪和风暴)的增加;腹泻疾病负担加重,以及一些传染疾病分布情况的改变等。
最近在WHO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Campbell-Lendrum等,2007)指出,当前重大的健康负担尤其有可能会因气候变化而恶化。从局部和全局的角度来看,扩大预防性环境健康的干预(如清洁水和卫生设施服务)对于减少当前的疾病负担是明智的投资,也是“无遗憾”的优良战略。作者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基础公共卫生保障的一项基本事情”,同时也指出有必要重新调整政治和财政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保护,能够对由于自然灾害和传染病模式变化引发的健康安全做出回应,采取更积极的做法,确保环境发展结果能够为改善人类健康这样的最终目标服务。
八、 减贫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是一组由国际社会认可的、关注到2015年使贫困人口减半。提高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福利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已成为建立发展目标和衡量工作成果的原动力。
改善环境健康问题的认识将直接促进对减贫与千年发展目标的认识,其中包括:(1)降低儿童死亡率(千年发展目标4);(2)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对抗(千年发展目标6);(3)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千年发展目标7)。同时它也间接促进了:(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2)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化;(3)促进两性平等。表1说明了每一个千年发展目标都包含有一个环境健康成分,环境问题处理的好,将有助于实现这一千年发展目标。
表1 千年发展目标和环境健康
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鼓励各国以“千年发展目标报告(MDGRs)”的形式,汇报每年所取得的进展。这些报告以全球发展目标和指标为基础,汇集了各国具体的目标和指标,便于各国将各自的发展情况纳入国家计划和预算体制中,而各国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例如,对于有资格通过“扶贫与经济增长融资(Poverty Reduction Growth Facility)”获得优惠贷款的低收入国家,以及有资格通过“高债务贫困国家(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倡议获得优惠贷款的低收入国家,都必须准备减贫战略文件(PRSP)(Klugman,2002)。而这些准备好的文件将作为一种手段将部门优先发展战略和减贫倡议融入更大的宏观经济发展框架中。减贫战略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国际捐助者和捐助组织支持减贫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
气候变化治理
(James Meadowcroft,世界银行)
本文将探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及措施缓解和适应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进行重点考察。
本文将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描述气候变化问题的总体特征;第二部分介绍施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所需考虑的先决条件;第三部分探讨气候变化治理的主要维度;第四部分展示这一领域最近的创新行动;第五部分提出了一些补充性结论。
行文之初需要对本文分析范围加以强调:
首先,本文的关注点是国家政治体和国内行动,而非国际组织或气候领域的全球管理体系。当然,我们的确需要在全球层面上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本文将讨论国内治理而非国际治理。虽然社会互动类型在不断变化,各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相依相存的程度在加深,一些国家政权也确实臣服于超国家制度,然而国家仍然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核心(Pierre和Pierres,2000)。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内法律,以强制税收的权力掌握着重要的财政资源,控制着裁决纠纷、分配资源和迫使服从的各种体系(Gill,2003)。代表机制和民主诉求使国家为其公民的公共财产采取的行动得以合法化。在国际层次上,也是国家来达成协议。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动员集体资源、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时,国家仍然是最强大的机构。
其次,本文主要讨论施行气候变化治理的过程和制度改革,而非具体措施kanbuqing碳税、温室气体排放管制、贸易体系等)的设计,更多地关注针对气候变化治理的整体机制,而非某些特定政策路径的优缺点。当然,具体的措施和路径也对公共体系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例如,实施碳税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内税务系统,而温室气体排放管制和贸易体系则需要适当的监管机制。
一、 气候变化对治理提出挑战
已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化(IPCC,2007)。虽然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仍不确定,但显然存在引发明显负面后果的风险(Schellnhuber等,2006)。要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需要在当前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减少年排放量。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讨论到本世纪中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然而如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呼吁规避的气候危机最终爆发的话,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就激增到一个峰值(Hohne,Phylipsen和Mohmann,2007)。此外,无论如何努力来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我们的社会都不得不在几十年内被迫适应业已发生的持续变暖。
减少国际排放量要求我们彻底改变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变意味着包括农业、运输、建筑、林业和能源等在内的主要经济部门的转型。这就需要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以及开辟新路径。在实现和加速向低碳发展路径的转变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每个国家仍有充分的自主权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气候问题。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措施,另一些国家却仍然无动于衷。随着气候变化已经和将会导致的影响的逐步加剧和越发的不可忽视,这种情况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得以扭转,国际社会在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以及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动)方面的共识也会不断加强。这并不是说富裕程度不同、排放量和排放历史也不同的国家应该在缓解气候变化中做出等量的贡献,而是指采取适当手段应对气候变化将会被视为国家层面“善治”的必要因素。一个政府要想得到其公民和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必须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展示决心。而采取切实行动的国家,也会无法忍受那些不愿分担共同使命的国家。
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愈发别无选择地需要推行针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而非仅仅是那些更具热情的国家、更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或是人均排放量更高的国家。
气候变化本身和针对气候变化的应对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国际经济问题:(1)国际金融流动;(2)贸易政策;(3)发展援助。例如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已经从调整关税的角度来限制从没有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地区进口产品。随着发达国家缓解气候变化的成本升高,而高碳排放的产业(及衍生就业岗位)向缺乏相关规制的地区转移,这个问题无疑会吸引更多关注。
这些事实警醒发展中国家尽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将可能危及其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墨西哥最近出台了排放控制目标,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果。海湾地区一些石油出口国在碳回收贮存(CCS)和可更新能源技术方面也有类似的尝试。
气候变化问题一些广为人知的特征,也对当前的治理机制造成了困扰,包括:
·社会影响。温室气体与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工农业活动密切相关。要转变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大幅降低排放量,并针对气候变暖采取必要的适应性行动,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生活实践。如此大范围地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在许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对于导致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有所了解,但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关于气候系统的敏感性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一定程度时,会带来多大程度的气候变暖);地区性的气候影响;以及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后果等。而目前的气候体系可能突发严重断裂的“突变点”也引起了关注(Lenton等,2008)。我们所了解的越来越多,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确定性仍会继续。
·分配和公平之间的联系。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都会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是可预见的,另一些则仍不确定。气候变化的“严重洗牌”改变了各国家、地区、企业、社会阶层和个人所面临的风险和机会,对政府而言,(国内和国际)公平问题一向非常棘手,而气候变化又雪上加霜(地区差异、南/北紧张、能源和贫困问题等)。
·长期框架。自工业革命以来,来自化石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升高:气候系统每十年、每百年、每千年都在变化;而控制气候变化是对本世纪的治理的挑战。这些长期性问题不能通过四年一度的选举周期,两三年的部长或高级官员任期,或是日常政治生活每天或每周的变化而得到解决。
·全球启示。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都是国际的。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其他联系更突出了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当然,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协调国际行动是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因素都使政府更加难以有效地管理气候变化。这些因素并非气候变化问题所独有,其他问题和政策领域也具备相似的特征,但鲜少同时如此凸显。
毫不意外的是,就管理气候变化而言,现有的治理结构和过程并不理想。现代治理制度中著名的宪法机制、代表制度、联邦结构、部门分立、职业官员、政策框架等,都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制度演变、各国之间互相模仿学习、反复汲取教训重新设计过程得以最终确立。在整个20世纪,OECD国家的政府活动更多地关注“安全”(秩序维持和公正管理)、“经济”(推动经济增长、货币稳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和“福利”(福利国家、公共物品提供、“社会安全网”)。而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政府过去60年的发展关注点始终是加速“发展”,即一个涉及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多维度进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环境治理的现代制度开始进入发达国家的视野,随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与政府架构中其他更为完备的部分相比,仍然显得很薄弱(Mead-owcroft,2009)。气候变化为创新和治理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文献中关于民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的重重困难有大量的讨论(Lafferty和Meadowcroft,1996;Eckersley,2004)。有证据表明,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其阻碍因素包括:政客在启动可能影响投票的改革时(例如征收更高的能源税)难免犹豫;政治领袖会倾向于反对其政敌倡导的更严格的措施从而吸引选民;强大的经济体能够施加影响保护其既得利益,抵制变化;多“否决点”和制衡原则的存在延长了决策过程;以及媒体在简化和分化辩论时的自相矛盾,等等。
这些现象都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它们的良好运作对更有效地施行气候变化治理非常重要。而另一方面,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气候领域的表现区别究竞有多大,这种区别又究竟有何意义,此刻尚不明朗。上述现象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而政治和行政过程也常常会造就反常的结果。当然,类似的过程在非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只是以隐蔽的方式。从长期来看,非民主国家政府也需要关注其政策对公民的影响。政治和政策竞争在任何国家都必然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需要谨慎对待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气候政策绩效对比的结果。一般而言,要想对政策变化进行研究,所需的最短期限是20年(Sabatier,1993),而针对气候变化这种长期性问题进行研究,所需的期限会更长。此外,由于根本不存在致力于减排的非民主的发达工业化国家,那么得出普遍性结论所依据的案例明显有所欠缺。
关于民主政治体系优越性的论调说明民主并非能够永远进行明智的决策。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民主体系的灵活性、适应性、选民和政客从过去政策先效中汲取经验的能力都不容小觑。选民会牺牲短期经济利益来支持某一政策以谋求长期收益和集体价值。如20世纪70年代关于“国家财政危机”(O’Connor,1971;Offe,1982)的大规模讨论,其动因就是政党的漫天许诺,刺激了选民要求昂贵的公共服务的呼声。那次事件最终并未导致政治垮台。选民逐渐意识到政府支出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而长期赤字会引发通胀,政客们便成功地使选民接受以减少公共服务和削减公共开支的“短期疼痛“换取“长期收获”。
不同的政治体系是以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为基础的,所以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任何成绩都会在短期内使政治形式变得更民主或是更专制。然而无论如何,更长时间内在管理气候风险方面的政府失效,无疑会导致政治不稳 定和政权更迭。
与考察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差异相比,同一类型国家之间的绩效差异更值得关注。例如,某些发达国家近年来通过出台政策减少了排放(德国、英 国,瑞典),另一些发达国家则没能抑制排放量的增长(加拿大、美国)。政治体系的特点(选举和政党结构、总统和议会构成形式、联邦制还是统一制等) 会对利益表述、政治竞争、政策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但如何影响气候领域的行动,是支持还是反对采取措施,取决于诸多特定条件。结构性经济因素、行政和;立法实践、观念(例如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分化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从结构来看,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出口工业的国家在减排方面缺乏热情, 在采取可更新能源方面也更犹疑不定。以瑞典和挪威为例,二者有着相似的政会传统,对气候变化都保持着高度关注,也都积极参与了国际气候公约,然而瑞典在摆脱化石燃料依赖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挪威则不然。此外,有证据表明有着共识性政治文化(反对冲突和诉讼)及国家干预推动集体工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法团主义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L’affierty和Meadowcroft,2000;Duit,2008)。
因此,与评述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各自的绩效相比,从整体上考察有利于积极气候政策的机制更具建设性。当然,任何机制都必须根据一国特殊的制度条件进行不同的调整。
气候变化治理仍然是个新课题。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启动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体系,但该领域的政策实践不超过15年。而适应性行动则更是全新的领域,人类社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验各种方法的优劣。关于气候变化治理,仍然没有成文的规则或公认的“最优策略”指导手册来传递经验。所以,本文将围绕核心概念和实践案例展开讨论。
二、 气候变化治理先决条件
在进一步深入审视气候变化对治理的影响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三个问题:适应和缓解之间的联系;不同发展程度对气候变化治理提出的不同要求;能源和毁林的极端重要性。
适应和缓解
气候变化治理需要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适应和缓解。适应是指随着不断 变化的气候条件,对人类社会进行调整。而缓解则要求我们改变目前的行为方式,停止导致气候进一步变化的活动。二者缺一不可。我们需要适应,是因为气候变化已经发生,而当前的排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气候持续变暖。而我们必须缓解,是因为适应不可能阻止气候变化。除非实质性地减少排放,否则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还会继续增加,而全球气温也将持续升高。
在适应方面的治理需要能够预测地区和地方层次上的气候影响,从而进行规划,应对其对人类行动的预期影响。随着气候不断变化,所需的适应性行动也在变化。科学报告中列举的重要的气候问题包括海平面升高、极端天气事件、温度波动以及降水变化等。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流失严重。这些都可能会改变人类的迁徙、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巨大的、激增的经济损失;直接威胁人类的生计和福祉(Stern,2007)。在压力面前,最贫困的国家和最贫困的人群将暴露出最严重的脆弱性,他们最直接地依赖自然资源系统(如农业)维持生计,而在变化来临时能够支配和动员的资源却最少。
成功的适应需要具备以下关键要素:对地区和地方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对气候、生态系统和社会影响进行系统监测;在长期规划如基础设施和主要社会经济部门规划中加入气候问题的考量;针对预期的气候影响进行公共教育,鼓励个人和集体的适应性行为(改变耕作方式、采用新品种等);开展关于气候变化影响和可行的社会调查方式的社会讨论。
而所能采取的具体治理措施则包括:要求通过国家、地区和地方规划过程(如土地利用规划)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根据适应性行动和长期适应成本的预测值准备周期性的国家和地区报告;与相关利益者一道通过以地区或部分的单位的适应性行动论坛,探讨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对策;与保险业通力合作瞄准脆弱性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在保护地规划以及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计划中,加入关于气候适应的考量;将适应性议题纳入研究经费预算等。
而在缓解方面的治理则要求掌握排放的源头、经济的减排措施和政策对策。有许多可行的政策手段都能够促进减排,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方案的设计本身,而在于实施这些方案的政治意愿。对有志于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实现减排的国家而言,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成本会刺激低碳经济。即便在缓解气候变化的可动员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无悔”政策,以低成本手段进行激励甚至创收。取消化石燃料使用补贴(虽然在政治上面临挑战)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在能效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有分析表明提高能效会产生多重收益。要提高能效,就需要针对工业设备、消费品、建筑标准等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提高最低能效标准。此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援助以鼓励它们的减排行动,促进减排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也是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现有的治理结构与气候变化治理直接相关,并直接影 响到政府在该领域的优先选择。
所有国家都需要建立能够施行气候变化治理的制度。每个国家条件不同,其制度形式和能力也不同。大致规律可以总结如下:
·具备有效、灵活的治理体制的国家,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就气候变化管理 建立更有针对性的制度;而那些治理体制效率低下、缺乏变通的国家,由于集中精力应付更紧迫的治理问题,气候部门设定的目标就更为有限。
·经济上发达的国家需要更完备的制度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绝对值,而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则更倾向于强调短期性的在适应方面的治理,启动以部门为单位或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行动。
为了明确各国在气候领域所应承担的义务,已有众多学者试图将国家进行分类(Baer和Athanasiou,2007;Hohne,Phylipsen和Moltmann,2007)。分类方式包括人均和绝对GNP,人均和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否加入京都 议定书、实现低成本减排的可能性等,分类标准莫衷一是。每个国家所应做出的努力程度,以及最发达国家应当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源的规模,正是当前国际谈判的重点所在。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高收入国家(无论是否纳入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以国家大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础)应当建立综合性气候治理体系,以(1)(在政治、行政和科学角度)为国际气候治理作出积极贡献;(2)监测、控制和减少自身温室气体排放;(3)采取适当的适应性政策和措施;(4)为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低收入国家应该根据自身能力建立基本的气候管理体系,以(1)参与到 国际气候进程中;(2)完成关于气候变化脆弱性、排放现状和前景的基本科学评估;(3)监测地方生态系统和气候影响;(4)围绕适应性行动开展公共教育,促进相关利益者参与;(5)寻求并有效配置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资金。
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更复杂多样,它们在气候变化行动和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和关注重点各有不同。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规模、经济增长率、从均排放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国际上对其减排行动的期望。那些正向着“高收入”迈进的国家应该努力构建更完备的气候治理结构。快速起飞的大国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内提高其国际地位,就需要针对气候治理设计更完备的制度,因为国际上对它们在减排方面的贡献期待更高,而它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大的适应性挑战(Hohne等,2008)。
未来几十年内,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这些区别仍将持续,高收入国家需要针对减排设计完善的政策框架,而低收入国家则更强调适应性行动。然而,所有的国家都终将需要将缓解和适应纳入同一体系,进行全盘考虑。
随着时间的推移,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棘手。消费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就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政府和国际社会至今未能加以切实解决。长期来看,消费增长和人口增长不能被视为外部变量,国家政权必须负起责任,以政策手段引导消费和人口的长期发展。
能源和毁林的联系
化石燃料使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气候变化与能源生产和消费密切相关。国际能源署(IEA)曾指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进行‘能源革命’”(IEA,2008)。
许多国家的能源利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很高,其中碳密集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排放量是碳密集程度最低的经济体(如瑞典)排放量的4倍。因此,建立低碳排放的能源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减少来自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整个生产/消费周期)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大规模低碳发电系统(如水电、核电);使用可更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生物沼气、小规模水能等)。以及在使用化石燃料的大型发电设施中进行碳回收贮存,等等。气候治理和能源治理要同步进行。这就需要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加速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源工程通常需要长期的准备工作、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漫长的项目周期,因此长期的公共部门规划是成功实现能源和气候政策目标的重心所在。
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和人均碳排放通常较低,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实现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能源需求。然而它们的能源政策也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影响,特别需要小心避免在容易被技术进步淘汰的技术上投入大笔资金。国际机构和国际碳汇市场都会为鼓励低碳排放提供经费支持。
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二者之间,进退维谷。它们中间许多国家都不会立刻来取强制性排放管制措施,只是接受国际通行的减排义务。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和人均排放量的增加)它们迟早会实施排放控制。因此有必要从现在起探 索低排放能源发展道路,避免对高碳排放形成路径依赖,从而加重未来转型的负担。这就需要更多地重视低碳发展的许多潜在的伴生效益(提高能效节省开支、降低化石燃料依赖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益、减轻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会保障能源安全等)。某些案例中低碳发展已经能够与高碳排放的燃料分庭抗礼 (IEA,2008)。
毁林多集中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和温带地区,占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25%~30%。中低收入国家可以降低毁林速度,实现森林的可 持续经营,从而在未来十年内为减排做出贡献。有可靠证据表明,毁林能够创造的长期经济效益有限,对生计的贡献甚微。所以改善森林部门的治理并将气候因素纳入考虑,会带来显著的气候效益及经济、社会效益。毁林问题的解决需要中低收入的木材供应国和木材消费者的切实努力,高收入国家也需要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巴西政府近来再次重申其制止毁林的决心,在该领域做出了表率
三、 气候治理的主要维度
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气候治理的4个维度,并就相关的制度创新进行
1. 战略能力建设
战略能力是施行气候变化治理的必要条件。提高解决气候问题的战略能力,需要重视以下4个方面:
领导权
目前影响气候变化治理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是最高政治领导权的介入(与否)。政治领袖的积极关注能够把气候变化治理推向前进。没有什么比首相或总统对公文的兴趣更能吸引官员和外部相关利益者的关注。
然而,领导权不仅事关领袖个人,也与制度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能力建设包括:
·建立围绕气候变化或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如“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内阁委员会;
·指派高级政府官员,专门负责气候变化政策;
·制定气候变化问题行政领导机构;
·建立政府内部协调委员会(由行政领导机构牵头),使气候变化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在一起集思广益;
·定期向议会汇报气候变化目标、政策和绩效等。
如果仍未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国家专门行动小组或议会工作组,开展听证会,进行调查,教育公众,以及向政府汇报工作重点等。
从国际上看,气候变化领域行政领导能力的构建有三种基本组织形式。第一种是指定环境部门承担气候变化政策的责任;第二种是建立独立的气候变化管理机构(如秘书处或代表处,可以与首相办公室协同工作);第三种是将气候变化议题拓展到其他高级部委(如能源部)。瑞典(环境部)、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和英国(新成立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门)分别是这三种形式的范例。
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交由环境部门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气候变化毕竟是个环境问题,排放规制是政策对策的核心(传统的污染问题也是同样的处理手段)。然而这种方式难免存在问题(例如气候政策的一刀切、巨大的经济影响、在适应和缓解两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环境部门的弱势地位等),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寻求新的路径。
表面上看,这些组织方式之间并无差异。当然,气候变化治理并非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到各政府部门,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包括能源、工业、空间规划、城市事务、交通运输、国际关系等等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各国的政治和行政条件存在差异,即使对气候变化问题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组建气候变化领导机构。每种方式各有其优劣。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可能会导致与更完备的中央机关和相关业务部门脱离,澳大利亚已经放弃了这种方式。但如果能得到更强大的支持得以执行,这一路径无疑非常有效。以环境部门为基础,能够提供关键的专业技术,并可以沿用完善的制度结构,但问题是环境部门通常相对薄弱。于是与能源部门的联系就显得非常关键(化石燃料燃烧是气候变化的根源),但仍然存在风险:气候政策可能会被更强大的能源政策所左右甚至湮没,并导致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被忽视。
要判断哪种方式绝对优越尚为时过早。关键是无论气候变化领导部门设置在哪里,都应得到充足的资源和来自高层的政治支持,及与政府部门同一领域的其他机构合作的职权。
知识和专业建议提供
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以及得到有效的科学建议,是善治的关键。其中包括:
·建立为政府提供权威建议的体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指派一名气候变化顾问,或建立国家咨询委员会等。定期公开这些建议能够增强公众对气候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支持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知识进步,特别是在源地管辖权方面;
·确保跨国家的气候生态系统监测;
·推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科学能力建设,这些知识是政策的基石。
不同国家在上述方面开展行动的能力取决于该国科学、研究、技术和经济基础的完善程度。即使是最贫困的国家,也有能力开发国家咨询和国内监测的能力。气候变化带来了大量开展能力建设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将争取这些资金支持置于优先地位。
明确国家利益,完善战略性政策框架
国家政府承担着对内和对外代表其公民集体利益的责任。然而国家利益的构成非常复杂,并历时而变。
很显然,政府需要对其国家利益进行严格评估,在全面了解将要采取的缓解和适应行动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的政策立场上应对气候变化。许多国家都是在应对突发性国内政治事件、或需要在国际谈判中明确地位时,再临时确定政策立场。简而言之,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片面的、断裂的,并非基于详尽的科学、解决和政治评估,也未能以多维度审视“国家利益”,缺乏长期视角以及对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所能创造的公共产品的考虑。
气候变化领域的善治要求从气候变化危机的角度重新定义国家利益,这就需要理解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缓解和适应性对策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所有的政府都能够全面认识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对国家福利的长期影响。
一些政府将这种认识具体化为指示性的温度指标,声明其政策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限制在某个特定值(例如欧盟的目标是2℃)。也有一些政府设置了具体的国内减排目标(例如到2020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还有一些政府更多关注国内的适应性行动。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温度目标、大气浓度目标或全球排放目标。
一些政府通过推动大规模研究,就气候变化和相应的对策进行评估。成功案例有Stern评估(英国,2007),Garnaut气候变化评述(澳大利亚,2008)和德国议会调查委员会(1987年设立)的报告等。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长达几十年的努力,所以各国政府应当建立清晰的战略性政策框架,为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长期投资(如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创造稳定的环境,并根据各国不同的条件,包括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价值等因地制宜地设计政策。澳大利亚的战略路径是强调对其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海岛大陆的保护,而瑞典则将气候变化政策与其传统价值观联系起来,寻求建设一个“绿色福利国家”(Papadakis,2000;Eckerberg,2000)。
战略性政策框架的具体内容因各国的不同条件而异。总体来说应该包括下列要素:
·该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总体观点;
·在缓解和适应两方面的国家目标;
·负责制定实施气候变化政策的机构;
·主要的政策路径、手段和筹资机制;
·对其他社会行动者(各级政府、商业企业、公民社会、单个市民)的期待;
·围绕气候变化开展国际合作的方法。
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防御政策方面都形成了相似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基本战略观点。完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单个文本不成问题,而确保政府及主要的外部相关利益者领会其核心战略方向却并不容易。过去十年间,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挪威、荷兰)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气候变化政策框架。以荷兰为例,该国的气候政策与其面临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其作为环境政策倡导者的历史传统,以及开放的贸易导向的经济结构紧密联系。
建立关注低碳经济的组织
应当调整现有的制度和项目框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有必要建立专们机构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这些专门机构能够构建创新网络、发展专业知识、催生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新路径。一系列这样的制度能够加速促进变化。
虽然多数气候变化项目由政府部门(如环境、工业、能源、健康等)直接实施,但鼓励政府体系之外的组织发展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些组织可以包括独立机构、公共信托基金、公司联营的非营利伙伴关系等。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半独立组织具备许多优点,它们免遭政治家的日常政治干预;在采购、雇佣和运作方面不受政府繁文缛节的束缚;能够更迅速地适应环境、寻找机会;能够调整其使命和组织形式来适应特定的工作目标(如教育、科研或为企业提供支持等);因其有效性和目标评估而获得声望;与政治官员相比,更容易取得公众和相关利益者的信任。
这些致力于低碳未来的组织所关注的领域包括:
·研究在社会、文化、经济、技术方面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对公众进行气候变化知识、预期影响和关键政策的教育;
·鼓励围绕低碳未来展开公共讨论;
·对国内和国际政策手段进行严格评估,对政府和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绩效进行建设性批评;
·支持尚不能商业化的低碳技术发展;
·鼓励社区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参与;
·针对低碳技术进行职业培训(如建筑贸易、设计等),为寻求降低碳排放的公众和私人部门提供帮助;
·为希望在低碳部门有所作为的社会行动者提供所需的支持。
当然,不同类型的组织应当发挥不同的功能。英国的此类组织包括碳信托有限公司、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等。而德国如Wuppertal气候、环境和能源所等研究组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瑞典的Mistra环境战略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围绕气候变化的教育和研究。加拿大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也是这一领域的范例。
长期来看,应当建立一系列不同的组织,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政府之外(公共经费不时为其提供部分支持),为实现构建低碳排放经济体系这一政治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些组织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的形式与不同的公众和相关利益者展开合作,推动积极的变化过程。当然这些组织之间也难免会有人浮于事和业务重叠的现象出现,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甚至冲突。一些组织可能无法实现其预期目标,另一些则可能会迅速扩张。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培育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组织,它们各有优劣,共同推动向低碳未来的迈进。
这些组织除发挥各自的功能以外,还共同确立了向零碳经济转型这一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中的领导权。它们与绿色商业组织和绿色非营利组织一道,成为完kanbujian阻碍社会调整的(政府内外)制度惰性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因此这些半独立机构的建设是政府谋求通往低碳经济的长期经济政治支持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2. 气候变化纳入发展决策
Bundtland委员会20多年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理念是环境与发展决策应当紧密相连(WCED,1987)。气候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只kanbujian与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和预期目标相一致,气候变化政策才会行之有效。尤为重要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应纳入主要社会经济部门(能源、工业、交通等)及主要地区(省、市等)的发展规划中(Lafferty,2004)。
将气候变化纳入发展决策,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形成合力(Gibson等,2005)。例如,一些旨在减排的方法可能会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取消能源备用补贴可以节省经费、减少排放)和健康效益(从煤炭到煤气的转变可以减轻城市空气污染,降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改进农村灶具能够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改变深耕农业也有许多好处,如抑制土壤退化、提高土壤固碳能力、减少化肥投入等。
政府组织可以采取下列方式,将气候变化纳入发展目标:
·在每个部门或机构指派专门人员或工作组负责气候变化问题;
·责成国家、部门和地区发展规划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问题
考虑;
·召开关于气候变化的部门或地区圆桌会议,促使相关利益者探讨发展路径的气候影响;
·将气候问题纳入所有公共机构,特别是能够影响能源治理、林业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公共机构的责任范围;
·要求所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提交气候变化影响报告(包括缓解和适应两个方面)。
从广义上说,“纳入”需要在制定部门政策时将气候变化因素考虑在内(Lenschow,2002;Nilsson和Eckerberg,2007)。因此在制定交通政策时需要权衡如何缓解气候变化,建筑产业政策也同样。如果能够及早关注气候变化,后期的调整和完善成本就会显著减少。
例如,过去20年中许多国家的能源政策都强调市场改革,在能源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并建立起监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低价、稳定的能源供应(Doern和Gattinger,2004)。但气候变化因素仍未能在新的电力供应体系中有明显体现。气候变化正日益上升为政治议程,电力供应部门的执行机构应作出切实调整,实现低碳电力供应,将提高能效视为自身重要责任之一。
公平是气候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气候变化会对公平问题产生复杂的影响。追求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公平是无价的。然而从治理的角度看。公平也具有工具性价值。追求公正会使社会行为人更倾向于接受风险,而感受到不平等则会激发社会对抗,使政策实施阻力重重。因此需要再三考虑适应和缓解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或证收碳税可能会伤害脆弱群体,就需要采取再分配措施保护穷人免遭这些管制政策的影响。
研究表明,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营机构,在危急关头都更容易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相关利益者相信他们必须做出改变才能够继续生存,就能够达成kanbuqing促进改革。因此,各部门和地区的再发展规划就为将气候政策整合到经kanbuqing行动中创造良好的条件。
例如,目前的经济低迷就为政府提供了一个通过气候政策进行经济激励的kanbuqing,可以将基础设施投资引导到有减排潜力的部门和项目上去。也可以kanbuqing目标中加入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指标,使新开工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应kanbuqing十年的气候条件变化。瑞典就是借助经济危机促进环境改善的良好典kanbuqing,20世纪90年代瑞典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低潮,失业问题严重,福利支kanbuqing见附。然而瑞典并未舍弃环境目标,政府始终将可持续发展置于经济复kanbuqing的核心(Eckerberg,2000)。
气候变化治理不仅需要构建特定的制度、组织和政策,也需要将气候变化kanbuqing到政府的日常事务中去。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
3.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对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社区、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改变既有的行为方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采取积极的社会行动和技术创新,并进行自我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是动员积极的社会力量应对气候挑战。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如下方法:
·通过持续的经济手段对社会行动进行有选择的激励,如鼓励提高能效,源于碳排放高的能源利用方式。
·针对气候变化的缓解与适应开展公共教育,需要:修订大中专院校的课程,增强新闻记者的意识,因为大众媒体是联系公众的重要渠道;有必要针对专业性组织(医生、科研人员、护士、建筑师、工程师、公务人员、教师、农民等)、和贸易联盟等进行教育,它们能够与其成员有效沟通并为他们提供更易于接受的信息。
·促进城市和地方参与。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目前世界人口绝大数居住在城市,地方层次的治理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使普通市民真切地了解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城市和地方政府是关键。将这些行动纳入社区建设,就能够够促生显著的变化。
·鼓励主要社会经济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许多具体的减排和适应性战略都必须在部门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所以动员主要部门(商业、工会和环境组织)的参与是采取行动的首要条件(Glasbergen,Biermann和Mol,2007)。
·鼓励积极的公共讨论。气候变化治理包含了许多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决策和艰难的政策选择。这些决策会对长期的社会福利和成本/利益分配造成影响,所以市民参与决策就势在必行。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公共思辨和讨论,就会更清晰地了解决策者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也会更乐于承担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调整自身行为的集体社会责任。
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态度历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市民能够积极地支持政府行 动、赞赏各部委工作的话自然是皆大欢喜,然而,激进的市民和相关利益者可能会索取无度,而开放的公共辩论会引发对官员的批评,加重政策建议的阻力。有时相关利益者和公众会组织起来阻止改革进程,或抵制政府行动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而发达国家政府有时在“教育”方面会更加谨慎,他们声称只能提供“信息”,而消费者需要自主决策。然而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如一再重申确保粮食安全)。一旦公众认为政治信息背离事实或有失公允,政府就很难再取信于民。
然而,气候变化所需要的社会变革程度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的持久性(50~100年甚至更久)使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效率的官员无法“脱离”群众来制定成功的政策。如果大众对政策导向不满,他们有太多机会阻挠政策实施或迫使政府进行调整。当然政府也不可能提前预知未来几十年内的低碳经济增长路径。所以(当一些社会行动者努力避免适应或缓解行动带来的成本时)阻力还会继续。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促进主要相关利益者在政策辩论和设计乏初的参与。
4. 学习如何施行气候变化治理
人类社会才刚刚开始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以及针对气候变化管理建立各种制度和措施。因为我们的所知非常有限,所以,本着“学习”的态度施行气候变化治理至关重要。
这种以学习为导向的方法包括:
·以可重复的方式进行政策制定,即在新一轮政策设计和实施启动之前,首先确立具体目标、选择政策工具、实施政策并评估结果。
·设定可测量的目标和指标。清晰的目标有利于监测其实现进度。
·建立监测体系追踪与气候相关的变化及政策影响。
·组建独立评估组织,严格评估环境条件、人为影响及政策效果。这些独立于政府执行机构之外的评估组织能够提供客观的建议从而为公众所接受,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Meadowcroft,2007b)。
·在政策设计、社会行动和技术发展领域推行实验方法。在生活的方方面,人们都通过实验来尝试新理念、积累经验和推动创新。政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支持新的社会实践和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时也需要进行实验(Kemp,Ro和Loorbach,2007)。实验总是存在风险,无法提前预知成败。然而通过对一系列实验进行管理,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选择成功几率更高的方案。此外,即使成功的经验中也会有需要记取的教训。
·高气候变化治理的透明度。
·促进社会“自省性”,即通过政治论坛、决策机构和公共领域等,针对社会及其实现方法进行持续的集体反思(Grin,2006; Kemp,2006)。
虽然“以学习为导向”的方法优势明显,然而政府在采用时却常常犹豫不决,许多国家(包括许多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官员依然对就政策手段和政府行为绩效进行独立评估的想法心怀恐惧。政客们担心“实验性”政策手段的说法会显得缺乏深思熟虑,他们需要对政策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然而向公众解释为何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为何有时最好能够进行政策试点随后从中吸取经验,是政府公共教育使命的一部分。公众教育不能只局限在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潜在影响上,公众需要更深入了解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明白在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面前推行有效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意识到“以学习为导向”的公共政策重要性。
以学习为导向”的环境政策方面,荷兰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该国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1989-2002年间的NEPP1到NEPP4)构建了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能够从每一轮决策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形成了应对环境压力的综合协调方法(NEPP4,2002)。荷兰环境评估局(PBL,2008)负责对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等领域的社会趋势和政策影响进行独立评估。评估结果被用于进行政策导向的调整,受到政府官员和政客的欢迎。自2002年起NEPP4采取了“转型管理”路径,围绕转型实验的概念,推动可持续性的实现。
“自省性”是各种社会机构互动和公共领域持续辩论和经验学习的产物。培养自省性的核心是:能够针对政策绩效和自我组织进行独立评估的、活跃的公民社会;透明的决策;企业和其他公共组织在气候领域的表现(例如强制上报要求);以及对重新考量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保持开放的态度。
四、 近来治理改革的案例
近20年来,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尝试了各种气候治理手段。本节将简要介绍英国、瑞典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的案例。
英国
过去十年中英国采取的气候治理创新手段包括成立新组织和确定详尽的政策框架等。最近又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主要内容是进行周期的“碳预Tyndall法定的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的减排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英国介入气候问题的时间较早,由于主要政府部门的切实承诺、充分效的科技投入以及(从煤炭到煤气的转变)杰出的减排成效,使其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领袖。英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在该领域树立政府责任的过程及机构建设,即建立直接从事气候变化工作的公共部门。
这些机构包括:
·碳信托基金。成立于2001年,旨在鼓励低碳经济的发展。该基金是一个独立公司,致力于教育工作并提供贷款和其他资助,下设一个基金会和一个科技孵化器,也负责发布碳信托标准和“碳印”。该机构最近启动了海风能源促进活动,将在5年内投入3亿英镑用于在中短期内降低海风能源成本的研究和示范。这个项目关注深海地基、减轻伴流影响以及电力调节体系等问题,诸如苏格兰电力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在风能和海风能领域的大公司也参与其中。
·Tyndall气候研究中心。其宗旨是协调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它由6个主要研究机构组成,有几十个合作伙伴,由3个研究委员会提供资助。
·Hadley气候变化预测研究中心。是英国英国气象局下设的官方气候科学研究中心,由国家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给予部分资助。该中心不仅参与长期气候模型构建,也开展围绕气候变化的延伸项目和教育项目。
近来,英国又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2008年10月)。该机构发端于商业企业和制度改革部(BERR)的能源部门和环境与农村事务部(DEFRA)的气候变化部门。新组建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负责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由首相直接领导,有两位部长和一位政务副相参与其中,组建该部门的目的是进一步协调能源和气候政策框架。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行动还是2008年的气候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将英国的官方减排目标确定为:以20世纪90年代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20年减少26%,到2050年减少80%。
·建立为期5年的碳预算,设定可行的年度减排目标。并准备随时启动长达15年的3批次预算,以中期视角关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碳排放变化。预期的时间框架为2008-2012年,2013-2017年以及2018-2022年。
·建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实现2050目标及碳预算规模、在碳能放交易体系下各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所需采取的减排行动提供具体建议,判裁kanbuqing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最佳平衡献计献策”(DEFRA,2008)。该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政府必须做出正式反馈。此外,该委员会每5年对长期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一次综合评估。
判断这种体系的实践效果尚为时过早,然而它确实有可取之处。首先,碳概念面向所有社会行动者强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受到碳排放的限制——国家发展不能突破生态系统功能的极限。正如一个家庭必须受限于其财政能力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在其碳预算范围内精打细算。其次,它以长期眼光审视行动。全盘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视角,将年度结算、5年预算、15年预算和40年长期目标结合起来,使当前行动能够贡献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它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家组,强调以科学知识指导行动,而政治意愿进行决策。第四,定期上报机制和议会的直接介入凸显了气候问题的严重性,为持续的政策调整和经验分享提供了可能。
瑞典
自20世纪80年代末气候问题进入国际议程以来,瑞典就始终活跃在最前面,追溯得更久一些,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瑞典就开始致力于环境问题,并于1972年承办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随后,在许多国家都取消了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采取的能效措施的情况下,瑞典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动能源的提高和费化石能源资源的利用。1991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继芬兰之后),引入碳税制度的国家。过去20年中,瑞典在气候变化领域施行的政府强调区域供暖、生物沼气和提高能效等。目前,区域供暖占瑞典供暖系统的40%,其中60%的燃料来自生物沼气。生物沼气的应用也增强了林业部门的重要性。2003年以来瑞典推行了绿色认证体系,促进可更新能源的使用。到2008年,瑞典的石油消费占能源供应总量比例从1970年的70%下降到30%。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从70年代中期的水平下降了40%多。
瑞典环境部负责领导气候变化问题,在与能源相关的气候问题方面与企业,能源和通讯部密切合作。最近又建立了“国家风能网络”(SME,2008),以推动相对薄弱的风能应用推广,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住宅、工业产业和交通部门的能效。
总的来说,瑞典在应对环境问题中十分倚赖政府干预和规划,同时也强调性要相关利益者和地区咨询会。20世纪90年代,“地方性21世纪议程”在动员公众和地方社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Eckerberg和Forsberg,1998)。
瑞典模式的一个独特之处是确立综合的环境目标体系,使气候政策能够服鉴于更为广泛的目标,中止环境影响的代际传递。
与相关利益者咨询之后,瑞典议会最终设定的环境目标覆盖了所有主要的环境问题,并通过定量目标和指标体系进行实际操作。瑞典环保局下设的一个秘书处负责通过“环境目标委员会”(由主要政府机构和重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组成)对此进行监管。
1999年议会确定了15个环境目标,作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2020年实现除气候变化以外的所有目标,到2050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现有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远大理想的一部分。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降低气候影响”,其他目标则涉及清洁空气、臭氧层、富氧化等。2005年增加了第16个目标,即生物多样性。
对这些目标内容进一步细化、确立实现目标的时间表、设定中期目标,选择合适的指标、明确实施方案等又花费了几年时间。所有的相关利益者,包括中央部门和机构、各级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都参与了咨询过程,并积极地加入到确定目标和规划实施方案中。2002年成立了国家环境目标委员会来监测实施进度。该委员会由来自中央机构、郡县行政委员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商业企业的代表组成,主要责任是对绩效进行监测评估,推动实施过程,并为政府提供其他所需措施的咨询(EOC,2008)。环境目标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对目标实现进行进度追踪,通过四年一度的详细研究对整体状况进行评估,并向政府提出建议。
实现环境目标最重要的手段是国家环境法典(1998年颁布),该法典使瑞典的环境法律法规得以一体化。郡县行政委员会和市政当局负责区域目标的实现,而国家层次上各个目标则指定不同机构负责。
就气候变化治理而言,瑞典的环境目标体系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在环境领域更广泛的政策框架中设定缓解气候变化的目标。虽然在20年内解决所有(国内)环境问题的目标今天看来过于乐观,但仍然反映了通过清理环境污染、推动生物圈的可持续利用来为下一代人构建更好世界的政治决心。在瑞典,这种理念已经普及,为推行严格的气候政策奠定了良好的意识观念基础。
其次,虽然这种方法涉及大范围的合作和咨询,并动员了多政府措施(和经济措施),但仍然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监管,借由瑞典规划过程的高效性和行政官僚体系的杰出能力得以落实。Lundqvist将之称为通过“目标管理”(2004)实现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会毫不犹豫地在树立的长期社会目标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第三,虽然该体系是在一个有着政府调控传统的、相对集权、较为同质性的国家背景下形成的,但仍然能够加以调整,应用于不同情境。可借鉴之处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由多相关利益者组成的机构,负责评估并提供建议。包括定性目标、指标和中期进度在内的整体愿景;在政府内部对各个目标的实现进行明确的责任分配;发布定期评估结果;以及议会在各个方面的积极参与等。
荷兰
荷兰也是环境和气候政策方面的先行者之一(Anderson和Liefferink,1997)。其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为以综合的、长期的视角管理环境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过去10年荷兰更多地强调新的政策手段,例如,在能效和气候变化领域政府与企业间的谈判协议等(Driessen和Glasbergen,2002)。荷兰也kanbuqing较早推动碳税的国家之一,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自然科学和经济社会领域的)化研究网络,也是欧盟气候政策的主要推动国之一。
“转型管理”是荷兰政府采取的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独特治理手段之一。该手段关注主要社会部门(能源体系、农业、健康等)的转型道路,开发了一系列“转型实验”实践来加速创新进程,探索可能的改革路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实施中实现了主要社会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
“管理转型”在2002年的第四个国家环境政策计划(NEPP4)中首次提出。该计划指出要解决根深蒂固的环境问题,就需要实现主要社会部门的大规模“转型”。例如,(由于对石油的依赖)要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危险的气候变化,就需要“交通运输体系”实现根本性转变。其他领域也需要实现相应的变化。当然,根本性变化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管理转型”的理念为引导和管理这种长期变化提供了方法。
管理转型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致力于政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杰出的研究者(Kempp和Rotman,2005; Geels,2005)。他们通过对历史上经济技术转型的回顾对变化过程的特点作.了总结,主要强调为新技术发展提供空间的重要性;尝试新政策选项的实验过程的价值;创新者协同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主导性的社会技术体系阻碍系统变化、倾向于渐进式调整的趋势。
荷兰模式的开展,得益于其负责能源政策的经济事务部的积极参与。初步行动包括资讯利益相关者、监测长期能源前景、选择关键政策确保“清洁、经济、安全”的能源供应等,并通过转型论坛围绕六个主题(连锁效应、绿色资源、新燃气、可持续交通运输、可持续电力供应和环境建设)细化预期目标,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转型路径”。目前已有各相关利益者倡导的十余个在能源领域尝试创新实践的“转型实验”得到了资金支持。此外,还设立“创新席”,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2005年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由壳牌主席领导的“能源转型特别工作组”)和包括6部委代表参加的跨部门的协调委员会,使整个治理过程得以正规化。
目前,荷兰的转型实验已经数以百计。例如,健康部门的一个指导委会负责评估相关利益者提交的建议书,对其中的最优方案提供支持,改善医疗服务。转型管理的核心是鼓励创新、促进面向未来的合作、支持在技术和社会领域推陈出新的实验实践等。
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荷兰的管理转型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明确声明要关注“路径依赖”、“制度惰性”和“系统锁定”等问题,寻求探索现有路径的极限,实现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为政府提供了加速和引导向低碳排放转变的可行途径。其次,它强调创新者的网络和动员能力。许多政府规定和补贴项目都针对普通的、甚至是落后的企业,而管理转型则以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和技术为目标。第三,该方式试图避免在短期内“挑出赢家”,而是鼓励不同技术发展和社会创新之间的竞争,为未来选择最有利于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留有余地。
五、 进一步讨论
气候变化治理为当前的政治/行政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文第一部分提到了五个主要挑战,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对分配所公平的影响、长期框架以及全球性影响等。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使问题进一步凸显。深刻的社会影响以及与分配和公平的联系,意味着现有的利益集团会因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受到威胁,而这些忧心忡忡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加上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全球协议的复杂性以及长期的时间维度,会使政府本能地推迟行动,避免与这些利益集团的敌对冲突,推行较为缓和的气候项目。如果政府还面临其他的内忧外患(如经济失衡、健康和退休体系改革及其他紧急的发展事项等)时,就更是如此。
所以,权力和利益冲突是政府迟迟未能建立气候变化治理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对这种现象不能再置之不理,而应当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气候变化治理(特别是缓解方面)的路径不可能不触碰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如能源、农业、建筑等主要部门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然而一些利益集团从现有的制度安排中获益巨大,他们对于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始终持谨慎态度。
当然利益分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变化多端。无论是理解和观念的变化,还是新的激励政策,任何改变都会重塑利益格局。气候变化治理需要政府敏捷地推动这种变化,保证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政府的受益。
政府能够采取的手段包括:
全盘考虑推进各种变革
社会变革总是困难重重,会带来各种社会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整理这些变革,包括道德观念、公共信息和教育以及物质激励等。这种对各种变化的通盘考虑是政治行动的基本特征,最成功的政治家会积极把握构建联盟、寻求支持的需求。然而如何构建这种联盟顺应气候变化管理带来的新要求,促进现状的改变,仍需进一步摸索。任何方式都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所以只有将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工业政策及创新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对减排的投入才不会“浪费”,才能够发展新技术,创建新企业和新的生产线,提供“绿色”职业岗位,促进出口等。缓解政策还需要与健康政策联系起来,如(通过提高、使用石油还是煤气的选择变化、开发非碳电力供应等)在减少碳使用的同时减轻环境污染等。这样气候变化就不再是负担,而是“机会”。此外,还需要将适应政策和缓解政策相联系。积极的适应政策能够为缓解气候变化的投资争取公共支持来分担成本(如基础设施项目),使公众更了解为何需要立即采取缓解行动,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而被迫采取更长期的(更昂贵的)适应性活动。
某种程度上,这种全盘考虑是对问题的“重构”,使更多社会行为人能够从行动过程中看到利益。因此碳回收贮存等技术创新也可以看作是拓展推动气候政策联盟的政治行动,是寻求新能源和减排措施的明智的政治选择。
争取反对者
够动员大量的财政资源,有必要对这些资源迸行配置,对那些因气候缓解行动而受损的人进行补偿。这种干预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对因裁员而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就业培训,为企业提供科研预算加速替代产品的发展(如汽车制造商生产混合燃料车),以及为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如碳回收贮存管道和示范工程)提供资金等。对替代污染源的行为也可以给予物质激励。这些举措施多重意义,在政治上无疑会消除反对的声音。德国政府逐步废除核能的项目,极大地激励了核能企业关闭工厂,就是能源部门采取这方面(与气候变化不直接相关的)举措的例证。
建立新型经济中心
政府对经济行为人的干预,是为了促使它们的行为能够满足特定的社会目标。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绿色企业(可更新能源、有机农业、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的激励。这些干预措施(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绿色能源推广、出口市场增长),也间接地促进了选民对变革的支持。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成熟体系、科学知识、就业岗位和出口收入的)经济体也会对政治施加影响。要消除这些影响,就必须建立起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能够提供就业、促进税收和出口增加的企业与之竞争。
引入新的制度机构
政府为其提供(财政、组织、道德)支持,鼓励它们自发地推动变革进程。将部分功能从政府内部转移出来会带来许多好处,如减轻日常的政治干预,避免政府工作的繁文缛节和僵化,增强公共信心,确保政治变化顺利推进等。新机构的组建有多种方式,可以是现有机构的分支,也可以整合几个具体的部门,或者构建全新的机构等。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促使其他相关利益方进行自我监管,政府也可以协助它们组建自己的机构,如鼓励各部门建立相应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等。英国碳信托基金就是这样一个半独立的机构。
调整法定权利和责任
政府通过干预对现有的法律义务进行调节,促进某些发展目标实现的同时,会使另一些目标的实现更加艰难(成本增加、冲突频发、风险加剧)。以要求企业公开其使用的危险物品为例,这种信息公开无疑更有利于抵制有毒物品传播的人群。同理,调整环境危害的相关责任机制或者要求产品和服务标性“碳印”(或能效标识)也会带来不平衡的影响。这就需要对监管机构的责任进行重新确定,如责成公共事业监管者确保可更新能源的发展;消费监管者评估零售商在碳减排方面的努力(如碳补偿);发展机构注意项目对环境产生的累加(而不仅是边际)效应等。
鼓励组织间的合作
政府鼓励现有组织在气候变化创新行动领域的新型互动。这些群体针对特定的问题集思广益,会使权力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它们可能已经致力于既有问题的解决,通过合作式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政策框架,就能够对问题和利益分配重新定义。由消费者、生产者、管理者、企业和研究者组成的“创新网络”能够使这些缺乏交流的群体通力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创新,鼓励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以及新理念和新价值观的传播,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可用资源。以荷兰为例,政府鼓励可更新能源供应商(地热取暖泵和太阳能专家)花卉生产者之间建立联系,推动温室生产部门能源绩效领域创新。
改变现有的观念、行为标准和社会期望
政府推动新的社会行为标准和期望,能够促使行为人朝着这个方向调整自身的活动。政治讨论常常忽视观念的作用和对“正常”、“可行”和“可接受”等标准重新定义的可能性。一些政策选择在今天看来如此“不可思议”,导致这些定义在短期内都有明确的界限并会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和与国家管制的削弱,使政策框架得以转变,也使我们认识到观念的巨大作用。过去20年以限制政府力量和促进市场发展为目标的改革,使公共和私营经济活动范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党派和政府都改变了其政治观念,并在不绝于耳的关于政策常态的辩论中不断地进行调整。候变化领域,类似的变化也在或多或少地发生。欧洲企业在投资决定中开始自觉地考虑碳排放的成本,航空运输中碳补偿市场的迅速扩张也十分引人注目。英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推动主要的零售商在商品和服务生产周期中密切关注温室气体的排放。当然,政府也可以在启动教育项目、资助第三 方等方面有所作为,以更好地推动上述的观念转变。
虽然气候政策必须是一个共识性的政策,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一体甚至会行动起来抵制气候政策。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遇到阻力。因此发达国家在大规模的政策改革(如引入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和清洁空气立法等)之前,会首先预测对经济兴衰的影响。欧盟主导的环境部门研究表明由于忽视规模效应和学习绩效,工业企业常常过高地估计接受新环境政策的成本。于是政府在施行气候治理时需要出台监管措施、动用价格机制或采取其他手段调节这些利益冲突。
要克服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重重困难,引入路径依赖和主导社会技术制度的概念也是一个可行之道。历次发展决策形成了今天的工业结构,业已建立的社会技术制度主导着社会技术领域(如能源体系)的方方面面。社会技术制度包括大量的技术、实践、行为人(主要是公司,也包括科学教育机构)和制度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这些要素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使制度本身处在持续变化之中,也变成了彻底改革的阻力。因此不能低估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制度障碍。再生能源部门为例,会面临的阻碍包括保险和财政资源、客户的期望、维护、网络架构和协议以及监管标准等。
当前的能源利用类型早已根深蒂固,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能源密集的经济体与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进行对比)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就可见一斑。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就始终追求廉价、充足的能源,以维持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今天,当化石燃料使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外部性日益凸显时,这种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基础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而当我们审视如瑞典和丹麦这些国家能效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时。要知道今天的成功不仅能够追溯到40年前(70年代的石油危机),而是自工业发展之初就初见端倪(例如瑞典和丹麦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进行了地区取暖系统的实验)。
以碳排放为基础的工业结构的制度根源,使碳税和碳管制贸易体系(寻求内化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外部性)这些措施无法独立导致政策发生明显变化。任何政治体系(即使在面临工业利益损失或能源开支提高而遭受抱怨时)的运作都要求(在政治上)保持低税率(或管制贸易体系的低标准)。这就要求针对以价格为基础的政策手段,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技术进步,克服实现创新的制度障碍。
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关键,能源部门更是如此。过去十年中,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相继制定了促进低碳电力供应的政策,例如通过配额制和政府电力收购制度对可更新能源生产进行补贴。这些措施的执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但大多数国家仍然需要开展综合性项目进一步鼓励创新。
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政府需要调整现有的技术、行为人和制度,义以最低的成本建立低碳能源体系。所以碳回收贮存等技术对一个拥有化石燃料储备和化石能源出口工业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等国对碳回贮存技术的热情就足以说明)而言至关重要。拥有完备的核能力的国家会倾向于技能的应用和推广。然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使气候变化治理必须有多种路径并建立灵活的应对机制。
“制度惰性”一词可用于描述改革的阻力,以及在有更好的选择时仍然推持现有发展道路的趋向。惰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社会体系的消极特征。事实上,许多阻力恰恰来自于某些积极的群体和组织,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阻止变化的发生。社会技术制度转型的阻力不仅存在于经济方面,也存在于政治领域。既得利益群体不愿失去他们(基于特定的基础设施投资、组织联系、技术过程、专利和智力资本等)的优越地位,就动员自己的政治关系,阻碍政策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改革就是消除中间派。上文已经论述了相应的政治手段。
要克服这种制度惰性,需要进行“全盘”改革,即通过激发鼓励积极变革的动力,为未来的改革开辟道路。从这个角度,能够更好地理解鼓励低碳排放企业和机构以及重组行政责任、“抵消”沿袭现有道路的惰性、引导社会在积极的方向上形成合力的必要性。以德国为例,就是由环境部而非能源部或产业部承受担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责任。这样安排的原因是:与主要的工业竞争者相比。新生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只能维持边缘性地位,而环境部与工业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会给可再生能源产业更多的切实关注。这种制度安排促使德国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同样的理念也使德国政府积极支持新成立的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机构不像国际能源署那样与化石燃料产业有千丝万缕的制度联系,所以能够独立运作。
外部动荡也会终结整个社会的制度惰性。从历史上来看,战争、革命、疾病流行和环境破坏等原因都可能引发这种动荡。同时政治机构也会针对特定的子系统和组织有意识地催生小规模的动荡,例如在国家部门内部进行制度重组,产权改革以及政策调整等。也可以从破坏社会组织运行的危机中寻找机会,重新确立发展路径。
当然,也可以通过渐进式转变发展道路来克服路径依赖,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削弱现有的发展导向,强化新的道路选择。当然与主导的发展路径相关的社会行为人会试图维持现有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阻力。
六、 结 论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层次上的气候变化治理,认为“气候友好的发展源于自身”国际公约有助于推动合作进而降低成本,消除不平等,管理集体行动。而各国自身的理解、行动和措施都会将国际层次的调整进一步推向前进。然而过度关注国际影响,坐等国际公约,反而会导致国家和地方层次上的被动和不切实际的期待。
从自身开始行动,首先需要学习如何在气候政策领域取得成功以及在无法推卸的未来责任中领先一步,从而为更广泛深远的国际交流构建基础。
气候变化中发展的未来:当前挑战和历史教训
(Nick Brooks, Natasha Grist, Katrina Brown)
一、 引 言
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促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威胁之一。温室气体(GHG)浓度的增长速度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的还快(Meehl等,2007),引起人们对其预测的保守趋向和过度乐观的担忧(Raupach等,2007)。21世纪全球气候系统可能会发生大规模、非线性的突变(Schneider和Lane,2006; Pittock.2008)。
这些变化对人类福祉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广泛,也极其危险。2007/08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曾警告,未来50到80年,气候变化会导致全世界营养不良人数新增6亿;海平面上升可能会使3.3亿人被永久性地异地安置;而2.2亿到4亿人会面临疟疾的威胁(UNDP,2007)。当然,全球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人口将会(也已经)最敏感、最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影响。《人类发展报告》见证了这些影响的严峻程度,认为是气候变化“定义着我们时代的人类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认为“气候变化……对相信人类进步会使未来比过去更好的启蒙运动理念受到质疑”(UNDP,2007),在此背景下,需要将气候变化置于发展话语中加以讨论,强调将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缓和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应对难以避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结合起来(UNDP.2007)。
我们看到,当前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发展规划和实践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仅仅关注非常有限的降低影响和增强适应性的一些行动。虽然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被发展机构(包括政府、多边机构和许多NGO)视为政策的重心和核心所在,但在重新选择发展方式和战略方面仍未能产生切实的影响。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增长”主流化是一种积极的回应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发展路径并无差异。在投资类型、增加财政和扩展市场(包括全球碳汇市场)变化方面的行动,并未能对形成“现代”社会与其环境互动方式中的那些关于增长和进步的基本理念形成挑战。
本文探讨了主导的发展范式的合理性,这种范式的基础是由增长、现代化和全球过程所支撑的关于发展的论调。本文第二部分将介绍这一范式,第三部分回顾近几十年应用这一发展范式的案例,第四部分总结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教训,第五和第六部分就发展将如何应对气候领域未来可能出现巨大变化进行讨论和总结。
二、 持续至今的发展范式
几十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发展”的含义的讨论和批评不绝于耳。“发展”与人类社会积极进步的宏大理念相关(Rist,2008)。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组织的发展行动从未间断,其目标与现代化紧密相连(Kingsbury,2007)。过去50年中,在发展方式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的同时,发展政策和项目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随后20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有3个共同特点:(1)将第三世界及其居民看做是同质的实体;(2)无条件地信仰发展这一概念本身,以及通过普适性过程构建社会的可能性;(3)坚信民族国家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根本所在(Shuurman,2000)。
然而发展主义方法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得更远,它源自西方的哲学话语,以支撑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假设或哲学前提为基础。这些假设中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人类社会正在继续一个由技术、经济和政治创新等诸多因素推动的前进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是旧石器时代,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民族国家的产生,最终形成现代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人类发展的观点经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过一系列分别以“蒙昧”、“野蛮”和“文明”(Daniel,1968)为特征的革命性阶段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而推广普及,在20世纪50年代“新考古学”中也有一定的体现(Trigger,1989)。当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更多地摒弃了这种进步论的社会变迁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是许多民族和政治话语,特别是那些与发展、全球化和现代化相关的话语的基础(Gray,2007),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发展观点有着显著影响(Cooper,1997)。
第二个假设是人类进步是由于人与自然环境的脱离,以世界人口中直接依赖糊口农业为生的比例下降为特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和对环境的人为管理有关,而环境可能被看做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将人类进步看作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和与其日常接触的下降的观点,哲学基础是将人类看作处于“自然”的“外部”或与之某种程度的分离,通常以“人类例外主义”学说来表述(Soper,1995; Macnaghten和Urry,2005,Heyd和Brooks,2009)。
当然,关于发展的认识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同时,也始终处于广泛的、深刻的辩论中。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基于上述假设的主导范式确实存在,并且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践的流行的发展观。该范式也影响了“从事”发展的主要国际投资、项目、工程和机构。二战后倡导的人类进步的发展模式,目的在于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重建世界经济,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角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促进资本主义主导的增长中的优先性。Rostow(1960)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以及“欠发展”国家的传统社会向更“高级”的国家发展阶段进化的理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高消费时代的出现,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践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得以修正,将发展中国家的前进道路转向企业私人化、自由化和撤销政府管制,将经济增长目标和宏观经济稳定置于优先地位,于是推动了全球化和市场导向的世界中不断扩张的贸易规模。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文化变迁被视为实现更高级的物质福祉的核心要素。
这些关于发展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不断地受到挑战而不断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后华盛顿共识。新的路径仍然重视经济增长,但是加入了多维度的减贫、可持续、平等和民主等主要目标,并在多数发展环境得以很大程度地实现,至少在纸面上如此。如今发展的概念已经将一系列包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赋权、政治发展、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整合在内(Clark,2002)。然而在学术界,发展理论家、决策者和实践者们对这种规范性、基础性的发展宏观叙事提出质疑,其观点称为后发展理论(Escobar,1995;Schuurman,2000)。虽然这些观点很难进入发展政策(所以常常被忽视),仍然引发了一些相关变化,例如加强了关注地方层次和对发展问题以社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小就是美”的路径。Scott(1998)描述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权威主义的国家规划忽略了在实现“现代性”的努力中的发展主体,他建议采取立足地方的发展路径。于是国际发展决策者将目光投向其他领域:首先是以目标瞄准为基础的千年发展目标,脱离了传统的宏观叙事,关注结果而非方法;其次是各地区特定的发展问题如治理、危机管理和可持续生计;再次是国家层次的减贫战略文伴(PRSP)和相关政策目标。
因此,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分解为更多关注实践和“微观叙事”的努力。但是McKay(2004)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本质不但反映在8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中,还仍然在持续影响着IMF和世界银行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还有人认为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各项子目标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Maxwell,2005)。发展实践和理论显然在不断扩张。然而,基于“进步”的概念,以及对社会将通过同质的社会变化过程变得更“高级”的信仰、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隔离的基本范式,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展主义的范式仍然主导着当代许多发展活动(Blaikie,2000;Gray,2007;Heyd和Brooks,2009)。下一部分将具体论述该范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
三、 发展模式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脆弱性有何影响?
从全球来看,这种发展主义范式的确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以人均GDP的增长为指标,使全世界众多人口脱离了贫困。然而,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同时,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都是不平等、不公平的。高昂的环境成本包括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等(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对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红树林消失等主要变化的经济分析表明,相对于贫困国家在破坏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而言,它们所承担的成本非常不合比例,进一步突出了所谓的“国家的生态负债”问题(Srinivasan等,2008;Turner和Fish-er .2008)。
表1通过3个案例来展示在过去50年的特定情况下,发展主义范式是如何对发展政策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的。这些案例说明发展政策如何加剧了社会和(或)环境应对过去及未来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最显著的例子来自西非草原(Sahel)。在那里,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发展政策寻求实现由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将之视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其动力是使迅速取得独立的国家有能力维持稳定、实现有效的国家经济,并进入世界经济体系(Cooper,1997)的强烈需求。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农业集约化,农业向那些未经开发的地区推进,破坏了传统的危机管理手段,使游牧民被边缘化(Thebaud和Battterby,2001)。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不寻常的湿润时期(Brooks,2004)。当20世纪60年代末期降雨量下降时,特别是70年代初严重的干旱发生时,农业和游牧业瓦解,随之而来的饥荒使数以万计的人和上百万动物丧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乱(Swift,1977)。西非草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表明关注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政策忽视了长期的(在这个案例中,只需10年)气候和环境变化,从而加剧了脆弱性,在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面前,这种脆弱性就会引发灾难(Heyd和Brooks,2009)。
表1 表现在不同发展模式中的发展主义范式
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非草原的政策,到今天仍然在全球随处可见。在墨西哥的Tlaxcala,对从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型的支持,破坏了小农户的资源基础,和应对与日俱增的气候不确定性的弹性(Eakin,2000,2005)。在巴西亚马逊地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由军政主导的移民和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导致了不可持续、不平等的发展。虽然历经政府换届,问题却依然存在(ClusenderGodt和Sachs,1995;Browder和Godfrey,1997,Barton,1999;Cox等,2004; Malhi等,2008)。表1对这些例子做了进一步阐述。另一个案例是肯尼亚的远景2030计划,其目标是通过一个包括新建2个海滨城kanbuqing和在半干旱地区建立一座新城,以及将商品化农业扩展到“新开放”土地和半干旱地区的现代化项目,在未来25年内实现GDP年度增率10%(肯尼亚共和国,2007)。在与该远景2030相关的主要文件中,唯一一次提到气候变化是陈述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时,肯尼亚将“在所有灾害易发地区加强灾害预防。增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肯尼亚共和国,2007)。
在所有的例子中,发展策略和行动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发展主义范式。在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各异的条件下,对环境变化和相关脆弱性缺乏考虑甚至无视却是相似的。在表1的3个案例中,发展政策和实践都未能考虑或规划气候和环境条件在季度和年度变化以外的时间维度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系统对业已发生的、或潜在的大规模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此外,由于对资源(例如农业投入、可获得的土地等)的获得性下降,还会导 致人们对气候异常和改变的适应能力下降,破坏传统生计和相关的风险分担手段。决策过程中忽略更广泛的环境条件,要归结为主导的经济范式,这种范式强调经济效率和建立在低效、低产的生产模式(可能包含基于内部冗余和多元生产体系的风险分担策略)上的生产最大化。牺牲生存弹性来换取生产力的路径。与从“低效”的糊口生产向“高效”的商品生产转型的“现代化”概念紧密相关(Cooper,1997)。
四、 以史为鉴:历史上全球气候重构的教训
表1中的案例表明发展政策如何加剧脆弱性,降低适应能力,以及当脆弱的系统和人口被置于大规模的、持续的气候变化中时,这些政策如何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动乱。在更久远的历史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教训,为我们提供大规模气候变化和相应的人类应对手段的案例。例如Costanza等(2007)从系统的观点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评估了自远古以来人们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形成改变历史的合力。本部分将详细阐释一些主要案例,并将其与发展具体地联系起来。
今天能够得到的关于人类对各种大规模的气候和环境变化适应的历史案例非常少a所以对21世纪下半叶可能发生的全球表面温度升高超过3℃的现象。无从进行精确的古环境学类比(Jansen等,2007;Meehl等,2007;Anderson和Bows,2008)。虽然如此,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回应大规模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地区都可能经历过一个持续的、全球维度的气候重构过程,发生在距今(BP) 6000到4000年前。在这一时期,北半球亚赤道地区的季风系统弱化直至崩溃,在一段时间的静止之后,规律的赤道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NSO)周期形成,中高纬度温度下降(Mayewski等,2004;Brooks,2006a; Sandweiss等,2007)。距今6000年前是个气候变化不稳定的时期,距今大约6000到5800年间,以及5200年前发生了寒冷、干旱“危机”(Brooks,2006a)。这一时期的全球气候重构发生在后冰川时代持续长达10000年的全新世的中期,终结了所谓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当时北半球亚赤道地区和毗邻地区比现在要湿润得多,中高纬度地区的温度也比现在高。我们用“中全新世”一词来描述距今6000到4000年的这段时期。考古学证据确认,这一时期针对主要的气候变化采取了极端的应对方式,包括移民、社会分层和扩张边界等。
在中全新世,许多地方的人都经历了资源的丧失,因为北半球亚赤道地区正从雨水丰沛的热带草原和灌木丛向沙漠转变(Brooks,2006a)。今天在亚非沙漠带仍然有证据表明当时大量土地被抛荒,导致受影响地区人口向环境适宜地迁入,以及向更湿润地区迁出。距今6000年前,当北部地区撒哈拉季风减弱时,撒哈拉和西非草原南部的居留地数量增加,而距今5000年前后撒哈拉季风消失时,撒哈拉中央地带居留地数量则大幅度减少(Vernet和Faure 2000)。
这些证据表明人口在向南迁徙。而当时在撒哈拉中邵发生的那种虽然能够获得地表水却仍然向某些特定地区的迁入,恰好补充说明了这一点(Hoelzmann等,2001;Brooks,2006a)。同时埃及的人们逐渐由沙漠向尼罗河流域迁徙(Midant-Reynes,1992;Wilkinson,2003)。距今5200年前,当最后一次明显降雨发生后,流动的游牧民族开始在Hierakonopolis永久定居(Mident Reynes,1992;Wengrow,2001)。在今天亚非沙漠带的其他地区,当周围变得越来越干旱而坐产力下降时,人们加剧了对河岸地区的开发,在河谷密集定居(Brooks,2006a)。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秘鲁北海岸地区,洋流的改变导致那里的海岸上涌,干旱加剧(Sandweiss等,2007;Brooks,2006a)。
北半球亚赤道地区和毗邻地区在中全新世发生的干旱化和资源稀缺程度加剧,伴随着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加剧。在撒哈拉地区宏伟的丧葬建筑与日俱增,以及当干旱加剧时陪葬品由动物变成人的事实,表明边界扩张和社会分层在加剧(Sivili,2002;di Lernia,2006)。游牧群体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能够负担起宏伟的陵墓,也表明了特定群体和特定边界之间的关系(di Lernia,2006;Brooks,2006)。埃及那些距今6000年前的精致、奢侈的陵墓正与人们集中定居在尼罗河谷时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精英出现有关(Midant-Reynes,1992,Bnewer,2005)。美索不达米亚壮观的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也体现了政治权力的崛起,其中一些正是疆域干旱化时期暴力和权威的最早体现(Pollock,1999;Brooks,2006a)。埃及在距今5200年前的统一可以被解释为暴力行动,标志着小规模政体之间斗争过程的宣告结束(Midant-Reynes,1992;Brewer,2005)。
大约同时,移民地的防御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盛行。距今5200年前正是一个城市国家竞相出现,破旧立新的转折时期(Brooks,2006a)。需要注意,21世纪西非草原的干旱所导致的社会冲突、抛荒和移民,以及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加剧,同样表明这种应对极端的、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资源稀缺的措施虽然并非普遍真理,至少从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相当可信(Keita,1998;Thebaud和Batterby,2001)。
在距今5200年前后,当今天北半球沙漠带的干旱气候完全形成之后,阶层分化的不平等社会开始加速发展,移民规模增加,人口向有限的区域集中,因为那里的降水和生产力还未被气候变化摧毁(di Lernia,2002;Brooks,2006a)。距今6000年到5000年之间,拥有宏伟建筑和高度社会分化和分层的、大规模的中心城市在埃及、西亚和南亚以及秘鲁的北海岸开始出现(Possehl,2002; Shady Solis等,2001),而在中国北方,封建领主统治的阶级社会也正在形成(Liu,1996;Lee,2004)。
这些证据表明,与流行的观点(例如Gross,2005)不同,最早的城市和国家(构成世界最早的“文明”)并非是在冰河世纪的恶劣条件之后出现的适宜环境中形成的。相反,它们是在广泛的、严峻的气候恶化情境中,在那些由于降雨减少和植被系统瓦解而导致极度资源稀缺的地点最早成型。考古学和古环境学记录表明最早的文明发展并非是由单一因素所驱动,所带来的利益增加是技术、经济和政治创新的结果。新的、正式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通常是权威主义的)出现,来统治日益复杂而高度分化的社会。新的制度更能代表在资源有限、需要对主要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管理的条件下,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对大规模人口进行管理的手段。这些社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未经计划的结果,它们不断地自我调整,随后在转型期经历了大规模的动荡(Brooks,2006a)。这种向“文明”生活的转型付出了成本也得到了收益,其中心原则是个人自主性的丧失(Kennet和Kennet,2007)。抛开进步所产生的成果不谈我们可以将最早的文明看作最后的庇护所。
这些早期的、复杂的国家社会也会带来对环境的不适应,在某些宋例中甚至导致其消亡或动荡。距今5200年前的干旱时期是全新世气候适宜时期终结的开始,其后延续了长达1000年的干旱危机。这次危机与埃及王国和阿卡德王朝的灭亡直接相关(Hassan,1997, Cullen等,2000,Tigger等,1983)根据这1000年间既定的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利用程度进行判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新的“文明”人对可获得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最大化,使他们必须依赖持续稳定的气候条件(最可能与规律的河流和洪水相关)而生存。最终,他们的社会不能适应随之而来的气候震荡,结果是中央政治权威倒台、文化解体、饥荒、暴乱和社会暴动。
总之,考古学记录表明居住在不同地理地点的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稀缺的方式却非常相似(例如移民、增加社会复杂性和分层),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和地理限制条件和机会如出一辙。
这种结论并非是向简单的环境决定论的回归。萌芽于中全新世气候重构时期的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往,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记录也表明他们采取的适应性行为各有区别(Brooks,2006a)。一些地区向环境庇护所的迁徙趋势也伴随着其他群体流动性的增强,证明了应对气候恶化方式的多样性(例如出di Lernia 2002)。
更晚一些的案例突出环境变化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例如,Scarborough(2007)分析了玛雅的兴起和灭亡,环境因素在玛雅社会发展的特定方面发挥着限制和促进的双重作用,导致其灭亡的最终原因与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他们的与世隔绝、集权和“自大”相关。因此Scarborough总结道在玛雅消逝中“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量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大于”环境变量(2007)。一项针对历史和史前的调查表明推动人类社会变化有诸多因素。物理或“自然”环境正是其中之一,却常常被认为其重要性不及如社会、经济和技术创新或冲突等其他因素。虽然如此,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单一的变量都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主导其他变量。中全新世显然提供这样的特定条件。使环境变化至少暂时成为世界许多地方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力。21世纪也有可能形成类似的条件,至少在特定区域是如此。
五、 当前发展模式和适应方式面临的挑战
上文已经讨论过,当前发展模式关于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理念基础有所改动,正是那些在相关学术领域饱受质疑的模式,导致了对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起源的误读。最重要的是,这些模式的内涵加剧了社会脆弱性,使人们适应气侯和环境变迁和变化的能力降低。这些模式还可能是“非适应性的”,导致在正常的气候变化和长期的气候变迁中脆弱性加剧,因此极其不适用于21世纪,因为在21世纪可能会发生气候和环境的巨大的变化,包括非洲南部植被体系在破坏(Thomas等,2005),在马格里布的极端干旱(Christensen等,2007),亚马逊雨林部分或完全消失(Cox等,2005),安第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地区严峻的水资源压力(Bradley等,2006;Cruz等,2007),以及低洼沿地区的土地流失等。
当前的发展模式虽然未能足够重视长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问题,却也探索了一些增强适应性的方法。发展机构在增强适应性方面的努力更关注气候变化那些更“便于管理”的方面,即季节和年度变化(例如降雨量),以及极端天气例如干旱、暴雨和洪水等的频度和破坏性(UNFCCC,2007)。适应在本质上是通过便于管理的、可预测的过程,在追求预设的发展目标和期望的发展产生时,“中和”、至少是最小化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方式(例如UNDP,2005)。当“气候防范”(例如非洲发展银行,2005;UNFCCC,2007)的强调也包含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适应就是找出和实施适当的手段(通常是技术手段)来佑护现有的、旨在消除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政策、计划、项目和实践。
气“候变化评估”正是最佳例证。这是一种通过评估当前发展计划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及消除这些风险的手段,将气候变化整合到发展规划中来的方式(Klein等,2007)。目前针对适应性的研究强调将其主流化到通行的发展战略(如减贫战略文件)中来,为援助和综合性发展措施提供适应性方面的参参(Kliein等,2007;Huq和Ayers,2008; Prowse等,2009)。因此,目前的适应性话语强调控制和最小化气候变化影响的必要性,其最终目标是一如既生地维持现状。关于适应性的管理学路径更多地强调对现有的制度、技术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消除风险的手段如灾害预警、灌溉和保险等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例如UNFCCC,2007)。这种方式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剧烈的、突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诸如移民之类的问题已经逐渐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相对难于处理的气候变化问题仍然被发展机构所忽视。因此适应性被纳入主导的发展范式,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外部条件进行有效处理。
上述适应性话语的假设并不符合经验证据。对历史上气候变化的应对进行审视,表明适应性方式导致了社会组织生产、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史上的适应性方式通常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生存活动的巨大变化等,均与政治组织的冲突和变化相关。这些适应性活动可能并不能使社会跟上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当变化过于剧烈时更是无能为力。在21世纪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气候剧变。过去的适应性活动都是被动回应式的,在气候和环境变化之后出现,经过一段时期的动荡和转型,形成了人与自然互动的新方式。当特定的适应性政策、策略和手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指导和调整适应性行为时,自发的、回应式的适应性行为无疑仍在继续产生。我们从历史和史前史得到的教训是:适应性行为本身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人们开发、管理和保护环境方式的根本变化等。这就必然会使我们与环境,以及我们彼此之间联系方式产生巨大的转变,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思我们是谁,身处何处。这些变化必定会改变一切。
当前的发展模式和适应性方式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它们关注增长和消费,将环境视为外部条件,这些都会加剧气候变化,进一步恶化脆弱性。多数发展实践者都将气候变化看作“影响”发展的因素,需要保护发展免遭其害。现有的适应性方式都假设可以通过简单地寻找和实施适当的适应性习性手段保证发展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来消除气候变化对发展投资的风险,反倒会使社会面临不可持续和非适应性发展的危机。已经证明,一些适应性行动会破坏系统弹性,甚至造成不适应(Nelson等.2007)。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种新的适应眼光。
六、 以史为镜,保障未来
本文不仅回顾了最近的历史,也涉及了全球气候经历系统重构的那个阶段。当时特定的、回应式的、自发的适应性行为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人类社会。由于全球地表温度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升高,我们可能会见证5000年来的首次全球气候系统重构,那么今天的核心问题是:在21世纪及更远的未来气候变化的后果会在多大程度上重演历史。
今天的世界早已与5000年前全新世末期气候适宜时期大为不同。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批文明正在广泛而剧烈的气候变化中萌芽,而现在我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已经了解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虽然其性质、时间及其影响的严重性尚不能精确预计,但有清晰的迹象和明确的证据表明哪些气体和地区会首当其冲地身受其害。于是,社会能够(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提前行动起来,采取防范措施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和地区。这些行动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基于持续性和稳定性假设的、主导的发展范式和现行的发展模式并不青睐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行动,它们将适应性视为维护这种稳定性的实施,而非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极速突变的环境中生存的手段。全球化对于解决全球气候在变化时期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至少在理论上)确保这些行动能够有利推动的制度来说,有利也有弊。投资、生产和消费类型,人和劳动力,技术和知识都可以、并已经迅速发展,以飞快的速度在全球配置。然而,这种全球化的综合力量,以及全球环境变化都使穷人更加脆弱,在许多案例中引发了不平等的加剧(Nissanke和Thorbecke,2005)。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意来远古的证据都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冲突、更为霸权的统治、更严重的不平等和更加阶级分化的社会。要建立更健全的制度来引导这些变化,防范一切可能性,我们就不仅要处理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也需要应对适应性行为身导致的后果。
我们从中学到了经验和教训:采取预警行动,应对预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在各个层次上行动起来;建立具备适应机制的制度;以及积极地学习。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如何设计和实施发展需要进行全面的反思。这就要求我们跳脱出当前强调管理和技术解决方案的全球气候变化话语之外,寻求与主导的发展主义范式和对可持续发展的现有理解的彻底脱离(Grist,2008)。最近的科学发现证明,如果全球的平均地表温度上升4℃或更高(Anderson和Bows,2008)能会触发气候系统“突然的”、非线性的变化(Lenton等,2008),我们可能需要采取适应性行动进行应对。于是,发展就需要建立在这样的系统和路径之上:能够应对一般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发生的巨变;随时间而加剧的气侯不稳定;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气候短期、中期和长期变化所引发的高度不确定性。此外,发展必须尽量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某些特定的后果,包括土地生产力下降、沿海地区的洪水问题、土地景观、生态系统和资源可获得性的系统变化,自然本身的变化,以及气候相关灾害的分布、频率和破坏性等。这些变化将使世界许多地方的发展无法遵循以往“一成不变”的路径。
例如,Hole(2007)通过分析叙利亚的历史和未来选择,表明这种系统变化虽然会受到限制,却必然会发生。叙利亚10000年的历史表明土地集约利用的脆弱性以及降雨的不规则性,然而现有的发展加剧了农业的集约化,消耗了地下水,破坏了干旱草原的植被。Hole总结在这些边缘环境中,极端情况下向宜居地大规模的移民“可能会超出环境负荷,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失效”(2007)。他认为这些条件和压力是由发展和自然过程(例如化石燃料使用和气侯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描述了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提出将倡导更为密切的监测作为解决方案,同时他也指出该地区的规划者们并未将未来的变化纳入 视野。
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来针对环境机遇和挑战构建发展,而非仅仅将环境因素纳入基于有争议的关于进步和现代性理念的发展政策、项目和实践中。这些新的模式需要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和不确定问题,在生产力(养活膨胀的人口)和生活弹性(例如应对降雨量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之间建立平衡。这就需要人们放弃在短期内将生产最大化的追求,这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的潜力,却将保护社会免于过于依赖“适宜”气候条件(在中长期内不一定仍然适宜)的生产。这些新的发展范式将优先考虑变化的气候不确定和生存存弹性,而非简单地在短期内将生产力和增长最大化,转而寻求对特定资源最小程度的消耗,以及在生产体系中建立剩余机制来分担风险。
表2比较了当前的发展方式和作者建议的、在动态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实现发展的方式。表中所总结的政策启示是基于如下4个原则的考虑:(1)拯救最脆弱的群体;(2)降低来自全球化的环境压力;(3)在不同层次上采取行动;(4)加强制度建设。
表2 对比当前范式和新范式及政策启示
接下来以现行的政策为例,进一步阐释第4个原则。要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对各个层次的制度进行水平(各国之间和国际上)和垂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层次上)整合。在加入UNFCCC和参与国际谈判过程时,这种整合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一些有效的国际行动例如START和“南南北”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力。然而,筹资和治理是关键所在。筹资已经通过NAPA和PRSP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但富裕国家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应对和适应性计划来加入这个体系(在建立国家适应性战略方面,发达国家远远地落后),他们可以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经验。
在国家层次上,气候变化和生存弹性的理念不应局限于环境部门自身,而就当通过将这些概念操作化为可行的、切实的、积极的政策目标,扩展到财政、能源和农业部门。英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财政部建立了一个气候组并编写了斯特恩报告,建议在财政储蓄的基础上针对气候变化采取预警行动。英国(和世界)将这一信息用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英国现在也建立了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该部门与政府领导紧密联系,与其他部门(如交通部、国际发展部、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积极互动,致力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通过政策手段来增强制度能力的另—个例子是欧盟的排放权交易机制,证明将碳排放许可纳入经济体系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理念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启动初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Euractiv,2009)。
虽然加强制度建设对于激励和支持消除气候变化影响和增强气候适应性的行动至关重要,但并不能确保这些行动一定合适或有效。只有在促使这些行动的那些模式、假设和方法正确的时候,制度才能催生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已经论证过,当前构建发展的那些模式、假设和方法漏洞百出。气候变化的现实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理念不相容,.肯尼亚的远景2030和其他一些国家级发展“蓝图”都没能将环境现实及其面临的未来考虑在内。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倡导一个新的发展方式,那将陷入普适主义的发展陷阱。我们只是建议要挑战构建和推动当前发展方式的、并不完美的、关于进步、现代性和经济增长的教条,希望通过围绕环境而非通过环境的发展,允许适合各地区、国家和地方情境的、能够充分应对变化的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产生和存在。从抽象的角度说,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发展机构和发展实践者的文化,这种文化将发展和人类社会看作是嵌入在物理或“自然”环境中,与其有着天然的“社会”联系(Heyd和Brooks.2009)。
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可能的发展方式可能会适合不同的情境。任何一种发展方式要想长期适用应该针对每个系统、特别是针对生态和环境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而量身定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社区,某些地方从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趋势被逆转,向农民提供粮食作物增强了他们的生存弹性,而通过增加栽培品种、增加种植地点和风险分担机制则降低了风险。另一方面,生产者从面向全球市场的低度多样性生产向针对地方和区域市场的高度多样化生产的转变则没有这么明显。如果市场或大规模商品生产失效的话,无 需政策激励,就会必然出现从糊口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Mortimore和Adams,2001)。在半干旱环境中,或是降雨不规律的地区,游牧活动被禁止。然而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手段如承认放牧权利等,游牧可能会是这些边缘、不稳定环境中确保粮食安全的有效手段(Brooks,2006b)。这种策略可能会遭到许多政府“现代”思维的抵制,它们将游牧看作是需要被“文明化”的落后标志,于是就需要彻底改变支撑当前发展模式的那些哲学和意识形态基础,发展活动可以针对这种流动性进行调整,例如向游牧民提供就地医疗和教育服务等,“将发展带到游牧民”而非“将游牧民带向发展”。在发达国家,围绕着类似绿色新合同(新合同工作小组,2008)这样的理念提出了许多建议,关注提高能源效率,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从而促进了绿色投资,开辟了就业空间。然而,这种方武仍然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从本质上与主导的发展主义范式无异。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关于繁荣和福祉的广泛辩论,而关于零增长的讨论和承认生态极限的论调也再度复兴(Jackson,2009)。
气候变化和适应性可能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变化。适应性有别于当前的发展后语不同,通常是在一段危机或转型之后发生,其结果不可预见,也并非全然良性。然而(在气候预防和主流化等话语中)对适应性的假设是管理学视角的,可预测的,代表着一种“中和”气候变化影响、保护或促进人类福祉的手段,需要进行仔细的评估。一些现有的适应行动也会对系统弹性造成损害,甚至导致不适应(Nelson等,2007)。虽然现有的适应活动都是由政策推动的,但是必须承认许多适应性行为都是自然产生的,有着独特的本质。因此,协调促进人类自身的适应行为,可能与在发展政策中“将适应性主流化”的建议大相径庭。原地适应这一观点也需要进行批判,更多地关注适应性极限的存在。虽然气候变化仅仅是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但要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最主要的推动力。
《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推翻关于人类进步的启蒙主义信仰的尖锐问题,需要得到比时至今日更多的认真审视。本文提供的证据无疑支持了这个观点,表明现代性本身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基础有着致命的缺陷。无论如何,如果认识到气候变化会对构建一个以个人自主和边缘群体赋权为特征的、更公平的社会的努力构成挑战的话,发展实践者们会更为慎重地思考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问题。
气候变化可能发生的范围、对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如何回应这些变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大规模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和土地利用方式的重构会在中短期内发生。我们需要转向风险最小化策略和生计管理和资源管理策略,将生存弹性和安全性最大化,确保气候变化不会进一步加剧以进步之名业已造就的深重的不平等和脆弱性。
第三部分
市场、贸易与贫困
农产品市场状况:高粮价与粮食危机——经验与教训
(联合国粮农组织贸易与市场部)
一、 世界粮食价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
1. 2007-2008年飞涨的世界粮价
2006年开始的国际粮价上涨已升级成为全球性的粮价飞涨,不断加剧的粮食不安全引发了暴力示威,甚至引起了人们对国际安全的忧虑。非洲也许受到的冲击最大,但问题是全球性的。关于高粮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影响的报告引发了各方呼吁,要求采取国际行动,扭转持续恶化的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粮食援助机构诸如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面临难以为继的高昂援粮采购成本,迫切希望得到额外资金。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在2006和2007年分别上升了7%和27%,并在2008年上半年持续上涨并加速。此后,价格开始稳步下降,但仍处于长期趋势线之上。2008年FAO粮食价格指数比2007和2006年分别高出24%和57%。
即使按粮食的实际价格[用世界银行制造业单位价值指数(MUV)扣除通胀]来看,其涨幅也很明显。粮食实际价格一直处于稳步下降的长期趋势,期间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价格大幅上涨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价格呈平稳态势;2000年价格开始恢复性上涨;2006年,价格猛升-2000-2005年价格年均涨幅为1.3%,2006年以来年均涨幅已猛升至15%。
汇率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粮价上涨的原因可部分归咎于美元贬值,因为国际价格倾向于以美元计价,如以其他货币计算,粮价的涨幅并没有这么剧烈,仍处于历史波动范围内.但无论如何涨幅还是较大的。
在评估农产品价格涨幅时,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还会影响对不同国家所受影响的评估。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国家的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上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些国家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诸如进口关税、基础设施和市场结构等影响价格传导的因素。由于大多数商品是以美元计价的,对那些本国货币比美元坚挺的国家而言,美元贬值使其产品成本下降,多少对粮价的上涨起到了缓冲作用。然而,对那些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弱于美元的国家,美元的贬值则增加了粮食的采购成本。而有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是与美元挂钩的。
是否所有农产品价格都以同样的趋势上涨?
尽管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至少以名义价格均有所上涨,但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涨幅差别很大。特别是,基本食品如谷物、油料及奶制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涨幅远远高于咖啡、可可等热带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原材料的价格。因此,那些依赖后者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其出口收入增速低于进口粮食成本的上涨速度。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净粮食进口国,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2007/2008年度的粮价上涨有何特殊之处?
此次粮价快速上涨与1995-2002年间商品价格长期下跌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该下跌趋势甚至曾引发恢复国际商品协定的呼吁。一些分析人士把粮价上涨看作是农产品实际价格长期下跌趋势结束的信号,《经济学家》杂志(2007)宣告了“廉价粮食时代的终结”。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是潜在的世界粮食危机的开始。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有趣的问题,此次粮价飙升与以往价大幅上涨是否有本质区别,以及实际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是否已告一段落,显示农产品市场行为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高价现象与低价现象一样,在农产品市场并不罕见,但高价往往比低价持续的时间要短暂些。但现阶段涨价现象与以往不同的是国际价格上涨波及的不仅仅是少数产品,而是几乎所有的粮食和饲料产品,而且价格在短期暴涨后仍将保持在高位。
伴随价格暴涨的是比过去更加剧烈的价格波动,特别是在谷物和油料部门,显示出市场更大的不确定性。在2008年的前四个月中,小麦和稻米价格波幅接近历史最高位(2008年小麦价格波幅是前一年的2倍,而稻米更达到了5倍)。价格波动不仅局限于谷物,植物油、畜产品和食糖的价格波动均大大超过前几年。波动性大意味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买卖双方决策的难度。市场不确定性的上升限制了生产者对信贷市场准人的机遇,往往导致他们以放弃创新和创业为代价,采用低风险的生产技术。此外,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越大、趋势越难预测,投机者通过投机于商品远期价格而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反复波动的市场会吸引大量的投机行为,使现货市场价格进入价格动荡的恶性循环。从国家层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的进口或出口。虽然粮价上涨会对出口国的经济带来短暂的好处,但也使它们进口粮食和农资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价格的巨大波动会影响这些国家实际汇率的稳定,给其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妨碍其减贫工作。
如何比较2007-2008年的高粮价与以往的粮食危机?
从以往粮价走势中可发现,近期的粮价上涨与以往不同。20世纪70年代出现所谓“世界粮食危机”时曾出现特别剧烈的价格升幅波动。本次高粮价与那次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天气原因和原油价格的猛涨导致粮食生产萎缩。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样,限制粮食出口被再次用作控制国内通胀的手段。然而,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是:70年代的危机是由粮食供应波动引发,而导致2007-2008年事件的关键因素是需求因素(特别是生物燃料需求),且可能带来更长期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高峰期,每吨稻米和小麦的国际报价分别涨到542美元和180美元。由于2008年初的价格远远超过70年代的水平,这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世界正面临着和70年代类似的危机。但是,美元现在的购买力与70年代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按实际价格看,便会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例如,按200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1974年每吨稻米的实际价格是2008年前四个月平均价格的4倍多。
“廉价粮食时代”的终结?
粮价飞涨带来的冲击可部分归因于全球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所谓的“廉价粮食”。2006年前,全球食品的实际价格在30年里几乎下降了一半,许多食品的实际价格以年均2%~3%的速度下跌。科技进步极大地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加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成员国普遍的财政补贴,导致其他国家高效、低成本的粮食生产变得无利可图,这使得一些国家作为世界粮食供应国的地位得以巩固。这种供应驱动的农业模式,使几十年来实际粮食价格呈螺旋下降的态势。此外,市场和政策环境变化也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导致库存水平下降,使人们更加计划性地靠进口来满足粮食需求。在以上各因素的作用下,主要粮食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供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这些国家出现减产,特别是连续几年出现这种情况,全球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最终导致高粮价和粮价大幅度波动的市场紧张状况就不足为奇了。近期的粮价飞涨就是上述现象的典型结果。在此背景下,全球收入和人口增加以及生物燃料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求,使粮食出口大国没有机会补充库存。
一些产品价格的极端剧烈波动是触发人们对大规模危机恐慌的另一原因。在价格上升和持续波动的时期,要区分市场不稳定与本质性高粮价是很困难的。因此,搞不懂国际粮食市场正在发生什么,就再次增加了人们对粮食危机即将来临的恐慌。
近期的高粮价是粮食实际价格下跌趋势的逆转,还是世界正在经历又一次价格上涨,而且涨幅还很大?过度动荡的市场波动未必导致根本性和永处性的价格转折。当它真的引起价格逆转时,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结构性突变”。计量经济学方法可用于查找农产品价格的结构性突变。用这些方法衡量后发现,甚至连20世纪70年代危机期间许多食品的价格高峰都没有显现出结构性突变的特征。在危机的最高点过去之后,价格又延续了先前的趋势。
从至今已出现的迹象看,难以就本次粮价上涨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研究至今未能探测到结构性突变。因此,要回答近期的高粮价是否与以往的涨幅明显但持续短暂、随后持续下跌的商品价格行为是一致的,或以往的价格行为模式已告一段落等问题,还必须探究表面原因背后的本质。导致本次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多种:粮食减产、低库存、油价、生物燃料需求、新兴国家的收入增长、美元贬值和投机活动等。虽然无法量化单个因素对粮价上涨所起的作用,但有些因素可能会对平均粮价持续产生影响。目前的形势有一些特点,主要是谷物库存处于历史低谷且对生物燃料的有着强劲需求,这就表明,尽管粮价已从2008年初的高位回落,但近期的高粮价可能还将持续几年。
先升后跌——当前粮价
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已从2008年上半年的顶峰显著回落。世界粮食价格下跌了50%,其他基本食品价格也随即下降。然而,这些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也高于其2007年的水平。在许多国家,特别在非洲,粮价仍远远高于2007年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中,2008年上半年出现的国际粮价高峰仍在国家市场中持续。
2. 粮价为何如此大幅上涨?
分析人士和评论家对粮价上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最常见的说法是用来作为生物燃料生产原料的某些农产品的需求在增长,特别是用来生产乙醇的玉米。历史最高位的油价和环保问题使人们对替代性能源产生了兴趣,美国和欧盟(EU)的政策措施均鼓励扩大生物燃料生产。高油价也对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和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其对粮食、尤其是畜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饲料对谷物和油料的需求。以上这些说法都注重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新”驱动力,认为农产品的价格行为可能已经有了根本性改变,高粮价还将持续。而“传统”的说法也很有道理,认为粮食出口大国因干旱导致供应量减少,而且谷物的库存量为30年来最低。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其他一些复杂因素,认为它们至少部分上导致了粮价上涨。这些因素包括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债券和股票市场萎靡不振,投机资金因而流人农产品期货市场。一旦国际粮价开始大幅度上涨,市场和政策为此而做出的反应又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例如,囤积粮食来应对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限制出口等。
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因素都组合在了一起。它们是粮价上涨的直接导火索,不过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面临产量增长缓慢、投资不足、农业发展援助份额不断下降、研究和发展资金日趋减少等长期问题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这不但使粮食不安全问题不断恶化,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于应对。
减产及低库存
传统上,人们在解释粮价波动时往往强调外部因素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特别是天气影响。本次价格上涨的关键导火线就是始于2005年并持续到2006年的粮食出口大国谷物减产现象。这两年谷物的减幅分别达到4%和7%。然而,在高价格的推动下,谷物产量在2007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美国的玉米产量。2007年谷物供应量快速增加是有代价的,其侵占了原本用于油料生产的资源,特别是大豆生产,导致油料产量下降。
库存在平衡市场和缓解价格波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库存量与消费量之间的比例过低,市场应对供求突发事件的能力就会减弱;供应量下降或需求量上升均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个比例自2006年起一直呈急速下降趋势,并于2008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库存水平,主要是谷物的库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实际上,1995年出现上一次涨价事件以后,全球库存水平平均每年下跌3.4%。《乌拉圭回合协定》签署后,政策环境出现了一些变化,成为导致主要出口国库存量下降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公共机构储备量的大小;储存易变质产品所需的高成本;其他成本较低的风险管理手段的出现;更多国家具备了出口能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大国连续几年出现减产,国际市场的供应就会趋紧;一旦出现意外事件,价格波动性和波动幅度就会加大。的确,销售季节开始时的库存水平(以库存量占即将到来销售季的预计消费量的百分比表示)与该季节形成的谷物价格之间明显成反比。这就意味着,销售季开始时全球市场供应偏紧往往会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这也是2006年国际谷物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持续的低库存量是较高价格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理由。到2008年销售季结束时,世界谷物库存量只在销售季初的低水平基础上提高了1.5%,达到了25年来的最低点。在2007/2008年度,世界谷物的库存消费比例为19.6%,大大低于24%的五年平均值,甚至比2006/2007年度的ZO%还要低。受谷物市场形势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小麦和粗粮市场的影响,油类/油脂和豆粕/豆饼的库存情况在2007年中期开始恶化;到2007/2008年度销售季结束时,油类/油脂的库存消费比例已经从13%降至11%,而豆粕/豆饼则从17%降至11%。
正确看待粮食和饲料——中国和印度
要想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消费需求,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收入增长通常也会引起膳食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对高价值食品(如畜产品)的需求,而对淀粉类主食(如小麦)的需求则会下降。由于这些变化是逐步出现的,不应该将其视作价格突然上涨的根本原因,如最近的涨价就不能归咎于此。因此,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引发本次粮价飞涨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导致需求上升,但这一看法尚有待于重新考量。
最近,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重点探究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增长对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所起的重要作用(IFPRI,2008)。研究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拉动了对肉类、奶类等畜产品的需求,最终也拉动了对饲料粮的需求。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确在全球农产品供应和需求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2007年和2008年的高价格似乎并非源自这些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谷物消费量增速实际要比其他国家要慢。
中国和印度的谷物进口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以年均约4%的速度下降,在过去三年中已经从80年代初的每年约1 400万吨下降为每年约600万吨。
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的谷物饲料需求增长主要是靠国内生产解决的,至少直到近期是如此。另外,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油料、植物油和畜产品进口大国,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数年份中,其总体农产品贸易基本上保持着顺差。印度的长期贸易地位也证明,认为它是导致国际市场粮价上涨的因素之一是错误的。印度一直是粮食出口大国。在1995-2007年间的多数年份中、印度的小麦、稻米和肉类出口量均超过进口量。即便是提到印度相对较大的植物油进口量时,也要考虑到它同时还出口了大量的豆饼。实际上,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或印度有突然增加油料、豆粕和油类进口的现象,所以无法将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归咎于它们。这些商品的价格是从2007年中期开始上涨的,距粮食(特别是玉米)的大幅涨价已有一年的时间。中国和印度并不是造成油类产品突然大幅涨价的原因,但这并没有削弱这两个国家过去和将来在粮食市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削弱消费方式的总体变化过去和将来在粮食市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生物燃料的情况又如何?
将某些农产品用作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意味着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资源出现了减少。生物燃料生产会减少市场上粮食产品的供应量,因为油和原材料价格对生物燃料生产更为有利,用粮食、食糖、油和其他基本食品作为燃料生产原料的“有效”需求可能会超过用它们作为食品的需求。这种新的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价格。在所有大宗粮食和饲料产品中,对玉米(用作乙醇生产的原料)和油菜籽(用作生物柴油生产的原料)需求的增长对价格造成的影响最大。例如,2007年世界玉米总消费量增加了近4 000万吨,其中仅乙醇厂家就吸收了近3 000万吨。需求增长大多数出现在美国,它既是最大的玉米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在美国,用来生产乙醇的玉米约占国内玉米消费量的30%。这使得国际市场的玉米价格从2007年初开始出现大幅上涨。价格如些剧烈的反应还与生物燃料新需求的快速发展(主要在2~3年里)和该项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90%以上)这一玉米出口大国有关。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世界玉米总消费量中约有12%被用来生产乙醇,60%被用来作为动物饮料。在欧盟,估计2007年成员国菜籽油产量中约有60%被用来生产生物柴油,约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25%,占全球菜籽油总贸易量的70%。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每种作物中有多少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而不是用作食品和饲料;其还关系到有多少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被挪用,去生产生物燃料所需的原材料。2006年中期以来玉米价格的持续走高已促使美国农民在2007年扩大了玉米生产。玉米种植面积增长了近18%。而扩大玉米生产的代价就是减少大豆和小麦面积。由于玉米生产的扩大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2007年美国玉米获得大丰收,不仅满足了美国包括不断扩大的乙醇生产在内的国内需求,还可供出口。然而,玉米丰收这一表面现象掩盖了另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小麦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在减少,产量也在减少。这就是价格大幅上涨的一个原因。当然,如果澳大利亚没有遭受干旱的影响,欧盟和乌克兰没有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那么就有理由相信粮价也不会如此大幅地上涨。
这种连锁反应在2008年似乎又再次重演,但这一次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大豆的相对价格较高,美国的农民减少了玉米面积,转种大豆。坚挺的大豆价格促使美国2008/2009年度销售季的大豆种植面积出现大幅上升。这一趋势也可以从期货市场中大豆和玉米的价格比中得到证实。从历史上看,每次该比例接近2,就表明玉米比大豆种得多,结果就是农民从种植大豆转向种植玉米。当该比例在2006/2007年度出现下降时,农民就大幅度增加了玉米的种植面积。但当该比例在2007/2008年度销售季中大大高于2时,农民却扩大了大豆的种植。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对于大豆市场来说是个好事,但玉米市场却因此变得非常不稳定。鉴于美国出台了新的《能源法案》,乙醇工业对玉米的需求预计会持续增长。如果玉米产量在2009年出现下降,那么美国要想满足所有国内需求(包括粮食、饲料、燃料和出口),而同时又不大幅度减少自已2009/2010年度销售季的玉米库存就变得很困难。美国将密切关注市场上出现的任何迹象,防备这种情况变成事实。在目前市场偏紧的时期内,玉米的价格会坚挺,很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大宗粮食和饲料作物。
除了巴西利用甘蔗制造乙醇外,生物燃料生产目前在没有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都没有经济效益口巴西用甘蔗生产的乙醇每升生产成本是最低的,这也是唯一一直保持比同类化石燃料低价的生物燃料。接下来生产成本较低的就是巴西用大豆生产的生物柴油和美国用玉米生产的乙醇,但这两种燃料的成本还是超出化石燃料的市场价。欧洲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比巴西的乙醇要高出一倍多,这说明原材料和加工成本较高。根据全球补贴动议,美国2006 年为生物燃料产业提供了58亿美元的补贴,欧盟的补贴则为47亿美元。这些政策性干预鼓励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生产液态生物燃料,由此增加对某些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此类补贴的一个出发点是生物燃料比化石燃料更环保,但目前人们开始质疑这一说法,因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某些生物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好。然而,由于生物燃料的补贴依然存在,因此它所带来的对农产品的扩大需求将会继续抬高农产品价格,继而也影响到其他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油价的作用举足轻重。油价越高,生物燃料生产的经济效益就越高,对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当油价达到一定水平,使生物燃料具备竞争力时,能源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会上升,而这一新增需求会抬高农产品价格。因此,农产品市场与能源市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联系。由于能源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相比之下更大,因此来自生物燃料部门的需求原则上能够完全吸收可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增产量,能源市场也就有效地为农产品设置了最低分。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使生物燃料生产不再具有竞争力时,这也是为农产品设置了最高价。因此,最终确定农产品价格的将是能源需求,而不是粮食需求,农产品价格将与能源价格捆绑在一起。显然,这将大大改变以往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投机起了什么作用?
最近有关高粮价的讨论中对投机者和机构投资者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视。随首其他资产收益的降低,这些所谓的“非商业交易者”开始在期货市场买入农产品。曾有人担心投机活动在粮价上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全球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衰退,资金为追逐利润而流入农产品期货市场,这些资金的来源既包括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传统机构投资者,也包括新生的与商品挂钩的、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期货和期权交易活动总量番了不止一番。在2007年前9个月,这一活动比上一年增加了30%。尤其是在商品市场的非商业交易者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对买人期货合约的兴趣提高。2005-2008年间,非商业交易者在玉米、小麦和大豆期货市场的存仓比例近乎翻倍,但在食糖期货市场的持仓比例保持基本不变。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数额巨大。然而,他们对农产品的投资量仍比不上对金属等其他商品的投资量。
非商业交易者在玉米、小麦和大豆市场份额的提高恰逢这些商品在实体市场的价格也出现上扬。过去几年农产品市场投机活动十分活跃,一些分析人士因此把粮价上涨与投机活动的增加联系起来。然而,尚不清楚到底是对农产品的投机推高了价格,还是价格自行上涨吸引了投机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期的一项研究结果认为,总体上看,是高价格吸引了投资基金流向农产品期货市场。这一因果关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大量资金流人至少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粮价会居高不下和出现波幅明显加剧的现象。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如果金融投资者的确对粮食价格造成了影响,那么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关注,一些国家甚至考虑对其加强监管。
并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粮价飞涨
粮食的美元价格飞涨并在2008年上半年创下新高,幅度之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出现这一走势的原因在于许多主要商品市场供求失衡,特别是谷物和油料。能够为粮价飞涨提供合理解释的主要是需求方因素。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供应方因素往往具有短期性,其涉及减产和主要贸易国采取的出口限制等政策措施。在需求方面,推动近期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屈指可数。需求方因素的变化与供应方因素不同,其通常较慢,也在意料之中。这是由于除新兴的生物燃料因素之外,粮食市场需求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基础变量呈渐变(且可预见)需求上位发展态势,这样就给供应方留出了调整的时间。近期高价格期间的形势也并未偏离这一趋势,粮食和饲料需求都没有发生突如其来或意料之外的增长,故无法对市场出现的价格大涨提供解释。投机和投资资金的流入更可能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只有生物燃料原料需求的迅速扩张是以往没有经历过的。然而,生物燃料需求本身并不能单独解释2007年和2008年初期价格的大幅上涨。石油价格创纪录提升了人们对生物燃料开发的兴趣,但其本身也推高了生产和运输成本,从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需求方面,出于对价格继续走高的担忧和原料需求的增长,价格面临着更大的上涨压力。世界市场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在人们普遍所接受的原因中,任意一个都不能单独解释近期价格走势的格局和幅度。实际上是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叠加才引发了戏剧性变化。虽然我们很难对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行解析,但证据显示生物燃料需求和石油价格是其中的主要驱动因素。
通过经合发组织和FAO的Aglink-Cosimo世界农产品市场模型所做的模拟,可以大概看出各因素对粮食价格产生的相对影响。这一模型可以根据影响市场和价格主要变量的未来数值做出的前提假定,对市场进行中期预测。采用不同前提假设并对相应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甄别每种影响的力度大。采用的五个主要假设包括:(1)粮食和油料用作生物燃料原料;(2)石油价格;(3)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EE5);(4)美元兑所有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5)作物单产。
在粗粮和植物油方面,如果生物燃料生产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不变,那么它对价格前景的影响最大。这些农产品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变化是很不确定的,不论原因是石油价格的变动、生物燃料扶持政策的调整还是新技术开发促使加工者购买不同原料。假定生物燃料生产维持2007年水平不变,那么得出的结果是2017年粗粮预测价格下降12%,植物油预测价格下降约15%。第二种情形显示,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预测对石油价格变化都极为敏感如果石油价格跌至2007年的水平,它们的预测价格将再下降8%~10%.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的情形显示,小麦和粗粮价格将仅比基线水平略微有所降低(1%一2%)。在植物油方面,由于一般认为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要大得多且上述五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提高,因此模拟的价格差超过10%。第四种情形模拟了美元走强造成以出口国国内货币计算的价格走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增加供应量的积极性。同时,美元走强将使进口国的进口需求降低。出口供应增加和进口需求趋弱的共同作用对世界价格形成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到2017年,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均将比相应基线预测水平低5%左右。假定谷物和油料单产提高5%,该情形将得出2017年小麦和玉米的预计价格将分别比相应基线值低6%和8%,但对植物油预测价格的影响不大。
价格为何回落?
2008年7月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回落,逆转了此前同样大幅的上涨趋势,并促使价格向2007年的水平回归。发生这一逆转是供求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高价格刺激了全球谷物生产的扩大。然而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中国和印度。除这3个国家外,2007-2008年发展中国家食物产量实际有所下滑。因此,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贫困农民并没有抓住高粮价的机遇-2007年增产幅度十分有限,2008年更是基本为零。粮食下滑与全球供应量增加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造成需求放缓,全球进入衰退使经济活动减少,而且石油价格出现大跌。需求下降对诸如橡胶等农产品原料的市场和价格影响最大(至少在初始阶段如此),但粮食价格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粮价下跌对消费者来说是个福音,但不能因此认为全球粮食体系的问题已得到解决。高粮价背后的多种关键因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依旧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尚未出现大幅提高,而价格刺激因素的趋弱也不利于其他地方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全球谷物库存量仍然较低,2008/2009年度谷物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仍低于五年平均水平。虽然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但随着原料价格的下滑和新的乙醇产能投入使用,生物燃料的需求依然旺盛。石油价格下跌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十分复杂。油价走低能降低能源和化肥成本,但随着生物燃料竟争力的下降,也会对用作生物燃料原料的农产品价格造成下行压力。高等效应将取决于石油与原料、尤其是玉米的相对价格走势。
中期前景如何?
国际市场粮价回落幅度很大,但仍明显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是否还将继续下跌抑或维持这样的历史高水平? 2008年下半年价格回落的幅度与上半年价格上涨的幅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波幅加大,两者恐怕均有“过火”之嫌,因此难以辨别这是否意味着要朝着一个新趋势调整。然而,被视作导致高价格的某些因素表现出长期性,这与以往农产品价格走势的格局迥异;以往价格飙升往往是短期现象,随后则长期低迷。如上所述,从更普遍意义上讲,除石油价格外,造成高粮价的各因素仍保持不变供应量没有显著提高,库存量依然保持低位。
《经合发组织-粮农组织2008一2017年农业展望》(2008)认为,农产品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均将从2008年初创下的创纪录水平回落,但今后十年仍将保持高于上一个十年的水平。这种回落刚刚开始,但只是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才表现得比预想的更为迅速。价格的回落将持续多久取决于从衰退中复苏的速度。但《展望》断言,在价格近期飙升的主要因素一低库存背景下的粮食主产区干旱、生物燃料原料需求增长、高油价、美元贬值和商品需求结构变化——中,一部分因素具有永久性,并预计在今后十年中使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展望》特别提及了生物燃料需求和石油价格。尽管从全球范围看,按绝对值计的粮食和饲料仍然是农业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但目前生物能源产业对原料的需求增长迅速。生物燃料需求成为数十年来最大的需求增长点,而且被视为支撑农产品价格上行的有利因素。生物燃料在农产品价格与石油价格之间形成了一种新联系,并有可能至少在中期打破农产品实际价格长期下滑的格局。
3. 高粮价的影响
粮价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
高粮价对靠购买食品生存的贫困人口影响显然最为严重。对发展中国价的;贫困人口而言,食品在其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少则50%,多则70%~80%。因此,价格上涨不仅影响到他们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也影响到他们的总体开支。粮价飙升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暴动,这就是负面影响的最直接体现。动乱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以及受国际粮食价格影响的程度可能最高,消费者感受到了粮价飞涨最猛烈的冲击。然而,农村贫困人口也受到波及,尽管他们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可能较弱。粮价上涨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关键取决于他们是粮食净出售者还是净购买者:如果是前者则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如果是后者则影响无疑是负面的。有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多数家庭,尤其是穷人,属于粮食净购买者,甚至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也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受影响最严重的都是那些其食品开支占自身收入比重最大和不拥有土地等资产的最贫困人口。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在两种情况中均占畸高比例,因此高粮价的负面影响还具有性别层面的意义,需要在政策应对中予以解决。
在面临粮价飞涨的状况时,贫困家庭不得不调整消费结构。据报道,有的家庭削减了食物摄入量或通过减少较昂贵食品或其他非食品开销的方式维持食物摄入量。在最贫苦人口组别,虽然价格上涨,但随着消费者舍弃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等较昂贵和更优质的食品而转向以谷物为主的膳食结构,人均谷物消费量甚至可能有所提高。虽然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飙升(尤其是小麦、大米和玉米等主食贸易品种),但有关这些主要农产品作为粮食消费量的最新数据显示,人均消费量具有弹性。多数低收入国家都呈现这一趋势,包括那些营养不足水平较高的国家。然而,随着所偏好的进口谷物价格出现上涨,消费者转而食用传统食物的情况也有发生。
粮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
粮价上涨对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均产生了作用。粮食价格的变化是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总体通货膨胀率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揽子固定商品(包括食品)的价格变动加权平均数,其中权数反映每种商品在典型家庭开支中的重要性。食品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越高,食品价格上涨对总体通胀率的推动作用就越大。对多数发达国家来说,食品支出比重一般在10%~20%。而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要高得多,在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和马拉维等国家要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除了对生活开支造成沉重负担之外,粮价上涨还可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更多的间接影响,比如要求提高工资已成为一些抗议示威活动的主题。中央银行如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那么就可能会在对非食品价格影响较大时采取措施来抑制粮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利率。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提高利率可能会影响到某些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迫切需要的投资,而这些部门正是脆弱国家摆脱贫困的途径。
高粮价意味着粮食进口费用提高
虽然近期国际粮价出现回落,但据预测,2008年全球基本粮食进口费用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比2007年增加近25%,主要原因是大米、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大幅提高以及运费上涨(许多航线的运费几乎翻了一番)。许多是贫穷国家属于粮食进口国,严重依赖谷物进口。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就意味着粮食进口费用提高,从而出现国际收支问题。2007年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总费用已经比2006年增加了33%,目前低收入缺粮国(LIFDC)的年均粮食进口费用已经在2000年的水平上翻了不止一番。
在国家层面,农产品高价格的影响还取决于该国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进出口的产品种类、贸易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因素。在谷物进口成本不断提高但出口产品价格增幅有限的背景下,最为脆弱的当属那些依赖谷物进口(在某些情况下80%的膳食热能供应量依靠进口)和热带产品或农产品原材料出口、其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兑美元汇率贬值的低收入缺粮国。而既是粮食不安全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又是净燃料进口国的形势显然更是岌岌可危。具有这些特征的共有20多个发展中国家,非洲至少占16个。
显然,最脆弱国家承受来自粮食进口成本提高的负担最为沉重,2008年低收入缺粮国粮食进口总支出比2007年增加了约35%,创下年度增幅的历史最高纪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低收入缺粮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往往较高,商品出口收入中较高的比例要花费在粮食进口上,而且其人均收入也较低。大多数低收入缺粮国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贬值,这进一步提高了粮食进口成本。这些国家面临来自备方面的经济压力。
此外,金融危机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信贷形势紧张可能会限制贫困国家获取资金的渠道,从而使其粮食进口能力受到制约。低收入缺粮国尤其可能面临难以通过借贷为其谷物进口提供资金的问题。财政压力可能加大。
消费者蒙受损失,但生产者能获益吗?
显然,高粮价对消费者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然而,从原则上,高价格对世界各地的农民说应该是福音粮粮价上涨理应提高农民生产相关产品的积极性。从原则上,粮价上涨能增加生产者投资所需的资金供应,从而提高农业增长率,有利于减贫。从这一意义上说,粮价上涨可以被看作是个机遇,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意外所得。能否获得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资产是决定谁能从粮价上涨中获益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规模越大,土地所有者受益就越大。从事高度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户也有可能受益,但相对于其他农民而言,这些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生产者一定会做出增加供应量的反应吗?似乎高粮价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机遇,生产方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如上文所述,虽然价格大幅提高,但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仅增长了不足1%,其中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出现了减产。期望中会出现的生产方积极响应的现象根本没有出现。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推动生产方的积极性是重要的战略和政策议题。本报告第2部分对此予以详细剖析。
二、 为什么高粮价对贫困农民来说并非机遇?
1. 国际价格上涨是否让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受益?
随着国际价格飙升,许多国家的粮食价格出现大幅攀升。但在另一些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并未随世界价格上涨,或者调整迟缓。如果价格上涨实际不能波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者,那么这些生产者就无法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中获益,他们也没有提高生产率和产量的积极性。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首先,国际价格变动是否能带动国内价格的变动;第二,如果国内价格确实出现了变动,那么价格变动是否能传导至生产者?
从理论上讲,如果在自由贸易环境下某个国家与世界市场接轨,那么该国的价格就应该随着以同一货币表示的国际价格走势而变动。如果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那么就会通过进口,在扣除运输成本之后实现与国际价格的趋同。如果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那么增加出口就会起到同样的平衡作用。在这些条件下,“价格传导”是完整充分的,在充满竞争的国际与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某商品的价格只应存在运输成本的差异。商品分析人士把价格的快速完整传导看作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标志。然而,在实践中,有一系列因素可能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家一级“传导”的程度形成制约。
口岸政策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内市场传导的程度具有影响。例如,出口限制或税收能阻碍价格信号的传导。从价进口关税,只要不是畸高,能够使国际价格变动按相对值完全传导至国内市场。因此,如果关税水平不变,国际价格的上涨将使所有时间点的国内价格保持同比例上涨。运输成本高昂造成的巨大营销成本也可能使国内市场与外界隔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薄弱可能造成较大的营销成本,因为把本地产商品运往口岸出口或把进口商品输往国内市场需要高额成本。由于高昂的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使套利无法实现,因此阻碍了价格信号的传导。其他因素,诸如消费者对本地产食品某些特性的偏好或国内与国际商品的质量差异等,决定着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食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国产食品,从而影响价格传导。短期与长期价格传导之间的区别也十分重要。某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动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传导至其他市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策干预、调整成本、营销链的复杂性、经济行为者间的合同安排、仓储和存货、运输或加工甚至惰性造成的延误等。因此,很难有完整或迅速的价格传导机制。
从非洲玉米看,运输成本、美元疲软以及消费者偏好都抑制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国内价格响应缓慢。在消费中,白玉米并非能轻而易举地被国际上买卖的黄玉米所替代。尽管如此,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各区域中的正规和非正规玉米贸易增量说明,各国市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体化。对1998—2008年各月份玉米价格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该区域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南非的黄玉米和白玉米价格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十分缓慢,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确在本区域各国之间实现了传导。在2006年6月至2008年6月间,国际市场黄玉米价格平均每月涨幅达3.9%,而在国内市场,白玉米和黄玉米价格的月平均涨幅分别为1.2%和1.6%。
肯尼亚和乌于达等非洲东部国家重要市场的玉米价格也与世界价格联动。平均来看,2003-2008年间国际价格变动传导至这些市场的速度相对较慢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玉米价格要在大约七个月后才能根据国际价格变动完全调整到位。尽管如此,2007年7月之后国际玉米价格的飙升在该两国均有所反应这说明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进行的调整可以是迅速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动与低库存或区域粮食供求紧张同时发生时,调整尤为迅速。在这一期间,内罗毕和坎帕拉玉米价格月平均涨幅分别为3.7%和7.1%,而国际价格每月涨幅为4.3%。
就亚洲大米而言,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也取决于兑美元的汇率、贸易和市场政策以及国内供求形势等。总体上看,2006-2007 年美元疲软部分抵消了国际价格上涨对一些亚洲国家的影响。例如,在印度、菲律宾和泰国,本国货币兑美元的升值使国际价格上涨的影响被拒之于口岸之外造成国内价格走势格局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基本面的因素,某些情况下也是由于对国际大米价格飙升做出了政策反应。在主要大米出口国印度。由于2007-2008销售季增产,而且采取了禁止大多数大米出口的政策措施(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国内价格涨幅较小。在净进口国,国内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2007年,且多数情况下与大米进口量的增加同步。在孟加拉国2007年的飓风和洪涝造成粮食短缺,致使国内大米价格大涨,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大米进口量出现了上升。
即使存在国际价格变动向各国市场的传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上涨一定能传导至所有生产者或消费者身上,但城市地区的消费者经受价格上涨的速度可能较快。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取决于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程度以及当地市场与更大范围的国内、区域或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不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价格的空间传导能力很强,而且小农也能充分参与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市场中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
小农参与的价值链通常与商业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农民不同。后者可能与大型粮食贸易、加工和零售企业、农产品交易以及仓储、面粉厂和超市零售商—体化网络之间存在业务联系,有时还属跨国公司所有,掌握市场信息,交易量巨大,拥有特定的分级规定和标准以及能够承接更为复杂的合同安排的法律系统。这与小农通常参与的非正规链形成了对照,这些非正规链的特点是市场现货交易,少量出售所生产的农产品,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薄弱,信息系统薄弱,而且农资供应、信贷和销售之间缺乏协调等。
有当多的证据说明,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小农只作为粮食出售者在有限范围内进入当地的市场。在这两个区域,只有很少一部分玉米生产者在积极向当地市场销售玉米;往往生产玉米的农户作为玉米购买者在当地市场的参与程度比作为出售者的参与程度更高。
由小农的市场参与程度有限,因此对于作为出售者在市场参与程度并不高的众多农户来说,价格上涨对其积极性未必会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由于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许多生产者实际上与区域或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区域或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对小农的境况就不具有影响。对非洲市场一体化和价格传导的经济计量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2. 价格上涨,但成本也在提高
无论价格上涨对生产者收入可能产生何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的提高都是一种反作用,甚至会完全抵消这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已多年呈稳步上升态势;农产品价格上涨对许多农民来说不过是效益空间不断缩小过程中的暂时喘息之机,但2007年农资价格暴涨,涨幅超过了农产品价格涨幅,这种暂时性喘息便告一段落。
石油价格从2003年开始大幅上扬,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燃料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直接原因是提高了农业动力和运输成本,非直接原因是石油是化肥生产的一项重要成本。能源价格上涨势头迅猛,路透商品研究局能源价格指数2003年以来已经提高了两倍以上
2008年头几个月,部分化肥(如三重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美元价格比2007年同期上涨了160%以上。化肥价格的这一涨幅大于农产品价格的涨幅。
产出与投入价格比率大体体现了农业利润空间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农资价格的稳步提高导致该比率呈下滑趋势。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该比率下滑对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非洲。随著2007年化肥价格突然大幅上涨,该比率急剧下滑。此外,有证据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并未彻底而迅速地传导给生产者,但农资(特别是进口农资)价格上涨的传导却十分充分和快速。
3. 生产方所面临的制约
即使价格能够刺激积极性,但许多小规模生产者与市场的整合不足也会阻碍他们做出反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农的经营结构大大地制约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种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劳动力比率下滑,这种变化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生产者对价格上涨做出反应的能力。来自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证据显示,玉米销售高度集中在少数农户(在某些国家,2%的农户即占到玉米销售总量的50%),其他小农没有投资生产更多的粮食用于出售的积极性,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农户(3~4公顷)也是如此。在乌干达,小农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平均土地占有面积不足2公顷的农民占粮食总产的90%以上。小农占加纳农业生产的约80%。
在整个非洲,小农经营的特点往往是生产率低下、技术落后、农资(包括化肥)用量极少、营销系统存在问题且收成损耗率较高等。农业单产保持相对稳定,大量农活由基本不掌握现代耕作技术的老年农民承担。由于无法保证稳定充足的利润空间,因此农民的投资积极性不足,在采用改良技术方面也存在较大制约,例如当地良种、种植材料和其他农资短缺等。虽然一些国家经过改革改善了农资供应,获得许可的经销商增多并可以进行较低数量的采购,但小农的农资用量仍然很低,继续制约着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可供出售的产品数量少,而且小农之间往往也缺乏组织,无法把少量农产品集中起来形成经济规模,再加上基础设施和通讯条件薄弱造成营销成本很高,因此对价格上涨的反应不积极就顺理成章。但在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的情况下,就无法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在整个生产和营销链中,缺乏获得成本合理的信贷渠道进一步限制了对提高生产率的活动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提高生产者积极性,就必须克服这些制约因素,还要通过政策干预打破使小农深陷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实体基础设施的发展似乎尤为重要。完善的运输,通讯、仓储和营销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农产品销售和农资采购。FAO对所有发展中世界的大量个案研究表明,运输基础设施的欠缺是一个重大制约因素,限制了生产者进入国内、区域和国际市场。
信贷市场能促进生产、消费平滑和新企业的发展。信贷市场是帮助穷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机制。获取金融服务(信贷和储蓄)的渠道不足使穷人在冲击来临时显得更加脆弱。但多数“结构调整计划”反而造成农村家庭获得的信贷量减少,信贷成本提高。
粮农组织研究表明,农民在获取信贷方面普遍面临困难。喀麦隆的小农基本没有获取信贷的渠道。虽然1992年成立了小额信贷机构,但这些机构在该国的分布仍不合理,有时也缺乏良好的管理规范。马拉维的小农也面临信贷难的问题,小额信贷机构往往对非农商业活动比较重视,现有的大部分农业信贷仅限于烟草产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中小商人没有获取信贷的渠道,无法采购存货以便在淡季时高价出售。由于粮食作物较易于以现金交易方式出售,一些农民便不再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在乌干达,农村居民唯一的信贷渠道是小额信贷业,而该产业却更重视非农活动。目前乌干达正致力于开发能够满足农村人口需求的金融服务并与全国金融系统进行整合。在危地马拉,农业信贷供应不足且还在不断减少。现有信贷大多流向出口产品(传统和非传统的),对基本粮食生产的扶持却很少。圭亚那采取了有关措施,帮助许多小农克服在获得可接受的抵押担保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NGO)于1986年成立了“私营企业发展机构”(IPED),向小型企业家提供贷款。该机构采用交叉担保的做法,小组的每个成员均对其他成员的债务负有担保义务。该机构在促进大量小农增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秘鲁在政府信贷供应计划中的做法却不成功,据报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农业部门的信贷大多来自商业银行,20世纪90年代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扶持的小农数量已经大幅
4.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能对高粮价做出反应吗?
有人断言,近期的高粮价对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来说是一个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并重新把农业确立为增长驱动力的机遇。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实际价格增长会导致产量增加,价格下跌会导致产量下降,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粮农组织的大量个案研究表明,仅靠价格上涨本身,并不足以提高生产率和供应量。通过对过去一段时间价格和产量变化的150个案例的研究,粮农组织发现,产量接预期方向变化的情况只占其中的66%,另外34%的情况不是在价格下跌时产量提高,就是在价格上涨时产量下降。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会对高粮价做出何种反应仍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身不足以推动粮食供给较大幅度提升。要实现大幅增产还需要进行投资,以提高小农的生产率。开垦新的土地来扩大生产也不足以满足未来的粮食需求。到2050年,耍以合理价格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粮食产量的年增幅必须达到1%以上,估计其中80%的贡献率将需要依靠单产的提高。此外,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还能刺激农村经济的前后联系,推动减贫工作。
以提升生产率为基础的大幅度增产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和稳定的激励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商品价格的上涨能传导至农民,而生产者也能购得价格合理的农资,并将其产品销往市场。这就要求解决限制小农生产率发展的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如技术落后、现代化农资和信贷渠道不畅、营销和运输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农村服务和机构不力等。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项必要条件得到满足。例如,印度在农业转型方面取得了成功,基础就是国家对信贷、农资和灌溉基础设施给予了扶持,而这正是市场未能提供的条件。然而,政策不当则可能阻断价格上涨向生产者的传导,扼杀积极性并妨碍产量的增长。
三、 政策应该应对?
1. 有哪些政策问题?
面对快速上涨的粮价,很多国家改变了政策或采取了新的政策措施。高粮价带来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最明显的短期挑战就是要确保贫困消费者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买到粮食,从而避免营养不良发生率的上升。尽管现有的粮食供应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短期内仍有机会采取措施,来增加粮食生产和平抑价格。然而,要想实现供给量大幅上升和更稳定的价格,其主要潜力仍在于中长期的目标。当前的问题反映出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形势仍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这种情况需要纠正。高价格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提供了激励和机遇.但如上所述,要想在中长期内实现供应量的大幅增加,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克服。世界各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种简单、速效和低成本的措施(尤其是贸易政策措施)上,以保障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平抑消费者价格。这种短视行为虽然在紧急情况下完全可以理解,但却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增产的中长期需要。在保护消费者免受高粮价影响的同时,需要保持对生产者提高生产率和产量的激励,这是稳定价格和保障供给所必需的条件。为了解决贫困消费者眼前的粮食安全需求,一些政府采取了短期措施,压低了生产者价格,因此也就打击了他们投资于提高生产率和增产活动的积极性。政策措施必须要有针对性,不具扭曲性作用且对农业投资有利。
政策问题不仅局限于农业和粮食部门。高粮价同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对粮食进口国而言,这些影响包括巨额粮食进口开支引起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更大的通胀压力,因为粮食在消费者商品构成中占相当重的比例。对于从世界市场高粮价中获利丰厚的出口国来说,它们可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增加的出口收益,以确保这些收益能用于生产性投资,刺激长期增长。
2. 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各国对高粮价的政策应对在性质和有效性方面均有所不同。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应用了现有政策措施。这种政策应对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针对消费、贸易和生产,而长期措施则相对较少。
保障粮食消费
很多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LDC),已经采取了干预措施,确保贫困消费者通过各种应急措施和“安全网”措施获得粮食。这些措施包括向最脆弱群体——如城市和乡村中最贫困的人群、学童或和住院患者等——分发基本主食(粮食、面包和牛奶)以及购买粮食的现金(或者以工代赈)。还广泛采用了消费者价格补贴,尤其是对主食的补贴。同时,有些政府已降低了消费税。例如,通过以预定价销售公共储备粮或颁布法令冻结零售价,对价格实施了控制。
粮农组织对7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其中55%的国冢已经采用了价格控制或者消费者补贴措施,力图减少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虽然这种措施可能在短期内对控制价格有效,但在预算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成本太高,并有可能扭曲粮食市场。价格控制可能导致定量供应,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收入转移比粮食补贴的扭曲性小,并且能够针对贫困和脆弱群体,而全民补贴的发放和价格控制措施则让富人和穷人同样受益。粮食和营养计划等其他安全网措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鼓励粮食进口,抑制粮食出口
很多国家采用了贸易政策措施,以遏制价格上涨,确保国内市场供给充足。这些措施包括削减关税以鼓励进口、限制出口和出口征税以将供应量调转到国内市场。粮农组织调查的77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已经降低了粮食进口税,四分之一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出口限制——要么是征税,要么是实际控制,诸如出口禁令和出口配额。这些贸易措施成本低且容易实施,在短期是可行的。然而,这些措施可能对以增加国内生产来扩大粮食供给的刺激手段有不利影响,而且,由于其进一步限制供应量,迫使价格继续上涨,也可能对世界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征收出口税能为政府带来额外收入,但一些出口国已经表示,出口限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产品低价格和农资高价格,实际上已经造成谷物种植面积萎缩。降低进口税会减少关税收入,进而可能实质性地减少用于发展的总体预算资源。
促进农业生产
减少生产者税负,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税负,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而广泛采用的政策。各国已经采用生产补贴,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补贴,来加大刺激力度。对化肥和种子等农资的补贴也很常见。虽然这种补贴和生产性农资(例如种子和化肥)的分配可以在短期或中期内刺激生产,但这些计划的成本可能很高,并可能导致这些农资得不到最理想的使用,在长期使用这些计划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尽管已经意识到需要确保充足的粮食供给,但有些国家仍在继续控制生产者价格,将价格设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水平,或者从国内供应商手里低价收购粮食用于储备。此外,以低价出售粮食储备也对价格形成了打压势态,阻碍了国内生产的增长。
3. 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措施?
如上文所述,各国政府对高粮价已经做出了应对,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可以理解,这些措施着重于能快速发挥作用的有限几种措施,以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给,降低国内消费者的开支。然而,不应当忽视提高粮食生产的中长期需求以及单个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到底什么是“最佳”政策选择取决于各种考量,其包括价格上涨的原因、其影响的严重程度、脆弱人群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政策选项和政府可利用的政策空间,财政和预算形势以及实施政策的行政和制度基础设施等。本节将更详细地探讨政策选择,审议各种可用政策措施的优劣。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应对两个基本挑战。其一是为消费者提供直接支持,尤其是脆弱人群中的消费者,通过所谓的“安全网”措施,帮助他们维持粮食消费水平;其二是通过操控粮食库存或贸易,或者在国内农业部门中促成短期生产扩大,来增加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量。从根本上,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产量,才是实现充足稳定粮食供给和稳定中长期价格的基础;必须谨慎行事,确保短期应急措施不要以牺牲此目标为代价。
为贫困消费者提供安全网
“安全网”是一个涵盖旨在帮助脆弱人群的各种计划的统称。它包括有针对性的粮食分配计划、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计划、供膳计划和就业计划。很多国家采用一种或多种安全网计划,人口覆盖面不同,提供的援助也各异。一项就业计划同样也可能是一项得到立法支持的保障计划。有针对性的干预可能是出于预算成本的原因,或者避免资源向非贫困人群流失。虽然这些干预对行政管理来说是个繁重负担,但可以准确瞄准受益者且不造成市场扭曲。“以工代赈’计划也可以做到自动瞄准,主要是通过选择合适的供发放的粮食,即选择适合贫困人群消费的粮食,或者瞄准一个具有最脆弱人群的地区。
在高粮价的背景下,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预算成本和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用了安全网计划。在没有采用安全网计划的国家。考虑到所要求的行政、机构和其他支持,在短期内要实施某项计划非常不易。只有在已有此类计划的国家,才可能在紧急情况出现时将计划迅速扩大。
现金转移包括发放现金或代金券,并可与公共工程计划和/或小额信贷动议的现金挂钩。如果粮食市场运转正常,而且干预的目标是改善粮食获取渠道,那么采用现金转移是合适的。除了提供购买涨价粮食的能力之外,不加限制的现金转移使家庭能够就如何使用现金或如何用现金进行投资做出决策。比加,有些家庭安排了劳力从事农活,所以可能已经生产出了足够的粮食,但可以用于其他消费或者投资的现金却有限。这种干预也能够促进当地粮食和其他商品市场的发展,因为它为私营部门提供激励,鼓励其采用规模更大、更稳定的营销渠道。
然而,在市场运作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在市场与其他市场的结合很差或时涨价反应有限的地方,这种干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为支忖能力的增强会保使稀缺商品出现价格上扬。政策设计要非常恰当。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公共部门的工资,将其作为现金转移的一种手段,可以帮助贫困的城镇消费者;但在另一方面,贫困人口主要从事非正式部门的活动,因此不太可能从中获益。在粮价迅速上涨的地方,需要对现金转移的价值进行调整以维持购买力,而这在行政管理上可能难以操作。
与直接现金转移相比,旨在确保贫困人口获得粮食的其他计划的灵活性就小得多。这些干预包括食品票或食品券以及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例如,以上学或者去诊所就诊来换取)。和现金转移一样,在当地粮食市场运转正常和以改善粮食获得为目的的地方,这些干预是适宜的。食品券可以成为粮食和其他商品市场中同时流通的另一种货币。这样,在促进当地市场发展方面,它们就能起到和不受限制的现金转移一样的积极效果,但往往不能用于投资。与基于现金的措施相比,这些计划的交易成本往往会更高;尽管其目的是限制不当消费,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些干预的设计可能会十分复杂。比如,学校供膳计划可能偏离目标人口,诸如没有孩童上学的贫困家庭。正如现金转移一样,重要的是事先确定干预对私营营销渠道所带来的潜在干扰。假如私营渠道扩大销售的能力有限,那么食品券、现金转移和营养计划等诸多方式就必须与公有粮店的针对性粮食销售结合起来。否则,通过干预促进当地市场发展的次要作用就将大打折扣。
通过发放粮食援助可以直接增加当地粮食供给,这在主要由粮食供给不足而导致消费量降低的地方是最为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现金转移会导致价格通胀,尤其是在市场不能正常运转、或者因市场整合不良(鉴于受到基础设施和政策的限制)而造成粮食供给短缺的地方。粮援也不容易被用于不当消费,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就更为适宜。除此之外,粮援对政府资源的预算压力也较小。
管理好市场和库存,增加粮食供给
很多国家政府还采用了各种其他措施,可以称之为“市场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的措施诸如通过行政法令实施价格控制,限制私营贸易商的库存量,限制粮食在区域间流动,反囤积措施,限制基本食品的期货贸易,为降低市场价格销售公共粮食储备的公开市场业务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措施在发展中国家中一度颇为流行,但在正常年份中就被终止了,因其并非“对市场有利的”措施,或者因为其偏向于私营部门的发展。然而,政府在粮食危机期间采用这些措施表明,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困境。
经验表明,很多这样的措施在很短期内可能奏效。然而,它们也可能破坏稳定,因为商业行为者通常的反应是囤积,这样就会进一步抬高价格,破坏了这些措施的基本目的。对这一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应该是采取措施,培育确保竞争性粮食市场正常运作的各种要素。全社会以及政府均认为,市场支配力的集中是问题的主要根源,农产品半加工品或加工品通常就是这样。解决方案在于有效支持竞争政策,而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
一项重要的市场管理政策是公开市场业务,即出售公共厍存来平抑或稳定国内市场价格。这些做法曾广为采用,但是很多国家目前已经取消了这些做法。尤其是在亚洲,这些措施曾被积极采纳,比如印度粮食公司的公开市场业务、印度尼西亚的Badan Urusan Logistikin以及越南的稻米营销局。政府的半国营企业通过国内采购或者包括粮援在内的进口来维持粮食储备,等到由于季节性原因或因为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使当地粮价开始上涨时,再释放这些库存。
这些措施的作用是在短期内平抑粮食价格。然而,只有在公共库存充足的情况下,才能通过释放公共库存来增加粮食供应量和平抑价格。维持库存的成本很高,这也可能是个问题。此外,释放公共库存平抑价格可能对生产者和贸易者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妨碍扩大生产和投资。与安全网措施不同,这些方法不具有针对性,可能使不需要支持的富裕消费者同样受益。
考虑到与公开市场业务相关的高成本以及可能严生的意外负面效应,绝大多数政府倾向于减少对库存运作的依赖,而更重视贸易政策措施,通过鼓励进口或限制出口来稳定价格。下文将讨论贸易措施。然而,有些国家政府并没有将贸易作为紧急情况下提供可靠粮食来源的办法,因此仍然在实施保持库存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做法。
削减关税,增加粮食进口
进口关税提高了进口粮食的价格,从而保护国内生产,减少国外竞争,并在些过程中增加了政府的关税收入。削减进口关税能提高粮食进口量,增加国内供给,平抑国内价格上升。作为一项影响整个市场的政策,削减进口关税对所有家庭,无论是粮食安全和粮食不安全的家庭,均有影响,这与上文所述的各种针对性政策相反。当价格从2007年一路攀升到2008年时,很多国家起初采取了降低关税的办法,但由于国际价格持续飞涨,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关税。要想让降低关税真正起到抵消价格剧烈上升的效果,原有关税必须足够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约束”关税率可能较高,但是实际征收的关税,也就是“采用”的关税,可能要低得多。现有关税数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关税都没有高到可以利用它在价格飞涨时稳定国内价格的程度。以60个低收入缺粮国为例,2006年对谷物和主要植物油征收的关税已经很低,平均为8%~14%,而且多数低收入缺粮国的关税比这个平均值还要低得多。这就意味着,削减关税,甚至削减到零,也只能稳定国际价格总体上涨中的一小部分,而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2008年的国际总体价格至少上涨了50%。所以,不能仅仅依靠削减关税来应对粮食价格的剧烈增长。削减或取消进口关税同时也会降低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是很多国家预算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将所有粮食进口关税削减到零,那将给最不发达国家带来21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除了降低国内价格以及由此削弱农民和食品加工者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之外,削减进口关税还将使国内农业和食品生产部门更多地受到国际竞争的冲击。激烈的竞争对国内粮食生产是一个挑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去提高竞争力,使消费者受益。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和食品加工部门十分薄弱,不太可能经受得住竞争,尤其是来自享有生产补贴的进口货的竞争。因此.削减进口关税很可能会打击国内农业和食品部门的发展。削减进口关税也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汇率产生影响,因为增加进口就会降低外汇储备。这可能导致当地货币贬值,尤其是在依赖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国家。如果农资也依赖进口,并以日益升值的外汇支付,那么这种高粮价的风险将可能再现,彻底抵消削减进口关税对平抑价格的效应。
限制出口,增加国内粮食供给
粮农组织调查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出口限制,以期确保国内粮食供给量。这些限制包括从提高出口关税到严格禁止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可能是应对粮价上涨所采纳的各种政策措施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分。然而,目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出口税没有限制,而且关于出口限制和禁止出口的规则也非常微弱,基本上不具约束性。将本应出口的部分粮食转移到国内市场,使国内价格下降,这对消费者是一种解救。在采用出口税的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并可能将税收用于资助其他措施,比如安全网。另一方面,出口限制降低国内价格,同时也减少了对生产者的刺激。生产者可能将资源从征税商品生产转移到其他生产。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生产率和产量下滑,这样就可能违背政策想要平抑价格的初衷。然而,人们之所以批评出口限制,主要原因是它导致国际市场萎缩,加剧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从而伤害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如果实施出口限制的国家是相关产品的出口大国,或者相关商品的国际贸易量很小,这种负面影响就尤为突出。出口限制同样具有长期影响,它可能伤害出口国生产者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受到不利影响。对于净进口国而言,作为可靠的粮食供给来源的国际市场的形象将受到损害,导致这些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正如削减进口关税一样,出口限制可能同样影响汇率。由于出口收入下降,对当地货币造成贬值的压力,同时提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包括农资的国内价格(从而进一步阻碍扩大粮食生产)。
克服生产方面临的障碍及体制弱点
从中长期来看,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是稳定粮食供给和价格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从原则上讲,农产品高价格为生产者扩大生产提供了激励。在这个意义上,高粮价可被视为一种机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克服生产方面临的一系列障碍,其中不仅包括农资成本高和一系列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还包括导致营销体系低效、购买农资难、信贷和技术困难等问题的体制弱点。体制弱点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低效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非洲的粮食生产。
总之,要想短期内解决和克服生产方面临的这些障碍是不可能的。然而,立即采取行动仍然有可能使农民能更好地获得必要的农资(例如种子和化肥)从而增加下一生产季节的粮食产量。如果能够有效实施,这些立即采取的干预行动可以提高小农的收入,可能缓解当地市场价格的上涨,进而改善完全靠购习粮食为生的家庭的营养状况。然而,要实施改善获得农资的计划可能需要较高的预算成本。这些计划可能包括生产安全网(例如种子和化肥分发),有选择性地降低化肥和种子成本的智能补贴,以及向有助于减少信贷障碍的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等。改善获得农资的短期行动需要精心策划,以避免各种潜在的负作用,同时要考虑供应更多农资的能力和对私营部门发展网络的影响。在农资市场运转正常和农资供应充足、但生产者缺乏购买农资的现金的地方,可以采用购物券的做法,因为免费发放可能会危害农资市场。在农资市场不能正常运转的地方,可以发放启动包。然而,如果当地农产品市场未很好地整合,那么这种促进增产的干预行动可能会导致当地粮食价格的下滑,损害生产者和工薪阶层的利益。
改善农资获得的短期措施需要和针对体制弱点的长期行动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此类行动包括:通过更加有效的推广系统来研究和推广改良技术,开发市场和信贷基础设施,以及能力建设。尤其需要将支持重点放在农村贫困生产者上,即那些极难对市场变化信号做出反应的生产者,使他们能够扩大生产并销售其产品。通常,他们甚至得不到必要的基本信息,不能就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做出合理有效的选择。他们需要市场机遇、价格趋势、合适的农资组合以及生产与销售备选方案等万面的信息。农业研究要将重点放在这些贫困农村生产者的需求上,通过更有效的推广网络,加强他们应用研究成果的能力。个体小农要想增产时往往受到销售产品和购买农资的经济因素的限制,因为他们不具备一定的规模。比如,化肥运输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点,而向需求量很小的个体小农供应化肥可能就不经济了。然而,如果个体小农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在获取农资(包括信贷)以及销售产品上进行合作,他们就可以从规模经齐中受益。他们可以将自己组织成各个小组,集体销售农产品,这样就可以实现仓储和运输的规模经济。农民组织、合作社和生产者协会都可以帮助小农更好地获得农资,以更好的条件更有效地销售产品。然而,很多生产者组织仍很薄弱,他们同样需要得到帮助,以加强自身发挥作用的能力。
抓住粮价上涨的机遇,促进投资
尽管高粮价可被视为农业增长快速启动的一个机遇,但从长远看,如果高价的额外收益被立即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那么农业部门和农户可能根本无法从中受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体制环境能够帮助创造投资机会,高价格才会对农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即使农业部门未得到价格或贸易政策的保护,或者体现价格或贸易政策的特征,政府都要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价格暴涨对商品生产国产生持续的收益,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国的成本,那么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都必须合理地利用价格暴涨的机遇。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以便为私营商业者提供激励,并为投资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和减贫。这就涉及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政策措施。
能管理高粮价风险吗?
农产品价格的急剧波动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风险,无论是生产者(收入和出口收入风险)还是消费者(粮食进口费用风险)。日益上涨的国际粮价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依赖商品型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更多地利用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得到好处,以回避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合约都可以被看作是针对不可预测的进出口价格变化的套期保值工具。然而,这些工具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稳定出口收入和进口开支,而仅仅是使其更可预测。这可能有助于资金和其他资源的更合理规划。从理论上讲,通过合理套期保值,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进口开支和出口收入的不可预测性。然而在多数国家中,要想通过进出口套期保值来促进粮食安全,首先要克服一系列体制障碍。
政策选择和互补性:双轨方法的必要性
针对最近持续高涨的粮价引发的问题,要想确定适当的政策解决方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既需要采取即时行动来保护脆弱群体的粮食安全.也需要为将来实现更加稳定的价格和供给而奠定基础。保护消费者免受高粮价伤害的措施可能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之间有着潜在的密切关系。如能精心设计互补的政策措施,就可以鼓励不愿承担风险的主粮生产者去冒必要的风险,投资于技术改良。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刺激地方市场的发育,增加交易量,降低波动性。然而,如果设计或实施不当,它们就可能扭曲激励机制,阻碍投资,造成预算资源不可持续的使用。很明显,这种政策冲突应该尽量避免。所需要的是非扭曲性的安全网措施,以便解决脆弱贫困人口眼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结合激励和支持,确保为实现长期粮食安全进行投资和提高生产率。这种双轨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连贯的政策战略,可以避免上文中警示的政策冲突。然而,预算成本可能会束缚一些政府的手脚,而通过内部或者外部借贷为这些计划出资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所以这方面需要国际支持。
4. 国际行动的必要性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对持续走高粮价的合理政策应对应该是一揽子安全网措施,以便满足近期粮食安全的需要,瞄准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同时要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生产方做出中长期应对,稳定粮食供给和价格。然而,人们同时也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资源、机构或知识能力去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安全网的预算成本高,在行政管理上也颇为繁琐。旨在可持续扩大粮食供给的政策对预算要求同样很高,需要扭转对农业投资的下降趋势。为此,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成本较低和易实施的政策,目的是增加粮食供应量和平抑国内市场价格,但这可能会损害生产者增产和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性,并可能对贸易伙伴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需要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国内政策问题也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出口限制,一个国家采取的增加当地粮食供给和限制价格的政策,可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粮食供应量,导致价格上涨。因此,起码需要对政策选择进行国际讨论,促进协调,避免不利的副作用。高粮价问题和政策影响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比如有关生物燃料的政策选择,也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有关系。更宽泛而言,国际粮食市场的发展和政策的诸多方面是世界贸易组织关心的问题,并正在多哈回合中进行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商定的规则对高粮价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
粮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需要全球讨论和国际行动。国际社会应该动员起来,通过缓解高粮价对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群的负面影响,帮助地界上众多贫困农民抓住产品需求上升的机遇来应对国际粮食危机。目前正在通过短期行动来满足贫困人口的即时粮食需要,其包括增加粮援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安全网,提供更多的国际收支和预算支持,帮助支付日益增加的粮食和能源开支,为旨在增加缺粮国农业产量的应急计划提供资金等。在中期,正致力于将农业纳入发展议程的中心,扭转农业投资长期下降的趋势,以确保农业能够继续满足日益增长的、越来越城市化和富足的世界人口的需求。除此之外正在推动更有力的政策协调,帮助各国做出有效的政策选择,在应对高粮价的行动中进行最大限度的协作,避免出现一个国家的市场干预伤害其他国家的情况
满足近期粮食需求的国际支持行动
近期的重中之重是确保最脆弱人群获得粮食。按照上述路线的扩大安全网计划被视为是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途径。这些计划可能包括以粮食、购物券或现金转移为形式的援助,就业计划(以工代赈或以工代现金),学校供膳计划和保险计划。帮助最脆弱人群的针对性计划需要扩大规模。然而,安全网计划涉及巨额预算成本,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粮国,上涨的粮食价格增加了粮食进口开支,加之较高的能源价格,导致这些国家需要国际收支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向这些国家提供国际收支和预算方面的援助。否则,这些重要的发展计划和项目就将面临危险,因为本来就很稀缺的国家资源正在被分流,用于满足近期粮食的需要。
尽管对粮食援助的需求在快速上升,但实际粮食援助量却在不断下降。援助机构发现,由于粮食价格上涨,采购粮食的成本也在增加。这使得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粮食援助机构纷纷提出额外资金的要求,以便至少维持其目前的援助水平。运输成本的上升更是雪上加霜。要解决高粮价,就必须扭转粮援下降的趋势,加强对国际救援机构的国际支持,尤其是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的支持。高粮价和高燃料价格意味着,在资源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粮援惠及的人数会减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粮援已从1999年的 1 500万吨几乎连续下降到2006年的700万吨。在2002—2007年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受益人提供粮援的成本增加了近70%。从2007年底到2008年初粮价的进一步上升意味着,即便想单纯地维持目前低水平的援助也需要额外的成本。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在制定安全网计划并将计划瞄准最脆弱人群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然而,这些组织需要外资源,以便有效地应对目前的局势。
在短期内靠国内生产增加粮食供给存在一定的空间。特别需要将支持的重点放在农村贫困生产者身上,即那些极难对变化的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的生产者,使他们能够扩大生产,抓住高粮价带来的机遇。事实上,当国际价格上涨时,低收入缺粮国(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的谷物生产在2007年下降了2.2%。很多低收入缺粮国的产量仍然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在化肥使用、高产品种、灌溉、综合营养和病虫害防治以及保护性耕作方面,这些国家都相对落后。国际援助可以帮助提供必要的种子和化肥。
对农业投资的支持
高粮价事件揭示了全球粮食供给与世界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平衡的脆弱性,同时也提示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在全球减贫努力中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尽管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人类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尽快让生产方做出反应,恢复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但这些都必须与推动农业持续增长的中期行动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增加农业产业量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很大。产量和生产率之所以没有增长是因为用于农业的资源在减少。需要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投资。同时还需要更多的投资,尤其是在水管理、乡村道路、营销和仓储设施以及研究和推广方面。然而,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投资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除此之外,对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投资步伐也在放慢,尽管业已出现了诸如气候变化和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增加等新的挑战。
对农业的外部援助显著下降是造成用于农业的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量,即双边与多边援助流量总和,已从1997年的439.49亿美元大幅度增加到2006年的1 209.42亿美元(所有价值均以美元现值计)。直接用于农业部门开支的专项官方发展援助也在增加,尽管缓慢得多,从3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0亿美元。
然而,官方发展援助中用于农业的比重却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7%下降到2002年的不到4%。但2006年用于农业的官方发展援助比例可能略有上升。
捐赠方需要提高官方发展援助中用于农业的比例。2008年6月FAO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上,很多捐赠方表示了提供额外资金的意愿,并做出认捐,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近期和中期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全球性衰退的形势下,也必须确保这些承诺得到履行。更宽泛而言,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提高自身能力,以协调而迅速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做出反应,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长期振兴农业生产的技术援助,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也需要采取行动,在国家预算中增如对农业的资源划拨,并出台有利于私营部门对农业进行投资的政策。
改善政策环境
除了需要确保获得关键生产性农资之外,如果生产者要对高粮价提供的机遇做出反应,而且进行必要投资以提高产量和生产率,有利的政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但如上文所述,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价格日益上涨的一些政策措施却打击了生产方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促进国家层面政策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仅因为缺乏有关关键市场变量的可靠信息,比如现有供应量、价格,特别是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库存,政策做出了不合理的政策选择。目前急需建立全面可靠的国际市场信息体系,为更有效的政策选择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国际组织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和支持,帮助它们缓解高粮价的影响,改善粮食安全状况,保护农村贫困农户的土地等生产性资产,使他们能够从高粮价创造的机会中获益。联合国(UN)系统可以推广经验和最佳措施,帮助各国制定政策框架和战略。其中可能包括:
·帮助设计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监测系统;
·确定哪些替代措施可以使生产者对市场改善的信号做出更好的反应,并评估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评估支持水平的变化对粮食商品影响以及税收对粮食商品所产生的影响;
·分析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粮食流通系统,并确定向脆弱群体销售粮食的最佳瞄准标准;
·评估粮食储备应该在减少跨年度价格波动和应急资源短缺中所起的作用;
·确定使私营部门更充分地参与农业发展,尤其是在粮食贸易和农资供应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最有效方式。
利用贸易政策措施来增加国内粮食供给也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出口限制。这意味着需要更好地实现国际政策协调,对此,国际组织可以发挥推动作用。国际贸易政策归属世贸组织的职责范围,其规则目前正在多哈回合中进行谈判,可为应对高粮价的贸易政策应对提供背景条件。下文将对世贸组织规则做进一步讨论。
不仅仅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增加粮食供应、平抑价格上涨。如果生物燃料生产真的占用了本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农产品和资源,那么削减补贴或采用限额将纠正所有市场扭曲问题。如上所述,新兴的生物燃料市场对一些农产品形成了新的巨大需求,诸如糖料、玉米、木薯、油料和棕榈油等基本食品。人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粮食产品被生物燃料生产占用是受政策的驱使,主要是受补贴的驱使。目前正在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生物燃料补贴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生物燃料生产补贴对粮食价格的间接影响,以及从世贸组织《农业协定》或其他协议的视角看,这是否构成交叉补贴。且不谈这些法律方面的因素,如果有些补贴从世贸组织的角度看完全合法,但会对粮食供给、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这些补贴是否应该被取消,这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确保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政策措施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URAoA)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生产过剩以及国内和出口补贴引起的贸易扭曲。沿着这条路线,多哈回合正在继续这一改革进程。在高粮价背景下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必要重新考虑某些贸规则,从而使政府和国际社会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粮食危机。《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或作为其前身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4年规则均没有对出口征税作任何规定,而且目前对出口限制的约束也相当弱,仅仅要求出口方提前通知,并适当考虑这些限制对进口方的影响。对出口限制规定不严的危险之一是使人们对国际市场作为粮食供给来源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如果多哈回合能成功结束,其可能对粮食援助的规则会更严厉。尽管这将防止出口补贴欺诈,但仍需要重新审议非紧急情况下——如极易发生的高粮价事件—— 粮食援助的条款草案,从而设置适当的前提条件,保证在非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提供粮食援助。
第三个考虑因素是特殊待遇国家的覆盖面。目前,抵御贸易自由化负面影响的几项特殊待遇仅限于《关于改革计划可能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的马拉喀什部长级决定》(“马拉喀什决定”)提及的两类国家,即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NFIDC)。除最不发达国家外,还有很多未被列入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缺粮国,它们也要求得到特殊待遇或者获得粮食援助、出口信贷、购买粮食的融资基金,等等。
目前的高粮价危机不仅被用来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尽快结束提供理由,也被用来反对新协议中可能提出的进一步削减保护措施的要求。那些赞成就进一步开放农业市场达成实质性协议的人提出,目前的保护和支持水平已经压制了全球市场价格,打击了很多粮食进口国扩大粮食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导致了最近进出开支的高涨。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提出了证据,认为随着补贴国家产量过剩降低,自由化将对价格产生上行压力。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进一步压缩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其农业发展而提供有效保栌的可用政策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部门的投资,这样会使各国在未来粮食危机中更容易受到快速上升的粮食进口开支的影响。正是特殊保障机制这一为保护脆弱农业部门而提出的机制,成为2008年7月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
总之,似乎目前的规则并不妨碍对高粮价做出政策反应,而且处于谈判中的协议草案也不太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仍可以改进和加强很多规则,使各国在未未能采取更适合于本国及其世贸组织伙伴的政策应对措施。目前的僵局提供一个契机,使得人们就可能减少未来粮食价格危机的潜在负面影响的规则和协议开展进一步的辩论和谈判。
全球稳定供给保障体系
国际粮价暴涨对那些依靠粮食进口满足其大部分国内粮食需求的国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国家中,很多低收入缺粮国更是受到重创。如果要改善低收入缺粮国(粮农组织清单中目前包括82个此类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如果它们不想采取代价很高的粮食自给政策,就需要建立一个双边甚至多边基础上的可靠的粮食供给保障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参照所商定的“合作协议”建立,就像国际能源机构为石油所建立的体系一样。所有相关方可以通过适当的国际或区域论坛探讨并商定这中协系。这些协议也将提供强化的国际合作形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格局。
区域粮食储备能否发挥作用?
全球谷物库存水平低是粮价上涨的一个原因,这引发了有关区域粮食储备是否有助于缓解粮食短缺和降低价格剧烈波动的讨论。如果协调管理得当,区域粮食储备可以帮助各国,尤其是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以稳定的价格获得粮食,特别是在危机时期。虽然这种概念具有充分依据,但计划实施却面临障碍,因为需要感兴趣和参与管理的各方事先达成协议,而事实证明要达程此类协议是很难的。目前,真正存在的这类计划为数极少,而且遗憾的是,这些计划的实施经验也不不尽如人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为促进缓冲库存的建立而设立缓冲库存贷款,其经验表明,利息和库存管理费用往往已经超过了缓冲库存实际获得的微弱价格稳定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同样,东盟大米应急储备是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建立的粮食储备计划,储备量仅高达8.7万吨,相当于东盟国家一天消费量的0.4%(总需求量的 O.1%)(日本农林水产省,2005),因此,对大米价格没有任何影响。
粮食储备在稂食严重短缺时期用于增加粮食供给的作用,可能优于其稳定粮食价格的作用,因为平抑价格要求有充足的资金来进口粮食。因此,应对粮食价格风险更可行的方式应是建立机制或机构,帮助各国为其进口粮食融资。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下。
建立全球担保体系,为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提供融资帮助
由于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短缺期间可能面临为正常水平粮食进口融资的困难,从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起这就是一个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各方达成了“马拉喀什决定”。马拉喀什决定中所提出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国际粮食供资基金。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粮农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所开展的工作表明,在粮食进口需求过高(由于来自国内的打击)或国际价格上涨的时期,发展中国家进口商面临着一些障碍。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就是信贷和风险上限,即出口融资机构(主要是银行)自行规定的面向各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限额。当出现过量融资需求时,诸如最近高粮价引起的过度需求,这些限制就阻碍了为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提供商品的私营出口商和这两类国家内部的进口商获得必要的信用证,以实习出口和进口融资,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有支付能力。从这种逻辑推导出的想法是,应该为金融机构(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一个公共担保体系(国家或国际商定的),以便在具体情况下提高相关信贷的上限。
其实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近年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已经采纳了类似的“贸易促进计划”,以增加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双边层面上,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农业部和其他机构已经这样操作了多年。然而,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进口商的此类做法却微乎其微,而且这些计划中也不包括帮助当地银行进行能力建设的内容,而能力建设正是整个环节中最薄弱的部分。此外,在创立世贸组织的过程中,经合发组织国家签署过一项承诺,要建立一个此类性质的机制。
就是在那种背景下,粮农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于2005年在日内瓦向代表团传发的文件中建议建立一个粮食进口供资基金(FIFF)。该基金无需新的机构或者额外的资金。它可以利用现有的多边基金,为相关进出口国的进出口融资银行提供额外的担保,支付在过高粮食进口开支期间的过高(额外)粮食进口开支。它将通过中央和商业银行向贸易商提供融资,由借贷国政府提供主权担倮。该基金可以利用捐赠方担保,让银行发放相关信贷。与目前的一些国际融资计划不同,该贷款将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比如,借贷国国际收支状况不理想)。然而,按照“马拉喀什决定”的规定,可以对面临粮食危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予以优先贷款。粮农组织估计,在1974-2003年间,要求得到这种担保体系提供“过高融资”担保的可能只占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粮食总进口成本的2%。考虑到人们对维持实体粮食储备是否可行存在疑虑,在当前粮价上涨的背景下,可以及时重新审议这项建议是否合理,并探讨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实施。
动员国际行动
在2008年6月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HLC)上,讨论了采取国际行动帮助遭受高粮价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以及通过何种形式进行帮助。181个国家的代表,包括43位国家元首、100多名部长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高级代表会聚一堂,审议高粮价问题,并研究如何应对挑战。
关于世界粮食安全的《高级别会议宣言》,呼吁国际社会通过紧急协调的行动,增加对受高粮价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会议还敦促捐赠方和国际金融机构为低收入粮食进口国提供国际收支和预算支持,并向国际机构提供充足资源,以扩大和改善这些机构的粮援工作和支持安全网计划。《宣言》要求为各国提供援助,以实施政策和措施,帮助生产者提高产量。不过,在围绕生物燃料及其与粮食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却较有难度,需要就此开展更为翔实的研究。
虽然高级别会议原本并不是一次认捐活动,但一些捐赠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利用这次机会,宣布要大幅度提高资金支持,总计超过120亿美元。从中长期看,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高级别会议的成果表明了人们重新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将其重新置于发展日程之中心,也表明了对扭转以农为主发展援助下降趋势的承诺。高级别会议明确要求增加粮食生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确保粮食安全。
金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Stephany Griffith-Jones, Jose Antonio Ocamp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一、 引 言
2003-2007年,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一轮令人侧目的经济繁荣,年增增幅达7%。该轮经济繁荣的出现得益于全球市场广泛存在的4个因素的推动:特殊融资(exceptional financing)、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在许多国家出现的巨额劳务汇款。前两个因素与上世纪70年代那一轮经济繁荣的情况一样,而三种因素同时出现却是以前所没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个亚洲发动机的崛起是第4个推动因素,它给全球贸易及商品价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自2008年中特别是9月以来,受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目前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些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在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时间里,商品价格曾持续高位运行。价格持续走高与外汇储备充足这两个因素一起推动了全球资本向新兴市场的流动,甚至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也没有改变。然而,目前,二者已双双开始下行。有迹象显示,作为本论繁荣第三个推动因素的劳务汇款的增长已大幅放缓,甚至正在走向负增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知道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增长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2008年第4季度的数据显示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更广泛来看,这些变化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认为发展中国家能避免陷入类似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二、 危机扩散的渠道
人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目前正被促成发展中国家最近一轮经济繁荣的3个有利因素发生逆转所推动:劳务汇款快速增长、资本流入以及国际贸易扩张。本文将首先对劳务汇款做一简要分析(信息不够全面),之后转向对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详细探讨。
1. 劳务汇款
在一些地区,已有强有力证据显示,;劳务汇款出现了大幅缩水的趋势。特别是拉美,2007年和2008年劳务汇款连续两年缓慢增长,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期也连续下降,与最近十年早些年快速增长的势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筑业移民务工收入最为敏感,到目前已连续下降了3年。人们应该可以将其当做2008年从美国汇到墨西哥劳务汇款呈现出绝对减少态势的一个重要解释,不过,劳务汇款绝对减少目前仍是个案。欧洲的劳务汇款正经历着相同的情形,要么增速大幅下降,要么绝对数量减少(比如西班牙,就是一个因建筑业危机而深陷衰退的经济体之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一些移民目的地,尤其是海湾地区,直到2008年第3季度仍然保持着繁荣,劳务汇款并未出现显著下滑。迄今为止,这一奇形似乎还在保持,但未来很可能会因油价骤降而出现变数。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务汇款总体上会在Z008年出现增幅下降的情况(2008年为7%,而2007年为16%),但仍会保持正的且强劲的增长。不过,到2009年,将会出现负增长,小则-1%,大则-6%(Ratha等,2008)。
总的来看,劳务汇款很可能会反弹,因此,它成为危机扩散主要渠道的可能性很低。然而,如果经济衰退加剧并持续下去的语,对劳务汇款的影响可能会加深。
2. 资本流动
与劳务汇款不同,私人资本流动是危机从发达国家扩散至发展中国家的一条关键渠道。其效应会通过这种资本流动的规模及其关联成本显现出来。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流动快速萎缩而形成的脆弱性一定程度上可被其良好的政策和比过去高的外汇储备以及比过去低的外债负担所削弱。如同下文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于缓减这些国家因国际环境恶化而遭受的冲击,但其为实施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所创造的空间比较有限。此外,新兴市场的投资者(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也已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的一个重要源泉,我们将在政策部分再讨论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造成脆弱性的新源泉也已显现,比如发展中国家国内日益成长的资本市场证券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的流失以及快速的利差交易(carry trade)回补(或平仓,unwinding)(这种交易主要通过迅速增长的kanbuqing生品市场工具进行)。此外,发展中国家银行外国投资人所持股份的增加也已证明不是一个增强力量的源泉,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成为更加脆弱的一个诱因。kanbuqing这些银行已撤回其在发展中及转型国家附属机构的贷款,从而来缓解其在kanbuqing国家面临的困难。
在资本流的数量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2008年一直在增加。私人资金流在2006年中到2007年中到达了顶点,在2007年第3季度受次贷危机影响而出现过短暂下滑之后,于2008年上半年有所恢复,但从2008年第3季度开始急剧下滑,到第4季度某些国家已出现负流动。债券发行限于停顿,银行贷款受到重伤,共同基金(mutual funds)资金流动急剧恶化,利差交易回补,从年度数据来看,资本流在2007年达到顶点随后于2008年下滑。人们普遍预期其在2009年将会继续萎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以及国际金融研究所等。)
就融资城本而言,尽管自2007年中以来新兴市场债券的价差(spreads)一直在增加,但这一态势却被基准利率(一般是美国10年期财政公债)的下调大为抵消,导致其收益并未随之强劲上扬。只在2008年6月出现过较大幅渡的增长之后,由于2008年9月中旬全球金融风暴的爆发而再次下行。
资本流数量和价格的变动是股票市场活动从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传导的主要机制。平均来看,以美元计,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自2007年10月末至四月初达到顶峰之后出现了比工业国更大程度的缩水。
新兴市场国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比低收入国家要大,后者融入国际私人资本市场的程度要低。事实上也是如此,流向低收入非洲国家的资本相对有限。虽然有些令人遗憾,但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前启动的债券发行也已停止。受冲击最严重的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引发的不利预期及国内金融体系的极度脆弱共同作用导致私人资本的快速撤离。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资本流的减少也很大,有些甚至令人吃惊。以韩国为例,国际金融研究所所估计2008年外国投资者将从该国撤出大约450亿美元的投资。印度和中国台湾也已出现了负的组合投资(negative portfolio investment)流动。在拉美,巴西和墨西哥受到了衍生品市场损失的冲击,首先来自于利差交易的回补。南非也未能幸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对各种私人资本流动而言,2008年末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发行的中断(在2009年初有所恢复,但数量有限)和银行间借贷的大幅萎缩,二者都是世界范围融资冻结的表现。贸易信贷(trade credit)已成为其一个重要的牺牲品。一些国家,如巴西,已能能够通过向那些无法获取国际私人贸易贷款的出口商提供支持的方式来很好地运用其外汇储备,然而,国际金融研究所和其他一些机构担心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净银行贷款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走低,因为银行的资本状况将限制银行放贷的能力和意愿。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流向新兴市场的银行贷款从2007年最高点的4 100亿美元已下降到了2008年的1 670亿美元。更值得忧虑的是,据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09年跌至-600亿美元。
第二个问题是私人借贷者分期债款总量很大,如加上各种贷款和财团债券的话,据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09年上半年将达到1 300亿美元,而2009年全年将达到2 500亿美元。更为突出的是,一些新兴国家2007年和2008年短期借款额度大幅增加,这也许会在短期资本流逆转时将其至于非常脆弱的境地。韩国和俄罗斯的短期资本流动尤其巨大,这些流动发生逆转已成为其经济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
另一类问题重重的资本流动是来自非银行渠道的净流动,如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2008年7月以来出现的工业国共同基金撤出及利差交易回补导致货币头寸(positions)的大范围逆转,从新兴经济体的高收益资产流向发达国家的货币。这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即使是那些经常账户盈余较多的国家。这也表明一些特定种类的私人企业几乎完全受国际因素所支配,例如全球风险规避,而受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要小得多。
国际金融研究所估计,短期投机利差交易头寸会大幅减少(而银行放款仍会持续高位运行),据此,它预测非银行私人贷款流动将在2009年反弹。然而,这些头寸和公司的透明度很有限,因为这些交易的大部分并不通过交易所,而且根本没有或仅有限度地报备(参见Griffith-Jones和Dodd,2008)。外商直接投资流动一直以来相对较为稳定。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的投资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估计,新兴市场外商直接投资额在2008年下降了10%,经合组织的估计更糟。不动产市场的萎缩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也许更可能导致流向这些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减少,这在拉美和非洲表现较为突出。
官方资本流动则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官方发展援助自蒙特利尔发展筹资大会以来,从2002年的570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1 070亿美元的峰值(包括债务减免),自那以后有微幅下降,2007年约为1 040亿美元。援助资金流动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按现有承诺来看,其增幅将很小,而国际社会强烈要求进一步增加。由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受本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将危及其增长和减贫目标的实现,增加援助尤其必要。然而,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非常严重的话,将会使援助预算无法增加甚至还可能会削减,从而给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带来负面影响。
与官方发展援助这一发展趋势相比,其他形式官方资本流动的态势还不明朗。首先,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及公共部门企业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积极地推动海外投资。这已导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流动净额出现负值,西亚石油出口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其次,由于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甚至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负流动,这一般会在储备货币国家对安全资产的投资中反映出来。第三,近年来,主要的多边发展银行收到的贷款需求在减少,一些国家实际上已偿还了部分贷款。本次危机的发生致使对这些资本流动的需求大幅增加,反映出这种类型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反周期作用。然而,可用资金规模相对偏低,仅为数十亿,而非私人部门融资净额动辄成千上万亿的水平。这一差距表明,全球目前存在比现有可用规模大很多的官方资金需求。
3. 贸易
几十年来,世界贸易显现出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世界贸易比世界总产出扩张得要快,这一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贸易结构的飞速多元化。在2003-2006年最近这一轮经济繁荣中,世界贸易年增幅高达9.3%,比世界总产出的增幅(3.8%)高出两倍还多。第二,在经济周期变动的过程中,全球总贸易对总产出的弹性直线上升,也因此,比生产更不稳定。这一特征的主要含义在于贸易虽然能促进世界经济上扬,但也同样使其下滑趋势乘数式加剧。2001年,全球贸易总量曾出现过萎缩,到2009年再次下滑。从2007年中开始,全球贸易总量增幅开始显著下降,到2008年9月仅维持在约2%的水平。如果我们以甚至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出口国——中国也出现出口和进口负增长现象的一系列报道来做出判断的话,到11月和12月,全球贸易增幅已跌到0以下。
当贸易总量萎缩成为把危机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国(旅游业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服务出口项目之一)的主要渠道时,价格动态将会显著影响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出口绩效。
近年来,无论从持续时间(5年)、繁荣程度还是所涉及产品的范围(世界银行,2009)来看,全球范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繁荣。在这一轮经济繁荣中,包括石油和其他能源产品在内的矿物产品比农产品表现得更为突出。2008年第2季度的情形对此有明显的反映,当时矿产品的实际价格达到了顶峰,大大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均值(能源产品更高,金属产品也一样),而农产品实际价格却仅维持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这是矿产品的繁荣,而非农产品(Ocampo和Parra,2008)。这一情形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矿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显著改善,农产品出口国则保持不变,而制造业出口国却有所恶化(联合国,2009)。
这一差异似乎表明,有多种因素在影响不同类别商品价格的变化。就矿产品出口而言,主要的问题是20世纪最后20年间价格长期持续低迷所导致的投资不足。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需求快速增长,导致其价格飙升。投资虽然增加了,但新投资转变为供给增加的进程却严重滞后。农业方面,尽管因生物燃料需求增加推动农产品价格有所上升,特别是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上一轮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最后阶段,但其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并不严重。
同期,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还包括美元汇率波动和金融投机。这些因素导致商品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在9月中旬金融海啸出现之前,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在7月份就开始波动,随后能源产品价格在8月份也开始震荡。之后出现的全球性信用紧缩导致大多数商品价格的跳水。经历了最大幅度价格上涨的能源产品和金属产品,也遭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
商品价格的前景仍会维持不容乐观的态势。它们已跌至世行最新预测水平之下(包括石油,跌得更多),即2009年能源价格将下跌25%,非能源商品将下跌23%(世界银行,2009)。不过,许多石油出口国和一些金属出口国已经建立了平准基金(stabilization funds),它将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对农产品出口国来说,一般没有这样的缓冲机制。
能源价格下降为许多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好处。实际上,一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能源价格下降将使能源出口国受损,但却会使更多的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受惠。
价格下跌将会从为数不少的依赖外部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在非洲、中东、北非和拉美)投资和经济活力萎缩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商品价格低迷将会是一个把全球危机扩散到贫困国家的主要渠道。对这些国家来说,面临的一个重要机遇是重新设计国际贸易战略来降低其对外部商品的依赖程度。
三、 政策回应
1. 国别对策
由于近几十年来对外开放成为全球性的趋势,目前出现的危机将会对展望中国家产生严重的冲击。上文已提过,劳务汇款将会出现反弹。金融海啸将对那些与全球金融市场融合度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相对较大的冲击,而依赖官方资本流动的低收入国家受资本流冲击的影响则会小一些。在商品价格下降同等程度下,国际贸易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但那些对外部商品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可能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它们大都是低收入国家。那些建立平准基金的国家(通常是能源出口国和一些金属出口国)将有能力利用过去的储蓄积累来缓冲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
国家层面的对策应把重点放在消除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影响和重新设计贸易战略上。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般取决于一国所面临的国际收支约束条件(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ts)。就财政政策而言,还会受到一国近期财政姿态(fical stances,即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基本态势)、既有公共部门负债以及是否拥有一个完善的债券市场(公共部门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从中获取紫金弥补其即期收支失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存在国际收支约束条件的制约,对外融资将至关重要。
表1汇总了90个发展中和转型国家最近一轮全球经济繁荣中3个主要外部变量——经常项目余额、外债和外汇储备的变化情况,每个国家2007年的人口都在500万以上。该表显示了各地区这些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简单均值以及本轮繁荣中在该指标上显示出改善迹象国家的比例。
表1 人口超过500万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部指标
资料来源: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估计。
2003-2007年的主要变化趋势是出现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越来越多。不过,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国家的外债情况却大幅改善,外汇储备积累形势也有所好转,只不过后者的幅度要小一些。负债率降低与国内政策和国际社会减免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有关。对外汇储备积累改善幅度的估计较低,与其不包括国外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平准基金所持有的财政资金有关。
就地区来看,中东、亚洲和独联体在这3个衡量维度上表现最好(独联体在外债方面表现稍差一些)。非洲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但在其他2个方面有显著改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效地避免了经常项目赤字的出现,而且在外债方面表现尚可。中东欧情况最差: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和外汇储备方面基本没有改善。
遗憾的是,对财政指标的表现没有进行类似的分析。不过,就能够获得数据的国家而言,出现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总体上并不多。中东欧和南亚国家财政状况最差,但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中央政府赤字巨大且公共部门负债累累的国家,如拉美的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以及中东的埃及与约旦。
因此,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拥有实施反周期政策的巨大空间。不过,中东欧是个例外,该地区传统上就薄弱的对外经济和财政状况导致这一地区频繁发生宏观经济危机。这种薄弱状况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除了南亚地区两个突出的案例以外(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都必须要调整其传统的宏观经济结构。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财政调整要注意避免再次出现过去顺周期(pro-cyclical,即在经济繁荣时刺激经济,而在衰退时使经济进一步恶化)调整政策的弊端,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维持社会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过去,关注政府收入增加的财政改革计划比大幅削减开支的政策更受欢迎。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一个国家经常项目的状况。对于那些负债少且外汇储备充足但财政姿态相对较差的国家(印度和哥伦比亚是典型代表)来说,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要大于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大多数新兴经济能够避免实施过去历次危机中出现的顺周期货币政策,并跟工业国一道实施扩张性政策。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的政策都是激励国内融资、用外汇储备支持私人企业以及降低国内利率(后者力度较小)。它们应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采取类似措施放松货币政策。
在财政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有所作为的巨大空间。它们应利用这一空间来缓和外部震荡带来的影响口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公共支出应当成为这些政策的首选领域。实施这一政策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框架。营养,教育和医疗方面普惠性政策应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不过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针对穷人的特殊扶持,如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也很有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 缺乏工业化国家所有的传统自动稳定器——失业保险,就需要实施专门性应急就业项目来弥补。在一系列可用的政策中,经验表明减税不一定会带来最好的效果,而拓展税基才应是决策者们要关注的焦点。
虽然贸易机会通常并不可控,但贸易政策能以至少3种途径促进恢复。首先,可以通过综合应用汇率贬值和部门激励等手段来鼓励非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特别是那些商品贸易依赖程度很高的国家。第二,增强国内制造业出口商品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度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第三,更为积极的南南合作kanbuqing通过利用现有融合进程刺激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发挥作用。各国央行之间的支付协定(payment agreements)也能在无需硬通货的情况下促进这种贸易而起到一定的作用。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危机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国内市场作用的机会,这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早已被决策者抛到脑后。事实上,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刺激国内需求而推动全球经济的恢复。保护性政策显然不利于生产激励,是在以邻为壑。但是,在那些将国内市场再次置于经济政策体系核心的一揽子政策中,关注消费品大众市场和鼓励中小企业(一般严重依赖地方市场)的政策也能发挥作用。
2. 全球对策
从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在全球范围扩散的各种渠道来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以前的历次危机已证明这一体系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方面有缺陷,而当前的危机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方面的严重不足暴露无遗。遗憾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历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深层次的缺陷已为人们所洞悉,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却一直裹步不前(Griffith-Jones和Ocampo,2003)。事实上,这次源自发达国家的危机提供了采取行动改革过国际金融体系的机遇,尽管这一行动伴随的风险会主要危及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峰会上,几个国家发起进行严肃改革的呼吁和联大主席组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就是值得赞扬的—个进步。
消除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当前的危机如此严重,显然与缺乏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有关。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金融自由化必须要辅之以谨慎监管的认识已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吸取了这一教训,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和英国却不为所动,放任自由化泛滥,对金融中介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Stiglitz,2008)。
新的监管模式应建立在一个由各国和区域当局组成且功能完备的网络基础之上,真正实施对全球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应对本轮危机的制度结构应充分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安排将不仅能提高应对机制的合理性,而且还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其次,应建立能确实影响各国监管机构的权力架构,特别是对那些大国,包括工业国。最后,人们应该考虑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将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监管组织包括进来,还要纳入那些关注增长与公平的机构。基于此,联合国应在新的制度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前以及以前历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的危机表明如果金融体系管理不善,危机将不可避免。所以,人们越来越一致地意识到,有必要对金融进行更加彻底和有效的监管。其主要目标必须要放在避免未来再次出现系统性风险上。
未来的金融监管应该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D’Arista和GriffithJones,2008)。第一个是反周期性,即要纠正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出现的市场失灵,即繁荣一衰退循环出现。核心的理念是,在风险发生时,应增加所需准备金(provisions)及或资本(Ocampo,2003)。这将有助于银行在繁荣期增强能力并避免过度放贷,同时在困难期维持放贷。
对于现代的、有效的监管来说,第二个原则应该是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要使监管有效,监管者的活动应与市场活动一样得到监管。这需要确保全面均等地透明,以及对所有金融活动、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对最低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也要同时予以监管。实际上,如果银行的流动性同过去一样很强的话,本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偿付能力问题就会小得多。
发展中国家要保证新的监管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牲,这样才能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和特点来使用它们。发展中国家还要推动发达国家改革其监管体制(如衍生品市场),确保自身经济不受其他地方造成的危机所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个重要调整应被纳入改革的进程(South Centre.2008)。第一个长期性的调整是建立一个有意义且切实发挥作用的全球储备货币,这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s)的基础上组建。这种货币应能克服以一国或几个国家货币为基础的全球储备体系所固有的不公正性和不稳定性弊端(Ocampo,2007)。特别提款权也可以用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反周期的官方融资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作体系的中心。这是唯一一条能让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发声的途径。
第三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是国际国币基金组织要在国际收支危机来临时快速充足地放贷,而不受过去放款条件限制,以减轻借贷国的负担,尤其在危机外生爆发时,如资本流突然逆转及/或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国币基金组织2008年10月批准建立的一个规模巨大且快速支付的贷款项目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这个新的短期流动性信贷是一个针对已实施强有力经济政策但仍面临暂时流动性难题诸国的一个可快速支付的融资机制。取得在短期流动性贷款项目下借贷资格的条件是:有关国家必须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此外,还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一年度所做的国别评估。国际货币组织声称,“由于对过去的绩效进行了特别的强调,这一融资机制可在不考虑为某一项资金安排所设立的标准分期、绩效标准、监督体系和其他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每个国家贷款的上限是其配额的500%。
美联储同时也宣布与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央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为借贷请求被拒国家保守秘密,以降低这些国家市场的不稳定性。然而,也存在一种担心,即短期流动贷款“实质上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A类是那些有资格获得无附加条件贷款的国家,其他则归为B类”。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Kemal Dervis(华盛顿邮报,2008年11月2日)所言,“不能轻易地把新兴市场划为两类,一类政策好,而另一类政策糟糕”。这种说辞看起来要比“仅向那些实施合理政策的国家开放短期流动贷款”要好得多(Bhattacharya,Dervis和Ocampo,2008)。
我们应该推行更大且更为迅速的改革,同时更积极地采用补偿性融资来降低遭到外生冲击(与其贸易条件有关)的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调整成本。由于商品价格急速下滑,早就十分紧迫的补偿性融资并未实施,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启动补偿性融资。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加强减贫和增长贷款(PGRF)(用来消除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和外生冲击贷款(减贫和增长贷款之外的一种补偿性融资)显然是不够的,特别在贷款的规模方面。鉴于当前危机的强度和其对低收入国家增长和减贫的潜在破坏(可能使它们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扩大这一贷款迫在眉睫。特别在最近商品价格急剧下滑的时刻,下述与补偿性融资有关的诸多建议更合时宜(更多细节参见Griffith-Jones和Ocampo.2008)。
扩大规模: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相对于冲击而言现有贷款的范围和每种贷款的规模偏小。这包括提供赠款和补贴(允许进行优惠贷款融资)所用的资源。我们应当放宽对贷款范围的限制(比如,提高获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配额挂钩的资源的比例)。
贷款和赠款同样有用: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赠款在应对各类冲击(比如自然灾害)时更有用,会带来更为持久的效果,不过,官方借贷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潜在的加速器,而且可能会激励这些国家调整经济,从而降低脆弱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贸易冲击的贷款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整:应该大幅简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它们太多了,而且很复杂。实际上,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所有贸易补偿性贷款合为一种贷款,即低门槛贷款。I
缩减附加条件:这显然很有必要。对那些政策合理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尤其在起因外部冲击出现收支失衡的时候。
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增长和减贫
目前本轮正方兴未艾的全球衰退需要一个协调性的应对政策框架,包括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扩张性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许多国家都正要实施这类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应加入这一行列,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协同实施扩张性政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一样,与以往危机相比,外汇储备充足且外债负担轻的国家有实施这些政策的巨大空间。对那些不具备这一政策空间的国家而言,应着力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贷款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总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的是让那些规模可观且快速拨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派上用场。
一些发展中大国实际上已具备了左右世界经济格局的能力。尤其是中国其人口数量大,外汇储备充足,而且财政状况量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较大。中国需刺激其内需大幅扩张,并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这将能给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带来好处。
大幅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能同时有效促进减贫和刺激全球总需求增长。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和低附加条件的优惠贷款(例如世行的IDA)对于贸易条件突然恶化(因商品价格骤降和其他外部冲击所致)的穷国避免实施紧缩性政策至关重要。这对穷国继续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有很大帮助。
过去的危机也表明,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在私人融资失效的情况下,作为贷款人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期间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口商可利用的商业贷款出现萎缩,这使得这些国家得以从危机中恢复的一条重要集道被切断。由此,多边及或区域发展银行提供巨额商业贷款及或担保应该是应对危机各类政策当中的核心环节,不应附件任何条件限制。为弥补私人资流动骤减留下的缺口,这些银行应迅速扩张其贷款规模。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危机应对措施缺陷时所指出的,官方借贷的规模与私人资本流动缩减的数额相比还很小。因此,如果信贷紧缩持续下去的话,扩大多边发展银行贷款的规模就显得至关重要。
3. 由发展中国家资助的区域应对措施
在改革的所有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应该与区域机构如清迈倡议或拉丁美洲储备基金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由于外汇储备充足且能被有效利用,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上述合作方面占据了有利的位置。2008年年中,发展中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高达5万亿美元。除此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其资产总额也超过了3万亿美元。各国央行之间建立的货币互换协议,用以充实储备资金或支持区域债券市场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通过加强对现有机构的投资或组建新的机构,这些储备资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被用来增强由发展中国家所支配的区域发展银行发挥作用的能力。
多边发展银行应维持其在国际发展协作框架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对人类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不过,由发展中国家所控制的区域和次区域金融机构也应发挥重要的补充功能,这些机构使发展中国家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且拥有了主权感。此外,区域和次区域发展银行还特别适合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
如果发展中国家将其外汇储备的1%,约500亿美元,用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实缴股本(paid-in capital),假设贷款和股本的比例是2.4,按上述金额扩资的区域和次区域发展银行将会创造每年1 200忆美元的新增贷款。这在当前的情境下弥足珍贵。
通过扩张或新建区域及次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中国家能为其提高自身当前及未来放贷的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最终实现发展的目标。鉴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外汇储备数量巨大,我们认为现在已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区域性发展银行的网络实际上已经开始运行,只不过在各个发展中地区发展的进程很不均衡。这些机构的发展和成熟很值得人们去期盼。
为什么多哈发展议程对贫困是不友好的
(Anne R.Williamson发展经济学评论)
一、 背景介绍
多哈发展议程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它是围绕农业谈判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问题进行的。农业贸易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视为谈判中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出于分析上的需要,关于发展,这里采用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极度贫困人口的减少,并探讨了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如何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可以考虑,如果说把改革的议题从谈判桌上完全抛开的话,那么与本应实现的政策目标比起来,多哈发展议程将会变得对贫困更不友好。而且通过以往的分析发现,只关注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补贴并不属于明显的贫困友好型(Hoekman等,2004;Anderson等,2006; Hertel等,2007)。我们支持这一观点,并且也在目前的研究中注意到,如果把具有局限性的改革要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会降低这些国家在减少贫困问题上的谈判能力。
基于涉及的贸易保护模式,我们建议通过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这会降低农产品价格)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成效,看起来这两种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把贫困线收入水平分解为收入效应、税收效应和支出效应变动的共同结果,同时也是为了在15个发达国家的样本中识别出导致贫困减少的起因。
我们采用以往关于多哈发展议程的模拟分析,比如Hertel&-Winters(2006)和Hertel等(2007)通过构造仿真的多哈回合成果(也即农业支持减少的措施),并采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GTAP)来估计这些贸易政策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生产要素、商品价格和政府收入的影响。而研究所使用的是15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别住户家庭数据中的要素收入和消费数据,并且在7个收入组之间都对贸易政策的减贫影响进行了预测。这15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约10亿人口以及1.5亿以上的贫困人口(按照一天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本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建模方法跟Hertel(2007)的一样。Hertel(2007)着眼于富国和穷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仅仅注它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影响的净效果。所以本文就集中研究如何分解不同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行对比。我们相信,这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尝试关注多哈回合中被忽略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对贫困产生的影响。
二、 分析框架
贫困模型
贸易政策的改革,使得估算贫困人口变化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选择(Winters等,2004;Hertel和Reimer,2005)。本研究以Hertel等(2004)使用的系列模型方法为分析基础,它源于全球贸易模型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微观模拟模型,在考虑了消费者需求体系、相关的效用函数,并且在定义了效用贫困线之后,如要估计贫困的变化,就可简单地通过估算低于效用贫困线的人口的比例即可。
Hertel等(2004)-个主要的研究发现就是根据主要收入来源对所有住户家庭进行分组异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家庭几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于农地经营。样本里最为贫困的一些国家中,一国的贫困程度通常取决于完全从事农耕的农户家庭,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价格的提高使得穷人更容易受益。但在其他国家里,一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则取决于对食物价格上升异常敏感的工薪族。为了描述不同的收入类型,这里采用Hertel等(2004)在研究中使用的家庭收入五分组法——几乎完全(至少95%以上)是根据收入对所有家庭进行分组。本篇研究则把所有家庭划分为七个组:农业个体经营者、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农村雇佣劳动力、城市工资劳动力、转移性支付受益者;剩下的那些家庭可再划分成两组,即农村多元化阶层和城市多元化阶层。
鉴于研究强调的是贫困人口,这里使用的是一种被完全分解的贫困弹性,以此来分析贫困线附近的所有家庭。分析的前提是第r个地区的第s个组的人均收人累积密度函数,即Frs=(y)。如果用 表示在最初价格p下的第r个地区为达到效用贫困线而需要的收入水平,那么
表示在最初价格p下的第r个地区为达到效用贫困线而需要的收入水平,那么 就相当于计算的是贫困率。由于假定一国的所有收入组有着相同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价格,那么收入贫困线就是唯一的。研究关注的是每个收入组s的贫困人口的弹性,即
就相当于计算的是贫困率。由于假定一国的所有收入组有着相同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价格,那么收入贫困线就是唯一的。研究关注的是每个收入组s的贫困人口的弹性,即 ,也就是关注位于贫困线的家庭的实际收入所出现的微小变化。假设商品价格不变,并给定函数
,也就是关注位于贫困线的家庭的实际收入所出现的微小变化。假设商品价格不变,并给定函数 ,弹性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弹性被定义为非负数):
,弹性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弹性被定义为非负数):

表1的前半部分给出了本研究15个样本国家的各收入组的贫困弹性(正数)。贫困弹性的最小值是0.000 6,它来自于赞比亚的农业个体经营者。在这个收入组中,几乎所有的人口都位于贫困线以下。贫困弹性的最大值是3.63,它来自于巴西的城市多元化阶层。在这个收入组中,人口密度在贫困线处变得非常高。
表1后半部分给出了本研究15个样本国家的各收入组对于总贫困的贡献率。尽管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的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家庭在贫困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完全从事农耕的家庭和农村多元化阶层家庭依然是贫困人口中的主要群体。表示一国贫困人口变化(受要素变动和商品价格影响)的等式为:

式中,表示在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率在一国总贫困率中所占的份额;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弹性;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弹性;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表示第r个地区的要素j带来的税后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的要素j带来的税后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可以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计算得出,而函数公式则与达到效用贫困线所需要的消费支出水平有关)。
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可以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计算得出,而函数公式则与达到效用贫困线所需要的消费支出水平有关)。
表1 样本国家的贫困分析数据
注:*各收入组的竖列数值是考虑了收入变动之后的贫困人口的弹性。最后一列是国家的贫困人口弹性,它是根据对每个国家的各收入组所占贫困份额进行加权求和而得到的。作者使用的是国别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来估算弹性。
**各收入组的竖列数值是贫困人口比例。这一比例值来自于国别家庭住户调查数据。
如果要用另一种税收手段来代替因贸易改革而损失的关税收入,就需要对税收构成进行进一步地分解分析。Hertel&Winters(2006)发现,伴随着贸易改革,选择一种税收收入替代工具对贫困有着非常显著地影响。由于相对价格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非常重要,也由于研究希望能把贸易改革对家庭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分离开来,就有必要使用某种变量来标准化市场工资和生活成本.这里诜柽的工具变量是净国民收入。
那么,一项贸易改革对一国贫困影响的分解方程就可以表示为:

式中, 表示在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率在一国总贫困率中所占的份额;
表示在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率在一国总贫困率中所占的份额; 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弹性;
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弹性;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表示第r个地区第s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表示第r个地区的要素j带来的市场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的要素j带来的市场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净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净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的替代性收入税乘数的变动率,同时Tr=(l+tr),t是第r个地区关税替代工具的税率;
表示第r个地区的替代性收入税乘数的变动率,同时Tr=(l+tr),t是第r个地区关税替代工具的税率; 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
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
所以,方程的第一项就是收入效应,相对于净国民收入,它能够识别工资收人中某一项的变化;方程的第二项就是税收效应;第三项是支出效应,相对干净国民收入,它能识别贫困线家庭生活成本变化。
考虑三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所引致的变化: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率的提高、税收力量的提高和主食价格的提高。由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是收入贫困中的—个重要成分(也就是 >0),相对于收入yr,工资率的提高会增加实际收入,这通常会使那些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移动到贫困线以上。伴随着工资的提高,收入组中人口的百分比变化将取决于贫困线附近人口的密度,描述这一变动的是εrs如果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密度很高,并且这一收入组在国家贫困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βrs),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相对来说会大量地减少。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削减了关税,预计所得税税率tr会提高,这会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再者,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主食价格的提高,那么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就会变得很大,由此可以预计贫困线处的生活成本会增加,相对于净国民收入来说,这会导致地区r的贫困人口增加。
>0),相对于收入yr,工资率的提高会增加实际收入,这通常会使那些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移动到贫困线以上。伴随着工资的提高,收入组中人口的百分比变化将取决于贫困线附近人口的密度,描述这一变动的是εrs如果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密度很高,并且这一收入组在国家贫困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βrs),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相对来说会大量地减少。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削减了关税,预计所得税税率tr会提高,这会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再者,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主食价格的提高,那么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就会变得很大,由此可以预计贫困线处的生活成本会增加,相对于净国民收入来说,这会导致地区r的贫困人口增加。
鉴于一个事实——贸易改革改变了所有的相对价格以及税收收入,那么为了了解国家贫困人口变化背后都有着哪些潜在的动因,贫困分解方程的作用就变得很重要了。接下来的研究就将转向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会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商品价格和税收如何根据贸易政策而发生变化。
全球一般均衡模型
关于贸易政策影响的全球一般均衡分析,其出发点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6.1版数据库(Dimaranan,2007)。本研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试验,以使那些很关键的贸易政策更新至2005年,并把这一年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基准年。同时,也修正了标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强化对于农业改革和模拟贫困影响的分析。研究也保留了看似简单亦属经验性的稳定假设,即农业改革研究中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典型的完全竞争特征。修正模型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多哈改革方案对分配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以解开为什么多哈发展议程对贫困更不友好这一谜题。贫困构成中使用的AIDADS需求体系同样也被放进了全球模型中,以通过这种修正来保证模型中需求方的一致性。因此,虽然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消费模式也有着不同,总偏好也是与那些被用来估计价格变化对贫困线家庭影响的偏好相一致的。
为了识别收入效应,模型也作出与要素市场有关的一些修正。在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最新研究中(Keeney& Hertel,2005),研究者给转换函数(可转换的农场能把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用途中)设定了一个不变的弹性,从而对农业/非农业迁移率建模,这里也采用这种方法。这种转换函数能允许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它有助于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在不同的要素市场上,减少富裕经济体对农业的补贴,对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或是农业资本所有者和非农业资本所有者)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而伴随着富国的贸易改革,发展中国家从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中获得的收益也有着相类似的效果。本研究根据经合组织(OECD)2001年对农业要素市场的调查,来参数化对外统一关税(CET)下的要素流动函数。
研究同时假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使用量的总水平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要素总供给是不受贸易政策影响的。另外,假定是在一个封闭式的经济中,这就使与净国民收入有关的政府支出、税收、净国民储蓄和贸易均衡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固定下来。采用封闭式经济有助于分析贸易改革对整体福利和个体福利的影响。
三、 政策情况介绍
本研究关注的是富国和穷国实施贸易改革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产生的影响,并且是分两个阶段来考察。首先,只关注富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穷国贫困产生的影响。其次,把它与穷国自己的农业贸易改革影响作比较。穷国的农业贸易改革被证明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对贫困的影响时,一些政策制定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低度农业保护会伤害到贫困农民的利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较低的贪物价格有助于减少贫困。研究使用的贫困分解方程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这一难题中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为分析15个样本国家中的贫困总效应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概念框架。最后,在研究中引入了非农业的贸易改革(在富国和穷国中),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改革方案。
我们既把全面自由化作为一个基准点考虑,也把它作为一个经仔细构建的多哈议程考虑——源于所谓的2004年7月的框架协议(WTO,2004)。多哈议程中采纳了Hertel&Winters(2006)关于核心贸易自由化假定。我们在多哈议程中综合考虑了削减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关税。研究假定,对国内产品支持超过20%的工业化国家,应把它们限制国内支持的承诺再减少75%,其他国家则减少60%。然而即使有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缩减计划,突出强调这种约束力也意味着,实际上仅有5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被要求减少实际上的支持力度,基于2001年的报告:澳大利亚、欧盟、冰岛、挪威和美国(Jensen&Zobbe,2006)。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捆绑的国内补贴应减少40%。在这种情况下,Jensen和Zobbe(2006)预测只有泰国的补贴会受到影响。研究也假定出口补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富国的农业关税根据一个分层公式进行削减,关税头15个百分点的边际减少率是45%,关税第15个百分点到第90个百分点之间的边际减少率是70%,关税余下部分的边际减少率是75%。同样的方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在农业中分别是20%、60%和120%的关税约束水平,那么四个区间的边际削减率分别是35%、40%、50%和60%。
WTO谈判的核心问题是部门之间的交易,所以我们在一个准多哈发展议程中也考虑了非农业因素的影响。我们特别地关注了非农业贸易中的市场准人,因为依然很难量化服务和投资障碍,所以短期内的WTO谈判看起来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率是50%,发展中国家的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率是33%,但豁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关税削减。
四、 分析结果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自由化,使所有样本国家的要素相对回报率、生活成本和所得税税率都产生了变化。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提高了,而非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下降了;非熟练劳动力(农村雇佣劳动力)的整个经济回报率提高了,而熟练劳动力(城市工资劳动力)的回报率却下降了。这一结果跟预期是一致的,因为富国的农业贸易改革倾向于使农业生产逐渐从北向南转移,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另外,根据净国民收入来指数化转移性支付,发现转移性支付对收入是没有影响的。
富国农业贸易改革对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价格影响是最大的,往下依次是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而它对非农业生产要素回报率和整个经济工资水平的影响要更小。富国农业贸易改革提高了所有样本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对所有样本国家的要素相对回报率产生了相同的影响。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当然也没必要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来弥补因改革而损失的税收收入。因为税收的变化是由贸易、生产、消费和相关税收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收入所得税税率的略微提高都会强化税收的力量。而除了马拉维之外,这种农业贸易改革也使得所有样本国家中贫困线家庭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和生活成本都对贫困有着负面的影响效果。
把富裕经济体的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在多哈方案下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根据多哈方案而做的部分改革)相比较,预计不管是在全面贸易自由化之下,还是在多哈方案的贸易自由化之下,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很相似,而在多哈方案下的影响要更小一些。研究大体上发现,贫困在农业个体经营者收入组中减少丁,在非农业个体经营者收入组中增加了,在其他收入组中则因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而减少了。所以,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非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外,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效应促使了贫困的减少,这一现象在多哈方案的部分改革措施中可见一斑。
如果要确定一国贫困受到的整体影响,就需要综合考虑每个收入组的收入效应、税收效应(税率变动的影响)和支出效应(消费价格变动的影响)。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收入变动最终都促成了贫困的减少。农业要素回报率、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都足以使贫困减少,即使是在那些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在整个贫困人口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的国家(比如哥伦比亚和秘鲁)。税收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生活成本的支出效应则倾向于使所有样本国家的贫困增加(马拉维除外)。
由于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要确定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国贫困所产生的净效果如何,就需要考察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了。研究发现,收入效应在9个样本国家中(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印尼、马拉维、秘鲁、菲律宾、泰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平均而言,富国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是有助于减少贫困的。与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相比,富国根据多哈方案所做的贸易改革就对贫困显得不那么友好了,其减贫效果也大约只占前者四分之一的水平,这可能就要归因于着重强调取消出口补贴和相对适度地削藏关税和国内补贴的措施了(Hertel&Ivanic,2006)。
发展中国家农业贸易自由化
这里按照相同的方法来分析穷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影响。非农业劳动力和资本,以及熟练劳动力都意识到了改革所带来的最大化收益,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实施削减关税的措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了,也造成了相应的关税收入损失。而这种改革对本就不景气的农业要素回报率的影响是混合性的,一些国家表现为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在那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出口(因南南贸易的增加)的国家则表现为回报率的适度提高。税收和生活成本在所有样本国家对贫困产生的影响效果是相当一致的,同时也伴随着所得税税率的提高(为了代替损失的关税收入)和生活成本的下降(因为消费者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获得食物)。
研究发现,专门从事非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最为一致地表现出了贫困的减少,其他收入组虽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但大致上显示了总贫困减少的趋势。专门从事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和农村多元化阶层家庭是最为直接地受削减农业关税影响(从收入的角度来看)的收入组。这种改革下的减贫模式与富国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呈现出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所表现出的是贫困在非农业个体经营收入组中增加了。所以从公平的角度上看,把穷国农业贸易改革和富国农业贸易改革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就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了,因为它们使贫困人口中不同的群体得益。
穷国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国内贫困的影响是混合性的,但总的来说减少了贫困。鉴于穷国削减了农业关税,这种发现多少是有些意外的。如果对收入所得税进行调整的话,收人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实际上除了巴西和墨西哥之外,所有样本国家的收入所得税提高都对贫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税收提高的平均绝对值几乎是收入效应的一半水平。
为了缓解贫困而削减农业关税的主要用处在于让穷人以世界价格获得食物。研究也发现除了巴西之外,所有样本国家本就不高的生活成本也降低了,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出口需求会提高食物价格。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是通过较低的食物价格而对减贫起着积极的作用。
综合考虑了收入效应、税收效应和支出效应之后,穷国农业贸易改革的总效应表现为除了一个样本以外的所有样本国家贫困的减少。它表明了这些改革甚至比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对于贫困更为友好。另一方面,穷国在多哈方案下的农业关税削减虽然对于贫困是友好的,但它对减贫的实际贡献却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农业贸易改革的总效应已知的话,可以发现只有墨西哥和乌干达的贫困人口增加可归因于农业贸易改革(因为乌干达采取的是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而墨西哥则同时采取了富裕经济体和发展型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由于农业贸易改革造成了贫困线附近人口的显著变动,这意味着把富国和穷国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综合起来进行运用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单独采用任何一种都更为重要。这一研究发现的直接事实推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都促进了贫困的减少,但它们的受益人群是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两者的贫困收益是互补的。
在15个样本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由于根据多哈方案的要求进行了部分农业贸易改革而使贫困人口减少了。不过这种影响却很小,甚至比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下的影响更小,而且这7个国家也并不都表现出贫困减少的现象。
非农业的贸易自由化
非农业关税的全面改革使得大部分样本国家的贫困人口增加了,但与富国或穷国的全面农业关税改革相比,这种影响又要小得多,因为它既混合着贫困增加的影响,又混合着贫困减少(贫困在越南大幅度地减少了)的影响。
与全面的非农业贸易改革相比,多哈方案下的非农业贸易改革在样本国家中多少有些一致地表现出了贫困增加的影响。所有商品贸易的全面改革在9个样本国家中(巴西,智利、印尼、马拉维、莫桑比克、秘鲁、菲律宾、泰国、越南)表现为贫困减少的影响,而多哈贸易改革仅在7个国家中表现为贫困的减少。
所以可以认为,多哈贸易改革对贫困变动产生的影响仅为全面贸易改革约五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对贫困也表现得非常不友好。这源自于一个事实——与全面贸易改革比起来,多哈农业贸易改革和多哈非农业贸易改革都对贫困更不友好。
五、 结 论
本研究考察了多哈发展议程下的贸易改革可能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并把它与全面贸易改革对贫困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与全面贸易改革比起来,研究预期小部分的贸易改革对贫困产生了较小的影响,事实上研究也发现这一情况属实。
在15个样本国家中,国内贫困的变动有着较低的平均绝对值(只占全面贸易改革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不考虑影响大小的情况下,研究描述了这两种政策是否对贫困友好的问题。此外,研究认为全面贸易改革对贫困的友好程度几乎是多哈贸易改革的两倍。
有两个原因能够解释这一结论:首先,富国在多哈谈判下采取的农业贸易改革,这种改革只强调进行小部分的政策改革——出口补贴和减少国内支持,总的来说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重要(Hertel&Keeney,2006),而且尤其对减贫不利(Ivanic,2006)。研究通过比较富国在多哈谈判下采取的农业贸易改革和全面贸易自由化的一致性趋势来突出强调Ivanic的观点。其次,缺少对于情况的了解,多哈发展议程大大地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本身采取的关税削减。同时也表明,这就是全球贸易改革对贫困最友好的一个方面,并且被作为富国贸易改革对减贫发挥作用的有效补充。富国贸易改革是倾向于提高食物价格的,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则通过削减商品关税来降低穷人获得食物的价格,这就促成了贫困的普遍减少。
第四部分
减贫实践和减贫案例
非洲能从中国的减贫成就中学到什么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
“非洲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现象的出现,通常被解释为后者对前者自然资源的需求。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非之间关系朝着更为密切的方向发展,更多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经济模式的榜样。中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摆脱贫困并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之一的例证。”(Ca lestousJuma,2007)
一、 引 言
正如中国政策决策的大多数方面一样,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更为实用的经济发展。中国对非洲地区的战略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输送资源”转向从非洲地区进口石油以及为其建设道路、港口、学校和医院。中国日益成为非洲大陆的主要投资者和援助者,这一角色的转变不仅得到了非洲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吸引了包括自殖民时代开始在非洲扮演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目光。一些观察者正在密切关注这种。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由此预测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
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其国内减贫政策的启示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欧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在过去25年中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目前现有的最完整的数据显示,在1981年中国大陆的居民中有2/3都生活在1天1美元(1993年国际价格)的标准以下。同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SA)这一比例仅为大约40%。然而2004年,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这一比例下降到10%以下,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保持在40%左右。图1展示了中国和SSA(以及除中国以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率的变化。中国减贫的趋势是1981-2004年间大约每年降低1.9%,SSA则为每年0.1%。即使忽略1981年中国的数据,这一比例也是每年下降1.4%,而除中国以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则仅为每年下降0.4%。如考虑人口增长,贫困人口数量下降速度的对比则更为明显。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例是非洲贫困人口的4倍,而1996年,SSA的贫困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换句话说,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1天1美元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5亿,而非洲则增加了1.3亿。

图1 1981——2004年中非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Chen和Ravallion,2007.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如此巨大的减贫差异面前,人们自然会问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如同Juma(2007)所述的非洲“经济模式的榜样”。来自中国的私人投资和援助将会使非洲的穷人受益良多,然而,吸取国内发展政策方面的教训是否让非洲获得更大更长远的裨益呢?
当然,非洲这些年来饱受冲突纷扰之苦,与中国的长期稳定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人们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314的非洲首脑被暴力夺权,即使到90年代中期,这样的情况仍然还普遍存在。相对于非洲的内乱不断,包括1/4的SSA国家经历了政府倒台(Van de Walle,2001),中国则在过去30年可谓一帆风顺。不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也曾有类似的状况发生,与非洲同期的状况并无显著差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动荡,前者甚至造成了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一次饥荒,死亡人数大约为1 500万到3 000万。然而正是这样的动荡催生了政策变化。目前,非洲政坛权力的更迭也开始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000-2005年之间,以规范的、非暴力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的比例占到80%(Posner& Young,2007)。
然而,非洲要想学习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仍需谨慎。一位德高望重的季洲发展观察家曾叹息“强调移植西方的制度实践往往会忽视对非洲适应性的关注,”(Hyden,2007),移植西方的理念存在巨大的风险,同样,假设整个垂洲只要复制中国的某些特定政策就能实现中国那样的成功也未免过于幼稚。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成就应当归功于一系列的(通常是激进的)经济改革,从高度政府调控逐渐转向市场导向。这些改革的成功主要基于独特的中国环境,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缺乏借鉴意义。
保持谨慎也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对于非洲来说,不仅需要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经验,也需要避免中国发展路径中的某些教训,例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同时,中国也并非非洲所能学习的唯一典范。中国的邻国越南在减贫方面毫不逊色,但它采取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政策。此外,在求助于远东地区之前,非洲首先应该将目光投向本地区。在非洲大陆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于非洲贫困也有大量的研究和实践,非洲人民完全可以从中获取经验。
必须承认,非洲目前也面临着一些中国即使在1980年前后也不曾遇到的困难。首先是过去政策失败的消极影响,例如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研究和推广相对薄弱的公共支持等。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会发现改革之初的中国和今天的非洲国家之间存在两个巨大差异:非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而人口密度更低。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SSA相比,“1天1美元”的贫困人口比率非常按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这一比例约为40%),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则低于除埃塞俄比亚和毛里求斯之外的所有国家。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增长速度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更低,这就意味着非洲国家需要获得比中国还要快的增长才能够实现中国那样的减贫成就。
其次,非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国低得多。关于低人口密度条件下非洲发展的成本已有很多研究,Herbst(2000)认为非洲相对充裕的土地使国内冲突减少,而(Herbst基于欧洲历史认为)这种冲突有助于在更长时期内维持一个强权国家。(而非洲的政治地理,即基于殖民分割的虽然武断但确定的边界划分,也无助于维持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权国家)。关于低人口密度的代价还有其他讨论,例如不利于技术创新,并且也会导致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等的供应成本更为高昂。
社会不平等程度更高以及人口密度过低等也直接加大了中非之间的差异性:非洲国家的国家机构通常较弱,影响了对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初始条件影响了减贫进程,但是这些通过政策都能够得到改善。例如非洲的高抚养率(主要是由于高生育率),及艾滋病导致的高劳动力死亡率对增长和减贫的限制。2006年.SSA总人口的43%是0~14岁,是中国同期的2倍多,比中国1980年前后的比例也大得多。目前,SSA的人口增长幅度(2000-2006年间为每年2.3%)不但高于中国目前的增幅(0.6%),也高于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增幅(1978年的年增幅为1.6%)。在1980年前后的改革开始之前,中国就已经进入了“人口转型”时代,而许多非洲国家也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也有反复的例子,例如肯尼亚的出生率又开始回升)。
抛开今天的非洲国家和1980年的中国之间这样那样的明显差异不谈,SSA毕竟是48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SSA和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方面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与许多同样拥有多民族、地理分散的小国相比,作为一个同质性很高的大国,中国由此得以在公共管理、内部产品供应、外部贸易谈判、国际市场、劳动力转移(通过降低劳动力生产率的地区不平等,大幅提高产出)、减少和管理冲突等方面更加有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洲无法向中国学习。本文将不局限于介绍中国的特定政策,而是通过理解中国改革的过程,及其从危机走向成功的原因,更深层次地探讨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其中一些经验不言自明,一些经验则可能出人意料。本文将更进一步从审视中国减贫成功的原因人手,再探讨对非洲的启示。
二、 理解中国(不均衡的)减贫进展
到过中国繁华首都的人,包括亲临2008北京奥运会的人,在听到中国仍然有10%的人口生活在与非洲40%人口几乎同等的贫困状态中时,无疑都会诧异,但是他们如果到中国内陆的农村去,就会发现极端贫困现象仍然是今天中国的顽疾。就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和非洲,农村地区的生活标准都比城市低,然而城乡差距在中国要大得多。2002年,22%的中国农村人口居住在1天1美元的标准之下,而在城市,这一比例仅为1%。相对应的是在SSA,居住在这一标准之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为51%,城市人口比例则为40%。
中国城乡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至少要部分归因于改革前就已根深蒂固的户口制度,这一制度大约始于1950年,类似于一种国内通用的护照。在这种制度下,农村居民即使进入城市,如果没能获得城市户口,也很难享受城市的服务,而获得城市户口非常困难,成本高昂,对于穷人来说更是难以负担。中国的户口制度后来进行了调整,放松了限制。事实上,虽然对国内人口迁移有着严格的限制,中国仍然实现了切实的城市化,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980年的19%上升到2006年的44%,迅速的城市化也是中国减贫的原因之一。分析显示,即使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采取相同的贫困测量指标,仍可将中国在1981-2001年减贫成就的1/4归功于人口的城市化(Ravallion和Chen,200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非洲由于城市化未能带来经济增长,穷人受益甚微。
为北京奥运会而来的游客一定会将中国蓬勃发展的、以城市和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也归结为减贫的成功因素。中国的工业发展令人侧目,在1985-2005年间年均增幅为12%,高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也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Dollar(2007)认为工业发展也促进了技术传播,管理水平提升和建立全球生产网络。与许多SSA国家不同,中国的政策鼓励这些外国投资。
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也就是说,是在减贫最大成就之后。从1981-2004年居住在1天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的减少,有2/3都发生在1981-1987年,而40%都发生在1981-1983年(Chen和Ravallion,2007)。然而,1979-2005年,中国有80%的FDI都在1995年以后进入的,而这段时间(1981-2004年)里贫困人口数量仅仅减少了15%。显然,FDI不是中国减贫成就的“秘方”。
中国的减贫成就也常被归因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制造业的扩张(世界银行,2002)。然而这一解释也面临与FDI类似的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催生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贸易改革,改革人民币汇率,为出口商提供优惠税制,在香港附近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国内贸易自由化也得到积极推进。然而,主体的贸易改革并没有发生在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的20世纪80年代,但不能否认的是经济特区的设置(自1986年以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显著贡献,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的这一阶段。
对贸易量(出口额和进口额占GDP的比例)数据的时间序列的考察,证明贸易扩张并不能在短期内带来减贫。Ravallion和Chen (2007)发现贸易量变化和贫困人口数量指数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0。而即使加入对物价上涨的控制,贸易量变化(无论是以当年价格,还是以2年前的价格核算)和主要的相对价格和政府花费也并不显著相关。
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也同样证明贸易改革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非常小。Chen和Ravallion(2004)考察了自1995年以来(直到中国加入WTO)的关税改革在家庭层面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贸易改革对家庭平均收入有积极影响,但是对不平等没有实质性的总体影响,而对贫困的总体影响也非常小。如果考察长期影响,可能会更为乐观(例如通过增长来推动新技术和新知识)。
Lin和Liu(2008)认为贸易扩张本身并不是中国减贫的促进因素,而是整体的发展政策促进了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对农业增长和对外贸易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相对劳动密集的省份和时段,贫困发生率会更低。这被解释为“发展战略”的效应,即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他们也证明,对外贸易量越大的省份和时段,贫困发生率会越低,这也反映了发展战略的不同。
在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初始条件非常适合于通过吸收劳动力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来推动迅速减贫。这种战略仍然需要有足够的基础教育。即使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工种,也需要基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但是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较好,改革初始之时,劳动力基础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数量充足,且工资水平低。
然而,即便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部门通过吸收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对减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大量贫困人口的减少是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的。Ravallion和Chen(2007)通过分析和回归的方法,认为1981-2004年间农村经济增长要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经济增长。同样,用部门产出比例作权重,对减贫率和部门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第一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对减贫的贡献确实高于第二产业部门(主要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部门(主要是服务业)。事实上,第一产业部门增长对减贫的贡献率是第二或第三产业部门的大约4倍。
可以认为,早期的农业改革对减少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成就,与后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就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解决农村人口(也就是发展制造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的来源)在食物、衣着、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基本需求问题,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难上加难。下文将会论证,虽然某些特定的改革是中国特有的,改革的这种先后次序对非洲也有重要的启示。
三、 中国的不平等在加剧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图2展示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每10年增加7%的速度意味着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会更加严峻,到2015年左右会达到50%。同时,虽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显而易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平等程度都在下降。
不平等加剧源自多种原因,例如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回报率的上升。不可否认,至少在起初阶段,某些不平等是“良性的”,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但是其他的不平等对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因为它们会产生机会不平等。中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新的不平等已经使未来的增长和分配令人担忧。中国不同地域生活标准巨大的不平等使公共资源分配更加不平等,也使每个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之间的机会更加不平等。

图2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Ravallion和Chen (2007)。
不同模式的增长也影响了中国不平等的演变。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的增长会降低不平等程度,这种增长不但会降低农村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降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程度(Ravallion和Chen,2007)。
从分配的视角来看,需要考虑增长类型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城乡维度。在农村地区不仅平均收入更低,收入增长率也更低。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内陆之间,收入机会也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为明显(Ravallion和Chen,2007)。同样地,虽然在某些阶段如20世纪80年代农业有过迅速发展,但是其后就乏善可陈。第一部门在1980-1985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5%,其后的平均增长率都低于4%,同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增长率为大约12%。中国农业的增长并不高,因为同期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平均增长率是4%,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位于SSA(世界银行,2007)。
中国增长过程中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使整体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大打折扣。如果能够保证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如此的经济增长速度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将贫困率降到10%,而不是20年(Ravallion和Chen,2007)。但并不是说以同样的整体增长速度且增长均衡对中国是不可行的,这一计算仅仅体现,在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部门增长的结构不同对延缓减贫会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如果追求均衡的增长,则难以实现高的增长速度,这也就是更公平的增长可能意味着更低的整体增长,亦隐含增长与公平的代价。下文将对此做简短讨论。
不平等加剧的第二个维度是地理维度。减贫的速度在不同地域是不同的,某些省份的减贫进展比其他省份要快得多。特别是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减贫成效要显著得多。如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中国也有很多土地贫瘠、资源稀缺的地区。中国内陆省份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趋势低于沿海省区的50%(虽然对于SSA来说,低于50%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然而,虽然农村收入增长较快的省份减贫率较高,但是在那些增长会对整个国家的减贫贡献更大的省区,收入增长率则并不高。
持续加剧的不平等是否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对增长和减贫付出代价?选择增长还是平等,要取决于不平等的来源,如果是机会不平等加剧造成的不平等上升,则可以看作是增长的一种代价。中国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很多经验数据都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首先,不平等程度随着时间而不断加剧,在快速增长的阶段并没有带来不平等程度的迅速降低。事实上,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的阶段(1981-1985午,以及1995-1998年),平均家庭收入反而增长得更快(Ravallion和Chen,2007)。其次.在第一部门实现最高增长的阶段(1983-1984年,1987-1988年,以及1994-1996年),其他部门的增长并没有放缓。第三,那些农业收入增长更快的省份,不平等程度也并没有加剧,甚至有所下降(Ravallion和Chen,2007)。
展望未来,中国如果不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想要保持过去那样的减贫成就会很困难。以史为镜,我们能够预见中国目前的不平等将会历史性地贡献于未来的减贫——正如在非洲的多数地区,严重的不平等往往带来增长和减贫一样。取决于不平等的来源(即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机会不平等),不平等程度高是个双重难题:不但意味着低增长,也意味着穷人从增长中获益甚少。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贫困对此反应越来越大。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贫困程度如此之高,以致不平等问题并不太令人担忧。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四、 实现有利于穷人的改革
非洲在减贫领域进展缓慢,贫困和失败以及不得人心的政策等相互交织,中国在1980年之前的大约20年间也经历过这种状态。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既得利益阶级和意识形态纷争对中国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破坏,与非洲八九十年代的情况如出一辙。
即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八九十年代的非洲并无本质区别,要理解贫困和糟糕的政策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也并非难事。只需假设有利于穷人政策的采纳程度取决于对穷人赋权的程度,即穷人(用各种方式)影响决策者的能力,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然而,需要注意阈效应,也就是说在政策改革启动之前,必须实现的赋权的最低限度。在达到这一最低限度之后,哪怕赋权的程度很低,在边际效益递减,最终收益归零的情况下,改革也能够快速实施。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将通过提升穷人对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控制力,反过来实现对穷人的赋权,增强他们对政策的影响。这里同样存在阈效应(虽然对这一模式来说并非必需),即在实现任何赋权之前,政策必须发挥最基本的效力(例如充分的脱盲率)。
如图3所示,受到这些条件的约束,经济将会在两种可能状态下(结合政策和赋权)保持均衡增长。图中的2条曲线表明一方面采取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取决于对穷人的赋权,另一方面对穷人的赋权也同样有赖于采取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图中的H点是赋权的峰值,这种情况下政策环境非常有利于穷人,而在L点也同样达到稳定状态,但是与H点的情况正好相反,赋权处于低点。无疑,改革前的中国就处于L平衡(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农村政策声称要向穷人赋权,但是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虽然出于良好的动机,对农村穷人的影响却极其有限)。

图3 多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
当一个国家处于L平衡无法脱身时,对政策的任何修补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一旦实现新的平衡,政策将对穷人更不利,赋权也更难实现。如果移动图3中的“政策曲线”,即在指定的赋权状态下改善政策,会发现新的L平衡将是赋权程度更低,同时政策也更糟糕。同样,如果将“赋权曲线”向右稍加移动,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在H平衡状态下,这种消极影响则不会加剧)。
于是,需要进行政策和赋权的有效改革,才能实现从L点到H点的变化。诚然,促使中国实现向H点的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1980年前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这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起点,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在仅仅几年之内(改革大约在1983年完成),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就消除了集体制,将土地分给单个农户,并且在公社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占有。农户只要交够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自由持有和出售。由于农户能够享有其劳动的全部边际产出,这种制度对于单个的生产者来说是更好的激励。同时,这一制度也是对中国穷人的有效赋权。改革前,中国最穷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对于自己的劳动力配置都缺乏控制权,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他们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随后的村级治理改革(当时还未进行村级民主选举改革)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经济赋权,使农民对乡村事务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也使农产品价格提高,生产资料更易获得,中国也就从L点迅速上升到H点。
中国的历次农村改革都是从危机中发源的,这一次的危机源头是粮食安全问题。集体公社制度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甚至在一些城市地区也出现缺粮的现象。当时,中国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当时众多的建议中,多数都集中在打破集体制,回归农户个人生产。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一危机的解决会遥遥无期,然而改革成就不能归功于一人之力。正如上文提到的一样,当时,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对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正在蔓延,农民属于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时至今日,虽然比20世纪70年代的绝对状况要好很多,他们的相对状况并无改变),他们无力改变社会体系。中国在L平衡的状态下徘徊了很多年。农村改革必须得到国家精英的支持,他们处于权力核心,他们真诚地希望帮助农村穷人改善困境,这一点至关重要。“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毛泽东的逝世也为解决当时农村面临的问题创造了政治契机。
中国改革的成功还归功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庆幸的是,大多数农村人口在社会主义农业政策下被迫进行集体经营后,到改革初始时仍然知道从事个体农业生产。虽然大部分农地属于集体所有,大多数农民都可以拥有一小块“自留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确保这一制度改革能有迅速地获得高额短期回报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中国农民较高的识字率(公社制度的积极影响之一)无疑也有利于在取消集体制时土地的公平分配。
由于这些有利条件,中国在改革失败的集体制度时,通过将经营责任下放给农户,赋权给农村穷人,迅速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私人经营的土地面积超过了集体土地的面积。农村改革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业生产的飞速增长,也促进了减贫的显著成效。1985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日程逐渐转向非农部门,但是农业部门的公共支出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期农村改革的阻力来自于地方精英,他们在改革中失去了权力和特权,一些人还仍然保有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不允许土地私有,甚至在他逝世之后,他的追随者仍然致力于土地的集体经营。改革需要地方精英的合作,而他们有能力阻碍甚至破坏改革。所以,消除这种阻力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于是,社区权威虽然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却仍然享有一定权力,例如分配土地、执行生产指标等。这是当时确保地方领导合作的唯一方式。后来,原本经营集体农场的地方领导变成了农村非农企业(即著名的乡镇企业)的企业家。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并没有推广单一的“模式”,而是给予农民和地方领导一系列选择(Du,2006)。于是,与政府签订协议的单个农民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事实证明,赋予主要相关利益者所有权这一过程本身,对于改革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
各地对于不同经营模式的“实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一些地方,严重缺粮直接导致了集体的解体。(在面对地方短缺时,并非所有的领导都抗拒变革。)在浙江温州地区的永嘉县和安徽凤阳县,当地农民和干部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单个农户,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如果缺乏来自中央的支持,这些分散的实验不可能得到推广。那么,这种支持是如何获得的呢?
1978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决策被打破,采用了一种更为实用的方式,即邓小平所述的“摸着石头过河”。共核心理念非常简单,即必须依托事实来采取公共行动,也就是“实事求是”(Du,2006)。事实依据急需基层实验的成功范例来支撑,于是经营模式创新的实验就用于游说领导层中的守旧分子,以证明改革将会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
这种转向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相反路径的被动反应。一些观察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人平等,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更好的沟通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领导者们最终找到了最适合基层的制度(Luo,2007)。
研究也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个官方支持(但充分自主)的智囊团于1980年成立,命名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正是他们在安徽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和细致可信的实地工作,促使高层决策者有信心对之进行推广(Luo,2007)。(改革过程中建立的其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研究中心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国务院下属的发展研究中心。)
回顾改革历程,1978年中央委员会上所倡导的方法正是今天中国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方式的开端,即依据对政策试点进行的客观“评估”,来影响中央决策。领导们有能力确保这种“集体学习”(Luo Xiaopeng使用这个词来概括)是去政治化的,同时也有可以信赖的研究机构来辅助决策。然而这一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的质量却不高,得出的结果也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推论。诚然,不可能进行随机实验,严格的政策影响评估(无论是采取实验数据,还是非实验数据)在中国也仍然缺乏,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没有参照组的情况下对政策试点进行历史性变化的评估.(在改革初期无需考虑这一点,因为全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这种方法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试点前后对比性的评估往往会忽视不同地区的区别,从而错误地得出某项政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央的新政策经常是在地方试点成功后,作为政策推广而出台的。从试点中总结经验,从而制定和完善中央政策。Hofman和Wu(2007)认为这种合适的渐进主义也是改革过程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当前的改革是在谨慎选择并确认成功的基础上进行,那么未来的改革机会就更大。正如非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试图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一样,中国各省也从彼此的经验和教训中受益良多。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消除贫困的努力和行政能力,使其得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也是中国减贫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
五、 中国成功的政策经验
成功的改革并非需要绝对遵循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但中国减贫的成功还是说明了一些基本观点,即更加开放的市场能够服务于穷人的利益。当制度改革使中国农民有机会进入市场时,他们对市场的激励做出了很好的反应。在这个方面,非洲的农民也应一样。
但是中国的成就并非市场的一己之力。如果不是国家机构有力地执行了支持性的政策和公共投资,改革成功将是不可能的。中国历来重视各个层次上行政能力的建设和巩固,其中也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成为实施农村改革排头兵的成千上万个村庄。(事实上,在追溯这种公共管理的历史时,中国可能是其发祥的源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乡镇和行政村的领导力尤其表现在经济发展领域,对上级政府负责,以及对其辖区内居民负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政治家认为非洲的国家机构长期以来能力不足(Clapham,2001;Herbst,2000;Van de Walle,2001)。幸好还有一些“正常的国家”(如Clampham,2001)正在兴起。然而,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评估,中国的传统是拥有强大的国家机构,非洲在这方面则明显缺乏。政策的执行能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必须建立这种能力。
当然,国家能力必须用于实施良好的政策,避免和摒弃糟糕的政策。中国的经验已经无可非议地证明了这一点,即政府需要避免伤害穷人,所能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减税。中国政府多年实施严格的粮食购销制度,对农业进行收税,并且将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维持在市场价格以下(来确保并不贫穷的城市消费者获得廉价的粮食供应)。这种做法使政府能够在短期内有能力对抗贫困,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高收购价来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虽然这种改革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每个SSA国家都会发现它们自身某些税制和规章是不利于穷人的。对非洲的研究已经表明,过去的政策对穷人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特别是在汇率和公共支出/税收政策方面对城市的倾向。
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来自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方面。中国经验表明避免通货膨胀的震荡对减贫至关重要。高通胀率就意味着高贫困率。(图1所示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贫困人口数量的回升,就是由于当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当然,农村经济的低迷增长也是一个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也印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对减贫的重要性。
高度的国内市场一体化也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虽然中国并未在这一政策领域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阻力已经显而易见,国内贸易虽然日趋和谐但仍然冲突不断。但即使在20年前的中国,这些也都比不上SSA所面临的整合内部市场的阻力。例如,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在非洲一些主要城市之间自如地驾车穿行,大城市彼此距离很近但是位于不同的国家。(例如喀麦隆的商业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Douala和相邻的尼日利亚的商业首都Lagos,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非洲各国与中国各省相比,内部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使得非洲国家各自仅仅只有一个很小的国内市场。
中国经验的另一个方面是仅仅促进增长的经济改革对于持续有效减贫来说远远不够。在获取资产和享受基本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使穷人无法从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在集体制改革之后,虽然公社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资源不能自由流转而保留下来,但是在公社内部有可能进行土地的公平配置。这种公平的土地占有(虽然仅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业增长,以及图1所示的迅速减贫。社会主义制度留下的积极影响以及儒家伦理也使改革开始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很低。在教育领域相对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有助于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增长转化为减贫动力。
增长类型对中国减贫成就的重要性,也值得非洲学习。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那么农业增长对减贫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业增长对于减贫的效力(至少部分)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在打破集体制时有可能实现相对公平的土地配置。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农业和农村发展对于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初级阶段小农生产能够大量吸收缺乏技术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大量文献对经济改革初期是否应将农业增长置于工业化之上进行了持久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产品足够充裕时,才能够将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非农就业。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或是粮食产品商品率很低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产量越高,粮食价格就会越低,新兴的制造业企业所需支付的工资就越低,对非农经济的激励就会越大。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成功,部分因为能够获得廉价的商品。
对中国来说,农业部门是促使产生有利于非农部门发展的积极外部条件的重要推动器。Ravallion(2005)通过对改革后中国4个省农村情况的考察,证明了这种地理上明显的外部性,它来源于当地的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源的回报率,以及基础设施硬件的供应能力的溢出效益。这也进一步说明农村地区欠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对特定的外部性的活动缺乏投资,特别是缺乏对最为重要的农业发展活动的投资。
发展中国家都热切盼望工业化能够加速发展进程,即使是中国,也过早地将注意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开了。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粮食安全之后,农民的收入越高,整体的政治经济就需要为本已处于优势地位的中高收入阶层提供更高的生活标准。中国这种部门和地域优先增长的模式,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也削弱了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这个方面,非洲可以向越南学习,越南在比中国更长时期内始终坚持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视。)
这一经验对今天的SSA更有意义。Christiaensen和Demery(2007)认为非洲的发展战略如果植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会对减贫产生更大更切实的影响。虽然不可否认,非洲将和中国一样必然将发展重点也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但是正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一样,以SSA目前的高贫困率和相对充足(却并不平等)的土地供应而论,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必将是长期有效减贫的核心。
实现这些增长并非易事。需要针对非洲特定的条件(通常靠天吃饭)进行农业科研投资,并使非洲农民得以享有这些研究成果。中国有能力帮助非洲建立自己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SSA在农业科研领域的公共支出在1981-2000年间仅增长了20%,而同期中国的投资则增长了3倍。参见世界银行,2007)。农业的高增长也需要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然而许多非洲国家目前的状况甚至比中国1980年前后改革开始时更差。如果非洲能够就支持农业增长进行正确的投资,其产品的市场就不成问题,中国也将是非洲的市场之一,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农业进口已经进一步放开。
一些非洲观察家认为,中国持续加剧的不平等是降低绝对贫困的必然代价。非洲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非洲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高,很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直逼(一些国家已经超过)拉丁美洲,而那里是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区。
然而,不应该悲观地认为穷国必须要以公平换增长。增长当然会造成不平等,例如由于缺乏技术和劳动市场上教育的高回报率。但是,增长也会减轻穷人所面临的市场约束,从而促进平等。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而国家间增长率和不平等程度变化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Ravallion,2007)。
所以,非洲不应该将中国的不平等看作是高增长、低贫困的必然代价。正如上文论证的一样,中国的经验(至少在某些省份,某些阶段)正好证明了不平等加剧并非是一个贫困国家持续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改革初期)以农业为导向的高速增长也大幅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六、 向非洲传递什么重要信息
近年来,非洲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各国的中央政府以更为民主的形式出现。一个更加稳定、和平的时代正在到来,滥用权力、强取豪夺正在受到制度约束。然而,由于缺乏两个附加条件,这种政治变革对非洲穷人的赋权,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有利于穷人的“更高的平衡”:一是经济政策的显著调整,二是执行政策的国家机构的效力提高。
在有关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及其非洲的启示的文献中,大多提到了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降低生育率以降低抚养率,加快国内市场整合,开放外国投资和贸易,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等等。非洲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需要不懈的努力。
一个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大多数穷人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情况下,启动发展进程时的部门优先顺序。中国自ZO世纪70年代末推动增长的改革就根据实际情况从农村经济人手,当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程度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二样。经济改革的承担者是不计其数的小农,他们得以进入市场,从而提高了生产力。随后,政策自然转移到非农和城市经济,于是吸收农村劳动力对于缓贫来说就更加重要。当然,有人会质疑中国转移部门优先顺序的时机是否正确。然而,对于SSA来说,要想在长期内复制出中国的减贫成就,就必须在短期内给予农业和农村发展更大的优先权。
问题是很多低收入、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将农业部门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将减贫的重任全盘推给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甚至试图迅速建立现代的、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门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发展路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由于人力资源发展不平等而加倍放大。例如农村劳动力得到工作的机会更少,只能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这种就业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并没有直接贡献,甚至会通过金融手段(例如对农业征收重税)和价格扭曲损害农村穷人的利益。穷人,特别是农村穷人不能寄希望于超越农业和农村发展阶段。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非洲极具启示意义。
当然,非洲不像中国刚开始启动改革时那样需要打破集体经济体制,但是非洲国家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农业改革方式,增加公共投资来提高小农的生产力。在大量关于非洲研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发展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的重要性,以及采用和发展农业技术的强烈需求,这就需要如同世界银行(2007)所建议的一样,结合研究、咨询和金融支持来增加农业投入。
在非洲,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不足以在长期内消除贫困,但是仍然是改革之初所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对于推动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进步也非常必要。遗憾的是,农业领域内低生产力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对于非洲的农业生产力缘何低于中国和多数亚洲国家(这种生产力差距巨大并且还在扩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的研究也很少。
多数非洲政府对农业部门的需求都缺乏政治回应(甚至在政策上继续部门倾向),也会加剧和恶化农村贫困,从而只能维持L平衡。正如中国的经验所示,改革也许需要危机来促进。如果当前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能够看作是一个危机的话,就有可能促进各种大规模的改革,吸引投资来扭转非洲农业生产率长期以来的停滞状态。
对于非洲来说,要实现长期的进步,更加高效的国家机构也是一个前提条件。本文始终在强调,中国的经验包括实用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强有力的执行政策的公共机构以及致力于减贫的坚强领导三者结合。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好的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任何变革来改变大量贫困的、缺少权力的人口受制于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政策这种“平衡”状态。相对于非洲来说,中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它的国家机构更强,毫无疑问,这一点有助于中国没有错误地认为更开放的市场会削弱它的国家机构。公共行政和决策过程也确保了国家成为对抗贫困的有效工具。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从各地各式各样的创新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而中央政府又有效地将一个地方的经验传递到另一个地方,并通过可信的实地调研使其得以巩固。
毫无疑问,恰当的政策决策与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相结合是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缺一不可。当国家机构弱时,意识形态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中国对非洲的启示是,如果非洲的国家机构仍然维持很弱,中国的“实事求是”的决策经验也将对它不会有多大帮助。
不应忘记,非洲是48个国家,而不是1个。所以会面临中国不曾遇到的限制(例如经济一体化和政策协调),但是也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上文中提到的非洲国家在特定领域的成功范例无疑将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受益匪浅,正如中国改革过程中走在前面的省和县对其他地区的示范效应一样。但是非洲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将成功经验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这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减少当前和未来的贫困
(Ariel Fiszbein,Norbert Schady等,世界银行)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s)是指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支持,这种支持提供的前提是必须将扶助资金用于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常来讲.人力资本水平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健康和教育?健康方面的投资包括对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定期体检,成长监测和疫苗注射,对产妇进行产前护理.以及要求产妇参加定期的健康咨询讨论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则包括保证入学,出勤率达到80%~85%以及在对在校表现的考量。大部分的CCT项目都直接向贫困家庭中的母亲提供现金资助,有些时候也将这些现金直接拨付给在校儿童。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CCT项目:拉丁美洲所有国家都已实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大规模地启动,東浦亚,马拉维、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国也正在进行试点。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来促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最近像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也开始在尝试。
在一些国家,CCT项目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援助项目。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例,该项目提供了上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一些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家,CCT项目被看作是降低社会不平等、有助于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提供儿童的健康水平、营养状况和入学率以及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方法。但这些目标都能够实现吗?是否有经验证据支撑?如何改善项目的实施?如何在还没有实施CCT项目的国家推行该项目?等等,这些都是本报告将要回答的问题。报告论述了实施CCT项目所需的经济和政治原则;展示了大量关于CCT的经验证据,特别是基于影响评估的结论;探讨了这些制度框架和影响数据对实践中设计CCT项目的启示;最后分析了CCT项目所适合的广泛的社会政策环境。
报告显示,CCT项目确实改善了穷人的生活。通常这种现金转移支付都能够很好地瞄准家庭,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从而减轻贫困,在一些国家,CCT项目的减贫贡献相当巨大。并且报告还显示CCT项目的一些预期的负面效益并不显著,如使受益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等。进一步而言,CCT项目为改革目标偏离的社会补贴、提高社会安全网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切人点。报告指出CCT项目是一项针对穷人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有效方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设计最为精良、管理最为完善的项目也无法满足一个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的全部需求。因此,CCT项目也需要结合其他的干预方式,例如工作福利、就业计划和社会养老等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
报告同时也阐述了项目受益者获得针对特定的健康和教育服务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家庭在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足,例如其父母对这些投资的回报期望值过高而不会对子女进行投资,或者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很大程度依赖外部条件时,这样的家庭就符合了获得资助的条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也优于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当意识到他们的钱能够在长期内贡献于减贫,特别是他们的努力能够改善儿童福利时,纳税人资助穷人的意愿更强烈。
CCT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引导贫困家庭更有效地利用健康和教育服务。但是,对于最终享有的健康和教育的改善程度究竟如何,还缺乏清晰的证据。也就是说,CCT项目增加了这些家庭带子女进行防疫检查的可能性,却不一定能够改善他们的营养水平;在项目受益者中,总体入学率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却不一定能够保证学习成果。这就启示我们,要使CCT项目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最大化,必须与其他项目相结合,提高健康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同时开发其他的支持性服务项目。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针对关注项目产出的条件进行试验,而不能局限于服务获取本身。
一、 CCT项目回顾
过去十年间,CCT项目在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其本身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参加项目的国家数量的上升,也体现在项目规模的扩大上。墨西哥的PROGRESA项目在1997年启动时只有约30万个受益家庭,现在已经增加到500万个家庭。(这一项目在2001年更名为“机会”。本报告将沿用这一新的称谓。)巴西则从巴西利亚和坎皮纳斯市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开始,随后扩展到地方政府,各部门都开展了联邦项目,随后进行了统一和调整。今天,巴西的家庭补助金项目已经惠及110万户家庭460万人。在其他国家,CCT项目扩展的速度虽然没有这么惊人,却也不容小觑。例如在哥伦比亚,项目启动之初设立的目标为40万个家庭,到2007年已有150万个家庭受益。
CCT项目的覆盖范围在不同情境下区别巨大。一些CCT项目是国家层次的,另一些只是针对地区的或更小范围,还有一些只是小规模的试验项目。一些项目要求受益家庭只能将资金用于学校教育,而另一些,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项目则要求受益家庭同时兼顾教育和健康。表1列出了本报告中提到的部分CCT项目。未收入表中的项目,一些是由于可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而另一些则是因为部分地偏离了CCT的原则。
表1 项目规模及其限制条件
CCT项目在社会政策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因项目设计和所处的特定情境而在各地有所不同。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项目规模方面。从绝对值来看,CCT项目的覆盖面从110万户家庭(巴西)到21.5万户家庭(智利)再到仅涉及几千户的试验项目(肯尼亚、尼加拉瓜)不等。而从覆盖的范围来看,则从厄瓜多尔的接近40%到巴西和墨西哥的大约20%,再到柬埔寨的1%不同。从预算来看,CCT项目的成本从在巴西、厄瓜多尔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占GDP的大约0.5%到智利的仅占0.08%而有所区别。最后,受益者的消费水平也从在墨西哥的占平均家庭消费的20%,到洪都拉斯的4%,再到孟加拉、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更低比例而有所差异。
在中等收入国家开展的CCT项目,大多都在寻求一种综合的减贫方式,以能够平衡社会援助和人力资本构建的双重目标。这些项目覆盖了从刚出生(或出生前)到青春期的儿童,要求为他们提供自出生起到5岁或6岁的健康医疗服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入学教育。这类项目大多由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或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其他独立部门负责操作。类似的例子包括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和土耳其的CCT项目。
墨西哥的机会项目是标志性项目之一。这一项目启动较早,并经过了慎重的改革,至今仍然运作得很成功。真正让其得以成为标杆性项目之一的原因,是它一直坚持收集数据进行影响评估,这些数据对公共领域产生了影响意义,由此诞生了数百篇论文,被数千次提及。
巴西也是应用CCT项目的典范。与墨西哥一样,巴西的项目也启动较早,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目前运作的项目(家庭补助金)与墨西哥的项目在覆盖面和重要程度上可以比肩。与墨西哥不同的是,巴西的家庭补助金项目中联邦的力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限制条件方面进行了较为柔和的、渐进的调整,以及更重视针对人力资本构建的再分配。同时,与墨西哥的机会项目不同,巴西的项目并没有设计明确的评估过程,于是也就很难得知其对消费、贫困、健康、营养和教育的确切影响。
智利团结计划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运作方式。项目仅针对极端贫困人群.即智利总人口的5%。这一点有别于经典的CCT项目对不同人群分别量体裁衣的设计。与社工密切接触的家庭开始了解能够帮助他们摆脱极端贫困的行动,从而致力于能够从中获益的针对家庭的行动计划。现金转移支付本身只是想激励受益者们更好地利用社工提供的服务。因此,智利团结计划本身自成一格,虽然其他一些项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它的经验。
CCT项目的另一个原则是关注低收入国家的教育。项目通常只涉及教育领域更为具体的方面,其中一些只关注中学教育(孟加拉的女童中学援助项目,柬埔寨的日本减贫基金和柬埔寨的教育部门支持项目),另一些只关注小学(例如玻利维亚和肯尼亚的项目,以及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项目建议书),也有一些项目二者兼顾(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弱者对策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理念不尽相同。孟加拉的女童中学援助项目是消除当时存在于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的战略的一部分,而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弱者对策项目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防止退学的应对措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项目则是为了应对艾滋病引发的危机对婴儿和脆弱儿童造成的威胁。
CCT项目也需要同其他现金转移项目相同的运作制度,这一制度至少包括几个方面:(1)如何确定对象资格以及批准程序;(2)提供转移支付的机制。同时最好建立监测评估体系,CCT项目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监测设置的限制条件的约束力,并协调运作项目所涉及的不同机构。CCT项目在这些方面都无可挑剔,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转移支付实践的典范。
几乎所有的CCT项目都结合了地域瞄准和家庭瞄准,不只局限于向穷人提供现金转移支付。许多项目也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方式或通过社区审查对象资格的方式,来增加透明度。在许多国家,CCT项目都率先掌握贫困数据,建立或改进家庭瞄准体系。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CCT项目在总体上推动了目标瞄准项目的发展,并提高了瞄准度。
多数CCT项目采用了最新的技术体系进行前瞻性的管理,在监测评估方面尤其如此。CCT项目的两个天然特征,即多社会行动者参与和需要大规模信息管理来保证限制条件的约束力,都在许多方面促进了监测评估的有效进行。多数项目都具备良好的监测评估体系,以及在存档和信息方面的高度透明,虽然并非CCT项目都有过人之处,却也使其非常受欢迎。CCT项目重视评估的风气,超越了社会政策的传统做法。许多项目都基于可信的反经验事实进行了影响评估,其中大多都至少在启动初期进行了实验。这种评估的风气不止在CCT项目之间传播,也对同一国家的其他项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CCT项目的功能及其设计一直在改进。基础模式在早期取得的成功,促使各国去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对社会服务覆盖范围的强调,是否应该辅以服务质量的改善?项目的资助条件是否应该改变,例如进行绩效奖励或是提供其他服务?怎样才能保证项目所支持的儿童完成学业后能够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在不同年纪的儿童之间如何平衡?在某些国家,CCT项目通过调整基本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催生了其他项目的变化。
二、 关于CCT项目的讨论
虽然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减贫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仅凭市场一己之力还是远远不够。公共政策在为市场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提供公共产品和纠正市场失灵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能够促使增长对减贫发挥作用。向贫困家庭直接进行资源再分配是政府能够采取的有效手段之一。虽然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在替代相应的公共投资方面机会成本较高,也可能无法对受益者进行积极的激励,但仍然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转移在许多例子中都是公平有效的。
CCT项目要求贫困家庭以特定的方式对子女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对所要帮助的人加以约束是个悖论。本报告将评述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讨论。
就对现金转移支付加以条件约束有两种主要的论点。第一种认为对儿童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太低,而第二种则认为除非对“值得的人”采取“对的行动”,否则政治经济条件对于再分配的贡献甚小。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对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在两个方面“过低”。首先,如果家庭决策者对子女教育和健康的投资缺乏正确的认识,或者对于这些投资的回报抱有幻想时,即使针对单个儿童的私人投资达到最优水平,也问题百出。例如,父母对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可能估计不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例子可以提供佐证。在墨西哥15~25岁的群体中,对学校教育回报率的期待(根据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进行计算)比实际的回报率(根据家庭调查的数据计算明瑟回报率Mincerian return)要低,而那些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得到的反馈则更为明显(Attanasio和Kaufmann,2008)。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收入调查显示,八年级学生对中学教育的回报率预期仅为1/4到1/3(Jensen,2006)。
父母也可能会严重低估了未来,特别是在对子女投资的回报率方面——即所谓的“不完全利他”。与此略有不同却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利益冲突不仅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相应的,也可能存在于父母之间。母亲可能更倾向于满足她所有子女昀目标,或更加照顾她的女儿。这种倾向使得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更多地给予母亲而非父亲,事实上大多数CCT项目也是这么做的。在许多南亚国家,女孩的入学率比男孩要低得多,然而女性教育的回报率在工资水平和子女健康方面都不亚于男性。对于考虑自身利益的父母来说,对女孩教育的低投入可能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女孩可能需要更多的钱来准备嫁妆,而且会嫁入丈夫的家庭,而男孩更有可能留在家中照顾父母,然而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会导致社会产出效率低下。CCT项目迫使父母将他们的女儿送进学校,是解决这种低效和不平等的性别分化的途径之一。
总而言之,上述这些基于信息的、来自实施者视角的,或是基于行为的观点,为更老套的、专制的、有条件的物资再分配论调提供了微观基础。
对儿童健康和教育的私人投资“过低”的第二种解释是个体的最优水平可能会低于社会的最优水平。当家庭之间的教育和健康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时,就会产生这种结果。从经验来看,许多对健康的投资都有着重要的外部利益。教育方面的外部性可能是训练有素的工人的回报率越来越高,或者教育会减少犯罪。
这些外部性究竟有多大,(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是否是改善这些外部性的最佳手段,仍然无法断定。太多数国家的教育和健康服务仍然需要加以补贴才能够维持,其中许多都是免费提供的。要讨论是否需要进行额外补贴以抵消这些家庭获得教育和健康服务所需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话,那么从外部性的角度看,就需要证明这些外部性足够大。
政治经济学派观点的核心是,目标瞄准可能会减少受益者与转移支付项目的纳税人的相对比例,从而削弱对再分配的支持。大量文献认为解决之道是建立更为广泛的再分配体系,并将中间阶级也纳入其中。本报告认为另一条可行的方式是唤起支持者的利他动机:一个将目标瞄准的转移支付看做“纯粹的救济”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要求受益者为改善自身及其子女的生活采取实质行动,转而加以支持。
CCT项目的理念中,包含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受益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理念通过在大量项目中使用“共同责任”(而非“条件”)一词表现而得以彰显,至少在拉丁美洲的项目中是如此。当条件被看成是共同责任时,受惠者就被当作是有行动能力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成人看待,而国家是这一过程的合作伙伴而非负全责的保姆。在不同条件下,CCT项目可能并非是一个自发的、透明的、无条件的现金捐赠,不是一种公民权利(这种观点更接近于无条件转移支付的书本定义),而是大量的、多采取实物形式的、由不同的提供者如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提供的专项转移支付。这样,对转移支付进行针对“良好行为”的条件约束.与其他的一些限制,例如投票给某一特定政党或加入某一指定社会组织相比,就显得不那么专制。
此外,针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构建而非简单地资助他们的父母,使CCT项目成为一种促进机会获得的手段,从而提高了其政治接受度。毕竟,我们不能因为贫困而指责儿童。于是,利用公共资源支持贫困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使CCT更像一个减贫项目而非援助项目。同时,出于认为母亲能够比父亲更好的使用资金的广泛共识,向母亲提供资助也在情理之中。
结论是,即使某个狭隘的技术评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无条件的转移支付比CCT项目更合适(即没有证据表明贫困家庭获得的信息不充分,或存在“不完全的利他”),CCT项目的约束条件也由于能够带来更佳的政治经济平衡而合情合理。政治进程几乎不可能像穷人提供大量的现金转移支付,除非能够证明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积极的措施”。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即便没有剧烈的政治变化,现金在分配模式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与特定形式的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相结合。
总之,在再分配的基本原理支撑下,CCT项目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穷人对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是次优的;其次,出于政治经济原因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在以良好行为为条件时,再分配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这一基本框架可用于决定是否运作一个CCT项目这一核心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将CCT项目作为合适的政策手段的决策树

三、 CCT项目的影响
从墨西哥的机会项目开始,CCT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对不同项目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可信的评估。本报告十分强调这些评估。的确,离开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项目管理者、国际资助机构和学者们完成这些高质量的评估的努力,就无法撰写这篇报告。有关项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经验证据的积累,一方面有助于现有项目的维持,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类似的项目。
大多数CCT项目都希望消除消费贫困,鼓励针对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投资。本报告严格考察了项目对福祉上述两个维度的影响。
四、 对消费、贫困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总体而言,CCT项目对于家庭消费和贫困具有积极的影响(以贫困人口指标、贫困距或贫困距平方测量)。支付数额最大时,对消费的影响也最大(如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络项目)。同时,由于转移支付都很好地瞄准了穷人,就能够将对消费的影响转化成为对贫困的影响。一些案例中贫困发生率下降非常明显。如(2002年)尼加拉瓜的贫困率降低了5%~9%。
测量CCT项目对福利影响的另一个方法是对比获得和未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家庭人均消费的累积分配。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依赖贫困线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能会过于武断。如果受益家庭的累积分配曲线完全处于控制组家庭消费分配曲线的右边,即所谓的一阶随机占优,那么CCT项目对当前福利的改善就毋庸置疑。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络项目的受益者的案例展现在图2的A组。而B组表明洪都拉斯的情况则乏善可陈,当然在转移支付数额那么小的情况下,这种结果也实属正常。

图2 CCT项目对消费分配的影响(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2002)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注:CDF=累积分配函数。
此外,CCT项目不仅影响整体的消费水平,也影响消费结构。大量证据表明接受CCT项目的家庭会在食物上花费更多。而在食物类中,对营养更高的食物花费比那些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当,却没有接受项目的家庭要多。
当CCT项目启动时,很多人担心会大幅减少成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因为受益者收入水平提高后可熊会花费更多时间进行休闲,或者会减少劳动来保持“足够贫困”的状态,好继续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然而实践中,CCT项目确实对成人的劳动影响甚微。在柬埔寨、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调查显示,家庭中的成人并未因为获得转移支付就减少劳动。
CCT项目并未降低成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但对儿童劳动的减少却十分有效,这也是许多项目设计的初衷。在巴西、柬埔寨、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尼加拉瓜,CCT项目的受益者们都减少了儿童劳动。在一些案例中,减少的幅度非常大。例如,在柬埔寨接受转移支付的儿童中,从事带薪工作的比例减少了10%。
除了可能会减少劳动力市场参与外,家庭某些行为的变化也会影响CCT项目对消费和贫困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因素对转移支付的抵消效应很小,从而CCT项目没有被劳务汇款或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所取代,它们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创收,也无法平衡价格和工资上涨带来的影响。有证据表明CCT项目受益者将其一部分用于投资,这些投资回报随后会带来较长时期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发生,在尼加拉瓜则不然),CCT项目转移支付有助于受益家庭在震荡中保持稳定消费。
五、 CCT项目对教育和健康成果的影响
在每个国家,CCT项目都带来了对教育和健康服务消费的增长,在某些例子中,甚至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项目受益者的学校入学率有了显著增加,在原本入学率很低的地方更是如此。无论是在率先实施CCT项目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拉美的低收入国家如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还是在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柬埔寨和巴基斯坦,这种变化随处可见。CCT项目对防疫服务也有较大的影响,虽然变化不及入学率变化那么显著。
进一步说,由于CCT项目对服务享有的影响集中在那些如果不进行干预就无法获得服务的家庭,所以更加能够实质性地贡献于消除教育和健康获取方面的分化。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女孩的入学率原本低于男孩,CCT项目消除了这种性别差异。柬埔寨的项目虽然覆盖面较小,却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家庭在入学方面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尼加拉瓜,CCT项目不仅提高了极端贫困家庭的学校入学率,也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了监测,如图3所示。阿玛蒂亚·森(1985)和其他研究者都曾指出,贫困有多种形式包括无法获得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基本能力。一个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应该是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CCT项目有助于消除穷人和富人,以及幸运和不幸的人之间的鸿沟。
虽然CCT项目对于教育和健康服务获得的推动已经无需证明,然而其对教育和健康的“最终”成果究竟有何影响,却并不明朗。一些(但绝非全部)评估显示CCT项目有助于特定群体儿童身高的发育,另外也有案例证明项目受益者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回到教育成果上来看,在墨西哥更多地参与机会项目的成人比参与较少的成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更长,但是由于差异不大,对加薪的影响也就并不显著。同时,一些评估表明更高的入学率并不一定必然会改善学习绩效,即使排除了不同学校的因素以后,结论仍然如此。项目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即高入学率却没有高产出,并非CCT项目所独有,但仍然值得警惕,告诫我们CCT项目在促进受益者的自我学习方面仍然有限。同时,也有证据表明CCT项目对于儿童早期的认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Macours,Schady和Vakis,2008;Paxson和Schady,2008),这就意味着早期干预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意义,项目对不同年龄和不同年级入学率的影响就能够证明这一点。

图3 影响随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而呈现异质性(尼加拉瓜,2002)
资料来源:Maluccio和Flores,2005。
关于CCT项目对教育和健康“最终”成果的影响甚微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一个可能是CCT项目的设计框架并未解决家庭所面临的主要限制因素,例如养育子女能力和经验欠缺、缺乏充分的信息,或对教育和健康的投入不足等;另一个可能是社会服务质量低下,对穷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单纯地加强服务的获得和享有无法建树更多。
六、 政策和设计
上文已经讨论了适合开展CCT项目的环境。那么,当一个CCT项目付诸实施时,该如何设计?接下来,我们将讨论CCT项目设计的问题,包括选择受益者、监测约束条件、转移支付额度和所需的其他配套干预。
选择目标群体
任何决策者在酝酿一个CCT项目时,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都是选择符合条件的受益者。CCT项目的目标群体是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贫困家庭(他们有着较强的再分配意愿)。
实践中,CCT项目选择目标群体需要基于贫困状况确定合格标准。和其他社会援助项目一样,选择“正确的”瞄准措施和合格的临界点(即谁能符合穷人的标准)都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步是确定瞄准的标准(即那些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家庭),这一步骤更为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符合贫困的标准,CCT项目只要确认这个家庭的子女处于“合格的”年龄,并送他们去上学或带他们去看病,就会准予。有时候也会采取以人口统计学特征瞄准的方式,直接对人力资本最为欠缺的群体提供转移支付。一些国家会瞄准子女正要从小学升入初中的贫困家庭,或是居住在营养不良率较高的地区、需要抚养年幼子女的贫困家庭。
这种瞄准方式可能无法同时顾及再分配和人力资本构建。当然,如果大部分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都有所欠缺且程度相当的话,无须担忧这种权衡取舍。但是,如果只有相对较少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极度欠缺的话,CCT项目最大化人力资本累积的设计理念就会限制其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的功能发挥。
设置合适的准入条件和转移支付额度
CCT项目对教育和健康服务享有的促进,仅仅是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效益所致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准人条件控制和监测力度以及对违反要求的家庭的惩罚力度都有重要启示。确实,很多证据(包括对不同项目以及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项目设计的目的性特征,以及家庭行为的结构模型等)都表明CCT项目在服务享有方面的影响并非其所提供的现金的一己之力。所以,对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加以条件约束就非常重要,至少应该包括提高学校入学率以及进行防疫保健这两个条件。
然而,享受服务通常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选择“正确”条件的第一步,就是厘清所享受的服务和所期待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带孩子到医疗机构是改善他们的营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的最有效方式吗?还是保障母亲的营养,对她们进行养育子女的知识的传授和培训会更有效?
对项目成果本身进行条件限制,是现金转移支付的另一种可行方式,特别是当所享受的服务和预期产出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或过于复杂,而受益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转移支付成果时,会更为适用。未来对这种新型的激励方式的试验(可以通过小规模的试点项目)的重要性会与日俱增。例如,可以对将项目资金用于满足基本的“参与”条件的家庭,进行绩效奖励。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适当的转移支付额度。如上文所述,大额转移支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消费贫困(或收入贫困)状况,这一结果看起来非常合乎情理。但是在教育和健康成果方面,问题会更为尖锐:收入弹性能够算是成果吗?更高的资金额度会使受益家庭的行为产生更大变化吗?以柬埔寨的入学率为例,虽然资金额的“基线”很低,其边际效益仍然下降得非常快(Filmer和Schady,2000)。然而,CCT项目适当的资金额度取决于对再分配和人力资本两个目标的权衡,并因不同产出和情境而异。结构模型和小规模试验有助于决策者们对这种互相抵消的效应进行识别和定性分析(Bourguignon,Ferreira和Leite,2003;Attanasio,Meghir和Santiago,2005;Todd和Wolpin,2006)。
进入和退出规则
一个有效的项目设计也需要慎重考虑进入和退出规则,从而避免预期受益者的误解,并使项目被操控和滥用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进入和退出规则也会提供意想不到的激励,特别是对劳动力的影响尤其大。目前,CCT项目采用代理权的方式而非收入临界值来瞄准受益者,所以项目进入资格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相关性要低于发达国家的许多福利项目。然而,这种代理权的方式在区别“贫困”和“非贫困”家庭上越有效,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就越高,于是对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激励作用就越小。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对受益进行约束限制(例如在智利或美国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或是采用分级受益的方法(重新进行资格审查后,一些家庭被更严格的标准排除,但是总体利益只有部分减少).来避免对劳动力供应的消极影响。
配套干预措施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提供都是失效的。基础设施落后、旷工缺勤、供应不足都是学校和医疗中心常见的问题。CCT项目的人力资本目标要想实现,就需要对服务供应进行改革。一些原本缺失这些服务的国家还需要政府或其他机构来进行提供这些服务。改善服务质量可能更加任重道远,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对表现良好的健康和教育服务提供者施以经济激励来解决。提高服务的可获得性,扩大服务的覆盖面都常与CCT项目同时进行,或者成为CCT项目的一部分。
除了质量堪忧外,在家庭层次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因素导致CCT项目难以改善最终的健康和教育成果。图5以厄瓜多尔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图中显示了在幼儿发育的早期阶段进行认知发展测试的结果。样本中大部分3岁的儿童的认知发展仅仅稍微低于参照系。当这些儿童到6岁开始上一年级时,最穷的20%的儿童的发展程度比预期落后将近3个标准偏差。结论很明显:CCT项目本身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甚至即便与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相结合也无法扭转这种劣势。最近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如果儿童在幼儿时期认知、社会和情感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他们成年后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很低(Cunha等,2006;Knudsen等,2006)。

图4 根据财富十分位划分的认知发展状况(厄瓜多尔,2003——2004)
资料来源:Paxson和Schady,20
注:TVIP指皮博迪词汇测验。图中的线条代表全国财富分布的第1个10%(最穷的)到第4个10%的人群。对测验结果进行了编码,100代表参考系的平均水平,标准偏差为15。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干预手段来提高父母的抚养能力,改善家庭环境就至关重要。机会项目和其他一些CCT项目试图将参与家长讨论作为一个约束条件,促使父母获得新信息并加以实践,所提供的现金转移支付用于保证父母加入并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然而,CCT项目提供的这种有条件的现金支持仍然不足,启动一个由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人群积极参与的综合性项目势在必行。
七、 社会保护政策环境中的CCT项目
CCT项目只是向贫困家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护项目的一种,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贫困家庭。例如,贫困的老人家庭、无子女家庭或是子女年龄不在CCT项目转移支付范围内的家庭都无法从中受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对这些群体的收入再分配。以贫困老人为例,现金转移支付对劳动力供应的消极影响相对不明显,但是对针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投资也不太可能。所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都是对贫困老人进行援助更好的手段。
另外,CCT项目也并非是进行社会风险管理的最佳选择。CCT项目可以缓减贫困人口在不同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但是其针对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和目标群体瞄准的方式,也让它无法成为解决暂时性贫困的最好手段。那些要求长期承诺(例如CCT项目的条件中所包含的那些)、目标群体自我识别(所以不需要对进入和退出项目做复杂的行政决策)、要求受益者参加对抗风险的活动(例如就业相关的活动)的项目,在风险管理方面比CCT项目更加适合。
因此在大多数国家,CCT项目和其他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可以共存并互为补充,瞄准不同特征的家庭,来解决这些家庭所经历的不同性质的贫困问题。CCT项目在拉丁美洲启动最早,运作也最为良好,那里的决策者和项目管理者们越来越多地把CCT项目看做是更为广泛的社会保护体系的一部分。然而要使CCT项目真正成为社会保护体系的一部分,就需要考虑项目基本设计的相容性,例如CCT项目资金额度必须与其他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保持一致,以避免违背项目初衷,确保平等,以及保证政治接受度。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各个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之间形成合力的潜力是巨大的。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进行行政瞄准的公共体系和向受益者提供现金的公共体系(如发放电子卡片)。许多国家正在设计或试验公共扩展和服务平台,各个社会保护项目的受益者们都能够通过这种一站式服务获益,并与项目管理者进行互动。
八、 结 论
CCT项目常常被批评得一无是处,也常常被说成万能灵药。本报告对CCT项目的评述印证了其在减少短期贫困、促进对教育和健康服务的享有方面的有效性。这些成就不应被抹杀,因为证据已经表明设计精良的公共项目可能会对关键的社会指标起到巨大的影响。CCT项目也产生了积极的制度外部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通过强调监测评估,有助于增强公共部门,至少是社会政策领域对结果评估的重视。需要对这一成果进行长期巩固。同时,本报告也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提醒需要避免出于对CCT项目的支持而将其固有的优点沦为盲目的鼓吹运动。
50年前,Albert Hirschman(1958)提出发展是“不均衡产业链”的观点,认为一个部门的扩张会对其他欠发达的部门的发展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获取利润的动机,或是对政府行为施加政治压力。CCT项目使贫困人口对服务的要求提高,并有望开启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领域的服务改革的新进程。判断现有的CCT项目是否能够实现这些远景可能有些为时过早,但是目前来看,前景十分乐观。
墨西哥采用新方法多维测量贫困
(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价委员会)
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价委员会(CONEVAL)介绍了墨西哥市用来多维测量贫困的方法。这个方法将作为墨西哥整个国家官方测量贫困的方法。多维测量贫困采用了社会权利的方法,其指标采用《社会发展总法》规定的教育缺口、卫生保健可得性、社会保障可得性、家庭基本服务、粮食可得性、人均纯收入、社会凝聚力水平等。该方法可以识别出处于多维贫困和由于社会剥夺和收入不稳定导致的弱势群体人群的生活状况。墨西哥2008年国家和地方的贫困报告采用了这种方法。
多维测量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贫困,除了测量收入,也对社会剥夺做了社会权利视角的分析。可以了解墨西哥整个国家人口的社会状况,而且也能了解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这个方法与墨西哥历史上采用的贫困测量不同,因为提供了能够更有效克服贫困的客观和直接联系的信息。多维贫困包括人类生活条件的三个方面:经济福利、社会权利和社区背景。根据这种方法,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且至少表现出以下六种指标中个一个,那么就处于多维贫困。这六个指标包括:教育缺口、卫生保健可得性、社会保障可得性、住房质量和空间,粮食可得性和家庭基本服务。而这些指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都有非常明确的可操作的测量方法。
一、 教育缺口
根据墨西哥义务教育法,下列人群被认为是受到教育剥夺:
·处于3~15岁阶段,没有参加基础义务教育,也没有参加正式教育;
·16岁及以上,当他们处于学习阶段却未能小学毕业;
·16岁及以上,没有完成中学教育。
二、 卫生保健剥夺
根据墨西哥法律,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或资格获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包括一般的保险,社会保障机构(国家或州的IMSS,ISSSTE; PEMEX,ARMY等项目)或私人医疗服务时,被认为面临卫生保健的剥夺。
三、 社会保障剥夺
社会保障缺失会导致家庭和个人面临灾害、疾病等事故时,生活标准和环境恶化。墨西哥采用以下指标衡量是否存在社会保障剥夺:
·有劳动工资的人群,如果没有享受医疗服务、带薪休假和退休储蓄(SAR)或退休基金(Afore);
·对于自由工作的人群,是否享有劳动权益或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规定的服务,是否享有SAR或Afore;
·家庭是否有亲戚享受社会保障;
·退休人群是否享受社会养老项目;
·只要符合上述指标1项及以上,就会被认为是受到社会保障方面的剥夺。
四、 住房质量和空间
这个指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房屋的建筑材料,另一部分是房屋的空间。如果家庭符合以下至少一个条件,则认为生活在这个家庭的人受到这方面的剥夺:
·地板是泥土;
·房顶材料是纸板或废弃材料;
·墙体材料是泥浆混合物、芦苇、纸板、金属或其他废弃材料;
·每个房间居住人数不低于2.5。
五、 粮食可得性
获得粮食和营养是个人体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再承受饥饿是保障食物的最低限度。考虑到测量的精准性,对食物剥夺的测量通过家庭中度或严重的食物短缺,包括缺少食物、食物数量和质量的变化、饥饿的经历。
六、 家庭基本服务
当个人居住在含有以下特征的家庭时,被认为是受到这方面的剥夺:
·从井、河、湖、水库中获取水;
·从其他家庭取水或者从公共水龙头处取水;
·缺少排水设施,或者排污管道直接与自然水体连接;
·缺少电力。
在这六个方面建立剥夺指标和指数,如果一个人承受某种剥夺,则得1分,如果没有受到这种剥夺,则为O分,当一个人的得分大于0时,则认为其至少受到一种剥夺,被认为是多维贫困的人口。当一个人受到至少三种剥夺,而他的收入又不足以支持他弥补这三方面的剥夺时被认为是绝对多维贫困人口。收入高于福利线且没有受到任何一种剥夺被认为是非多维贫困也不具有脆弱性。在社会凝聚力方面,通过测量,社会凝聚力的水平通过四个指标测出:经济不平等程度、社会分化程度、社会网络和收益率。
墨西哥 2008年多维贫困测量结果表
根据新方法,墨西哥2008年有超过4 700万约占总人口44.2%的人处于多维贫困,这些人平均受到2.7种社会剥夺。有3 600万人(占总人口的33.7%)处于中度多维贫困,即平均每人受到2.3种剥夺,1 120万人(10.5%)处于绝对多维贫困,至少受3.9种社会剥夺。此外,由社会剥夺造成的脆弱性群体占总人口的33%,有3 520万。由收人造成的脆弱性群体有480万,比例为4.5%。 ‘
在社会权利方面,全国77.2%的人口至少受到一种社会剥夺,30.7%的人口至少受到三种社会剥夺。21.7%的人口表现出教育剥夺,40.7%的人口不能获得足够的卫生保健,64.7%的人面临社会保障的剥夺,17.5%的人口住房受剥夺,18.9%受到家庭基本服务的剥夺,21.6%的人没有足够的粮食。
2008年,墨西哥基尼系数达到了0.506,是非常典型的收入高度集中的情况。此外,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出不同人口群体的多维贫困状况和脆弱性,2008年,有75.7%的土著居民处于多维贫困的状态,39.2%的人处于绝对多维贫困的状态。
墨西哥这种多位测量贫困的方法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201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将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应用这一方法进行评估。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
地址:北京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86-10-84419655 传真:+86-10-84419658(电子地图)
版权所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京ICP备202003919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