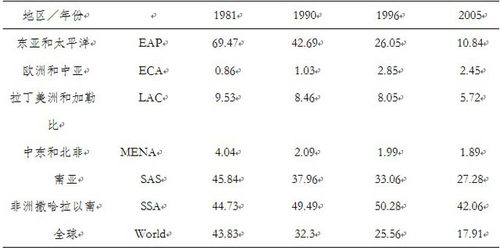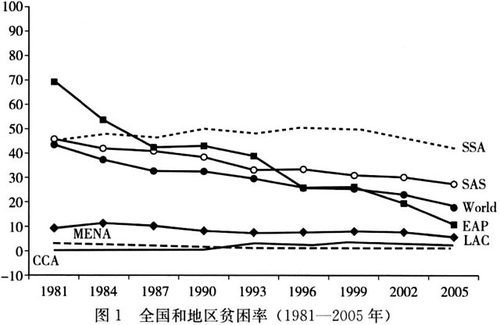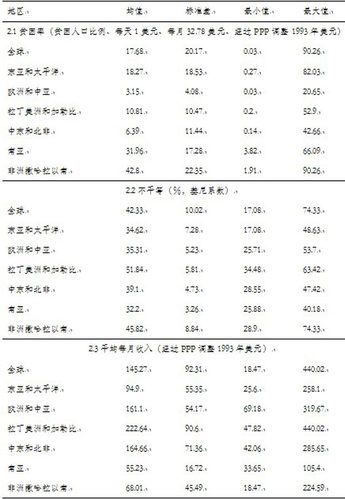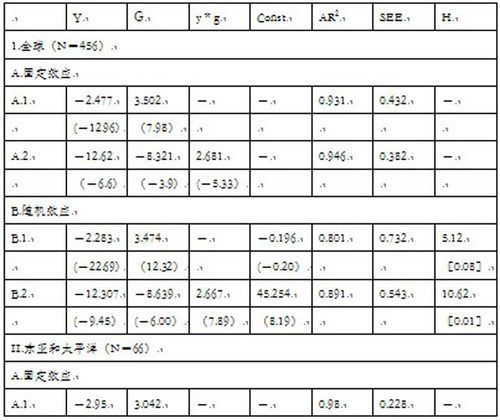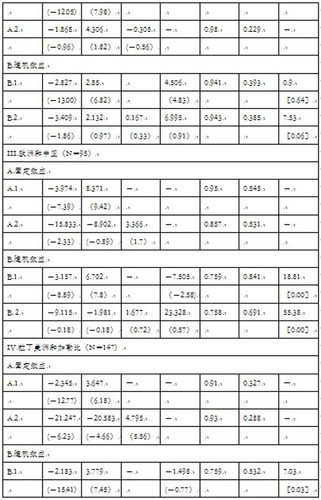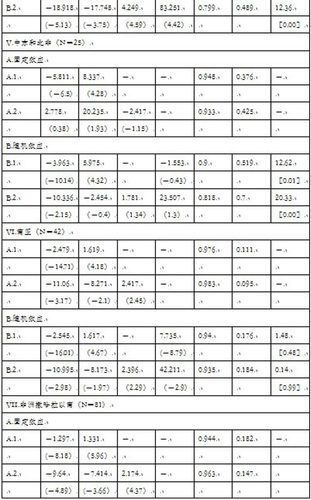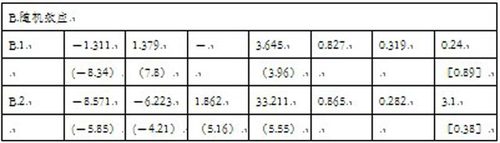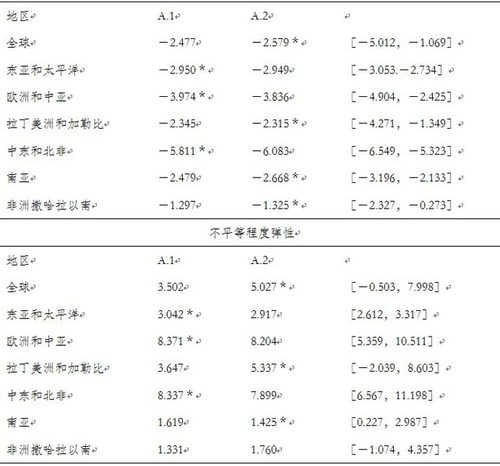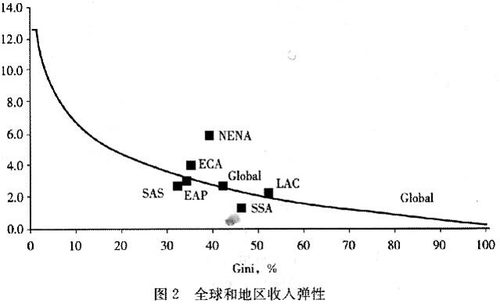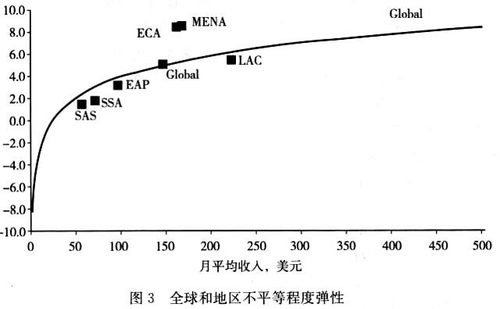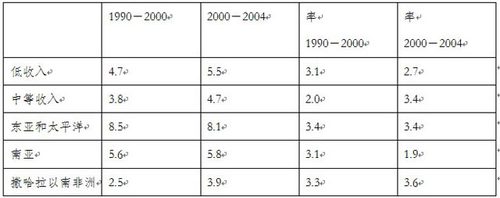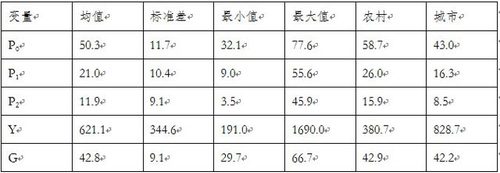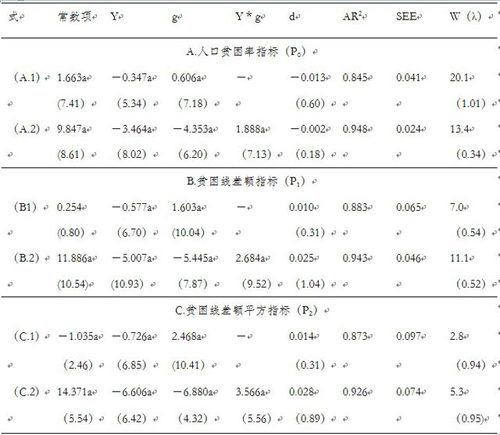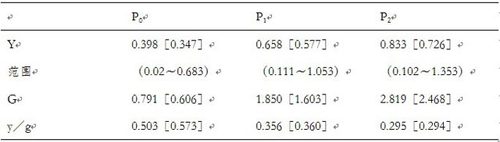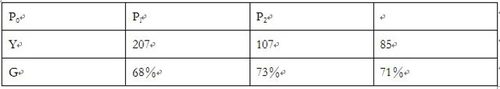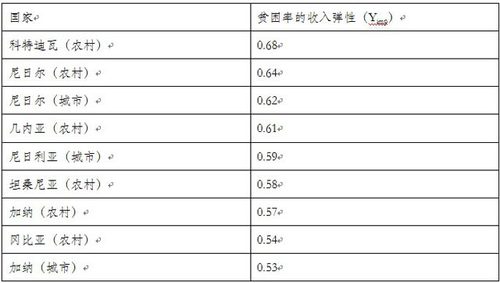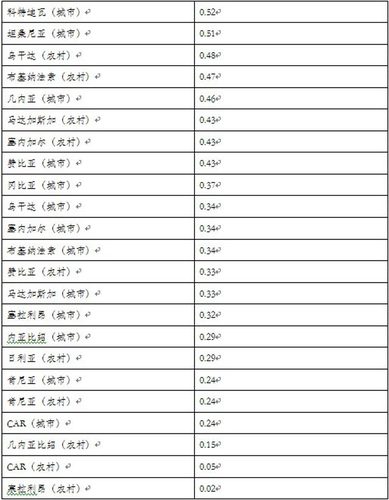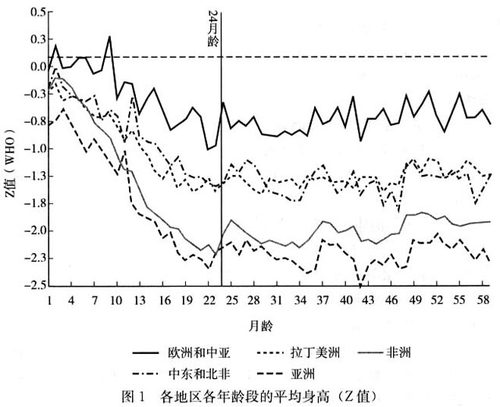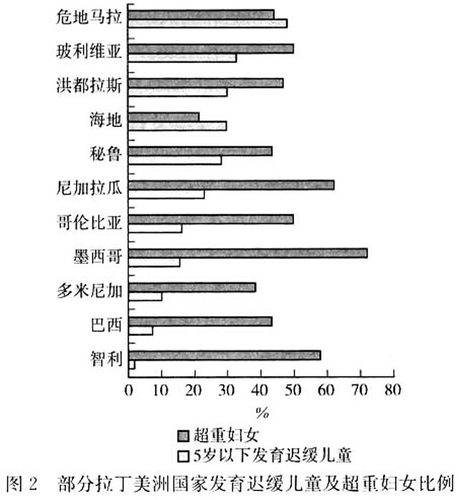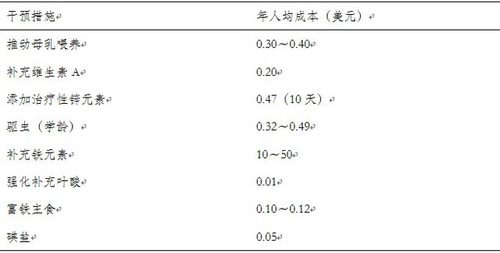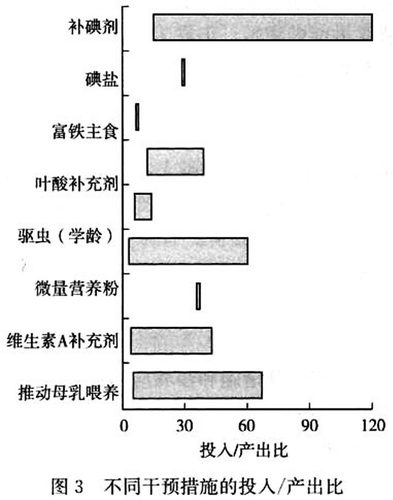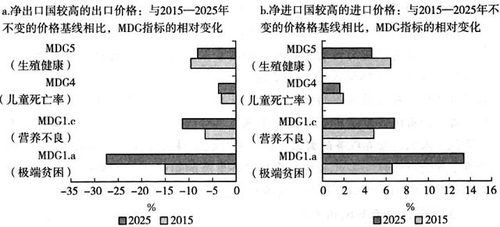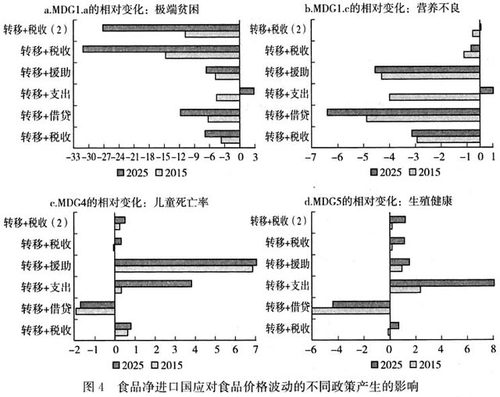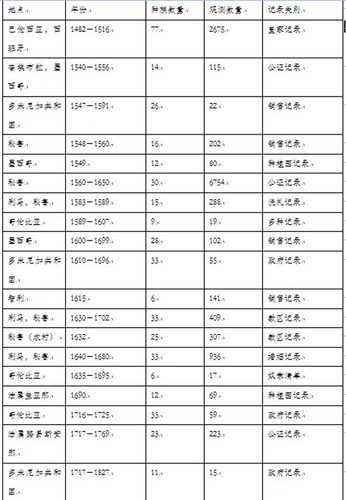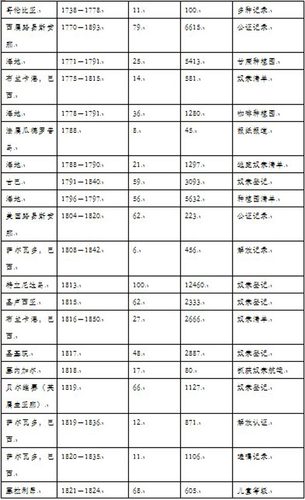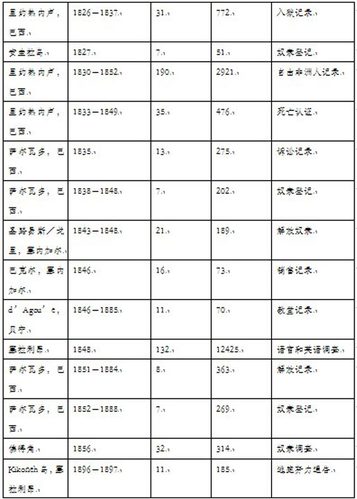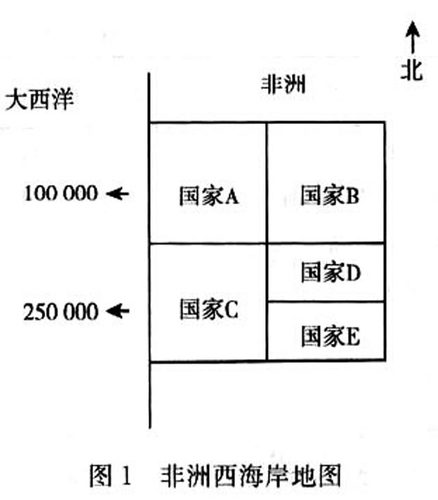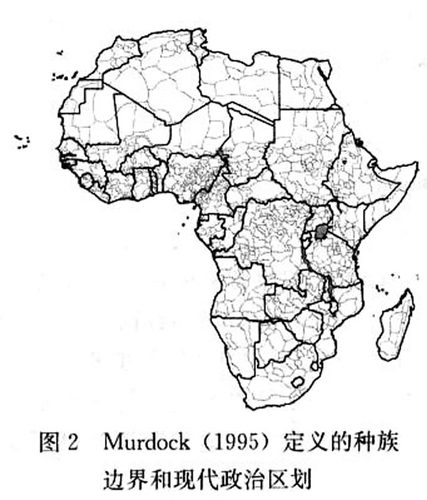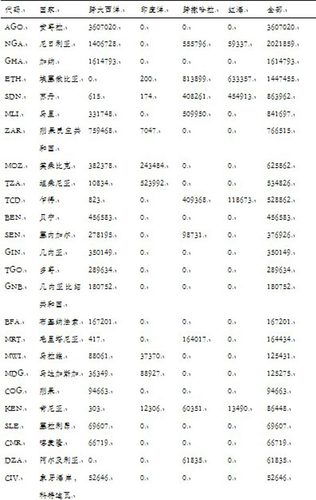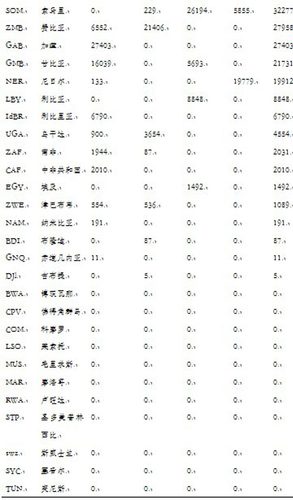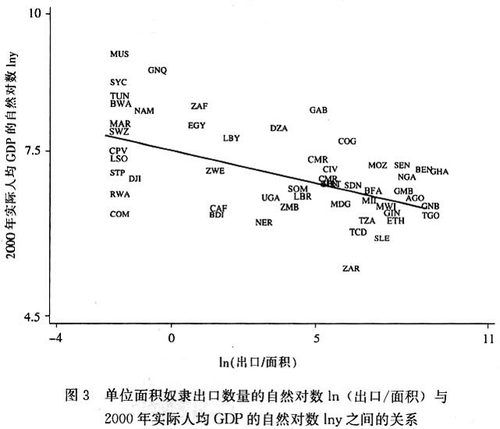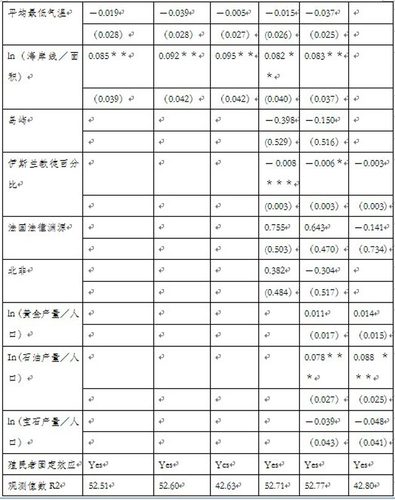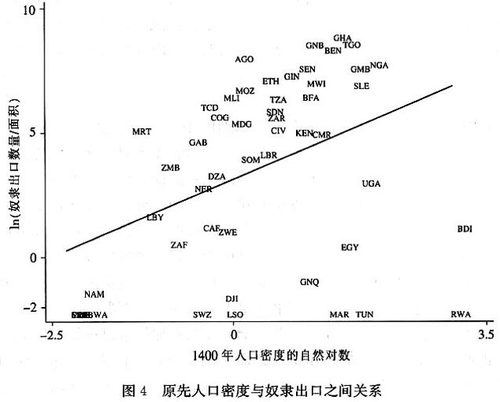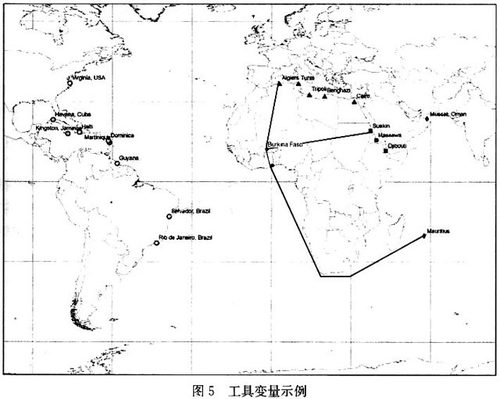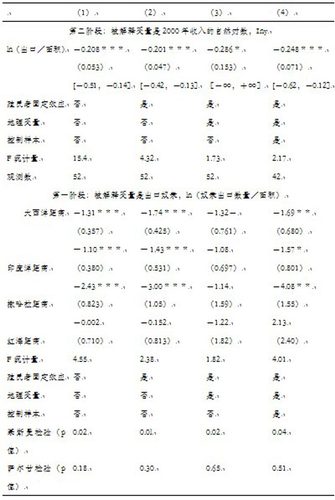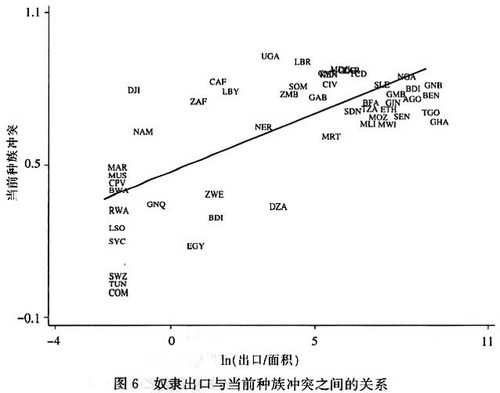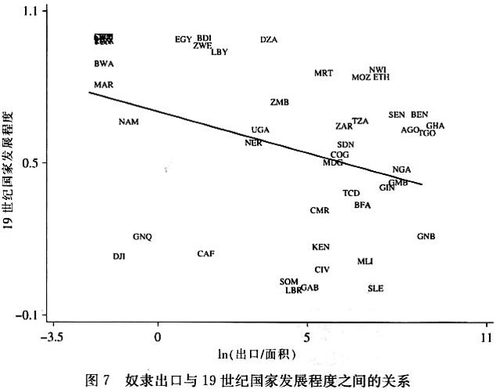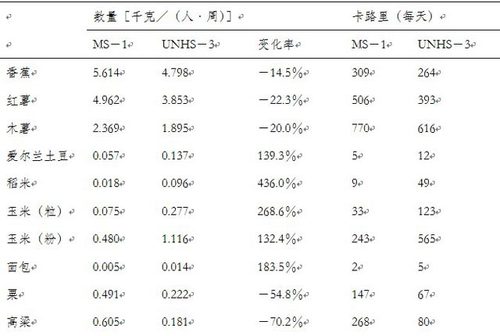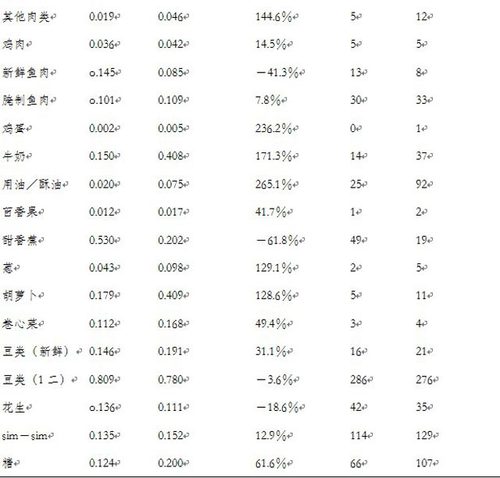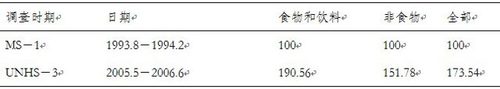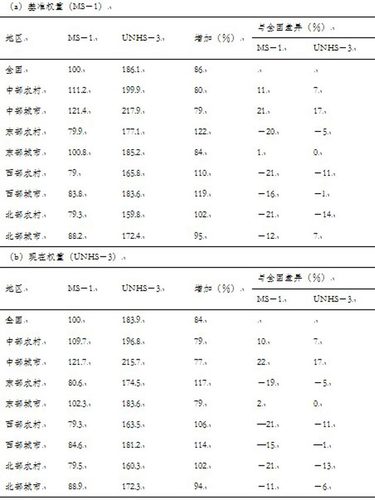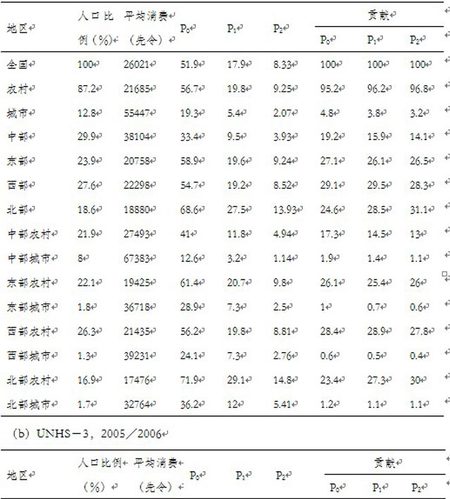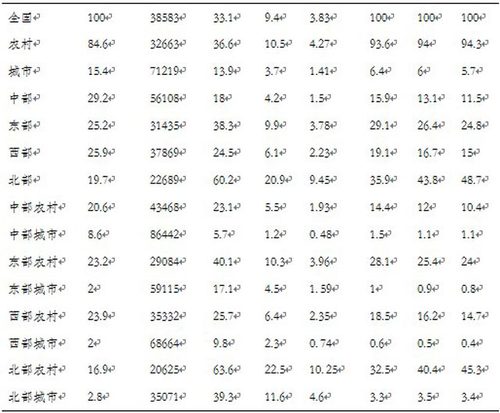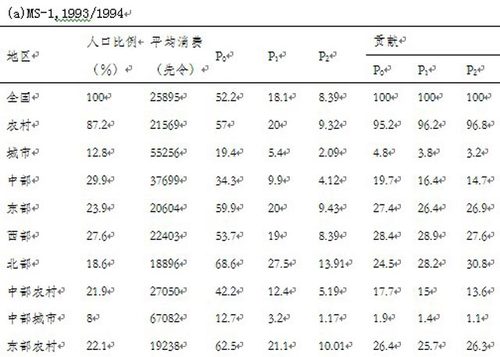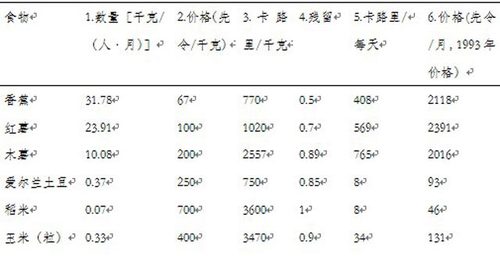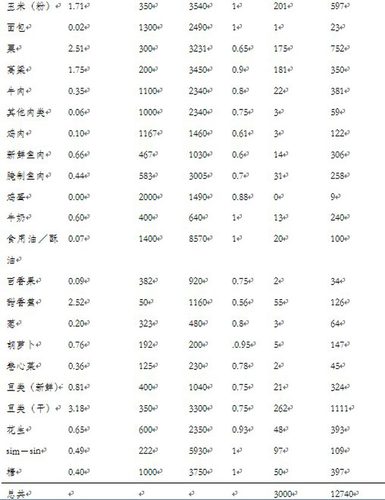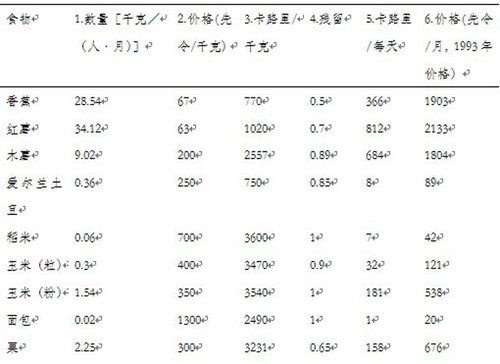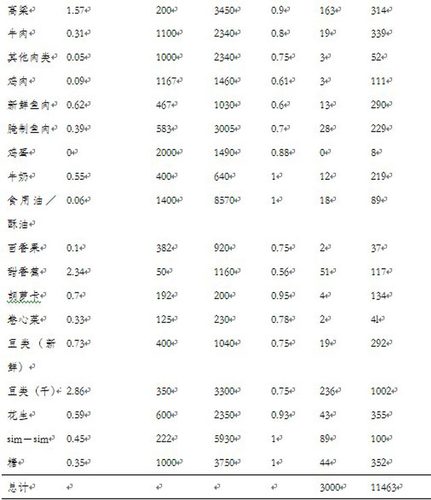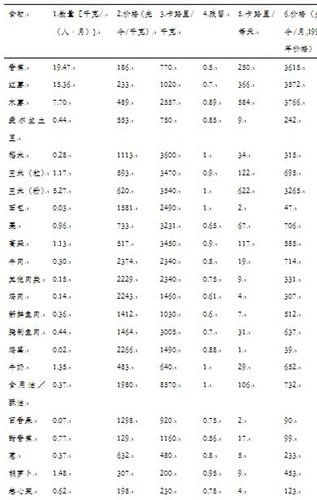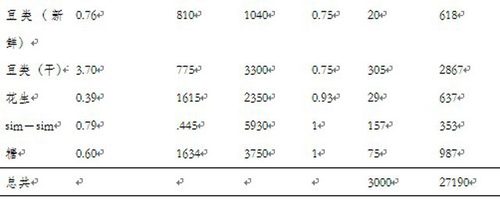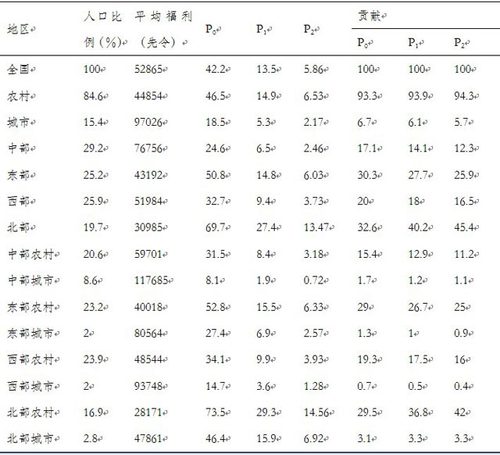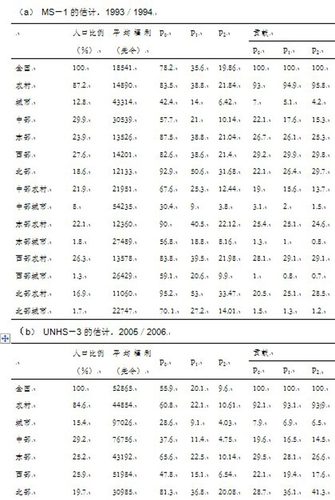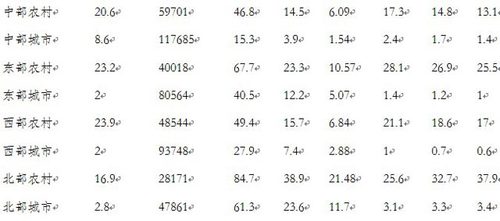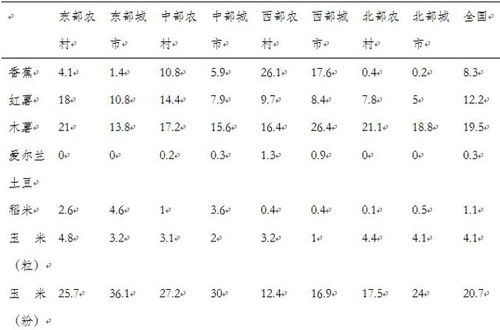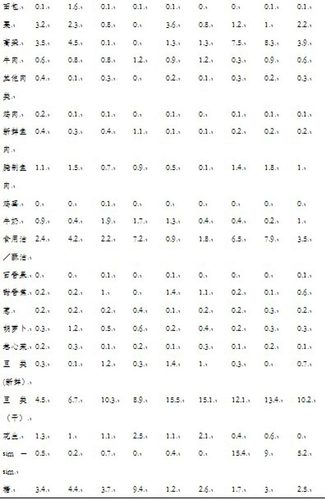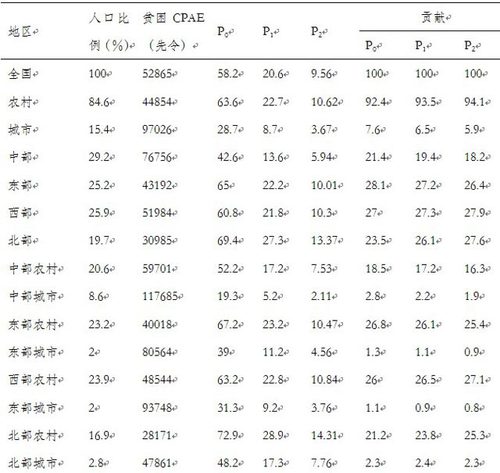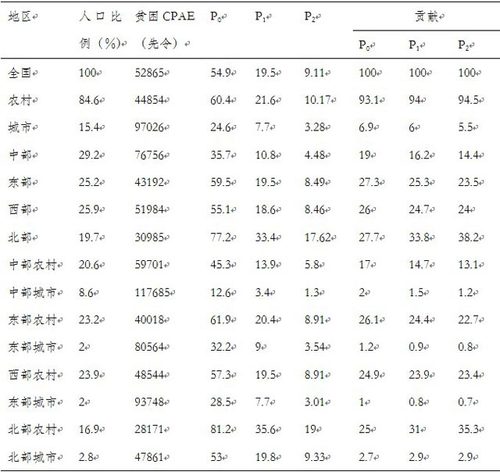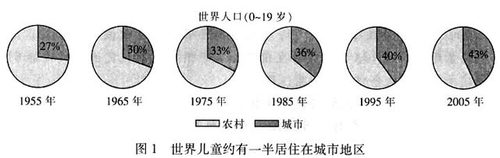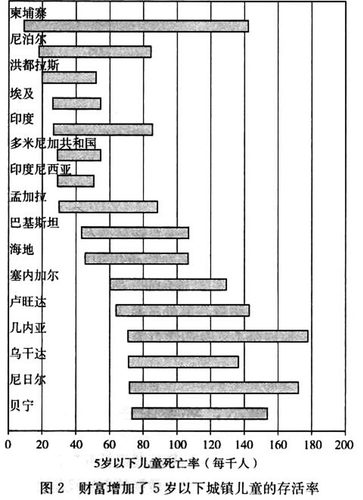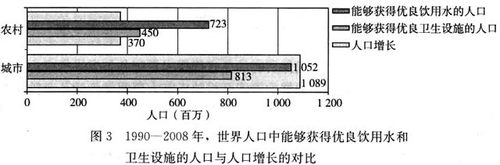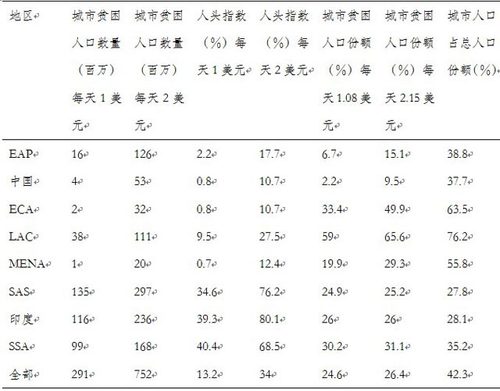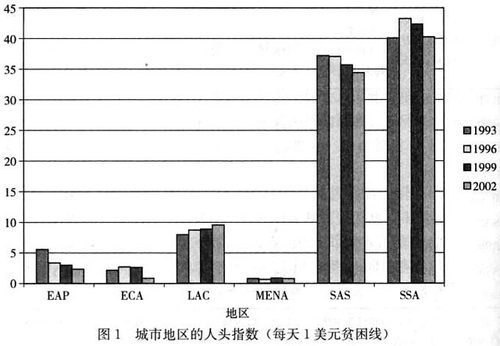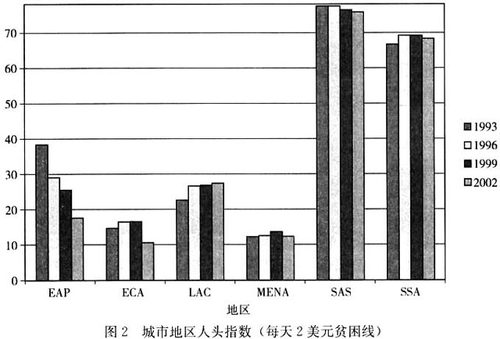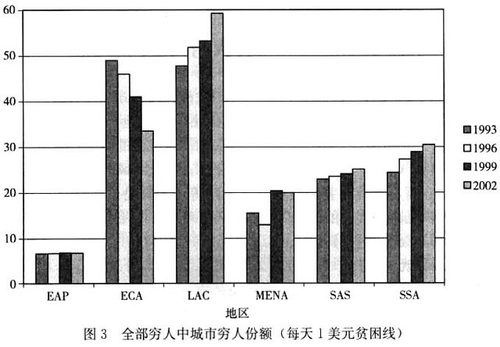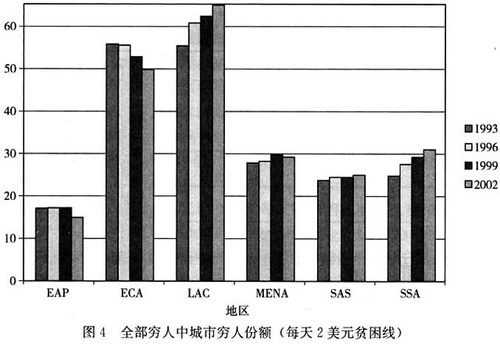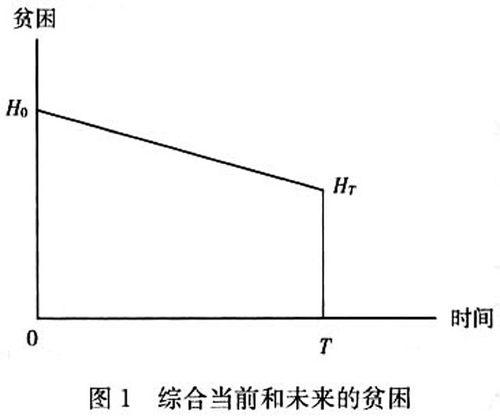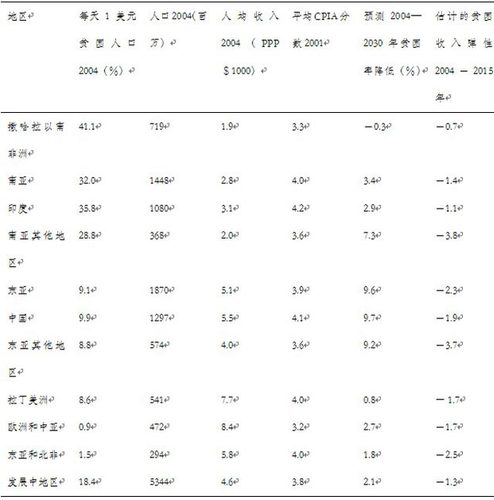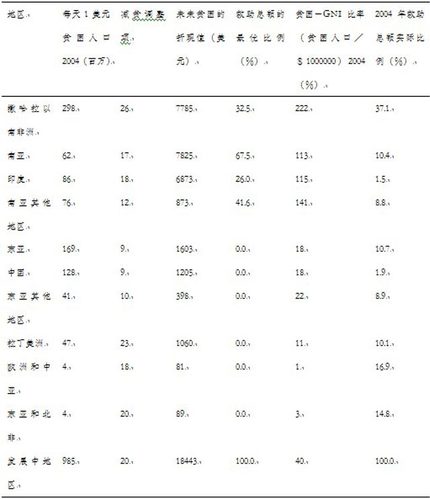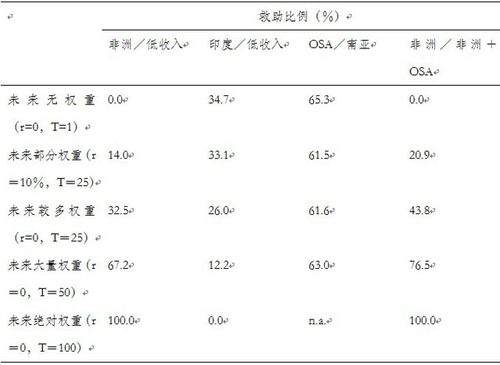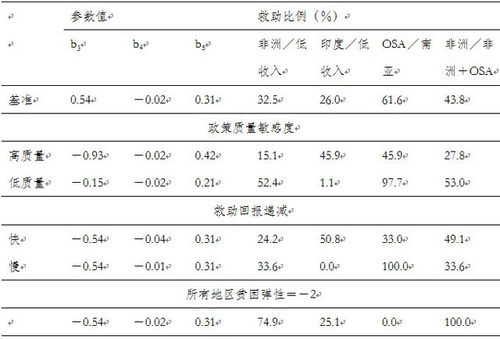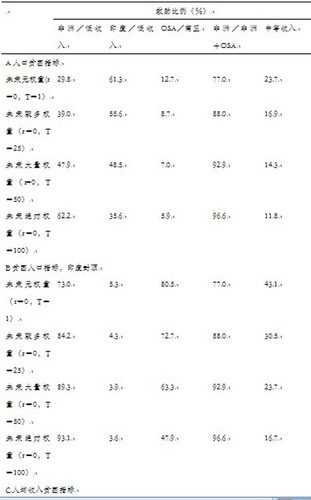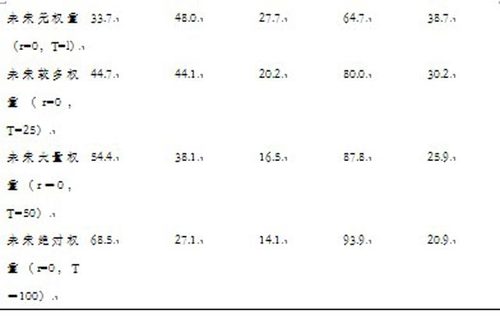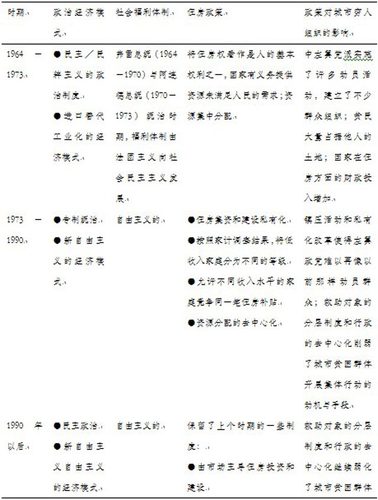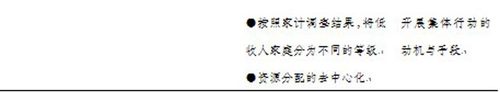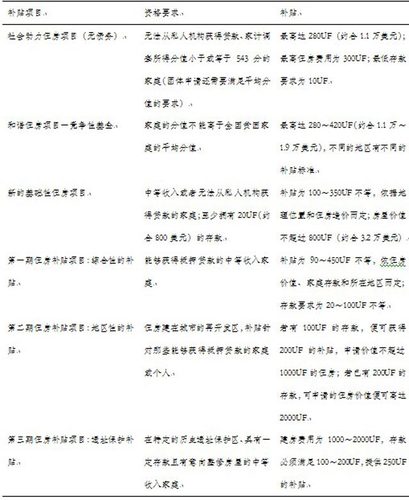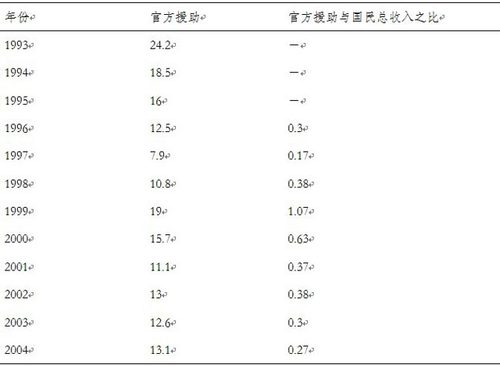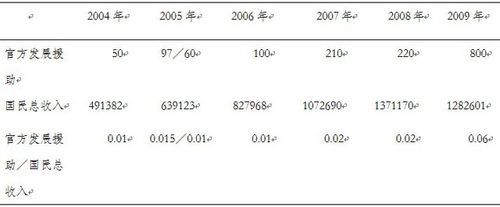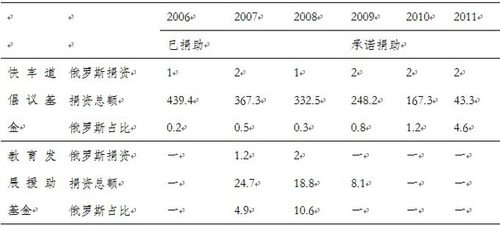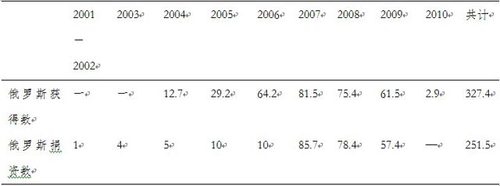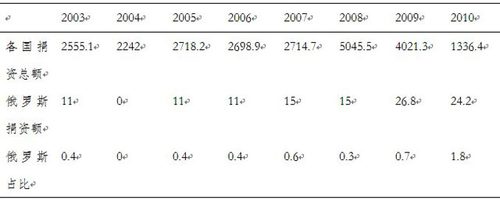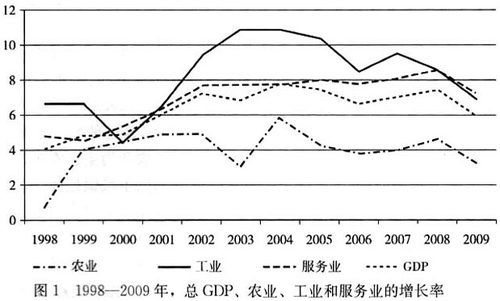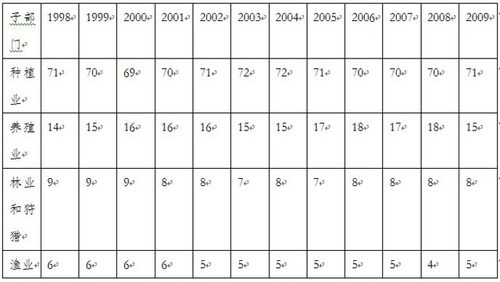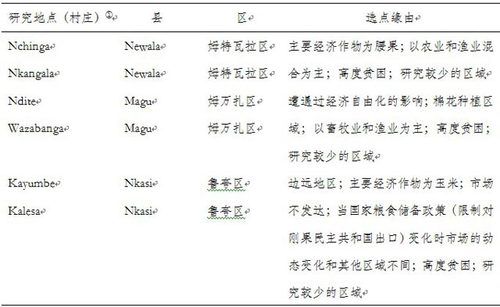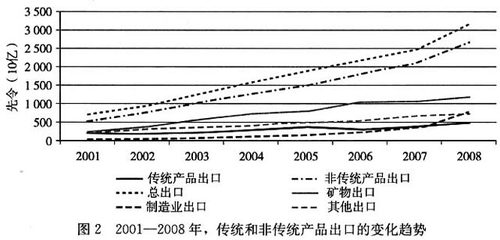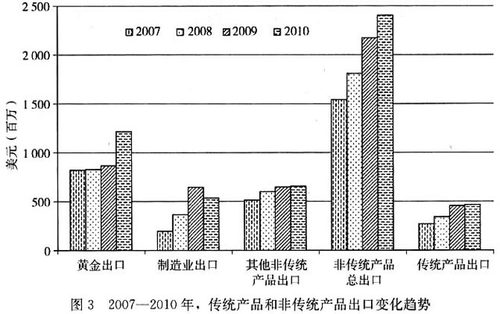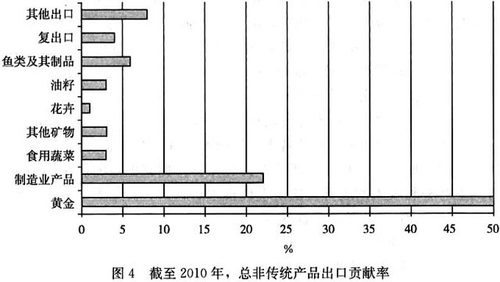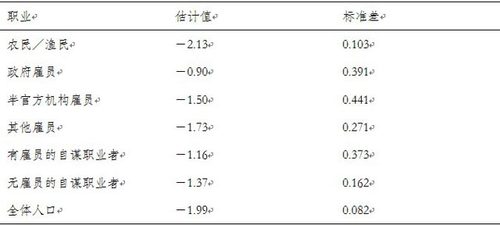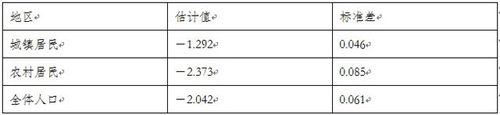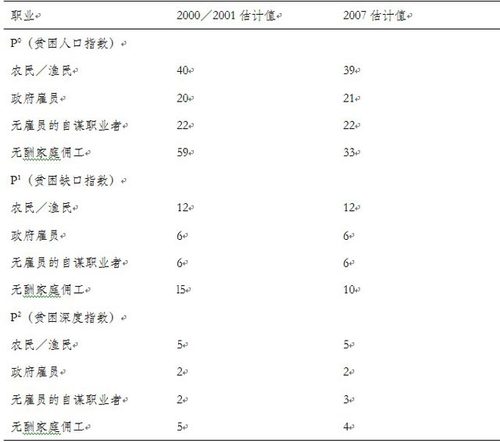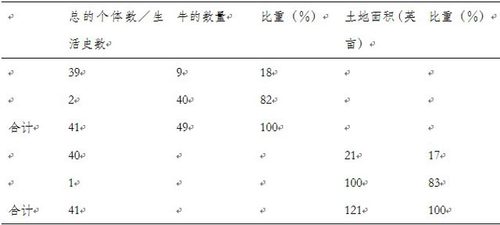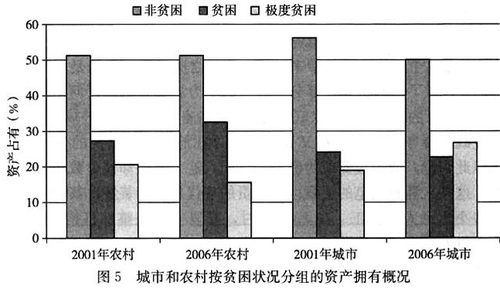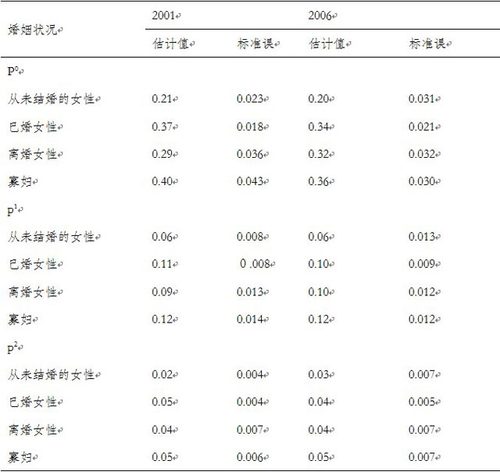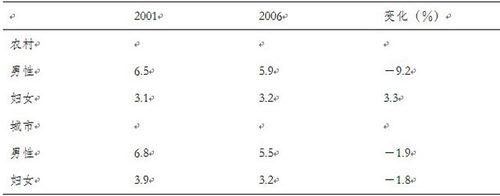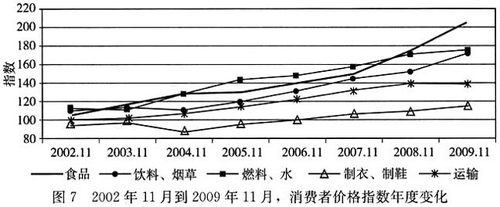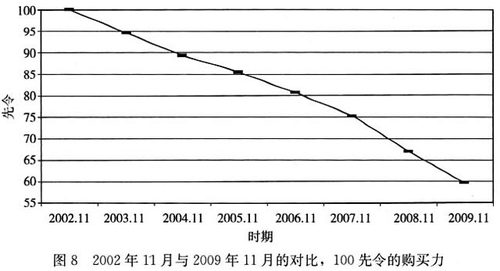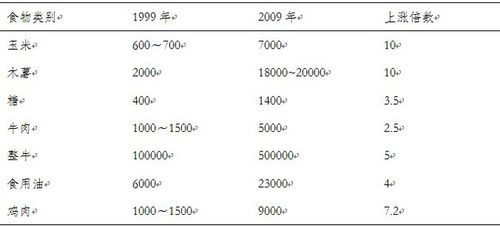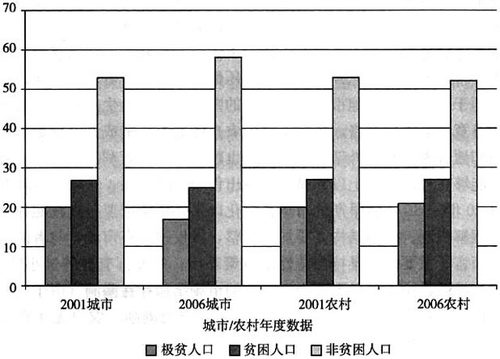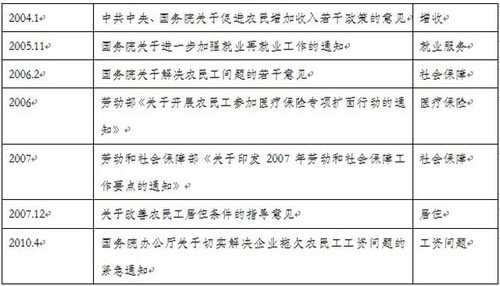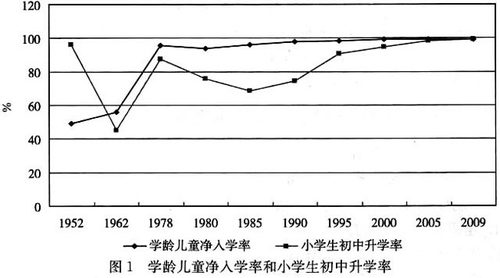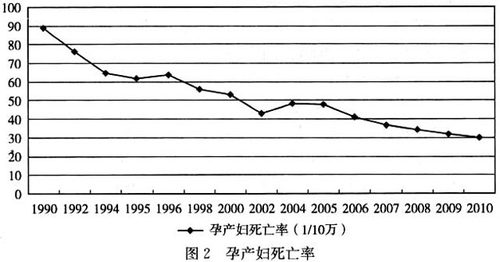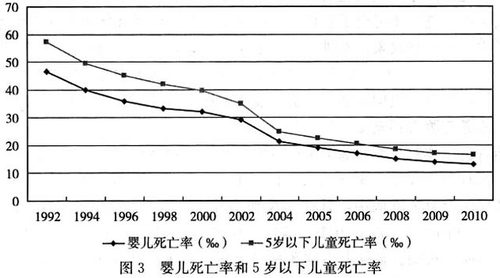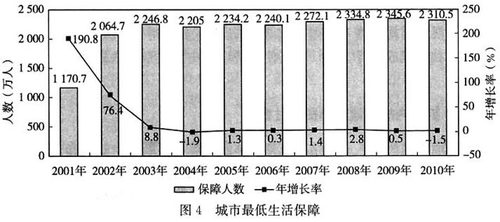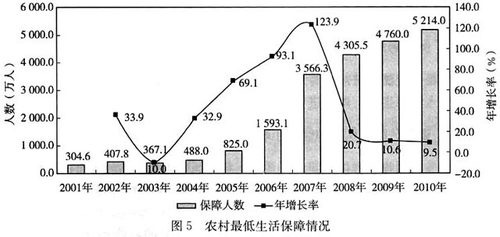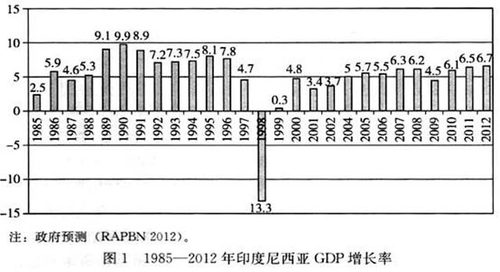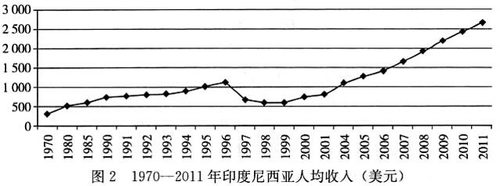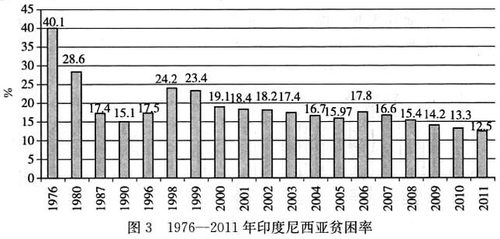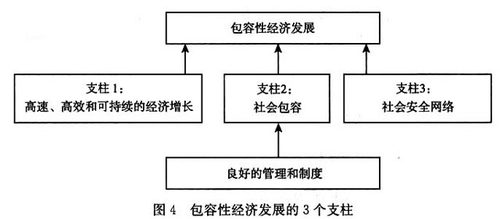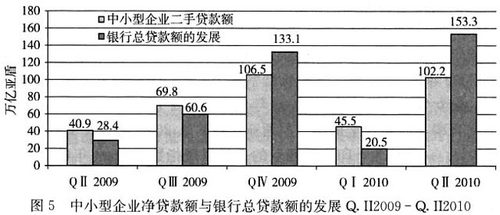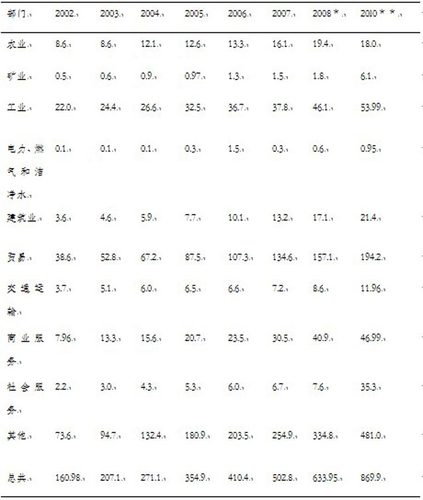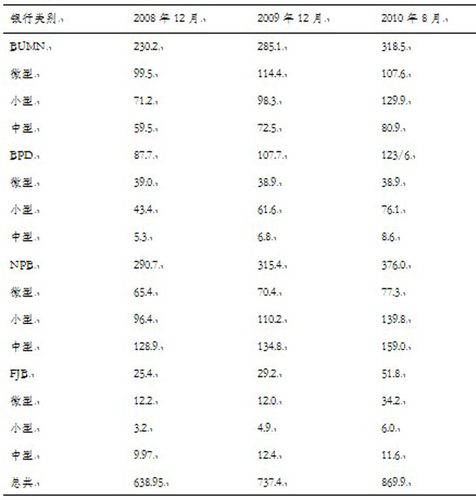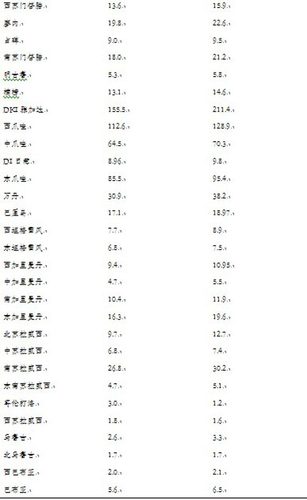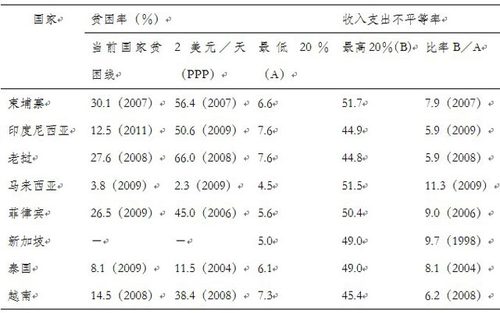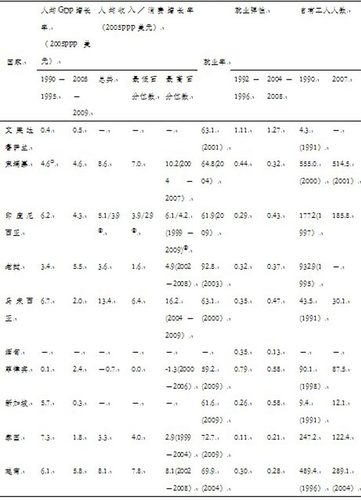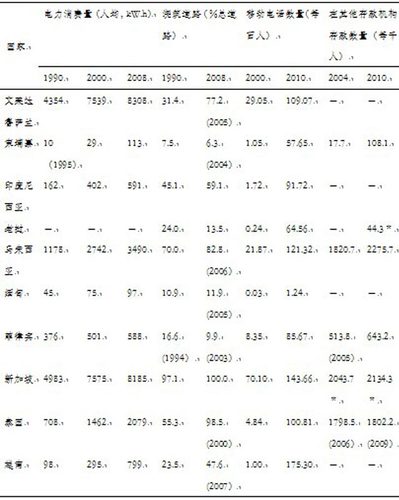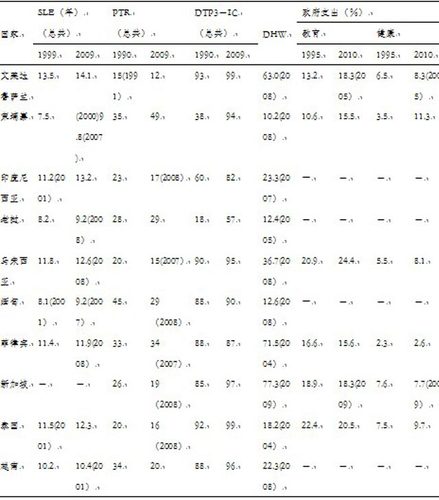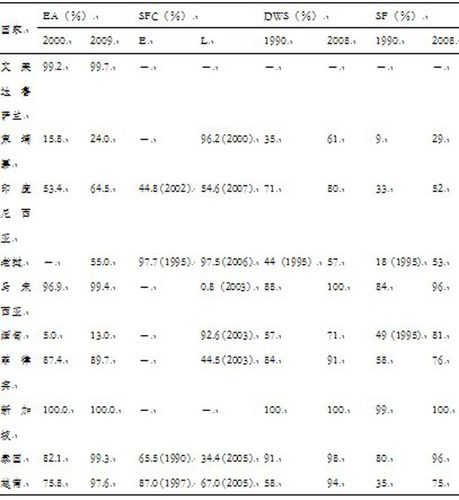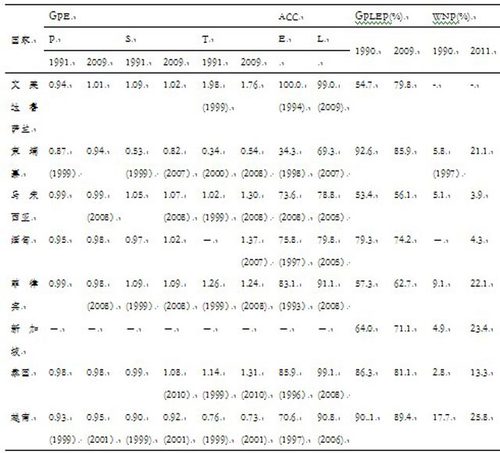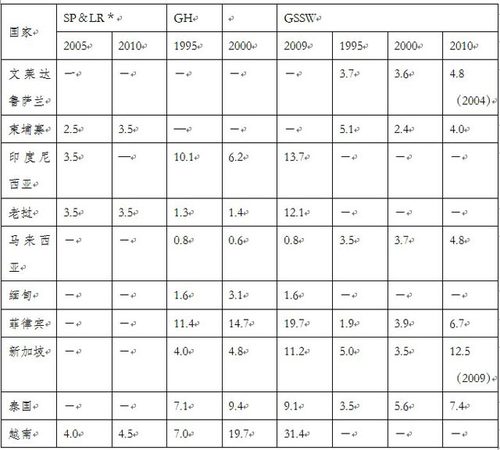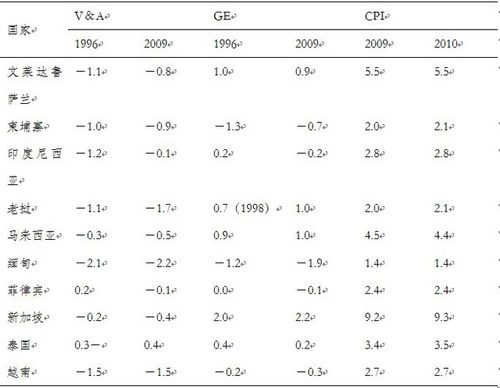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3
第一部分
减贫理论
不平等、收入和贫困:全球比较证据
Augustin Kwasi Fosu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摘要:本文试图提供收入不平等相对于收入增长在减贫中的作用的全球比较证据。本文基于1980-2004年全球大样本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一个协方差分析模型,其中贫困人口比例(贫困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基尼系数和经过PPP(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平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估计同时采用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贫困率对于收入的响应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递减函数,贫困率的不平等弹性实际上大于贫困率的收入弹性,而且不平等程度对于贫困率的作用在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相对于传统看法而言,收入分配在减贫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虽然该作用在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
一、 引 言
作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2015年将贫困率降低一半的首要目标,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主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困率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大幅下降(世界银行,2006a),收入分配在减贫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关注(Bruno、Ravallion、Squire,1998;世界银行,2006b)。从国家的层面而言,许多文献已经分解了不平等和收入对于贫困率的作用(Datt&Ravallion 1992;Kakwani 1993)。Datt和Ravallion(1992)和Kakwani(1993)估计的结果认为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都对减贫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地区的层面而言,基于非洲跨国数据,AIi和Thorbecke(2000)发现贫困率对于收入不平等比对于收入本身更加敏感。
一些文献进一步强调了不平等在决定贫困率如何对收入增长反应时的重要性(Adams,2004;Easterly,2000;Ravallion,1997)。基于贫困率的收入弹性随着不平等递减模型,Ravallion(1997)采用计量方法检验了“增长弹性争论”(growth elasticity argument),即较低的不平等程度一方面有利于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使得贫困人口承担经济萎缩的成本。与此类似,在评估布雷顿伍兹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项目的作用时,Easterly (2000)在贫困增长方程(poverty-growth equation)中界定了收人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交互作用项,并发现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增强了项目的作用。在强调收入增长定义的重要性时,Adam(2004)提出的弹性估计方法显示:低基尼系数(低不平等程度)群体的贫困增长弹性更大。
除了上述文献以及其他研究,类似于本文这样充分地描述了不平等在减贫中作用并全面地提供了不平等对贫闲的作用的全球比较证据的研究尚属少见。基于贫困人口比例,本文首先展示了全球主要地区关于贫困率趋势的全球比较证据: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欧洲和中亚地区(ECA)、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南亚地区(SAS)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SSA)。本文的关注点是1美元标准,1美元标准虽然存在争议,但却是衡量贫困的最重要参照,并出现于“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其他提高全世界最贫困国家生活水平的相关争论中。本文还估计了关于贫困率和收入关系的协方差分析模型,其中不平等程度同时作为独立变量及与收入交互的形式进入模型。采用1980-2004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分别采用全球样本和地区样本估计了模型的完整形式和简化形式,这样做的目的是合理地评价不平等对于贫困的作用以及得出国家层面和她区层面的政策建议。
二、 贫困率变化趋势
基于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表1和图1描述了每天1美元(每月32美元)标准的贫困人口比例的全球和地区趋势。数据表明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从1981年的43.8%下降到2005年的17.9%。然而,地区间存在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81年的69.5%下降到2005年的10.8%。类似,南亚地区的贫困率也从19 81年的45.8%下降到2005年的27.3%。相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动,只从1981年的44.7%下降到2005年的42.1%。与此同时,欧洲和中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贫困率一直以来就很低(低于10%),中东和北非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率略有下降,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贫困率略有上升。
表1全球贫困率趋势
单位:%
注:为了进行比较,表l中的数据是基于每月32美元并经过2005年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收入,且与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贫困率相对应(2007)。因此,此处贫困率与下文回归中的数据相当,但是小于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新标准下的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
图1 全国和地区贫困率(1981-2005年)

注:贫困人口比例,每天1美元,(每月32美元)标准。
贫困率趋势的跨期变化也存在地区差异。例如,大多数南亚地区国家的贫困率降低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时期几乎没有进展;如贫困率只从1993年的33.1%下降到2002年的30.2%,之后才下降到2005年的27.3%。相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稳步下降,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率直到20世纪90午代中期才开始下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上升,并在90年代晚期达到峰值50.0%,然后下降到2005年的42.1%。然而,从1996年开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地区的贫困率分别下降了8.2%和5.8%,各自达到16.3%和17.5%。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每天l美元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比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地区在减贫方面的表现不相上下。
三、 数据、估计和结果
(一)数据
正如上文所说,本文数据来自于一个全球样本(世界银行,2007),包括1980-2004年中456个可用的非平衡面板观测值。样本中的国家数据差别很大,根据获得的调查数据,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多。为了实现国家间数据的可比性,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采用相同的贫困线即每月32.74美元,大致相当于每天1美元(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1993年真实美元)的国际标准。
表2给出了回归分析中采用的全球和地区样本的总结性统计特征。表2的结果基于世界银行2007年没有加权的数据,与表1基于世界银行2009年数据且根据人口加权的结果大致相同。唯一例外的是中东和北非地区,表2的总结性统计特征显示了相对于表1更高的贫困率。该异常主要是由于小国吉布提偏高的贫困率显著拉高了中东和北非地区没有加权的均值。
表2不平等、收入和贫困——总结性统计特征(1980-2004)
注:所有数据都没有加权且根据1980-2004年数据估计,除了印度还根据1977和1978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7)。
(二)估计和结果
我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过程中采用了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FE)。虽然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统计上比固定效应更加有效,但是如果不可观察的国家特征因素存在且与解释变量相关,那么随机效应的结果是有偏的。由于样本量巨大,估计效率没有问题。因此,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更加可取。表3同时显示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并且同时显示了每种情况下的Hausman检验统计量以判断随机效应是否与固定效应相比存在显著差别。结果包括全球样本以及6个地区样本。
表3不平等、收入和贫困——全球以及地区回归结果
注:被解释变量是贫困人口比例的对数(每天1美元标准);y是平均收入的对数:g是基尼系数的对数。小括号中是异方差一致文件t值。AR2是经过调整的R2,SEE是估计的标准误:H是豪斯曼检验值,中括号中的是相应的p值。
表3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例如,在模型的简化形式(A.1和B.1)中所有的估计模型y和g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因此,收入增长降低贫困率,而不平等程度提高增加贫困率。模型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也与预期的一致。y的系数为负,说明收入增加降低贫困率。g的系数也为负,当y很小时,不平等程度增加降低贫困率。正如上文所述,在低收入国家,将财富从富人转移给穷人实际上会使更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从而提高贫困率。假设给定交互项系数为正及其规模大小,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将使得g的整体效应为正。交互项的正号进一步说明g的增加将降低y对于贫困率的负效应,从而降低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
根据表3豪斯曼检验,固定效应在统计上优于随机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A.1和A.2作为估计贫困率的收入弹性和不平等程度弹性。估计结果见表4。
表4不平等、收入和贫困——全球及地区贫困率的收入弹性和不平等程度弹性
注:方括号中的数值分别采用地区基尼系数和平均收入的最小和最大值估计得到的弹性的下限和上限。*代表基于AR2、SEE和系数精确程度而言更好的拟合度。如果采用模型A.2,交互项显著,意味着贫困率弹性在国家存在差别。
从表4可以观察到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弹性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基于带*号的模型(根据AR2、SEE和系数精确程度具有更高的拟合度),收入弹性低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1.3(绝对值),高至中东和北非地区的5.8(绝对值),全球平均为2.6。类似的是,不平等程度弹性低至南亚地区的1.6,高至欧洲和中亚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8.4,全球平均为5.1。因此,收入增长或者不平等程度改变会在地区间导致不同的减贫作用。例如,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最小的,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是最快的,而不平等程度增加在南亚地区对于减贫的阻碍是最小的。
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弹性的地区差异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与Brambor、Clark和Golder(2006)的预测一致,图2和图3允许我更加全面地探索收入弹性Ey,和不平等程度的关系以及不平等程度弹性Eg和收入的关系。图2显示在全球样本中收入弹性Ey与不平等程度呈单调关系,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随着不平等程度稳步下降并且当基尼系数趋向于100%时趋向于O。基于此图,给定一国基尼系数的大小即可预测Ey。

同样,图3显示在全球样本中不平等程度弹性Eg随着收入水平增加,Eg为正为负都有可能。月收入低于22美元,Eg为负,意味着不平等程度降低将提高贫困率。该发现支持上文讨论的理论,即在一个足够低的收入水平,不平等程度降低将提高贫困率。然而,全球和地区样本中平均收入都足够大,总体上所有地区的Eg都是正的。注意到月平均收入地区估计结果与全球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说明地区间存在特质上的差异。例如,如图2所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与全球曲线很接近,而南亚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则不是。根据全球水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地区被高估,相反,欧洲和中亚地区、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低估了。因此,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收入增长降低贫困的程度小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恰好相反。从排名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收入弹性(绝对值)最高,然后依次是欧洲和中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因此,可以预期中东和北非地区收入的减贫作用最大,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小。换言之,非洲要达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高收入增长,除非实现普遍的低不平等程度。

根据图3,南亚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不平等程度弹性曲线都略低于全球曲线,说明根据全球不平等程度弹性曲线这些地区的不平等程度弹性将被略微高估。相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则会被低估。相对于全球而言,在这两个地区的不平等程度增加将会更快地提高贫困率。从排名上来看,欧洲和中亚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并列具有最高的不平等程度弹性,然后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地区。对于减贫的目的而言,南亚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相对于欧洲和中亚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不平等程度上升没有那么重要。
此外,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而言,贫困率对于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响应的区间很大(表4)。因此,为了最有效地降低贫困,以强调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程度相对重要性的国别处置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收入增长对于减贫很重要,但是对于特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长速度同时降低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更加有效的策略。
四、 结 论
在分析1980-2004年全球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的基础上,本文提供了关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贫中的重要性的全球比较证据。全球比较证据包括:一是间接途径,较高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收入增长减贫的作用;二是直接途径,不平等程度恶化会导致贫困率上升。基于基本需求法,本文估计了一个协方差分析模型,其中贫困人口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基尼系数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研究发现不平等程度通过两个途径影响贫困率:①高不平等程度限制了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②不平等程度恶化会以平均收入水平递增的速度导致贫困率增加。收入弹性和不平等程度弹性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显著变化,这意味着贫困对于收入和不平等程度的响应因地而异。而且贫困率的不平等程度弹性一般比收入弹性更大。因此,在不扭转收入增长方向的程度内,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减贫作用会比传统上认为的更加有效。本文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最优减贫策略需要根据国情强调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程度的相对重要性。
资料来源: Augustin Kwasi Fosu, Inequality, Income, and Poverty:Comparative Global Evidenc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1, No.5,Dec.,2010.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农村贫困:新背景下的老问题
Steffen Dercon 牛津大学教授、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
近年来,虽然世界很多地区的贫困率都大幅降低了,尤其是东亚、中国以及近些年来的南亚,但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贫困率仍然很高。贫困的持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高度相关。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依然主要是农村和农业现象,大多数农村贫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
本文将回顾几个已经充分讨论的相关问题:农村发展和农业增长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地位如何?农村增长和减贫的主要约束是什么?最新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否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减贫提供了更多的指导?本文将结合世界最贫困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讨论上述问题。我将利用最新理论模型以及基于刘易斯(1954)模型的理论作为指南展开讨论,给出经验证据,尽管并不完善,但是基本佐证了本文结论。
在很多关于发展的一般性讨论中,上述问题已经得到充分讨论而且占据显著地位。教科书在不同层次上也涉及这些问题,例如Ray (1998)、Barhan和Udry(1999),而专著方面有Timmer (2002)、de Janvry等(2002)。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合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具体情况,回顾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经验证据,因而针对性很强。总而言之,近几十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农业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表现不佳,因而强烈需要对非洲农业的关注,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必要条件。例如,Sachs强烈呼吁在非洲将“绿色革命”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Sachs,2005)。更翔实的分析如《世界发展报告2008》,强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挥农业刺激经济其他部门增长的关键作用(世界银行,2007),并要求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环境和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本文第一部分简要总结农村贫闲演变的现有证据,并比较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现有证据证实了农业人口游离出农业与总体贫困率降低相关的传统观点。然而,非洲既没有发生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也没有出现农业人口的转移。当然,这并不证明存在因果联系,也不足以质疑关注农业增长的合理性。我的问题在于理论和经验证据如何才能说明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地位。
第二部分提供了关于农业在增长和减贫中作用的宏观看法的讨论。这要求我们回顾一些关于部门和城乡联系的古老且看似过时的问题,以更好地理解在非洲背景之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作用。回顾的一个核心困难是证据相对不足,所以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虽然简单但是有效的城乡联系模型说明问题。结合最近关于非洲经济增长范围研究的新方法,强调发展机会的异质性(Ndulu等,2008),我们能够确认农业发展在刺激增长和减贫方面发挥实质作用的特定情形,以及农村发展在其他情形下的本质和作用。我将着重阐释农业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形下可能非常不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利用制造业的优势、一个国家是否依赖于自然资源以及一个国家是否深处内陆且资源贫乏。我认为特别是在最后一种情形下,重视农业增长是一条脱离贫困的重要但艰难的途径。
最后一部分,关于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可能性的微观视角补充了上文宏观观点中的关于市场本质的严格假设。我将着重讨论针对市场严重失灵的三个案例——信用、风险、空间效应,此外还将回顾这些问题的理论影响和经验证据。上述市场失灵,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贫困陷阱的市场失灵,使得农村和农业政策恢复旧状,并据此得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潜在政策的结论。
一、 农村贫困模式
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农村现象。在世界上随机选择一个穷人,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和劳作在农村的农民。虽然数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世界上76%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远远高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即58%(Ravallion等,2007)。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例外:不仅具有最高的贫困率,而且农村贫困率比城市高25%,农村人口比例为65%而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70%。根据现在的增长、减贫、人口增长模式,贫困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依然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农村现象(Ravallion等,2007)。
情况是否正在发生变化?Ravallion等(2007)的数据提供了从1993-2002年贫困的城市化模式的深度观察。虽然城市贫困率在世界范围内略有下降,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反而上升了(从19%上升到24%),因为迁移导致城市人口增长快于农村人口。与此同时该模式存在很大变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贫困率下降幅度更小、城市贫困率停滞不变以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是造成贫网城市化和总贫困率几乎不变的主要原因。在减贫效果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的贫困城市化趋势以及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事实,说明农村减贫对于全球减贫发挥主要作用:Ravallion等(2007)基于一个简单分解计算出80%左右的贫困率下降来源于农村减贫。但是这样并不能证明城市化和贫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也不能证明农村或农业经济内部原因是贫困率下降的原因。
具体而言,应该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背景下认识上述模式。人均GDP的增长、贫困率的下降与农业GDP比重和农业人口的缓慢下降同时发生。例如,从1990-2004年全球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在5%左右,而农业GDP比重从32%下降到23%(世界银行,2005b)。与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以及南亚地区的相对较快发展和贫困率大幅度下降,见下表。我们观察到在东亚和南亚GDP增长速度高于农业GDP增长速度,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如此,GDP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相近,分别为2.5%和3.3%。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仍然为2.3%,远高于上述其他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很低。换言之,与更加成功的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表现出贫困城市化,但是不存在结构转型的证据。
GDP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世界银行。
部分学者认为农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Timmer,2007)。如果非洲农业增长率很高,即使当前的增长率不能作为农业快速转型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希望的象征。因此,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增长起飞。标准理论模型着重关注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联系(Johnston和Mellor,1961)。《世界发展报告2008》倾向于上述观点,主张在当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农业高增长速度是经济起飞的途径。虽然历史经验表明农业在欧洲工业革命开始阶段的促进作用很大,以及农业增长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但是还很难确认农业增长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经验证据模糊不清。
历史学家还在极力争辩18、19世纪时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农业革命是否是英国及其后来欧洲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和随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Crafts,1985;Allen,1999)。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的时间充满争议,一些人认为远远早于流行观点(Allen,1999);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英国在1560—1850年农业没有任何生产率提高的迹象,因此,作为经济增长先导的作用微乎其微(Clark,2002)。农业劳动生产率力提高可能是由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先导(Gantham,1989)。关于欧洲和17~19世纪期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率的最新比较表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率接近欧洲当时表现最好的国家(英国和低地国家),这一发现进一步反驳了农业发展状况允许欧洲工业化起飞的观点。毋庸置疑的是政策转变在近来中国农业增长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够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中去。例如,韩国并没有在农业生产率方面进行投资,但是成功地实现了快速工业化(Amsden.1989)。
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中,普遍认为农业和增长之间的联系很大(Staatz和Dembele,2007)。尽管可能,但是很难找到证据,这主要是方法上的间题。时间序列的计量结果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受到联立性困难的影响,而面板数据分析只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结果(世界银行,2007)。大多数分析都依赖于模拟模型(例如,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一产出模型),这些模拟模型又不得不依赖严格和未经证实的行为假设以得到结果(Dorosh和Hagg-lade,2003)。
强硬的证据表明农业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向贫困人口倾斜,但这一结果可能依赖于特定背景。例如,中国农业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比工业和服务业增长高4倍(Ravallion和Chen,2007)。有利的土地分配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东亚其他国家如越南得到了相关经验的证实。印度的经验传递了更加微妙的信息:在减贫效果上农业增长的作用与服务业增长基本相同,尽管非农业增长的作用在那些农业生产率高的省更加明显(Ravallion和Datt,1996、2002)。此外,Foster和Rosenzweig(2004)的证据表明,印度农业生产率增长最慢地区的农村非农可贸易部门的增长率反而最高。
关于农村贫困的模式和演变的讨论有利于促进关于非洲的深入分析。贫困在农村最严重,但是这是着重关注农村和农业的充分理由吗?成功的减贫并不简单等同于较高的农业增长率。最多只能认为与增长相关的快速减贫时期农村增长对于减贫可能很重要,但是成功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与超过农业部门增长的非农部门增长相关联。
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要理解农村贫困的变化不能天真地单纯关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此类分析应该考虑城乡联系,并且在总体增长和变化的背景之下展开。可以说第一个系统分析这类问题的是刘易斯模型(Lewis,1954)。该模型是城乡互动理论的重要部分,尽管该模型关于城市背景下市场发挥作用、尤其是激励和决策的本质进行了一些特定假设。后来的很多研究已经使得此类分析更为精炼,很多文献都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在开始时很多经济活动和劳动力都分布在农业和农村中,那么在此状态下如何实现增长和减贫?在最新研究中,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
然而,相对于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状况和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特别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取得巨大发展。非洲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及国际贸易正在日趋自由化。全球化、不断提高的开放度、商业化农业投资、市场化正不可逆转地稳步改变着整个环境。商品价格尤其是谷类价格的居高不下为农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所有这些因素为回答下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农业是否可能和应该成为增长的动力?农业是否可能和应该在增长的背景之下成为减贫的动力?
二、 非洲农村和农业增长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作用
很多关于农业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的分析都是基于筒单的假设。例如,因为贫困人口从事农业,所以农业是减贫的基础。与此不同的是从关于贫网数据得到的基本结论:经济的全面繁荣伴随着更少的人口依赖农业谋生。关键的问题却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
本文分析基于Eswaran和Kotwal(1993a,1993b,1994,2002),它是该问题中分析最清晰的文献,该文尽管包括精彩的经济理论分析但却没有任何方程。Eswaran和Kotwal研究的相关性体现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给予回答;尽管其他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和观点,但是却很少有Eswaran和Kotwal那样简明而令人信服。我将在本节结合印度情况简要总结Eswaran和Kotwal的主要观点,并请读者品味他们的分析。然后,我将讨论这些结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的适用性。
Eswaran和Kotwal的分析可以看成是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之下的刘易斯模型,舍弃了刘易斯原始模型中的一些最困难的假设,而现在的很多研究仍然保留了这些假设。简言之,去除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假设,因而没有剩余劳动力可供剥削。而且工业劳动力在农业总产出下降时不会以更多的工业品替代粮食的消费。
(一)理论框架
Eswaran和Kotwal模型假设一个两部门经济,即工业和农业。存在两种商品,即衬衫和粮食。两部门的生产受到各自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限制,农业生产同时使用劳动和土地。农村经济中存在地主和工人,工业部门存在工人。关键假设是偏好根据“字典式的排序”:工人首先消费足够数量的粮食然后消费衬衫。关键假设满足恩格尔效应,即富裕人口在必需品上的消费比例更低,但是显得更加极端。换言之,对于极度贫困人口而言,工业品价格下降不足以诱导消费者削减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尽管实际上该假设并不直观,但是它慎重地认为贫困与生活必需的粮食消费的剥夺相联系。正如Eswaran和Kotwal所证明,放松该假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结果,但是减少了不同技术约束下的二元经济在理论含义和其他发展方面的冲击力。经济的初始禀赋不平等,富人拥有土地等财产,穷人只能出卖劳动。首先,穷人只消费粮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财富满足基本需求;一旦满足粮食的消费需求,不再过多消费粮食。因此,存在一个粮食消费的最高水平,而穷人只消费粮食。
进一步假设存在出清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在农业或工业部门工作没有差异:与刘易斯模型相反,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分割的,而是一体化的。产品市场出清,需求等于供给。所有关于市场的假设说明如果劳动需求上升导致实际工资增加,贫困将减少。换言之,贫困人口的实际工资上升与否决定贫困率是否下降。然而,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基于以上假设,可以发展出一个通用的模型以比较在不同战略下如何实现减贫目标。理解不同战略在什么背景和环境下是减贫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一,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应该考虑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来实现(中性)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在上述假设之下,Eswaran和Kotwal证明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能够生产更多的衬衫。衬衫的价格下降,但是贫困人口并不关心这些更便宜的衬衫,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人有激励转移出农业部门,不然粮食供给下降、食品需求上升。最终,只有富人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受益,富人有足够的粮食而且已经消费了衬衫,由于价格下降富人可以消费更多的衬衫。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上升,但是衬衫的价格下降。就业没变,并以工资、食物价格和穷人的实际工资与之前相同。虽然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但是贫困状态依然维持原状。
第二,考虑一个封闭经济和(中性)的农业技术进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粮食。这将显著影响所有工人:相同数量的工人拥有更多的粮食。一旦有更多的粮食可供消费,一些人将跨越食物消费的临界值,开始购买和消费衬衫,结果导致衬衫价格上升。这对工厂扩张生产和雇佣更多劳动力承担额外的生产任务提供了激励。劳动力需求增加将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农村工资也会随之上升,粮食价格由于产量上升会略有下降,而且穷人脱贫后会将其部分需求转移到衬衫上。在均衡状态下,劳动力会从农业转移到衬衫生产中,实际均衡工资的上升意味着贫困的减少。
两种情形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农业增长对于减贫至关重要,而工业增长没有影响。需求联系是关键因素,但是对于减贫而言需求联系只是通过穷人的消费实现。Mellor (1999)-直强调该过程的重要性,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增长的联系,同时也是贫困的联系。农业成为减贫的核心动力。以上结果深受开放性假设的影响。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关于需求和供给的约束对于可贸易品而言无关紧要。粮食可以进口,衬衫可以出口。因此,如果假设两种商品都是可贸易品,只有世界价格水平才会起作用。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两种情形。首先,考虑工业进步的影响。相同数量的劳动力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的衬衫,但是价格维持不变,因为世界的价格不变。工厂存在扩张生产的刺激,因此劳动力需求和名义工资都会上升。即使粮食供给下降,在粮食可以进口的情形下工人也可以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最终劳动力的农业边际产品也上升,城乡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上升。粮食进口与实际工资一起增加意味着消费的粮食更多、某些工人开始消费衬衫。结果是贫困下降。其次,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与工业进步类似。对于实际工资和产出的联系而言,需求联系无关紧要,实际工资上升,更多的人购买衬衫。
简言之,减贫可以通过任何相对于国际的国内竞争能力的提高来实现,这-与封闭经济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也同时产生了经济的脆弱性: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高以及相对经济竞争力(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丧失将对贫困产生不利影响(即工业和农业的衰退)。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超越贸易伙伴非常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第一波走向开放经济浪潮的背景下,Eswaran和Kotwal坚定认为印度在这方面存在极大潜力,尤其是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而且即使在农业和农村部门进步有限的情况下,开放的贸易模型也有利于减贫。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科技进步也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分析相对简单,但是模型说明了一些核心问题。第一,在任何背景下,关于减贫定义的确定性特征似乎与非农部门逐渐吸收劳动力相关联。关于农村贫困,没有什么特定的性质,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典型标志,同时也是增长动力不当的标志。第二,为了理解农业部门在减贫中的地位,有必要考虑开放经济情况下的状况。如果是封闭经济,农业增长对于减贫非常重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相对于工业进步而言,农业增长在给定需求联系的条件下更能够直接地实现减贫。在开放经济下,情形并非如此。全球化背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关于农业地位的动态理解:开放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需要合理理解随之而来的陷阱和风险。第三,把劳动力、生产技术和部门的异质性引入模型不会改变上述模型的基本逻辑(Eswaran和Kotwal,1993a)。然而,如果科技进步不是中性和劳动密集型的,而是劳动替代型的,该模型预测到技术进步的减贫作用更为微弱,因为劳动需求和真实工资上升的幅度更加有限。Eswaran和Kotwal(2002)扩展了模型,引进了服务业部门和不可贸易商品,互动作用更加微妙但是不影响主要结论。
这对于农业增长有什么重要含义?一般而言,这很重要:在很多背景之下,这是最适合的减贫机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科技进步包括逐步采用新的投入品,例如新的品种、肥料和种子。这包含一些不能令人愉快的算术,农业方面的很多进步本身基本是一次性。例如,对于特定作物而言,采用新肥料只能一次性提高20%的产量,但是不能实现每年持续的收益增长。任何增长效应都将极大地依赖于广泛的关联效应。一些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关联很普遍(例如Mellor,1999),正如之前认为的那样,基于特定的国家采用特定的方法获得的经验证据,例如依赖于关于行为的强假设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关于印度的证据虽然具有启发性,但不是结论性的。Datt和Ravallion(1998,2002)以及Ravallion和Datt(1996,2002)基于1995年以前的省际均值数据讨论了印度增长和减贫的经验,该时期处于印度经济逐渐开放之前,虽然印度在1980年晚期的总体增长已经加速。换言之,印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该研究的第一个发现是,基于增长和贫困的部门构成,农业增长对于减贫十分重要,而工业增长并没有影响贫困。显然,这是上文模型直接预测的结果。上述证据证实了农业收益增长极大影响贫困。
第二个发现是,减贫深受特定(地区内)初始条件的影响。可以用关联效应来解释这种现象:其他条件相同,较好的禀赋如科技水平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作用方式是经济体的自我强化。证据表明关键的初始条件包括较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与工人潜在生产率相关)、农村地区较好的初始禀赋(包括没有土地的人较少、初始收益较高,反映了较高的科技水平)。该证据显然与普遍提高工人生产率因素的影响一致,不同的是通过农业部门发挥这些因素的增长作用。这与封闭经济模型的预测相符,虽然并不能证明该模型完全正确地代表真实情形。
印度经济的开放以及成功融人世界经济消除了Eswaran和Kotwal模型中关于需求关联的根本约束。不管生产率进步是劳动密集或者中性,生产率提高出现在哪个部门对于减贫已经不太重要。近年来,其他部门在研究与开发上的巨大投资为减贫提供了新的可能,虽然高科技服务业投资的减贫作用主要通过与低技术含量部门如建筑业的增长联系实现的。
(二)非洲的适用性
上述结果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吗?在Eswaran和Kotwal模型中,如果增长是由农业部门劳动密集型或者中性技术进步的增长驱动的,那么这种增长的减贫作用十分巨大。土地在非洲多数国家分布不存在高度不平等。非洲国家没有土地的人相对较少,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土地分布极其平等。生产率提高有利于贫困农民,因此增长的减贫作用十分巨大。非洲农业环境的变化,如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消除了很多对农村的歧视,使得减贫潜力得以实现。“非洲绿色革命”具有巨大的回报。
然而,农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必要性并非确定不移。正如上述模型所示,在开放经济中,减贫对于农业进步的绝对依赖消失了,因为需求与农业的关联不存在了:其他部门劳动密集型的增长同样能够促进减贫。为了评估农业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考虑非洲的增长机会。Ndulu等(2008)提供了以三种方式描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增长机会的基本模型;Collier(2007)也采用了类似的描述。研究人员区分经济增长机会:第一,资源丰富型国家;第二,沿海或位置优越型国家;第三,内陆资源贫乏型国家。每类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减贫过程中将会遇到完全不同的困难。
对于资源丰富型国家而言,关键问题是怎么管理财富:怎样将国家控制的潜在财富转换为持续的共享式繁荣的基础。他们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荷兰病以及治理问题,更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刚果。
对于沿海国家或者位置优越型国家,他们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所以没有直接的财富来源,需要创造财富。他们充分利用两种生产要素:人口和位置优势;非洲的很多沿海国家,特别是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和南非,就是此类国家。他们主要的挑战是怎样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的机会。沿海国家在原则上应该利用世界贸易的机会,所以首要任务是建立贸易基础设施,制定市场制度和规则,对技术进行投资,支持高质量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些挑战完全不同,但是全球化提供了重大机遇。如果没有利用自身的优势,沿海国家将落后;但是潜在的优势仍然存在。
内陆资源贫乏国家受制于产业集聚效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而且只能完全依赖于邻国克服困难。如果位置优越或者资源丰富的邻国经济落后或处于战争冲突状态,将使情况更糟。这些因素都将产生负的外部性。例如布鲁迪、布基亚法索和埃塞俄比亚。
那么,什么时候农业增长是必要的?农业增长在该框架下的地位如何?首先,考虑资源丰富型国家。农业不太可能成为增长的必要来源。然而,此类经济需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农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以农业增长推动总体经济增长的负担不存在了,集约化或多样化的努力可以更加向扶贫倾斜,包括关注小农农业,例如支持新技术和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活动。但很显然有很多方法促进国家财富分配,而刺激农业增长很难说是首要的。而且,在农村地区投资,包括基本服务如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再次分配的有效方式,并且从长期来看(相对于狭隘地关注农业而言)具有更高的回报率。例如,确保投资集中在高潜力领域的压力相对更小。
其次,考虑位置优越型国家。位置优越型国家具有利用世界经济机会的最佳地理位置。通过劳动力市场、技能、规则和投资环境保持比较优势是重中之重。农业的作用类似于开放经济中的Eswaran和Kotwal模型:工业化进步是利用贸易机会的最佳路径和最佳工具。农业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当贸易导向型增长开始起飞时,作为从农业退出的途径,农业进步具有很大意义。如果能够促进熟练劳动力被吸收进合理的部门,通过健康和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最为有效。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的经验让人联想起它积极的农业政策以及城市工业经济部门最终大量吸收劳动力的过程。对非洲经济而言,主要挑战是克服其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相对于东亚很多经济已经建立起工业基础的国家而言,非洲国家作为后来者处于不利地位。这虽然需要对制造业发展的特殊支持才能实现潜在的地理位置优势(Collier和Venables,2007),但仍然是增长的最佳途径。
内陆资源贫乏国家又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困难。在很多情形下很多国家的农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埃塞俄比亚和布基亚法索。而且他们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的风险非常大。这类国家主要依靠位置优越型邻国给他们带来一些贸易导向型的机会,包括劳动力迁移。在积极的政策方面,空间很小: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投资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投资的领域,它们在很长时间内排序仍然很靠后.因为位置优越型邻国还没有融人世界经济。结果,看待这些经济的最佳途径是将其作为封闭型经济,而忽略其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正如模型所预测,农业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都十分重要,但是不要期待任何奇迹发生。
积极追求农业技术进步以及促进农村生产率提高的其他方式是促进增长的主要途径,同时对于减贫具有很大影响。农村、农业的发展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些国家一般处于农业薄弱落后地区,但农业也是最值得努力的领域。为了减贫,在发展潜力较大地区促进农业发展(如增长的要求)和在边远贫困地区促进农业增长之间存在重要的权衡取舍。如果商品价格很高,促进增长和减贫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更加明显,因为提高农业总产出更为重要。
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对比十分鲜明。埃塞俄比亚在最近几年试图实施开放政策,但是位置优越的邻国未能利用贸易机会,一般而言,埃塞俄比亚与他们的关系冷淡(如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这严重限制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择空间。
埃塞俄比亚最好只能建设基础设施和培养劳动力技能,增长只能通过农业系统而持续地降低农村贫困率来实现。埃塞俄比亚的人们无法利用与邻国贸易和迁移的增长机会。
印度的一些小块地区甚至省份(如比哈尔省)也正如埃塞俄比亚一样面临自然资源匮乏等发展困境。但是印度经济广泛一体化,部分落后省份充分利用了日益提高的开放程度和优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而且增长的外部性和就业的机会为落后的省份提供了机遇,降低了当地贫困率。
即使如此,埃塞俄比亚也不能单独通过农业政策实现奇迹。相对内陆的位置、依赖降水的多少等使得农业丰收暂时大幅压低农民的粮食价格,因为出口粮食价格很低(世界粮食价格减去从农场运到世界市场的费用)。例如在2001-2002年,在一个短暂的收益增长和地区扩张之后,风调雨顺的天气使玉米大获丰收,但是价格低到丰产变成不丰收。这些事件延缓了农业的转型,对于具有高额运输成本的内陆国家而言,需求增长以避免价格的突然降低十分必要。
三、 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了宏观或者一般均衡模型中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作用的阐述。整个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高的开放程度和市场自由化经济的进程,改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分析中得到完美结合。但这个分析建立是在要素和商品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设之上。正如最近几十年关于农村发展的很多研究表明,即使消除了很多政策造成的市场缺陷如农产品市场,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只有不同要素的边际回报相等时资源的分配才是有效的。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要素市场,对不同的人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其结果是差异性的形成,如具有不同初始禀赋的人可以利用不同机会(如增长所带来的机会)。农村非市场制度安排的发展可以部分替代或弥补市场失灵,但不可能完全替代。这对于经济增长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对于贫困人口可以参与经济增长的程度而言都很重要。上文讨论过的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一般经济增长机会的潜在分类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因而经济增长的减贫和经济过程的广泛包容性的效应才能实现。
我在本节将尝试将过去几十年关于家庭和制度的大量微观研究的核心成果应用到减贫和增长的更加广泛的境况中去。核心问题在于:关于农村贫困人口参与乃至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关键制约因素是什么?最近很多关于农村问题的学术文献探讨了要素市场的市场失灵,如土地、劳动力、信贷和保险。这些成果构成了研究生微观发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核心。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微观问题是否能够放到增长和减贫的广阔背景中去。
我将考虑的问题是:即使是在已经开始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中,什么因素会导致一些农村穷人陷于贫困之中?此外,对于通过增长来减贫且其增长完全依靠农村发展努力的国家而言,如内陆资源贫乏且邻国经济落后的国家,解放农村潜在生产力的需求意味着当我们试图解释什么原因导致某些特定农村地区增长落后时需要特别注意。我重点讨论三种情形,阐释最新理论文献的一般原则和发现,其中一种是经验证据发现的:初始贫困和市场失灵一起使得部分贫困人口持续贫困甚至陷入贫困陷阱。我还会关注市场失灵的三个问题:资本(信贷市场失灵);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空间外部性(地理诅咒)。
(一)信贷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
最为明显地可以观测到的市场失灵是信贷市场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偏离。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任何可盈利的项目都能在当前利率水平下获得贷款。如果市场是完美和有效的,没有银行会要求抵押担保贷款。现实生活中,没有抵押就不会得到贷款。抵押要求可以理解为信贷市场处理困扰这类市场的核心问题即不完美信息的重要手段:信息不对称,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执行问题。不完美信息意味着贷款人不能从很多项目中区分哪个项目的风险更大,不知道借款人在获得贷款之后是否会采取当初承诺之外的行动,所以会要求抵押担保贷款。抵押还可以确保贷款的偿还。
如果一些人初始就没有财产,市场失灵对穷人而言极其有害,排除了穷人获得贷款进行有利投资的机会。很多含义丰富的模型如Eswaran和Kotwal(1986)展示了信贷市场失灵的关键含义:富人不仅通过财产获得更多收入,而且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财产。市场失灵迫使穷人处于低效的状态,这进一步加剧了初始的不平等。农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类似过程,而且通常与信贷市场失灵相联系。模型的一个重要预测是穷人土地的边际回报高于富人,穷人的土地每亩①平均产出也高于富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耕种土地数量和每亩单位产出之间的负向关系。Binswanger等(1995)对这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且寻找不同的解释。土地质量差异是部分原因,但是与信贷相关的要素市场失灵也是部分原因。
该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但是它潜在的动态含义在直觉上很吸引人。资产不平等,富人回报更高而且资产增值更快,穷人采用新技术或进行其他活动的回报率更低、而且也不可能开始财富积累的过程。很多增长模型给人的直觉是一些人陷入贫困陷阱而另一些人不断积累财富。Banerjee和Newman(1993)发现资产不平等对于增长的影响与信贷市场失灵相关。当进入不同经济活动存在一定的资产门槛时,那些只有有限资产的人进入特定项目的机会就被排除而陷入贫困陷阱,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进入某些职业并开始攀升。贫困陷阱是一种均衡结果,如果没有外在的帮助就无法改变状况,如正向的意外收益、收入再分配、援助、市场运行方式的根本改变等。很多其他文献认为贫困陷阱、整体无效率、增长乏力是信贷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贫困和不平等造成的,因而部分人无法利用增长带来的投资机会(Galor和Zeira,1993;Benabou,1996;Aghion;Bolton,1997)。信贷市场失灵模型同时也是《世界发展报告2006》(世界银行,2005a)的中心内容;该报告还讨论了这个模型引申含义的相关证据。
如果信贷市场失灵导致农村的贫困陷阱、或投资不足的普遍存在,这会抑制经济增长。此外,如果经济增长加速,但是有利的机会需要一定的投资门槛(例如家庭成员迁移成本、项目的沉淀成本),那么信贷市场失灵将会使穷人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虽然证明信贷导致贫困陷阱很困难,但是在非洲农村存在进入成本的证据(特定项目)以及资产(投资资产有限)导致家庭拥有更少的有利组合(Dercon,1998;Barrett等,2005)。
如何用政策干预信贷市场还不清楚。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一直是受到偏爱的干预手段,如近年来的小额信贷,当然其他很多干预措施对于解决信贷市场失灵可能也很有效(Besley,1994)。贫困群体是否从小额信贷中收益最多同样不清楚(Amendatriz de Aghion和Morduch.2005):这需要等待从最有影响的小额信贷产品的评估得到更多的发现(Karlan和Goldberg,2006)。对于非洲而言,关键问题是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培养农村穷人参与经济的手段是否被过度高估了:在农村环境中,小额信贷被看作帮助农村穷人脱离农业生产,而进入受到限制的非农经济活动的手段。虽然信贷市场的限制将农村贫困群体排除在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之外,但是大规模的减贫不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独立经营活动来实现。很多国家实现高收入和低贫困的途径是提供更多雇佣工作岗位、不断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长期来看,对健康、教育和技能的投资将获得高收益,对于资源丰富和制造业出口导向的非洲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允许部分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的经营活动会有助于经济转型的完成,但是靠大规模人群从事创业经营活动不大可能是成功的经济转型之路。
此处存在一个困境:只要经济还没有起飞、劳动力需求没有加速,此时援助穷人从事创业经营活动有助于减贫。在非洲很多国家,教育回报率随着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加:小学很低,更高程度教育的回报率更高(Soderbom等,2006),因而在劳动需求很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投资教育不是脱离贫困的快捷途径;如果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局面将会改变。小额信贷为穷人提供了脱离贫困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小额信贷本身还不是大规模减贫的有效途径。在很多情况下,小额信贷不要只面向创业活动,而是更多地面向普通的家庭金融需求,这会使小额信贷的作用更加有效(Karlan和Mullainathan,2007)。
(二)保险市场失灵和风险诱导型贫困陷阱
另一个过多影响贫困群体的严重市场失灵是贫困群体面对风险时保险和保护的缺失。完全保险市场(或更准确地说,完全或然市场)的存在是现实中不成立的另一个假设。与导致信贷市场失灵的原因相同,不对称信息和执行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保险机制覆盖率有限的主要原因。穷人即使愿意,也无法为他们面对的风险获得任何保险。
没有保险的风险给穷人带来很多困难。发展中国家频发自然灾害、干旱、冲突、动乱以及经济冲击,如物价上涨和货币危机。健康问题和农作物虫害更为广泛。这些都被看成暂时性问题,急需临时解决方案,如安全网的建立,之后回到更加根本的问题即发展。政策制定者也认为这些社会问题不应该转移他们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社会贫困的注意力。然而,这是误导,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风险和冲击是低增长的原因,低增长又造成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集中关注贫困人口有助于增长和平等;任何情况下都是确保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工具。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机制应对风险。典型的是两种措施: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应对策略。风险管理策略包括通过选择项目组合优化降低风险以实现管理风险的目的。例如,选择低风险的活动或者通过不同的风险搭配多样化风险组合,如种植耐寒作物、进行小额交换或者收集柴火、季节性迁移等。风险应对策略包括处理收入下降风险的后果。两种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储蓄实现自我保险,通常在急需时出售耕牛和其他牲畜;非正式互助机制,小组成员或社区成员基于互助的基础上在急需时提供转移性资助(Faf-champs,1992)。
这些策略都有成本:收入风险管理策略导致平均收入降低和收入波动变大,收入风险应对策略调整财产组合处理风险通常要求持有低收益的流动资产,放弃生产性的同定投资。这影响了他们的长期收入,并且削弱了脱离贫困的能力。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策略意味着贫困人口遭受严重的效率损失,而富人一般受保险、财产和信用的保护不需要承担损失(Dercon,2002)。Morduch (1995)展示了在印度因为在一定的环境下风险太高而无法采用更有利润空间的技术。即使存在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农民仍然可把持有牲畜作为预防风险的措施(Rosenzweig和Wolpin,1993)。Rosenzweig和Wol-pin(1993)发现印度样本中的最富的五分之一人群和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群之间的效率损失差距超过25%,这是由于面对风险而调整资产组合所致。在埃塞俄比亚,Dercon和Christiaensen(2007)发现很少采用现代投入是因为很少获得风险相关的投入贷款,即使由于降水原因作物歉收,也需要强制偿还上述贷款。长时期内,这些结果导致大量效率损失,极大地影响穷人。
这些风险管理策略会使穷人陷于贫困:为了避免极端贫困,他们被迫放弃盈利但有风险的机会,也就放弃了脱离贫困的机会。即使如此,他们并不能完全保护自己:虽然很多证据表明风险管理策略能够减少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波动性,但是它们仍然无法处理一些严重的重复发生的冲击,如那些影响整个社区、地区甚至国家的冲击(Morduch,1999;Dercon,2002)。这些没有保险的冲击破坏家庭财产,迫使家庭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们甚至可能跌落到一定的水平之下,落入贫困陷阱之中,例如由于风险策略需要避免更加严重的穷困或其他。
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上述过程是导致持续贫困和永久处于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Jalan和Ravallion(2003)利用来自中国的数据检验贫困陷阱是否存在,虽然没有发现纯粹的贫困陷阱,但是发现家庭需要很多年才能从一次收入冲击中恢复过来,而且贫困人口的恢复更加缓慢。Dercon(2004)利用埃塞俄比亚农村的面板数据发现非洲也存在相关证据,没有保险的冲击与持续贫困有关,前4年的降水量冲击影响当前的增长率,甚至1984-1985年饥荒是20世纪90年代家庭收入增长率的解释因素之一。而且,埃塞俄比亚农村的一种重要储蓄方式是牲畜,它们平均需要10年才能恢复到1984-1985年饥荒之前的水平。Elbers等(2007)利用基于模拟的计量模型校准了一个增长模型,并用津巴布韦农村数据直接测算了风险和风险反应。他们发现风险大幅降低了增长,降低了40%的资本存量(稳定状态)。三分之二的损失是由于家庭试图最小化风险影响所采取的策略所致。Barrett(2005)基于肯尼亚牧民牲畜持有量发现了贫困陷阱的证据。
健康和教育也由于没有保险而受到冲击,其长期影响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例如,干旱对于儿童的永久影响已经被详细阐述,更低的成年身高、更差的教育质量、更低的永久收入。例如,在津巴布韦农村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儿童遭受干旱和战争的影响,永久性收入损失了7%~12%甚至更多(Dercon和Hoddinott,2003)。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农村没有保险的严重后果,尤其对贫困人口而言。如果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且该失灵由于贫困而加重,那么显然存在一种既能减贫又能刺激效率和增长的干预措施;无论如何,这些干预措施能够保证穷人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保险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被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大量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直接转移支付解决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高昂的行政成本和高度的信息要求。简言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
有很多应对措施可以考虑,如减少农村家庭的风险(例如预防性健康服务,或者更好的农业用水管理),加强现有应对措施(例如投资建立更多的储蓄产品,或者运行更好的针对牲畜的资产市场),改进保险形式,拓宽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范围。虽然每种措施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近年来采用了很多针对保险的有价值的创意,即使其潜在的收益并不是很大。
(三)空间效应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普遍原因是空间外部性的存在。如果经济或其他交易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在交易主体的考虑范围之外,那么就存在外部性。标准的案例是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因为环境污染不在商品的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考虑之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更广泛的现象是,以外部性的概念理解特定地理区域处于落后的状态——贫困的邻居、贫困的地区和贫困邻国。如果仔细观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就会非常震惊地发现一些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正在日益被边缘化,伴随着低经济增长、持续的人口增长和持续贫困。虽然研究得较少,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在高增长国家,仍然存在系统性落后的地区,从收入增长和贫困降低角度看这些地区没有从总体经济增长中获益。中国和印度的特定区域正是这种类型。虽然描述得较少但是依然真实的是,类似非洲国家增长和减贫方面的地区间差距在这类国家也存在。
关于工业集群化及地理位置的理论对上述地区间差距现象给予了很好解释,这些理论预测企业为了追求地理外部性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回报而集中于同一地区(Fujita等,1999)。其推论是某些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地点会失去增长的机会:不经这些地区得不到所急需的投资,而且这些地区现有的资本也会为追求利润而逃离该地区。那些失去增长机会的地区就遭受了那些成功地区的负面外部效应。显然这也是一种贫困陷阱:尽管这些地区起初没有差异,但是那些失去增长机会的地区只有依靠外部帮助或大规模的努力才能脱离贫困陷阱。这些地区遇到了吸引或者留住资本方面的门槛。
其他解释同样强调与特殊的当地环境相关的外部性,例如公共品、公共产权资源和私人财产等当地禀赋。如果经济起飞也面临一定的当地禀赋门槛,那么禀赋贫乏的地区难逃贫困。要证实这一点很难,但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是有一些证据。对于非洲而言,Christiaensen等(2005)根据很多国家的证据讨论了非洲地理位置偏远对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
上述外部性也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影响着财产较少的贫困人口,不过在这里财产定义是广义的,即包括当地公共品和环境。给定已经确认的贫困陷阱,上述经验证据论证了“贫困地区”项目的合理性,即贫困地区需要大规模投资项目来增加地区或社区的资本存量。然而,这些经验研究缺少充分的细节以及关于外部性如何发生的说明。因而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引导乃至指出哪种干预手段更为有效。
例如,很多农村“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偏远,主要与缺乏道路和通信基础设施相关。最普遍的捐助政策指向是为贫困地区修筑道路。虽然这种捐赠无疑为偏远地区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这不一定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起飞所需要的。在一些国家,证据表明捐赠修建道路确实是一项合理的措施。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修筑道路是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反应或者至少说是承认当地经济增长潜力的一种标志(例如经济作物或煤炭),但不是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反,例如灌溉、健康和教育对于解放增长潜力更加重要。
无论如何,少量努力是没有帮助的,为了使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大规模投资是跨越起飞门槛的必要条件。也许创造更多迁移的机会是更好的政策。然而,这不但成本很大而且可能困难不少。如果劳动力迁移面临的门槛也很高,那么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将无法抓住其他地方的增长机会。但是这不过是前面潜在农村贫困陷阱的例子,解决方案需要仔细考虑城乡背景以及其他关联,只关注农村地区是无效的。
四、 结 论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几十年里增长缓慢、贫困率居高不下。由于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也许会认为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政策是增长和减贫政策的核心。
本文在非洲背景之下利用了宏观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微观视角讨论了一些核心问题。基于Eswaran和Kotwal(1993b)的模型框架以及Ndulu等(2008)关于非洲增长机会的证据,我得出结论认为在非洲对于内陆资源贫乏型国家而言,农业增长很重要,虽然农业增长本身也很难实现。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位置优越有利于制造业和出口或者资源丰富的国家,农业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即使农村发展可能是实现经济缓慢转型的重要措施,但是农业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然而,上述分析基于运行良好的要素和商品市场,没有考虑初始禀赋对贫困人口利用经济增长机会的影响。但是农村完全市场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大量证据表明即使经济起飞,贫困人口仍然被排除在有利的机会之外无法摆脱贫困,甚至落入贫困陷阱。农村发展政策以贫困人口以及刺激贫困人口从事的农业生产为目标,可能是促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我充分讨论了信用和保险市场失灵以及贫困地区的空间效应,并分析了排斥贫困人口的机制。相关合理发展政策措施的证据仍在不断出现,更需要更多的试验和研究。
资料来源:Stefan Dercon.Rural Poverty:Old Challenges on New Con-text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24, No.1(February 2009).The World Bank Observer i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BANK.,2009.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减贫能力的影响:
来自非洲城乡经济部门的证据
Augustin Kwasi Fosu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摘要:本文基于20世纪90年代非洲城乡经济部门样本研究收入分配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本文采用基本需求法,推导并估计了一个协方差分析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是贫困人口比例、贫困线差额比例、贫困线差额平方比例三个贫困率指标,解释变量分别是基尼系数、购买力平价收入。本文发现经济增长对于贫困率的影响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递减函数,尽管不同贫困衡量指标的递减速度不同:贫困人口比例最慢,贫困线差额其次,贫困线差额平方最快。贫困人口、贫困线差额、贫困线差额平方的收入弹性的范围分别为0.02~0.68,0.11~1.05,0.10~1.35。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对于贫困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差别,而在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这意味着相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更需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别。
关键词:收入分配;增长;减贫
一、 引 言
贫困现在成为全球关注的主题。作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首要目标——争取到2015年将贫困率降低一半,贫困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SSA),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率全都大幅降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很难达成“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率减半的首要目标。事实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日均生活水平低于1美元计算的贫困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0年的46%,而2000年正是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一年(世界银行,2006)。然而,近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2004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率为41%(世界银行,2007),近似于1981年的贫困率水平,尽管全球其他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面对该挑战,本文将着重研究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贫困问题。
对于收入分配在减贫方面重要性的关注与日俱增。许多研究分解了收入分配效应和收入增长效应(Ali&Thorbecke 2000; Datt&Ravallion 1992;Kakwani 1993)。Datt&Ravallion(1992)与Kakwani(1993)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因素与收入增长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减贫贡献都很大。基于非洲跨国数据,Ali和Thorbecke (2000)发现贫困对于收入不平等比对于收入本身更加敏感。
一些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不平等程度在决定收入增长对于贫困率的影响方面的重要性(Adams 2004;Easterly 2000; Ravallion 1997)。此类研究均以具体的问题切人分析。例如,Ravallion (1997)采用计量方法检验了“增长弹性观点”(growth elasticity argument),即低不平等程度一方面有利于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使得贫困人口承担经济萎缩的成本;Easterly(2000)在“贫困增长方程”(poverty-growth equation)中界定了相互作用的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程度,评估了布雷顿伍兹研究所(Bretton Woodz Institute)项目的作用,并发现该项目的作用因低不平等程度而更加明显;Adam(2004)强调收入增长定义的重要性,提出的弹性估计方法证明,低基尼系数(低不平等程度)群体的贫困率增长弹性更大。
首先,本文采用基本需求法推导了一个关于贫困和增长关系的协方差分析模型,其中不平等程度既以独立于收入的方式又以与收入相互作用方式进入模型。其次,本文采用20世纪90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城乡截面数据样本估计了模型的完整形式和简化形式,发现收入不平等降低了收入增长在减贫方面的作用,对贫困的严重度(贫困线差额平方)影响最大,贫困的深度(贫困线差额)其次,贫困的广度(贫困人口)最小。本文基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揭示了收入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现有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高效地降低贫困,更多地强调收入增长还是更多地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需要根据非洲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
二、 数据、估计和结果
(一)数据
本文数据包括20世纪90年代16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城乡经济的32个观测值。该数据是基于家庭普查并且同时提供城乡经济情况的数据(世界银行1997)。本文采用非洲国家的截面数据而没有采用面板数据主要是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可用的面板数据,尤其是具体到城乡部门的经济情况数据。而且,由于本文感兴趣的是跨国家的贫困率弹性比较而不是跨时间的贫困率比较,面板数据的缺失并不会导致太大问题。
实际上,在以截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不控制国家因素正是导致国家之间贫困率弹性差异的因素。这些正是本文深入探索并据此设计适合国情的减贫政策的因素。而且,正如Adams(2004)所说,收入分配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国家之间的差异才是关键所在。最后,本文数据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其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经济部门,因此可以估计在一个国家内部部门之间贫困率收入弹性的城乡差异。
(二)贫困线
本文采用的是Ali&Thorbecke(2000)的“准相对贫困线”(quasi-rela-tive poverty line)。准相对贫困线的概念综合了固定的绝对贫困线和与收入同比例变化的相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是都存在问题(Foster 1998)。事实上,基本需求可能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基本需求也可能在城乡之间和不同时期之间变化。
因此,贫困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合情合理。真正的问题在于增长的幅度是多少?假设如相对贫困线所言,基本需求与平均收入同比例变化,那么除非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即收入比例增长恰巧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收入增长对于贫困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采用相对贫困线容易低估收入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假设贫困线随着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增长,生活水平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那么采用固定贫困线容易高估收入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因此,准相对贫困线代表两种极端的合理折中。在本文中定义准相对贫困线概念的办法是采用一条关于收入的二次函数的贫困线。
(三)统计数据描述
相关变量的总结统计如表1所示。据此,20世纪90年代50.3%的非洲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从加纳的32.1%到中非共和国的77.6%不等。类似,贫困人口收入距离贫困线的差距(以P1表示)平均为21.0%,低至加纳的9.0%.高至塞拉利昂农村地区的55.6%。贫困线差额平方(以P2表示)平均为11.9%,低至加纳的3.5%,高至塞拉利昂农村地区的45.9%。平均年收入为1985年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621美元,低至赞比亚农村地区的少于200美元,高至肯尼亚城市地区的近1 700美元。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平均为43%,低至科特迪瓦农村地区的30%,高至塞拉利昂农村地区的近70%。
表1收入分配、增长和减贫:总结统计
注:变量Pi (i=0,1,2)分别是人口、贫困线差额和贫困线差额平方衡量指标,以百分数表示;Y是以1985年经过PPP调整的美元计算的平均收入,基于Summers&.He.ston (1991);G是百分数表示的基尼系数。农村和城市的数据分别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Ali&.Thorbecke (2000)和世界银行(1997)。
表1存在普遍的城乡部门差异,三个指标的平均贫困率农村部门大幅高于城市部门。该现象使得Ali&Thorbecke(2000)认为非洲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农村现象。农村部门平均收入大幅偏低的现象同样值得注意,说明农村部门相对高的贫困率可以被其偏低的收入所解释。然而,有趣的是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城乡不平等程度没有差异。
(四)估计和结果
本文所用回归方程的完整形式和简化形式都采用怀特异方差一致标准误差和协方差方法(White heterosc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and covariance procedure)。简化形式的估计是为了将完整形式的估计结果与简化形式的估计结果相比较,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对于收入的减贫作用没有影响。简化形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式(A.1)、(B.1)、(C.1)分别表示贫困衡量指标Pi(i=O,1,2),式(A.2)、(B.2)、(C.2)分别是完整形式的估计结果。
然而,在讨论估计结果之前,本文首先基于怀特统计量(White Statistic)进行模型形式的检验。该检验不仅提供了是否存在异方差的证据,还提供了“误差是否独立于解释变量,模型是否正确设立”的证据( White 1980,第823页)。根据表2的结果,除了式(A.1)之外,本文不能拒绝“模型正确设立”的虚拟假设,支持估计过程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和内生性的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表2中的式(A.1)、(B.1)、(C.1)。对数收入y和对数基尼系数g的系数高度显著,且具有预期的符号,即收入增长降低贫困,不平等程度增加提高贫困。上述结论类似于Ali &- Thorbecke (2000),该文采用一个类似的模型分别估计了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子样本,并得到了类似结论。然而,为了增加自由度以提高统计的效率,本文将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子样本混合在一起,并引进虚拟变量d以描述两个部门之间可能的贫困率差异。正如表2的结果所示,同时考虑收入和不平等程度,虚拟变量不显著说明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贫困率差异甚微。该结果说明Ali&Thorbecke的发现,即贫困是一种农村现象,主要由于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之间的收入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异。虽然农村部门的贫困率远高于城市部门,但是一旦控制了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城乡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
表2收入分配、增长和减贫:回归结果
注:估计采用怀特异方差一致方法。被解释变量Pi分别为logPi (i=0,1,2);解释变量y为logY,g为logG;d是虚拟变量,d=l表示城市。估计采用20世纪90年代16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城乡经济的32个观测值。AR2和SEE分别是经过调整的R2和标准误。W(λ)是怀特检验的统计量,服从K (K+l)/2自由度的X2分布,其中K表示包含常数项的解释变量个数(White,1980)。a表示在0.01显著水平上显著(双尾)。括号中为t的绝对值。
本文现在讨论完整形式的估计结果:表2的式(A.2)、(B.2)、(C.2)。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些结果相对于没有考虑收入和不平等程度的交互项的结果表现出更好的拟合度,例如完整形式的模型表现出更高的拟合优度(AR2)以及更低的标准差(SEE)。正如预期,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y(收入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说明高度不平等程度会降低收入的减贫作用。具体而言,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贫困率的收入偏弹性P0将降低1.9个百分点,P1将降低2.7个百分点,P2将降低3.6个百分点。因此,不平等程度降低收入增长减贫作用的显著性将随着贫困人口、贫困线差距、贫困线差距平方三个贫困衡量指标依次递增。
g(基尼系数对数)的系数为负,说明在低收入水平上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会降低贫困。正如上文所述,虽然表面上与直觉不符,但确是正确结果。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大多数人在给定国家中很可能属于贫困人口;因此导致更高不平等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将使得更多人的收入高于贫困线,从而降低贫困率。上述结果不可能出现在简化形式(A.1)、(B.1)、(C.1)中。事实上,这里的模型可能揭示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程度的减贫作用的非线性和非单调的本质。
表3展示了贫困率关于y和g的偏弹性。首先看在均值水平上估计的数据(不是圆括号或方括号中的数),我们注意到关于y的弹性估计值明显低于关于g的弹性估计值。该结果类似于完整形式模型(有交互项)和简化形式模型(没有交互项)。因此,我们发现贫困率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响应比对于收入增长的响应更加敏感。其实,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贫困率的收入增长弹性很低,尤其是当以P0估计的弹性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在2.0和3.0之间的弹性相比时(Adams,2004)。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偏低的贫困率弹性实际上有利于解释近来的事实,即非洲国家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早起增长得更快,但是贫困率在90年代和2000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世界银行,2006)。然而,上文中提到的贫困率已经从2000年的46%降低到2004年的41%(世界银行,2007)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最终转化为贫困降低的一个标志,这与上述发现相符。
表3收入分配、增长和减贫:贫困率的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弹性
注:弹性根据表2中各式的结果估计。y(对数收入)和g(对数基尼系数)相应的数据基于均值根据带有交互项的完整形式模型[式(A.2)、(B.2)、(C.2)]估计。中括号中的数据根据没有交互项的简化形式模型[式(A.1)、(B.1)、(C.1)]估计。Y/g相应的数据是y的弹性与g的弹性的比值。小括号中的数据是范围,上下限分别根据g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相应方程中估计。
表3显示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程度对贫困率的作用按照P0、Pl、P2依次递增。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收入增长对贫困的重要性而言,不平等程度在解释贫困率时的重要性也按照P0、P1、P2依次递增。由于P0、Pl、P2指标分别考虑贫困的广度、深度和严重度,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差异的敏感度依次递增,该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正如表3所示,P0、P1、P2的贫困率的收入增长弹性范围分别为0.02~0.68、0.11~1.05和0.10~1.35。因此,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大小各不相同。 从理论上而言,收入增长和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单调的,结果如表4所示。以本文所用的样本而言,无论采用何种贫困率指标,贫困率是收入增长的单调函数。因此,从实用目的出发,非洲国家收入增长会降低贫困率,尽管降低的速度相对于不平等程度指标递减。类似的,正如上文所说,如果收入水平低于表4的门槛,不平等程度增加实际上可能降低贫困率。幸运的是至少就本文所用样本而言,只有P0的最小值191美元低于收入门槛值207美元,并且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因此,从实用目的出发,不平等程度降低会降低贫困率。
表4收入分配、增长和减贫:域值
单位:美元
注:当收入低于y相应的数据时,基尼系数增加将降低贫困率。该数据是P0、PI、P2分别基于式(A.2)、(R 2)、(C.2)并根据文中式9对4.353/1.888,5.445/2.684,6.880/3.566去反对数得到。当基尼系数高于g相应的数据时,收入增加将提高贫困率。该数据是P0、Pl、P2分别根据文中式8对3.464/1.888,5.007/2.684,6.606/3.566取反对数得到。
(五)城乡差异
从政策层面出发,本文阐释了贫困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响应的城乡差异。表5所示的是每个国家分部门贫困人口比例(政策制定中最为常用的贫困率指标)的收入弹性。我们注意到农村部门主导了最高四分之一和最低四分之一;然而,部分国家城乡差异很大。例如,尼日利亚的城市部门处于最高的四分之一,而农村部门处于最低的四分之一;因此,尼日利亚农村部门要达到一定的减贫力度需要更大的收入增长。相反,冈比亚农村部门的收入弹性高于城市部门,因此城市部门需要更大的收入增长才能达到一定的减贫力度。
但是一些国家的两个部门的收入弹性相近。例如,加纳和尼日尔的收入弹性都处于最高四分之一,说明这些国家的两个部门的收入增长都将轻松地转化为贫困的降低。相反,中非共和国和肯尼亚两个部门的收入弹性都处于最低的四分之一。整体而言,从表5中很难看出任何一个部门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最高和最低四分之一农村部门占据主导,第二个四分之一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平分秋色,第三个四分之一城市部门占据主导。实际上,从表5看,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弹性的平均值分别为-0.408和-0.404,因此平均而言贫困率对于收入增长的响应程度没有部门差异。但是也正如上文而言,国家之间的城乡收入弹性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异。
表5非洲经济样本的贫困率收入弹性
三、 结 论
本文基于基本需求研究途径推导和估计协方差分析模型,评价了不平等程度在收入增长和贫困率关系中的重要性。本文采用20世纪90年代非洲经济的城乡部门数据,发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提供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然而,不平等程度降低本身的效果可能相反,甚至在低收入国家可能提高贫困率。
本文揭示了虽然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都可以从收入增长中实现减贫,但是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减贫的幅度大不相同。P0、P1、P2的贫困率的收入增长弹性范围分别为0.02~0.68、0.11~1.05和0.10~1.35。公平的收入分配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按照P0、P1、P2依次递增,即P2最高,P1其次,P0最低。
本文的发现说明一套有效的减贫措施应该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强调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不同国家城乡部门之间贫困率的收入弹性差异巨大,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各自的城乡最优政策。虽然收入增长对于非洲国家有效地降低贫困率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在特定的国家应该更加关注恶劣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基本原因。为了保证收入再分配破坏经济增长的后果不至于抵消其减贫作用,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十分重要。
资料来源:Augustin Kwasi Fosu,The Effec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Aility of Growth to Reduce Poverty:Evidence from Rural and Urban African Economies,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69, No.3(July,2010).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开放世界贸易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吗?
——农业扭曲的争议角色
摘要:在最近几十年里,贸易政策改革已经大幅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业扭曲的损害,然而全球贸易在农产品方面仍然远比非农产品更加扭曲。文章总结了一系列新的全球和国家整体经济实证研究,关注剩余的扭曲对世界商品贸易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最终影响。
全球连锁(LINKAGE)模型结果表明,移除那些剩余的扭曲会减少国际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农业净收入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并且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占全世界的3%)。
本文的分析基于以15个国家为样本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和9个独立国家的案例研究。
一、 引 言
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收入都很低迷,是由于支持城市和一国政策中的反农业偏见以及富裕国家的政府愿意采取进口壁垒和补贴。进口壁垒和补贴这两项政策会减少国家和全球经济福利,抑制经济增长,增加不平等和贫困,因为不少于世界四分之三的十亿贫困人群仍然直接或间接地以农业为生(World Bank,2007)。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直在降低他们的部门和贸易政策扭曲,而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已经开始改革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然而,无数政策措施通过许多复杂的方式仍然扭曲着世界粮食市场(Anderson,2009)。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消费者提高食品价格和农户的收入,而发达国家却降低了这些。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农村和城市有一个混合物赢家和输家,尤其是因为许多农户家庭获得的一些收入是来自于非农资源。对于洞察价格扭曲政策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使用整个经济的定量分析模型与最新的价格扭曲数据以及理想情况下不同群体的乡村和城市的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的信息资料。
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政策改革有所贡献,需要进行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依然强劲。部分是由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这些政策改革和后续的收入增长使生活在不足1美元一天的人口的数量在1981-2005年间几乎减半,并且他们占全球人口的数量从42%下降至16%。然而,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在2005年仍然近乎9亿,而且它可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超越这个数目。此外,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有很大改善,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05年的贫困率略小于1981年,大约40%(总计3亿人)。尽管中国成功了,但是它在2005年存在超过1亿人仍然处于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其中90%的人在农村。在印度,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仍然顽同地接近于3亿人,74%在农村,即使他们的农民有大量的补贴。
压力虽然比极度贫困要少,但个人福利仍然重要,它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过去,地方不平等水平影响个人的效用,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增强了收入差异的意识,不仅在局部地区并也在国内外。在国家层面,人们担心乡一城不平等和这些广泛地理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农村地区,例如,收入差异在没有土地的非技术农场工人、自给自足的农民、更大的商业农民和在农村城镇的非农工人之间是巨大的。
评估世界收入分配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什么取决于个人的焦点。Mi-Ianovic(2005)指出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跨国不平等,是指在不考虑人口规模的情况下比较国家的平均收入,每个国家在世界上都有一个平等的重量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似乎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第二个是国际的不平等,这仍然是比较国家平均收入,但是这一次是国家人口加权。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似乎已经减少,尽管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快速增长(Bourguignon,Levin和Rosenblatt,2004;Atkinson和Brandolini,2004)。第三种可能的重点是全球不平等,这涉及比较个人的收入,不考虑国籍。因此,考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忽略了国际上个人赚取他们国家的平均收入的不平等方法的观点。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倾向于体现增加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此,通过这最后的定义,全球不平等似乎从1980年末基本保持恒定。
根据目前的依据,本文问题的重点是:有多大范围可以进一步减少世界的贫困和不平等,并且在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清除剩余的扭曲为激励来面临那些单方面可交易或全球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以实证研究为背景进行对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表明,在2001年,当这一轮被启动,策略驱动的扭曲对农业激励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福利成本商品的贸易壁垒和补贴(Anderson和Martin,2005)。尽管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应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外,没有对农民和食品消费者扭曲的激励措施获得全面的估计。一个最新研究中利用了一个新的关于扭曲农业激励的数据库已经证实了早期的结果:Valenzuela,van der Mensbrugghe和Anderson(2009)表明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占据70%的全球福利成本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鉴于农业与食品在全球GDP和贸易份额分别只有3%和6%,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农场和食品政策的贡献对于全球贸易保护政策的福利成本要更大,是72%,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它们自己的政策。即便如此,建模对估计价格扭曲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护他们欠竞争力的农民远离进口竞争,所以如果所有市场都打开了,一些农户家庭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Anderson,2009)。
世界银行最近的关于价格扭曲(Anderson,2009)的研究表明,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从51%下降至32%),对农民协助的比率相对于生产者的非农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它已经全部消失(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1%上升到2000-2004年的+1%)。后者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淘汰落后的农业出口税,因为援助通过进口限制在此期间显示已上升。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利率(NRAS)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时两组国家之间存在持续的巨大差距(尽管小于20世纪80年代)的相对利率。
根据这些依据,上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可以更具体地表示为,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重要的是其自身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如何影响穷人福利?什么农业政策导致了这些结果?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国家去制定他们的国家政策和谈判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
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去解决这个多元化的问题,至少是因为两个政策性原因。其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努力协定多变贸易组织间的多哈谈判,并且农业政策改革再一次成为最受争论的话题之一。其二是更贫穷的国家正奋力在2015年前实现他们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关键是要缓解饥饿与贫困。
这里也有一些原因需要去说明,为什么非要在现在这个时间去更彻底地将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拥有先进的方法并以迅猛的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涉及微观仿真模拟。微观仿真模拟是根据家庭的调查数据,且结合整个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作出的模拟。举个突出的例子:Hertel和Winters(2005,2006)的研究和Bussolo a和da Silva(2008)的研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农村地区正在迅速使他们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已经产生出超过农业土地和农场劳动力能够创造出的财富,包括农场外的兼职工作和汇兑。所以,在对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时,家庭收入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Otsuka和Yamanc 2006,Otsuka,Estudillo和Sawada 2009)。早期在农民收入净额或农业GDP与农户的福利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是呈衰落趋势的,甚至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同样如此(Davis,Winters和Carletto,2009)。通常情况下,很多穷人,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是主粮的净买家,因此至少在短期内通过增加主粮的价格,会导致他们受到不利影响。
第二,与跨国家分析相比,全国住户调查的编制分析发展很快,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调查,现在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该数据集已经开始与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的联动模式相配合,用来评估全球收入分配问题(Bus-solo, De Hoyos和Medvedev, 2008)。
第三,世界银行最近编写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新的全球数据库,可以更新和扩大我们对此的理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激励机制的扭曲这方面。从那些已被作出的估计,能够使他们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模拟(Valen-zuela和Anderson,2008)。他们不同于常用的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贸易模拟,因为它们是根据国内直接到边境的比较价格,而不是与( 与GTAP数据集,Narayanan and Walmsley 2008)进口关税和其他主要边境措施的适用税率相比。
第一次尝试利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数据库,是在最近已经被用来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贫困的相对影响,以及在国内和国外的农业和非农业贸易政策的不平等问题上。本文对此做出了总结,并借鉴了已经出现该研究项目的文件。
在一开始就应明确,在实现国家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的这个目标上,农业和贸易政策向来就与最好的政策工具差得很远,这是国内社会福利和所得税政策措施所持有的特权。然而,假如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与国家贸易有关的政策,会日益恶化特定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则他们又会提供另一个原因,就是处在顶端的一般性国家从贸易中受益,是因为这些国家单方面改革了他们的政策。如果国家贸易政策改革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的缓解效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那就为国家积极参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全球模拟研究揭示出,全球多边贸易改革将会缓解全球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话,它则强调使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DDA)雄心勃勃的改革承诺,迅速地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个消极的结果(例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贸易自由化将提高贫困)是无法成为贸易改革提高福利的原因之一的。相反,这样的结果可以用来提供指导,对那些需要有针对性的纳税证明或社会计划,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这种改革的经济利益(Ravallion,2009)。全球改革的成果,还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议价能力,例如寻求援助换取贸易方面的支付,以减轻因多边商定的贸易改革而导致的可以预计的贫困的任何增加。
本文从大纲的分析框架和通过综合全球和诸多国家的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共同经验方法的两个方面着手,然后将它与之前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政策的影响下,全球和诸多国家模拟中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是根据两项研究,各自使用一个全球性的模拟,在已经确认的许多国家的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来研究农业和非农业价格和贸易政策对全球贫困及其分布的影响。再加上,9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横跨了3个关键的亚洲地区(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那里),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二、 分析框架
为了充分掌握贫困和不平等对价格扭曲政策的影响,必须谨慎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户依赖农业企业为几乎所有的收入,而且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部分国家贫困集中在这样的家庭是巨大的。事实上,最穷的家庭在最贫穷的国家都集中在农业,意味着那些家庭有可能受益于农业生产者价格上涨带来的贸易政策改革,其他条件相等。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因为贫困家庭也把大部分收入花费在主粮上(Cranfield等,2003),所以,如果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改革,那么这个不利影响他们的家庭支出可能会超过抵消有益影响他们取得更高收益。城市贫民也会受到主粮的消费者价格上升的不利影响。然而,它可能是一个贸易改革,上升的食品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熟练工人的需求(根据生产要素的相对强度在经济不断扩张的领域),这取决于劳动力是流动的,可以提高穷人家庭的收入超过提高消费的价格。
目前研究中所采用实施上述理论的方法是一个由Hertel和Winters(2005,2006)开创的变体方法,使用在对未来世贸组织多哈协议的研究中。目前的研究和先前的研究在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第一,重点是国内农业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从其他商品贸易政策的影响来区分;第二,我们检测不平等和贫困;第三,我们关注当前政策的影响,即全部(而不是部分)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而Hertel和Winters的研究主要关注于2005年的多边部分改革提案。这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检测的不仅仅是多变贸易改革,也是个别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的单方面改革。单边行动的影响与国外完全自由化会产生什么进行对比以便能够评估国内的相对重要性。为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有所区别(超过国家通过贸易谈判的间接影响)。全国性的CGE模型可以估计单方面改革对农业或所有商品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以国家性的模型来估计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需要从全球模型输入。世界银行的LINKAGE模型就是以这个目的来选择的。它也被校准到2004年,基于Version7的GTAP全球保护数据库(Narayanan和Walmsley 2008)除了取代它的应用为发展国家的农业税和更全面的一系列国家价格扭曲的估计(Valenzuela和Anderson,2008)。
有多种方式传送来自一个全球CGE模型的结果,如LINKAGE至单一国家的CGE模型,像Hertel和Winters(2006)。我们采用的方法是Horridge和Zhai(2006)开发的。对于进口而言,Horridge和Zhai提出的边界价格变化的使用,是从全局模型对其他世界自由化的模型(即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
所有下面提到的CGE模型是比较静态的,他们假设了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公司和产品市场。在所有情况下除了南非(和一个较小程度上对尼加拉瓜),失业率被认为是不受贸易政策制度影响。这些假设仅仅因为缺乏足够的所选择被建模的国家数据和经验证据来加强。使用的这一组标准的假设降低了各国结果的差异,差异是南不同的假设投资行为或垄断竞争的程度、公司的非均质性、规模经济或总就业对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这一原因造成的风险(Helpman,Itskhoki和Redding,2010)。这样的规格通常导致低谷国家的净复利收益,但是增加了贸易改革(Francois和Martin,2010)。尤其是没有动力学的模型特不会从释放市场或从最终生产率/效率的贸易中产生股息。因为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减少贫闲的主要方式(Ravallion,2006),缺乏动力学意味着这项研究结果几乎肯定低估了潜在的贫困减轻自由化的后果,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显示贫困人口增加,而实际上是减少的。
所有的国家案例研究中,一个全球建模研究调查使用了除了社会核算矩阵(SAM),还利用了家庭调查数据。SAM是CGE模型的数据的基础,家庭调查数据用于微观仿真建模。 通常这些实验是在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在全国实施CGE模型的政策冲击(无论是单方面的自由化还是对边境价格的外生冲击和LINKAGE模型提供的出口需求),这个在国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上产生变化。第二阶段是消费和价格的变化因素传送到微观模拟模型,来观察它们是如何改变各种家庭类型的收益(根据他们来自各种因素的收入的份额)和他们的生活成本(根据在各种消费产品支出的份额)的。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家庭收入信息的分布,诸如在不平等和低于1美元一天的贫困线的人数。
所有国家的案例研究在使用一组公共模拟,以使它能来比较不平等和贫困在每个国家的影响和全球其他地区政策对农业品市场的影响(包括轻度加工食品)相其他商品。其他全球研究称在下一环节中使用相同的2004年全球保护数据集,而实现全球改革冲击对每个15个发展中国家使用稍微不同的全球模型,并附加了全国家庭调查数据以进行微观模拟。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的模拟也在实行,经常来解释国家案例研究中在特定的对相关关键假设的敏感性的结果。
即使这里接受调查的模拟符合完全竞争的所有标准,具有报酬不变规模和比较静态的整个经济体系的CGE模型。但在其特定的设置下,捕捉重要的现实情况(如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或数据的限制)时,他们也有所不同。为了确保它们的可比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符合一组共同要素市场的假设和关闭规则,但是把2004年作为他们的基础平台,并使用相同的一组进行通用模拟这种情况除外。
全球扭曲的数据集。特别是,当所有的建模假设如下:一个固定总存量(包括没有国际流动性)的因素,除了在对尼加拉瓜和南非劳动力的研究中,一些总就业贸易政策的反应是允许的,因为高失业率的基准可能是一些具体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但大多数的资本和劳动的类型是被假定为在一个共同的灵活回报率或工资与部门间移动的。土地被假定为特定的农业部门,移动在该部门不同的作物和牲畜的活动中。被大家默认的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宏观闭合规则,即每个案例的研究都采用一个固定的电流外币账户,以避免考虑是否需要借外债,且稳定政府支出和财政平衡。因此,通过追溯在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和税收上的变化,从而不影响家庭以外的实用程序。财政平衡是从取消部门贸易税和补贴中,通过使用统一税率(一般是直接牧入)取代净亏损收入来实现的。
三、 实证研究结果的概要:全球模型的结果
本节是从两个全局模型(联动,GTAP)0.4总结的结果。
在分析两组被拉到一起的经验教训之前,汇集了来自9个国家情况更详细的研究结果。这将是惊人的,如果所有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同的全球和国家模型的混合强度更容易暴露测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设置比只有单一类型的模型采用的各种决定因素。
(一)联动模型结果
Anderson,Valenzuela和van der Mensbrugghe(2010)使用世界银行全球联动模型(van der Mensbrugghe.2005),以评估全球农业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市场影响,以便于能够讨论国际不平等(Mi-lanovic,2005)。考虑到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有关贫困(使用一个简单的弹性方法),该模型还提供了估计其余的世界政策在进口和出口价格和需求的影响,是下一节中对9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讨论的基础。
联动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2004年农业和贸易政策被全球性地废除,发展中国家将取得近两倍的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平均福利增长0.9%,相比而言,高收入国家为0.5%)。因此,在广泛意义上,世界仅有的两个大国集团,完成全球性改革的进程将减少国际不平等。结果在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厄瓜多尔增长了8%的情况下,一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将受到特别大的不利贸易条件的变化(其主要的出口产品,香蕉,目前在欧盟市场受到严重歧视,那里的前殖民地和最不发达国家享受优惠的免税访问)。
要记住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四分之三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作为他们的主要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农场规模远远的大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联动研究还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回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国际不平等。 我们发现如果这些政策被废除,发展中国家的净农业收入将上升5.6%,非农业产值增加1.9%。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中会下降,但印度例外。印度大量减少农业GDP,这在高收入国家里,部分反映了在印度进口竞争型农民目前在边境享受相当客观的保护。在高收入国家酌净农业收入平均水平将下降15%,相比而言真正的非农业增值略有上升。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国内的措施来补偿,在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将会增加,特别是在印度。他们还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和高收入国家的农户之间将大幅减少不平等。如果只有农业政策被废除,与非农业贸易政策相比,这些不平等的结果将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强调了农业巨大的扭曲。
该研究报告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其中大部分在农场工作,将从改革中受益(其次是熟练工人,然后是资本所有者),在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下降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水平上升3.5%。然而,最相关的消费价格对于穷人,包括许多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劳动的贫困农民及其他农村家庭收入,是食品的净购买者,主要是为了食物和衣服。因此,降低食品和服装价格指数比总体CPI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指标来反映这些工人的福利变化。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将会增长5.9%。即在发展中国家非熟练的工薪阶层和富裕得多的资本所有者(人或物理)之间的不平等将减少。
上述净农场收入的结果表明,贫困以及国际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以全球性减轻农业和贸易政策白由化。这项研究更进一步来明确地评估改革对贫困的影响,即使联动模型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单一的代表家庭。他们这样是使用弹性的方法,包括估计真正的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应用一个估计收入贫困弹性去评估贫困人数指数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他们专注于改变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并假设在贸易改革后那些工人免于直接所得税征收来取代失去的关税收入(一个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假设)。
在完整的商品贸易改革方案中,极端贫困的人口(依靠一天不足1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将下降2 600万,相对于不到10亿的基线水平下降了2.7%。减少的比例远高于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了约4%,甚至在拉丁美洲和南亚更高(除印度外),分别下降7%和10%。相比之下,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印度(虽然不是在其他南亚)预计上涨4%。更为温和定义之下的贫穷——那些生活在不超过2美元每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数将下降近9 000万,比2004年的聚合基线水平的略低25亿,或3.4%(尽管在印度每天低于2美元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只有1.7%)。
(二)GTAP模型结果
Hertel and Keeney(2010)利用广泛使用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的全球整体经济模型。他们的研究像其他研究调查一样采用相同的价格扭曲,运行相同的场景,但对多边贸易改革的场景从GTAP模型生成自己的世界价格变化。这些价格变化在GTAP模型改变边境的各个国家的价袼,其中一个子集附加的详细家庭调查数据。这允许作者讨论关于贫困的影响在一系列不同的经济体使用一种内在一致的框架,来抓住所有的收入变化因素的分配影响。这个多国研究关注了15个发展中国家:5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4个非洲国家(马拉维、莫桑比克、乌干达和赞比亚)和6个拉美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总的来说,得出的结论是废除当前全球农业和贸易政策会减少贫闲,主要是通过农业改革。这15个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数的未加权平均数下降每天1美元)了1.7%。亚洲子样本的平均下降是其两倍,然而——这就是在亚洲,是几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极度贫穷人生活的地方(虽然样品不包括中国和印度)。把其结果转为特定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的示例,即智利、泰国和越南这些扶贫最会发生的地方。15个国家的大多数贫困人口从非农业改革中增加学习经验,虽然未加权平均数在15个国家表现出了一个轻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越南大幅下降。这些GTAP模型结果接近于本论文第一部分中的关联模型的结果。
作者详细地探讨了农业贸易改革,鉴别影响实际税后农业与非农业改革收益因素。他们的分祈扩展到通过观察分配的家庭地层特定贫困的变化。他们发现更多农业改革的有利影响是由于农民劳动力增加的回报以及非技术性农民工更高的回报。他们还发现,粮食市场的自由化代表着对减贫的最大贡献,并且那些大宗商品市场上取消进口关税,主导着高收入国家取消补贴的增加贫困的影响。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全国贫困人数的百分比变化,当贫困不再受制于贸易改革后所得税上升所替代的贸易税收收入。这个假设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隐式的由非贫困向贫困家庭转变,并从而产生了扶贫预测的明显变化。贸易改革要想略微减少贫困中的15个案例中的大多数在减少贫困的所有情况下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它减少了泰国和越南大约四分之一的贫困比率。总体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当贫困也被认为要征收所得税以代替失去的贸易税收时,区域和扶贫的总平均程度是四倍多。三个地区的未加权的平均贫困人数的下降所示是符合联动模型人口加权平均值,前面类似的代替税的假设,亚洲(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后来的30%和拉丁美洲的6.8%均高于GTAP模型的14%和5.7%,而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8%仅仅低于Hertel和Keeney样品的4.5%。
四、 系统实证结果的概要:国家模型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看看与全球模型的结果相比9个更详细的国家的案例研究结果。类似于两个全球的模型,他们着眼于2004年的价格扭曲的政策,印使他们的CGE模型和他们的家庭调查数据的数据库通常可以追溯到10年前,包括家庭和劳动类型。所有的国家研究结果包括对模型的微观模拟图,如上述的GTAP全球模型。
实际GDP和家庭消费的国家结果表明了GDP将从全球贸易改革中增加,但在所有9个国家中只增加了1%或2%。在消费品价格下降的条件下,真正的家庭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会增加的非常明显。一般来说,这些数字是略大于全球LINKAGE模型所产生的数据。他们共享全球模型的功能可能低估了贫困缓解贸易改革的好处,考虑到广泛共识的文献,贸易自由化促进增长这成为了扶贫的一个主要贡献。
不应该期望的是,Hertel和Keeney(2010年)所产生的各地区的贫穷的未加权平均数的结果是相似的,因为Hertel和Keeney在15个国家中只取了5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为样本。在所有12个中除了3个之外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比较(农业、非农业和所有商品),中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在现有的国家案例研究样本中预计的地区平均贫困减少水平要比Hertel和Keeney的15个国家的样本要大。
至于个别国家的结果,除了菲律宾,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困都由于全球农业和非农业自由化而减少了,当所有的商品贸易自由化时,减少的程度范围会从接近于零变为约3.5%个百分点,除了巴基斯坦是6%以上。平均而言,近三分之二的减少是由于非农业贸易改革,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巴西,那里的农业改革是其大型扶贫作了主要贡献。后者的结果是,尽管巴西的贫困进口竞争型农民的关税保护的存在和自由化后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增加,这显然超过了废除农产品关税的贫困影响。一个国家为贫困减少做出的改革的贡献似乎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同样重要,虽然对于农业和非农业改革都有相当大的分歧。
研究结果显示,在3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所有商品的贸易自由化之后不平等会下降,或只是农产品的不平等会下降。在本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改革中,非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则比较复杂,这是敦促贸易谈判中不能忽视农业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全球其他地区和全球农业改革都导致样本中除了泰国以外的每个国家的不平等减少(加上菲律宾轻微的全球改革),而单方面的农业改革减少(或保持在一个常数上)一小些国家包括中国的不平等,菲律宾和泰国例外(但后者的影响小)。非农业的全球改革略微增加3个国家的不平等。在印度尼西亚不平等的非农业改革影响的增加超过了农业贸易改革的平等效应的抵消,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菲律宾和泰国会增加不平等的程度。
几个国家的研究调查改革的影响,可以来补充贸易改革,最明显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消除贸易税收收入。如果这些收入可通过税收收回,不用让穷人承担,那么对减少贫困改革的影响会更有利。中国的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减少迁移出农业壁垒,通过改善土地市场运作和减少户籍制度的流动壁垒。这些措施,以及为增加中国市场准人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被采用于减少贫困,例如这些措施综合运用会有利于所有主要的家庭群体。
五、 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不管是基于计量经济学(如2007年的Harrison)的事后或事前的经济范围内的模拟(如在2006年Hertel和Winters),本研究仍然得出那些复杂的难以总结的结果,特别是当要衡量到贫困带来的影响的时候。然而,仍有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最重要的标志可以去衡量,就是用开放所有国家的商品贸易这种手段,去考察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的影响。在总结以上的研究时,发现这种情况导致的影响存在着重叠的部分,即在所有已显示的32个例子中,有2个例子一致指出,其带来的结果是整个全球贸易改革将会减少贫困。
贸易交易完全自由化对世界贫困的有益影响相对于非农业改革来说,将更多来自农业改革;并且,在农业方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更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移除对农民的大量支持。根据目前研究中使用的经济模型,这些改革将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益,这些工人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收入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收入有密切关系。除了减少贫穷,这也将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根据Linkage的模型显示,随着全球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极度贫穷(日消费水平低于1美元)人数下降了2.7%。其中,中国和非洲撒哈拉地区更是下降了4%,但是在印度却增长了4%(或者是在每天2美元的标准下增长了1.7%)。
GTAP模型通过对15个国家的研究得出结论,贫困下降率要比预计中的更大,其中9个国家的案例表明,不论只是对农业产品还是所有商品的改革,自由贸易都有效地减少了贫困,其中收益粗略等于家庭和国外的改革。之后的研究还表明,在所有的案例中,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改革,亦或是否包括非农业产品,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下降率要远超过城市。
根据LINKAGE模型,全球贸易开放将会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总收入和每户收入的差距。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更富裕,除非改革促使一个经济飞跃(这些研究使用的不是捕获的比较静态建模)。
全部商品的自由市场贸易,或者只是农产品,同样也会导致样本中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及国外的改革下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在城市和农村的地产拥有量不会因为贸易的改革产生太大改变,但贸易改革会显著缩减城市农村的贫富差距。
政府在税收的途径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GTAP模型,假设(事实上)穷人不在享有免受贸易税而是按照比例征收,那么在被调查的15个国家中,贫困指数将会比现在提高四倍。
两位顶尖分析专家认为,相对于非农业贸易的改革,去除所保留的农业政策会对消除贫穷有更强的作用。9个地区案例分析的加权平均结果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国家间的数据还具有一定的离散程度,但这9个案例同样也表明国内改革与外部改革有一定的相关性,国内自身的改革降低贫穷率等于外部的平均数。
六、 注意事项
农业和其他贸易改革的影响是复杂的,同时影响了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政府预算和对外贸易。本次经过调查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事前建模的观点,包括全球和各个国家的模拟。通过使用最新的微观模拟和贫困弹性的方法,已经有相当多的关注目光投放在了捕捉对贫困的影响上。而使用相同的价格进行失真估计和使用相同的全球模拟,则是为得到其余的世界边境的9个国家的模拟冲击、类似的行为假设、税务更换的假设和封闭模拟。然而,仍然有足够的范围,可以通过额外的比较,去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深入到每个模拟结果,探讨其起源的形式。
这里考虑的改革仅指商品贸易自由化。而开放全球服务贸易也有可能给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带来收益,包括这些国家的农民也同样会受益(Francois andHoekman 2010)。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无疑也会增加这些收益(Hoxha,Kalemli-Ozcan and Vollrath 2009),其道理就如同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Walmsley and Winters 2005;World Bank 2005)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一样。而这些改革将如何同农场和其他货物贸易改革相互作用,又会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状产生怎样的影响,注定是复杂的,所以期待着更加复杂的全球模拟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个主要挑战依旧是把握自由化带来的持续影响,特别是它们导致的一般均衡分配(贫困和不平等)的后果。实证文献中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最近才开始着手解决,并且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现有的局部均衡分析里强烈指出,贸易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比当前的研究中捕捉重新分配的静态影响更加重要。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一旦放到动态模拟中,他们将会加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里,关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改革是贫困和不平等减少现象的源头部分。
另一个更深入的模拟改变是引入随机尺寸的大小,从而去获得陷入贫困概率的变化情况。如果扩大开放程度则会增加粮食价格暴涨的风险:一个上涨的尖峰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的粮食短缺,甚至饿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均衡的实证模拟,它都包含足够的部门和家庭的细节,即使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并且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是可以对贫困状况分析有所帮助的。然而,这一领域发展迅速的深层次原因是为了响应早期的原型Ahmed,Diffenbaugh和Hertel(2009),满足对气候变化研究的需求。
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去探索伴随着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改革产生的辅助性国内改革,在经验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伴随着贸易改革的扶贫,那么效果将会扩大几倍。由Zbai和Hertel(2010)在中国的案例研究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印度这个国家,后者的改革可能依旧不会加剧贫困。假如更高效的传输机制被放在高回报的基础设施投资中,那么将会得到逐步淘汰的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即便是政治策略里最好的国内政策,也不一定有比任何与贸易相联系的政策更为复杂,然而,它着重强调有必要进行不限制其重点边境政策措施的全面的政治经济分析。
七、 对政策的影响
以上的实验结果对政策有一系列的影响。首先最为关键的,无论单边还是多边的贸易政策改革,其对缓解贫困和不平等都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国家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其次,在各国案例分析中常常出现的主题是,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总体实际收益的基础上,缓解贫困与不平等所带来的益处往往在全球贸易改革中比本国的改革中更为显著。例如,在印尼的案例中,单边贸易开放对缓解贫困起到的作用很小,但全世界的开放则会明显地减少贫困。菲律宾对现阶段的国内保护所进行的改革可能会使贫困率略微上升,而国外的开放几乎能完全抵消掉这种影响。
第三点,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证明,贸易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和最为贫困的个人。不过也很明显,一些极端贫穷的国家与个人也可能失利。所以,补偿政策具有优势,最理想的是重视公有而非私有财产,以保障对于促进增长的因素的投资,比如农业人力资源。
第四点,尽管包含政治敏感,最大的益处来自于农业改革,并强调保证此领域改革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确实有比贸易政策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政府的贫困与饥饿“千年发展目标”,但这些手段都是对国库财政的巨大消耗,尤其是对于高度依赖贸易税收的低收入国家政府。一种解决方法是扩大贸易援助,作为正式发展扶助计划的一部分。
最后,基于对各国国内改革研究的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其他国际磋商的过程中无需减缓国内改革的步伐。并且,从减轻贫困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协商豁免权或因为在WTO多边协议框架内的改革的延误,承受较大损失。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编译者:林海 张海森)
营养、千年发展目标与食品价格变化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 概 要
即便食品价格的上涨是暂时性的,也会对儿童的长期发育造成危害。生命早期(从胚胎形成到2岁之前)的发育水平将是成年期体质的基础。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和认知水平受损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终其一生也无法弥补。
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食品价格的些许波动就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食品价格危机最严重的影响表现在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低收入国家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其他无法弥补的损失包括发育迟缓(个头矮小或体重不足)、学习能力低下等。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成人之后也更容易罹患如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此外,危机会轻易地夺走他们在经济繁盛时期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
高昂的食品价格对最脆弱的人群的影响,首当其冲地表现在营养不良。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更高,面对价格上涨也更加脆弱。家庭内部的分配机制加上家庭成员不同的身体状况(生物脆弱性),意味着孕妇和儿童面临着更高的风险。而死亡率和退学率等指标,也表明女童比男童更加脆弱。
除了抑制价格上涨之外,还有许多措施能够增强个体及其家庭的应对能力,消除长期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干预措施的重点应该是通过现金转移、食品和营养项目、以工代赈等方式维持家庭的购买力、卡路里①和微量营养物质的摄入量。要确保针对儿童和妇女的干预效果最大化,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妇女经手转移物资。而在长期内,干预措施的重点应该是增强小农农业与营养获取之间的联系,解决季节性饥馑问题,提高妇女收入,改善女童的教育状况。 具体的干预措施应当通过改变行为方式来瞄准脆弱儿童,例如母乳喂养、病童喂养、卫生、微量营养元素、驱虫(以促进微量营养元素的摄取)、设计针对疾病的预防和食疗性食谱等。最后,各国政府在消除食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能够实施的措施包括:应当改善营养监控数据(各年龄段的身高、体重和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质量、推动新的行为方式(母乳喂养)并加以干预;扩大营养干预项目的范围;针对各国实际,与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一道设计可行的干预措施,来应对营养安全问题;以营养敏感的路径来推行跨部门项目(社会保障、健康、农业与增收项目等)。
二、 食品价格飙升如何影响MDG
高昂的食品价格会阻碍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影响个体的食品消费、营养摄入、社会服务获取以及对婴幼儿的照料等;从而导致儿童(学习能力下降、存活率下降)、成年妇女(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影响胎儿发育和未来成就)和成年男性(影响他们的生产能力)的营养不良率上升。此外,营养不良还会影响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治疗效果。专栏1总结了食品价格危机和营养不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据Grantham-McGregor等(2007)的保守估计,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2亿人面临着贫困、健康不佳和营养不良等风险,其家庭也不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导致无法达到应有的认知发育水平。儿童救助会(2011)预测,最近的食品价格飙升使40万儿童的生存堪忧。
三、 食品价格如何影响营养
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食品安全是改善营养状况的重要投入,拥有一定的身体能力和经济能力以社会和文化可接受的方式获取足质、足量的食品。而营养安全是描述健康状态的产出,即健康的环境、必要的照料和家庭的食品安全(世界银行,2006)。例如,一个母亲也许能够获得健康的食品,但是由于身体不好、照料不周、知识缺乏、性别偏好或是个人喜好等原因,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去关注食品营养,最终导致食品不安全。而只有家庭全部成员都拥有安全的食品获取、卫生的环境条件、充分的健康服务和必要的知识水平,才能实现营养安全。一个食品安全的家庭或一个国家)的部分(或大多数)成员有可能是营养不安全的。
因此,食品安全是营养安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虽然家庭决策可能会影响其成员的营养状况,政府资助和政策条件才是家庭行为的决定性因素(IFAD,WFP和FAO,2011)。 营养安全是个多维度的概念。在某一国家改善营养状况,要求贸易、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市场等营养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而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等社会部门也需要参与其中(Ecker,Breisinger和Pauw,2011)。在食品价格危机等经济震荡面前,家庭行为与政府行为都将有所改变。
(一)家庭与个体层面的影响
l.影响膳食质量与食品数量
随着价格上涨,家庭会首先放弃昂贵的食物,用廉价食品来满足卡路里的摄入,或者选择残次食品。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这种替代方案也不再现实,只能降低卡路里的摄入量。在第一次调整期间,贫困家庭会放弃肉、鱼、蔬菜和水果,靠谷物和根茎等主食充饥,蛋白质和微量营养元素的摄人无法保障。而幼童(从胚胎期到婴儿期)对铁、维生素A、锌等营养物质的需求很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遭受“隐性饥饿”的长期影响。而在第二次调整时,家庭的卡路里消费会降低,例如巴基斯坦的城市家庭(Friedman,Hong和Hou,2011)以及海地的贫困家庭(世界银行,2010b)。此外,体重不足的儿童数量也会增加。Gibson和Kim(2011)在越南发现,大米相对价格升高10%,卡路里摄入量减少约2%。然而,如果贫困家庭不能及时用低质量大米来取代越南家庭通常会通过降低食品质量来维持卡路里摄人量)的话,这一比例将会超过4%。
在城市地区,贫困人口主要靠街头食品维持生活。在加纳的阿克拉和拉丁美洲地区,街头食品占城市贫困人口食品支出的将近40%(Ruel,2000)。因此,食品价格升高就意味着街头食品消费增加,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食用油和淀粉。这种膳食结构具有高能量(富含卡路里)、低营养的特点.加剧了城市地区本就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例如墨西哥(CONEVAL,2009)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1).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营养问题也正在从营养不良转向营养过剩。
2. 妇女儿童劳动负担增加
妇女的劳动增加会对家庭的收入和购买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也可能会改变儿童照料的安排。母亲劳动量增加对子女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子女的年龄、家庭可替代资源,以及负责子女看护和喂养的家庭成员所具备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危地马拉城和阿克拉的城市贫困社区的母亲们能够同时承担养育子女和获取收入两项主要职责(Levin等,1999;Ruel等.1999,2002)。然而一旦发生危机,妇女的工作压力增加(补充家庭收入的不足),用于看护子女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女童死亡率也就随之升高,印度农村就是一例(Bhalotra,2010)(农村家庭中的文盲或第一个子女已经长到十几岁的母亲们更易发生这种情况)。因此,针对子女照料和孕期需求的干预措施(例如印度在临时居所附近修建的托儿所)将有助于改善儿童福祉。
食品价格上涨对儿童劳动量的影响尚不明朗。如果家庭无法负担教育费用,儿童可能会被迫参加生产性农业劳动。而退学儿童在危机过后也不太可能返回校园,即便能够重拾书本,学习成绩也将受到影响。此外,儿童的收入也会成为家庭维持卡路里摄入的重要来源。然而,价格危机通常也伴随着就业危机,例如在2008年的欧洲和中亚,或是1988-1992年间的秘鲁,在这样的条件下,儿童的劳动参与并未增加。
3. 家庭照料减少和健康服务缺失将会危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影响其营养水平
如果家庭不能承担医疗健康开支,家中的成人和儿童的健康状况都会受到影响。而健康水平恶化又会降低新陈代谢、造成吸收和消化不良、影响胃口、中断母乳喂养,最终影响营养状况。一些流行病如急性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等,也会阻碍小肠对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的吸收,而缺乏维生素A又会破坏免疫系统,使儿童更易患病,形成恶性循环。家庭对儿童的喂养方式变化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由于腹泻而降低液体食品的摄入,只会适得其反。
穷人首当其冲遭受初级保健和社区基础的营养干预资金减少的影响(Al-derman,2011b)。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美的经济危机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削减,赤贫的人受到的冲击最为显著(Musgrove,1987)。Ferreira和Schady(2009)对比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案例,再次证明了在危机中关键性的健康服务供给对儿童营养不良预防的重要性。在秘鲁,公共医疗支出在危机中减少了60%多,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也急剧下降(例如生育率升高,但孕检率却在下降)。婴儿死亡率从1988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7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尼西亚,援助规模的增加弥补了政府开支的不足,婴儿死亡率虽然从1996年的30‰上升到了1998年的48‰,但是诸如儿童消瘦、发育迟缓、贫血等营养方面指标却没有恶化。
4. 家庭内再分配和照料安排能够缓减或加剧食品价格上涨对特定家庭成员的影响
妇女通常通过降低自己的食品消费来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食物,从而成为“家庭食品不安全的重要缓冲器”(Quisumbing,Meinzen-Dick和Bassett,2008)。美国和加拿大的农村贫困妇女(Mclntyrc等,2003)在经历食品不安全时会降低或改变自己的膳食摄取来保障子女的需要(特别是能量、维生素A、叶酸、锌、钙和铁)。而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和赞比亚的一些社区(Holmes,Jones和Marsden,2009),当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时,家庭会首先保障儿童的营养;在另一些社区,男人的营养则最为重要。然而,没有一个社区会为妇女提供最有营养的食品,妇女(包括孕妇)的需求总是被忽视。在印度尼西亚,母亲们在1997-1998年间的危机中保障了子女的卡路里摄取,与之相伴的却是孕产妇的营养不良和贫血(Block等,2004)。
妇女缺乏教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也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和照料不周。在南亚,儿童喂养方式不当使得营养不良率高发,其中女童尤甚。在许多国家,母亲们无法进行6个月的母乳喂养,而替代食品通常缺乏能量和重要的微量元素。负责儿童照料的祖父母或年长的其他子女在知识储备方面可能更为缺乏。在1970-1995年,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儿童营养不良的减少贡献率超过了50%(Quisumbing等,2000)。而周到的儿童照料能够缓减贫困和母亲的儿童营养知识缺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Armar Klemesu等,2000)。
5. 单纯增收远远不够
即使是食品安全的家庭,营养不良率仍然有可能较高。例如,在巴基斯坦,假如收入水平最低的40%的家庭与收入水平居中(即中间20%)的家庭具有同样的营养特征,贫困问题也许得以解决,但仍有38%的儿童营养不良。在埃塞俄比亚,最为富有的20%的家庭中,也仍有40%的儿童发育迟缓,而且这种现象随处可见(Haddad等,2003),这就促使干预措施要超越宽泛的减贫目标,瞄准特定的营养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所述,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
●孕妇摄取的卡路里和蛋白质不足,加上孕妇携带的性传播疾病等感染没能得到医治,导致新生儿重量不足。
●母亲们没有时间照料年幼子女,也无暇顾及自身。
●新生儿的母亲们没有保留初乳,错失了增强婴儿免疫系统的最佳时机。
●母亲们很少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进行母乳喂养,而母乳是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能够抵御许多感染。
●给婴儿喂食同体食品的时间过晚。2岁以下的婴儿获得的食品太少,食品中的能量也不足。
●虽然家庭的食品充足,但是家庭内部的分配方式可能导致妇女和幼儿的能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她们的膳食中微量元素和蛋白质含量不足。
●在儿童感染腹泻或高烧时,没有进行正确的喂食。
●看护者卫生状况不佳,其携带的病毒和寄生虫可能会污染食品。
专栏2就孟加拉在2007-2008年食品价格危机期间的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个体劳动参与、家庭内部分配模式、服务获取渠道和其他应对机制等进行了总结。
(二)国家层面的影响增加食品购买和补贴支出能够促使资源(从其他部门)流向健康和教育部门。由于营养不良通常与可预防疾病(例如腹泻)和缺乏营养知识(例如婴幼儿的最佳喂养方式)密切相关,健康和教育可以说是影响一个国家营养水平的核心部门。在食品价格上涨时,许多政府通过扩展(或设立)食品补贴项目来缓减经济困境。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此类项目的比例占GDP的5%~7%,然而,这些项目投入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其他投资。此外,价格补贴通常只针对微量元素含量较低的食品,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可能会对危机之后人们的膳食结构多元化调整造成消极影响。例如,摩洛哥的面粉补贴为加工部门提供了支持(世界银行,2005)。对基础设施硬件特别是道路的投资没有被看作是改善营养状况的重要投入,却对食品供应链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能够连接食品消费者和生产者,也能够为贫困家庭提供获得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的渠道。 经济增长显然能够贡献于减贫,但收入增加与营养获取之间的联系却并不显著(Ecker,Breisinger和Pauw,2011;Headey,2011)。农村的营养不良率(以体重不足测量)的下降速度仅是GNP增速的大约一半(Alderman,2011a) --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在印度是28%,中国是67%,孟加拉是76%。然而,Deaton(2010)发现印度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在1997-2007年有所下降,而同期的人均收入和消费都在持续增长。卡路里摄入量的下降可能与体力劳动减少(例如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减少)或发病率降低有关,但仍需进一步探讨。
(三)危机与生物学相互作用
1. 短期震荡,长期影响
食品危机最严重的生物学影响在于婴儿死亡率,特别是女婴死亡率的上升,在低收入国家尤其严重。Baird,Friedman和Schady (2011)最近的研究表明,人均GDP下降和0~1岁婴儿死亡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该研究分析了来自59个人口与健康调查的1 700万新生儿数据,揭示了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的新生儿死亡率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明显,再次说明在危机面前贫困人口首当其冲地遭受其害。此外,女婴死亡率对收入波动更加敏感。在另一个同样类型的调查中,Friedman和Shady(2009)发现,2008年的危机可能导致200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婴儿死亡人数增加了大约35 000~50 000名,几乎全是女婴。
解决婴幼儿死亡问题,将会惠及整个国家的增长。除道德论战之外,Bal-dacci等(2004)和儿童救助会(2008)发现,婴儿存活率每增加5%,该国未来十年中的年经济增速会提高0.85%~1.0%。
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危机对营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会影响儿童的早期发育,从而影响他们的人生际遇。营养不良、健康和学习三个因素共同导致儿童发育迟缓,而这种不利局面终其一生也难以改变。例如,确保儿童不退学比促使退学儿童复学要容易得多。危机发生的时机也十分重要,从胚胎形成到儿童2岁之前是身体和认知能力发育的关键时期,更容易遭受风险。这一时期的营养缺乏会导致无法弥补的生长迟缓和社会认知发育不足(Victora等,2008)。在生命的开始阶段所承受的压力(如照料不周,反复致贫和返贫等)对成年时期的工资水平和生产能力都有长期的影响。
2. 经济低迷时期的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繁盛时期的人力资本增加不成正比
《全球监测报告2010》指出,经济衰退时期人类发展指标的恶化程度远甚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些指标的改善程度。例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预期寿命可能会降低6.5年,而经济发展时期预期寿命则仅会提高2年。同样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是经济飞腾时期婴儿死亡率下降的3倍(分别是24‰和8‰),经济危机导致的小学教育完成率下降是经济飞腾时期小学教育完成率增加的6倍(分别是25‰和4‰)。在婴儿死亡案例中,1/3是由于营养不良。此外,营养不良还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缋。
经济倒退对女童的影响远甚于男童。在危机中,女童的预期寿命降低了7年,而男童的预期寿命则降低了6年(在经济繁荣时期,男童和女童的预期寿命都仅增加2年)。女童和男童的小学教育完成率分别降低了29%和22%。在经济复苏之后,则将分别升高5%和3%。在经济低迷时,入学率的男女比例将会显著升高,而中学和高校的退学率将高于小学退学率。
3. 大规模的严重危机导致新生儿体重不足、个体消瘦和发育迟缓
阿根廷在1999-2002年的危机期间,新生儿体重不足率低出生体重对与GDP的弹性系数是-0.25‰(Cruces,Gluzmann和Lopez Calva,2010)。而严重的突发打击也会导致发育迟缓率的增加,例如1994-1995年津巴布韦的干旱(Hoddinott和Kinsey,2001),1995-1996年埃塞俄比亚的作物减产(Yamano,Alderman和Christiansen,2003)和1988-1992年秘鲁的大规模经济萎缩,等等。
4. 一般性危机的影响因人而异
一般性危机产生的影响包括体重不足、贫血和健康服务的剥夺等。在喀麦隆,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府结构调整项目导致3岁以下儿童的体重不足率从1991年的16%升高到了1998年的23%(Pongou,Salomon和Ezzati,2006)。经济低迷和健康服务缺失使得城市社区的营养不良现象恶化。而在农村地区,营养不良率也有所升高,以贫困家庭教育水平较低的母亲所养育的婴幼儿为甚。然而,服务缺失究竟是由于支付能力降低还是服务供给不足,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爪哇中部在1997-1998年遭受了旱灾和金融危机,导致当地人口的含铁血红素浓度均值下降了6.1%,贫血率增加,严重影响到了新生儿和胚胎的健康(Waters,Saadah和Pradhan,2003)。也就是说,缺少绿叶蔬菜、禽蛋和食用油的摄人所导致的孕产妇营养不良,有着更具风险性的母婴传播渠道。
5. 把握时机:从胚胎形成到24月龄期间的风险与机遇
生命早期发育水平对成年之后的人力资本有重要的影响,涉及身高、技能(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和能力(例如身体素质和社会交际)(Victora等,2008; Friedman和Sturdy,2011)等方方面面。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期从在子宫里的前几周就开始了,直到2岁之前。早期认知能力、感官运动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发育,将会影响儿童的学前教育和学校表现。这一时期也是身体发育的最佳时期:在胚胎时期身高将增加50厘米,1岁之前增加24厘米,2岁之前再增加12厘米,随后生长速度将会减慢,直至青年时期停止生长。如图1所示,不同地区儿童与健康的参照组相比,其发育差距在24月龄之后不会变化。
影响低收入围家儿童发育的因素包括宫内生长不足(11%的新生儿)、发育迟缓(大约1/3的5岁以下儿童)、缺铁(1/4到1/3的4岁以下儿童)、缺碘(世界总人口的1/3)、产后抑郁(1/6的产妇)和认知刺激不足(Friedman和Sturdy,2011)。缺铁会导致胚胎和婴幼儿发育迟缓、认知能力欠缺,成人体力不足、效率低下,以及产妇死亡。维生素A缺乏会引起眼盲症并加剧传染,严重时导致死亡。缺锌会引起发育迟缓,腹泻和肺炎高发。缺碘会影响认知能力和智商水平。营养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摄入不充分,都会降低家庭收入,削弱国家资源;而对产妇和婴幼儿的照料不周则会导致新生儿体重不足、儿童消瘦和发育迟缓等症状的高发,继而对儿童发育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资料来源:Victora等,2010。
资料来源:Victora等,2010。
6.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相互交织:儿童时期营养不良可能导致成人时期过度肥胖
胚胎发育状况会影响长期的健康水平,而在胚胎期和婴幼儿时期营养不良的儿童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更高,例如2型糖尿病、腹部肥胖、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等。例如,在1944-1945年饥荒期间受孕的荷兰儿童在其中年时期表现出更高的患慢性病的风险,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能力低下等症状(Alderman,2011a)。在印度,婴儿时期瘦弱随后却发育迅速的儿童患糖尿病的比例更高(专栏3),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营养不良儿童和糖尿病患者。许多拉美国家也面临着曾经历营养不良的成人的超重和肥胖问题,同时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也居高不下(图2)。营养问题正在从营养不良向营养过剩转变,而营养不良的儿童未来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更高。由于缺乏营养知识和微量元素的摄取,儿童的长期发育仍然不容乐观。
在食品价格升高的时候,营养不良与慢性病的风险都会升高,肥胖症和营养不良现象可能会同时出现于某一家庭或某一个体。如上文所述,贫困家庭放弃有营养的食品,转而购买“无营养卡路里”食品,以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为例(Robles和Torero,2010)。加上新陈代谢的变化,这些“无营养卡路里”就会在中等收入国家引发发育迟缓和贫血现象,同时也催生超重和肥胖等后果。在埃及、秘鲁和墨西哥,大约一半的贫血妇女都超重甚至肥胖。
胎儿期发育对成人期的影响可能与胎儿对子宫压力的调整性适应有关。如果胚胎只能获取有限的营养物质,胎儿就会进行自我调整,以有效地储备资源。然而,当个体随后进人到资源富裕的环境,这种调整方式就会导致营养过剩,个体患慢性病的风险也随之加剧。母亲所患的高血糖、糖尿病等病症会加剧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从而可能威胁到下一代的健康(Delisle.2008)。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儿童发育、营养不良和体重指数(BMI)的全球数据库。
危机可能是暂时性的,但危机对幼儿的影响则不然,如果不加以干预,这种影响会持续终生。厄瓜多尔1998-2000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出生的贫困儿童到2005年时(当他们5~7岁时)表现出发育迟缓加剧、识字能力低下(测量认知水平发展)等特征(Hidrobo,2011)。这一发现表明他们获得了有限的看护,他们的家庭也没能保护他们免遭(因厄尔尼诺引发的)环境健康恶化和公共服务削减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村家庭和城镇中能够获得医疗服务的家庭遭受的影响较小,其子女的身高发育正常,但识字能力同样不容乐观。
如果加以干预,营养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塞内加尔的全国营养项目以社区为基础的路径开展了“千日计划”,实施了系统的营养监测,并交南非政府组织网络来执行(Alderman等,2008)。几年之后,该项目增加了蚊帐的发放,加强了对极端营养不良现象和食品营养添加的社区监管,并在最近推行了现金转移支付。孕妇照料的比例从1/3上升到2/3,6个月以内的新生婴儿母乳喂养率提高到58%,正确使用蚊帐的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59%。2005年的儿童发育迟缓率和体重不足率分别下降到1990年水平的59%和65%。
儿童时期经历过多(极端事件如干旱、内战、饥荒等,以及一般性事件与降水量减少等)将对成年生活产生长期的持续影响。经历过中国1959-1962年大饥荒的人口具有文盲率高、就业困难和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等特征。而经历过希腊1941年底到1942年初大饥荒的人口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而那些正处在生命早期阶段的儿童遭受的影响更为显著。经历过饥馑的儿童一般识字率低,进入中学和技术学校的比例有限,职业成就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一般性事件,例如出生时降水量减少等,也会影响儿童发育,导致儿童发病率升高(如印度),甚至影响他们成年之后的身高和学习成就等(如印度尼西亚)(Maccini和Yang,2009)。很显然,一切都是营养问题。在生命早期(6月龄起)阶段的母乳替代品至关重要。
身高是测量人力资本的最佳指标,而营养不良会直接危害人力资本。发育迟缓的儿童在学校表现不佳(其得分之低,相当于缺失了两年的学校教育)。以每1年的学校教育会增加9%的成人期年收入计算,Grantham-McGregor等(2007)认为这些儿童成人期的年收入将会损失22%~30%。在危地马拉进行的长期的历时研究(Hoddinott等,2011)表明,营养不良的长期影响不仅表现在体型和健康方面,也将在就业类型和职业工资等方面有所体现(专栏4)。发育不良的长期影响十分严峻,应该采取营养补充、早期基本医疗服务等干预措施,改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产出。
四、 增强恢复力:以干预手段缓减食品危机的影响
食品危机在发展中国家时有发生,而针对营养不良现象的干预措施能够缓减食品危机的影响。食品危机对家庭和个体福利多元化的影响路径也为干预提供了不同的切人点。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些切入点及与之相应的成本:消费与社会保障;生物与健康;生产与创收。干预措施当然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能力水平和所面临的特定问题而因地制宜,然而就其目标实现则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世界银行,2012)。
(一)消费与社会安全网
在食品价格升高时,食品生产体系就会相应地进行调整。一些社会安全网项目试图维持短期的消费支出,特别瞄准更加脆弱的人群。这些干预手段能够产生长期影响并且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动的保障食品安全措施产生对接。这些措施有:短期的转移支付、救灾和保障消费以及针对食品产出增加进行长期投资。
1. 现金转移支付
通过向特定群体进行现金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消费,应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措施之一。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如Fiszein和Schady,2009)。Fernald、Gertler和Neufeld (2008)认为,墨西哥的“机会”项目能够对儿童身高产生积极的影响,Attanasio等(2005)对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计划,以及Ferrreira等(2011)对巴西的现金转移支付的研究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Macours、Schady和Vakis(2008)对尼加拉瓜一个旨在应对如干旱、风暴和极端贫困等危机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试点项目对营养和儿童早期发育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该项目要求学龄儿童入学,而学前儿童则必须进行防疫体检。家长们能够获取有关营养和食品选择的相关信息。试点项目对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技巧(社交能力、人格发展和识字水平)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该项目促使家庭的支出更多地倾向于多元化的膳食、为幼儿提供更有营养的食品,以及书报等更有意义的物品。此外,儿童也能够从健康服务机构的营养干预中获益,例如得到微量元素摄人、进行发育监测与促进、进行驱虫处理,等等。在马拉维,Miller、Tsoka和Reichert(2011)发现无条件的现金转移能够保障受益家庭避免食物短缺,改善膳食结构,促进儿童的体重增加和健康发育(Miller等,2010)。而Skoufias、Tiwari和Zaman(2011)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表明现金转移能够保障多样化的饮食摄取。
2. 食品与营养转移支付
维持消费的另一个选择是直接针对脆弱家庭进行食品的转移支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将会贬值,一些潜在受益者可能更希望得到直接的食品支付。这种食品援助有助于维持充足的蛋白质和能量获取,但通常缺乏微量营养元素。然而,随着营养转移支付项目开始包含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多样化口粮,以及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食品,这种现象正在改变(Gentilini和Omamo,2011)。其他措施包括食品援助的地方采购、维持食品市场稳定;通过添加安全的添加剂或提供具有一定治疗作用的食品来提高营养含量;以及在家庭主食中添加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颗粒或粉末等。
3. 学校加餐
2008-2009年的危机和眼下的危机都对低收入国家的学校加餐计划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相比之下,其饱受质疑的投入/效率比也不再重要(Alderman和Bundy,2011)。学校加餐应该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实物转移支付,通过医疗和教育手段支持低收入家庭(缓减贫困)补充营养,积累人力资本。学校加餐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课间餐,一种是可以带回家的口粮。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学校加餐的成本大约是儿童基础教育经费的10%~20%。然而对于一些低收入的非洲国家而言,这种加餐的成本几乎与基础教育的成本持平(Bundy等,2009)。
学校加餐项目对受益儿童年幼的弟妹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布基纳法索,享受学校口粮分配的女孩的弟妹们(12~60月龄)平均体重增加了0.38个标准差。而乌干达的学校加餐项目表明,“课间加餐”的受益学生身高增加了0.36个标准差,而享受“口粮外带”的学生身高却无明显改善。 学校加餐项目能够通过强化食品营养提供所需的微量元素,然而这些食品却不会出现在本地市场。影响项目的整体效果也会受到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存储成本高昂,许多社区都无法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加餐就成为危机中的首选。当然,对其运输成本和可持续性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4. 支付营养工资
食品援助和以工代赈项目都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地保障消费。转移支付形式(现金或食品)取决于地方能力、市场条件和文化接受度等因素。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经验表明,以工代赈项目能够改善食品安全,增加儿童体重,但其瞄准机制有待加强。而在印度尼西亚,大米、食用油和豆类等形式的转移支付对儿童发育和产妇贫血状况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Wodon和Zaman,2008)。
一种新的支付形式是营养干预。以工资的形式进行瞄准是非常有效的自我筛选机制,能够吸引来自贫困家庭的劳动力积极参与,以解决其子女的营养不良问题。在吉布提(和尼日尔)所采用的方式是:在传统的以工代赈项目中加入营养元素,推动受益者将额外的收入用于改善家庭的营养状况。在吉布提(Silva,2010),这种支付形式为有工作能力的成人提供(由社区选择和设计的)社区工作和服务(仅针对妇女)的机会,例如采集、回收、用塑料袋制作地砖等。而项目中的营养元素瞄准参与者家庭中那些脆弱的、无法从事劳动的成员,包括每个月定期召开针对营养问题的社区会议、社区工作者每两周进行家庭探访,以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提供食品等。
(二)生物与健康
针对营养不良问题已有成熟的、有效的解决方案。食品摄入不足会导致体重不足(极端性营养缺乏)、发育迟缓(长期性营养缺乏)、免疫能力退化、发病率升高并引发各种疾病。联合国的“增强营养”(SUN)计划(专栏5)确定了三大领域共计13种有效的、稳定的干预措施:
●行为改变。包括推动和支持母乳喂养;以咨询和营养教育(但不直接提供食品)的方式推动辅食添加,养成用肥皂洗手的习惯,培养卫生行为。这些服务主要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营养项目来完成。
●微量营养物质和除虫。包括补充维生素A、锌(针对腹泻)、复合营养粉等;进行驱虫处理;为孕妇补充铁和叶酸;推广富含铁元素的主食;碘化盐;为无法获得碘化盐的孕妇补充碘等。这些服务主要通过儿童健康活动、社区营养项目、基本医疗体系和市场机制来完成。
●食疗。包括对6~23月龄婴儿的预防性和治疗性喂养,针对极端营养缺乏状况添加可信赖的治疗性食品。这些服务主要通过社区营养项目和基本医疗体系来完成。
社区生长发育监测和推动项目为各种服务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已经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专栏6)。以社区为基础能够推动项目瞄准引起营养不良的诸多原因,对妇女和2岁以下的婴幼儿给予更多关注。这些项目能够积极地改变营养观念和儿童发育理念。秘鲁的地方改革运动(RECURSO)成功地让家长意识到儿童个头矮小是营养不良的征兆,呼吁他们“要求营养改善”(Walker,2008)。此外,新的测量手段也能够提高家长对儿童过瘦、超重和矮小等问题的警惕,例如通过测量臂围来直观地跟踪儿童身高发育状况等。健康干预也能够通过向幼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特殊服务而来改善营养状况,例如贫血的预防与治疗、改变饮食习惯、营养餐和疾病(特别是腹泻、急性呼吸道感染、麻疹、痢疾和艾滋病等)防控,以及改善生殖健康、推行计划生育等(世界银行,2012)。这就要求在危机时能保障基础健康体系的经费运行,这对许多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
(三)生产与农业
食品安全议程(主要是农业发展)与营养安全议程联系起来(如联合国SUN框架所倡导的)形成合力能够惠及整个国家。SUN框架下的一些干预措施具有性别视角,许多国家的妇女都面临着缺乏生产投入和资产的困境,而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减贫和改善营养状况。农业生产方式变化会通过种种途径影响健康和营养水平(Hoddinott,2011;世界银行和IFPRI,2008):
●提高农业生产能够促进增收。家庭额外收入能够用于购买改善健康和营养的食品,或以资产形式储存起来,如修建房屋和卫生设施等,会对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农业生产变化会改变膳食结构,促进饮食多元化,特别是引人生物强化作物时(如富含维生素A的水稻和红薯)更是如此。
●作物类型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增加或减少劳动量,对虫害、人畜共通传染病和意外事故等都产生影响。
●农业回报率升高时,家庭会通过雇佣帮工、减少闲暇和使用童工等方式增加农业劳动投入。
●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家庭内部再分配结构。例如妇女收入增加可能会影响消费方式、食品分配方式和资产持有方式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健康和营养状况。
由于农业项目和农业研究的成果很少提及营养问题,而农业干预成本会显著高于直接的营养干预。上述结论虽然缺乏数据支持。但仍有研究表明收入增加、饮食结构调整和生物强化食品的确能够改善营养水平(Masset等,2011)。
1. 增强农业与营养的联系
一些农业战略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与营养之间的联系,例如关注脆弱群体(如小农,特别是妇女);生产多元化(包括房前屋后的食品生产),提高豆类、蔬菜和动物产品的可获得性;应对水传播疾病和动物传播疾病;在农业生产中结合营养教育等(Pinstrup-Andersen,2010;世界银行,2007;世界银行和IFPRI,2008;世界银行,2012)。改变生产行为的最显著成效体现在饮食结构的多元化。
在许多小农经济中,特别是在非洲,妇女主要负责家庭的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因此,农业干预应当避免增加妇女劳动量而导致的对家庭营养产生的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方案并不困难,只是鲜少能真正触及妇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妇女很难像男性一样获得化肥、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赋予她们同等的机会,她们的玉米、豌豆和鹰嘴豆的产量会比男性高出22% (Quisumbing,1996)。
推广营养丰富的食品能够促进饮食结构的多元化。从事花卉生产或养殖业(家禽、豚鼠、水产等)的家庭的营养改善程度更为明显。生产类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饮食质量和微量元素的摄入。此外,营养物质储存方式改良和收获之后的营养强化处理,也能够提高食品的营养含量。
另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是生物强化。推广橘色甘薯(富含维生素A)对莫桑比克的幼儿和妇女的维生素A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也贡献于当地的能源消费、妇女营养知识获取和妇女赋权,同时增加了家庭收入。粮食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的工作旨在增强铁(贫血)、锌(发育)和维生素A(夜盲症、免疫系统和发病率)的生物强化,以解决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其中一些作物已经在推广阶段,例如印度的富铁富锌的珍珠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富铁水稻、卢旺达的富铁大豆、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的维生素A木薯以及赞比亚的维生素A玉米等。2008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将生物强化确定为(除直接营养干预之外)解决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的第五种低成高效手段。
2. 应对天气变化和季节性食品短缺
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食品储存方式,能够解决季节性的食品短缺问题,而构建社会安全网则能够产生更为长久的影响。如上文所述,从胚胎形成到2岁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时期会跨越几个农业生产季节,其中难免会发生食品短缺,而儿童利益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这种季节性短缺将更频繁、更严峻。低成本的食品储存技术(如晒干)能够保障一年中较长时期内的食品多元化。而选择早熟或晚熟品种和抗旱作物也能够有所裨益。构建水资源管理体系,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提高生产力、预防水传播疾病,并减轻妇女的取水负担(Pinstrup-Andersen,Herforth和Jones,2012)。如果辅以社会安全网,这些干预措施就能够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在孟加拉北部的研究(Khandker,Khaleque和Samad,2011)表明,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减青黄不接时的季节性饥饿现象,其中NGO执行的项目成效尤其显著。
3. 减少收获后损失
减少收获后的营养物质损失能够提高农业收入,改善营养状况。收获后损失主要发生在富含微量营养物质的水果和蔬菜生产中(Pinstrup-Andersen,Herforth和Jones,2012)。增加对道路和仓储设施的投资能够有效地连接市场、降低损失。最后,农民营销协会能够提供价格信息等服务,其作用也不容忽视。
4. 瞄准性补贴
政府通常选择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来提高产量,然而这种补贴由于成本高昂、瞄准偏离、破坏地方市场和无法贡献于减贫效果差等种种弊端而饱受争议。针对马拉维的农业投入支持项目进行的模拟结果表明,该项目的产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贴的筹资方式、争夺稀缺的政府资金的公共投资的回报率以及小农通过使用化肥和种子而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Buffie和Atolia,2009)。当生产资料补贴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时,项目产出尤其不尽如人意。因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在长期内推动农户的生计多元化,从而保障其食品安全。而对比加纳和马拉维的补贴项目和现金转移支付项目(Taylor和Filipski,2012)结果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在改善儿童营养不良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
5. 妇女收入和女童教育
从1970-1995年的观察(Smith和Haddad,2000)表明,妇女教育(43%)比食品可获得性(26%)对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贡献更大。在南亚一些营养不良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其妇女地位很低。在危地马拉的研究(Ruel等,2002)发现,通过提供工作机会等方式增加妇女收入,能够改善城市贫困社区的儿童看护状况。在印度和塞内加尔(世界银行,2011a)瞄准性的现金转移支付和为妇女支付薪酬能够增加家庭消费、促进饮食结构多元化并提高儿童照料质量,从而改善了儿童的营养状况。
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是减贫和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嫁妆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妇女的嫁妆越是丰盛,其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就越高(女童尤其如此),女童的发病率就越低(Quisumbing和Maluccio,2000;Quisumbing和de la Briere,2000)。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婴儿抚育和营养的重要投入,因此投资于女童的教育将使其终生受益,其收入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也将惠及后代。
(四)成本
1. 不作为的后果
营养不良会降低个体生产力,并反映在国家的GDP损失上。在印度,个体生产力下降导致其一生收入减少10%,引起的GDP损失也高达3%~4%世界银行,2009)。在塔吉克斯坦,营养不良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4 100万美元。其中,由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劳动力死亡损失为1 230万美元,个头矮小、缺碘、儿童贫血和体重偏轻等问题导致的损失为2 860万美元。
2. 营养干预
Horton等(2010)对增强营养运动中的13种干预措施进行了成本核算,得出的最小值为每年118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预计将来自富裕家庭自身花费在补充和强化食品方面的成本,仍有103亿美元的缺口。如果能够筹资成功,营养干预将能够覆盖全球36个国家,90%的发育迟缓的目标人群。如果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另外32个营养不良状况较差的国家,预算又将提高6%。筹资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每年投入55亿美元,其中15亿用于微量营养元素和除虫,29亿用于行为方式改变,10亿用于能力建设,以开展和推广更为复杂的、瞄准性的食品项目。
第二步:每年投入63亿美元,用于资源禀赋较差地区的食品援助和食疗工作,其中36亿用于补充食品以缓减和预防一般性营养缺乏,26亿用于治疗严重的营养不良。
当然,每个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和步骤应当针对自身的营养问题(如季节性波动、城乡分配格局、蛋白质和能量不足、营养物质缺乏等)和行政能力(能力较高的国家会更迅速地开展第二步工作)而有所侧重。
针对营养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的系统分析仍然空白(世界银行,2010a),但经验表明,每种干预手段的投入/产出比都高于2:1(表1,图3)。如推动母乳喂养行为方式干预措施的回报率在5:1到67:1;补充维生素A添加剂的回报率在4:1到43:1;食盐加碘的回报率为30:1;驱虫处理
表1 营养干预措施的年人均成本非常低
资料来源:Horton,Alderman和Rivera,2008。
的回报率在3:1到60:1。而针对胚胎期到2岁这一生命早期阶段的营养改善措施的最新研究表明,回报率可能会更高。而新技术的出现,如复合营养粉(颗粒)、食疗和通过媒体进行的现金转移支付等,使这些干预措施的执行更加简便。

资料来源:Horton,Aldcrman和Rivera,2008。
全球增强营养运动的干预措施的成本低于在农村、农业和农业企业发展领域(2010年的140亿美元)和社会安全网构建方面的援助承诺。当然,从1995-2007年,用于基础性营养干预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每年3亿美元,这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并非所有的农业、医疗和社会保障项目都旨在缓减营养不良,而这些领域的一些干预措施显然能够在适当稍微提高成本的基础上就能极大地改善营养状况。在国家的层面上,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用于社会安全网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1.9%(Grosh等,2008; Marzo和Mori,2012)。而在危机中,总投入为6 000亿美元(Zhang,Thelen和Rao,2010)。如上所述,这些干预措施能够成为改善营养状况的平台(世界银行,2012)。
3. 推动综合的、稳健的跨部门营养项目要求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革
加速加大针对营养问题的投资包括建立跨部门合作基础,要求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和贸易等社会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有:国家层面上营养不良数据的陈旧(人体测量数据特别是身高数据)、微量营养元素缺乏数据的不足(血液检查)和如母乳喂养和洗手等行为改变方式数据的滞后;潜在直接受益者(幼童和孕妇等)缺少表达利益诉求渠道的缺乏;政治承诺的缺乏。
在政策环境、项目实施和效果各异的国家进行的针对营养政策和项目的系列案例研究表明,“低优先序”的恶性循环正在被打破。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原因如下:最受威胁的群体开始群策群力,共担风险,推动变革(以运动的形式);结成(广泛的)联盟与阵线(包含一个或多个发展伙伴),统一发声,影响决策者和决策过程;政治“机会之窗”已然打开,而上述运动和联盟能够抓住机遇,促进改革(专栏7)。
这些因素也会互相促进。例如,运动能够创造政治“机会之窗”,而形成联盟又能够促进运动的发展。在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改革通常会以失败告终。而如果这三个因素能够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就能够形成共享性的政策文本,以推动营养干预,确定和聚焦于特定的政策优先事项,并以数据和干预产出为基础提出制度发展和资源动员的诉求。
五、 政策回应及对营养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预期影响
食品价格上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在各国和各个社会经济群体中不尽相同。一个国家是(世界价格发生变化的)食品的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该食品(对贸易、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性如何?同样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回应(例如动员储备资源来弥补政府支出的增加等)也会影响世界价格。要分析危机期间的支出方式和筹资行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MAMS模型来分析各国的策略(包括应对营养不良的策略)。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食品价格到2015年将会翻番(随后保持不变),分析器对两种类型的低收人国家的影响。这两种低收入国家类型在许多维度能够代表低收入国家的中值,区别在于不同的贸易结构,一个代表食品净出口国,另一个代表食品净进口国(专栏8)。
在微观层面上,两种类型的国家都迫切地需要进行政策干预。虽然食品价格上涨对于净出口国而言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某些特定类型的家庭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在短期内的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完全依靠食品购买的家庭可能会面临真实收入减少的压力,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从增长中受益(例如依赖国外劳务汇款的家庭,其国内购买力会因货币升值而降低),其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而净进口国则无论如何都需要进行广泛的政策干预。
干预类型和筹资方式也会对营养干预和改善MDG指标的表现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加以展示,我们构建了6种模式,每种都代表净进口国在食品价格升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回应,随后再与不进行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对MDG指标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其中,前4种模式(补贴+税收,补贴+援助,补贴+借贷,补贴+支出)都包含了普惠式的食品补贴,以保持国内加工食品价格到2025年前的稳定(作为基线)。在这4种模式中,都需要进行额外的筹资(GDP的5%),例如国内税收(补贴+税收)、国际援助(补贴+援助)、国内借贷(补贴+借贷)或国内支出缩减(补贴+支出,如减免针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和农业支出等)。而后2种模式[转移+税收,转移+税收(2)]也如同补贴十税收模式一样提高税率,却不对食品进行补贴,将财政收入用于瞄准性转移支付,瞄准对象为以人均收入测量的城乡贫困人口(即收入在后50%的人口)。转移+税收模式假设转移机制能够由现有的政府机构实施,而转移十税收(2)模式则需要支付i5%~25%的成本用于增加工作人员和其他成本,这一成本将逐渐下降。
这些政策回应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发人深省。不考虑成本的转移支付(转移+税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极端贫困(MDGl.a),需要支付成本的转移支付[转移+税收(2)]和援助式食品补贴(补贴+援助)次之。事实上,援助式食品补贴能够保护国家经济免遭进口价格上涨的影响(图4a)。依赖国内资源的普惠式食品补贴在减贫方面乏善可陈,而通过缩减开支(补贴+支出)所产生的影响与增加税收(补贴+税收)的效果如出一辙。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缩减开支对贪污浪费的影响,以及税收究竟是在提高分配效率还是在阻碍投资等。通过国内借贷支持的普惠式食品补贴(补贴+借贷)初期略有成效,但最终却导致贫网率(与基线值相比)不降反升。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借贷打击了国内的私人投资,降低了资本存量,导致GDP下降。这种负面效应在初始阶段并不显著,随时间而日益加剧,与营养不良对儿童的影响路径有相似之处。
由于抑制了加工食品的价格上涨,补贴是应对营养不良现象的最成功手段(图4b)。援助(补贴+援助)模式也十分可取,随后是紧缩开支(补贴+支出)和增加税收(补贴+税收)。在其他3种模式中,到2025年营养不良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对于两种转移支付模式来说,其原因在于真实收入增加,消费者的食品消费降低而其他消费增加。而对于国内借贷支持的补贴来说,主要原因则是家庭真实收入的降低。需要注意的是,补贴通常只针对富含卡路里但缺乏微量营养元素的粮食作物。因此,即使体重有所增加,发育迟缓和微量元素缺乏也可能持续(以洪都拉斯为例)。

最后,对于MDG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MDG5(生殖死亡率)的影响取决于增长对真实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健康消费(转化为政府健康服务;图4c和4d)。以援助支持的补贴(补贴+援助)不会触动国内政策,而私人部门的购买力也会由于货币增值而有所提高,因此,能够最有效地降低5岁以下儿童和产妇的死亡率。而来自其他筹资渠道的补贴则会导致5岁以下儿童和产妇的死亡率提高,其中削减政府开支进行补贴(补贴+支出)带来的影响最为严重,而来自国内借贷的补贴(补贴+借贷)影响次之。这些结果表明,削减政府开支不仅会影响政府服务的提供,也不利于私人消费的保障。增加税收[补贴+税收,转移+税收以及转移+税收(2)]不会影响政府服务,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上文分析表明,如果考虑管理成本,各个国家应该引入瞄准性措施(包括瞄准性转移支付)。如果不考虑管理成本,普惠式的食品补贴是对抗营养不良的最有效方式,其中援助支持的补贴因避免了国内资源重组的重重困难而成为首选。然而,补贴模式并不能解决发育迟缓和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问题。如果补贴的筹资方式破坏了国内资源流动而产生了抵消效应(如影响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和政府对人类发展服务的需求等),那么最好的选择是维持现状。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分析中长期内的国际食品价格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格局也应当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认为仅仅是消费者的食品购买价格发生了变化,将会大错特错。
六、 政策建议
1. 加强营养状态、行为和干预的信息建设
设计干预措施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少关于基本营养指标、价格变化和干预措施等的可靠数据。如果能够了解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对象和影响方式,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政策回应。然而,鲜有全国性调查会采集家庭和个体层面的食品消费数据,预测也就无从谈起。一些国家甚至缺少新生儿数据,导致对儿童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也十分困难,无法收集个体发育数据,更谈不上计算各种发育指数。对微量营养元素的测量需要采血,涉及复杂的后勤安排,而基于生物标记的新技术还没能推广。此外,针对成本、影响和跨部门干预的数据也十分稀缺。MDG指标之一是儿童体重不足,而近来的研究表明,身高不足才是测量营养不良的最佳指标。如果能够开展多目标的、全国性的家庭调查,收集关于食品消费、营养状况(包括微量元素信息)和市场条件等信息,将有助于各国监测营养水平,设计瞄准性干预措施。
2. 营养投资需要高回报
全球增强营养运动的成本看似很高,然而不作为的成本更高。推动全球营养运动可以节约单位成本(表1),(即使进行保守估计)回报率也非常可观。针对营养问题的筹资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能力问题被凸显:各部门形成合力并共同实施营养干预的能力不足,基本的营养服务能力也有欠缺。最近,营养关注重新成为援助方的援助热点,包括多边援助机构如联合国、双边援助方如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挪威和英国等,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儿童救助会等。“增强营养”框架也可能会催生新的行动(专栏5)。
3. 瞄准从胚胎形成到2岁这一生命阶段
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对营养状况产生间接影响。而针对婴幼儿及其监护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特殊干预则会为人力资本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上文已经对从胚胎形成到2岁这一生命阶段所经历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的身体机能和社会认知发展所产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阐述。这一时期进行干预的回报率较高,也能够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整体性路径需要考虑营养、健康、幼儿激励(如游戏、规范)等方方面面。高水平的幼儿看护和照料对营养状况改善和社会认知能力提高都至关重要。一些行为方式的改变需要因当地的社会环境而有所调整;同时健康系统的工作重点要实现从治疗到预防的转变。
4. 根据各国的实施能力和营养问题制定适当的干预措施
虽然只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才会得到筹资和救助,然而针对长期性营养不良也应建立应对机制。很少有国家会经历严重的蛋白质和能量缺乏等营养不良,因此营养不良问题主要是突发性(非洲之角)、季节性(例如孟加拉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饥饿季节”)、局部性(吉布提、肯尼亚北部和巴西东北部的“饥渴地区”)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方式(专栏6)能够解决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应对食品短缺和市场失灵;短期的食品转移支付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却无法预防长期的营养不良。
“隐性饥饿”(即缺少微量元素)需要进行多种渠道的干预。大部分人口都会缺少铁、维生素A、锌和碘等微量元素,而“增强营养”计划建议的干预措施包括在重点地区向脆弱人群供应添加剂(如为孕妇和儿童提供维生素A和铁,向腹泻儿童提供锌片),以及在食盐、面粉和食糖中添加碘元素等方式进行食品强化。对主要的粮食作物进行强化需要私人部门的支持。未来,生物强化作物可能会在防止微量元素缺乏方面大有作为。驱虫也会改善妇女儿童的卫生和贫血现象。健康部门通常负责驱虫、婴幼儿喂养和微量元素补充,而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则是行为方式改变和营养监控的最佳平台。
食品进口国和食品出口国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会采取相似的干预措施。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起社会安全网,并在危机中扩大其覆盖面。食品补贴是稳定食品价格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其成本过高,营养改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瞄准性补贴或现金转移对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的意义更为显著。本文的一般均衡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考虑管理成本,那么瞄准性措施(包括瞄准性转移支付)是最佳选择。而如果不考虑管理成本,援助支持的普惠式的食品补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改善营养不良状况。然而,如果普惠式补贴的筹资方式会导致其他社会服务资源的减少,就应该果断放弃。
瞄准幼童所在的贫困家庭能够改善高危人群的营养状况,避免营养不良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在社区层面或健康部门层面实施综合性的儿童发育监测和促进项目,也是对营养问题进行干预的一个切入点。该项目应当包括信息传播功能(例如秘鲁的RECURSO项目),以动员大众、提升意识,避免营养不良带来的长期影响,保护儿童和孕妇免受其害。专栏9展示了海地在2010年震后重建食品安全的策略及其为完成政策优先事项而采取的首要措施。
5. 在跨部门干预中引入营养敏感路径
要想同时实现食品安全和影响营养安全,就需要权衡短期救助和长期投资的投入/产出比。长期投资通常能够提高(特别是小农的)生产力,发挥跨部门效应,将营养问题与健康、农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应当促使健康、农业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干预手段中加入营养视角(世界银行,2012;也见http://www.securenutritionplatform.org/pages/home.spx)。全球食品贸易环境会影响国家特定的政策选择,国内市场同样也重要,所以有必要完善市场机制(公开价格信息、避免价格扭曲)并促进私人部门的市场参与。
在地方层面上,食品价格上涨将会对地方市场和生产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成功的干预措施需要政府与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建立联盟。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意识提升项目来促进行为习惯和社会风气的革新。大规模的社区营养项目已经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取得了成功(专栏6)。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意识倡导和服务扩散的功能。私人部门在食品强化和食品添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也贡献于改善营养食品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编译者:赵丽霞 张悦)
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效应
Nathan Nunn哈佛大学/国家经济研究局
非洲当前落后是否能够被奴隶贸易所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航运记录和历史文件收集的数据估计各国在非洲奴隶贸易中出口奴隶的数量,发现一国出口奴隶数量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考察了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的历史证据并采用工具变量的计量方法,结果表明奴隶贸易对于经济发展存在负向效应。
一、 引 言
非洲的经济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乏善可陈。关于非洲落后的一个非正式解释是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等不幸的历史遭遇。Bairoch(1993,第8页)写道:“毫无疑问,(非洲)经济落后的许多负面结构特征根源于欧洲的殖民扩张。”Manning(1990,第124页)赞成Bairoch的观点,但是更加关注奴隶贸易:“奴隶贸易是肮脏的,充斥着偷窃、贿赂、野蛮和欺诈。奴隶贸易成为现代腐化堕落的根源之一。”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洲的历史可以部分地解释当前的落后状况。这些研究集中关注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当前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Grier,1999;Englebert,2000a, 2000b; Acemoglu, Johnson,and Robinson, 2001,2002;Bertocchi and Canova.2002,Lange,2004)。然而,非洲历史上另一重大事件——奴隶贸易,还没有进行充分有效的实证研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奴隶贸易对于非洲的发展至少与殖民统治同样重要。从1400-1900年近500年的历史之中,非洲大陆同时经历着四类奴隶贸易。与此相比,殖民统治从1885年大约持续到1960年,总共75年左右。
本文首次提供了关于非洲奴隶贸易影响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为此,构建了1400-1900年每个世纪非洲各国奴隶出口数量的估计。奴隶出口数量根据航运记录和历史文件估计,其中航运记录记载了从非洲各个港口或地区输出奴隶的数量,历史文件记载了输出奴隶的种族。发现在一国奴隶出口的数量和随后的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今天非洲最穷的国家正是那些输出奴隶最多的国家。
这一发现还不能作为奴隶贸易导致随后经济发展差异的最终证据。一个至少同样可能的解释是那些经济上和社会上最落后的国家才参与奴隶贸易,并且这些国家继续保持最落后的地位。换言之,奴隶贸易可能与不可观察的国家特征相关,从而导致奴隶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效应的有偏估计。
采用了一系列策略以便更好地理解奴隶出口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背后的理由。首先,审查了非洲历史学家提供的关于奴隶贸易的证据,也利用了奴隶贸易之前人口密度的历史数据来检验是否是非洲的相对落后地区选择参与奴隶贸易。以上两方面证据都表明实际上非洲最发达地区才更倾向于参与奴隶贸易。其次,采用工具变量去估计奴隶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是在四类奴隶贸易之中从各国到最近的奴隶劳动力需求目的地之间的航海距离。与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一样,工具变量的系数也是负的并且显著,说明奴隶贸易期间输出更多的奴隶导致了随后更差的经济表现。
接着考察了奴隶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背后的因果关系的具体途径。以历史证据作为参考,检验了通过内部战争、掠夺和绑架获得奴隶是否会导致国家和种族分裂。发现数据和这些途径相符。
这些发现补充了Engerman&Sokoloff(1997,2002)关于奴隶贸易在新世界导致的制度演变无益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证明奴隶的使用不仅破坏社会,而且通过国内战争、掠夺和绑架的方式获取奴隶本身就对随后经济发展存在负面作用。
二、 历史背景
在1400-1900年,非洲大陆同时经历4个奴隶贸易。规模最大的是始于15世纪从非洲西部、中西部、东部将奴隶运往欧洲各国的美洲殖民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其他三类奴隶贸易——跨撒哈拉奴隶贸易、红海奴隶贸易和印度洋奴隶贸易,都早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中,奴隶从撒哈拉沙漠南部被运往北非;在红海奴隶贸易中,奴隶从红海内陆被运往中东和印度;在印度洋奴隶贸易中,奴隶从东非被运往中东和印度或者印度洋的岛上种植园。
非洲奴隶贸易的很多特点使其区别于之前的任何奴隶贸易。第一,贩卖奴隶的总数史无前例。仅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大约1 200万奴隶从非洲输出,其他三个奴隶贸易另有600万奴隶被输出。以上数据不包括在掠夺中被杀死或者在运输途中死亡的奴隶。根据Patrick Manning(1990,第171页)的计算,奴隶贸易的总效应表现在1850年非洲的人口只有在没有奴隶贸易的假设情况下的一半。
非洲奴隶贸易的独特性还表现为同一种族内部的一些人强迫另一些人成为奴隶。这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社会和种族的分裂、政治的动荡、国家的弱化和司法制度的腐化。
获取奴隶的最普遍方式是通过村落或国家之间的相互劫掠(Norhtrup1978;Lovejoy 1994)。村落之间原来发展成更大规模的村落联盟,现在却发展成相互敌对关系(如Azeved0 1982;Inikori 2000;Hubbell,2001)。结果导致村落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进而妨害更广大的共同体和更广泛的种族认同的形成。Kusimba(2004,第66页)写道:“种族内部安全保障的缺失导致了相互交流的限制。”因此,奴隶贸易是解释今天非洲严重的种族分裂的重要因素。在给定种族分裂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奴隶贸易导致的种族分裂显著地影响经济发展。
由于当时不确定和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每个人都需要武器进行自卫,例如铁制刀具、标枪、剑或者火器等。这些武器可以通过绑架和强迫当地人为奴隶,并与欧洲人交换获得。这进一步促进了奴隶贸易和由此导致的安全保障的缺乏,而安全保障的缺乏再进一步促进了强迫他人为奴隶而保护自己的需要(Mahadi 1992; Hawthorne 1999,第108-109页)。历史学家将这个恶性循环命名为“枪——奴隶循环”(如Lovejoy 2000)或者“铁——奴隶循环”(如Hawthorne 2003)。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是一个部落劫掠另一个部落,而且是同一个部落内部一部分成员劫掠和绑架另一部分成员。这些例子有Balanta、Minyanka(Klein 2001),中东非的Makua、Chikunda、Yao (Alpers 1969,第413-414页,1975,第225页;Isaacman 1989,第191-192页)。
一般而言,内部冲突的后果是政治的动荡乃至一些情况下原有政权的崩溃(Lovejoy 2000,第68-70页)。在16世纪的Senegambia北部,葡萄牙的奴隶贸易导致Joloff联盟分裂,被Waalo、Kajoor、Baol、Siin和Saalum等一些小国取代。Senegambia南部出现同样的情况。在奴隶贸易之前,非洲复杂的国家系统正在自我演化。然而,自我演化在葡萄牙于15世纪到达之后迅速停步不前了(Barry 1998,第36-59页)。类似的动荡状况也出现在东非(如Isaacman 1989;Mbajedwe 2000)。在19世纪晚期,导致了东非Shambaa王国、Gweno王国和Pare王国的分裂(Kimamb0 1989,第247页;Mbajedwe2000,第341-342页)。
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可能是中西非的Kongo王国。早在1514年,绑架Kongo本地公民作为奴隶出售给葡萄牙就已经泛滥成灾,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秩序和国王的权威。在1526年,Kongo的国王Affonso写信给葡萄牙抱怨道:“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大量商人。他们将这个国家带向毁灭。每天人民都被绑架而强迫为奴隶,甚至贵族和王族也无法避免。”(Vansina 1966,第52页)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至少部分地导致曾经强盛的国家的弱化和最终覆灭(Inikori 2003)。其他的说班图语的许多种族在早期社会稳定,但是奴隶贸易结束时这些古老国家已经荡然无存了。
原先的政权结构普遍被现存统治者或军阀控制的奴隶劫掠黑帮取代。然而,这些黑帮一般无法演变为稳定的大国。Colson(1969,第35页)写道:“掠夺奴隶的黑帮以及他们建立的新国家都只是一时兴起的幻影。没有一个黑帮的头子能够将权利转移给一个合法的继承者。即使一个黑帮的头子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继承依然是一个问题。统治只维系在个人身上,而不是一套政治体系。”
奴隶贸易还通过腐化原先的法治构架促进了政治的动荡。在很多情况之下,以巫术或者其他罪名恶意起诉他人成为获取奴隶的普遍方式(Koelle1854;Norhtrup 1978;Iovejoy 2000)。Klein(2001,第59页)写道:“部落开始强迫自己人为奴隶。司法惩罚原先采取鞭打、赔偿或者流放的形式,现在转而采取强制为奴隶的形式。”领导阶层自己经常支持甚至鼓励司法系统的滥用(Mahadi 1992; Hawthorne 1999,2003;Klein 2001)。为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部落不受劫掠,领导阶层经常选择通过司法系统滥用获得的奴隶作为礼物支付。Hawthorne (1999,2003)详细研究了这一方式在Cas-sanga(今天的Guinea Bissau)的情况。Cassanga的首领利用“红水的神裁”(red water ordeal)获取奴隶及其财产。那些被指控为有罪的人被强制服下一种有毒的红色液体。如果他们呕吐,那么他们被判决为有罪;然而,那些没有呕吐的人通常由于毒发而死亡,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家庭成员被贩卖为奴隶。
现有文献关于一国的国家政权历史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表明奴隶贸易的效应对于当前经济发展可能非常重要(Bockstette,Chanda,and Putterman 2002;Chanda and Putterman 2005)。一些人辩称非洲的落后是非洲在殖民统治以前就存在的积弱而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败的直接后果(Herbst 1997,2000)。由于非洲奴隶贸易是影响政治落后的重要因素,所以他们可能是今天非洲国家治理落后的核心原因。
三、 奴隶出口数据
利用两类数据估计奴隶出口数据。第一类数据记载了从非洲各个港口和地区输出奴隶的总数,把这些数据称为海运数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据来自于Eltis等(1999)整理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修订版)。这个数据库记载了在1514-1866年34 584次航运的资料。原始的海运数据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各种文件和记录。在欧洲的大多数港口,商人需要登记每一艘船的每一次运输商品的数量和价值,而且那时存在多个不同的登记机构和登记文件。在数据库中,1700年之后的77%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据有多于一个来源的资料,每一次海运的数据记录平均达到6种。该数据库包括了82%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据(Eltis&Richardson 2006)。
Elbl(1997)提供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缺乏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早期数据。至于印度洋奴隶贸易、红海奴隶贸易和跨撒哈拉奴隶贸易,数据来源于Austen(1979,1988,1982)。这些数据基于所有可能的文件、记录、当地人和政府机构的描述。
可以根据航运数据计算得到从各个沿海国家输出奴隶的数量。然而,这并不能准确描述奴隶们最初是在哪里捕获的。从一个沿海国家的港口输出的奴隶可能来自于一个内陆国家。为了估计从内陆国家捕获但从沿海国家输出的奴隶数量,还利用第二类数据,即从非洲输出的奴隶的种族。该数据来自多种途径,如销售记录、奴隶登记、奴隶逃跑通告、诉讼记录、教堂记录和公证文件等。
确定一个奴隶的种族或国家存在多种方法,最简单的一种根据奴隶的名字。奴隶经常被赋予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和一个标志种族的姓氏(如Tar-dieu 2001)。同样,一个奴隶的种族还可以通过一些种族标记鉴别,如伤痕、烙印、发型和牙齿(Karasch 1987,第4-9页)。Oldendorp(1777,第169页)写道:“所有的黑人都在皮肤上留有特定的标记。在我还不能通过黑人其他方面分别他们的国家时,这些标记帮助我区分黑人的国家和种族。
由于奴隶是合法持有的财产,从事奴隶买卖的商人具有强烈的动机准确地确定奴隶的出生地或者国家(Wax 1973)。Moreno Fraginals(1977,第190页)写道:“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奴隶贸易是世界上资本投入最多的行业。如果准确地确定商品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那么当时最重要的奴隶贸易也就不会分门别类地详细记录了。
关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的种族信息来自于54个不同的样本,总共80 656个奴隶,229个不同的种族。表1总结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样本的信息,包括地点、年份、奴隶数量、每一样本可鉴别种族的数量。其他三个奴隶贸易的信息见Nunn(2007)的表格。
表1奴隶种族数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印度洋奴隶贸易的种族数据来自于6个样本,总共21 048个奴隶,80个种族。红海奴隶贸易的数据来自2个样本(一个是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另一个是印度孟买),总共67个奴隶,32个种族。跨撒哈拉奴隶贸易的数据来自2个样本(一个是中苏丹,另一个是西苏丹),总共5 385个奴隶,23个种族。Austen(1992)的运输数据提供了关于运输的起点和终点,有时甚至运输的奴隶种族的额外信息。
为了说明怎样根据种族数据和航运数据构建估计数据,以图1为例。图l是一幅非洲西岸的虚拟地图,每个方格代表一个国家。

首先,根据航运数据计算从非洲每个沿海国家输出奴隶的数量。假设10万个奴隶从国家A输出,25万个奴隶从国家C输出。单纯根据航运数据的问题在于很多从国家A输出的奴隶可能来自于国家A的相邻内陆国家B。根据种族数据计算来自于沿海国家和来自于相邻内陆国家的奴隶比例。这要求确定种族所属的国家并据此计算国家的奴隶总数。在操作中,这一步骤基于非洲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大量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如Koelle(1854)、Curtin (1969)、Higman(1984)和Hall(2005)。
假设来自国家A的奴隶和来自国家B的奴隶的比率是4:1,这意味着从国家A输出的奴隶中有20%来自国家B。因此,来自国家B的奴隶估计为2万人,来自国家A的奴隶估计为8万人。假设来自国家C、国家D和国家E的奴隶的比率为3:1:1。同理,来自国家C的奴隶为15万人,来自国家D和国家E的奴隶各为5万人。在实际操作中,每一次奴隶贸易单独进行上述估计。随着奴隶贸易的不断开展,获取奴隶的地点也越来越向非洲内陆延伸,因而需要根据每一个时间段(1400-1599、1600-1699、1700-1799、1800-1900)单独进行上述估计。
因为种族通常比国家小,将种族归人国家一般不存在问题。图2展示了根据Murdock (1959)分类的非洲种族示意图以及现代政治区划图。从示意图看,种族分布区域显然小于政治区划,因而种族分布区域能够归入政治区划。

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从一个国家的港口输出的奴隶来自于本国或者来自于相邻的内陆国家。然而,实际上从一个沿海国家输出的奴隶可能来自于一个相邻的沿海国家。利用三个已知奴隶种族和奴隶输出港口的样本,Nunn图2 Murdock(1995)定义的种族边界和现代政治区划(2007)检验了该假设的可靠性和上述估计过程的总体准确性。结果表明上述估计过程能够以83%~90%的概率正确地确定样本中奴隶的来源。
测量误差的第二个来源在于来自内陆的奴隶在种族的样本中倾向于被低估。这是由于只有那些在离开非洲的航运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奴隶才会出现在奴隶种族的样本中。其他条件不变,来自于内陆国家奴隶的行程更远,从而也更可能在旅途中死亡。因为奴隶贸易中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这一测量误差可能影响显著。然而,内陆奴隶在样本中被低估的程度在最小二乘法估计中偏差接近于0。而且,我们可以采用与测量误差不相关的工具变量得到一致的估计。
在数据建立之后,得到了四类奴隶贸易在四个不同时间段(1400-1599、1600-1699、1700-1799、1800-1900)中从非洲每个国家输出奴隶数量的估计。表2报告了非洲国家输出奴隶总数的估计以及非洲国家在四类奴隶贸易中的每类输出奴隶数量的估计。总之,以上估计与非洲历史学家关于奴隶来源地的普遍看法一致。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的最主要来源地是所谓的“奴隶海岸”(贝宁和尼日利亚)、中西非洲(扎伊尔、刚果和安哥拉)和“黄金海岸”(加纳),这些国家是输出奴隶最多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也是输出奴隶最多的国家,因为他们是红海和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中主要的奴隶来源地。南非和纳米比亚输出奴隶很少,佐证了非洲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地方实际上没有奴隶输出的观点(Manning 1983,第839页)。地缘相近的国家之间输出奴隶的相对规模也与非洲历史文献的定性证据相符。Manning(1983,第839页)写道:“一些相邻的地区差异却很大:多哥只输出少量的奴隶而刚果则输出了很多。”我的估计与Manning的观察相一致,多哥输出的奴隶远远少于加纳,加纳输出的奴隶少于刚果共和国。
表2 1400-1900年各国奴隶出口总数估计
四、 基本关系:最小二乘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
首先检验一下过去奴隶出口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用土地面积表示的国家规模标准化一国输出的奴隶数量。图3显示了在1400-1900年在四类奴隶贸易中单位土地面积出口奴隶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与2000年人均GDP自然对数之间的关系。正如图3所示,在原始数据中明显存在收入和奴隶出口的负向关系。

控制了潜在影响当前收入的其他国家特征变量后,我进一步检验了上述关系。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是:
 (1)
(1)
其中,lnyi代表2000年国家i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In(exportsi/areai)代表在1400-1900年单位土地面积奴隶出口人数的自然对数,人均GDP是2000年数据,取自Maddison(2003);Ci是一个由虚拟变量构成的向量,代表独立之前殖民者的来源,意在控制非洲殖民统治的影响;Xi是一个由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意在控制国家间地理和气候的差异。
表3报告了式(1)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第一列报告只有殖民者固定效应的式(1)的估计结果。第二列加进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具有潜在重要影响的地理方面的控制变量:距赤道的距离、经度、月最小降水量、平均最大湿度、平均最低气温、海岸线与领土面积比率的自然对数。除了经度之外,其他因素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是亚热带气候,进而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和农业生产率(Kamarck 1976;Sachs等2001)。经度是为了区分非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差异。第一列和第二列都给出奴隶出口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关系。
表3奴隶出口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表3列(1)和列(2)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国家观测值中包括岛国和北非国家可能会导致估计偏差。列(3)中舍去了岛国和北非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塞舌尔、毛里求斯、科摩罗、圣多美普林西比和佛得角群岛。舍去这些国家结果没有太大变化。奴隶出口的估计系数保持负向显著,估计系数实际上略有增大。
在表3列(4)中增加了反映岛国或北非国家与非洲其他国家区别的控制变量。北非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两个核心区别一是北非国家伊斯兰教主导,二是北非围家法律体系基于法国民权法。为了甄别这些差别,还增加了伊斯兰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和是否具有法国法律渊源,北非围家固定效应和岛屿国家固定效应。正如表3所示,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奴隶出口的系数,其仍然保持统计显著的负向关系。
国家间差别的最后一个变量是自然禀赋。列(5)是1970-2000年黄金、石油、宝石的年人均产量的自然对数。列(6)包括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但是将岛国和北非国家排除在样本之外。结果依然表现得很稳健。
关于奴隶出口和收入之间的估计系数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符合经济学意义。通过计算标准化的beta系数,可以发现单位土地面积奴隶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增加伴随着收入对数值的0.36~0.62个标准差的减少。如果仅仅从举例的角度看,可以将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看作因果关系。假设如此,则根据列(5)的估计,一个国家原来的平均收入是1 240美元,奴隶出口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减少将使得收入增加到1 864美元,即收入增加50%。
五、 计量问题:因果性和测量误差
虽然最小二乘法估计证明奴隶出口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奴隶贸易是否和当前收入之间存在因果性关系。关于二者关系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原先落后的社会更容易参与到奴隶贸易中来,并且这些社会在今天继续保持落后的状况。因此,即使奴隶贸易对于随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奴隶出口和当前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这部分我通过两种方法检验奴隶贸易和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利用从非洲历史学家那得到的历史数据和定性证据,我评估了参与奴隶贸易的重要性和特征。如下文所示,有证据表明是否参与奴隶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一般而言都是最发达而不是最落后的社会参与到奴隶贸易中来。给定这些证据,奴隶出口和当前收入之间的显著关系不太可能是由于样本变差的选择效应引起的。另外,这种选择效应倾向于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偏向于0。其次,我采用从每个国家到奴隶需求目的地的距离作为奴隶出口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结果进一步确认了最小二乘法估计。
(一)在奴隶贸易中关于选择效应的历史证据
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早期贸易很大部分是商品贸易而非奴隶贸易。当时,只有那些具有充分发达的制度和机构的国家才能和欧洲进行贸易。在1472-1483年,葡萄牙人沿着中西部非洲的西海岸向南航行,尝试了很多登陆点而寻找贸易伙伴,在扎伊尔河以北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贸易伙伴。Vansina(1990,第200页)写道:“当地沿海国家人口和领土都太小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制度都不支持对外贸易的进行。”直到葡萄牙人找到扎伊尔河以南的刚果王国可持续的贸易才开始。刚果王国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权、全国统一的货币、发展成熟的市场和贸易网络,能够与欧洲进行持续的贸易。
当欧洲全部转向奴隶贸易时,欧洲依然继续偏好与非洲最发达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因为最发达的地区通常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如果能够挑起当地内部战争或冲突,就能够有效地获得大量的奴隶(Barry 1992;Inikori 2003)。反之,那些最野蛮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社会,一般会拒绝欧洲购买奴隶的行为。例如,由于加蓬原居民对于葡萄牙人的不服从和暴力抵抗,加蓬的奴隶贸易很有限。这种违抗持续了几个世纪,导致葡萄牙人的活动只能退缩到更南部的沿海地区(Hall 2005,第60 - 64页)。
利用原先人口密度的数据,我检验了是更加发达还是更加落后的地区更容易被选择参与奴隶贸易。Acemoglu等(2002)已经证明人口密度是经济繁荣程度的一个合理指标。图4给出了1400年人口密度的自然对数与单位土地面积奴隶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数据进一步确认了奴隶贸易期间选择效应的历史证据。图4显示以人口密度衡量的1400年非洲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受到奴隶贸易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选择效应的第二个潜在来源可能是本来存在奴隶制度的社会更加可能参与奴隶贸易。假设如此,正如Engerman和Sokoloff (1997,2002)说明的那样,那么国内奴隶制度和随后经济发展之间负向关系的估计结果会是有偏的。历史证据表明非洲原先进行更久远的伊斯兰奴隶贸易的地区存在奴隶制度,但是国内奴隶制度是外部奴隶贸易的原因或者结果尚不清楚。没有参与伊斯兰贸易的非洲地区是否在与欧洲接触之前就存在奴隶制度是非洲历史学家的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如Fage 1962;Rodney 1970)。这场争论中,陆续被挖掘出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国内奴隶制度不曾存在。Hilton(1985)证明在16世纪原先表示“佣人”或者“罪犯”的字词引申为“可贸易的奴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Jan Vansina(1989)利用更加翔实的语言学数据,进一步证实了Hilton的发现,证明在西部非洲不存在表示奴隶的字词。Vansina追索了“pika”(原先表示佣人,后来表示可交易的奴隶)的语源。这个字词最初产生于参与奴隶贸易的沿海港口,然后传播到参与奴隶贸易的内陆部落(Vansina1989,1990)。最近的一些关于其他地区的研究也肯定了外部奴隶贸易之前不存在国内奴隶制度(如Harms 1981;Irukori 2000;Hall 2005,第16页)。
(二)工具变量
采用的第二个方法是利用与奴隶贸易相关但与其他国家特征无关的工具变量。该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即使奴隶出口数据存在测量误差,仍然可以得到潜在一致的估计。如果工具变量与由于样本被低估的内陆国家出口奴隶数量引起的奴隶出口数据测量误差无关,那么与最小二乘法估计不同,工具变量法依然会得到一致的估计。
采用从每个非洲国家到奴隶需求目的地的距离作为奴隶出口的工具标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如下前提假设,即尽管需求目的地的位置会影响供应地的位置,但是供应地的位置不会影响需求目的地的位置。如果由于西印度群岛距离非洲西海岸更近将蔗糖种植园建立在西印度群岛,那么该工具变量就不合理。然而,如果相反由于非洲西部距离西印度群岛相对更近将奴隶从非洲西部运往西印度群岛,那么该工具变量就可能合理。根据奴隶贸易的历史,是需求目的地的位置影响供给地的位置而不是相反。非洲奴隶的需求目的地的位置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且与奴隶供给无关。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进口奴隶是因为气候条件适宜种植甘蔗、烟草等高附加值可以进行全球交易的商品。在巴西,金矿和银矿的存在是奴隶需求的一个决定因素。在撒哈拉北部、阿拉伯和波斯,盐矿需要奴隶劳动力。在红海地区,奴隶作为珍珠采集工人。
工具变量衡量了每个奴隶贸易中每个国家到最重要的目的地的距离。4个工具变量分别是:
(1)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距奴隶出口国家中心最近的海岸到最近的主要奴隶需求市场的航海距离,采用了9个最大的奴隶进口地,分别是美国弗吉尼亚、古巴哈瓦那、海地、牙买加金斯敦、多米尼加、马提尼克岛、英属圭亚那、巴西萨尔瓦多和巴西里约热内卢。
(2)印度洋奴隶贸易从距国家中心最近的海岸到最近的两个奴隶目的地(毛里求斯和阿曼马斯喀特)的航海距离。
(3)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从国家中心到最近出口港口的陆上距离。市场是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开罗。
(4)红海奴隶贸易从国家中心到最近的出口港口的陆上距离。港口为马萨瓦、萨瓦金、吉布提。
图5用4个奴隶需求地到布基纳法索的距离说明了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估计如表4所示。列(1)报告了没有控制变量的估计,列(2)报告了殖民者固定效应,列(3)和列(4)包括了殖民者固定效应和地理特征。列(4)舍去了岛国和北非国家的观测值。
第一阶段估计如表4下半部分所示。工具变量的系数一般是负的,说明一个国家距离奴隶市场越远,出口的奴隶越少。唯一的例外是从红海港口出发到市场的距离,统计上不显著,且在一个模型中出现正数。
第二阶段估计如表4上半部分所示。因为第一阶段F统计量降低,所以报告了条件似然比(CLR)的置信区间。单位土地面积奴隶出口数量自然对数变量的估计值全部都是统计显著的负数。第三列置信区间没有上下界,这是因为第一阶段F统计值较小造成的。点估计的区间从-0.20~-0.29。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著大于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鉴于奴隶出口的测量误差以及选择效应倾向于使得那些原先最发达的社会参与奴隶贸易,这二者都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偏向于0。因此,最小二乘法估计小于表4的估计毫不奇怪。
表4奴隶出口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估计
表4估计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到达奴隶市场的距离可能与到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地点的距离相关。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估计距离工具变量与非洲内外收入之间最简单的关系得到评估。可以发现,在非洲内部四个距离工具变量与收入正相关,并且除了红海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都是高度显著,距离奴隶市场越远增长越快。然而,在非洲之外不存在距离工具变量与收入之间的明显关系。如果表4的结论依赖于到达奴隶市场的距离与到达其他地点的距离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期望距离与非洲之外的收入存在正向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体而言,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进一步确认了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的奴隶出口和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还说明了最小二乘法估计可能低估了奴隶贸易一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
六、 因果关系的可能途径
现在转而考虑奴隶贸易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在此处的讨论只是初步和解释性的探讨。仅仅52个非洲国家的观测值无法确定不移地解释奴隶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背后的具体途径和机制。在此仅是简单考察数据是否与本文第二部分提供的历史事实相一致。
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削弱了村落之间的联系,因而妨害了更大的部落和更广的种族认同的形成。通过检验奴隶出口与Alesina等(2003)提供的当前种族分化冲突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数据是否与这个途径相一致。正如图6所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这与历史学家描述的奴隶贸易妨害了种族认同的形成相一致。

由于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种族分离冲突是影响经济发展必要条件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奴隶贸易的这一后果很重要。自Easterly&.Levine(1997)关于种族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之间联系的标志性文章发表以来,La Porta等(1999)、Alesina等(2003)、Aghion等(2004)、Easterly等(2006)的研究更加深入地考察了种族分化冲突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种族多样性对于社会凝聚力、国内制度、国内政策和政权质量都很重要。AJesina等(1999)、Miguel&Gugerty (2005)以及Banerjee&Somanathan (2006)的研究同样发现种族分化冲突降低了公共品的提供,例如教育、健康设施、水资源和交通基础设置等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
与奴隶贸易紧密关联的第二个后果是国家弱化和发展程度低下。为了检验数据是否与这一途径相一致,考察了奴隶贸易之后奴隶出口与国家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采用了Gennaioli&.Rainer (2006)的一个前殖民国家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这个指标基于Murdock(1967)以当地部落之外的司法层级数目衡量的关于当地种族部落之间的政治复杂性的种族学数据构建的。原始测量指标从0~4,0代表“无政府社会”,4代表“大政府社会”(Murdock 1967,第52页)。基于这些数据,Gennaioli&Rainer(2006)构建了测量一国当地人口属于状态2、3、4的种族部落比例指标。
奴隶出口和19世纪国家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如图7所示。图中所示关于奴隶出口与国家中央化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与历史学家阐述的奴隶贸易导致长期政治不稳定进而削弱和分裂国家的观点相一致。

最近的实证研究证明一国政权发展程度的历史是当前经济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Bockstette et al.(2002)以及Chanda&Putterman(2005)发现国家机构发展深度的衡量指标与1960-1995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速度正相关。Gennaioli&Rainer(2006)发现非洲内部前殖民时期具有中央集权国家机关的国家今天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例如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
Herbst(1997,2000)也注意到国家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非洲差劲的经济表现是后殖民时期国家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前殖民时期政治的落后和动荡。Herbst(2000,第2~4章)认为由于在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明显的政治发展,前殖民时期有限的政治结构延续到独立之后。后果是,独立之后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继承了一个没有巩固政权和控制全国的基础行政设施的国家。许多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正常征税,导致无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
Herbst观点的推论是奴隶贸易的影响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表现得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当前殖民时期的政治结构成为新独立国家成功的核心因素时,其重要程度突然提高。尽管低奴隶出口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即大多数国家还在殖民统治之下时更加富裕,两个组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显著扩大,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大多数国家都获得独立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与奴隶贸易影响国家形成的观点一致,虽然国家形成及其制度发展在殖民时期重要,但是在后殖民时期更加重要。这是由于受奴隶贸易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地区一般具有最落后的政治体系,独立之后这些国家依然处于贫弱和动荡的状态,经济发展相对而言也更加缓慢。
七、 结 论
结合海运记录数据和记载奴隶种族的历史文件,构建了在非洲四类奴隶贸易期间非洲每个国家输出奴隶的估计数量。发现在一个国家输出奴隶的数量与随后的经济发展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 采用了很多方法检验这一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如果是原先落后的国家才参与奴隶贸易,并且如果这些国家今天继续保持落后,那么这可能是解释观察到的奴隶出口与当前收入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回顾了关于遭受奴隶贸易最严重的一些非洲国家特征的历史证据。定性和定量的证据都表明实际上非洲最发达的地区而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更倾向于参与奴隶贸易。还利用从各个国家到达奴隶需求地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了奴隶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估计进一步肯定了最小二乘法结果,说明遭受奴隶贸易越严重经济表现越差。
检验了奴隶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背后的作用机理,发现关于奴隶贸易妨害更广泛的种族部落的形成进而导致种族分裂和贫弱落后的政治结构的历史描述与数据相符。
资料来源:Nunn,N.2008.The I_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Trad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lcs, 123 (1): 139 - 176.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第二部分
前沿问题
如何确定贫困线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度?
——一个关于乌干达的案例
Simon Appleton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
引 言
减贫是乌干达政府从第一个“减贫计划”以来制定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等机构的首要宗旨。为了衡量减贫的成果,首先需要指认哪些人可以划为贫困群体。传统的主要方法是确定一条贫困线,并将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界定为贫困。Appleton(2001)采用Ravallion和Bidani(1994)的方法确立的乌干达的贫困线被广泛接受。该贫困线被应用于由乌干达国家统计局(UBOS)主持的一系列家庭调查并据此公布乌干达的贫困率(乌干达的贫困率从1992年的超过50%降低到2005年和2006年的不足1/3)。本文将分析最新的家庭调查(UNHS-3),回顾计算贫困线的家庭调查(MS-1),并且评论乌干达目前的官方贫困线。
贫困线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食物贫困线,即基于一个满足热量需求的食物篮子估计的贫困线;另一部分是非食物贫困线,即基于一个同时满足其他需求的篮子估计的贫困线。乌干达的贫困线是根据1993年和1994年的家庭调查(MS-1)进行估计的。食物贫困线反映了当时最贫困的50%人口的食物篮子,非食物贫困线反映了他们的总体消费。经过各年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收入的调整,由此得到的贫困线将保持实际收入不变并与各年的收入相对应。虽然保持贫困线的实际收入不变对于记录生活水平的绝对变化很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线的相关性还是遭到了质疑。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贫困线的估计方法并说明出现的几个问题,尤其是下列问题特别重要:
(1)贫困线的食物篮子是否依然适用于乌干达,还是由于饮食习惯的较大改变已经不再适用了?
(2)贫困线的非食物篮子是否依然适用于乌干达,还是南于消费习惯的较大改变已经不再适用了?
(3)基于城市价格估计的CPI能否准确地反映农村贫困人口消费的价格?
第一部分回顾目前乌干达官方贫困线的估计方法,并进一步分析能否改进该方法。根据以上分析和最新的调查数据(2005年和2006年),本文将提出一条新的贫困线,并估计新的贫困率。这只是为相关方面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而非正式提出贫困线和贫困率的替代方案。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认为本文是探索性的研究。第一部分的技术性很强,贫困线和贫困率对于任何操作问题和数据问题都非常敏感。即使主要原则保持不变,咨询会议和评审意见也会促使研究人员显著地修正一些具体数值。另一个促使本文的一些建议成为探索性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一条贫困线的确定是一项复杂的统计工作,也是从本质上反映了关于满足体面生活的最低要求的主观判断性慨念。贫困线的确定可能影响政府配置资源的决策,例如向高贫困率的地区分配更多的资源。因此,相关利益主体将积极影响贫困的界定和测量。此类咨询过程还可能导致乌干达贫困线的进一步修订。
本文第二部分从跨时期问题转换到跨地区问题的考察,特别是探讨了贫困线是否应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内部的地区差异。现在的贫困线允许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非食物构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不同地区之间非食物价格的直接信息。然而,该贫困线却采用了一个统一的全国食物篮子估计食物贫困线,问题在于不同地区消费的食物种类可能不同,采用统一的国家食物篮子估计食物贫困线是否合适?采用地区性的食物篮子和地区贫困线作为替代是否合适?正如第一部分,尽管有很微妙的方面,该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笔者建议坚持采用统一的国家食物篮子,因为据此估计的贫困率能够更好地反映个人对资源的掌控及其他们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然而,地区性的食物篮子可能提供关于人们是否真正达到基本营养需求的更深刻信息,因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该问题最终依赖于一个人是关注于能力还是相信结果。
一、 更新的国家贫困线
1. 食物篮子的结构变化
乌干达贫困线以一个特定的食物篮子的成本为基础,即乌干达最贫困的50%人口消费的食物篮子。该食物篮子提供了基本生活所需的热量。给定该食物篮子是根据MS-1中观测到的消费数据确定的,那么问题在于至MS-1数据调查以来乌干达的食物消费习惯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表l报告了MS-1和UNHS-3基于乌干达贫困人口消费习惯的食物篮子,这两个食物篮子都提供了一个基准热量水平(3 000卡路里/天)。MS-1的食物篮子基于乌干达最贫困的50%人口——因为最初的分析认为贫困率接近该水平。然而,这个比率对于UNHS-3而言无疑太高,因为此次调查的统计贫困率约为1/3。因此,UNHS-3将食物篮子基于最贫困的1/3人口。出于可靠性的考虑,我们同样推导了UNHS-3的基于最贫困50%人口的食物篮子,并在后文中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MS-1数据估计乌干达目前的贫困线时是基于修正后的食物篮子而非原始的食物篮子。
表1 MS-I和UNHS-3的岔困人口合物篮子
注:MS-1,贫困人口定义为按照每人消费的实际食物排列最低50%人口;UNHS-3,贫困人口定义为按照每人消费的实际食物排列最低33%人口。
表1显示了两个食物篮子构成之间的一系列显著变化。UNHS-3食物篮子中主食的热量比MS-1食物篮子少5%,该部分由增加的油类、糖和动物产品弥补。两个食物篮子之间某些主食的数量也存在明显变化,高梁和粟的数量大幅减少——分别为70%和55%,红薯、木薯和香蕉也明显减少,玉米则大幅增加——食物篮子中玉米增加了149%。在UNHS-3数据中,玉米成为提供热量最多(23%)的一种食物,面包、稻米和爱尔兰土豆都在UNHS-3中以较大数量存在,但仍然是乌干达低收入人群获取热量的次要来源。
虽然食物篮子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估计贫困线而言重要的是食物篮子中食物总体成本的变化。相对于从MS-1估计的食物篮子而言,从UNHS-3估计的食物篮子从不变价格来看略微贵一些。然而,如果以UNHS-3价格计算,差异将非常小,仅为0.5%。UNHS-3食物篮子每月花费28 821先令,MS-1食物篮子每月花费28 690先令。如果以MS-1价格计算,差异会显著扩大。如果以MS-1价格计算UNHS-3食物篮子,UNHS -3食物篮子每月花费14 559先令,相对于MS-1食物篮子的花费(13 381先令)高了8.9%。以上差异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各种食物的消费数量倾向于向相对价格变化的相反方向变动。这与消费者增加消费价格增长较慢的食物相一致。例如,玉米的价格增长慢于其他一些主食如香蕉、木薯、高粱和粟,因此玉米将会替代香蕉、木薯、高梁和粟这些主食。
关于食物篮子结构分析的启示是食物消费习惯的变化虽然很大,但是其自身并不会导致乌干达食物贫困线发生重大修订。虽然食物篮子发生了变化,但是价格,至少是当前价格,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2. 与通货膨胀同步
从家庭调查数据对生活水平变化进行推论时,针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步。从家庭调查数据可估计出名义收入和名义消费。CPI是获取真实价值最常见的平减指数,乌干达目前的贫困率统计中也在使用CPI作为平减指数。表2报告了调查期间CPI的平均值(包括调查前一个月)。整体而言,CPI表明UNHS-3期间的价格水平比MS-1期间的价格水平高73.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食物和饮料的价格水平相对于非食物的价格水平上升得更快,前者高了90.6%,后者高了51.8%。这意味着UNHS-3期间的食物价格相对于非食物价格比MS-1期间高了25.5%。但是乌干达的CPI只记录了主要城市中心的价格,因而不能用来调整价格水平的地区间变化(如城乡之间的价格变化)。如果以此调整通货膨胀就隐含着假设全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一样。
表2调查时期的CPI数据(1998=100)
注:MS一1原始CPI数据基于1989年9月=100; UNHS-3原始CPI数据基于1998年=100。两个序列在1998年1~10月重合,以1989年价格汁算的CPI平均值为319.03,以1998年价格计算的CPI平均值为95.83。因此,我们将MS -1数据转化为1998年价格需要除以3.239(=319.03/95.83)。
乌干达贫困率的估计基于家庭调查数据中购买食物的单位价格而估计的食物价格对地区之间的物价差异进行了调整。这些单位价格被用来构建8个地点的食物价格指数(4个行政地区各自的农村和城市),并作为平减指数把名义食物消费调整为不变价格下的食物消费。该方法不适用于非食物价格的调整,因为家庭调查报告了大多数非食物的价值但没有报告数量。因而假设非食物价格水平全国相同且与CPI中的非食物价值同步变化。
把食物价格指数与CPI相比可以用来检验全国平均价格与主要城市中心价格是否同步运动的假设。表3(a)报告了根据家庭调查数据构建的食物单位价格指数数据。从全国整体来看,CPI和食物价格指数估计的食物价格通货膨胀率相一致。食物价格指数表明在MS-1和UNHS-3期间通货膨胀率(86%)慢于CPI(91%)。然而,不同地区之间的食物单位价格增长幅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最低增长幅度(在MS-1和UNHS-3期间增长79%)是中部城市。中部农村表现出与中部城市几乎相同的增长率(80%),东部城市也存在微小差异(84%),其他地区食物价格增长水平快于CPI增长水平,东部农村(价格增长122%)和西部地区尤其显著。一般而言,食物价格在MS-1期间高的地区倾向于增长较慢(中部地区和东部城市)。这降低了食物价格在全国各地的分散程度。表3(a)最后两行记录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虽然中部地区依然具有最高的食物价格,北部农村地区具有最低的食物价格,二者之间的差异缩小了。东部农村的食物价格曾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在UNHS-3期间差异只有5%。西部农村地区的同类差异也从21%降至11%。地区之间食物价格差异的缩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地区之间交通的发展和市场一体化的进步。
表3地区食物单位价值指数
表4报告了我们使用入户调查数据和食品物价指数调整食品消费而得到的贫困率估计值。这些估计结果可以与根据乌干达估计贫困率的现行方法计算得到的同类结果(表5)进行对比。整体而言,无论是用CPI还是用食品价格指数来对跨期价格变动进行调整,对贫困率影响不大。用食品价格指数意味着从MS-1期间到UNHS-3期间的略为少一些的贫困率下降,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仅下降18.8个百分点(从51.9%降至33.1%),而用CPI计算该贫困率则下降19.6百分点。这个差异更多地产生于东部农村地区,较少地发生于中部地区。前文曾讨论过东部地区的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得最多。
表4采用家庭事务价格指数而非CPI作为平减指数的贫困率
(a) MS-1, 1993/1994
(b)UNHS-3,2005/2006
表5采用目前的方法估计的贫困率
(a)MS-1,1993/1994
(b)UNHS-3,2005/2006
食物价格指数以乌干达所有人口的平均消费习惯为权重。如果只关注乌干达贫困人口的消费习惯,MS-1中最贫困50%人口消费的食物篮子,那么结果将不同。例如,考虑MS-1期间最贫困的50%人口消费的食物篮子,如果以家庭调查的全国平均单位价格计算该篮子的价格,UNHS-3期间该食物篮子的价格比MS-1期间的价格高114%,这大大高于CPI的增幅(93%)和食物价格指数的增幅(86%)。同理,UNHS-3期间最贫困50%人口消费的食物篮子的价格比MS-1期间的价格高98%。这些结果意味着贫困人口消费的食物的价格比总体食物的价格上升得更快。乌干达当前的贫困率统计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此低估了全国贫困水平,从而为重新修订当前贫困线提供了理由。
3. 转化因子及重新修订1993年和1994年食物贫困线的必要性
基于UNHS-3数据提供的关于食物消费习惯演化和食物价格变化的信息,本文第一部分第2节和第3节为修订乌干达贫困线提供了论据。然而,通过审查原来的食物贫困线和基于UNHS-3数据估计新的食物贫困线,我们还修订了基于MS-1数据的食物贫困线。表6报告了食物贫困线的修订推导过程,表7报告了原来的推导过程以作比较。修订包括了一系列抽样和价格处理的微小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来自于关于红薯及其转化因子的技术问题。
表6 MS-1修订食物贫困线的推导过程
表7 MS-1原先食物贫困线推导过程
目前,食物贫困线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其基于一个红薯所占比例最高的食物篮子。这很出乎意料,因为一般认为香蕉是更重要的主食。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红薯的高比例是由于采用了一个不合理的转化因子。转换因子将调查对象回答食物消费时采用的非标准计量单位(堆、捆等)转化为标准的计量单位。在确定乌干达目前的贫困线时要求尽量减少对于转换因子的依赖,转而采用标准的计量单位。每千克的价格估计是从调查中获得的数据推导而来的,并被用来根据被调查家庭报告的购买价值估计购买的数量。但是该方法应用于红薯时导致了严重的偏误。
就红薯而言,实际上没有以计量单位报告的观测值,只有以迪贝斯(debes)为单位报告的合理的购买数量。因为1迪贝斯相对于1堆而言是一个更准确的数量单位,所以每千克红薯的价格是基于迪贝斯而不是堆的单位价格估计的。该方法不适用于UNHS-3数据,因为没有任何家庭以迪贝斯为单位报告购买数量。但是UNHS-3数据的市场调查员记录了购买的食物数量,并且为一系列数量单位推导出了转换因子。所有地区通用的唯一单位是堆,堆的大小各地不同,从北部农村的1.45千克到中部城市的3千克不等。如果将这些转换因子应用于家庭调查报告中以堆报告的购买数量,我们将得到MS-l中位数价格为114先令/千克,UNHS-3中位数价格为251先令/千克。这远高于MS-1采用迪贝斯为单位报告的购买数量的中位数价格64先令/千克。因此,很可能以迪贝斯为单位购买红薯存在批量购买折扣。采用折扣价确定贫困线是不合理的,因为批量购买红薯的家庭很少,而且贫困家庭中批量购买的更不可能(表8)。
表8采用MS-1修订贫困线估计的MS-1贫困率
当修订MS-l数据的食物篮子和食物贫困线时,决定采用以堆而非迪贝斯为单位的红薯消费量数据,从而降低了红薯在食物篮子中的比例,但提高了其价格。修订后的食物贫困线比原先的食物贫困线高20%-其中,这一增量的2/3源于对红薯的处理方法。这一贫困线增量的其余来源可能是由于采用单位价格均值代替了单位价格中位数的缘故。表9报告了以更高的贫困线估计的1993年和1994年的贫困率。食物贫困线的修订对于贫困人口数量具有重大影响,从52%上升到63%。这是贫困率估计过程中对于操作中技术性问题的敏感性的典型例子。
表9 UNHS-3食物贫困线推导过程
4. 基于2005年和2006年数据的新食物贫困线
本文第一部分的第1、2节建议重新修订食物贫困线以分别反映乌干达居民食物消费习惯的变化以及贫困人口消费物价的更为准确的变化,第3节说明由于技术性问题重新修订是必要的,尤其是计量红薯消费量的转换因子。本节在上述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2005年和2006年乌干达新的食物贫困线。新的贫困线基于UNHS-3数据中乌干达最贫困的1/3人口消费的食物篮子,目的是反映消费习惯的变化。新的贫困线根据2005年和2006年家庭调查的估计值计算价格,而非根据CPI计算价格。表9报告了新贫困线的推导过程,以2005年和2006年价格计算,给出的贫困线每个成年人每月为27 190先令。这相对于以1993年和1994年价格计算的旧食物贫困线11 463先令高了137%,相对于第3节讨论的修订后的MS-1食物贫困线高了99%。
表10将新的食物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与旧的非食物贫困线(调整通货膨胀)估计的贫困率结合起来。这意味着UNHS -3数据中42%的乌干达居民处于贫困状态,旧的估计认为31%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新食物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相对于旧的贫困线更高。第一,相对于CPI和当前贫困线的估计而言,贫困人口所消费食品的价格似乎增长得更快;第二,目前的贫困线低估了红薯的价格,并且高估了红薯在食物篮子中的比例。
表10 UNHS-3新的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UNHS-3,最贫困 的1/3人口)
与旧的非食物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
采用新的食物贫困线和旧的非食物贫困线并非因为保守,只是因为非食物贫困线是食物贫困线的参照标准。如果食物贫困线正如所说的那样应该上升,那么也会导致非食物贫闲线的上升。
5. 上升的非食物贫困线
在确定乌干达贫困线时,非食物消费构成并没有细化到各类物品,这与食物贫困线的详细推导过程相反。虽然Rowntree在19世纪为约克郡估计的第一条贫困线中非食物贫网线对非食物物品的类别做出详细的划分,但是据本文作者所知从那以来试图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并没有进行相应的研究。问题在于试图具体估计非食物贫困线需要关于许多琐碎的物品价值的判断。例如,Rowntree需要决定孩子是否需要两双鞋。就食物而言,卡路里可以作为确定需要的标准,但是就非食物而言不存在相应的标准。与试图细化非食物物品需求类别相反,现在实际的做法是基于非食物支出的比例确定相应的份额。例如,对于乌干达贫困线而言,非食物贫困线是通过那些恰好处于食物贫困线的人的非食物支出进行估计,并以此作为非食物贫困线。
确定非食物贫闲线的方法使得其依赖于非食物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在乌干达,这个比例从贫困确定以来已经上升了很多。在MS-1中,那些恰好处于贫困线的人花费43%在非食物支出上。在UNHS-3中,这一比例上升到60%。非食物支出比例的增长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家庭调查的简单总结统计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给定乌干达的收入增长,食物消费支出的比例下降是在预料之中的。食物支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下降是如此广泛的一个现象,以致被冠之为“恩格尔定律”。然而,恩格尔定律不能简单地解释那些恰好处于食物贫困线的人口的食物支出比例下降的现象,因为我们估计食物贫困线时保持收入不变。恩格尔定律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运行而非针对个人: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即使是收入保持不变的个人也倾向于增加非食物支出。社会习俗和期望可能改变,所以更高水平的衣着、教育和住宿将被认为是必需的。关于非食物支出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价格:正如上文所讨论,在MS-1和UNHS-3之间食物价格相对于非食物价格的CPI上升了26%。这会导致家庭选择消费更多的非食物。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非食物日益便捷的消费渠道——例如手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非食物支出的增加在所有主要的非食物物品和服务中都被观察到。问卷的调整不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非食物支出的大幅增加意味着在贫困线的构成中非食物的比例也大幅增加。表11提供了2005年6月乌干达估计的新的贫闲线,采用了本文第4节推导而来的食物贫困线以及对那些收入等于贫困线的人口估计的非食物支出比例。结合新估计的非食物贫困线和新的食物贫困线得到一条新的贫困线,以2005年6月价格计算43 254先令每个成年人每月。这可以与目前的以1993年和1994年价格计算的16 444先令贫闲线相比。新的贫困线相对于原先的贫困线在名义价格上高了165%,在此期间CPI增加了73.5%。
表11食物比例与2005年和21106年新贫困线推导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估计相对于目前的官方贫困线而言意味着更加宽裕的非食物支出。如果我们接受在本文上节估计的新贫困线,并允许60%的开支用于非食物,那么用于非食物的支出在名义价格上将高于目前贫困线的228%。给定CPI记录的非食物价格增长为75%,这导致在实际水平上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长。这可能是采用目前贫困线所使用的方法去更新乌干达贫困线的最重大的问题。这种方法只是确定一个绝对的贫困线,但是更新贫困下的结果使得乌干达贫困线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随着乌干达收入增长,其贫困线也将增长。
6. 综合: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估计
新贫困线估计的乌干达贫困率相对于目前的贫困线高很多(表12)。例如,2005年6月生活在新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为56%,生活在目前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为31%。1993年和1994年,生活在新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为78%,生活在目前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为51%。新贫困线还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贫困率的大幅下降——无论采用哪一条贫困线,贫困率都下降了20%~22%。
在解释新贫困线之下的贫困率更高时需要注意几点,虽然两条贫困线都以满足卡路里需求为标准,新贫困线允许更高非食物需求。总体而言,在新贫困线之下,非贫困人口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准。因此,新贫困线之下的贫困率与原先贫困线之下的贫困率不是直接可比的,至少在对贫困人口的绝对生活标准进行推断时应该如此。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贫困线修订时考虑了相对贫困问题。贫困线告诉我们的只是在给定典型饮食模式和食物比例的情况下乌干达的低收人家庭需要多少收入才能满足热量需求。相对于1993年、1994年而言,2005年、2006年时乌干达家庭增加了非食物方面的支出,因此需要更高的收人才能保证他们摄入充足的热量。这一点在其自身看来并不奇怪。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非食物支出增加的程度,乌干达的低收入家庭,不管总消费的增长情况,真实食物消费没有增长太多甚至略有下降。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新贫困线之下估计的2005年和2006年贫困率高于在原先贫困线之下估计的1993年和1994年贫困率。乌干达贫困人口摄人的卡路里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非食物支出。在重新贫困线修订时,非食物支出增加被认为是当然的,所以并不会降低贫困率。
表12新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
(a) MS-1的估计,1993/1994
(b) UNHS-3的估计,2005/2006
二、 地区贫困线
1. 国家食物贫困线下的地区差异和趋势
乌干达4个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以及贫困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部最发达,西部、东部居其次,北部最落后。1993年和1994年该现象已很明显,并且该趋势随着时间进一步强化。我们根据目前官方贫困线回顾该趋势(表5),本文第一部分无论是目前官方贫困线还是新的贫困线都将国家作为整体采用统一的食物篮子,只允许非食物需求存在地区差异。
北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乌干达其他地区,减贫进度缓慢。北部每个成年人真实消费只有1.5%的年增长率——低于全国增长率(3.4%)的一半。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北部地区贫困率的降低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大幅度贫困率下降而显得太慢。根据目前官方贫困线,2005年和2006年乌干达北部还有60%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1993年和1994年也只有68%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国家贫困率在此期间从53%降低到33%。
乌干达的其他3个地区,西部地区表现最好,真实消费增长率为4.5%-远高于中部(3.4%)和东部(3.6%)。这些趋势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在贫困率方面与东部地区拉开距离,越来越接近于中部地区。根据官方贫困线,1993年和1994年贫困人口中部为34%,西部为54%,东部为59%。2005年和2006年贫困人口中部为18%,西部为24%,东部为37%。 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异交错。乌干达城市人口集中在中部地区。因此,乌干达分为8个地区更加合适-4个城市地区和4个农村地区。总体而言,城市地区经历的消费增长和减贫相对于农村地区更加缓慢。中部城市的真实消费年增长率平均为2.1%,使得中部地区的增长率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很高(4.0%),与西部农村的增长率相近(4.3%)。西部和东部的城市地区增长强劲(分别为4.8%和3.9%)。相反,北部城市地区的增长疲软,人均增长率仅为0.6%,贫困人口实际从1993年和1994年的36%增长至2005年和2006年的39%。
采用第一部分新的贫困线使所有上述贫困率增加,但是大多数定性结论保持不变。一个例外是北部城市地区贫困人口上升的结论。根据新的更高的贫困线,北部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在1993年和1994年之间下降而非上升。
2. 简单的地区贫困线
乌干达目前贫困线基于一个全国同统一的食物篮子。虽然贫困线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食物比例与非食物比例存在差异,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食物种类并不存在差异。这提出了贫困线在不同地区的符合程度问题。乌干达至少有6种主食,但是它们的消费在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变化。一个全国统一的食物篮子不可能很好地描述乌干达贫困人口消费的实际食物篮子。各种主食在获取一定的热量时所需要付出的价格不同,使得地区之间的差异极其重要。结果是,一个全国性食物篮子可能比一些地区性食物篮子便宜,而比另一些地区性食物篮子昂贵。
乌干达在饮食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区变化。一些主食全国都食用,如红薯、木薯和玉米。然而,另一些如高梁和粟只在东部和北部的特定地区才会食用。更有甚者,香蕉作为一种主食在乌干达北部地区完全不能生长,因而在北部几乎没有人食用香蕉。地区之间在主食消费方面的差异可能很重要,因为主食在提供同样的热量时所需要的价格不同。例如,在乌干达高梁是一种能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热量的主食,而香蕉则是一种昂贵的主食。
Jamal(1998)的研究认为采用地区食物篮子而非全国统一的食物篮子可以大幅改变乌干达贫困率的地区间结构。Jamal在1989年和1990年基于每个地区食物篮子结构的简单假设估讣贫困率,中部农村以及西部和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昂贵的香蕉获取热量,北部地区主要通过廉价的粟获取热量。基于地区食物篮子,Jamal认为东部农村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北部农村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差别不大。该结果与目前乌干达官方贫困线的贫困结构迥异,根据官方贫困线,北部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贫困水平排名的差异不是因为福利的空间分布在时间中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是因为采用了地区而不是全国性的食物篮子。
我们可以通过2005年和2006年乌干达最贫困的1/3人口的饮食习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来认识食物消费的空间差异。表13给出了地区食物篮子,它采用乌干达各个地区最贫困1/3人口(根据真实人均消费排名)的平均消费,并据此估计各种不同食物提供热量的比例。玉米和木薯为穷人提供了最多的热量,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很重要。红薯和豆类在全国所有地区都被大量消费,虽然其相对比例变化很大。红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占主导地位,豆类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占主导地位。香蕉和高粱的主要消费地区不同,甜香蕉是西部和中部农村地区的主要热量来源,分别提供了26%和11%的热量。然而,香蕉在北部和东部很少消费。高粱为北部农村提供了7.5%的热量,在中部农村很少消费。
表13 2005年和2006年乌干达最贫困1/3人口的地区食物篮子结构 单位: %
这些食物篮子的地区差异可能很重要,因为主食提供热量的价格不同。基于2005年和2006年调查的价格,我们可以从表8计算热量价格。高粱、玉米和木薯是最廉价的热量来源,5~6先令/卡路里。红薯、干豆和粟是中等,10先令/卡路里。甜香蕉是最昂贵的主食,14.5先令/卡路里。
根据每个地区贫困人口的典型食物篮子以及获得充分热量所需要的成本,我们可以利用表13的信息推导出地区食物贫困线。我们采用每天获取3 000卡路里所需要的价格作为贫困线(我们以从事维持生存的农业的男性所需热量作为标准)。表14报告了据此而来的及不变价格(调查的中位数价格)计算的简单的地区食物贫困线。这些地区食物贫困线通过与国家食物贫困线比较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最低食物贫困线是北部农村,比全国食物贫闲线低20%。这反映了北部地区食物篮子缺少昂贵的香蕉,大部分热量通过廉价的高粱获得。相反,西部农村的食物贫困线比全国贫困线高23%,反映该地大量消费香蕉。中部农村消费的香蕉少于西部农村,食物贫困线比全国贫困线高10%。东部农村食物贫困线与全国食物贫困线相近。东部不消费香蕉,但是因为收入高,所以比北部农村食物贫困线高。
为了理解这对所估计的贫困率的意义,我们需要设定非食物需求,进而得到总的贫困线。与估计全国贫困线的情况一致,我们以总消费恰好满足热量需求的家庭的非食物支出估计非食物贫困线。该估计来自于一个关于食物比例的简单模型(Ravallion和Bidani,1994)。在解释变量中控制收入和7个地区解释变量(4个地区,城市和农村,其中一个地区作为基准组),在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每个地区的拟合值。表14报告了据此估计的地区贫困线,包括非食物需求在内的总贫困线基本没有改变地区之间的相对贫困状况。相反,主要的效应是使得城市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贫困线提高了,因为城市家庭相对于农村家庭在相同的食物支出的情况下倾向于更多的非食物支出。
表14 2005年和2006年乌干达地区贫困线——简单的和收 入调整的 单位:先令
表15报告了2005年和2006年基于简单的地区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无论采用国家食物篮子还是地区食物篮子,全国总贫困率都很稳定。然而,贫困率的空间分布对此却很敏感。采用地区贫困线替代全国贫困线将导致城市贫困率大幅上升,从15%上升至28%,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城市地区贫困率的大幅增加,从9%上升至19%。更一般地说,采用地区贫困线导致中部地区总体贫困率估计值显著上升(从29%上升至43%)以及北部地区贫困率估计值显著下降(从81%下降至69%)。Jamal(1998)基于乌干达1989年和1990年的数据和地区贫困线关于贫困率的估计与世界银行(1993)基于同一数据和乌干达全国贫困线的估计之间的差异与本文上述的对比差异类似。使用地区贫困线还是全国贫困线对于乌干达贫困率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表15 2005年和2006年基于简单的地区贫困线的贫困率
3. 收入调整后的地区贫困线
地区食物篮子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只反映收入差异程度。只是因为城市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收入更高才使得这些地区的食物篮子更加昂贵吗?虽然我们把关注焦点局限于乌干达最贫困50%人口的饮食以尽量减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即使是在这一半人口中收入差异的空间模式依然在整个样本都存在。即使就最贫困的一半人口而言,城市地区的家庭仍然比农村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北部地区的家庭拥有最低的平均收入,中部地区拥有最高的平均收入。中部地区低收入家庭的食物篮子可能包括更加昂贵的主食,因为这些家庭虽然是低收入,但是比其他地区的低收人家庭状况好得多。
不受地区收入差异影响的地区贫困线可以通过构建关于收入的食物函数来建立。这允许我们在一个共同收入标准上预测地区消费的差异。这个方法与Ravallion和Bidani(1994)提出的估计非食物贫困线的方法相似。问题在于哪一收入水平应该作为估计地区食物篮子的基础。国家食物贫困线是基于低收人人口的食物篮子构筑的,那些在收入分布底层的50%人口可由按相当于成人的人均消费来排列。因此,我们是在乌干达最贫困50%人口的平均收入上预测地区食物篮子。我们在构建国家贫困线时包括了27种食物,但是为了简单化,在考虑地区消费差异时只包括了6种热量的主要来源,6种食物包括5种主食(玉米、木薯、香蕉、红薯和高梁)以及干豆。这些食物为乌干达穷人提供了75%的热量。我们对待不在为入列食品的食物的方法与我们构建国家食物贫困线时的做法相同,并且在每个地区的食物篮子中放置相同比例的上述未入列食品。对比之下,我们基于乌干达最贫困1/3人口的平均收入分别预测每个地区6种食物中每种食物的消费。我们按比例增加所预测的食物的数量直到根据WHO标准这些食品充分满足热量需求的75%。这一分析中的关键步骤是估计6种主食中每种的消费数量(千克)。我们采用Tobit模型以允许数据中高比例0值的存在、并且防止所预测数值中负值的出现。在解释变量中,收入和地区等控制变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家庭相当于成人人均消费量的对数值及其平方控制收入,地区通过7个虚拟变量进行控制。从Tobit模型,我们预测出在家庭收入等于乌干达最贫困50%人口的平均值时每个地区消费的主食数量。
为了估计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贫困线,我们采用表8的贫困人口的食物篮子并据此估计提供75%热量需求的成本。这部分成本与提供其余25%热量需求的非主食的成本加总,一起构成国家贫困线。结果得到表14以2005年和2006年价格计算的估计贫困线的第三种方法。这里报告的是总贫困线,其中,非食物贫困线同样也依据Ravallion和Bidani(1994)的方法通过估计食物消费恰好等于食物贫困线的家庭的非食物支出得到。即使在控制收入的情况下,地区之间因为消费主食种类不同也会导致满足热量需求的不同成本。这可以通过比较基于国家食物篮子和经过收入调整后的地区食物篮子的贫困线得知。中部农村的食物贫困线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一样。然而,西部农村严重依赖于昂贵的热量来源香蕉,导致经过收入调整后的食物贫困线高于国家食物贫困线13%。相反,北部农村和东部农村不食用香蕉,经过收入调整的食物贫困线分别低于国家食物贫困线6%和7%。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经过收入调整的食物贫困线明显不同于简单的地区食物贫困线。特别地,所谓的简单的食物贫困线意味着一个极高的中部地区食物贫困线,但是我们对收入调整后,这个极高的食物贫困线就消失了。控制收入也消除了东部农村和北部农村之间的食物贫困线的差异。
表16报告了采用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食物篮子得到的2005年和2006年贫困率。总的影响是提高食用香蕉的西部地区的贫困率,并轻微降低其他地区的贫困率。与国家贫困线相比,部分贫困率的变化很大。西部农村按人头计算的贫困率从按国家食物篮子计算的49%上升到按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食物篮子计算的57%。北部农村的贫困率从85%降低到81%。有趣的是城市地区的贫困率远远低于以简单的地区贫困线估计的贫困率。这意味着即使是乌干达的低收入人口,城市食物篮子相对于农村食物篮子更加昂贵,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差异而不是饮食偏好。与此类似,由于使用简单的地区食物篮子而导致的中部地区贫困率上升也仅仅是收入效应作用的结果。
表16 2005年和2006年基于收入调整的地区贫困线的贫困率
4. 我们应该允许食物篮子的地区变化吗?——规范问题
我们已经发现允许食物篮子的地区变化导致乌干达贫困率空间模式的巨大变化。然而,虽然采用地区食物篮子将导致巨大变化,但是并不一定非要采用地区食物篮子。是地区食物篮子还是国家食物篮子更优先?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食物篮子显然优于简单的食物篮子。如果一个家庭相对于另一个家庭选择消费更加昂贵的食物只是仅仅因为更高的收入,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设定一个更高的贫困线。在乌干达,采用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食物篮子与采用简单的地区食物篮子得到不同的贫困率估计值。特别是城市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食物篮子更加昂贵是因为收入差异而非饮食偏好。
(经过收入调整的)地区食物篮子是否应该在确定贫困线时采用?这最终是一个微妙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不含争议的技术问题。这取决于一个人怎么评价福利。关注地区食物篮子是由于满足实际食物需求的重要性。这自然与人们关于满足人类各种基本需求的角度一般性考虑贫困问题结合在一起。近年来,福利多维性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也许还存在关于福利到底具有几重维度的争论以及维度之间如何相互转化的争论,但是像乌干达这样的低收入国家基本食物需求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如果这一点被接受,那么一国的某些地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热量需求可能会导致争议。这其实是在某些地区确定一条更高的贫困的理南。
以乌干达为例,根据地区食物篮子差异确定贫困线的理由如下。在乌干达西部,人们习惯上更喜欢香蕉(一种昂贵的提供热量的来源)。结果是在其他条件(如健康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给定一定的收入这个地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营养状况更加糟糕。至少在营养的维度上,西部地区更加贫困,甚至可能牺牲其他领域的福利来满足基本的营养目标。如果营养水平没有被充分满足,人们可以预期这会对其他维度的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如糟糕的营养状况导致健康受损;或者是间接的,如糟糕的营养状况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以上讨论支持了地区贫困线应该反映当地食物篮子的论点,因为食物篮子将影响需要多少收入来满足多维福利的理想需求。
那么,反对地区食物篮子的理由是什么?一些习惯于认为福利只是单一“效用”而非多维的经济学家会提出反对意见。效用可以间接地解释为与心理状态(如幸福)相关或者偏好满足。二者都不会对满足热量需求产生特别意义。热量标准经常被用来确定贫困线,其实热量标准本身并不重要,只是用来解决确定贫困线时遇到的“标准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乌干达西部地区实际选择低热量的食物篮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乌干达西部居民可以购买便宜的食品达到热量需求。乌干达西部居民可以被认为是通过其他福利弥补热量摄入不足。这些福利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如乌干达西部居民从他们偏好的食物篮子中获得热量之外的心理享受。或者不需要探讨消费者的消费动机:乌干达西部居民偏好他们实际的食物篮子的事实意味着他们的福利至少与他们选择另外一个更多热量的食物篮子的福利相同。如果给定特定的心理习惯,反对地区食物篮子的辩论无疑是正确的。乌干达西部居民可能从以香蕉为主的饮食模式中获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类似收入水平居民的饮食模式更多的效用。然而,人际比较是否能够证明他们相对于相近收入的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享受其食物还不清楚。食物的偏好可能受童年以及以后的习惯的影响,对于某一食物形成偏好的人会偏好这一食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对于其他偏好另一种食物的人更加享受他们偏好的食物。反对采用地区食物篮子确定贫困线的各种论点都是基于以偏好而非特定心理习惯解释的效用。
因此,地区和国家贫困线的问题可以部分的归于一个人的福利观念。那些认为福利是偏好(效用)的人选择国家贫困线,那些认为福利是多维的人倾向于选择地区贫困线(如果他们对于如何评价福利的货币数量标准感兴趣的话)。选择可以通过区分以下事实进行解释。选择可能会被食物需求的实际满足还是满足食物需求的能力所影响。给定偏好香蕉的饮食模式,在收入确定情况下乌干达西部居民实际满足以热量衡量的食物需求的能力低于拥有相同收入的乌干达北部居民。然而,乌于达西部居民在心理上与将收入换取低廉热量来源的乌干达北部居民一样满足。应该以最后结果还是以能力衡量福利?用Sen(1985)的术语来说就是应该关注功能还是能力的问题。在由Sen的研究引发的大多数非技术性的文献中,“功能”和“能力”是同义词,但是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 Simon Appleton,How sensitive should poverty lines be totime and space? An application to Uganda. manchester.ac.uk, 2009.9.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贸易与贫困
——贸易援助如何减少贫困
摘要:经济增长是最有力的消除贫困的武器。事实上,每一个创造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成功地抓住了逐渐开放的世界市场中的商机。但是,还有许多低收入国家被如何扩展和丰富他们的贸易而困扰。除此之外,贸易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能在贸易扩展、经济增长以及消除贫困上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改革和自由化所造成的影响是不一而足的,主要与贫困人口的消费习惯,以及贸易是否能拉动穷人聚居地区以及大量就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有关。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国际社会依然认为扩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提供贸易援助是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帮助其建立供应方面的能力和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才能使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获益。
贸易援助,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是一种紧密联系援助项目和贸易政策的实施工具。它应当帮助保证贸易政策的收益突出,特别是当政策自身不足以自动在贸易过程中产生预期的收益时。 虽然,贸易相关的援助已被提及多时,但是只有少数双边援助国家对他们的援助项目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意在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到贸易有关的活动中的项目更是少之又少。基于减贫目的的贸易援助需要被人们更好地了解。援助机构急需将贸易专家的意见纳入国际项目和实施团队中。这种由经合组织提出的贸易发展的主流,承诺援助者将提供额外的资源来帮助低收入国家挣脱紧绑的贸易束缚,以便千年计划的实现。
该研究的目的就是使援助国和参与国都意识到贸易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潜在贡献,实现这种潜力的挑战以及贸易援助在解决这些挑战中的角色。这篇文章为援助国提供“更好更多的”贸易援助提供了一个基本原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援助在扶贫开发战略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具。
本研究后续内容展示了为什么贸易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有章节谈到虽然有许多国家在贸易中获利,但是也有国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下一部分是分析贸易援助是如何增强贸易对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影响的,以及哪些政策工具对减贫是最有效果的。随后的一章说明了经济一体化需要一条紧扣国情的特色化道路。最后的段落总结了主要的政策工具以及在有风险的大环境下的潜在收益。
一、 贸易的重要性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是产生财富的重要源泉,它也是自我维持式的增长以及减少贫困的重要方式。
(一)贸易改革与增长
说到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创新与增长联系起来,但是涉及贸易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太了解。事实上,贸易与贸易自由化从以下5个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创新。
1. 增加竞争
生产力增长不仅来源于技术改进也受益于效率的提升。贸易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会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强烈地刺激新技术的采用。
2. 技术转移
无论是直接外国投资带来新兴技术,或者是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便利的途径获得技术,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更快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竞争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3. 规模经济
广阔的国际市场让企业更加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和快速收回研发投资成本。
4. 全球利益链
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全球技术标准,让人们了解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对低成本供应商的不利影响,以及鼓励贸易的便利化,以便供应商可以对发展需求做出快速反应等,贸易和贸易改革可以帮助形成全球化分散生产的格局。
5.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自己增强创新都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二)贸易与消除贫困
由于运输与沟通的成本降低,从1980年起,国际货物与服务的贸易不断升温,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化,有许多的历史事实显示了贸易与消减贫困和经济增长呈现正向相关性。然而,案例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内的社会群体都能从贸易中获得成功。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中低收入国家致力于贸易壁垒的消减,但是却没有在这些国家形成持续的出口增长。这些案例表明,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限制住了贸易减少贫困的影响。经济理论认为,贸易通过提升要素价格,增加低技术水平劳工的收入可以直接减少贫困。但实际更加复杂,贸易对消除贫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资水平与就业方面,也取决于口岸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政府收支的改变等多个方面。而贫困人口是否能有效参与到贸易活动中,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①贸易多大程度上引导了贫困人口大量就业的部门的增长;②贸易引起的增长是否直接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③增长是否能带动其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部门的增长;④贫穷人口是否具有胜任新工作的素质。当然,这些都不应该影响到援助团体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视,只是得更加了解并且解决贸易不能发挥出它的潜能的情况。
二、 贸易的限制因素
虽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市场扩张中受益,但有些低收入国家依然面对如何增加出口量和丰富出口产品的困境。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全球比例甚至有所下降,他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呢?主要有来自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的阻碍。
最主要的外部障碍是,多边贸易国不能就以何种形式消减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国家内部的贸易政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贸易的能力。自乌拉圭回合以后,OECD国家间关税的下降程度远大于其与非OECD国家间关税的减少。另外,关税升级政策阻碍了穷国参与到更加长期和更高附加值的市场利益链中。除此之外,非关税壁垒也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贸易壁垒也有待削减。因为这些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减少相对价格变动的幅度以及结构性调整的成本。这也为中低收入国家逐步学习和发展规模经济,进入高附加值市场提供了可能。
除了持续存在的外部限制因素外,由于低人力资本、糟糕的政府和机构、缺乏激励机制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的基础结构的薄弱和供给能力的缺乏,再加上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的瓶颈,以上就是低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开拓其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不错的出口表现特别依赖于相关机构的有效运转、有良好的运输与信息基础设施。由于这些方面都比较缺乏,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就远高于发达国家。
要建立良好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体制僵化,不能灵活有效地重新配置资源,增加了调整的时间和成本。这主要是因为缺少必要的金融服务,垄断的资源分配结构又限制了公司自由进出市场从而阻碍新部门的生成等因素造成的。
正如之前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增长正相关,但受到国内政策的巨大影响。而国内政策又限制着这些国家贸易改革的推进,原因是它们自身的脆弱性。主要表现有以下4个方面:①进口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②多边贸易自由化会削弱本该给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③关税的减少会导致政府收入的下降;④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国内经济调整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短期内,不可预知的调整压力通常不是来自贸易自由化,而是来自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汇率的变动。快速的技术进步也会形成调整的压力。因此,一国经济必须要更加富有弹性,才能更好参与新的经济活动和扩展已有的经济活动。
三、 贸易援助
贸易是形成自我维持式增长的重要“武器”,但只是贸易自由化和强化市场渠道而不培养相关国家的贸易能力是不能有效达成目的的。而贸易援助就是以帮助被援助国家建立贸易能力,减少贫困,并且融人世界经济为目标的。WTO发布的共识的序言中就指出,国际社会需要将能够让多方参与主体“提高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列为自己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也致力于完成发展中国家多方面的贸易改革和全球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才形成了多哈发展议程以及香港宣言的相关内容。
贸易援助计划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克服制度限制,扩展其薄弱的生产和竞争能力以及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以及投资中获利的能力。它将设计一个将一系列的援助活动与贸易和发展策略协调一致的总体框架。目前,与贸易援助有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①消除供给限制,建设生产能力;②增加贫困人口分享贸易收益的机会;③减少调整的成本。
(一)提升贸易表现——消除供给方面的限制
贸易援助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表现。 1.寻找出口机会高收入国家主要通过灵活的生产线来多样化其出口的产品,而中低收入国家是通过增加生产线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技术援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几类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并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因此,援助需要按照细化国际分工的思路来进行,而不是生产完整的产品。OECD的分析也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升产量,这也带动了大量中间产品的生产与贸易。
2. 提升人力资本
自由贸易能够减少具有良好基础教育的国家的收入不均衡状态。尽管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被普遍认识,良好的中高级教育对一个国家长期的增长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贸易援助需要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
3. 提升物质产能
贸易援助帮助形成有效的资金链和技术进步,有效地提升了产能。这样就减少了在低收入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国内生产部门与出口部门的隔阂。
4. 解决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
基础设施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输费用,因此对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将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贸易援助不仅可提升出口能力,也由于改善了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还提升了进口能力和技术更新的能力。
(二)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
减少供应链的瓶颈,并不会自动给最贫穷的群体带来收益。因此,需要对贫困人口给予特别的关注。贸易在穷人生活中的角色,是决定贸易如何影响贫困的关键因素,只有当穷人们能够有有效的途径接人市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改善。目前,许多贫困人口还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生存的,发展农业市场是他们的福音。当低收人人口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后,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当地有优势的农产品让人们获利。当然,做出生产决策需要依赖气候以及市场信息,所以相关政策与机构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减少市场费用与风险。除此之外,扩展基础服务、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改善利益分配的机制、增强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等都对消除贫困有利。成功的全球化,需要把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整合成为一体,让农民也成为这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注意的是,贫困人口也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城市与乡村贫困人口,男性与女性,对于不同群体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当贫穷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出口引导经济增长的战略并不能有效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增加穷人参与的贸易机会。当形成自由贸易时,并不能说明国内市场不存在扭曲。国内市场和政府的错误会阻碍贸易改革的溢出效应。只有政策的合理调控,才能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实际的减贫。
(三)减少调整的震荡
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对以下3个调整因素十分脆弱:①减弱了最惠国关税下的偏向性;②关税减少后政府收入的减少;③鼓励竞争后市场混乱的情况。有明确目的性的贸易援助可以帮助改善相关的问题。当然,贸易有关的调整依然需要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与良好施行。贸易自由化最后会得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时为了长期利益而进行的短期调整影响会比较大,也较明显。对短期动荡的准确预期,可以在事先就设计好相关的保障网络,并且同样的变动对不同的穷人群体影响也是不同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从宏观来看,如果一国之前有很高的国内保护程度,调整成本就会很高。但相比最终贸易的收益,调整成本就小很多,而且调整期也是短暂的。即使这样,对于某些穷人,变动的影响却是剧烈的,因此需要向他们提供政策帮助。
通常最成功的贸易改革项目都是与一些减少调整震动的援助项目一起进行的。在一些情况下,定向帮助比一般的援助更加有效和公平。为了增强有效性,这些定向的援助需要:①具有清晰的策略,并且有时限;②不与产量挂钩;③专注于普通劳工的再就业;④与通常的保障制度相匹配;⑤易于观察和计量。
选择合适的政策共同实施以及提高有效保障网络的设计是获得贸易收益的关键。 与此同时,提升教育水平可以填补扩张部门对高教育学历或者是技术工人的需求,多样化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提升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和机动性。而且对女性的教育尤其重要。
其他政策的施行也很必要,如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财政政策,完善医保制度,强化产权,增加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投资和拓宽信息渠道。总结起来,就是要符合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促进竞争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保证产权和确保商业交易,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机构;能够稳定未来增长预期以及鼓励投资促进未来增长的宏观环境稳定。强化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可以使其更好地面对贸易改革中的社会变动,以及支持改革自身和强化经济的稳定性。
四、 全球之路,本土之道
外部的障碍有时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解决。而且不同政策施行时必须连贯一致,不能目标相反。贸易自由化需要在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同步进行。发展中国家追求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道路就是要遵循一些共同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关于强化劳动力和资本向扩张部门转移的相关政策。每国的国情不同,哪怕施用同样的一系列政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些不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多样的物理和地理特征;政策措施施行的情况;实施改革的机构的能力和数量;政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政策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国家现存的制度框架决定了国家最后贸易的发展情况,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套用。
五、 总 结
在能充分释放贸易机会的情况下,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很重要。而且,为了让贸易援助更有效,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也是重要的。第一,贸易援助需要得到削减外部障碍的国际合作的支持;第二,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需要施行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总结来说,有4个实用的步骤可以来提高贸易援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效果。第一,人们需要认识到贸易援助是值得去实施的;第二,贸易援助可以为多个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第三,贸易援助需要有明确的目标;第四,贸易援助必须能够达成相关的目标。
资料来源:OECD。
(编译者:林海 张海森)
绿色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
供决策者参考的报告概要
OECD 2012年6月
一、 引 言
面对日益急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加强努力,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作为新的增长来源。以绿色增长动能为基础,更加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评估生态系统补偿价值等手段,有助于加快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的进程。
绿色增长是一个涉及经济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课题。它同时解决了两个重大的迫切难题:发展中国家需要维持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同时,需要改善环境管理以应对资源稀缺和气候变化等所带来的挑战。当绿色经济增长借助2008—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开始推广时,一些国家的政府从短期增长的视角来接触这一理念:即通过增加在一些绿色(尤其是低碳)技术领域的投资,有望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其他成员国政府从环境的视角来理解绿色经济增长概念:有可能将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要求作为主流纳入经济决策中,如通过资源定价和土地使用/基础设施的选择,来实现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第三个迫切难题是平等和包容性,近来这一问题已被更多的提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理念是绿色经济增长应服务于那些被排斥在现有经济体系之外的民众。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规模很大,在任何转型至绿色经济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了解非正规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危害,以便为贫困群体带来更多体面的工作机会和能抗拒风险的谋生方式。因此,围绕绿色经济增长的理念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目前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持续,而且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此外在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也不公平。
这同样是一个结束效果欠佳的实践方法,开启绿色发展机遇的问题。此外,这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调整,以便更好地实现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之间的衔接。前提是确认他们能产生协同效应,同时明确在不同环境下需要进行利弊权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以及需要开展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等。因此,形成国家绿色经济增长政策框架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目前正编纂《绿色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报告》,以检视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绿色经济增长,并商讨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框架的组成要素,以便发展中国家能用来促进经济向绿色增长转型。该报告探讨了诸多的政策工具作为绿色经济增长框架的一部分,同时兼顾各国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该政策框架不仅涉及环境政策,也涵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它将带来重大的长期投资和创新,这对于避免发展中国家被禁锢在效率不高、成本高昂的技术工艺和基础设施之内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让这些投资和政策取得可持续和可观的成果,必须作出适当的政府治理安排,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政府机构能力发展。
本概要文件阐述了《绿色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报告》(草稿)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分析。本报告诠释了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下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概念框架,绿色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以及在最近已经启动并将在2012年继续开展的一系列磋商咨询活动中,了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绿色经济增长议程的担忧。报告还讨论了绿色经济增长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报告评估了最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发展趋势,并推测未来几年经济和社会趋势将如何发展演变。基于这一证据,构建了一个国家集群的概念用来分析各个国家的状况,集群内的国家可运用类似的方法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相关的国家框架和一系列政策框架(涵盖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以及拟定诸多的细节,让他们如何能通过现有机制和发展政策的连贯性来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报告还将介绍如何评估工作进展,包括通过现有和新设的统计指标和统计能力建设来获得相关的数据,最后一部分描述了报告的咨询商议过程,并概述紧随其后的诸多步骤。根据正在进行的磋商咨询,本报告将提出需要深入分析的具体议题。
1. 绿色经济增长:为什么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
发展中国家是实现全球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环境退化对经济社会的潜在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严重。它们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更依赖于开采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从缺乏能源、食品和水资源供给安全,到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风险等。他们的民众也面临过早死亡的威胁,这源于环境污染、水质不佳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疾病。所有这些因素损及他们的发展。第二,尽管在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中所占份额远低于经合组织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如果他们采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会增长。随着这些国家更密集地消耗自然资源,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
为了应对上述经济增长和发展领域的诸多挑战,而不在未来经济成长和减贫目标方面做出妥协牺牲,绿色经济增长的理念脱颖而出,成为重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新方式,并可重新评估很多的投资决策,以满足能源、农业和用水需求,以及经济成长对资源的需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绿色经济增长定义为促进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同时确保自然资源持续提供民众福祉所仰赖的资源和环境服务的手段(OECD,2011b)。不过,发展中国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绿色经济增长,该理念已引发一些关注和担忧。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罔顾其政治地位,近来开始在国内大力开展绿色成长的进程,甄别和开发具有发展机遇和比较优势的特定领域。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采取的行动包括课征碳税,设立绿色能源基金,实施生态系统补偿计划、可再生能源倡议、可持续公共采购倡议和自然资源管理倡议等。但是,这些国家很少准备构建整体性的,或系统性的“绿色经济增长”政策、战略和公共机构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成长战略表现卓越,包括柬埔寨的绿色经济增长路线图,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发展计划等。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某些方面成为全面综合的绿色经济增长政策框架的组成部分,但绿色经济增长很少在主流的经济政策、预算政策和财政政策中提及。
2. 推动绿色经济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
绿色经济增长主要涉及协调和加强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等各个方面。其付诸实现依赖于将自然资源的全部价值纳入考虑范围,并承认自然资源在经济成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推广成本节约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方式,指导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选择,如果得到有效的规划和实施,有望达到预期的成果。因此,我们首先回顾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经济增长方面越来越追求的一般性成果。
二、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本报告汇总了持续演变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他们在当前环境下影响深远的众多衍生系统,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财富及权力分配格局。在21世纪,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已快速增长。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往往伴随着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OECD,2010)。
这些趋势是由多个全球性的因素导致的: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发展形成,相关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大幅增加,以及大宗商品,尤其是化石燃料和工业金属的需求持续高涨。发展中国家相应地可划分为3个“集群”:燃料出口国,除燃料外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制造业出口国。以制造业、燃料和其他采掘工业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二氧化碳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冲击。这些趋势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后果,包括降低农产品单产,淡水供应紧张,极端天气事件,以及失去控制的污染事件导致民众过早死亡等。
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让秉持的政策有助于取得具体且可度量的进展,迈向提振包容性经济增长和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经合组织预计,未来4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取得长足的发展。因此,这些国家遵循更加绿色环保的经济增长路径,对于全球绿色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存在环境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之间发挥协同效应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可将环境问题纳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之中,并能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以改善民生,创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绿色经济发展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让他们跨越难以持续,挥霍浪费的生产及消费模式。尽管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沉淀资本的路径依赖,但他们充裕的融资资金和生产能力会给发展中经济体在建造支撑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方面带来机会。
在3个“集群”的中低收入国家中(以燃料为基础的经济体,除燃料外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制造业出口国),按二氧化碳强度来衡量的经济增长轨迹存在明显差异。当我们检视在1990-2009年,每个“集群”中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看到存在显著的差异。一方面,在以燃料为基础的经济体和除燃料外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当中,这两个人均指标往往呈线性关系,不过在前者的集群中要陡峭得多。而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出口国当中,这两个人均指标之间似乎存在着两个相互背离的趋势。一个是高强度的趋势线,以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作为代表,南非可能包括在其中。另一个是其他国家的低强度趋势线,成员国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制造业出口国和除燃料外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组别之间,二氧化碳强度的水平看来较为相似。
三、 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增长的政策框架
很多国家将绿色经济增长理解为,采取融合、创造和维持环境和社会价值的方式,促使包容性经济发展成为主流。它包含持续调整和改善政府机构、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参与主体,以及消费者的绩效表现,并要求对主流政策和政府治理体系开展大刀阔斧式的系统性调整——也就是说,让经济管理方式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绿色经济增长战略即将发展并付诸实施时,一国政府应从3个维度进行审视:
——一个全国性的绿色经济增长计划,以创造赋能的条件;
——让绿色经济增长成为主流的机制,以确保人们通过现有经济活动来探索发展机遇;
——绿色经济发展政策工具,以获得在空间系统和资源系统内的特定发展机遇。
1. 维度1一一创造赋能条件的全国绿色经济增长计划
只有在整个政府治理和政策环境适宜,且利益攸关者充满信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绿色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必备条件是拥有某些类型的,全国协调统一的绿色经济增长计划,该计划能较好地融合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角色,并为绿色经济增长创造放权赋能的诸多条件。在编制国家绿色经济增长计划的背景下,需要应对6个经济层面的政策挑战,在每个领域中,政府都能发挥领导作用。一般而言,政府为促进经济成长构建赋能的条件,通过促进包容性的赋能条件来加以强化,并采取环境保护的赋能条件来调节经济。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现有政策、倡议和体制为基础,并加以“捆绑”,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协调配合。迄今为止,重点关注这些因素已证实能有效地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这也能确保最有希望的政策选项能得到迅速启动和推广,以免遭遇立法和其他方面的拖延。
2. 维度2-让机制成为主流
但是,创立一项计划作为绿色经济增长的唯一工具,可能导致一些参与者和当前的发展机遇获得优先特权,干扰绿色经济增长可能性及参与者的宽泛程度,并限制绿色经济增长对现有经济活动所能推动的变革。各国政府应甄别准入点并加强作为主流的机制,以便让绿色经济增长活动取得最大的成果。一些正在成为主流的机制改善了他们的有效性。
3. 维度3一一采用绿色经济政策工具以捕捉绿色发展机遇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机遇分布在许多常常相互重叠的空间及资源系统内。他们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容易耗尽和可栽培的自然资源),到能源、城镇和制造业系统。因此,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甄别具体的绿色经济增长政策工具,并以不同的组合和力度来加以使用。鉴于发展中国家着重强调绿色经济增长的公平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当运用这些工具时,应特别留意该政策工具对扶持小型生产商,减少贫困及鼓励创造就业岗位的影响。
4. 付诸实施的绿色经济增长政策
很多发展中国家已实施多项政策和采取诸多行动,以将上述讨论绿色经济增长框架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付诸实施,其中涉及国家和地方层面,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等。本章节概述了几个具体的国家范例。 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的生态环境补偿(PES)计划于1996年依法创立,通过对燃料和用水征税来筹措资金。由于森林有利于保护河流水域和生物多样性,并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该计划通过向森林拥有者支付环境服务补偿费的方式来阻止采伐森林。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支付生态补偿金超过2.3亿美元。
巴基斯坦、肯尼亚、印度: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印度的普纳,以及许多其他城市,‘贫民区’居民联合会正与当地政府一道改善住房条件和减少自然灾害风险。他们已经向政府展示他们有能力设计和建造住房和基础设施,且比政府委托承包商建造的房屋成本更低廉和质量更好,以及他们有能力承担数字统计,以及绘制规划升级所需非正式周转房的任务。在那些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携手合作的地方,绿色经济所能实现的规模已显著扩大(Satterthwaite,2011)。
阿塞拜疆:2001年约一半的阿塞拜疆人处于贫困状态,但随着石油开采业蓬勃发展,已帮助该国在目前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阿塞拜疆在2003年正式签署《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Initiative,简称EITI),在2009年成为首个获得该行动计划正式成员国资格的国家。根据该计划,所有的石油、天然气和金矿公司都有义务报告他们向政府缴纳的金额数目,与此同时政府要公布收缴的数额。但阿塞拜疆需要加大打击腐败的工作力度,并确保经济的多元化。
尼泊尔:森林占尼泊尔国土面积的约40%。《尼泊尔森林法》和森林管理条例承认社区森林使用者组织是“管理和使用社区森林的自治性法人机构”。社区林业通过森林保护、树木砍伐、原木采伐和木材以外的林产品来创造就业岗位和收入,已为恢复森林资源做出了巨大贡献,扭转了森林覆盖率下滑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每年的森林覆盖率下降1.9个百分点,而在2000-2005年,转变为森林覆盖率每年上升1.35个百分点。
孟加拉国:WasteConcern是1995年在孟加拉国成立的一家社会企业,该公司将路边的有机废物收集转变为农业堆肥。根据WasteConcern的计算,在2001-2006年期间,通过减少化肥进口就节省外汇124万美元,该机构每年加工124 400吨废物,直接创造986个就业岗位,凭借出售堆肥赚取了110万美元。在自身成功的基础上,该机构目前资助10个亚洲和10个非洲城市效仿其运作模式。
斯里兰卡:Brandix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服装生产商,该公司已被公认为遵循很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该公司改建的展厅生态中心(showcase Eco-Centre)工厂减少了80%的二氧化碳排放,节约了46%的能源,降低了58%的水资源消耗,该公司因此赢得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 Green BuildingCouncil,简称USGBC)颁发的美国LEED绿色建筑认证有史以来的最高评级。
四、 国际社会如何能提供帮助?
创造一个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全球架构,将需要各国进一步加强筹划安排以设法赢得全球公共体系的使用权,维护全球公共产品的品质,加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提供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并为清洁技术的普及推广提供便利条件。加大努力以增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流动,也有助于巩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有必要提高警惕,防范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政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这可能导致政策失去连贯性,从而损及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前景。
一个国际赋能的环境有助于带来适宜的政策和市场信号。它将通过设定环境法规和规章,提振环境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及供给,刺激在能源、交通、农业和其他领域的绿色经济增长努力,以激发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发展动能。它将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融资、技术和创新。此外,一个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国际赋能环境会促进国际社会交流绿色成长相关的知识,或在科学、技术和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高效综合的知识共享平台对于国际社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知识、良好做法和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经合组织和国际社会可在多个领域帮助搭建一个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这些领域包括:
——增强能力。能力是绿色经济增长的核心:包括改良和运用绿色技术的能力,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能力,促使绿色成长成为增收节支项目的能力,将环境问题纳入决策过程的能力,协调各个行业的能力以及推动环境相关财政改革的能力。国际社会能够扶持发展中国家构建和增强这些能力。其努力将主要集中在3个议题上:分别是将绿色经济增长考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的能力,国家预算过程和重要经济领域。
——增强官方发展援助(ODA)。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创造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赋能环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该援助“针对那些对民间投资的激励有限且资金流动稀缺的领域,包括基本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政府机构能力建设等”(OECD,2011a)。捐助机构在刺激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并一直在加大环境扶持方面的资助力度。官方发展援助往往资助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农业和低碳运输网络等方面的重大项目。它也扶持规模较小,但可能具有激励带动作用的工作,如可行性研究、开展试点项目和技术培训等。绿色经济增长的理念应充分融入开发合作的各个环节。应通过确保气候灾害防范和减灾方法成为官方发展援助所资助公共投资项目的主流,让致力于绿色经济成长的官方发展援助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此外,在可持续生产系统和价值链领域,发展合作资助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项目应吸引和补充民间投资。贸易援助倡议(Aid-for-Trade Initiative)在贸易基础设施开发、生产性能力建设和履行贸易协定等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该倡议应集中于绿色贸易相关的投资,以及构建履行新的贸易规则,如绿色或低碳认证的能力。
——促进创新和加快绿色技术的传播。经合组织国家可通过消除目前在技术传播和转移,以及贸易等领域的障碍,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绿色经济增长。此外,扶持发展中国家普及科学知识和开发绿色技术,也有助于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此举降低了私营部门投资于新技术的成本及风险(OECD,2011a)。为了加快创新技术的传播推广,经合组织国家目前正形成加强技术转移的新机制,如通过自愿专利池和其他协作机制,降低申请知识产权(IPRs)的难度。为了扩大绿色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需要采取多边行动以降低这些国家推广绿色技术的成本。其中的一些关键性举措是开展国际合作以资助专利许可费,买断重要技术专利,为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提供便利,以提高公共机构开展基础研究的知识系统性。开展学术合作和跨国高等教育交流计划.也能促进技术转移,并引发当地创新系统的溢出效应。
——为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提供便利。通过建立国际生态系统补偿市场,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机遇。经合组织国家能采取将环境外部性定价的政策方法,把以后年份财政收入的足够部分拨付用作生态补偿,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准备实施的生态补偿机制创造需求。国际社会也能通过促进国际标准的统一协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这其中包含环境保护、清洁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认证体系等。
——编制连贯的政策。发展政策的连贯性(PCD)在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国际赋能环境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看,有效实施绿色经济增长政策组合拳将依赖于当局的政治领导力,广泛的公众意识,以及普遍承认变革是有必要且具有支付能力的(OECD,2012)。为了将PCD带来的发展机遇最大化,经合组织国家需要确保他们在发展合作之外的政策不会破坏发展中国家在改善资源管理、农业、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等领域付出的诸多努力。尤其是发达国家需要确保其绿色经济增长政策不会导致高碳排放或污染密集型项目漂洋过海搬迁至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增长政策与多个部门,政府整体运作的方式融合之后,能相互交织产生最大的协同效应,带来与其他行业的共同利益,并对减少贫困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 衡量进展
相关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为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且是监测进展和评估成效的关键。监测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增长的进展需要一些特别的考虑。经合组织已拟定了衡量绿色经济增长的框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组织测量指标,甄别相关的,简洁且可衡量的统计数据的思路。该框架表明绿色经济成长具有完整性,并描述了需要监测的4个主要方面:①该国的经济环境和资源生产力;②自然资源禀赋;③生活环境质量;④由此带来的经济机遇和政策响应等。
监测发展中国家绿色经济增长的进展需要一些特别的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多各式各样的挑战(贫困、政府机构能力薄弱、缺乏粮食安全、性别不平等、基础设施落后等),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优先项目不同于发达国家。但经合组织的衡量体系框架是一个稳健的工具,能适应不同国家的状况和优先事项。它赋予了各国对反映本国绿色经济增长目标的指标予以重点关注的灵活性,这些目标包括打造经济和环境的韧性,以及确保经济成长的包容性等。
整体统计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绿色经济增长监测体系框架的最大障碍之一。在面对其他紧迫优先事项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一直难以调动必要的能力和资源,以收集、编纂、分析和传播相关的信息来支持其政策发展。
拟定一个监控体系框架是任何绿色经济增长战略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协同效应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编纂一整套测量指标来监测绿色经济增长的进展并不会增加统计工作的负担。实现国家统计系统的现代化和改善的倡议,如“21世纪促进发展的统计伙伴关系(PARIS21)”下的巴巴多斯统计核算方案现代化(MBSS),以及国家统计发展战略(NSDS)过程,为绿色经济成长成为主流提供了重要机遇,尤其是将环境纳入经济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考虑范围。
六、 接下来的一些步骤
在理想情况下,本报告将了解到绿色经济增长政策和工具的经验分析。在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经验,且没有迹象显示其将提供此类经验的情况下,本报告转而利用数量少,但分布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绿色经济成长磋商所涌现的政策行动计划,以及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者向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10+20,UNCSD)提交的政策倡议,近来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和绿色经济联合会(GEC)就这一主题开展的国家对话,以及一群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实践方面,这些经验更具实践性,但有时难以令人信服且零散松散。
一些发展中国家表达的忧虑表明,在缺乏磋商咨询过程、学习借鉴和达成共识过程的情况下,绿色经济增长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和持续变动的特点,使得发表一个最佳绿色成长政策框架的声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本报告将尝试提供构建此类政策框架的诸多要素,以及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展的磋商咨询过程,以提供一个过程用以凝聚和构建相关的共识。在本报告草稿的商讨中,经合组织对以下素材表示欢迎:更多有关卓有成效政策及其影响的证据,尤其是在涉及经济成长方面;指明本政策框架内部的分歧;以及如何出色地化解这些分歧的构想,包括所需的调查研究。
经合组织和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共同主办的首次磋商活动,于2012年5月在韩国首尔的全球绿色峰会间隙举行。本报告的评论内容广泛,从绿色经济增长课题的定义或概念,到发展中国家有关绿色经济增长议程的特别关注,以及有必要通过能力发展和经合组织同家的支持开展全球合作。本次磋商得出的最重要信息是,除非绿色经济成长能在短期或中期内明显促进减贫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否则它几乎不会取得什么重要进展。大多数的反应是务实的——绿色经济成长应被视作一个正在改善的主流政策,而不是一些极端的新范例。而基于实践经验的案例研究,似乎是一个在未来会受到普遍欢迎的研究方法。
与发展中国家的下一次磋商在6月17日举行的巴西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进行,这一努力将指导本报告的关联衔接,并进一步精简绿色经济增长政策框架所需的诸多要素。
资料来源:Green Growth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2012 0ECD。
(编译者:毛小菁 姚帅)
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
——城镇世界中的儿童
一、 引 言
儿童时代的生活体验正在日益城市化。目前,世界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城镇,其中包括10亿儿童。
尽管城市一直与就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相联系,但仍有数以亿计的城镇儿童成长在资源稀缺和被剥夺的环境中。《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呈现了这些儿童所面临的困境,这不仅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也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报告审视了城市儿童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移民、经济冲击和重大灾害风险等。
然而,取得进步也是可能的。《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展示了一些积极的案例,表明了在改善儿童所生活的城市现实方面的成功;同时也指出应将广泛的政策行动纳入到所有的发展战略中,以惠及遭排斥的儿童,并在贫富悬殊的城市环境中促进社会公平。二、 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城市中
世界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6 000万,到2050年,70%的人将居住在城镇地区(专栏2)。城市扩张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来自农村的移民一直是城市规模扩大的主因,在一些地区仍然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但1998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显示,出生于城市的儿童已占到城市新增人口的60%左右(图1)。
许多孩子享受到城市生活提供的种种优越条件,包括良好的教育、医疗和休闲娱乐设施。然而,仍有很多儿童被剥夺了清洁饮用水、电力供应和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哪怕他们就住在这些设施附近。数量众多的儿童被迫从事危险并被剥削的工作,而不能上学。还有很多儿童面临流离失所的威胁,尽管他们现有的居住条件已经十分不堪——摇摇欲坠,过度拥挤,很容易遭到疾病和灾难的袭击。
城市贫困社区中的儿童所面临的网境常常被统计平均数所掩盖并延续,而统计平均数常常被用作发展规划和资源分配的依据。由于平均数将个体混杂在,一起,某些人的贫困就被其他人的富裕所掩饰,于是本就被剥夺的儿童继续被排斥在基本服务之外。
从能够获得的详细数据来看,获取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导致城市儿童在存活率、营养状况和教育等领域存在显著差异。在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生活在城市贫困社区和非正式住所内的儿童每天都面临着权利遭剥夺的困境,尽管公共服务设施唾手可及。在很多国家,城镇贫困儿童的营养不良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农村贫困儿童的状况相当,甚至更差。
城市生活常常充斥着贫困与排斥。三分之一的世界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非洲这一比例超过60%。到2020年,将有约14亿人生活在非正规住所和贫民窟中。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又因违法犯罪、无力参与决策、缺乏安全产权和法律保护而雪上加霜。基于性别、民族、种族或残障的歧视也会加剧贫困人口所遭受的排斥。
当然,并非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贫民窟中,而贫民窟居民也并非都是贫困的。尽管如此,贫民窟仍旧是为权利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表现和后果。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政策及土地使用和管理法规,导致贫困人口难以获得体面的房屋和安全的产权,只能租赁或搭建非法的(临时)住房。
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居住环境助长了疫病的传播,尤其是肺炎和痢疾这两个威胁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杀手。在人口密度很高而防疫水平很低的地区,麻疹、肺结核和其他免疫预防疾病也更为多发。
此外,贫民窟居民常常面临被驱逐和被虐待的威胁,其中包括政府“清理整顿”的风险。被驱逐将导致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并破坏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体系和支持网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使儿童因搬迁而受到的影响最小化. 儿童和青少年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是最脆弱的,尤其容易受到贫困和不平等的冲击。除贫民窟里的贫困儿童和边缘儿童外,在街头谋生和工作的儿童时常被拐卖或成为童工,也应得到特别关注和针对性措施。
注重公平就需要给予最弱势的儿童最高的优先性,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除非城镇政府和国家政府、资助方和国际组织跳出统计数据的均值之外来解决(全世界众多城市儿童所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儿童权利才能得到充分行使和保护。
三、 儿童在城市中的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承认居住在城市中的儿童拥有全面的公民、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的权利;以及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不同权利得以保障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超过三分之一的城镇儿童在出生时没有登记,这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7条的规定,并可能引发其他的侵权行为。缺乏正式身份妨碍了儿童获得重要服务和发展机会,并加剧了他们受到强制劳动等各种形式剥削的脆弱性。
儿童的需求最紧迫,但权利侵犯也最严重。城镇儿童所面临的艰难包括:饥饿和不健康;住房不足;难以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缺乏教育和社会保障等。
生活条件恶劣是儿童权利侵犯的最普遍形式之一。没有体面、安全的住房,缺乏饮用水和卫生等基础设施,使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愈加艰难。在受污染的环境中健康成为奢望,缺乏安全的游戏场所也失去了玩耍的权利(专栏3)。2010年,有大约800万名5岁以内的儿童死亡,死因大多为肺炎、痢疾或分娩并发症。在城市地区,贫困的集中和服务设施的不足导致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图2)。
在人口密度较高、新传染病原体持续涌人的脆弱社区,免疫水平过低致使免疫预防疫病频发。全球疫苗普及率正在提高,但在贫民窟和非正规定居点,接种率依然很低。
2008年,有超过35万名妇女死于妊娠和分娩,而每年有数量更多的妇女因此而受到身体损伤,其中一些是终身性的机能残疾。只要她们能够在拥有相应医疗设备和卫生用品的医院里获得专业医护人员的照顾,或者紧急产科护理,这些死伤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城市提供了就近生育和急救服务,但贫困角落的服务获取、使用和质量往往要差得多。
资料来源:WHO估计和DHS,2005-2007年。
四、 健康和营养
《儿童权利公约》第6条规定各国“应尽最大可能保障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第24条强调儿童有权“获得最好的健康条件,享受最好的医疗和康复设施”。尽管城镇地区拥有大部分的现代医疗设施,仍有太多生活在城市周边的儿童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城市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也在蔓延。城镇的贫困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日益高于农村地区。即便在表面看来食品充足的人口(即能够获得足够的热量以维持日常活动)也可能遭受微量元素营养不良的“隐性饥饿”,即缺乏从水果、蔬菜、鱼类或肉类中获取数量足够的如维生素A、铁和锌等营养物质。如果缺乏这些微量营养素,儿童死亡、失明、发育迟缓和智商低下的风险就会增加。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由于营养不良。
室内空气污染每年也导致约20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收入较低的家庭往往在通风不良的空间里使用危险的燃料来做饭,是造成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的原因之一。城市生活也将孩子们暴露在严重的室外空气污染中。
在城市中穿梭的汽车不仅排放有毒气体,也对孩子的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在缺乏安全的玩耍空间、人行道密布和交叉路口众多的环境下更是如此。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道路交通伤害事故导致全世界每年130万人死亡。交通事故伤害是15~29岁人群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5~14岁少年儿童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二。
最近的数据表明,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正在减少,且在怀孕、分娩或哺乳期间阻断艾滋病毒母婴传染的服务获取也得到改善。2010年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仅有2005年的1/4。尽管如此,2010年每天仍约有1 000名婴儿通过母婴传播而感染了艾滋病毒,另外,每天有2 600名15~24岁的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毒,主要原因是不安全的性行为或注射操作。城镇地区的艾滋病流行依然十分严重。
五、 供水,环境卫生和保健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可实现的最高健康标准”包括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消除环境污染的危险。不安全的供水、糟糕的卫生设施和污染的环境每年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其中,每年有12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痢疾。
总体而言,全球城镇居民能比农村地区的居民更好地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即便如此,供水和卫生设施的覆盖率也难以跟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图3),导致大排长龙或漫天要价。由于无法与供水主干线相连,城市贫困人口获取一升水往往要比他们富裕的邻居多付出50倍的时间。卫生设施也依然是个大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露天大小便的人数也在增加,在1990-2008年增幅为20%。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区,这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尤甚,而公共卫生设施往往拥挤、破旧而肮脏,针对儿童的专门设施更是罕见。
拥挤且不卫生的条件使城市贫民窟成为传染病的高发地区。如果不能获取充足、安全的饮用水来满足基本的卫生需求,儿童的健康状况将会受到影响。改善供水设施和服务质量将是降低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关键。

资料来源:WHO/UNICEF联合监测项目,2010年。
六、 教 育
《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规定各签约国应承认儿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并承诺“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这项权利”,但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会损害儿童的这项权利。在城镇地区,贫困、健康状况不佳和营养不良往往导致教育计划因儿童缺席而臭名昭著。儿童早期教育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将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中有超过2亿名儿童未能充分发挥其认知潜能。
尽管许多国家已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仍因父母收入、性别或种族等原因而存在不平等。截至2008年,仍有600万名小学适龄儿童辍学,其中53%为女生。同样,城镇地区在儿童受教育年限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贝宁、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城镇地区最富裕的20%和最贫困的20%人口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距超过了农村地区。
城市地区人口结构复杂,包括少数民族、难民、移民等,儿童可能会在街头谋生或工作。政府应关注那些讲不同语言、没有正式身份或已经失学的儿童,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继续教育方案。
在公共教育服务缺失的贫民窟,一般家庭的选择要么是花钱送孩子上一所教学质量欠佳且人满为患的私人学校,要么干脆让孩子辍学。即便能够得到免费入学的机会,额外的费用(如校服、课堂学习用品或考试费)也常常高昂到让人望而却步。近来对巴西圣保罗、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调查发现,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超过25%,尽管他们付出了不菲的费用和艰苦的努力,年轻人的教育成就也难以让他们找到适宜的就业机会。政府必须将为城镇地区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开展针对空缺职位的培训作为优先事项。
七、 儿童保护
儿童保护始于出生登记。确保所有的儿童都得以登记和备案必须成为最优先的事项——致力于社会公平的努力可能会将缺乏官方证明文件的儿童排除在外。城镇地区的出生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多没有登记注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南亚地区,该比例接近50%。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规定签约国“应采取所有适当的法律、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来确保儿童免受各种形式的身体或心理暴力、伤害或辱骂、忽略或疏忽、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害”。该公约第32条涉及经济剥削和危险工作,第34条针对性侵害,第35条专门关注儿童贩卖问题。
人口贩卖导致约250万人成为强制劳工,其中22%~50%为儿童。即便没有人口买卖,很多儿童还是会为了生存而被迫工作。2008年,约有2.15亿名5~17岁的儿童沦为童工,其中1.15亿人从事着危险工作。据估计,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在世界各地的城镇或城市的街道上谋生或工作,其数量随着全球人口增长、移民和城镇化仍在持续上升。在街头谋生往往让儿童容易受到暴力活动的袭击,但很少有人调查针对他们的犯罪活动,更鲜少有人会在他们奋起反抗时施以援手。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城市中在街头谋生或工作的青少年都会成为逃犯或流匪的主要目标。研究者、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表明,世界各地的警察和保安也会打骂虐待城市街头的青少年。
八、 城市生活的诸多挑战
1. 移民
儿童无法改变社会等级、阶层或种族。他们出生在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终其一生都将受到集体认知、传统惯例和刻板陈规的阻碍,很容易被视作他们无力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随着他们的成长,儿童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尽管大多数儿童是随其家庭一起移民,由寻求就业或发展机会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带领,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儿童和青少年独自在国内进行流动。与成年人一样,儿童迁移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一些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或教育机会,或仅仅为了摆脱贫困;而其他人则为了逃离冲突或灾难,躲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食物短缺。此外,家庭因素(如失去双亲之一、家庭不稳定或生活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不管儿童的迁移是否自愿,保护他们免遭与此相伴的诸多风险,就要求采取与其年龄相称的应对措施。没有家长陪伴的儿童移民尤其容易受到剥削、虐待和贩卖,本身就是难民或流民(或随难民和流民一道迁徙)的儿童而言更是如此。全世界登记的难民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
此外,因升学而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常常无法实现其目标,他们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而工作强度之大导致工作和学业无法兼顾。
2. 经济冲击
2007年,高收入国家金融资本崩溃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余波仍未平息,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作条件持续恶化、真实收入不断下滑,食品和燃料价格飙升且难以预料。由于贫困人口将50%~80%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食品和燃料价格攀升尤其会让他们深受其害。
从全球看,2010年末的失业人口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增加了3 000万,而失业人数在2011年还在继续增加。15~24岁的工人失业状况尤为严重。在经济滑坡时,年轻人失去工作可能加剧社会动荡。挫败感使他们成为2011年席卷北非和中东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主力军。
从统计数据来看,年轻人的失业状况并不严重,可能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尽管如此,已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危机致使“有工作的穷人”数量增加,其中,年轻人所占比例偏高,导致世界各地的减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进展缓慢。政府有义务保护最贫穷、最弱势的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其害。
3. 城市暴力
犯罪和暴力活动影响了城市地区数以亿计的儿童。一些儿童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一些儿童则成为参与者或目击者。过早地暴露在暴力环境下可能破坏青少年对成年人和社会秩序的信仰,妨碍他们的成长。在暴力中长大会导致学业不佳、辍学率高,带来焦虑、抑郁和攻击性等负面情绪,以及缺乏自制力。
导致暴力活动的原因很多并且十分复杂,但首当其冲的是贫困和不平等。在公共服务、学校和娱乐休闲场所不足时,犯罪和暴力发生率就会升高。对全世界50个最富裕国家中的24个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犯罪、暴力和入狱的比例就越高。
在世界很多地区,完全或部分由青年人组成的城市匪帮无恶不作,包括敲诈勒索、持械抢劫和谋害凶杀。青少年加入黑帮的平均年龄约为13岁,而有证据表明这一年龄值正在下降。在城市边缘,这些团伙会以物质奖励和归属感来招募年轻人。
防止暴力活动需要社区的全面参与,并加强儿童、家庭、学校和其他机构,以及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
4. 灾害风险
对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来说,城市贫困因台风、洪水、泥石流和地震等灾害风险而雪上加霜。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记录的自然灾害数量已增长约十倍,其中大多是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环境脆弱和人口稠密使城市生活尤其危险,而儿童是最易遭遇死伤的群体之一。
自然灾害对生活在危险环境中的城市居民会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他们往往对极端事件准备不足,灾害过后的重建也困难重重。城市贫困家庭的儿童通常生活在不太牢固的住所中,连建房的土地也不理想:例如坡地容易发生泥石流,低洼地带容易遭遇洪水,或者靠近工业废弃物堆放地等。此外,健康欠佳和营养不足也导致儿童更容易遭受环境的冲击。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旨在降低灾害风险的行动计划。2005年,168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签署的《兵库行动框架》呼吁增强社区和国家的抗灾能力。来自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向社区居民和灾害幸存者(尤其是儿童)普及防灾知识,能够有效地降低地方灾害风险。
九、 联合起来帮助城市儿童
当政治、文化和商业精英人物舒适地享受城市生活之际,数以亿计的儿童和年轻人在同样的城市中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他们的童年时光都用于工作而不是上学,生活居无定所甚至在街头徘徊,并处在暴力和剥削的风险中。城市环境的设计并没有将儿童考虑进来,儿童和青少年也从未得以参与规划方案的制定。
目前,大约一半的儿童生活在城市中。随着这一数量的增长,急需采取下列紧急行动来促进他们的发展,并保障他们的权利。
(1)增强对影响儿童的城市贫困和排斥的范围及特征的理解。必须优化数据收集工具,以更准确地反映儿童状况之间的差异,识别最边缘的儿童及其家庭。对旨在提升儿童的生存、健康、发展、卫生和教育权利以及保护城市儿童的干预措施进行研究和评估时,必须对城市数据进行分解。信息必须进行广泛传播和分析,才能有效地揭示因果关系,并应对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为了理解贫困和排斥的变化及其如何影响城市儿童的生活,以及权利剥夺如何实现代际传承,我们所需要做的还有许多。
(2)通过更好地理解排斥,识别并消除阻碍导致边缘儿童及其家庭运用如法律保护和房屋产权安全等基本公民权以实现社会融合的诸多障碍。
这些障碍包括歧视、收入贫困、直接和间接成本、恶劣交通的条件以及缺少官方文件等。公平的政策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如取消服务费、构建社区伙伴关系、加强服务的推广和使用等。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等创新性举措已在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取得成功。找出每个城市的瓶颈问题,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促进社会公平。
(3)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提供和减贫及推动社会平等的努力中,敏锐地关注儿童的特殊需求和优先序列。同时,必须考虑年龄、能力和性别。
《国际儿童友善城市行动倡议》提供了将儿童权利融人城市治理的成功范例。加强问责是这些努力的基石。许多城市政府安于现状,导致大量未经规划的非正式定居点不能满足居民需求。
该议程也涉及保护儿童免受暴力、药物滥用和交通事故等伤害。著名的国际行动倡议如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推动的《人人共享的安全友好城市》,旨在促使妇女、儿童、警察、城镇规划者和决策者共同寻求降低性别暴力的路径。哥伦比亚、瑞典和荷兰的国家行动计划已通过设立无车区、大力发展自行车和行人路线以及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降低了交通事故死伤人数。
(4)在各个层面上推动城市贫困人口和政府的伙伴关系。促进公共参与(尤其是儿童和青年人参与)的城市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惠及儿童,也促进了社区发展。
这些行动取得的积极成果包括: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厄瓜多尔科塔卡奇识字率和委内瑞拉圭亚那城出生登记率的提高等。
地方政府和社区需要更紧密地协调行动,以最有效地利有限的资源,保护贫困人口来之不易的生计资产,并使贫困人口(常常占人口的大多数)能有效地参与城市发展和治理。
(5)共同努力以实现儿童权利的可持续改善。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各个层面上的行动者(从地方到全球,从民间团体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汇集资源和能量,以创造有利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城市环境。
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国际伙伴关系能够促进能力提升,进一步保障儿童福利,并加强世界各地社区之间的联系。以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为例,该网络汇集了34个国家的草根城市贫困人口联盟,使它们能够交流土地产权、房屋质量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促进解决方案的实施。这些网络有能力与社区、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一道,共同促进能够惠及最边缘群体的城市发展。
在促进儿童参与城市治理和社区决策中,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 迈向更公平的城市
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城镇和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城市环境中长大。他们的童年生活反映了城市的不平等:富人和穷人比邻而居,机遇和艰辛结伴而行。
平等必须成为保障城市儿童权利的指导原则。其中,需要特别关注贫民窟儿童,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最具挑战性的贫困与边缘环境中。然而,不能以损害其他地区儿童的利益为代价。更广泛的目标必须持续关注人人共享的、更公平的、更健康的城市及社区——从儿童开始。
资料来源:UNICEF。
(编译者:唐丽霞 赵丽霞)
第三部分
减贫实践
2012年全球发展展望:
世界变迁中的社会凝聚力
OECD 2011
自新千年伊始,世界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财富迁移”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世界的经济重心已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促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格局。新的情况意味着给创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带来一些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告探讨了在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并为决策者提供了如何增强社会融合的诸多建议。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能增进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打击排斥性和边缘化,创造一种归属感,促进相互信任,并为所有成员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本报告从三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性、社会资本和社会流动性。
本报告认为,社会凝聚力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目标,它也有助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广泛的不平等和排斥感,不容许表达不同政见,其经济成长的路径将是难以为继的。本报告强调,有必要在财政税收制度设计、就业、社会保障、公民参与、教育、性别和人口迁徙等方面制定统筹协调的政策。因这些领域的政策在影响社会成果方面都相互关联,因此每个领域的政策设计都需要兼顾其他领域的政策。
一、 财富迁移给社会凝聚力带来机遇……
在错过20年的发展机遇且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的整体经济状况已经复苏。过去几十年中,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初首次实现经济增速超过高收入经济体。在21世纪初,有83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增长率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均增长率的两倍[人均增长率是《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报告》中用来界定“趋同国家(convergingcountries)”的衡量标准],而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12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平。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在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复苏的过程中陷入停滞,21世纪1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比21世纪初更为黯淡。鉴于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如从前,新的10年势必会考验新增长引擎的动力和财富迁移的可持续性。
在21世纪初,大约50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人均年增长率超过3.5%。如今,在全世界20亿每天生活费在10~100美元(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中,近10亿人生活在趋同国家,这一数字到2030年预计将超过30亿。高增长率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可用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成长过程并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及其对社会凝聚力的贡献则尤其如此。
二、 ……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各国政府必须应对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新的压力和负担。这些严峻挑战包括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满足公民对生活水平和获得机会方面的更高期待。生活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民众希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生活水平有着持续升高的期望。由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更多地与发达国家的民众进行比较,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对优质服务的需求预计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泰国和突尼斯等高增长国家的人民满意度下降所示,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状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各国政府不应忽视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辛劳奔波,也不应低估他们动员民众,施压政府变得更开放透明,或要求提高服务水平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社会凝聚力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策目标。若政府忽视社会凝聚力问题,可能面临社会不稳定和干预政策效率低下的威胁。从2010年泰国争取民主运动到阿拉伯之春,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理论:如果漠视民众对包容性政治进程的诉求,仅仅运用技术健全的政策框架是不够的。
三、 政策可产生明显效果
尽管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过程对趋同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共政策可产生明显效果。再分配的政策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曾经收入差距悬殊的经合组织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重新对收入进行分配,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在拉丁美洲),税收和转移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较为有限。
增强社会凝聚力需要长期的愿景和承诺。尽管一些政策干预或改革举措能相对较快地产生了效果,但其他政策则难以在短期内奏效。比如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和平均教育水平,就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转化为代际间社会流动的增加。此类政策的长期愿景和承诺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执行多个领域的政策协调任务可能会构成严峻挑战。促进协调的工具包括跨部委的小组或委员会,预先的法律影响评估以及基于主题的水平式预算。譬如,根据男女性别制定的预算通过甄别解决产业政策存在性别差距所需采取的干预措施,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划和预算来推进性别平等。
四、 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的政策领域
1. 财政政策
较大的财政空间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促进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为了将这些机遇付诸实现,需要改革财政政策。财富迁移带来的意外巨额收益和资源可用来资助社会项目。但他们自身还不够:这些项目应该是负担得起且可持续的。在这方面,一个关键问题是确保社会项目资金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财政收入取决于动荡的大宗商品价格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即将枯竭的情况下,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是一个难以确定的目标。趋同国家的税收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依然相对较低,因此,仍存在拓宽税基或调高税率等税务改革的空间。
然而,民众对如何课税和财政收入如何支出的信任度较低,较低的信任度通常会影响到脱离互补性开支和机构改革来考虑税收改革举措的效果。一些社会因素对较低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明显影响,尤其是在对财政政策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这可能演变为财政收入水平下降,以及财政政策往往在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创造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机遇方面效果欠佳。此外,即便存在正规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或只能有限度地使用影响政策的集体机制,财政政策也倾向于体现精英阶层或强势游说集团的利益。
实行让公共支出与目前波动的财政收入脱钩的经济及财政制度,是确保社会凝聚力政策获得可持续资金支持的关键。宏观经济财政政策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创造充足且可预见的财政空间,以便为社会凝聚力相关的重点发展支出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重点项目包括社会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教育或青年就业计划等。如果财政政策能迫使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存下一笔钱,以便他们能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持公共投资的水平,则财政政策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样,主权财富基金可帮助不可再生大宗商品出口国将资源相关的财政收入留在今后或供后代使用。
税务管理改革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透明度和纳税道德的另一个强有力方式。但是为了做到有效.税务管理改革必须成为加强社会契约的协调努力的一部分。各项改革措施(如设立半白主治的税务征缴机构),如果与公共支出政策的改革相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成效。只有改善公共服务,税务征收才会变得更好和更透明。以公共服务换取纳税举动的财政交换手段,是创造遵守税务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之间良性循环的关键。
2. 就业与社会保障
财富迁移带来了深层转型,这需要有能够促进劳动力市场发挥其制定工资、人员调配和配置等作用的市场管理机构。旨在为工人和集体谈判系统制定保证条款的改革可以首先建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将协助市场根据新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更平稳地调整工资,同时,确保工资薪酬能够反映生产力得到提升的状况。维护工人的利益不一定意味着保护就业岗位。确实,拥有成熟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兴国家可以促进这样一个议程:它致力于通过使失业者和老年人获得失业保险、救济及收入补助,以及包括保健医疗在内的一整套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障方式来实现收入安全,而不是保障就业岗位的安全。
从短期看,较为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手段,尤其是最低工资,在一些国家的就业政策辩论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较贫困的国家。即使在遵守劳工规章有限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也是应对工作贫困的一个有益工具。确实,最低工资上涨的情况也会扩展至非正规部门,促使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升高。巴西等一些国家已经广泛使用最低工资的做法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不是有针对性的手段,一般会产生广泛的副作用: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导致成本高昂,或在使用不当时导致就业人数减少的效果。此外,提高最低工资的效果在工人中也不均衡,这取决于政策执行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细分。因此,积极使用最低工资机制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做法,不应取代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保劳动力市场机构有效发挥制定价格的作用。
评判劳动力市场机构和社会保障系统不仅应依据其工作效率,而且应根据它们防止或减缓二元制和市场割裂的能力。近年来,社会保障领域的创新(扩大有条件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社会养老金、新型医疗保险覆盖等)有利于减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方面的差距。不过,这些措施往往导致二元系统:最贫困者由社会救济覆盖,而富人则享受基于缴款的社会保障或私人保险。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缺口——大部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中等收入工人正“失去中等水平的”保险覆盖。若要让社保制度以最低的冲突实现社会公平的结果,这些机构将需要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全体民众普遍享受社保权益能促使社会保障与就业状态脱钩,因此,具有最好的保险覆盖前景,并为激励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架构。
全民享受基本社会服务可能无法在短期或中期内实现,但各国政府仍可采取一些更支付得起的措施。例如,通过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来扩大社会服务就相对经济实惠。巴西、印尼和墨西哥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花费不到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实现了对多达三分之一人口的覆盖。正如拉丁美洲国家推行的失业保险储蓄账户一样,以缴款为基础的保险制度可放松管制,使之对未纳入保险覆盖范围的工人们开放。
通过社会服务和其他项目来加强社会凝聚力既取决于可获得足够的资源,也取决于提升公共支出的效率。政府一方面宣称付不起巩固社会保障的资金,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政府经常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或支付,而受益者往往不是穷人。例如,燃料和食品补贴可能就是十分昂贵和非常随意的。燃料补贴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补贴富人的倒退性举动。
3. 教育
由于教育成果影响到社会凝聚力三角形的所有三个层面,因此,它是任何社会凝聚力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体民众能够负担得起优质受教育机会时,教育就成为强有力的发展机会均衡手段,即便弱势群体也能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从长远来看,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是趋同国家减少工作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在教育回报随着财富迁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除注册入学外,需要注重教育质量,使教育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率上升、更亮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劳动力市场机会改善等。
确保具有任何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儿童都拥有平等的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本,是加强社会凝聚力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一些干预措施能有助于减少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鼓励来自所有阶层,包括最弱势群体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教育。应该把减小个人受益于正规教育的能力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学校以外的投入,如幼年营养项目和学前培养计划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估计超过2亿名儿童因为发育不良和缺铁、碘而未能实现其发展潜能。
同样,采取措施降低继续教育的机会成本也能够提升教育水平。降低学校教育成本是鼓励学生完成中学学习,进入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和教育换食品补助计划是公认的提高就学状况的有效措施。
缩小受教育的性别差距尤其重要,因为除了规定男女儿童平等获得受教育机会以外,这一工作还有助于打破贫困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的确,教育对儿童的健康和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意性别平等的学校政策和设施确实促进了社会融合。
上学经历本身也影响到社会凝聚力,因为它塑造并传播了作为社会资本和包容性支柱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儿童的方式对于建立他们的社会归属感非常重要。应该对学校教育进行适当的组织,以扩大弱势群体儿童的参与,从而使教育更具包容性。提高教学技能,编制教学大纲以支持社会多元化并提高本系统内及社会上其他人的正面感受,也可以赢得更好的包容性。这尤其适用于将少数民族整合纳入教育体系中。一般而言,学校包容性较好的国家,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也较高。此外在学习成绩方面,包容性学校教育体系的表现也胜过割裂式的学校教育。
4. 性别
尽管在过去20年里很多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们尚未在提高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文化积淀和社会管理机构处于现有权力关系底层的事实使得对歧视性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困难重重。因此,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变革应该首先在就业、教育和创业等方面启动,比如,提高妇女获得信贷和科技知识的机会,并特别针对改造歧视性的社会习俗(如包办婚姻和早婚)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突破性别平等方面制度性瓶颈的一个重要起点是,通过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和继承权来增加妇女的生产活动。妇女和青年女性获得资源的渠道有限,从而降低了他们赚取可持续收入的能力,这可能导致她们从事工资较低或缺乏保障的工作。此外,由于妇女无法获取及控制土地,全家的粮食安全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使得妇女更容易面临贫困或遭遇暴力,从而妨碍她们获得银行贷款或金融服务,并导致她们的决策权下降。
5. 人口迁移
在过去20年,南南迁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迁移)显著增加并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这一趋势在将来可能会加剧。但移民融人不仅对富裕国家而言是一个挑战,对贫穷国家也是如此。新兴经济体的经历表明,世界各地的移民国家都面临移民融人当地社会的挑战。虽然移民的确与当地民众面临着同样的生活挑战,但他们往往被剥夺了获取适当公共服务的机会。尽管新近成为移民目的地国家的资源有限,令人担忧这些国家会针对移民制定排斥性的社会管理措施,但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融合历史似乎表明,各国越早处理移民融人当地社会的问题,政策干预措施就会越成功。
与人口迁移相关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必然会超越反歧视措施的范畴。移民顺利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应该特别包括一套完整的社会、就业、教育和住房领域的保障措施。政府还应努力改善原住公民对外来移民的看法。鉴于社会排外情绪仍是外来移民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最大单一障碍,政府应出台政策防止和转变对移民的社会排斥;促进移民和当地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为创业提供便利、改善移民技能与当地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以及鼓励教育培养等方式来提升移民的社会流动性。
五、 制定和实施社会凝聚力政策
1. 民间参与:一个包容性的政策议程
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关键。为使经济增长过程不至于脱离正轨,政府必须利用民间参与和政治反馈的机制。这一观点在财富迁移的背景下尤其适用,因为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社会错位都需要创新性的政策响应。对于构建社会凝聚力而言,制定政策的过程与政策本身同样重要。社会凝聚力将因包容妥协而协调一致的决策过程而获得提升。
包容性的决策汇集了包括政策实施者到最后受益人在内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政策将得益于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多的民众支持,而合法性和民众支持是最终决定政策效果的两大因素。促进民间参与和地方分权可能被证明是改善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有力手段,而它们本身也值得重视。妇女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她们全面参与民主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实施社会凝聚力的政策议程需要多个政策层面的有效管理和协调配合。强有力的机构和优质公共服务是政府行动取得成功的基础。首先,各国应集中力量加强公民服务和提升监管质量,此外改善对公职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实施“根据绩效编制预算”的机制。其次,由于各干预措施的效力具有相互关联性,需要在各部委之间开展横向合作。第三,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权力分散和地方能力建设来加强公共管理机构的能力,但其成效并非水到渠成。不同政府层面的各家参与机构需要妥协磋商,才能确保问责机制的落实。总而言之,政策各领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而需要纵向和横向的协调工具,中央政府必须积极承担起管理的职责。建章立制需要一些时间,因此,贯彻实施社会凝聚力议程也需要做出长期的承诺。
2. 更好的数据,更好的评估,更好的政策
决策过程还需要更多地以证据为基础。在实践中,旨在加强社会凝聚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需要一个对政策影响进行预先和事后评估的框架:它们造成了更多的还是较少的社会排斥性?它们是否增强了社会信任和民间参与?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监测和评估社会凝聚力政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需要获得新的数据。正如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Sen-Stiglitz-Fitoussi Commission)在其2009年报告中所倡导的那样,衡量社会进步应该涵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之外的指标,以获取在其他维度衡量民众福祉的信息。衡量社会进步的绝对指标及客观方法应该与相对指标及主观感受相互补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评估结果。
为计算这些衡量指标而开展的数据收集努力目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并大部分由私营机构进行。如果各国的国家统计局(也能)收集这些数据,就能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和质量。但是数据的潜力得以全面发挥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①拥有收集数据的国际标准;②各国根据需要推动统计能力建设;③数据尽可能地公之于众。
3. 展望:社会凝聚力能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各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为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可能性。更多可获得的财政资源能用来发展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保护全国人口的所有社会阶层。一些国家在改变歧视妇女习俗方面取得了成功,应能激励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一个更加全面融合的经济中,发展有助于社会向上流动的教育模式变得势在必行。
提升社会凝聚力并非促进一个面临社会挑战却不关心政治的愿景。只有一个社会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执政当局、企业组织和民间团体)都参与其中,积极携手努力并采取集体行动,才能实现提升社会凝聚力这一整体目标。捐赠国可以通过帮助培育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且政府担负起责任的环境来提供支持。许多趋同国家正在经历的转型过程可能会是波折动荡的。但只要管理得当,它将使我们有机会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民众的归属感,进而增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编译者:毛小菁 姚帅)
城市贫困:全球展望
Judy L.Baker
一、 引 言
全球人口数据估计表明,世界城市人口数量自2007年以来已开始超过农村人口数量。城镇人口仍将继续不断增长,预计2030年将达到50亿。城市化将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将最多。
城市人口增长来自自然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增长是减贫的关键因素。在城市里,经济实体的规模和集聚吸引着投资人和企业家们。他们的到来促成了经济的整体增长。城市能为一些人提供机会,特别是穷人,因此,一些人被美好的就业前景、服务的易获得性所吸引。城市也为一些农村地区逃避社会和传统约束的人提供庇护。然而,城市生活也有不好的一面,如居住拥挤,交通拥堵,失业,贫乏的社会和社区网络,以及犯罪和暴力等社会问题。一些移民将从城市提供给的机会中受益,然而,另外一些人因缺乏劳动技能则被边缘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与城市生活挑战作斗争。
城市贫困原因复杂繁多,如资源或能力限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不力、对城市发展和管理缺乏规划,等等。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城市规模都在快速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来自城市贫困和城市管理方面的挑战不能得到强力解决,那么它们将会在许多地方进一步恶化。
目前,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是穷人,即世界贫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Ravallion,Chen,和Sangraula,2007)。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小城镇,而小城镇的贫困发生率通常高于大城市。虽然这些比例在过去的10年中伴随着持续的城市化没有显著改变,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预计将上升,贫困问题将日益成为一种城市现象。
通过贫困评估、城市级别知识的学习、学术研究和其他分析工作,人们对贫困的总体认知在过去十年中突飞猛进。很多贫困研究是在国家层级上开展的。贫困评估通常包括大量的国家层级的贫困分析,但很少对城市层级贫困进行动态分析。对贫困评估进行细目分类,可分为城市和农村层级,或国家层级。然而,用细目分类评估贫困,对城市贫困和更为详尽的关于城市穷人面临的具体问题论述较少,而这些内容正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必要基础。
旨在了解城市贫困特点的研究尽管数量少但日后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开展。当前,城市贫困研究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以及东亚和太平洋等区域级别的研究,也有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也门和其他地方的国家或城市层级的研究,还包括对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居民的微观层面的纵向研究(使用1969年、2001年的调查数据)。小区域的评估数据将越来越多地可以被获得,用于绘制贫困地图和贫困分类分析,因此,也有助于增加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的特征。
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着力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报告,这与贫困朝着城市转移的趋势相吻合。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城市贫困的认知,以及在较有限的范围内,认识城市贫困的动态。但是,对于有关城市贫困的诸多关键问题,以及理解针对城市穷人的项目和干预政策的影响,仍然还存在很大的认知差距。
基于对过去10年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供一篇城市贫困综述。文章的结构安排为,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介绍了有关城市贫困的范围;第三部分列举出有关城市贫困的关键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城市贫困的区域特点;第五部分从瞄准城市贫困的项目和政策中总结出我们所能学到的经验和教训。
二、 城市贫困的范围
测量城市贫困绝非易事。由于贫困具有多维特性,因此,单一使用货币来测量贫困引发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贫困线的设置、如何在国家层级贫困测量上处理城市生活具有较高的费用等问题上。城市概念的定义争论也颇多。
虽然解决这些辩论超出本文内容,但最近有关贫困测量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些研究新进展能让我们对城市贫困的特征和范围有更好的理解。Ravallion,Chen和Sangraula(2007)分析了近90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这近90个国家的人口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95%,同时,80%的样本人口有随时间变化的观测值。这项研究考虑了生活成本的差异,对特定国家的贫困线进行调整,对1993年、1996年、1999年和2002年4个时点的贫困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计。虽然各地贫困线不同,但平均而言,城市贫困线比农村贫困线高30%左右。估计中使用两条贫困线:1993的购买力平价的每天1美元和每天:美元(实际上为每天1.08美元和2.15美元)(表1)。
研究者们指出了这项贫困分析不足之处,即研究中所使用的城市概念不统一,以及在国家层级上贫困概念也不统一,以及跨国数据缺少统一标准和定义(这一不足之处是任何这类研究都将面临的共同问题)。
基于这项研究的结果,按照每天消费2美元的贫困标准,2002年发展中国家城市约有7.5亿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按照1美元贫困标准,约有2.9亿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13%。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人口约占国家总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期,按照每天1美元贫困标准,2002年,几乎一半的世界城市穷人在南亚(46%),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穷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34%)。使用每天2美元贫困标准,这一比例非洲为40%,南亚(SAS)为22%。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贫困发生率最高。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东欧和中亚(ECA),中东和北非(MENA)等地区的城市贫困发生率显著较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东欧和中亚(ECA)的城市贫困人口相对总贫困人口的比例最大,这是这些地区的高城市化率的结果。总体而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城市贫困发生率最低且拥有最低的城市贫困份额。
表1使用1.08美元和2.15美元每天的贫困线估计的
2002年的城市贫困(1993年购买力平价)
注:人头指数代表城市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城市贫困人口份额代表城市贫困人口占全部(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Ravallion,Chen和Sangraula (2007),
城市贫困发展趋势
1993-2002年,按每天1美元标准,全球城市贫困发生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按每天2美元标准,全球城市贫困发生率随全球贫困发生率呈整体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城市化为移民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对那些留在农村的人口也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减贫的步伐一直慢于农村,折射出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即“贫困城市化现象”。依据2美元每天的贫困线,总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7%,其中的4.8%来自农村减贫贡献,2.3%来自城市内部,还剩下1.6%来自人口转移效应(Raval-lion等,2007)。
区域趋势表明,按照1美元和2美元每天的贫困标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和东欧和中亚(ECA)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人头指数)相对于国家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下降的幅度较小;然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IAC)、中东和北非(MENA)略有增加(图1,图2)。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没有显示出明确的趋势。从城市贫困人口占全部穷人的份额来看,除了东欧和中亚(ECA)下降外,各地区都有所增加(图3,图4)。因此,世界银行2005年曾建议要求关注城市贫困。贫困的这种变化趋势在中国也很显著(Ravallion和Chen,2007)。
对未来的预测表明,城市贫困呈增加趋势,但全球大多数穷人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仍然分布在农村地区(按照1美元每天的贫困标准,在2040年全球大部分贫困人口将分布在城市;按照2美元的贫困标准,2080年,全球大部分贫困人口将集中在城市)。
三、 有关城市穷人的关键问题
虽然跨区域、跨国家、甚至城市内部,城市穷人差异非常大,但是可以总结出城市贫穷人的一些共性,如城市穷人面临着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诸多剥夺。在文献中提到的这些剥夺包括: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剥夺;②不足和不安全的居住条件;③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④应对风险的脆弱性,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环境灾害和健康损害风险等,尤其是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群;⑤抑制流动性和交通的空间问题;⑥不平等,如与不平等联系最密切得排斥。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1. 收入和就业
无论针对农村还是城市,贫困的实质是收入和就业机会受限。虽然城市经济体为一些人提供了机会,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都能从这些机会中受益。城市穷人面临着低技能、低工资、失业和隐性失业、缺乏社会保险、恶劣的工作条件等诸多挑战。在一些国家,贫民窟所处的空间位置、基础设施不足等也制约着就业。对商品经济的高度依赖致使城市贫困人口特别容易遭受冲击。
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现有的估计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70%。尽管非正规部门能为那些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能提供正规部门不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但是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工作环境较为糟糕、缺乏社会保险、缺乏法律保护,并且其自身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到储蓄不多的穷人。
城市贫困人口的失业通常较高,即就业不足。例如,在孟加拉首都达卡,最贫穷的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为10%左右,是最富有男性工人失业率(5%)的两倍。对于女性来说,约25%的贫困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而非贫困人口仅有12%失业(世界银行,2007a)。在一些城市,年轻人失业是主要问题,这与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联系越来越紧密,它可能会导致城市骚乱。根据2003年的数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平均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25.6%)和撒哈拉以南非洲(21%),而最低的是东亚(7%)。
童工问题在许多国家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特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为显著。虽然童工问题数据较少,但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对几个非洲国家的估计显示,在2004年,26%以上5~14岁的儿童从事经济活动。尽管童工通常是农村现象(孩子为家庭劳动),但它也存在于城市,尤其是服务部门、建筑部门和加工制造部门使用童工。在城镇工作的儿童更可能游离出家庭的保护。女孩通常是最脆弱的,经常被派送到非正规部门工作,或充当家庭仆佣。高比例的童工导致了非常低的学校入学率,进而影响到孩子日后机会。
2. 居住条件和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城市穷人的居住条件可能十分糟糕。城市和农村穷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挑战,如因过度拥挤、通常不卫生的居住条件所增加的负担。比起农村穷人,城市穷人的住房消费占更高的日常消费比例,这是城市土地价值较高的原因造成的。
虽不是所有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城市穷人住在贫民窟里。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即接近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联合国人居署,2006)(表2)。在非洲,72%的城市人口居住贫民窟,这一高比例令人吃惊。联合国人居署2002年的专家组会议对贫民窟的共识定义为:在城市地区一群人拥挤住在同一屋檐下,这群人在居住方面最少有如下4项剥夺中的一项:缺乏改良的供水系统;缺少改良的卫生设施;过度拥挤(3个或4个人住同一个房间中);使用非耐用材料建造房子。如果一个住户具有一项或所有这4项剥夺,他们将被算作贫民窟居民。获得安全的土地所有权被视为第5个指标,但这种类型的数据很难获得,因此不被包括在内。虽然使用这种方法测量贫民窟有一些不足,如缺乏空间维度、无法捕捉到时间维度上单个指标的改进等,但这些评估为理解在全球城市地区居住剥夺的范围提供了基础。
除了对贫民窟度量的争论外,贫民窟的一般特征可以描述为非正规定居点,其住房质量差、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不安全的土地产权。然而,关于贫民窟的大小尺度、位置和年限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贫民窟的位置或者位于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城市中心,或位于比较隔离的城郊地区。随着人们的日益富裕,较老的居民定居点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服务和质量更好的住房。
穷人往往住在不安全的公共或私人土地上,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是一个功能差的土地和住房市场、对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缺乏规划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安全的土地使用权致使城市贫困人口不断遭受被驱逐的风险,这阻碍了他们资产积累和获得信贷,抑制了他们把家作为创收活动的场所,还限制了他们在提供服务方面的投资。在达卡,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捐助者把缺乏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例证为在贫民窟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投资的一个主要障碍(世界银行,2007a)。
当发展机构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分目标7中的第11项,即要求改善最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而工作时,理解贫民窟的范围和特点已经成为优先事项。联合国预测,仅有少数国家能通过快速、持续地降低贫民窟增长率来实现以上的千年发展目标。那些最不可能解决贫民窟目标的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主要原因是迁移导致的,并且还在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没有足够能力去容纳新来的居民(联合国人居署,2006)。
表2贫民窟的区域特征(2001)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居署,2006。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住房、供水和卫生设施,交通运输、电力和电信等。许多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没跟上,因此,面临着严峻的基础设施不足的挑战。如果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供水和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估计将耗费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Foster,Gomez-Lobo和Halpern,2000)。
获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城市穷人来说尤为迫切。尽管城市地区比起农村地区,拥有较多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公共服务获得量,但是城市穷人获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仍是非常低,质量不高,并且还负担不起。在许多情况下,贫民窟内的获得率与农村地区大体相当甚至低于农村地区。
质量是一个主要问题,并且很难去测量。在一天内,仅提供几个小时的公共服务。穷人往往依赖于公共服务替代品的供应,这些替代品可能质量较差。提供方式包括自行提供或非正式的服务供应者(例如,水的供应商),或共用服务选项(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
对许多人来说,公共服务的可负担性也是个大问题。一些国家的贫困家庭比非贫困家庭需要支付较多,原因是他们由于缺少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私人供应商不愿意为低收入社区服务,因此,必须依赖昂贵的公共服务提供。根据来自47个国家和93个场所供水价格数据的一项研究结果,私人商贩卖水的平均价格是正规管道输送水价格的1.5倍,是点源供水价格的4.5倍,甚至比流动的批发商水价高12倍(Karuiki和Schwartz,2005)。
公用服务支出占贫困家庭的收入或支出相当大的份额。在阿根廷,五等份分组中最贫穷20%人口的家庭平均公用服务花费占总支出的16%。这个比重在五等份分组最富裕20%家庭中仅为11%(Foster,CEER和UADE,2003)。除了公用服务的消费成本,共用服务的连接成本很高,这可能让穷人负担沉重。连接成本包括连接费用和附加投资(这是一个家庭必须要投入的,如布管道和布线网)。在危地马拉,电力连接费是146美元,约相当于一个处于极端贫困线的5人家庭一个月的收入(Komives等,2005)。分期付费的融资项目成了穷人接受公用服务的重要替代品。
鉴于城市穷人需支付服务高费用率,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穷人愿意为服务支付大量费用就不足为奇啦。例如,在巴拿马,一项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穷人愿意为购买1立方水而支付0.46美元,超出每立方米0.21美元定价的两倍多(Foster,Gomez-Lobo和Halpern,2000)。
4. 风险
住在城里,特别是居住在高密度的贫民窟中,可能也意味着容易遭受到一些灾害、健康和环境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对穷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由于低收入人群定居点的位置,一旦遭受到自然灾害事件,城市穷人通常处于最高风险之中。这些定居点的位置通常是易遭受到洪水,山体滑坡的位置,基础设施薄弱或缺乏,住房建筑标准不合格,容易发生火灾或倒塌。有大量地震、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的例子,这些灾害给城市穷人带来深重灾难。从灾难中恢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对穷人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资源或足够的安全网来抵御灾害风险,同时,公共政策往往又优先考虑重建城市的其他部分(Fay,Ghesquiere和Solo,2003)。
关于城市居住,尤其是住在贫民窟中,有几个因素可能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贫民窟人口的高度聚集、不足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排水不畅、固体:的管理与室内污染等导致了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腹泻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如肺结核、肝炎、登革热、肺炎、霍乱和疟疾)(Montgomery和Hewett,2004)。质量差的住房条件也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的后果和增加了居民弱性(Cattaneo等,2007)。在城市地区,艾滋病的发病率非常高。非洲些城市地区发病率超过50%。在这些城市,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被细化分解到贫民窟后发现,尽管在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能更好地获得医疗一服务,但居住在贫民窟中居民的得病和死亡的比率是较高的。例如,在罗毕,在贫民窟地区腹泻患病率为33%,而在肯尼亚的其他地区,发病率低于20%。
生活在城市贫困区域的孩子面临较高的健康问题风险。但在拉丁美洲勒比,婴儿死亡率在农村和城市穷人中大体相同(Fay,2005)。很多国家城市穷人还面临着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问题,这个比率不低于农村贫困人口。在贫民窟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中,有l8%来自室内空气污染和急性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联合国人居署,2006)。艾滋病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特别影响到妇女和年轻女孩,她们转而危及到大多数人的安全。据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1200万儿童的父母因艾滋病死亡。
由于住房质量差并且过度拥挤,供水、卫生、排水、卫生保健和垃圾收集的不足,较之城市非贫困人口,环境问题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也是不成比例的。城市贫困人口还经常住在环境不安全的地方,如靠近固体垃圾场,遭受露天排水沟及污水沟污染的地方和工业用地附近,因为这些地方是城市穷人唯一可以获得居住的地方。
虽然气候变化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这方面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穷人受负面环境影响的风险,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海平面上升,升高的温度,对生态系统的不确定影响和增强的气候模式变化来进行的。
5. 位置,流动性和交通
尽管城市穷人住在别人不愿意住的地块上这一总趋势十分明确,但他们定居的空间位置模式在不同城市间变化很大。这是城市扩张,土地和住房的限制,低效的土地市场,以及糟糕的公共交通系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人居住在城市内,虽然住房质量较差,但那儿工作机会多并靠近市场;另外一些人居住在城郊,那儿虽不易获得劳动市场但是可以支付得起居住费用的位置。城市穷人选择的居住位置和交通模式显示了一个复杂的在居住位置、出行距离和出行方式之间的权衡(世界银行,2002)。
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较偏远但能负担得起的地方,这引发了较高的交通费用和较长的上下班出行时间。对于一些拉丁美洲的城市,如利马、里约热内卢,穷人上班距离通常为30或40公里,导致每天上下班路上平均花费3个小时(世界银行,2002a)。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居民生活在城市外的贫民窟被举证为缺乏公共交通而制约获得工作的例子(世界银行,2001)。居住在城市周边,特别是不能获得足够的交通服务,就意味着被排除在一系列的城市配套设施、公共服务和工作之外,恶化了社会排斥问题。基于社会构成的基础,贫民窟影响存在“近邻效应”。这种效应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产生朋辈影响(个人行为和机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在许多地区,附近区域的污名问题对穷人来说也成为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因为污名可能对人们获得就业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增加其他类型的歧视。据里约热内卢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在贫民窟的污名促成了贫民窟居民的失业和不平等(Perlman,2004)。
在其他地方的城市,特别是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市,居住模式的异质性很明显,穷人和非穷人混在一起居住。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往往有较短的上下班交通距离,往往依靠步行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在孟买接近三分之二的穷人步行上下班。很多人也依靠公共交通工具,虽然票价可能是非常高的。贫困家庭中主要挣工资的人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交通费用花费高达其收入的19%(Baker等,2005)。
6. 不平等
在获得服务、住房、土地、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可能会产生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在城市中,收入不平等尤其明显,因为在城市里贫民窟和现代都市区距离很近,反差很明显。在许多国家,在城市地区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内部生活水平很接近。不平等程度也似乎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虽然这并没有得到广泛地证明。巨大的在财富、服务和机会方面的差距可能导致穷人的挫败感、惶恐感和被排斥感。
在文献中所定义的排斥维度可分为三类:①经济排斥,表现为被排斥在平等获得经济/金融、社会,人类和自然资源之外;②公共服务排斥,被排除在获得基本服务之外;③社会排斥,限制人们公平参与地方和国家的社会生活(世界银行,2006)。对于城市穷人,排斥是非常明显的,如日常生活中,从教育不平等到获得工作空间的障碍上。
虽然在不平等、排斥、犯罪和暴力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在一个稀缺资源分配不均或弱制度环境下使用权利的背景下,犯罪和暴力被引证为会更加频繁地发生,这是城市非常典型的一个特性(联合国人居署,2006)。有证据表明,犯罪和暴力在城市往往有较高的发生频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城市内的暴力活动水平的高低是基于附近地区的收入水平,收入较高的地区将遭受财产相关的暴力犯罪,然而严重暴力集中在收入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城市外围的贫困区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和排斥的城市似乎也很容易导致不安全,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南非贫民窟举行的抗议活动(2005),发生在洛杉矶、内罗毕和里约热内卢的暴力冲突等。
当前瞄准阻止犯罪和暴力的方法集中于改善自然环境上,这种方法被运用于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系统、停车场和娱乐空间、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和那些最易遭受暴力和犯罪的市区等方面(Mtani,2002)。
四、 城市贫困的区域特点
除了全球城市穷人的几个一般共性特征外,城市贫困的几个区域特征也被总结出来。下文中对城市贫困进行的跨区域论述时行文体例不一致,因为城市贫困在拉丁美洲得到很好的研究,但在其他地区则未能得到系统研究。例如,在非洲和南亚地区,关于城市穷人的研究就很难获得。这尤其表明,对城市贫困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1)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随着城市地区的增加,非洲是城市化最迅速的地区。使用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该区域大约有40%的城镇居民是穷人;使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近70%的人口是穷人(Ravallion等,2007)。此区域的城市化是发生在特别具有挑战的环境背景下,而其他区域没有面临历史上的全球竞争,也没有艾滋病对家庭、社会安全网和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等压力,但有充足的应对外来迁移的办法。大约有6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全球来看,城市地区比在农村地区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这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穷人(UNAIDS,2004)。
该地区的另一个特点是贫民窟最盛行和最低水平获得安全饮用水和改良卫生设施。在全部城市地区,自来水获得率仅有约36%,五等份分组中最贫困的一组人口几乎没有人能获得自来水。除南非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超过1%的最低五等份家庭能够获得自来水(Banerj ee等,2007)。只有约一半的人口能获得改良的卫生设施。对这些基本服务的有限获得对健康和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水传播疾病在非洲国家城市非常普遍,如疟疾;2003年,据估计,约2亿非洲人生活在城市疟疾流行地区。
(2)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城镇人口比例(28%)和总贫困人口比例(25%) -直保持相对稳定,但该地区在世界上仍然具有最大的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按每天1美元标准,有1.35亿城市贫困人口;按每天2美元标准,有2.96亿城市贫困人口,2002)。国际上有5个特大城市落在南亚地区,城市贫困人口大量集中在这些城市内。在孟买(人口1 880万)、新德里(人口1 600万)、加尔各答(人口1 450万)、达卡(人口1 300万)、卡拉奇(人口1 220万),城市贫民窟蔓延和城市管理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要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仅印度一国,就占了17%的全球贫民窟居民(联合国人居署,2006)。这类城市其中一些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达卡在2020年人口预计将达到2000万,变成世界上第三大的城市。虽然城市化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为一些人提供机会,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个增长不产生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尤其是会影响到穷人,其中一些人是从农村新到城市的移民。在印度,估计每年有100万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但有组织机构的服务部门在过去十年中每年仅创造76 000个新就业职位(Glinskaya和Narayan,2007)。在该区域,童工是备受关注的,“儿童,主要是女童因商业性服务在诸如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德里的城市中心被拐卖”(美国劳动部,2006)。
(3)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城市化进程继续稳步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推进,约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比其他地区,这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城市化水平,虽然预计它将会大幅增加。该地区已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城市的贫困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城镇居民,但导致了非正规就业的显著增加,这仍然将是今后10年本地区城市贫困的一个特点。在东亚,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居住在贫民窟中,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居民都是穷人(跟其他地区一样)。这些贫民窟居民大部分都在中国(联合国人居署,2006)。
预测显示,该地区城市化将继续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到2030年该地区大多数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同年,估计显示,超过60%的中国人口、80%的菲律宾人口将居住在城市里。预计增长主要将发生在城市周边。
(4)中东和北非。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该地区60%的人口住在城市。在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家,这一比例分别高达80%和90%。由于高出生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国际劳工流人,该地区城市增长速度高居全球第二。该地区城市还有另一个特点,即青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伴随着高出生率,到2025年该地区儿童人口估计将增加约30%,也门、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和阿曼甚至更高(Lynkeus Censis,2004)。
此地区的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展反映在总体低的城市贫困发生率上。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水平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该地区的城市穷人面临特定的挑战,如缺水,在某些情况下,还非常严重;高比例的城市青年人口和与之有关的较高的青年失业率。在该地区和一些国家社会不平等也很普遍。社会不平等与异常高的青年失业率和政治不稳等问题一旦搅和在一起,就将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
(5)东欧和中亚地区。这个区域高度城市化,使用斯拉夫语和加入欧盟的国家城市化率是最高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在该地区不再明显,但城市向城市迁移仍在继续。城市贫困低于其他许多地区。该地区城市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转型和国有企业的衰败导致的。大多数城市贫困人口集中在二级城市,它容纳了大约85%的城市人口。这些二级城市一般前身为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大型工业企业的集聚中心(世界银行,2006c)。随着许多行业规模的缩减,现在就业机会很少。
该区域城市穷人相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恶化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随着转型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的人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贫民窟,尤其是城市郊区。这些地区一般都得不到很好的公共交通服务,这导致了社会排斥和隔离的问题。
(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该地区高度城市化,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该区域大约有60%的贫困人口,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贫困的城市化,预计将继续在某些地方持续下去,尤其是在中美洲,这个区域特别容易遭受自然灾害,这将严重影响城市穷人。
拉丁美洲的城市往往是高度隔离的,这导致了社会排斥问题和“近邻效应”,这又反过来可能减少就业机会和降低教育成效。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西的贫民窟,在该地区的犯罪和暴力问题,也是该地区的一个重大挑战,尤其影响城市贫困人口。
五、 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和项目:我们能学习什么?
自2000年以来,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开始力推采用国家推动的方法来进行减贫,这标志着在扶贫方式上发生了转换。超过50个低收入国家已制定了国家减贫战略。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调整了他们活动来配合推动这些国家减贫计划的实施。在国家减贫战略中,把共享式增长作为减贫的主要驱动力得到广泛认可,其实现路径为:实施促进较高增长和在人口中(尤其是穷人中)实现公平利益分配的政策。这一途径十分有利于促进城市减贫。而且,这一共享式增长在城市化的推动下是可持续的。
(1)经济增长。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50%~80%。一项全球14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在减贫领域做得不错的国家,都通过实施系列政策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些政策包括: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产权界定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政策、实施有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完善要素市场功能的政策、促进能广泛获得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政策等(世界银行,2005b)。另一项来自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发现,在1998-2003年,那些经历了持续增长并经历了贫困大幅减少的国家,城市贫困对政策的反应比农村贫困更加积极。在这一时期,不同国家因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发展初始状况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其贫困减少的程度也不相同。在一些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例如,CIS)向穷人倾斜的国家,贫困下降的速度快于预期(世界银行,2005c)。
越南是一个成功地处理好增长和减贫(包括城乡贫困)关系的例子。这主要归功于贸易自由化、促进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在1992-2003年,越南的城市贫困人口每年按照11%的速度在降低(尽管农村每年以4.2%速度在减贫)。伴随着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巨大需求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扩展(满足了人们进入非正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非农产品和劳务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越南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国家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设置了优先序,把基础设施建设定位于那些贫困人口多、增长潜力大的农村地区。在城市,推动资本充足和技能丰富的城市中心区域发展;在农村,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财政收入向农村地区转移。此战略对增长和减贫的影响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Besley和Cord,2007)。
除了推出培育经济增长的促进政策,各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城市贫困的挑战。通常情况下,项目和政策是广义国家减贫战略的组成部分。针对10个国家,开展了一项评审,看一看减贫战略中有关城市问题的论述(Baker和Reichardt,2007)。评审结果发现,通常的城市问题和那些与有代表性城市穷人相关的问题在减贫战略中未被很好地论述。在那些对城市化和城市贫困问题有坚实分析基础的国家,在减贫对话中对这些问题有很好的论述。这一分析为减贫战略(PRS)提供直接的信息。城市利益相关者被纳入减贫战略(PRS)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在减贫战略中覆盖城市问题。最后一个主要发现是,实施城市政策需设置优先序和需强有力的政治承诺。这些发现指出,需要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进行投资,确保研究结果被广泛传播,并与政策制定者进行讨论以更好地让他们了解政策有关的过程。
瞄准城市穷人的项目可分为3类:①瞄准改善居住条件的项目。主要是对贫民窟进行升级改造,同时还可以通过公共房屋计划、宅基地供应和服务计划提供信贷和住房贷款,租金管理,土地所有权转让,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用事业补贴等。②瞄准于改善收入的项目。旨在提高穷人的收入,如就业培训,发展微型企业,提供孩子料理服务。③瞄准于最脆弱群体的安全网项目。这类项目有现金转移支付,粮票,供餐方案,费用减免,补贴,及公共工程项目。
(2)改善居住条件。在过去的15年里,一些国家在减少和稳定贫民窟增长率方面取得进展。巴西、埃及、墨西哥、南非、泰国和突尼斯的成功是因为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政治承诺,承诺改造大规模的贫民窟和通过贯彻土地方面法律、法规改革、调整项目和实施包容性政策等为穷人提供服务(联合国人居署,2006)。
总体而言,在瞄准城市穷人的项目中贫民窟改造可能是最常见的。贫民窟改造项目通常侧重于提供基础设施(水和卫生设施,废物管理,电力,道路),如果范围再宽一些的贫民窟改造项目还包括旨在提高土地使用权保障,改善社会基础设施,提升住房质量,获得信贷,以及获得社会项目(健康和教育,白日料理,职业培训和社区管理)的干预措施。贫民窟改造项目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盛行。
最近的一项研究回顾了过去的30年,世界银行为改善居住条件开展贷款业务的经验教训(Buckley和Kalarickal,EDS,2006)。贷款包括278个项目,分布在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总体而言,研究者发现,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大规模政策有关的援助需求,世界银行的住房贷款是积极有效的。这种贷款组合取得了显著成绩,其贷款总额占全部城市贷款的一半以上。然而,研究还发现,世界银行的住房贷款已经偏离了贫困定位的核心,因为支持低收人群体建房的贷款仅占10%这样一个非常小的份额,支持低收入国家的住房贷款仅占20%。这种偏离减贫做法的原因是,捐助者关注焦点的变化(Viloria-Wil-liams,2006)。
然而,最近又涌现出一股对城市贫民窟改造项目的兴趣,这可能与城市化推进以及城市穷人日益迫切地需要解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有关联。2005年,一项对内罗毕贫民窟居民的调查识别出他们想优先发展的4个领域(世界银行,2006d)。他们的反应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上:厕所(24%),供水(19%),医疗诊所和服务(13%),电力(12%)。
虽然出现了一些经验证据(如关于在为城市穷人成功交付基本服务方面,总体上,贫民窟改造项目是相当积极的),但有关贫民窟改造的经验和影响的证据是有限的。从现有的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关于贫民窟改造项目的评估中可以归纳出贫民窟改造项目带来的好处,包括通过建造房屋和小商店买东西改善谋生机会;环境、健康和安全状况改善;能获得较好的路;安装路灯后犯罪减少;提供娱乐中心和青年培训场所等。提供土地使用安全保障激励了业主投资自己的家园建设。在一些情况下,社团组织积极寻找其他资金来源来建设社区,包括参与社区规划和规划实施。最近有一篇综述文章指出:“整体的、综合的升级改造项目使居民能够发展和提升他们的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磨炼他们的领导能力,比其他社区拥有同样个人利益的普通市民更加享受”(Viloria-Williams, 2006)。
一项关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改造项目的研究发现,该项目覆盖范围得到很大扩展,包括负责项目社区的水和垃圾收集(Soares,2005)。然而,关于财产价值、健康结果、盈利状况等,没有进行对这些方面的改善状况进行深入评估。
一项对印度3个贫民窟改造项目的评估发现,改造项目为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这种改善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的,如改善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花费较少的时间去取水,改善了棚户区的面貌,以及财产价值的升值等(Amis,2001)。在孟买,一项采用参与式和响应需求的方法(以前的方法不使用参与式方法)实施的贫民窟卫生项目,展示了在服务交付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功之处。
墨西哥项目“Piso Firme”,开始于2000年,内容为改善住房,即通过用水泥地面替换以前肮脏的地面,以改善儿童健康,减少肠道寄生虫感染。这个项目的影响评估者把幼儿健康的显著改善归因于这个项目,因为项目实施后测得了寄生虫感染率、腹泻、贫血患病率下降。测量结果还发现,孩子的认知能力(包括语言和交流技巧)得到显著改善。同时,评估结果也发现,项目实施后,成年人关于他们的住房和生活质量有较高的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的困扰(Cattaneo等,2007)。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项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影响评估。土地所有权的安排是一些贫民窟改造项目的部分内容,评估发现使用土地所有权抵押以获得贷款和私人住房投资方面显示出积极的影响(尽管非常适度)。此外,土地所有权降低了户主的生育率和家庭人口规模。这些规模较小的家庭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投资更多(Galiani和Schargrodsky,2006)。 审查回顾世界银行项目中的经验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点(Buckley和Kalarickal,2006):①如有可能就在原地对贫民窟进行升级改造,这在许多国家具有经济意义。把贫民窟夷为平地以满足市区重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大量市区改造项目成功的例子,这些项目涉及增加市区的密度,以容纳中低收入家庭和混合用途。②搬迁也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在许多人口密集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运河)受到了贫民窟居民的侵占,恢复退化服务的成本超过对居民家庭搬迁到其他地方并提供更好设施的成本。当贫民窟位于高风险或环境风险区域时,搬迁也是适当的。③在地方的政治支持下,把责任下放到适当的最低层级和实施问责制对于贫民窟改造项目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基于这些经验和教训,新一代的贫民窟改造项目正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因素部分。世界银行最近在巴西、牙买加、越南、伊朗和其他地方的项目也被设计用来解决就业、犯罪和暴力、儿童保育、青年、卫生保健等问题。世界银行对住房贷款的审查回顾要求改进银行的住房贷款方法,尤其强调为低收人家庭住房,特别是为贫民窟住房改造(尤其是在非洲)提供支持。回顾审查还建议,对攀升的援助需求做出回应,尤其是在提供住房补贴方面,强调通过改进融资和提高政府支出瞄准穷人的有效性,和通过慎重的扩展住房贷款的范围。除了这些建议之外,投资地方能力建设和做好长期规划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投资的主要作用是可能有助于防止贫民窟的孳生扩散。
(3)收入和就业项目。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核心是就业。有一系列旨在提高穷人收入的项目,如就业培训,发展微型企业和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在这些项目中,如幼儿照料中心和小额贷款在城市贫困区域中有巨大的推广潜力。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例子。
大多职培训项目是针对青年开展的,但培训的结果好坏兼有(Betcherman等,2004)。一项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评估的跨国评估概要显示,培训对被培训对象的影响表现为负面的和通常不显著(或者适度正效立)(Kluve,2006)。然而,在工业国家,就业培训项目被发现有积极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证据很有限。4项有关拉丁美洲(阿根廷、智利、秘鲁和乌拉圭)就业培训项目的评估显示,把培训和工作经验与其他服务事项(包括心理发展和职业评估)联合起来的密集投资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执行能力在公民社会、私人部门以及灵活的竞争性的和分散的服务交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培训对就业和收入在短期内(培训后几个月到一年)似乎有相当积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或没有人知道是否有影响。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TVE)的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职业课程与就业之间的影响非常强,但它仅仅有选择性地与高工资有联系(Ryan,2001)。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支持培训与就业和收入正相关的证据,这似乎与缓慢的就业增长和疲软的就业需求的宏观环境相关(亚当斯,2007)。
在减少贫困方面,小额信贷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由于它能够帮助穷人积累资产,增加收入,减少其应对经济压力的脆弱性(CGAP,2006)。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贷款项目也显示出积极的影响。然而,一些城市穷人仍然没有获得来自银行的小额贷款,因为银行不愿意给没有抵押品的穷人贷款。就孟加拉而言,著名的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不在城市运营,原因是在城市运营被视为具有风险(世界银行,2007a)。以上的论述反映,需要在城市穷人中推广小额信贷。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约束,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是没有足够多的托儿所。来自危地马拉的证据表明,那些把孩子送去参加幼儿照料项目的妇女,他们的收入提高了30%(Ruel等,2002)。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就大脑发育和学业成绩来说,孩子的早年时光很重要。参加幼儿照料的儿童比不参加早期干预项目的儿童有更强的学习动机,更好的成绩和更高的对自身的关注。早期干预也已被证明能通过较早提供重要的学习技能而提升成功就业前景(Young,2003)。
(4)社会安全网项目。安全网项目瞄准于穷人或那些容易受到贫困冲击的人群。在城市这些项目十分重要,因为城市更加依赖市场经济,这使城市家庭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虽然有对安全网项目的详细回顾,但对城市地区这些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相关的问题却很少进行分析。
墨西哥的Opportunidades项目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安全网项目,该项目目标十分鲜明,即为城市穷人而设计的。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起源于Progresa项目(主要在农村地区运行)。该项目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现金,条件是正规学校的出勤率和定期的预防保健服务接受情况。在2002年,该项目扩大到城市地区,当时,它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对城市穷人的瞄准和调整等。例如,有工作的母亲没有加入或退出这个项目,因为活动的时间与她们的工作时间相冲突(Latapi和de la Rocha,2004)。
虽然该项目最初在城市和农村的受益对象的瞄准是一样的,但项目对两地区家庭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城市,项目对入学、毕业、辍学的影响远小于在农村地区(Parker,2004)。这与城市较高的机会成本以及到学校的高花费有关系(据报道,这个花费约占用80%的学校补助金)(Latapi和de la Rocha,2004)。项目对城市受益者的一个最大的(意外)影响为家庭环境的改善,例如财产管理规范化,获得基础设施服务,升级建材质量。
在城市设计和实施这类项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包括来自瞄准15~24岁相对脆弱的年轻人方面的挑战。给定福利异质性条件下,即使在非常小的区域内,例如在社会经济特征混合的贫民窟内,地理定位可能是困难的。资产调查也很困难,因为比起农村家庭,那些可能有资产的城市脆弱家庭甚至更加容易陷入贫困。城市家庭通常缺乏产权,这就可能把他们从能够参与社会项目的资格名单中排挤出去。
城市贫困青年是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通常有更高的失业率,并易被暴露于犯罪和暴力,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诸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和就业培训等社会安全网项目可以帮助该群体最小化其面临的风险,便利这些处于脆弱期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编译者:张海森)
前瞻性最优救助资金分配方案
Adrian Wood牛津大学教授、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原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救助机构没有完全接受在各个国家间分配救助的Collier-Dollar模型——尽管该方法也以减少贫困为目标——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与千年发展目标暗含的救助分配方式存在分歧。在更广泛的救助分配模型中,救助机构既关注未来贫困的减少也关心解决眼下的贫困问题。上述分配方式只是更普遍的救助分配模型的两种特例。该模型可以根据发展中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在分配公式中添加减贫调整项能够解决两种分配模型的分歧。
关键词:外国援助;减少贫困;Collier-Dollar模型;千年发展目标(MDGs)
一、 引 言
Collier和Dollar (2001,2002)这两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献实证地提出了一个在贫困国家中分配世界援助的模型,并最大程度减少贫困。该模型广被各个救助机构所了解,深刻影响了著名救助机构的行为。 然而,实际的救助分配方式不断与Collier-Dollar(C-D)模型发生背离,即使是那些以减少世界贫困为目标的救助机构也是如此。背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非洲的救助超出了C-D模型建议的数量,导致对其他落后地区特别是南亚地区的救助不足。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和Millennium Project (2005)进一步强调了该现象。可是,鉴于非洲发展缓慢并难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2005年,G8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却继续呼吁增加对非洲的援助。
下文将论证出现这种显著背离的原因,正是C-D模型没能完全契合救助者(以及纳税人)减少世界贫困的偏好。C-D模型遗漏了时间变量,导致判断不同国家对援助的迫切程度仅仅依据当前的贫穷程度,然而救助机构和人们更关心是——基于理性和道德的理由——既包括当前也包括未来的贫困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救助机构追求千年发展目标导致给予非洲过多援助而对亚洲贫困地区援助不足的原因是:①救助机构希望减少当前和未来的整体贫困程度;②认为非洲减贫的速度远低于亚洲贫困地区。
救助机构正在救助分配中试图调偏好和理念,MDGs与C-D模型不仅在理论上对长短期的考量不同,而且目标导向型的MDGs与最大化约束下的C-D模型存在着实践上的差异。本文旨在综合C-D模型和MDGs并提供一个博采众长的模型。

图1揭示了综合二者的基础所在,纵轴表示一国的贫困数量(贫困率乘以人口),横轴表示时间,从现在到未来T0 C-D模H分配救助只依据初始贫困数量H0:一国初始贫困数量越大,就应该分配越多的救助。而以MDGs为基础的分配方案则主要关注H0到HT之间的斜率,一国贫困减少得越慢就越应该获得救助。下文将详细阐释该观点,第二节扼要重述了C-D模型;第三节总结该模型对救助者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第四节介绍了一个考虑前瞻分配模型;第五节说明C-D模型和以MDGs为基础的分配方案只是前瞻分配模型的两个特例;第六节鼗发展中地区的实证数据应用于该模型,并将分配方案与前述两种模型进比较;第七节分析救助机构应该如何修正现在的C-D模型,以便修正后的C-D模型能够实现前瞻目的;第八节总结全文。
虽然模型用于国家间的救助分配,但是该模型也适用于区域间的救配。表1采用世界银行地区分类,将中国和印度分别作为独立的地区,分计8个地区。以2004年为基期,表格展示了每个地区的救助分配的数值。贫困数据包括初始人数比例、预计的贫困人口减少率(从2004-2030年)和收入弹性(2004-2015年)都来自于世界银行。本文将人口加权的地区平均CPIA分数作为Pi的代理变量。
表1 影响救助分配的变量
表2展示了一个最优救助分配。第一列数据是每个地区初始贫困人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表1),第二列是在贴现率为0、期限为25年(对应于1990-2005年的千年发展计划和2004-2030年的贫困预测表)情况下的减贫调整项。政策制定者赋予每年贫困程度相同的权重,且不考虑期限外的情况。第三列是在进行援助之前的未来贫困的“折现值”。第四列是最小化世界未来总贫困贴现值(第三到数据最后一行)的地区间救助分配方案。世界救助总额根据救助机构2005年的承诺约为1 000亿美元,资金分配方案的百分比是救助资金绝对数量的百分比。分配方案是基于C-D模型中的 ,并使用C-D(2002)变型I里面的b3,b4,b5(分别是0.54,0.02,0.31)。
,并使用C-D(2002)变型I里面的b3,b4,b5(分别是0.54,0.02,0.31)。
表2基于减贫调整的C-D模型的救助分配情况(r=0,T=25)
中等收入地区在表格的下半部分(东亚、拉美地区、欧洲、中亚以及非洲中东部和北部地区)没有获得救助,甚至拥有超过1亿贫困人口的中国也没有获得救助。该结果与C-D(2001,2002)文献相似,尽管地区加总数据掩盖了中等收入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而夸大了该问题。其产生原因是,对C-D模型中的 而言,救助只能通过增加国家收入减轻贫困,从而更有效的救助方式是将救助分配给那些每1美元国民收入对应穷人数量(Hi/Yi或者hi/yi,)更高的地区——Hi/Yi是一个指示变量,正如表2第五列所示,中等收入国家相对非洲和南亚获得援助较低的原因,既是因为较低的贫困数量hi也是因为较高的国民收入yi。
而言,救助只能通过增加国家收入减轻贫困,从而更有效的救助方式是将救助分配给那些每1美元国民收入对应穷人数量(Hi/Yi或者hi/yi,)更高的地区——Hi/Yi是一个指示变量,正如表2第五列所示,中等收入国家相对非洲和南亚获得援助较低的原因,既是因为较低的贫困数量hi也是因为较高的国民收入yi。
低收入地区间的救助分配乍看让人惊讶。尽管存在着前瞻的减贫目的以及相对南亚更慢的预期减贫速度,非洲地区仅得到总救助的1/3。印度尽管拥有五倍于南亚其他地区的初始贫困人口数量以及更慢的预期减贫速度,印度得到的援助也少于南亚其他地区。对于该结果的解释是,不同地区对援助利用效率不同成为影响分配的主导因素,抵消了在需求迫切程度方面的差异。一个低的CPIA得分和一个低的贫困弹性的组合导致非洲地区获得的减贫救助大幅度减少。在印度一个远低于南亚其他地区的贫困弹性和一个稍高于南亚其他地区的CPIA评分,使得把救助更多地分配给南亚其他地区而不是印度更有效率。
表2的最后一列是援助分配的实际情况,显示援助分配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的巨大差异。中等收入地区获得了总救助金额的一半,与理论预期中完全不给中等收入地区救助相比较,证实更多的援助分配并不以减少贫困为判断标准,而有着其他种种判断标准(Alesina&Dollar,2000;C-D,2002)。低收入地区的分配也同样存在着差异:印度实际上获得的援助仅占低收入地区总援助的3%,即世界总援助的1.5%,远低于预期中26%的世界总援助份额,反映了其中存在的偏误;并且非洲实际获得的救助额是南亚其他地区的4倍,而在理论上的最优分配中,二者的比例不会如此悬殊(尽管非洲地区实际获得援助份额非常巧合地与理论上最优份额相似)。
表3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展示了如何在具有不同的贴现率和时间跨度情形下对低收入国家进行救助分配,表格中间行和表2的假设一样都是0贴现率、25年期的情形。表格上面2行表示更少考虑未来的情形:C-D模型作为本模型的特例之一,其期限仅为1年,在第1行给出其结果;一个25年期限和10%贴现率的组合情形展现在第2行。表3的最后2行展示的是更加重视未来的情形:表2中虽然也假设了O贴现率,但期限设定为25年,而此处的第4行和第5行则将期限分别拓展为50年和100年(这正是MPGs作为本模型的特例,最大限度地看重未来的减贫情况)。
表3 r和T不同取值对于救助分配的影响
表3的第一列显示了非洲在低收入国家救助额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也是在整个世界救助额中所占的份额,因为中等收入国家按照模型分析没有获得救助)。第一行,救助的目标是减少当期的贫困,尽管拥有40%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非洲竟然完全没有获得救助。鉴于表l中非洲的CPIA分数和贫困弹性,以及对C-D模型中对“救助促进经济增长功能”的假设参数值,对非洲进行的任何救助都毫无效率可言。[这一结果与C-D(2001,2002)文献不同,在那篇文献中,即使完全不考虑未来,非洲地区仍然被分配了大量援助,主要由于C-D模型中的贫困弹性比表1中的数据更有利于非洲。]
然而,从表3的第一列由上往下看会发现,尽管非洲的救助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在逐渐变得更加前瞻的模型中,对非洲分配的救助份额迅速上升。假设r=0,T=25,非洲获得的救助份额从O增长到了1/3,T=50的时候,救助份额增长到了2/3,T=100的时候,非洲获得了全部的救助。印度获得的救助在低收入国家救助中占有的份额(第二列)相应的减少,但印度和南亚其他ECHO 处于关闭状态。地区所占份额的相对比例(第三列)变化不大,而非洲和南亚其他地区所占份额的相对比例(第四列)迅速增加。
表3中的数字变化说明了救助者不同目标对救助分配结果的影响,表4中,r和T保持不变,显示分配结果如何随增长函数的参数值以及贫困弹性的变化而变化。第一行是基准情形,和表2相同。下面2行改变b3和b5,分别增加和减少分配政策的敏感性分数[这是C-D (2002)中的变型Ⅲ和变型Ⅳ]。接下来的2行改变b4分别增加和减少救助的报酬递减率。最后1行将b3、b4和b5都恢复原状,令所有地区的贫困弹性一致等于-2,正如C-D(2002)所假设的。
表4救助分配对于C-D救助——减贫方程参数的敏感性
表4的后4列展示了前述变量的种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主要考察了4个方面,和表3的考察内容相同(所有的变化都是建立在不给中等收入地区任何救助的基础上)。比如,更少的政策敏感性分数大幅度增加非洲地区获得的援助,减少印度获得的援助使其接近于0,并使南非获得的援助也略有增加。相比之下,更高的救助报酬递减速度使得印度获得的份额翻倍,而南亚其他地区(更大程度上)和非洲地区获得的救助减少。消除贫困弹性的变化对印度基本上没有影响,但原本更加具有贫困弹性的南亚其他地区获得的救助减少至0,而非洲获得的救助份额从原本的1/3升至3/4。
Cogneau和Naudet(2007,表4)的文献表明,他们提供的前瞻救助分配模型也对贫困弹性的变化十分敏感。他们还指出,正如表4的最后一行,在将各地区的贫困弹性统一设定为-2之后,按照C-D模型的 进行估计,非洲将得到几乎所有分配给低收入地区的救助(虽然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何1/3的救助被分配给了中等收入地区)。当Cogneau和Naudet允许贫困弹性随国家不同而变化,则非洲只能获得低收入地区救助的一半份额(在目前的计算中,如果使用基准参数值,并令r=0,T=35,则非洲也将获得低收入地区救助的一半份额)。
进行估计,非洲将得到几乎所有分配给低收入地区的救助(虽然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何1/3的救助被分配给了中等收入地区)。当Cogneau和Naudet允许贫困弹性随国家不同而变化,则非洲只能获得低收入地区救助的一半份额(在目前的计算中,如果使用基准参数值,并令r=0,T=35,则非洲也将获得低收入地区救助的一半份额)。
总的来说,表3给出的在地区间进行救助分配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世界减贫目标的时间跨度。如果只考虑短期情况,完全不给非洲地区分配救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将救助分给非洲以期实现减贫目标是非常低效的。相反,如果考察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将救助全部分配给非洲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而表4中的数据则提示我们,对最优救助方案存在的分歧可能是由于对救助在减少贫困方面起到的效果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分歧所导致的。
二、 在实际中的应用
图1明确揭示了本文的主旨:合理分配救助实现高效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同时兼顾解决现在和未来的贫网。本节将探究该观点能否以及如何在救助机构分配过程中应用。
建立一个所有救助机构都能接受的模型并不现实,每个机构特定的分配惯例难以取代。这些惯例在不同机构间中于其所处环境而大相径庭,影响机构惯例的环境既包括政治环境(比如减贫在机构目标中所占的分量)也包括行政环境(比如在救助过程中存在多边或双边合作,以及双边合作中是否有多个机构参与)。大多数文献只能为此提供一些改进的建议而已。
救助机构应用简单的分配公式而不是复杂的最优化模型,虽然这些简单的分配公式背后其实也都有一定的模型作为支持。典型的救助分配公式中的分配比例Si,是基于一些国家的贫困程度以及政策质量而综合制定的。
 (1)
(1)
 即贫困的数量(贫困率乘以人口),Pi是政策系数,)γ是政策的重要性。一些救助机构的分配公式还包括诸如救助对减贫的效果等变量,此时Piy可以看作对救助效率的综合度量。
即贫困的数量(贫困率乘以人口),Pi是政策系数,)γ是政策的重要性。一些救助机构的分配公式还包括诸如救助对减贫的效果等变量,此时Piy可以看作对救助效率的综合度量。
和C-D模型一样,公式(1),只关注目前的贫困情况,相对于以减少贫困为目标的机构,倾向于减少非洲的救助,因此并没被采用(或调整后使用)。同样,这样的公式也与千年发展计划的目标冲突。解决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调整衡量贫困的方法,使现在与未来的贫困都被纳入到衡量体系中。公式调整为:
 (2)
(2)
 (3)
(3)
 是各国的减贫调整项,在以前,
是各国的减贫调整项,在以前, 是对未来T年贫困减少速度的预计,r是当前政策制定者相对于现在折现未来贫困的贴现率。
是对未来T年贫困减少速度的预计,r是当前政策制定者相对于现在折现未来贫困的贴现率。
修正后的公式(2)和公式(3)可以被应用于救助机构认为最好的任何贫困衡量指标。贫困率 可以是任何指标(如贫困人口等)以及基于任意贫困衡量维度,前提是该指标以合理的方式综合为单一的指标(MDG就是这么做的)。减贫速率
可以是任何指标(如贫困人口等)以及基于任意贫困衡量维度,前提是该指标以合理的方式综合为单一的指标(MDG就是这么做的)。减贫速率 必须根据制订的贫困率指标计算,并调整人口增长的影响。
必须根据制订的贫困率指标计算,并调整人口增长的影响。
修正后的公式存在一个明显的操作问题,如何预测每个国家减贫的成果。我们很难期望每个救助机构都亲自做出全面的预测导致难以实现提高救助协调程度的目标。一个较好的方法是由大型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提供一个所有救助者共同使用的预测结果。在该领域基于人均收入的贫困预测成果(比如:World Bank,2007a,表2、表3)和不基于人均收入的千年发展计划实现程度的预测成果(比如:World Bank,2007b)都已有出版。
测算未来的救助应当考虑到各国未来减贫的速率 。正如公式(3)基于简化假设:某一时期的救助将减少未来的贫困程度却不改变未来的减贫速率。实际上,救助机构有理由相信,现在对各国所分配的救助将潜在地提高各国未来的减贫速率
。正如公式(3)基于简化假设:某一时期的救助将减少未来的贫困程度却不改变未来的减贫速率。实际上,救助机构有理由相信,现在对各国所分配的救助将潜在地提高各国未来的减贫速率 ,比如救助可能会消除某些贫困国家发展的瓶颈,因此,应该针对这些国家设定一个向上调整的减贫速率
,比如救助可能会消除某些贫困国家发展的瓶颈,因此,应该针对这些国家设定一个向上调整的减贫速率 。
。
修正模型的另一个操作问题是如何选择方程中的r和T,不同的选择将影响各国调整项的相对大小(给定各国的预测减贫速率)。政治家和其他高级政策决策者不太可能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偏好在模型中的具体初始参数值,但他们的偏好参数值可以从他们在r和T不同的各种分配方案之间的选择中推断出来。他们更可能接受模型中经常使用的参数值,甚至所有的救助机构或许都会同意DAC框架下设定的r和丁。
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是设定r=O,T=25。将期限设为25年基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因为他正好可以匹配1990—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而0折扣率则有助于获得对未来贫困更大的关注程度。甚至在接下来的25年中,他们将更加关注当下的贫困,当然这里几乎没有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讨论。
从前文对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修正后的公式(2)的用途,表5是根据与表3相同的贴现率,.以及期限T计算出来的分配方案,其中假设),r=2。表5的前4列与前面的表格相同,都显示了应当如何将救助在低收入地区进行分配;最后一列数据表示分配给中等收入地区的救助份额,尽管以减贫为目的的教助者不希望救助流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自行支付减贫所需要的费用,并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来融资。
表5基于减贫调整项公式的救助分配
表5A部分的第1行,一个较低的期限T带来的结果与未修正公式(1)得到的结果相似:非洲地区只获得了低收入地区总救助30%,而印度地区则获得了一半;在考虑对贫穷的不同程度关注时,将期限T增加到25年,使非洲得到的份额增加了10%,并减少印度地区获得的救助;将T增加到50年,使非洲地区获得的份额与印度接近;而将T增加到100年,非洲地区获得的份额增大至62%,并使印度地区获得的份额减少至36%。
总体而言,表5的结果和表3十分相似,然而,参数的选择对最终分配份额的影响变小很多,尤其是对非洲而言。此外,中等收入地区在表3中无法得到任何救助,而在表5中,中等收入地区获得了可观的救助。由于二者的减贫目标是相同的,表3与表5的差异源于二者对救助在减贫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的理解不同。更准确地说,对于Hoi,表3的测算是基于C-D模型的一个特例,而表5则使用了救助者行动中潜藏的分配公式。两种分配有一定程度的重叠,而不同的地方则在附录中有所阐释。C-D模型假设救助只能通过使国家发展来减少贫困,而救助者们认为救助可以特定的分配给国家中的贫困人群。
由于在实践中,救助者对分配给印度救助进行了调控(donors cap theirallocations to India),表5B部分展示了假设印度只获得了世界总救助份额的3%时,其他地区获得的救助份额。此时非洲地区获得的救助占低收入地区的份额显著上升,比如,在r=0、T= 25时,非洲获得的份额从39%上升至84%,而对印度救助数量的调控也使得南亚其他地区获得的救助占南亚地区获得救助的比例上升(在本例中从9%上升至73%),但并没有改变非洲地区和南亚其他地区获得救助份额的比例。
虽然修正的公式(2)对任何衡量贫困的标准都是有用的,但是从分配公式得到的分配结果往往取决于衡量贫困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将会改变各国相对贫困的程度(或者改变各国的减贫速率)。为了证明该观点,表5C部分展示了当衡量贫困的标准按照目前大多数救助者所使用的“平均每单位资本带来的收入”时的结果,正可以和A部分“按照收入测算的贫困人数”得到的不同结果进行对比。这两部分数据的产生在计算等方面都是相同的(两个部分都未对印度获得的救助数量进行调控)。
从表5A、C两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印度在改用“贫困人数”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会显得更富裕一些,获得的救助更少,进而降低了印度在低收入地区总救助中获得的份额,增加了另外两个地区获得的份额,其中,非洲地区增加的份额不大。而在改用“平均每单位资本带来的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时,南亚其他地区相对使用“贫困人数”作为衡量标准时更加贫困。
三、 小 结
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以减贫为目的的救助机构给非洲地区分配的救助要多于C-D模型所建议的最优数量以及C-D模型与千年发展目标存在着冲突。为此,本文指出,由于C-D模型只考虑当下的贫困程度,而救助机构(以及千年发展目标)是前瞻的——既关心当下的贫困,也考虑未来的贫困。
本文对C-D模型进行了改进,使其既保留了C-D模型的优点从而保证了分配的效率,也将未来的贫困纳入到模型之中(这意味着模型贴近了救助者的目标)。本文也针对救助者而对分配公式进行具体的修正:增加了贫困调整项。这一修正使救助者们的决定更加一致(避免他们为非洲进行单独的配额分配),并减少了分配公式与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上述改进尚不能完全解决救助分配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无效率或者对现期与远期贫困的关注程度不同仅仅是人们在救助分配方面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即使那些认为救助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世界贫困的人们也未必能认可当下的救助分配,因为他们在贫困衡量标准方面并不能统一意见。此外,更根本的是他们或许对救助以何种方式减少贫困的认识不同。
因此,本文只是部分地改进了在国家间进行救助分配的模型,而救助分配本身也只是促进救助事业这一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假设全球的救助数量是外生的,而且没有探讨如何才能高效地将救助发放到需要救助的地方,当然也没有讨论何种救助形式最有利于消除世界贫困。本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有限,但仍值得一读,因为它将加深我们对时间维度和以穷人为中心的救助目标方面的理解。
资料来源:Adrian Wood, Looking Ahead Optimally in Allocating Aid,World Development, Vol.36, No.7,pp.1135 - 1151, 2008.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让金融部门为穷人服务
Strahan Spencer,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经济顾问
Adrian Wood,牛津大学教授、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原首席经济学家
在金融和发展领域,双边援助方像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3项最主要的援助项目中,它应该最优先提供哪项援助,且它可以使用哪些国际性的、政府驱动的、作用于私人部门的工具呢?这篇文章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
一、 金融部门和穷人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的起点必须是它的中心目标,即减少贫困。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其任务之一是在1990-2015年使世界上每日生活费用少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其他的任务有改善教育、医疗、性别公平,以及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减少贫困方面,有一些重要方面是难以被量化的:降低穷人面对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增强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掌控能力,加强他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参与度。
金融部门和这些目标的相关之处在哪里呢?我们会对金融部门对穷人的帮扶功能进行回顾,当然也会回顾一下它们的失败史,并且提出让金融部门更好地服务的一些原则。
(一)金融部门如何帮助穷人
一个很重要的(尽管只是间接的)金融部门帮助穷人的方法是加速他们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它的作用渠道已经很为人们所熟悉。它可以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和适应人们需求的到期日的金融工具来调动起人们的储蓄。它可以通过筛查投资项目计划和监督股票发行方和借方的行为来提高投资效率。金融部门能够提供分散风险和给风险定价的方法,使得大规模、高风险的经济活动能够进行。它还可以通过提供便利且廉价的交易媒介来减少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这使得买卖双方都能够更好地参与商业活动。
由于以上的原因,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对于其贡献是否存在和贡献大小的计量经济学估计仍旧存在争议。金融指标和国家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确定,并且近年各种研究(比如Calderon和Liu,2003)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证据(既有因也有果)。一些研究还发现这种因果联系还是相当强的:比方说,Leving,Loayza和Beck (2000)估计了银行给私人部门的贷款每加倍一次(相对于GDP的比例来说)几乎能为长期增长率贡献两个百分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这样的结果说服(Zingales,2003),并且建立因果联系和精确估计的技术问题等固有的困难使得任何经济计量结果的解释都需要谨慎。
金融部门的发展服务于穷人的另一些方式则更为直接一些。正如Ruther-ford (2000)指出的,金融服务能够让穷人把小额积蓄日积月累地转化为大额存款,从而使穷人不仅能够通过投资而取得收入,而且还能降低穷人受到经济冲击的危害、应对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需求购买一些有用的耐用消费品。因此,举例来说,人们有一些储蓄行为以后,金融部门就能提供给人们为总储蓄而制定的储蓄计划;在人们有储蓄之前也可以提供贷款服务,而作为于过去和未来发生的储蓄的交换,它也能提供保险服务和ROSCA(一种存贷轮流的结合品)。因此,金融服务不仅能够减少收入贫困,也能够减轻其他方面的贫穷,如通过提供送孩子上学和医疗的帮助来提高穷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通过给予妇女获得金融资产的渠道来提高性别平等。金融服务还能够改善环境:太多的环境恶化是因为穷人在缺乏任何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一些短视的行为。
Rutherford等还正确地强调了穷人需要一系列金融服务这样一个事实。小额信贷可以为减少贫困做出很有价值的贡献,但是还不够:对于那些极度贫困的人小额信贷的作用非常小,因为他们有更大的风险规避程度和投资机会更为有限。对于那些最穷的人,储蓄和保险计划更加合适,不仅降低他们受到经济冲击的危害程度,而且还能使他们的家庭能够承担更高回报但更高风险的投资。并且,给穷人和他们公司的小额信贷的收益取决于当地经济投资机会的范围大小,后者又取决于穷人所在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这使我们回到了金融部门的间接帮助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
(二)金融部门是如何无助于穷人的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在我们下面所概括的几种情况下常常是无助于穷人的。金融部门并没有为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其主要是因为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比方说,低收入国家的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在1999年只有GDP的43%,而高收入国家则达到了148%(世界银行,2002)。他们在金融中介方面非常的低效:比方说,低收入国家的利率价差是高收入国家的3倍多(低收入国家是15%,高收入国家是4%(世界银行,2002),并且这种差别不可能仅仅是更高风险的反映。他们的银行系统更加的脆弱:在一份跨度为20年的50个国家的样本中,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要大一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危机支付的财政总费用据估计有1万亿美元,大约等同于1950年以来所有国外援助金额的总数(世界银行,2001)。最后,低收入国家的银行系统常常无助于其大部分的生产部门——不仅包括中小企业,还包括各种行业的企业,而他们却往往将存款投资在短期国债上。
金融部门同样不能给穷人提供直接的帮助。穷人往往缺乏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条件:比方说,在乌干达,只有8%的农村家庭拥有银行账户,很可能是由于92%的农村家庭住在距离最近的银行5千米以外的地方(IDC,2000)。非正规金融部门也是一样,虽然其经常起到了有用的合适的替代性作用,但是它缺乏正规金融部门所具有的调动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小额信贷的出现使得上述缺失得到了一些弥补,但是相对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其他的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规模而言,小额信贷提供的金融服务仍旧是小规模的。比如说,乌干达的人口为2 000万,而小额信贷机构总共只有18.3万信用客户和26万贷款客户,并且对于5个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供给据估计只占到了总需求的6%。另外,迄今为止很少有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凭借其自身经营能力而存在。
(三)如何使金融部门更好地为穷人服务
在寻求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时,人们需要一开始就具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找到原因。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甚至解决的原则:比方说,反应更高风险而非低效率的高利差部分是不能被消除或压缩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特征。即使原则上有解决方法,通常这些问题是市场失灵导致的,因此,实际上解决起来并不能保证其收益大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历史上包含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意图良好的(行政)干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表1仅提供了框架性的概览。对应于两种金融部门服务穷人的主要方法(间接的,通过加速增长;直接的,通过微观层面),表1有两个主要栏目,每一个栏目又被分成“问题”和“回应”两个子栏目。该表的每一行对应于特定种类的问题原因,并且该行被分成两大类原因:市场失灵和公共部门失灵。我们用“公共部门失灵” (Public Failure)而不是“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是因为我们将援助方的失灵和国际组织的失灵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失灵都包括在内。
表1金融部门助贫分析矩阵的结构
在“市场失灵”状况下,有一些常见的原因:公共品、垄断、逆向选择和不对称信息。即使没有市场失灵,原则上不平等也是行动的合理原因,但是矩阵中并没有列出,因为实际上这种动机常被滥用于证明给非贫困人口信贷补助的正当性。这些市场失灵的结果是贫困陷阱——一个经济体陷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由于协调困难、信息缺乏或者交易费用等原因无法跳出贫困陷阱而迈向一个有潜在可及的高水平均衡。我们相信经济学家过于隐含地假设均衡是唯一的,而更经常的是均衡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表1里的“公共部门失灵”,也包含了标准的问题原因——比如道德风险和挤出效应——但还包含了相关公共机构能力不足和不当激励等。
“回应”的那一栏不仅包括了可能解决相应问题的行动的描述,而且还包括了(在括号里面)负责识别问题、设计及执行相应对策的主要执行者的身份。此外,矩阵区别了相关问题对策回应的执行主体:国际团体,国家政府,私人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中能带来变化的一个重要团体是商会,该团体通过克服协调失灵问题以及传播信息和新想法而帮助贫困人口和国家脱离贫困陷阱。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矩阵中列出的那些对策回应在有些情况下是尝试性的,并且矩阵本身必然是不完整的。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组织思考的框架。
二、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和其他双边援助者)所扮演的角色
给定矩阵中问题、对策和执行者的类型,类似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这样的双边援助机构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一)优先对象和可利用的工具
所有双边援助机构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确定援助的先后次序。在现有的背景下,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于改善金融部门的资源比例问题,这部分的资源投入就会与所有其他重要的资源投入需求相排斥,比如说普及基础教育目标和抗击HIV/AIDS目标;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去安排投入到金融部门的资源以实施不同类型的干预任务。原则上,对于这两个问题正确的答案是如何做到减贫效果最大化,但实际上我们缺乏我们所需的实现这种最优安排的信息。
这个困难与另一个困难纠缠在了一起,即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可以也应该利用每个国家政府自己设定的计划和优先顺序。但即使如此,信息仍旧不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可诊断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并确认使金融部门能够得以发展和强化的行动,同时,他们的标准与准则遵守情况报告(ROSCs)可监督国际标准与准则的施行情况。然而,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和标准与准则遵守情况报告(ROSC)极少关注贫困问题。相比之下,虽然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关注贫困,但往往缺乏足够的对金融部门的分析。
其他一般性考虑是双边机构的作为受限于它们能够使用的工具范围。一般认为,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的所有工具都是两种成分的混合:基于我们员工和顾问所掌握知识而提出的建议,各种基金的额度。这两种成分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方案。比如,技术援助的建议部分比例较高,一般预算支持则资金比例较高,其他项目则介于两者之间。即使这样,可选方案仍旧少得可怜,即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仍旧有许多想做而无法付之于行动的事情。
接下来,将回顾一下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在金融部门的活动,用矩阵中的三类推动变革的行动方框架:国际团体、各国政府和私人部门。针对每个行动方,我们都会概括出指导我们行动的原则,并且给出所做过项目的一个案例,还包括对该项目是否成功的一个评价。
(二)国际性的行动
有两个主要理由促使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采取国际性行动。其一,是有一些问题只能在国际层次上来处理,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改善国际金融结构。其二,对于本质上不需要国际协调的问题也适用,就是往往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与其他援助者一起协作将更为有效率,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合作。这种效率的提升部分是因为资源的整合即数量上的优势,其他部分来自于高效分工协作,即不需要每个捐赠者去做所有的事。集体行动还能够给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机会,去影响其他捐赠者的政策和实践,特别是说服他们不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毫无帮助的事情,比如给农村信用机构提供补贴。
让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工具是英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委员会当中的席位,通过这个渠道我们能够提供建议且能够试图施加影响。另一个工具是同行压力,这是改进其他捐赠者和机构运作的非常有效率的方式。我们的资金使得我们能够对多边机构、信托基金和我们认为重要的目标的多边倡议有所贡献。最后,我们可以发起、参与及资助国际论坛来提升研究、协调及信息共享。 我们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行动的例子是工具的最后一类:CGAP,扶贫咨询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它召集了从事小额信贷的29个多边、双边、私人部门的捐赠者。在矩阵里,我们参与的动机之一是纠正市场失灵,即提供信息和高质量的技术援助。CGAP为特定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了全球市场信息清算机构、有的放矢的支持,其目的是使小额信贷从业者扩展最佳实践。我们的其他动机是对付公共部门失灵,即这个领域当中不同捐赠者之间缺乏协调,包括他们没能按照主流最佳实践方式运作。为此,CGAP提供培训、制定公共准则,并且试图使在一个特定国家中从事小额信贷的不同捐赠者更加协调地工作。
CGAP是否有用呢?就信息传播而言,我们估计它是非常有效的:CGAP是小额信贷捐赠人的最重要且最受尊敬的信息共享的全球渠道。就协调而言,它则没有这么成功,基本是因为一些捐赠者缺乏意愿。这样的结果给我们上了重要(尽管是事后看法)的一课:有许多捐赠者参与的国际性倡议仅仅在每个捐赠者都有意愿使其有效时其才会有效。
(三)通过政府行动
对于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而言,需要遵照英国政府的意愿而行动。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因为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在很多关键大事上并不是正式的牵头部门:在某些情况下,财政部才是,其他时候则是英格兰银行或者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这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影响英国政府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我们必须设法去影响其他部门。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的职员在这件事情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且就其减贫而言收益成本比似乎与其他活动相比还不错。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还设法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发挥作用,这些国家政府承担着让金融部门为穷人服务的最基本职责。“通过”一词值得强调:我们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双边援助者的作用是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其职责。困难的是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政策工具这一主题。
项目和技术援助这些传统工具在改变系统或者机构及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方面还是很有效的。然而,即使用好这些工具(其实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这些工具在建设政府自身的发展和实施长期可持续政策的能力方面并不是那么有效。这个缺陷让我们及其他捐赠方转向使用其他类型的工具,包括更高层次的政策讨论和直接向政府预算引入资金(部门层面或者是总体层面)的混合使用。这个方法原则上是比传统的捐赠人独立支配的大批项目要好。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能够使用,仅仅对于那些有能力规划好政策和拥有较好的公共会计系统的政府才有效。而且,即使在有些能力使用这种新方法的国家里,仍旧可能存在互补性的传统援助工具。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执行过一个监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的项目。这个项目给几个主要为非洲国家的政府提供了技术援助和拨款,目的是使之能够通过对投资者的调查、更为全面地且更为及时地监管进出的私人资本。我们做此事的动机是希望对国际金融流动稳定性这样的公共品有所裨益。这不仅要求在国际层面上有作为,而且要求这些国家在管理资金流动方面有更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一个必要成分就是信息,且我们承担这个特别项目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很多国家对其资本账户部分解除管制损害了它们之前依赖的主要信息源。换句话说,有必要在无高度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找出其他方法去得到资金流量的信息。 这个项目做得是否成功?在某些方面,确实很成功。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因而收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尤其是,流入非洲国家的私人资本比原本估计的要多很多。比如,进入坦桑尼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被发现是我们想象的量的5倍。这个项目中,是否应该将这种收集信息的能力发展为可持续的政府行为仍旧要打问号,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仍旧需要收集信息,虽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是为了让这样的结果更有可能发生,我们在想,在这个项目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在区域金融机构建设过程中实现这方面的职能转移。
(四)作用于私人部门
由于大部分金融活动参与者都是私人部门的机构(包括NGO),因此,理论上作用于私人部门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于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和其他的捐赠者、包括多边的捐赠者而言,直接作用于私人部门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区别于NGO的那些营利性的机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机构有很多。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或者其他任何人是绝不可能作用于大部分的这些机构;如果我们挑出一些,就会明显的有副作用。资助几个特定的公司很有可能会引起扭曲和无效率,并且提供了腐败的激励。资助还干涉到了原本属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活动的范围。只有在当地政府缺乏必要的能力或者潜在有用的活动已经失败了的情况下,捐助者的这种行为才能被证明有用,比如说,在没有政府部门有能力处理小额信贷机构的情况下。
对于工具的选择来说,倡议和信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它们比拿钱资助更不可能造成不利的副作用;其二是倡议和信息,通过传播和贯彻新思想,对于逃离低水平均衡迈向高水平均衡有很大帮助。然而,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还会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对于实验或者试点活动而言拨款是比较合适的,如一种新方法或者新机构的初创。但是作用于特定的私人企业还是有产生负面副作用的风险,如给予一个公司不公平的优势、扭曲竞争,或者为无效率提供资助。进一步说,一旦拨款已经划出,我们对受助公司并没有持续的影响力。
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一个新领域是2002年国际发展法案允许的非资助性金融工具,该法案允许使用贷款、证券投资、担保和多种债务证券计划组合等金融工具。这些新型金融工具允许我们以接近于市场条件而非纯粹的援助条件下提供资金,而且不易造成市场扭曲或其他负面影响。这个法案还创造了一种使用我们的资金撬动更大量资金的可能性,特别是把我们的资金与私人资金合并在一起。这类工具的问题是国际发展部缺乏设计和管理这类金融工具的专业知识、也缺乏一个适合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此类运作,因而使得我们不得不通过中介机构对这类非援助性的金融工具进行早期试验。
近几年,我们用的另一种金融工具就是挑战基金,这主要是与私人机构分摊成本的援助款项。这种资金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当有效且可行的资助私人部门创新的方法(然而“可行”一词必须达标:从挑战基金申请资助需要相当程度的能力和深思熟虑,定会排出很多小的或者非正式部门的公司)。我们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作用于私人部门的一个例子是金融深化挑战基金(Financial Deepening Challenge Fund)。这个180万英镑的国际基金为私人公司或者联营企业,或者它们与政府机构或者NGO的合作提供“匹配援助”。这些援助的目的在于资助创新动议,从而促进非洲和南亚国家的穷人对于多样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且尤其重视能够被复制和规模化的计划。我们的一部分动机是去纠正导致针对穷人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和研发投资不足的市场失灵(研发尤其能够有益于穷人);另一部分动机是去纠正公共部门失灵,即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
金融深化挑战基金(Financial Deepening Challenge Fund)有多成功呢?因为申请过程是具有竞争性的,因而在透明性上做得很好,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能够回答“你为什么要选那个公司”的问题。这个过程还很快:援助款项申请、批准和下拨周期仅仅占传统项目周期的三分之一。它还撬动了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过程的头两轮,我们拨出了270万英镑的援助款项、吸引了480万英镑的匹配资金。然而,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其一:即使是得到了配套援助款项的单个企业也倾向于不去做那些改善整个部门发展环境的业务、及利人利己的事情。为了抵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基金中引进了新的使环境更具能动性的窗口以吸引项目申请。其二:有些公司会因为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原则上拥有它资助的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而失去兴趣(尽管这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最后,我们了解到挑战基金机制对于公共团体并没有太大作用。政府部门的申请量非常少,明显主要是因为很难把竞争的资助和正常的公共部门预算过程相配合。
(五)进一步研究的事项
我们的问题始于“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得金融部门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在概括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已经传达出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意识到金融部门在减贫方面的潜在重要性,并且我们知道这种潜在重要性并没有被完全认识清楚。我们希望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即旨在改善现状的有效干涉需要对金融部门的详细了解和分析。我们感到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了解和分析,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自信我们能够为金融部门投入正确数量的资源或者能够用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下面我们谈一下我们认为我们仍需要更多了解和分析的一些领域。
国际标准和守则有多有效呢?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赞助且支持了金融部门改革和强化(FIRST,Financial Sector Reform and Strengthening)的动议,这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国际认可的金融部门的守则和标准提供技术援助的多边基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赞助的项目,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了解这些守则和标准的影响。它们之中哪个是最重要的,实施它们能够改变什么,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何向穷人、农业企业和小企业提供全范围的可持续的基于商业基础的金融服务呢?正如Matin,Hulme和Rutherford(1990)所说的:第一个“小额金融革命”揭示了“可以对穷人提供银行服务”,第二次革命将面临的挑战是显示有可能对穷人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来满足他们生计的所需。与此相关的,我们想知道如何使小额金融进入正式金融部门。我们仍需补足的知识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不同类型的、非援助的、支持私人部门活动的金融工具的成本收益比较。
很容易在这张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的清单后面添加新东西。了解这些知识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政策方面的研究。因此,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欢迎关于文章涉及的这些事项的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且期待着未来研究的进一步进展。
资料来源:Strahan Spencer and Adrian Wood,Mak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Work for the Poor.The Journal of Developtnetit Studies, Vol.41.No.4,May 2005, pp.657 - 675.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第四部分
国别案例
定向救助和社会资本:
智利在新自由主义民主时期的住房政策
Paul W.Posner
一、 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各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双重进程。民主化过程可谓步履维艰,右翼军事势力经常策动政变推翻民主政府。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这样的情况已经极为罕见了。其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激进的政策往往会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感到不安,要实施经济自由化,政府就得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以更加谨慎务实的态度来构建经济和社会秩序。
然而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又加剧了拉美地区本已根深蒂固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失序日益凸显,弱势群体在政治领域更加缺乏对话能力(Lechner,1998;Roerts,2002;Kurtz,2004;Weyland,2004)。也就是说,民主改革或许扩大了社会的开放度,但国家与经济改革却增加了“民间部门”①的经济脆弱性,削弱了人们的社会凝聚力和组织能力。本研究发现,民间部门的政治影响力在减小,他们难以对政府官员构成压力,进而使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到重视。
 在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拉丁美洲,“民间部门”指的是包括许多阶层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其中既有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也有正式部门里那些无组织的工人,他们通常生活中大城市中心周边的棚户区,还有一些人也住在城市以外的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更深讨论,请参见Oxhorn(1995).
在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拉丁美洲,“民间部门”指的是包括许多阶层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其中既有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也有正式部门里那些无组织的工人,他们通常生活中大城市中心周边的棚户区,还有一些人也住在城市以外的地区。有关这方面的更深讨论,请参见Oxhorn(1995).
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国内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市场导向派”认为,要减少结构调整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好是培育社会资本来推动发展。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在他那本广受赞誉的《使民主运转起来》里提到,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些能够决定社会互动质量和数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World Bank)。由于许多地区的市场改革都未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减贫以及缩小收入差距,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社会资本便成为了世界银行分析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Fine,1999;Bebbington等,2004)。
普特南与世界银行的定义颇受争议。尤其是从事不发达地区研究的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的联系并非如此简单;由互惠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常常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帮助人们应对物质生活的窘迫,让那些被排挤在正规经济部门以外的人得以生存(Portes,1998;Anderson,1999;Tironi,2009)。尽管如此,这些不同的声音并未撼动世界银行的地位。拉丁美洲的许多政府都采用了世界银行的建议,试图培育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来减少社会和经济对他们的排斥,从而缓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这套做法与以往的结构调整有着一定的区别,因为以往的做法强调的是国家力量对市场缺陷的干预;而现在则是依靠增强目标群体的社会互动来促进市场的良好运作(Fine,1999)。各类定向救助与社会整合项目有意让弱势群体融入市场经济,以同时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凝聚力,进而巩固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
那么,这些目标最终都实现了吗?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得到发展了吗?他们的合作是否稀释了市场的竞争压力(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增进了社会凝聚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在宏观层面对拉丁美洲的福利改革进行了分析,其中,哈格德和考夫曼的《发展、民主与福利国家》,塞古拉一乌维尔格的《拉丁美洲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堪称佳作。这两个研究基于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失效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社会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为了保证新政的落实,提高经济效益,国内的改革者还与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进行了合作。上述两个研究既分析了改革的原因,也提到了它的缺陷,即穷人的福利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哈格德和考夫曼发现,定向救助项目不但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增加就业或是减贫(Haggard和Kaufman,2008)反而还“让贫困群体内部出现了一定分化”(2009)。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拉美的社会福利改革进行了“小样本的”定性研究,着重分析了定向救助项目对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体内聚力的影响。早在1990年,Esping - Andersen就开创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既可促进、也可削弱阶级间与阶级内的内聚力,它的结果如何,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架构。有些社会福利政策能够推动贫困群体形成强有力的联合,让他们能够对民主型领导人施压,使其注意到穷人的诉求,保证社会民主与公平。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拉丁美洲实施的定向救助项目是否实现了这样的效果呢?考虑到拉丁美洲的住房资源极为紧缺,而国际发展机构又一再强调实施定向住房补贴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妨先来看看现在的住房政策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拉丁美洲,1.28亿人生活在拥挤而又破败的贫民窟中,至少需要提供2 800万套住房才能让该问题有所缓解(Jha,2007)。尽管因经济水平的差异,各国情况略有不同,但住房问题仍是拉美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巴西和墨西哥这些收入较高的国家,1/3的家庭居住条件恶劣……而在收入较低的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这样的人口则多达半数以上”(Rojas,2006)。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IADB)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为主的国际机构就已涉足定向救助,试图解决拉美人民的“住房难”问题。
智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以前,国家是住房资源的供给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智利启动政治经济改革,转为以市场为导向,直接瞄准穷人不同程度的需求为其提供住房补贴。在此过程中,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和其他帮助。在它们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推动下,到了90年代,智利的住房改革已被称为“最佳实践”,成了拉美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Gilbert.2002;Jha,2007)。
抛开这所谓的成功暂且不谈,仅从不同政治体制下住房政策的变化来看,智利案例就值得好好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国家主导的住房政策让城市贫困人口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社会流动。在皮诺切特主导的军政时期(1973-1990),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协助下,按照市场规则对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住房政策)进行了重新设计。自1900年民主化改革以后,中左党派组成的民主联盟(Concertacion)上台,表现出了对社会和谐的高度重视,在执政期间制定出了清晰的目标,增加了社会支出,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为例,该部门的目标是:“实现和平共处,推进社会共融,加强公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集体主义的责任感,确保城镇规划与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MINVU,2009)。也就是说,住房政策是新政府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手段,若要更好地揭示这套政策对整个社会与城市贫困的影响,我们便得采用一种历史比较分析。
基于这样的方法,本研究最终指出:市场关系以个人主义、竞争与个体利益的强调为特征,而社会关系却建立在互信、合作与集体利益之上,虽然智利的住房新政旨在调和二者,通过对弱势群体实施定向救助来培育社会资本,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住房补贴的发放与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分化,让工人更加脆弱地暴露在了市场风险之中,同时还削弱了城市贫困人口的集体行动意向。这项政策激化了“民间部门”内部的竞争,扼制了社会资本的发展,使得城市贫困人口难以集齐众力对政府官员施压,让他们倾听和满足自己的诉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建立了一套概念框架,随后用其分析了智利三个时期的住房政策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这三个特征鲜明的时期是:民粹主义时期(1964-1973)、新自由主义——专制时期(1973-1990)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时期(1990年至今)。笔者通过对政府官员和贫民窟居民的访谈,掌握了大量有关当前住房政策的一手材料,并依据社会分层和市场保护两个维度,查看了1990年以来住房政策对圣地亚哥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影响。最后介绍了访谈和分析的方法,引出了本研究的结论。
二、 福利体制和社会组织
福利制度旨在提供社会分层和市场保护(即去商品化)。从市场保护来看,它可以让“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或一般福利”,根据这个目标实现程度的差异,福利制度便可分作几个类别(Esping - Andersen,1990)。我们需要借助如下三个指标来衡量福利制度的去商品化效果:①福利水平;②公民获得福利的途径;③福利的覆盖面。提供的福利水平越高、覆盖面越广,公民的社会权(Social Right)保障得越充分、获得福利的途径越多,那么福利制度就越是能够保护公民,让他们免受市场的负面影响;反之,公民受到的保护就会大大受限,而且社会分化的程度还会加深。不管是推行去商品化还是加强市场的主导性,政府大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设计相应的福利体制管理架构。例如,在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下,福利的水平、覆盖面和可及性多多少少都是标准化了的,这样的架构有助于实现社会融合,给福利国家持久的支持。与之相反,在分散化的管理体制中,福利的覆盖形式是碎片化的,国家会实施各种各样的项目,让目标群体相互竞争。因此,福利的可及性相对较低,社会分化加深,不利于社会整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引入艾斯平一安德森的福利体制框架(1990)。他根据上述三个指标——福利水平、获得福利的途径以及覆盖面,将福利体制划分为三种理想型,即自由主义、法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主义的体制下,福利的供给水平和覆盖面是最低的,而且,提供福利的条件十分严苛,政府通常会借助家计调查给人们赋予略带耻辱性的特征,只有满足了这些特征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福利。此外,国家还鼓励私人部门提供福利,从而进一步约束了社会权,结果造成“一种混合的景象——国家和市场均提供了一些福利,接受国家福利的那些人都相对贫困,而大多数人在市场中接受差别化的福利,两者之间存在政治、阶层方面的分立”。在这种福利体制下,人们难以结成基数庞大的联盟来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简言之,在经济方面发展得较好的公民能够在私人部门满足自己的福利需求,他们不愿意资助那些市场中的失败者。如果非得由公共部门给予这些人救助,那么,他们必须接受家计调查,被打上带有耻辱性的标签,只有这样才有享受福利的资格。通过这些行政手段,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大大约束了人们的福利要求,同时也限制了他们获取福利的途径。除此之外,政府还会实施各种各样的项目来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从而阻碍他们的联合。
与自由主义不同,社会民主福利体制基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深度结盟。国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遵循普遍施惠的原则将所有社会阶层都纳入进来。结果导致高度的去商品化,增进了社会总体的凝聚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福利国家的执政之基。法团主义的福利制度同时兼具上述两种制度的特点:和社会民主体制类似,国家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市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另一方面,它还跟自由主义体制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所能享受到的福利是有差别的,因此,这种体制不利于阶层之间的联合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借用此概念框架,可将半个世纪以来的智利历史分作三段。1973年军事政变以前,基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制度,智利的福利体制由法团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新自由主义专制统治时期(1973-1990),政府建立起了一套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1990年以后,尽管政治经济模式变为新自由主义民主,但先前的福利制度依然得以保留。这三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模式与对应的福利体制有着鲜明的特征和深厚的含义,它们影响了社会福利的本质、程度以及公民社会的组织(表1)。
表1 1964-2006年智利的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改革
从20世纪30年代至1973年,民粹主义联盟统治了智利逾40年,其最初实施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法团主义的福利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只有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有重要作用)的民众才能享受社会福利,而包括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在内的其他群体则被边缘化。由于中左翼党派(主要是社会党、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代表着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它们执掌的国家又有着高度的集权化与干预主义色彩,于是,执政党逐渐将先前那些边缘群体纳入到福利体系之内,使福利体制的本质开始由法团主义转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社会福利的管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福利水平、覆盖面以及公民获得福利的途径都大大增加。1973年政变发生前,“智利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全面的福利体系,覆盖了各种社会风险并建构起了较为成熟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这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实属罕见”(Segura -Ubiergo,2007)。
执政党的动机主要是想赢得更多的选民,从而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然而,政府的承诺过多使得人民对住房的需求暴增,民间团体的运动也此起彼伏,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压力。结果导致恶性通胀和政治动荡,前后两届执政党均以失败收场(Borzutzky,2002)。
三、 政变之前的住房政策
1964-1973年,阿连德总统上台,智利的住房政策有着一些明显的特征。例如,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执政(1964-1970)还是人民团结联盟执政时期(1970-1973),政府都大大激发了民间部门的住房需求,甚至使之超出了国家的供给能力。它们将住房看作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认为国家有义务去满足人民的这项需求。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雷总统带领基督教民主党(PDC)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改革引发了民间部门对住房的需求与期望。为了实现理想中的图景,基督教民主党启动了一个“全民发展”战略,一方面旨在缓解资源的极度稀缺,提升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有意为该党赢得新的支持。按照预想,这种新型的法团主义制度会激发人们的民族认同;中央政府直接提供救助和补贴,也会促使人们产生集体行动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然而,由于僧多粥少,弗雷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远远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住房方面的需求),“全民发展”最终以失败收场。为了解决智利面临的住房紧缺问题,弗雷政府宣称“住房是每个家庭皆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无论经济条件如何,所有家庭都应该拥有住房”(MINVU,2004)。为此,政府于196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住房管理的部门——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MINVU),并在随后组建了几个相关的自主经营的国有公司①。这些官方实体负责落实政府的“宏图大业”,力图在弗雷任期内建设36万套住房,而且其中的21.3万套(约60%)都是供给穷人的。但由于从农村地区涌入的移民大大扩充了城市贫困的队伍,政府建设的住房对于源源不断的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缓解城市住房危机,弗雷政府还启动了“Operacion Sitio”项目,但最终也未满足民众对低成本住房的需求。棚户区居民运动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基督教民主党的控制。成千上万无房可住的家庭组建了“无家可归委员会”(Comites Sin Casa),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起占地运动,要求政府兑现承诺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其他一些城市服 务。对此,弗雷政府最初采用了镇压的手段。但考虑到1970年大选在即,而城市贫困群体在1964年的大选中为基督教民主党的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为了不疏远这些选民,弗雷政府又放松了对他们管制。面对政府态度的转变,这些移民在“无家可归委员会”的带领和组织下,占领他人的土地并搭建了临时的住所和帐篷(Castells,1983)。随后,左翼团体(主要是共产党、社会党,其次便是左翼革命运动和基督教民主党里的一些左派人士)动员了大批群众继续占地,从而给政府施压,希望其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Castells,1983; Kusnetzoff,1987)。据统计,1968年智利共有8起土地侵占事件,到了1969和1970年,这一数字就增长到了73和220起①,进而引起了商界对左翼极端主义行为泛滥的担忧。弗雷政府愈加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在1964年支持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右派人士也撤回了援手,帮助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联盟②赢得了1970年的大选。
阿连德的上台并未让弗雷执政时期的极化现象有所缓解。1971年,土地侵占事件共有560起,是1970年的两倍多(Castells,1983)。与弗雷相似,阿连德的政治主张也助长了人们的需求和预期。执政之初,阿连德宣称:“无论收入多寡,所有智利家庭都应享有住房权
这一根本权利”(Kusnetzoff,1987)。这位有着社会主义理想的总统还说:“住房不能进入商业领域……国家有义务为人民提供住房”(MINVU,2004)。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阿连德政府在住房和社会这个联盟主要包括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以及人民团结行动运动(MAPU)。
数据引自Stallings(1978:115)和Csstells(1983:200).
福利方面增加了巨大的投入。“1971年,政府开建的住房是前些年所有新建住房数量的3倍多,财政支出增加了70%以上”(Ascher,1984)。贫民运动再加上政府干预,使得数以万计的人总算有了居所,同时也享受到了一些其他的基本服务。1972年,超过50万人通过占地住进了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其中80%的人都集中在圣地亚哥(Castells,1983)。在弗雷和阿连德先后执政的9年里,40万套住房拔地而起,其中62.5%由公共部门提供(Kusnetzoff,1987)。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贫民运动的壮大与政府干预的加深让企业家们深感不安,唯恐人民需求和财政支出的激增会带来通胀压力,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于是,历史再次重演,阿连德政府腹背受敌:一边是有组织的工人与新的贫民联起手来提出更多的要求,另一边则是商界人士与国内军队结盟,力图推翻这个社会主义政府。
四、 军政时期的住房政策
眼看民间部门具备了越来越强的谈判能力,并且在跟政府的交涉中屡屡获胜,右派已经无法等闲视之了。1973年的军事政变以及后来的独裁统治便是右派对此作出的回应。要想理解皮诺切特在新自由主义一专制时期中的制度和社会福利改革,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其实,在政变爆发前的这50多年时间里,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右派一直致力于削弱民间部门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皮诺切特上台后实施的改革大多也是基于这个初衷。为了实现该目标,右派引入了国际市场的力量,希望在智利这个小小的不发达经济体向工人施压。值得一提的是,除此之外,经济自由化要取得成功还需其他一些关键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建立一套独特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套制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而是强化市场竞争和市场分层。
在新自由主义专家的帮助下,军政府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开始极端地推行艾斯平一安德森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制度。许多原本归国家控制的资源和社会功能都被私有化了。同时,公共部门遭到大大削减,一些难以在市场领域立足的人只能依靠仅有的一些劣等公共资源存活了。而且,政府还根据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的不同,对一些特殊群体实施了定向救助。这样一来,一套高度分化的社会福利系统便构建了起来,让普通民众不再享有共同的社会福利,也就难以凝聚在一起了。
通过住房新政,我们就可见一斑。住房方面的改革分为3个方面:①将住房投资和建设的主要责任划归私有部门;②根据社会行动委员会(CAS)的调查结果,按照收入、存款和其他指标把低收入家庭分成不同的层级;③允许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竞争同一笔住房补贴。在行政分层方面,1985年,军政府对行政系统展开了去中心化,中央政府将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一些政策项目的实施权交给了地方政府。在这个制度下,市政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将新成立的“地区住房和城市事务服务局”、其他相关的行政部门和政策服务对象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去中心化本质是一种责任的分散化①,削弱有关去中心化类型的深入探讨,详见Posner(2003;2004)作者分析了智力军政府实施的中心化改革。
地方政府与底层社区的权力。因为中央政府在将行政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的同时,依然严格控制着政策制定和税收。政党和社会组织丧失了影响政策的能力,难以再像以前那样组织底层民众,将他们的利益诉求反映给国家。
在这样的行政安排下,地方政府主要发挥4个方面的功能。首先通过统计调查了解辖区内所有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为了方便搜集这些信息,1979年政府在地方层面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社会行动委员会(CAS)。其首要职能是开展“社会分层指数调查”,评估各个社区的紧要需求及其程度,配合针对 有关去中心化类型的深入探讨,详见Posner(2003;2004),作者分析了智利军政府实施的去中心化改革。穷人的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工作①。其次,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根据贫困程度的高低对辖区内的贫困家庭进行分层②;然后,同样是基于之前的数据信息,根据不同家庭的需求筹划资源分配。最后,将这些资源送达指定的家庭和个人(Gallardo,1989)(表2)。
表2 2000-2006年的住房补贴,资格要求和资源
注:UF,是西班牙语Unidad de Fomento的缩写,直译为“发展单位”,是智利的一种指数化货币单位。在2010年3月,1个UF约合40美元。
资料来源:MINVU (2004)。
不幸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些工作不但没有改善本已凸显的住房紧缺问题,反而还使之更加严重了。单以住房投资和建设的私有化来说,这个巨大的变化让新建住房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赤贫人口的需求。在1960年和1972年,智利公共部门承担了将近80%的住房建设和投资(Raczynski,1994)。然而,到了军政时期,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7% (Kusnetzoff,1987),结果使得军政时期政府提供的服务包括学前教育、营养护理、住房补贴和医疗保健(Vergara,1990).
社会行动委员会的调查将贫困人口分成1-5个等级,1级表示情况严重的。其中决定因素包括家庭特征(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卫生设施和燃料的使用类型,等等)、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等。只有1-3级的家庭才有资格获得国家补贴的住房缺口翻了一倍,仅有56%的家庭住进了新房子①。而且,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住房补贴应该发放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但实际上一半左右的补贴和1/3的住房都给了中等收入群体。更甚的是,那些最底层的人群所获得的住房质量很差,往往坐落在公共资源、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都很差的社区(Vergara,1990)。
住房投资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释放出来的。首先,政府将保障房建设的职能几乎完全托付给了私人部门,那么私人部门肯定会挑最便宜的地皮来建房——这些地方在最贫困的地区,资源贫乏,距市中心较远,没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其次,除非人们有着大量需求和支付能力,否则私人部门就没有充足的动力去建设那些低成本的住房(Castaneda,1992)。但现实情况是,最穷的阶层往往不具备足够的收入和存款去购买房屋,而地方政府又根据统计信息,将那些本有实力购买住房的家庭纳入补贴项目,对穷人构成竞争。结果,许多政府资源就分配给了中等阶层以及那些低等阶层中的佼佼者(Vergara,1990)。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政府又启动了另一个项目(社会住房项目,简称SHP),专为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提供补贴,帮助他们租住或是购买28~35平方米的房子。无论是对于中等阶层还是以前的那些穷人来说,这样的房屋面积都相当小(Castaneda,1992)。因此,该时期所有政策的叠加效果便是:贫困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申请银行贷款,而且还得和他人竞争那些最廉价的、也是条件最差的住房。在这一过程中,民间部门被政府的经济指标拆分成多个层级,从而失去了原先的那种凝聚力与集体行动的基础。
这是1974-1989年的平均数字,与之新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0-1973年,这个平均数在32%以上。详见Raczynski(1974:38,83).
五、 后转型时期的住房政策
在皮诺切特掌权的17年里,智利的住房缺口不断扩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0年民主联盟上台之后便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力图将这些资源有效而直接地输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但是,有关住房保障的管理体制还是保留了下来。结果,尽管住房供给增加了,最穷的群体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但民间部门的分化依然没有多少改观,住房资源分配体系对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资本培育都形成了负面影响。
1990年,埃尔文总统就职,他领导的新政府唯恐民主的重返会让城市贫困人口再次发动占地运动,为了防患于未然,政府增加了针对住房的公共投入,实施了一些专门针对低收入合住家庭的项目,同时还改善了扶贫资源的分配效度。在后来的弗雷总统执政时期(1994-2000),政府依然延续了这些工作。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以平均每年9万套的建设速度,大大缩减了住房缺口,而且让大部分贫困人口从中受益(MINVU,2004)。一项1998年的政府调查显示:从1994-1998年,政府的这些资源主要给了全国最为贫困的40%的人口。尽管有着这么些成效,但住房政策对民间部门组织能力的影响还是与政府的承诺形成了巨大反差。政府此前宣称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团结与公民参与;而住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却恰恰造成了民间部门的分化、竞争与不信任。首先,政府给那些有着更多存款和信用的棚屋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补贴种类,与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相比,他们能够获得的房屋面积可以达到对方的两倍多(例如前者只能获得42平方米的房子,但后者可以获得100平方米的房子);而且他们申请补贴也要容易得多,能够从享受国家补贴的私人机构获得贷款①。其次,国家通过家计调查,根据低收入群体的相对需求对其进行了分层,确定了不同层级家庭(或个人)的补贴资格。这两种手段成功地将竞争元素引入了住房分配体制。
六、 研究设计和分析
按照艾斯平一安德森的分类,智利当前的住房政策便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福利体制。政府严格按照家计调查的结果,为人们提供最低程度的住房补贴。相对而言,那些有着更多存款和信用的棚户区居民更容易获得补贴,而且可获得补贴的种类也比较多。据此笔者推测:针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分层和定向救助措施强化了潜在受益者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感,因此,住房政策不但不能缩小城市贫困人口的经济差距,反而还会加剧这一趋势,进而阻碍他们合作起来向国家争取住房资源;其本质是不利于形成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的。
此处的“社会资本”是指那些有助于增强人们合作能力,提升集体福利水平的条件。这样的社会整合正是当前住房政策的目标之一。政府在《住房共融基金——社会赋权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手册》上清 有关补贴类型和申请资格,详见Saball(1994)和MINVU(2004:第8章)。http://www.minvu.cl/opensite_20070411164518
楚地写道:该政策“旨在推进我国最贫困的家庭融入社会,让每一个穷人都成为永久的公民,尤其是在住房方面不被排斥在外”(MINVU,2008)。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将社会赋权看作是“一个增强个人长期发展能力的过程,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强化自主性,将自己整合到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促成合作与集体行动,从而走出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的状态”。尽管在实践中,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并没有将这些定义操作化,用一些定量或是定性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但不管怎样,社会整合始终是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而且与社会资本的形成息息相关。因此,如果政府的政策或制度安排在贫困群体中制造了不信任感、损害了群体的融合与凝聚力,那么它也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住房政策正是如此,定向救助和社会团结项目的实施和它的目标背道而驰,即加强社会团结、发展公民社会。
为了评估住房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影响,笔者在1993、2001和2006年分别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官员做了访谈,同时还抽样调查了一些直接参与住房项目的棚户区居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年份,是因为它们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能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①。调查社区的选择则是受到凯西·施耐德(Cathy Schneider,1995)的影响。她在做有关军政时期棚户区运动的研究时,根据反独裁动员能力的大小将社区分成了三类:低水平动员社区,指的是那些在1983-1986年,没有发生任何抗议活
 Arend Lijphart(1971:689)提到,在同一个民族内部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增加案例间的可比性,因为这样,民间独有的特征就不会干扰我们对其他变量进行因果分析了。
Arend Lijphart(1971:689)提到,在同一个民族内部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增加案例间的可比性,因为这样,民间独有的特征就不会干扰我们对其他变量进行因果分析了。
动的社区;偶发性动员社区,尽管会经常发起抗议活动(通过报纸的报道来衡量),但它们的活动很少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且也缺少政治性的活动;激进社区则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最大限度地参与了全国层面的抗议活动,而且活动中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性,无论在学者还是活动组织者看来,这些社区都是非常激进好斗的(Schneider,1995)。
基于施耐德的分类方法,笔者每个类型选取了一个社区来开展调研,它们分别是:危楚拉巴市(位于圣地亚哥北部)的拉平科亚(低水平动员社区);培亚尼罗雷市(位于圣地亚哥东部)的罗赫米达(偶发性动员社区);拉格兰哈市(位于圣地亚哥南部)的永盖(激进社区)。从军政时期的动员能力来看,这三个社区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它们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人口状况都非常相似,都属于圣地亚哥最穷与最落后的社区。多肯多夫(Dockendorf,1990)展示的数据便可佐证这一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格兰哈、培亚尼罗雷和危楚拉巴是圣地亚哥婴儿营养不良最高也是医疗条件最差的地区;很多居民的住房条件都非常恶劣,按照这个指标来排序,培亚尼罗雷和危楚拉巴甚至分别位列倒数第一和第三。而且,这几个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都位居圣地亚哥前列,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极低,财政赤字堆积如山,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最为凸显。这三
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基本相似,但在军政时期的社会动员水平却又明显不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如果后转型时期的住房政策对它们各自的社会组织都造成了类似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具有一般性的结论。
为了评估后转型时期住房政策的影响,笔者在上述地区做了30个访谈。其中,大部分访谈(25个)都是在2006年1月完成的①。访谈共分两组,第一组对象主要是那些参与住房项目的国家和地方官员。在国家层面,我对Jaime Riquelme和Maria Cucurella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两人供职于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下属的住房管理处。在地方层面,我对三个调查地的市政官员都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Maribel Zuniga(拉格兰哈区社会分层管理处)、Tamara Saez(培亚尼罗雷区住房管理处的社会助理)、Alejandro Rojas(危楚拉巴区住房补贴主管)。
第二组访谈对象主要是上述三个社区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笔者随机选取的。他们均向政府申请了住房补贴,有些人已经获得了补贴。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社区至少都有一名受访者曾经领导了
一些运动来争取国家的住房补贴。笔者随机访谈的方式主要是在三个社区询问路人,以及在区政府办公室挑选那些参与了国家住房项目的社区居民;还有些个案是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的,即由被访者来推荐其他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②。
许多文献都表明,这种案例数量相对特少的深度定性分析非常有用。例如,Lijphart(1971:685)就曾说过:“在人力财力都有限的情况下,与其对许多案例做表面的数据分析,还不如对少量的案例进行深度的比较研究”
由于本研究属于案例比较研究,因此,笔者选取访谈对象的方法不同于定量研究的抽样方法,无需刻意选取一些在统计特征上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住房补贴的分配过程与集体行动的机理,所以,那些申请过住房补贴项目的人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此外,访谈对象的选择过程是非常开放的。笔者并没有事先限定受访者的人数,而是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去寻找另一些适合的受访对象,直接获得的信息变得重复,没有新的内容为止。有关这种方法论的深度讨论,详见Charles Ragin(1945:85-7),Mario luis Small (2009:226-7) 和Robert Yin(2009:54-60)。
笔者对政府官员的访谈一般是在他们的办公室进行的,而对于那些棚户区居民的访谈则是在他们的家里开展的。采取的方式都是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每次时长都超过1小时,有的甚至还要持续数小时。每次访谈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询问受访者与住房项目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参与经历;其余问题还包括住房补贴的类型、发放的方式(例如申请者需要具备的资格条件)及其对圣地亚哥城市贫困群体相互合作、集体行动以及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尽管在对第一个棚户区居民进行调查时,笔者就已发现了住房项目的分级式管理导致他们互不信任,但在接下来的包括对政府官员的所有访谈中,笔者依然坚持询问了这个问题。此外,笔者还详细询问了有关团体申请住房补贴的要求和过程,以查看现行政策在多大程度促进了合作而不是个体化的行动。
在比较分析了三个社区的访谈资料之后,笔者梳理出了一些共性。棚户区居民普遍认为:①政府对他们的资格评估带有专断性,因为在他们看来,邻里间的生活水平和相对需求并无多少差异,但评估员却将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几个等级;②评估过程具有主观性,因为评估员仅仅依据邻里间的比较,便做出了对居民生活条件的判断;③评估过程带有竞争性,因为住房资源本就稀缺,而评估过程是带有专断性和主观性的。基于这样的想法,有意于申请住房补贴的人们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展现自己生活条件的恶劣。例如,他们会在评估员来调查之前,将家里贵重的设施和电器(例如木地板、电扇和电视等)搬走或藏起来。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尽管有不少棚户区居民对此表示了不满,但更多的却是理解。他们认为,是资源的紧缺和家计调查的严格才催生了这样的行为。正如一名受访者所说:“这不光彩,却情有可原”①。
这一评价反映了受访者普遍持有的两个观点:①住房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基于个人的需求而不是集体的需求;②即便某些个人的逐利行为带有一定欺骗性,但这依然是对制度做出的理性回应。受访者普遍认为,住房补贴项目推行的是个人主义,支持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至于这样做的结果是好是坏,大家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住房保障和城市事务部的Jaime Riquelme(在军政时期就担任现在的职务了)以及负责危楚拉巴区住房管理的Alejandro Rojas都对此表示了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项目能够激发人们的主动性,让他们自力更生。而另一些人则感叹项目的实施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加强了棚户区居民的经济分化,因为那些有能力获得商业贷款和住房补贴的人更容易分得好的住房(面积大而且基础设施好)。
这种负面效应充分体现在了补贴资格评估的过程中——为了让自己能够申请更多的住房补贴,有些棚户区居民会在市政调查员面前掩饰自己的真实生活水平,表现出强烈的住房需求,结果激化了邻里之间的愤懑与不信任。正如一名草根领导者所说:“这个政策造成了社区的分裂,它加剧了各个家庭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竞争。
如果哪家有电视、木地板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显得他们比周围的邻居过得要好,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评级,他们就会在市里的官员到来之前把东西都搬走。邻里之间变得非常多疑,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再也没法团结一致了。”①在这个问题上,其他社区的领导也是反响强烈。例如,在危楚拉巴区的拉平科亚,“亲友委员会”的组织者Sabina说:“我挺不赞成这种衡量穷人需求的方式……只要社工前来访问,人们就会把自己家里的那些东西都藏起来。这个评估系统逼得人们去撒谎,而且最后得出来的评级结果也不一定是公道的,所以我觉得挺不好。”②另一名来自拉格兰哈区永盖的社会运动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个系统很不公平,因为好多社会工作者在评估人们的住房需求时,都带着主观看法。例如,有些家庭或许花了很大努力才获得了一些物质资产,然而有些社工单凭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些人没有住房需求。”③
这种评估方式激化了邻里之间的不信任。的确,通过地方政府官员接到的抱怨我们便可见一斑。一名供职于拉格兰哈区社会分层部门的政府官员说道:
住房补贴僧多粥少,人们也因此怨声载道,他们会问“为什么我和我邻居的生活条件一样,但是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评级去申请补
①对Soledad Araos (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亲友委员会的主任)的访谈,1993年10月25日,圣地亚哥圣米格尔区的拉维多利亚棚户区。
②对Sabina的访谈,2001年6月23日,圣地亚哥危楚拉巴区的Comites de Allegados (直译过来就是“亲友委员会”)。亲友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争取住房补贴,这个名字反映了智利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即多个家庭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或是寄居在朋友篱下。
③对Carlos Ramirez的访谈,2001年6月19日,圣地亚哥的拉格兰哈区。
贴,我们就不可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确实是可以修改家计调查的结果,但如果人们声称他们没有工作(失业者可以申请到更多的补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又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们。现在,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那就是有些获得补贴的人根本没有在自己社区里接受过调查。他们为了获得更低的评级,往往会待在合住屋(多个家庭共同聚居)里接受访谈。
另一名在危楚拉巴区参与住房补贴管理的政府官员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即棚户区居民会利用评估制度来让自己获得更低的评级: 有好几次我去人们家里做调查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先在外边等。有些时候,因为窗户或者窗帘没有关紧,我都能看到他们在里边忙忙慌慌地藏东西。等到收拾妥当以后,他们才会让我进去,告诉我说他们生活很困难,没什么家什……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糟糕的是,由于历史使然,智利人的社会救助意识非常强。每天都有人前来找政府要食物、水泥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还包括住房补贴。人们希望国家扮演一个全能的角色来帮助他们,这是不对的。人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培养自己的独立谋生能力。
 这名政府官员将上述现象部分地归咎于穷人,认为城市贫困群体缺少自力更生的意识,对国家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刻意夸大自己的被剥夺处境,以期获得国家的救助。这种看法与现代化理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颇为接近。尽管如此,受访政府官员和棚户
这名政府官员将上述现象部分地归咎于穷人,认为城市贫困群体缺少自力更生的意识,对国家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刻意夸大自己的被剥夺处境,以期获得国家的救助。这种看法与现代化理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颇为接近。尽管如此,受访政府官员和棚户
①对Maribel Zuniga的访谈,2006年I月9日,圣地亚哥的拉格兰哈区。
②对Alejandro Rojas的访谈,2006年I月5日,圣地亚哥的危楚拉巴区。
区居民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在遭受物质剥夺和住房补贴紧缺的背景下,人们面对严厉的家计调查所采取的一种理性反应。这些限制强化了棚户区居民的竞争和分化,侵蚀了他们互相信任的基础。
这样一来,住房政策通过严格的团体申请制度,阻碍了穷人的合作与集体行动。尽管政府为申请住房补贴的团体提供了许多项目资源,但繁多的要求和激烈的竞争最终促使那些条件较好的人离开团体,转而采取个人化的方法来争取资源。团体申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①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必须属于同等的贫困评级;②所有成员都必须拥有一定量的存款;③团体需要提交一份购房或建房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充分满足所有成员的需求,以及相应项目的申请条件。这三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例如,针对第一个条件,若是有人的评级高于相应的最低要求,即便他们和团体内的其他人有着非常好的个人关系,或是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帮助整个团体争取住房补贴,最终他们都会被排除在团队之外。拉平科亚棚户区的亲友委员会主席Raul Oyarce解释道:
 你在家计调查中是什么样的分值,就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住房。我认为这种制度设计不太合理,因为大家本应都有房子住……在一个委员会里,各个家庭的分值都必须低于520分,如果超过了,它们就会被自动取消资格……按照我自己的分数,我本来应该离开委员会的。但出于责任感,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为其他人努力,我可不想什么事都没做成就走人了。
你在家计调查中是什么样的分值,就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住房。我认为这种制度设计不太合理,因为大家本应都有房子住……在一个委员会里,各个家庭的分值都必须低于520分,如果超过了,它们就会被自动取消资格……按照我自己的分数,我本来应该离开委员会的。但出于责任感,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为其他人努力,我可不想什么事都没做成就走人了。
①对Rdl Oyarce的访谈,2006年I月6日,圣地亚哥市危楚拉巴区的拉平科亚棚户区。
尽管有着对集体的使命感,但在接下来的访谈中,Oyarce提到他将很快以个人名义申请住房补贴,为自己找一套合适的房子:“我准备去申请统一标准的补贴,给自己争取住房……我可能就要离开委员会了,剩下的人还得继续等待并为之努力。但我等不了那么久了。”在该案例中,一名有责任感和能力的领导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团体,依靠个人的力量去争取稀缺的住房资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家计调查与市级的住房补贴项目将群体拆分开来,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求让他们失去了集体行动的动力。
针对团体最低存款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态势。Oyarce先生在拉平科亚亲友委员会担任主任期间,便遇到了这样的困境。
我们本来有39个家庭申请补贴,但其中只有16个家庭满足政府的存款要求。我们又不能一直等着其他那些家庭慢慢地把钱存够,所以,后来我不得不放弃了他们。这实在不是我一个主任能做的决定,我们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投票,市里的社会救助部门也对我们给予了支持。
来自永盖棚户区的另一名社会运动领导人点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
在一个有着40个家庭的委员会里,大家必须存够18万比索(约合300美元,相当于每月最低工资的两倍)才能申请最基本的住房项目。如果委员会里有成员达不到存款要求,哪怕只有一个,所有人的住房申请也都会跟着泡汤。所以啊,委员会复杂得很……我自己的住房是靠自己申请的,不用靠其他人一起来争取补贴,所以也省了不少麻烦。
①②对Rdl Oyarce的访谈,2006年I月6日,圣地亚哥市危楚拉巴区的拉平科亚棚户区。
即便所有的团体成员都有了足够的积蓄,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获得住房补贴。因为他们还得提交一个完整的项目计划,需要详细地说明他们在哪儿购置土地,怎么修建个人住房,等等。而这又得耗费一笔费用,请相应的咨询专家来帮忙完成。计划制定完毕以后,他们还得跟本地区的其他团体竞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地区住房和城市事务服务局发放的补贴。总的来看,智利政府在住房政策中引入了竞争元素: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地方官员决定了人们有什么样的资格去获得哪种补贴,造成家庭间的竞争;在最后的审查阶段,地区住房和城市事务服务局又决定了团体递交的申请书是否能够通过,强化了团体间的竞争。
这种精巧的制度设计给城市贫困群体的集体行动施加了不少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倾向于个人化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他们更愿意独自争取住房补贴。如果在正式部门有份稳定的工作,并且有着良好的信贷记录,人们便能通过商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相反,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就只能去和那些最为弱势的群体争取补贴。如此一来,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分层化现象就波及住房政策的目标群体,让贫困人口的分化愈趋明显。正如一位单亲母亲所说的那样:
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这个不算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信贷记录很好。由于有收入和存款,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信用去争取更多的贷款。但我要是去银行贷款的话,人家肯定不愿意贷给我……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其他东西来证明我有还贷能力。而且存款对于我来说也相当难,毕竟两个女儿都得靠我来养活。上次我女儿摔倒了送去医院,我还花5万比索的存款来给她治疗。①
该案例尖锐地揭示了住房政策的实质:它不但没有减少市场竞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压力,反而在很多情况下起到了负面作用。此外,尽管这一政策旨在促进穷人的集体行动,让他们携起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但它最终却加强了穷人的分化与彼此竞争。
即便有些人最终获得了政府项目的资助,但社会融合与合作的情况也没有太多起色。总之,政府补贴的住房项目最终造成了空间和社会层面的隔离,公共空间的欠缺阻碍了社会互动的发生,并且过于狭小的住房空间也限制了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不足都对社会融合,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培育形成了不利影响。例如,大多数安置房都建在了市郊,让居民不得不远离熟识的亲友和邻居,从以前的社会网络中游离出来,形成了空间和社会层面上的孤立,从而扰乱了邻居之间通过相互信任与支持搭建起来的系统。此外,由于新建的住房面积过小,使得大家庭(例如几代同堂的家庭)难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样一来,代际的社会联系便遭到了削弱,而家庭活动和社会互动空间的贫乏,则让孩子们游荡街头,暴露在毒品、暴力和其他社会问题之下,使得贫困现象更容易蔓延(Ducci,2000)。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将造就一批低收入的社区,而且“社区里的住户唯有贫困这一个共同点……大家都会持久地生活在互不信任和缺乏团结的氛围之下”。
①对Yesna Salazar(棚屋居民)的访谈,2006年1月13日,圣地亚哥拉格兰哈区的永盖棚户区。
七、 结 论
本文对圣地亚哥3个贫困社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智利政府分配住房补贴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政府原本希望借这个政策来促进城市贫困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合作的增加来平抑市场竞争的压力,从而促进社会整合。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稀缺的公共资源和严格的家计调查加剧了社区居民之间的竞争和互不信任。由于团体申请的程序极为繁冗,许多人放弃了集体合作的形式,转而以个人的名义来争取稀缺的资源。从军政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便通过去中心化的行政管理方式实施了对社会的控制,使得公共投入始终不足,一些政党和社会组织也遭到排挤。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是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延伸,导致了不同阶层在政治领域和地理空间上的继续分化。而且,新修的安置房大多集中在市郊,这进一步加重了城市贫困人口的边缘化趋势,减少了他们的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住房政策对社会组织造成了消极影响。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贫困人口的集体行动能力会受到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此外,社会福利政策是我们认识民主的窗口,查看福利政策本身及其对公民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民主的质量。如戴蒙德和莫尔利诺(Diamond andMorlino,2004)所说,公民参与可以加强政治的问责性和代表性,最终增进民主;无益于公民参与的制度和行政结构必定有损民主。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利的住房政策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所嵌入的福利体制是按照市场原则建构起来的,限制了弱势群体的合作能力,也就难以形成一套有利于他们民主制度。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定向救助的方式来分配社会福利资源的确比较有效率。然而,本案例显示,这种模式从长远来看并不是解决穷人困难的根本之道;相反,它还削弱了穷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让他们更加难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要求政治精英听取并满足自己的诉求。也就是说,发展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不一定能够实现对他们的赋权,进而带其走出困境。这个结论对世界银行与泛美发展银行长期坚持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值得认真对待。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编译者:唐丽霞 罗江月)
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建设
在2006年出任“八国集团”主席国的前一年,俄罗斯开始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建设工作,确定了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向,并决定大幅提高外援总额。政府在分析大量公开发表的文件、官员发言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制定了官方发展援助的管理制度,确定了援助总额和主要的援助方向。俄罗斯尤其注重与从事国际发展援助活动的国际性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强同国内外从事该领域活动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和非商业组织之间的合作。本文重点介绍俄罗斯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建设情况及相关问题。
1. 从受援国到援助国
前苏联制定了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活动的政策。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20世纪末的激进转型,俄罗斯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不得不靠接受外国援助度日。从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同中东欧及其他转轨国家一道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发展援助委员会列入第二批受援国名单。由于未被列入官方发展援助计划,因此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被称为官方援助(表1)。
2005年,由于对快速发展国家的援助被削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停止了第二批援助的实施。俄罗斯及其他在2004-2007年加入欧盟的国家所接受的援助数据没有被统计到官方援助资料中,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库中找不到俄罗斯接受援助的资料。目前,俄罗斯属于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新伙伴——援助国。
表1 俄罗斯接受外援数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s 1997-2005资料绘制。
2. 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俄罗斯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法律正在建设中。通过对一些法律法规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被援助国经常使用的如“官方发展援助”一类非常重要的术语和概念,要么未被提及,要么没有加以界定。还有一些概念的界定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定义不同。①还有部分对外援助政策或在单独的法律文件、或在俄罗斯参与的地区一体化联盟条约以及一系列战略构想之中。例 如:2000年8月31日俄罗斯联邦政府第644号决议《援助外国消
除紧急情况的规则》,2000年10月10日关于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1999年12月8日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条约,2007年关于俄罗斯联邦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构想,俄罗斯2020年前对外政策构想,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构想。
一些概念(如“人道主义援助”、“技术援助”)在俄罗斯作为受援国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法律文件中有正式的界定,例如:1999年9月17日俄罗斯联邦政府第1046号《关于审核登记技术援助项目和计划以及出具技术援助资金、商品、工程、服务所属证明的原则》的决议。
为准备2006年出任“八国集团”主席国,俄罗斯于2005年积极开展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立法工作,要求政府执行机构从制度上保证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活动。2006年11月政府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国际发展援助构想草案,最终方案由2007年6月14日的总统令批准。援助构想中表述的宗旨如下:建立俄文国际发展援助执行机构的制度基础,将俄罗斯提至“八国集团”伙伴国在该领域传统捐资国的地位。
援助构想的法律基础是俄罗斯宪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预算法典。2007年上述部分文件有的改动较大,有的重新制定:2008年7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2009年5月13日通过了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2009年12月17日提出俄联邦气候学说、2010年2月1日提出俄联邦粮食安全学说。在2009年国情咨询中俄罗斯总统委托制定为促进俄联邦长期发展而系统有效地利用对外政策因素的纲要,提出在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构想中必须体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及其他领域的变化,利用外交活动解决现代化问题,提升拉美地区在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等①。俄罗斯认为上述目标是可以通过落实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战略的具体措施来实现。
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构想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及该领域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如千年宣言、蒙特雷共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2005年《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等。
援助构想认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必要且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快速稳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近邻的经济状况,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②稳定发展直接影响到现代集体安全体系,该体系通过降低恐怖主义泛滥、流行病、非法移民及生态灾难的风险而构筑。
 预计通过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可以下列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利益:①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②稳定俄罗斯伙伴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③同伙伴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④预防俄罗斯周边地区出现紧张和冲突源地;⑤为俄罗斯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预计通过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可以下列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利益:①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②稳定俄罗斯伙伴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③同伙伴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④预防俄罗斯周边地区出现紧张和冲突源地;⑤为俄罗斯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① http: //www. runewsweek. ru/country/34184/11. 05. 2010。
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斯托尔恰克曾说:“援助构想中包含着对俄罗斯而言的革命性原则……帮助穷国,首先是在帮助你自己。”该原则意指穷国的发展在未来会促进他们对援助国所生产的商品的消费②。 2007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援助构想的实施计划,包括采取具体措施建立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并准备在2008-2010年具体实施。 由于实施计划的落实情况不佳,必须制定2011-2015年的新计划,以此体现俄罗斯对出任2014年“八国集团”主席国的重视以及在2015年即将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国际发展援助系列活动的整体性。
3. 负责实施援助的国家机构
援助构想及实施规划中列明负责援助事务的联邦机构包括:①总统;②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③俄罗斯政府;④外交部;⑤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⑥财政部——联邦国际发展署;⑦经济发展部;⑧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⑨农业部;⑩工业贸易部及能源部;⑾教育部;⑿ 生保健和社会发展部;⒀自然资源和生态部;其他相关部委。
总统办公厅在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活动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总统参与“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为总统准备参加峰会的各类文件。总统的代表具体负责与主要工业国家集团及“八国集团”成员国首脑代表联系的事务,这些事务与直接发展援助活动密切相关。外交部和财政部负责协商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费用问题,其中包括确定优先援助的国家和地区,援助政策的合理程度,援助额度、渠道、形式以及援助条件。
②http: //www.minfin.ru/ru/press/speech/index.php? pg4=45&id4=37560
外交部参与负责援助事务的即有地区分支机构,如负责同世界各地区合作的机构,也有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如国际组织司等。
根据财政部国际金融关系、国家债务和国家金融资产司的条例,该部门负责提交国家在双边和多边关系基础上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建议。2009年12月该司分解为国际金融关系司和国家债务及国家金融资产司,国际金融关系司成为财政部负责协调国际发展援助问题的主要负责部门。
2008年9月成立了联邦独联体、海外同胞以及国际人文合作事务署,隶属于外交部,主要负责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为俄罗斯海外侨胞提供支持以及在海外推广俄语。该部门并未取代为实施援助构想计划而设的俄罗斯国际发展署。
4. 捐资数额
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无论是规模还是形式都曾一度受限,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从未停止参加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并按期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为需要减轻债务负担的国家减债。
俄罗斯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特点是由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同时与俄罗斯在当代世界的作用以及广大的纳税人“视俄罗斯为强大的援助国的准备程度相关”。专家们在讨论援助构想时就曾强调指出,构想本身并不会增加联邦预算的支出,因为通过构想并不意味着用于官方援助的支出会自动增加,只有将相关费用列入联邦预算法才能够得到保障。
由于没有国家统计系统,2004年前的官方援助数据来源差异很大。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统计,2005年联邦预算的发展援助实际支出9 700万美元,不包括免除最贫困国家的债务额①。财政部一位副部长说,在2003-2005年俄罗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额达到5 000万~6 000万美元(表2)②。
表2俄罗斯官方发展援助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M. P. PaxMaHryjioB. CraHOBJieHHe cHCTeMbi cofleftcTBHH MejKAyHaponHOMy pa3BHTHio b Pocchh. BecTHHK MejKayHapottHbix opraHHsauHH. 2010. No2 (28)。
俄罗斯常驻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梅什科夫称,2010-2011年俄罗斯承担的发展捐资额已超过10亿美元③。
俄罗斯政府估计,2006年俄罗斯参与多极发展援助的拨款不仅少于“八国集团”中发达的伙伴国,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④。
经济危机期间,俄罗斯不仅履行了此前承担的义务,还大幅提高了用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支出。俄罗斯财政部长在2010年2月17日召开的《全球化体系中的发展融资新伙伴》研讨会上称:“2009年俄罗斯基于双边和三边基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联邦预算资金达到8亿美元,而前一年的数额是2.2亿美元。”⑤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佐利克高度评价了俄罗斯为发展援助所做的贡献,据他估计2009年俄罗斯所有援助的数额达到9亿美元⑥。俄罗斯外交部代表确认,2009年官方发展援助数额激增与全球经济危机所需的紧急资助有关。
俄罗斯官方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值很低。在援助构想中提到“随着相应的社会发展条件逐渐成熟,俄罗斯联邦会持续不断地提高国际发展援助的捐资额,以便在未来达到联合国建议的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0.7%的水平”⑦。
在俄罗斯总统关于2010-2012年预算政策的预算咨询报告中首次将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作为优先方向,其中包括向最贫穷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而在2007年的预算政策文件中还只是提到俄罗斯

① http://www.prodemo.ru/_template.html? sec= 11718&doc= 517996910
② http://www.minfin.ru/ru/official/index.php? id4=68950
③ http: //www.mid.ru/ns-dmo.nsf/cfabe4e8ed2f8ad7432569ff003cdlc0/432569fl0031eb93c32575 ce003cc96do
④ http: //www. prodemo, ru/ _ template, html? sec=1171&doc=51799691。
⑤ http ://www. mgdf. ru/rus/ press/ speeches/opening _ kudrin。
⑥ Zoellick R. Welcoming remarks for Moscow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Partnerships i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The World Bank, http://go. worldbank. org/T4TBW5JW70。
⑦ http :Ilwww. gks. ru/free _ doc/new _ site/vvp/metod. htm。
要把积极响应将减免最穷国家债务当作主要任务之一①。
5. 加入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
俄罗斯是多个从事发展援助大型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国,如联合国系统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 援助构想中重点强调俄罗斯要加入国际组织。在建立俄罗斯国家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之前,俄罗斯的国际发展援助主要以多边基础上提供援助的形式进行,即通过向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首先是联合国计划、基金和专门机构、地区经济委员会及其他实施发展计划的组织缴纳专项经费和自愿捐助。另外,还参与“八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系统组织框架下实施的国际倡议捐助经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2008年俄罗斯向主要的发展援助国际组织缴纳的费用达到1.17亿美元,其中67%(7 840万美元)资助了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全球基金),16.7%(1 950万美元)——国际发展协会,12.8%(1 500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 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国地位是其扩大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制定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构想时,俄罗斯首先借鉴了“八国集团”伙伴国的经验。构想中承认,“八国集团”成员国援助的显著增长,是直接影响俄罗斯联邦政府执行机构从事国际发展援助活动的重要因素。2006年,俄罗斯担任“八国集团”主席国,促进了国际发展援助国家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援助优先方向的确定。
 ①http://kremlin.ru/news/6752。
①http://kremlin.ru/news/6752。
2006年4月6~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由俄罗斯主持的题为“全球化社会中发展援助的新资助者”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肯定了非传统资助者和新资助者以及重新回到资助者行列的国家在国际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实现国内发展目标的显著成绩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可以向力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经验。圣彼得堡“八国集团”峰会以各国承担具体的义务而结束,其中包括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义务。峰会的文献中包含“八国集团”为发展援助首先是卫生领域提供大量资金的计划,承诺了各种期限(1~20年)的资金额达247亿美元。传染病-216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发展医疗系统——10亿美元,抗禽流感和预防可能的流感大流行——5亿美元,13亿美元拟划人预防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预算,划入其他国际机构预算的资金共2亿美元,包括根除脊髓灰质炎全球倡议、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非洲艾滋病疫苗等计划①。
为了提高国际社会对病毒扩散的监控能力,俄罗斯倡议在本国境内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欧亚和中亚流感合作中心。作为主席国俄罗斯还建议建立东欧和中亚地区抗艾滋病毒感染疫苗的地区协调机制②。
①http://www. iori. hse. ru/publications/herald/material/4 _ 09/g8 _ g200
②Bopb6a c HH$eKUHOHHbiMH 6ojie3HHMH. http://g8russia. ru/docs/10. html0
目前,除俄罗斯以外,“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全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俄罗斯同巴西、印度、中国及南非一样,属于不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提交自己援助计划的国家,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承认这些国家旨在发展的合作意义正在提升。
俄罗斯联邦政府承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中没有俄罗斯为官方发展援助捐资的信息不利于促进俄罗斯国际形象的改善,因此,俄罗斯未来在努力提高国际发展援助水平的同时,还争取让国际社会正式承认自己的捐助,将其列入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发展委员会发布的统计资料中。
按照2010年“全球发展融资体系中的新伙伴”会议的报告,俄罗斯向发展领域的新伙伴国建议一起请求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专业从事援助统计报告以及援助管理的工作组合作③。
一系列国际组织积极挖掘俄罗斯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政府机构的潜力。例如:联合国发展计划正在实施项目,旨在提高俄罗斯政府机构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声誉。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与俄罗斯财政部共同落实旨在加强国际发展援助管理能力的倡议——《作为资助者的俄罗斯》④。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资助在俄罗斯发展基础设施的项目,并同俄罗斯政府在北维环境合作项目框架下具体实施项目。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代表称:俄罗斯其实本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由处于转轨初期的国家所倡议的该银行框架下的活动,或者利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基金援助西巴尔干和中亚地区⑤。
③http://www.mgdf.ru/rus/press/speeches/chairmans_summary。
④TheWorldBank. 14. 05. 2009. URL:go. worldbank. org/03TNN7YRRO0
俄罗斯同时也是几个国际机构资金援助的获得者,所获资金主要流向私人部门。俄罗斯是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最大的受援国:1991-2008年获117亿美元,占该机构此间资助总额的27%,2008年占31.5%⑥。国际金融公司向俄罗斯进行大量投资用于资助企业活动和急需资金援助的地区发展。
6. 提供援助的方式及原则
援助构想中指出,战胜贫困和落后的主要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身上,但是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只有在国际社会协调一致援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提高发展援助效率的方法之一是伙伴国在制定发展政策和协调发展战略时要遵从有效管理原则⑦。
俄罗斯外交部和财政部认为,不能系统性地使用官方发展援助预算资金不能给俄罗斯的受援国带来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不能给俄罗斯带来应有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俄罗斯提供国家发展援助的原则是受援国必须对俄罗斯持政治上友好的方针,表现出全面持续发展双边合作的意愿。援助构想规定,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政策的基础是把握援助目标与实现目标可能性之间的合理平衡。解决国家对外政策及国内任务的经济和财政举措必须首先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包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而参与国际事务的规模要与加强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实际贡献相当。
⑤http: //www.ebrd.com/apply/tambas/track/tam/etc.htm。
⑥http: //www.mgdf.ru/files/2008。
⑦http: //www.oecd.org/dataoecd/36/63/35023545。
俄罗斯提供发展援助的渠道正逐步拓宽。如果说近年来俄罗斯参与国际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减免前苏联为最贫穷国家提供的贷款,那么目前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国际基金和项目出资的机制,未来则是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建立和开发国家系统的国际发展援助工具。
2008年11月7日获批的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构想中有如此的阐述:俄罗斯联邦对外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支持的方向之一是利用相关贷款和国际发展援助机制将俄罗斯的商品和服务推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①。
俄罗斯当局认为,新的捐助者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们能够提供额外的资源,还因为他们有自身经济发展和接受外援的成功经验,可以同受援伙伴国一起分享。同时,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活动也要求建立多边和双边援助的有效协调机制。对新资助者的利用,无论是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传统工具还是创新的金融机制,都应该受到欢迎。
7. 援助的领域
 目前,俄罗斯发展援助的重点还是2006年任“八国集团”主席国时确定的,首先是能源、卫生和教育领域,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荐的重点也包括在援助构想之内。部分政府机构代表解释将能源作为重中之重“是因为没有电力的发展根本就谈不上卫生和教育的发展”①。
目前,俄罗斯发展援助的重点还是2006年任“八国集团”主席国时确定的,首先是能源、卫生和教育领域,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荐的重点也包括在援助构想之内。部分政府机构代表解释将能源作为重中之重“是因为没有电力的发展根本就谈不上卫生和教育的发展”①。
②http: //government.consultant.ru/doc.asp? ID= 49135。
(1)免除债务。发展中国家资源极度缺乏,同时欠前苏联大量债务,免除这些债务以前和现在都是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工作的重要方面。2003年普京总统宣称,按照免除发展中国家债务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说,俄罗斯占世界第一位,而免除债务的绝对量则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法国和日本②。
在2005年“八国集团”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俄罗斯承诺免除非洲国家113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严重负债贫穷国家倡议”框架内的22亿美元。
2006年12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免除债务国的债务,条件是债务国在2006年12月31日前加入“重债穷国债务减免倡议”。截至2007年,有6个被列入“倡议”的非洲国家对此做出回应。一个国家被列入“倡议”的条件是履行作为债务国的义务,并在参与减贫项目中取得一定成绩。得到俄罗斯免除债务的国家包括:贝宁-1 175万美元,赞比亚-1.122亿美元,马达加斯加-1.024 5亿美元,莫桑比克——1.486亿美元,坦桑尼亚——2 068万美元,埃塞俄比亚——1.628亿美元。获得免除的债务要作为发展的资金来源,俄
罗斯本着此项原则与这些伙伴国家约定将免除的债务金额有效地用于俄罗斯所规定的三个优先发展方向。
①http ://www. minfin. ru/ru/press/interview/index, php? id4=48 。
②http: //archive, kremlin, ru/text/appears/2003/06/47770. Shtml。
2008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声明:“最近我们免除了一些国家首先是非洲国家的债务,总额达160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在援助非洲项目框架内,俄罗斯2008年总共减免非洲国家200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外交活动一览》报告中说:“总共减免了200亿美元的债务。”文件中指出,俄罗斯正在与贝宁、几内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就减免债务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强调说,“俄罗斯对非洲援助项目所做的贡献仍然主要体现在减轻非洲贫穷国家债务方面上”。
俄罗斯财政部2011-2012年工作重点和成果报告中指出,苏联时期出于政治考虑提供优惠贷款,没有考虑受援国按时全部履行还债义务的能力,接受苏联贷款的大多是发展落后的国家。据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月1日,俄罗斯共有11个债务国(其中一个属于独联体国家),俄罗斯表示尽力在2012年前将债务国减至一个,但如何达到目标没有解释④。
(2) 能源援助。俄罗斯提出在非洲国家的农业地区建设能源基础设施,该倡议得到了“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支持,球村”能源伙伴的参与下得到实施。该项目框架下正在建设小型水电站和输电线路,以保障非洲国家边远地区的用电。俄罗斯计划自2007年开始4年为该项目拨款近3 000万美元。
能源援助。俄罗斯提出在非洲国家的农业地区建设能源基础设施,该倡议得到了“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支持,球村”能源伙伴的参与下得到实施。该项目框架下正在建设小型水电站和输电线路,以保障非洲国家边远地区的用电。俄罗斯计划自2007年开始4年为该项目拨款近3 000万美元。
①http://www.minfin.ru/ru/press/interview/index.php? id4 = 48。
②O^HunaJIbHbift caftT F[pe3HAeHTa PoccnftcKoft OeAepaunn. 03. 07. 2008. http: //kremlin.ru/news/657。
③俄新网 RUSNEWS. CN 莫斯科 2009 年 3 月 6 日电 http: //www. xjjjb. com/html/news/2009/ 3/36839. htmlo
④http://wwwl.minfin.ru/common/img/uploaded/library/2009/ll/doklad2010 - 12。
(3)教育援助。从2008年10月俄罗斯开始实施教育发展援助项目,即俄罗斯政府同世界银行共同合作方案,旨在加强俄罗斯作为新资助国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低收入国家的教育质量。经过选拔有7个国家参与该项目,包括4个非洲国家、2个中亚国家以及1个东南亚国家,该项目下的信托基金在5年之内使用,总额3 200万美元(表3)。
另外一种教育发展援助的方式是由俄罗斯预算出资培养外国大学生。2009年设奖学金数达到9 091人,比2008年增加了1 330人,涵盖161个国家。计划近两年提高至1万人。
(4)卫生援助。2000-2005年,俄罗斯为解决全球卫生问题捐资5 293万美元,其中包括对专业国际组织的捐助。2006年仅1年就达2 985万美元,之后的2007和2008年更是大幅增长至1.2亿和1.5亿美元,2009年继续增长④。
 2006年俄罗斯决定放弃全球基金的受援国地位,承担了向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的国家拨款义务,该项目由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实施,由此节省的资金可以用于援助其他国家。俄罗斯政府高度评价全球基金的作用,认为其经验是最为成功的(表4)。
2006年俄罗斯决定放弃全球基金的受援国地位,承担了向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的国家拨款义务,该项目由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实施,由此节省的资金可以用于援助其他国家。俄罗斯政府高度评价全球基金的作用,认为其经验是最为成功的(表4)。
① http: //wwwl. minfin. ru/common/img/uploaded/library/2009/ll/doklad2010 - 12。
②www. siteresources. worldbank. org/EDUCATION/Resources/278200 - 1256666213814/READ _ AnnualReport _ 2009。
③http: //www. mid. ru/brp _ 4. nsf/0/458DB10D6AF25B85C32577340055CCCF. 2010/06/01。
④https://admin, rospotrebnadzor. ru? press _ center..
(5)农业和粮食援助。近几年粮食大丰收使得俄罗斯能够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达到千年发展的第一个目标(即将世界饥饿人口数降至一半)做出更大的贡献(表5)。
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梅什科夫称,自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俄罗斯共划拨7 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克服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包括紧急救助项目①。
表3俄罗斯为“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基金会的捐资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Education for All-Fast-track Initiative。
①http: //www. mid. ru/ns-dmo. nsf/cfabe4e8ed2f8ad7432569ff003cdlc0/432569fl0031eb93c32575 ce003cc96do
表4全球基金和俄罗斯的互相捐资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Global Fund Disbursements on 11 May 2010,The Gloh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Contributions to Date April 2010。
表5俄罗斯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捐资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Government Donors Contributions to WFP:Comparative Figures 2005—2010 as of 11.05.201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俄罗斯提供粮食援助的主要合作伙伴。合作始于2002年俄罗斯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的互相谅解备忘录,俄罗斯向世界粮食计划
署捐出首批资金,2005年俄罗斯成为该组织的定期捐资成员。尽管与“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相比,俄罗斯的捐资数额不高(2009年仅排在法国之前),但年捐资额及占比逐渐提高。自2005年开始,俄罗斯捐助的资金可供应10.6万吨粮食①。
俄罗斯的粮食援助首先惠及独联体国家——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其次是亚洲近邻——朝鲜和阿富汗,非洲国家——安哥拉、几内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古巴。
除了定期资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外,俄罗斯还资助一次性的粮食援助。例如2008年援助孟加拉、几内亚和津巴布韦共350万美元,2009年俄罗斯向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助额近3 000万美元②。
接受俄罗斯粮食援助的国家数量不多,塔吉克斯坦是俄罗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之一,2005年——600万美元,2006年——200万美元,2007年——300万美元,2008年——200万美元,2009年——500万美元③。在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协商后,2010年俄罗斯的资助由几个国家分享:塔吉克斯塔——550万美元,阿富汗——500万美元,亚美尼亚——250万美元,刚果民主共和国——200万美元,吉尔吉斯——500万美元。2010年一次性紧急行动预留1 000万美元,其中420万美元资助海地,另外还向帕莱斯蒂纳提供粮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④。
据国际发展学院的统计,2002-2004年间,俄罗斯人道主义援助中的35%是粮食援助,印度——43%,南非——59%,韩国——24%①。俄罗斯民防、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活动提供物流支持,2008年,签署了关于在紧急情况下俄罗斯提供航空运输的备用协议。俄罗斯政府认为有希望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储备俄罗斯粮食(如在意大利城市布林迪西),并且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安排世界粮食计划署用于应对紧急状况的人道主义援助储备物资。
htp://www.mchs. gov. ru/news/detail, php? ID= 30776 04. 03. 2010。
②htp://www. mid. ru/brp _ 4. nsf/0/03C55FD1668E89BCC32576DC0056FF3B04. 03. 2010。
③htp://www.mid. ru/brp _ 4. nsf/0/712847854B22A240C32576AC0042835E 15. 01. 2010。
④htp://www.mchs. gov. ru/news/detail, php? ID= 3086810. 03. 2010。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将提供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视为对俄罗斯粮食出口商的支持。2009年4月,在通过政府关于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民防组织捐资的命令时强调,“相关的”专项资金应该在俄罗斯购买小麦和面粉,并且用于支付俄罗斯企业运输上述物资的费用。如此有计划部分地解决了国内市场的余粮,保证国内农业商品生产者和加工企业的额外销售,并使运输公司的潜力得到发挥。
俄罗斯政府机构官员表示,俄罗斯已做好准备扩大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未来的合作将不只限于提供人道主义的粮食援助,还要介入发展援助领域跨部门的项目,包括涉及在粮食储备不足的独联体国家的共同行动。2010年3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乔塞特·希兰访俄时签署了扩大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在亚美尼亚实施学生营养餐的试点项目,以期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等
 独联体其他国家推广。试点项目所需食品计划先由俄罗斯政府采购,之后再在地方市场采购,这样将保证该项目的自给性和可操作性。
独联体其他国家推广。试点项目所需食品计划先由俄罗斯政府采购,之后再在地方市场采购,这样将保证该项目的自给性和可操作性。
htp://www.odi. org. uk/resources/download/234. Pdf。
http: //www. prime-tass. ru/news/0/% 7B3A679320-5960-468C-808B-F8552B984EE7% 7D. 24.04. 2009。
俄罗斯大量的粮食援助(尤其是在发生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情况时),都是应各不同国家的请求在双边基础上提供的,这项工作同时也属于俄罗斯和国际粮食援助计划的常规活动。俄罗斯参与2008年5月获批的世界银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项目是对伙伴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例证。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稳定的应对危机政策,来降低粮价急剧上涨的不良后果,创造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率,发挥农业市场的作用。l 500万美元的资金由俄罗斯粮食危机快速应对信托基金拨付,2009年和2010年塔吉克斯坦通过该基金获得625万美元,拨付给吉尔吉斯的680万美元正在审核中。
俄罗斯政府正在致力于建立欧亚农业政策检测和分析中心以促进农业发展。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领域的活动中俄罗斯具有提供食品援助的优势,因为该国有大量的粮食和加工食品储备。在农业方面积极的援助计划(包括双边援助计划)不仅能使受援国粮食安全得到稳定的保障,还能够提高俄罗斯技术和机械制造产品的出口量,这可能成为制定农业领域国际合作项目时被考虑的因素。
8. 提供援助的地域
俄罗斯援助的地域很广,涵盖91个国家,并且运用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各种渠道。同时,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援助效率,援助构想中将受援国进行分组,确定优先援助对象,首先是与俄罗斯接壤的统一经济空间成员国、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以及独联体国家。文件中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视为急需国际援助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实施的地区发展援助项目为数不多,在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实施大型援助项目①。

①www. worldbank. org /financialcrisis/pdf/WBGResponse-VFF. pdf24. 03. 2009。
在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构想中有如此表述:地球上最穷的非洲国家未来会进入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对投资和投资性商品会有大量需求。那里有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将成为俄罗斯企业的原料供应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至关重要。鉴于非洲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必须落实以下重点工作:①积极利用贸易特惠制度和财政、技术援助(国际发展援助),在该地区推广俄罗斯的产品和投资;②扩大教育服务的出口,加强人才培养的技术协作;③同非洲的地区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包括非洲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同盟及其他组织②。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努力,俄罗斯初步建立起本国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2014年俄罗斯即将再次出任“八国集团”主席国,2015年将举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峰会,为此俄罗斯政府势必会努力完善该体系,扩大国际影响。有俄罗斯专家建议政府密切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采取措施切实落实俄罗斯2011-2015年的国际发展援助构想,以顺利实施俄罗斯国际援助及相关的国家战略。
(编译者:宋艳梅 董红婷)

① http: //www. mgdf. ru/files/New _ Africa _ Partners _ 072408-final. pdf21. 07. 20080
② http: //government, consultant, ru/doc. asp? ID= 49135。
加纳乡镇企业计划
——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
乡镇企业计划(REP)旨在减少贫困,减缓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为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做贡献。该计划也旨在解决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领域存在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低下,收入较低和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该计划希望通过转让技术解决这些方面的不足,从而改善技术及生产率水平较低的状况,并帮助改变目前受益者收入水平偏低的状况。
该计划的目标受益者是一些具备“创业精神的贫困个体”,其定义为一些拥有经商潜质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果他们获得该项目干预的资助,有望发展成为个体经营户或微型企业。根据该计划,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失业和半失业的年轻人,以及大学毕业的实习生都是目标群体。该项目的支持将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企业发展服务,技术推广和支持学徒工培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渠道,扶持小微企业组织发展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乡镇企业计划已成功地在两个阶段付诸实施:第一阶段是从1995-2002年,获得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的930万美元资助;第二阶段是在2003-2012年实施,获得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850万美元)和非洲发展银行(650万美元)的共同融资支持。迄今为止,该计划已在加纳全国的66个地区实施。
(1)改善民生和增加家庭收入。该计划已改变了受益地区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他们以往基本上依赖农业维持生活。该计划还通过积极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对提高贫困农民、辍学青年和妇女的收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实地调查的评估表明,在参与实地调查的340个项目受益者中,280人提到该计划已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加入乡镇企业计划之前,他们每月的收人为455加纳塞地(合255.62美元)。而在获得乡镇企业计划资助后,目前受益者的月收入已增加至755加纳塞地(合424.16美元)。
来自实地调查的证据也显示,该计划也为家庭层面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大部分受援者(86%)表示,该计划已通过创造收入提升了他们获取健康食品的渠道。据62%的援助对象反映,这有助于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
Isahaku Saluh是一位“接受过乡镇企业计划培训”的自豪者,丹布鲁肥皂企业(Down Blow Soap-Buipe)的首席执行官。Isahaku Saluh由于经济困难,在上中学后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他曾担任商店服务员工作5年。在2008年,Isahku参加了乡镇企业计划下属的制作肥皂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技能培训。此后,他经营一家肥皂生产企业,并已接受小企业管理、发蜡和头发护理产品等方面的培训。
“……我照顾我叔叔家的几个孩子。目前一个孩子是培训教师,其他两个孩子在上高中。我希望真主赐予我力量以资助这两个孩子上大学。我已经将他们3人全部在全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登记注册,因此当他们生病时,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正在盖一所房子,可以自信地说,大部分所需的原材料都已经购置,包括袋装水泥,钢筋和屋顶薄钢板等。我已经开始养牛,目前有8头牛。我现在收了两个学徒工。”
(2)促进技巧转移和技术开发。该计划也通过技术技能培训和示范,资助技术推广和支持学徒培训。 加纳共建成21座农村科技中心,通过培训工艺大师,来自技术学院及大专院校的学徒和工业辅助员工,促进农村技术转让。根据该计划,共有4 393名工艺大师和17 538名学徒工接受了培训。总之,102 000人接受了各类基于社区的技能训练模块的培训。除了已经由乡镇企业计划安排工作的受训学员外,很多人已凭借他们的毕业证书在外地找到正式的工作岗位。
Isaac Kojo Antwi,Twifi Praso地区一名接受乡镇企业计划援助的残障人士。“在乡镇企业计划给予我援助之前,我从事小规模的家禽养殖。但由于在我开始饲养家禽之前就实际上已经被支付了报酬,饲养家禽的收入非常微薄。尽管目前我的收入很少,但我不得不继续做下去,只是想让人知道我并不是个没用的人。”
“乡镇企业计划培训我从事皮革工作,并给我设备支持以创立自己的企业。目前,我生产的皮鞋和腰带已经畅销,甚至销往外地。我在靠近Twifo Praso地区的帕索(Paaso)拥有一座6英亩①的油棕榈树农场,我目前在争取获得海岸角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Coast)的远程教育课程文凭,这将促使我获颁管理和商业学位证书。该计划的确已经表明,残障人士可借助适当的扶持来取得成功。
① 英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I英亩=4 046. 856平方米。——编者注
(3)创造就业。乡镇企业计划的社会技能发展模式已经为以下领域的中小企业(SME)提供技能培训:农产品加工,如鲜果汁和棕榈油加工;食用菌栽培,蜜蜂养殖和养鱼等。根据该计划,共有35 742名个人接受了不同的中小企业活动培训。这些培训以促成了总共新创设24 052家中小企业。培训的示范带动效应和创立的中小企业已创造了54 683个就业岗位。
Zaliatu Ibrahim女士在2007年参加了制作肥皂的BAC培训项目。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女缝纫工。Zaliatu于2007年开始生产肥皂。最初,她每周生产两箱条状肥皂;目前Zaliatu手下拥有4名兼职员工,每月生产260块条状肥皂,400瓶液体肥皂和360箱各类小块肥皂;她平均每月可赚到280美元。
Zaliatu已经能够给她的家庭和整个社区的很多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她已经成为Obogu社区内妇女和年轻人的致富模范人物。在她服装制作企业工作的5名学徒工也全部成为肥皂生产的培训学员。她已经有能力资助弟弟接受高中教育,与此同时让两个妹妹上初中。Zaliatu目前整理基本的商业交易记录,并能够计算出自己的盈亏状况。
自从Zaliatu开始生产起;她已经创造了20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0个经她培训的员工目前已开始生产肥皂。此外,她的成功创业已增加了本地区15个肥皂零售商的收入水平。
(4)改善信贷获取渠道。6 900个已注册成立企业和参与BAC的项目受援者已能够获得信贷支持。600位私人金融机构(PFI)专家已接受基础管理培训,以支持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5)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该计划已通过聚焦于妇女和弱势群体,62%的该计划受益者是妇女,从而巩固了非洲开发银行作为最可信赖的中小企业发展伙伴之一的形象。该项目已培训各类妇女团体从事生产润发油、洗衣粉、漂白剂、肥皂以及养殖藤鼠。据妇女们介绍,目前她们也能够为各自社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位于Sissala West地区Gwollu的妇女Alhassan Mamuna表示:“在实施乡镇企业计划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妇女在当地社区并没有像样的谋生方式。大多数妇女的收入来源收集木柴然后出售。但由于本社区剩余的木柴很少,我们不得不步行到野外打柴。这不仅是个苦差事,而且我们辛苦努力但赚到的钱屈指可数。现在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我们已拥有别的谋生方式,不再拾柴出售了。”
1. 在Fanteakwa地区Dorminase和Otuarter连片社区的妇女团体
这些妇女团体接受了生产润发油、洗衣粉、漂白剂、肥皂以及养殖藤鼠的培训。总计有72名妇女已接受两个成片社区内两家机构的培训。在培训闭幕式上,地区议会的工作人员、各社区的酋长和广大民众都踊跃出席。
这些受益者已组成团体,他们在创立自己的企业后,很快开始生产并在短期内实现盈利。一个妇女团体起步资金只有大约320加纳塞地,经过3个月的经营运作,她们的运营资金已增加至705加纳塞地。
其中一位妇女Salomey Tetteh说,“这些技能培训是拯救生命的干预行动。在当地没人可以看不起我了,因为现在我享受到高度的尊重。我现在可支付家里孩子们的学费,而不用等到我丈夫收获一些农场的木薯或芭蕉来卖钱。”
这位妇女表示,她们现在也能为各自社区的发展作贡献。她们目前在筹划购置机械化的肥皂制作机器,以提升生产水平。 促进结成伙伴关系以改变现状:乡镇企业计划的实施也已促进了加纳政府机构内部和外部多家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政府机构如共同实施该计划的地区议会等。该计划已发展了与中小企业扶持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如加纳全国小规模企业理事会,GRATIS基金会,ARB Apex银行有限公司和多家金融机构等。该计划通过创造不同机构的认识机会和相互交流,也形成了各类非政府组织(NGO)的伙伴关系和协同效应。加纳反饥饿计划(THP)为培训活动提供了20%~30%的对等资金。其他中小企业援助机构包括卫理公会发展和救济社(MDRS),国际关怀组织加纳分会,根茎和块茎改良及营销计划(RTIMP)等。
2. 面临的诸多挑战和约束
乡镇企业计划的第二阶段起步进展缓慢,主要受制于以下多个因素:①执行机构和监督部委的调整;②该计划分支机构的重新安置;③招聘国家级专家的步伐缓慢和采购领域面临诸多考验;④3个负责协调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制度安排面临诸多挑战;⑤领取贷款的规模较小,因私人金融机构对项目客户的敏感性不足,且部分农村私人金融机构无法达到加纳央行设定的认证标准。
3. 前景
总之,该计划已表明,技能提升通过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和企业,能为提高加纳民众的生活水平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加纳政府的要求和早期乡镇企业计划取得的成果,该计划的第三阶段目前正在规划中。第三阶段料将扩展到加纳全国的其他84个地区,配以基于地区的小微企业支持系统作为全国公营和私营机构体系的主体,以增强公共部门一私营企业间的合作关系(PPP)。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
(编译者:毛小菁 姚帅)
坦桑尼亚2000-2010年的
农业增长与减贫:农业为穷人
服务的路径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O.Mashindano K.Kayunze L.da Corta F.Maro
一、 引 言
(一)农业增长和减贫
1. 农业增长的路径
农业一直是坦桑尼亚最大的经济部门,它包括了种植业、养殖业、狩猎和收集、渔业和林业。在2010年,农业贡献了大约28%的GDP份额以及24%的出口收入(Msambichaka等,2009)。在近10年内,农作物出口收入在总的外汇收入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从2000年的34%下降到2007年的不足20%。虽然农业的绝对份额一直在增长,但是由于其他经济部门如旅游业和采矿业的兴起,农业的相对份额在下降。
在1998-2009年,农业部门每年的总体增长率在0.8% (1998)~5.9%(2004)波动(图1)。而GDP每年的增长率在4.1%(1998)~7.8%(2004)波动。不管是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相比,还是与GDP的增长率相比,农业的增长都显得缓慢:1998-2009年,农业的平均增长率为4%,工业和服务业平均增长率为8.3%和7%,GDP平均增长率为6.4%。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说明了过去10多年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不是亲贫式增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农业支持着超过70%的人口,而农业相对于其他部门增长缓慢。

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种增长模式,发现GDP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的。而农业的年增长率在过去的10年内一直处于停滞的状况,并且是持续的低水平和生产率的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化肥和优良种子的使用率低,农业机械化投入不足,灌溉水资源短缺,农业推广、科研、技术和农业相关的教育培训覆盖面窄,政府农业部门的投入预算低以及市场基础设施的低水平。
2. 农业部门的分解
从规模上来讲,农业仍然是坦桑尼亚的GDP增长、就业和创汇的主导部门。表1说明种植业在这12年期间甚至更长时期一直占据农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平均贡献为70%左右;养殖业和林业(包括狩猎)次之,平均贡献分别为16%和8%;渔业的平均贡献为5%。
表1 1998-2009年,农业部门的分解
单位:%
尽管占GDP份额21%的种植业一直在农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贫困举措(自从1961年独立后立即实施),但是农村的贫困现象仍然普遍存在(NBS,2007)。有学者认为跨境贸易的管制抑制了市场的发展,进而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Baregu和Hoogeveen,2009)。在减贫计划(PRSs)实施的初期,GDP增长趋势很明显,但是这种增长不是亲贫式增长,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以农业为生。农民家庭收入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的降低要远低于城镇地区。
(二)研究目标、背景和方法论
1. 研究地点
在坦桑尼亚大陆3个地区的6个地点开展研究。这些地点是从坦桑尼亚ECHO 处于关闭状态。2007年家庭预算调查(HBS)中447个抽查地点中选取的(NBS,2009)。这些抽查地点能够反映坦桑尼亚不同的地区、农业生态区和农业生计方式,而且在这些抽查地点贫困的发生率相当高。
2. 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是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执行,采用的是传统的双Q(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Davis和Baulch,2009)。坦桑尼亚HBS2007调查和最近开始的NPS调查是这项研究的起点。在这两项调查的基础上,为了收集这6个研究地点的定性资料,研究团队还设计了一整套方法,包括焦点小组访谈法、生活史访谈以及关键人物访谈。
(1)焦点小组访谈法。在每个抽样调查地点,研究团队试图组织4个焦点小组访谈。第一个焦点小组访谈对象是当地有见识的人,让他们自己绘制一个社区时间表,识别出社区内的主要习俗和惯例、主要生计来源并对生计来源进行排序以及理解主要资产、工资和价格的价值。
第二个焦点小组访谈对象是妇女,第三个访谈对象是男人(反之亦然),组成“贫富排序小组”。由社区领导者选出参与者,要求这些参与者在横截面上能够代表整个社区。这个贫富排序小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人开发一套研究地点的贫富分类体系——将农户福利水平分为6级,从1级的赤贫到6级的富裕。排序时要考虑到以下因素:农户的资产、收入、消费水平和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当保留当地相关性时能够在不同抽查地点运行;抓住不同抽查地点贫困线附近人的明显差别;抓住赤贫农户具体独特的经历。第二部分人分别对24户1999-2009年HBS抽样农户进行贫富排序,然后识别出他们福利状况改善、恶化或者不变的原因。我们希望借此对每个研究地点的社会经济动态变化有个大致的了解。在这6个抽查地点,我们对24户家庭进行了8组(男性4组,女性4组)贫富排序,总共有144个排序结果(理论上来说应该是192个,但是有2组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排序的)。
第四个焦点小组访谈内容是确认主要的结论,探究突出的问题,向社区反馈我们初步的分析结果。
(2)生活史访谈。通过106例生活史访谈来深入了解被访谈者的生活,探究他们福利水平变化的原因。基于贫富排序的发现,研究团队从24户HBS抽样农户中挑出10户左右来进行生活史访谈。这10户生活史样本要求能反映出福利水平变好、变坏和不变这三种趋势和确保受访者年龄分布合理。访谈针对每个家庭内的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在每个访谈的结尾部分,将受访者的生活轨迹史描绘在坐标轴中,通过6级贫富分类体系(y轴)反映福利水平在时间维度(x轴)上的变化。
(3)关键人物访谈。关键人物访谈是要深度挖掘某一特定研究主题。看情形选择受访者,主要是焦点小组访谈和生活史访谈里争论比较突出的问题。关键人物访谈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社区领导者、农作物贸易商、债主、农业推广人员、教师和医疗卫生工作者。
基于以上准则,我们选择了坦桑尼亚大陆以下几个抽样调查地点:Nchin-ga(姆万扎区)、Nkangala(姆特瓦拉区)、Ndite(姆万扎区)、Wazabanga(姆万扎区)、Kayumbe(鲁夸区)以及Kalesa(鲁夸区)。表2简要说明了选点缘由。
表2抽查地点选择的理由
(三)文章的结构
本文从第二章开始对GDP和农业增长进行分解,审视农业是否有增长以及增长以何种路径转化为减贫?值得一提的是,关注了农业增长是否存在一个较短的迅速提升时期,以及显著下降的传统农作物出口是否被少量增加的非传统作物出口所代替。在第三章,通过从6个研究地点取证为什么农业增长幅度不大,我们注意到了产量和市场的限制性作用。第四章主要关注了新的制度安排对于农业转型的影响,比如说仓储和信贷政策。除此以外,我们突出了农业在哪些贫困地区起到作用以及原因。我们发现正是新技术、可靠的市场、混合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多样化)以及稳定的制度综合高效运作使得贫困地区出现了增长。我们随后探讨了如何进行制度和政策改革以进一步巩固增长。第六章是结论和相关建议。
二、 农业增长及其减贫转化路径分解
坦桑尼亚约74%的人的收入和生计是从农业中获得。然而农业部门持续低增长,以至于不能实现明显减贫和提高大多数人生计和生活标准。而在一些地区农业出现适度增长,这种增长可以从一系列指标反映出来,如贸易机会(跨境贸易网点)、牲畜产量、仓单计划、非传统出口的表现、农业相关技术变化、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产量以及播种面积的变化。然而,这种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贫困的减少和生计的改善。本章试图分解农业部门内部的增长,审视农业增长的主要转化路径来证实农业增长在改善生计方面的有效性。
图2和图3显示了坦桑尼亚传统和非传统产品出口变化趋势,主要关注两个时间周期:图2关注的是2000-2008年,图3关注的是2007-2010年。在2001-2008年,出口在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业出口,以年均38%的速度增长。
非传统产品出口总的以年均21.8%的速度增长。当非传统产品出口成为最大份额总出口(80%)时,它的增长速度明显影响到总出口(年均增长20.8%)。而传统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最慢,约为13%。

同样,在2007-2010年,非传统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83%~85%,明显高于传统产品出口。截至2010年3月,非传统产品出口同比从21.812亿美元增加至24.191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传统产品出口表现相对欠佳导致了主要经济作物出口增长乏力。几乎所有传统作物出口的增长波动都很厉害,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比如说棉花和咖啡的出口仍然没有走出最近全球冲击的影响。

1. 鲜切花产业
非传统产品针对出口市场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成立鲜切花产业和芒果种植者协会。坦桑尼亚北部地区大部分大型公司都从事花卉出口产业,特别是阿鲁沙区和乞力马加罗区。而南部高原(伊林加区的Njombe和Mufindi县)鲜切花产业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主要生产出口玫瑰花。甚至在达累斯萨拉姆区(Kigamboni区域)也有一些鲜花产业投资者。据估计,在2005-2006年出口到异地的鲜花量为5 862吨,在2006-2007年这一数量增加到6 897吨,同时种植面积也达到了137公顷。鲜切花产业为青年男女熟练工和非熟练工提供了就业机会,除了提供月薪以外,还提供不断增加的工作保障和员工附加福利。如果鲜切花产业的挑战得到解决的话,鲜切花产业是增长转化为减贫的一个路径。
经验表明在面对出口市场时富裕的农户比贫穷的小农从园艺产品中获利更多。当生产线的性质和条件性别化后,不仅对产业造成影响,而且对男性、女性以及他们家庭的生计和福利造成影响(Kessy,2004)。Kessy发现产业内的劳动力女性化以后,使得女性员工比男性多。并且不同性别劳动力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工——女性从事收割、分级和包装工作,而男性从事喷雾、灌溉和一些体力活,如花房的修建和维修。这种职业分化导致了工资差异:女性集中于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类别。其他方面的挑战主要涉及福利方面的问题,包括生产工具的缺乏,工作时间长却没有加班费以及大量的使用化学物质对员工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
2. 芒果种植者协会
坦桑尼亚的芒果种植者协会(AMAGRO)成立于2001年,旨在共同寻找有效种植水果以及实现盈利的知识和技能,以获得出口市场的机遇。具体来说,这个协会成立主要有3个目的:培训会员最优种植芒果的办法;提供便利可获取的农业投入服务和其他服务,例如农业推广;加强联合销售以提高农民讨价还价能力。AMAGRO在提高农民生产效率和减贫方面确实起到模范作用。它不仅为坦桑尼亚80个不同地区的芒果种植者提供直接帮助,而且为那些不是会员的农民带来正的外部效应。
协会会员现在比以前拥有更好的种植芒果技术知识,可以达到国际标准要求;能够获得那些对于个体种植者太昂贵而不能进口的农业投入①;拥有更好的加工处理芒果及生产相关副产品方面的知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此感受到生产率和收入的改善。使用现代技术后,1个农民在1英亩土地上能够种植多达64棵芒果树,每棵树至少能结300个熟芒果,1个芒果至少能卖到250坦桑尼亚先令,这意味着一个农民每英亩地每年能够获得差不多4.5百万先令的收入(每棵芒果树获得75 000先令收入)。而1英亩的芒果树的生产成本(从种植到收获期间所有的开支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投入)最多为300 000先令。因此,1英亩芒果的净利润至少为4.5百万先令——平均月薪甚至高于绝大多数拥有硕士学位的政府官
员。而且通过加入AMA-GRO,农民每英亩收获的芒果数量要比之前没有相关技术和投入的条件下翻上一倍。
3. 非传统出口
非传统出口产品主要有9种:黄金、制成品、鱼和鱼类产品、蔬菜、油料种子、园艺作物、复出口货物、其他矿物质以及其他出口货物(图4)。在Magu、Nkasi和Newala 3个被研究地区,除贸易和做小生意,作物种植,捕鱼和牲畜养殖是主要的创收活动。传统出口包括Newala(姆特瓦拉区)的腰果和芝麻、Magu(姆万扎区)的棉花。非传统出口包括Magu和Nkasi的稻谷、鱼、蔬菜和其他园艺作物(三地都有)。在3个被研究地区都有边境贸易存在,Newala的外境市场是莫桑比克;Nkasi的外境市场是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卢旺达和苏丹;Magu的外境市场是肯尼亚。Kalesa村(鲁夸区Nkasi县)有90%左右的商人在坦噶尼喀湖沿岸交易,他们大多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赞比亚。剩下10%的商人在Mwandima (Nakasi县一行政区)、Makazi(Nkasi县首府)和松巴万加(鲁夸区首府)之间往来交易。
大部分的杀虫剂在出口国是通过大量(如50升)而折价销售的,对于单个农民来说太贵,难以负担得起。正常情况下农民只需要很小剂量(0.5升),而AMAGRO以协会组织大量购买,然后以小剂量卖给会员而不增加任何其他费用。

如上所述,尽管一些作物特别是传统作物的出口在下降,但是非传统作物在过去的10年内出口却有所增加。那些表现比较好的非传统出口作物有稻谷、西红柿、玉米、木薯和油料种子(落花生和芝麻),以及其他一些香料调味品(香草、豆蔻、辣椒、花椒和生姜),还有一些园艺和花卉产品。大部分的非传统作物是由穷人种植的,而花卉、水果、香料调味品和豌豆是由富人种植,主要是为了出口。
因此,在鲁夸区和姆万扎区,非传统出口对生产者出口创收方面的重要作用十分明显。据焦点小组访谈(FGDs)的结果,在以上两个地区,贸易是增长转化为减贫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途径。但是这一过程受到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
(1) Kalesa村私营贸易商提供的价格不合理,因为他们不反映市场价格。而且这些私营贸易商为己利擅自压价,制定价格,让消费者毫无选择余地。
(2)渔业是Kalesa村的第二大经济产业,渔业贸易特别是活鲜鱼贸易赚钱多。与作物不同,鱼产品是被运送到Kayumbe和首府松巴万加。然而,由于在鱼产品保鲜储藏方面缺乏适宜技术,贸易商们只能采用原始的储藏技术和设备,这种储藏技术和设备效率低下尤其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3)由于得不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农民们不愿通过跨境贸易出售农产品,这样就导致了他们不能获得境外市场更高价格带来的利润。例如在布隆迪市场提供的价格高于当地市场价,据说是由于它与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其他市场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4)通过小型、简陋和劣质的船只穿过坦噶尼喀湖到达布隆迪和赞比亚市场危险性很大,尤其是当湖面浪很大的时候。
(5)正如上面指出的,鲁夸区Nkasi和邻国布隆迪、卢旺达、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商大多为外国人。本地人没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这一挑战和抓住这个机会。
(6)据焦点小组访谈结果,在姆万扎区Magu县农业表现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气候条件差,而且农业投入方面的限制和市场出路的匮乏:他们不允许卖到Magu县以外的地区,也不允许跨境与肯尼亚进行贸易。这样,农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为制造的障碍和控制的影响。而在过去牲畜养殖人员在Magu县和肯尼亚之间往来交易很容易,因为Magu县处在两国贸易和市场上的战略位置上。
(7)对于出口总体表现不佳,政府主张通过从事非农活动和提高非传统出口作物的生产,以实现农业多样化。尽管非传统作物的扩大种植能够提高一部分农民收入,但是从事非农活动这一农业多样化方式并没有成功解决农业部门面临的问题,因为它需要向农民传授组织和企业方面的技能,这样的话从事非农活动才能成为农民切实可靠的生计来源。
三、 农业收入增长的障碍
农业在这3个研究地点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这种增长不足以达到显著减贫、改善农民生计和生活标准要求。农业增长的长期停滞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在这一部分我们回顾了研究地点资料分析所呈现的阻碍因素,这种因素同样是农业收入增长和农业部门转型制度设计的障碍。
(一)农业市场结构和定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的可及性以及对生产者来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能够将增长转化为减贫。AMAGRO、鲜切花产业以及仓单计划就是提倡改良的市场和定价体系方面的典型案例,因此,它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随后发生的产量和播种面积的变化说明了这3个研究地点的农业部门都有了适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与减贫和生计变化无关(专栏1)。
根据焦点小组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造成这种失衡现象有以下一系列原因:这种市场导致了当地农民与外部(区域出口)市场脱钩,农民不能获得具有吸引力的生产价格;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了真实生产价格持续低水平;由于少数的商人故意压价,最低限度支付当地农民,窃取了农民创造的财富。这些商人通过异地倒卖获得丰厚的利润。 除此之外,当农作物获得大丰收时,巨大的库存使他们找不到销路;而当农作物歉收时,饥荒发生了。农民们抱怨商人们收购行为没有规律,收购时短斤少两而且脾气暴躁,人为压价以及对农民的投入贷款征收重息。囊中羞涩的农民们被迫在丰收的季节抛售所有的产出,放弃晚些时候价格上涨所获得的利润。这些都是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包括鲁夸、姆万扎和姆特瓦拉)农业收入增长的典型阻碍因素。
专栏2是Newala地区一个焦点访谈小组关于2009年和1999年的经济表现和生活标准比较的回应。社区成员现在面临的经济压力要比10年前更为困难。他们反复重申两点原因:一个是通货膨胀因素,在2009年通胀率为12.1%,而且现在也一直保持在8%的水平;另外一个是现存的市场结构对生产价格的压制。
如果农业增长的障碍能够得到解决(这样的话农民的生计就能得到改善),农村社区的贫困现象能够得到大幅度减少。确实如此,因为社区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的贫困收入弹性(如平均收入增长)相比其他职业要高(-2.13),比如政府雇员(-0.90),有雇员的自谋职业者(-1.16),无雇员的自谋职业者(-1.37)(表3)。
表3按照职业分组的全体人口的贫困平均收入增长弹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同时,农村居民的贫困收入(平均收入增长)弹性要高于城镇居民(表4)。
表4按地理区位分组的全体人口贫困平均收入增长弹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
仓单计划必须尽可能进行改革完善,推广到其他作物上以及边远的农村地区。因为在农村地区生产价格持续低水平,而且当地农民或市场与外部市场普遍处于脱钩和断裂状态。私人交易商通过限制农民获得市场信息而组成卡特尔组织严重阻碍了小农进入外部市场。仓单计划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使农民直接与外部市场对接,消除被外部市场孤立的情形。
在城市地区,由于基本需求成本的上涨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尤为明显,原因在于城镇居民更加依赖于就业市场,而且城市地区的物价水平高于农村地区。姆特瓦拉地区Newala县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在邻村一头母牛的价格大概在100 000先令左右,但是在Nchinga村却要花费500 000先令。此外,在Newala的城郊地区人们往往需要支付租金,这也减少了他们可购买的食品量。
(二)生产性资产的获得:土地、牲畜和捕鱼装备
生产性资产的拥有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个加剧了大部分以农业为生计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因此,生产性资产分配和拥有的不公成为农业收入增长和农户生计改善的障碍。
在被研究地区,与土地、牲畜和捕鱼装备(船只、网和着陆场)相关的这些问题尤为明显。表5所示的贫困指数说明了社区(大部分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渔民的贫困现象比起其他职业居民更为严重,这一部分群体需要优先进行发展干预。
表5按职业分组的贫困指数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
土地资源匮乏和冲突同样导致了农业低增长,进而扰乱了减贫举措。在鲁夸区Kalesa和姆万扎区确有其事。在Kalesa,当Suku ma人(牧民)带着大量的牛群从坦桑尼亚北部迁移过来时,冲突开始发生。Sukuma人占据了土地,并且开始从土著Fipa人手里购买更多的土地。据说他们之所以囤积大量耕地的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公牛来耕种一部分地而且剩下的土地可以用来放牧。现在,土地十分稀缺和昂贵:租用1英亩土地1季需要花费100 000先令。囤积土地的行为十分普遍,地主们正在经营的是一桩大买卖。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敌对的气氛越来越浓(专栏3)。
土地的稀缺是人为造成的,由于害怕失去土地,地主们有时都不愿意将其租出,因为那些人可能租人或借进土地一季,然后在租借期限快要到的时候隐瞒地主将土地卖给陌生买家。
牲畜集中在那些从坦桑尼亚北部迁移过来的牧民手中,饲养牲畜更多时候是与文化有关而非经济方面。在过去,尽管大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大部分家庭也都有大量的牛存栏(同样也有山羊和绵羊),在20~200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原因造成了许多家庭放弃了养牛,这些原因包括气候的反复无常、偷牛和走私牛。例如姆万扎地区的农民生活史表明过去许多家庭拥有巨大的牛存栏量,然而人们的识字率却很低并且整体生活水平非常贫穷。纵然他们拥有很多母牛,但是这个不能给他们带来金钱:他们之所以不卖牛奶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失去部分牛。他们不为消费去屠宰任何动物。当他们年老死后,剩下的母牛会分给家庭子女,这样牲畜存栏量便慢慢减少以至消失。
渔业既是鲁夸区Kalesa村又是整个姆万扎地区一项重要的生计来源,大多数人以此为生,或为鱼商或为渔夫。然而,这个产业却被少数相对富裕的人控制着,这些人拥有大笔的生意以及昂贵的现代化打捞装置。其他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些小生意人和劳工。在Kalesa村,安置一套完整的打捞装置(渔网、独木舟、机器等)平均花费100万先令左右。
土地稀缺、无力购买肥沃的土地、土地租赁障碍、牲畜数量减少以及捕鱼装置和商业资本的缺乏影响着被研究地区人们的福利和生计。生产性资产分配和所有权偏向少数富人,他们将其他人视为自己的劳动力和市场。
6个调研村庄41个生活史访谈反馈显示:在大部分被研究地区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倾向于少数人,他们大多是外来者。例如在41个生活史访谈中,2人拥有了49头牛中的40头(82%),39人拥有9头牛(18%)(表6)。同样的,1人拥有了121英亩土地中的100英亩(83%),剩下的40人仅仅拥有21英亩土地(17%)。这2个40头牛和1个100英亩土地拥有者不是本地人。很明显,这除了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因素外,生产性资料和(或)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冲突产生的潜在因素之一。
表6生产性资产的获得(土地和牲畜)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
同时,研究发现极度贫困的人仅仅拥有一小部分资产(图5)。在2001年,城市和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人分别仅仅拥有21%和19%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2006年数值分别为16%和27%,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在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和食品安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从过剩区运输食品到短缺区时。实地调研资料显示样本地区的交通运输网高度不发达。撇开水路运输(姆万扎区的维多利亚湖和鲁夸区的坦噶尼喀湖)来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的公路网非常有限,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季节性的公路。
尽管新建公路方面有一些明显的发展,但是产地因以上原因和市场联系不足。公路网在连接城乡经济和促进边境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姆万扎区,城镇受访者反映,在1982年姆万扎到塔里梅(Tarime)之间主干道修建完成之前,他们农产品的市场销路极其有限。当这条路修建完毕,他们能够穿过位于Silali的国界线到达肯尼亚的市场。据一些关键人物访谈所言,跨境贸易刺激了农业企业的发展以及帮助人们脱离贫困。同时,跨境贸易的价格引诱刺激了水稻种植量的增加,许多农民重新分配自己的资源,由种植棉花转向水稻。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棉花市场价格的下降,进一步扩大了稻谷的产量。然而在食品短缺的时候,跨境贸易量受到短期的粮食作物出口禁令的影响。从Kayumbe到鲁夸区中心城市松巴万加之间的主干道是另外一条连接生产者和其他商业城市交易商的重要线路。农民们能够将他们的玉米运到关键性的粮食采购点,同时中间商也能够从那些负担不起运输费用的农民那里买到农作物。
姆特瓦拉的Newala地区和邻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非农产品。贸易的商品包括织物(Batik和Kitenge)、电器、房屋封顶的铁皮、石油油料、杜松子酒和糖片(从莫桑比克到Newala);以及腰果、玉米、二手衣服、床垫、沙丁鱼和一种本地生产被用来制作烈酒的腰果梨Kochoka(从Newala到莫桑比克)。然而,关键人物访谈揭示了出口莫桑比克的城镇农民不太多: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尚且不够完善,特别是穿越Ruvuma河的水运设施(专栏4)。据估计大约有10%的Newala地区村庄的商人从事边境贸易。
市场结构不发达而且管理混乱。特设委员会的搬迁是一些城市地区农业综合经营商不断向下面流动的主要原因。在姆万扎Ndite村,受访者抱怨说地区直辖市频繁搬迁中心市场扰乱了他们的经营业绩。(四)性别不平等
性别分析对于理解坦桑尼亚经济增长和减贫关系起着重要作用①。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女性承担越来越多原本被认为是男性应该负责的工作。这些原因包括:男性外出务工、离
 婚、被男性遗弃、全职照顾家人、由于艾滋病和慢性病造成的守寡
婚、被男性遗弃、全职照顾家人、由于艾滋病和慢性病造成的守寡
①参见如 Boserup (1970),Sender 和 Smith (1990),Kessy (2004,2007).
以及酗酒造成男性大量的缺席岗位。女性承担的男性责任如农事工作(农耕和劳力)以及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家庭贫困和代际贫困管理。
当女性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承担越来越多男性部分的责任时,同时她们维持家庭所面临的现金成本也在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包括食品价格(营养需求和/或高质量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如医疗、卫生、教育和饮用水方面的通货膨胀。这个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能造成代际贫困(子女体质、认知和教育能力的损失)的深刻影响。
然而,由于肥沃的土地十分短缺,再加上女性独自肩负起创收的重任,她们通过务农来满足家庭开支时已经力不从心。家庭每个后代继承的土地规模在不断减少而且维护肥沃土地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对于那些由于丈夫去世而丧失婚姻资产拥有权的女性,这种短缺十分普遍。尽管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但是那些离婚和被抛弃的女性却丧失拥有耕地、家庭和其他资产的权利,而且他们还得继续全职赡养子女和老人(表7)。
表7按婚姻状况分组的贫困指数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
表8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土地拥有的份额。女性大约只拥有男性一半的土地,这与女性在农业中的地位不相称,因此女性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紧密(图6),所以对于那些被遗弃和离婚的妇女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表7)。
表8按性别分组的贫困农户土地拥有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
官方对此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女性从事商业(贸易和小制造业)和为女性提供更优惠的贷款。但是,所有被研究地区的女性都面临启动商业活动所需资金的问题。即使她们成功获得资金支持的话,她们会发现女性在这种市场上已经人满为患了(比如鲁夸地区的番茄和鱼类商人;姆特瓦拉地区的甜甜圈和其他熟食、番茄和衣服商人)。此外,这种商业依赖于农民的购买力。当农民的收入降低时(由于价格很低或者产量不好,不管是多少年或者仅仅是一个季度),这种生意的市场同样不景气。例如在姆特瓦拉地区的Nkangala,由于1999-2006年腰果价格全球性下跌导致了当地鱼类、衣服和快餐商人纷纷面临商业倒闭的情形。

在鲁夸地区Kalesa,我们同样注意到单身女性从事贸易或者商业活动要比已婚女性自由。当已婚女性外出经商,丈夫们信不过他们的妻子。已经发生过女性借经商之名幽会别的男人。因此,大多数男性都不允许自己的妻子从事商业活动。这一原则和规定仅仅针对女性;妻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担心被认为是不正常。丈夫们因此非常自由,他们从事商业活动要远高于女性。不管怎样,与10年前相比,女性总体上来说更为自由,更有权力。她们参与贸易和商业活动的程度显而易见要比10年前更高。
(五)技术、支持服务和制度
坦桑尼亚第一个减贫计划(Mkukuta I)实施过后两年的国家农业抽样普查2002年和2003年显示:18%的小农使用改良过的种子;17%使用杀菌剂,12%使用有机肥料以及6%使用混合肥料。令人惊讶的是,74%的农户没有使用农家肥料,而66.7%的农家肥料是由当地生产的。大约有61%的牲畜饲养者距离兽医服务站15公里开外。
生活史访谈发现农户对农业投入用途方面的小知识掌握甚少。很多受访者认为是指经济作物的投入,其他的受访者仅限于关心化肥方面的问题。受访者透露农业低投入的诸多因素:化肥价格昂贵、缺乏相关意识、农资商店距离远以及对土地肥力的信任,尽管所有研究地点的受访者一致性反映农业产量和土壤肥力的下降。
在一群腰果种植户中有一个农业投人受益者,他使用了硫黄并且每棵树收获了8千克的腰果(别人每棵树收获不超过5千克)。如果按照推荐比例在腰果树上喷洒硫黄的话,据估计每棵树能收获多达10千克的腰果。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农民几乎没有提到有关农业投入代金券方面的问题。在同一个村庄内,有些农户收到了投入代金券,但是大部分农户没有。这意味着投入代金券计划没有告知所有的农民,它的分配可能需要区别对待。因此,收入代金券不足以及分配低效率。
我们发现在耕种0.5~5公顷的地块时,所有的受访者都是采用手锄耕种。这种生产工具既费时又费力,而且会导致收获量不足。这样的话生产仅能维系生存,没有多余的可卖。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改良的推广服务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大约只有15%的农户接受到畜牧业推广服务以及34%的农户接受到作物生产服务。同时,一名区农业官员指责农民将这种服务关系到政治方面,这导致了农民对推广服务的响应低(专栏5)。
因此,在所有的被研究地区农业是一种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手锄是主导性生产工具以及有限的改良种子和化肥使用。四、 农业部门的增长点
如上文所述,坦桑尼亚农业部门在有限的领域取得了适度的增长,而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经济作物价格变化、作物和农畜产品产量变化、作物种植面积变化等。当然,这些成就并未贡献于减贫和生计。
(一)仓单系统
仓单系统由自2007年的农业市场体系发展项目(AMSDP)引入,虽然也遭到部分农户的批评,在改善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生产力及其效率、增强农业生产者信心、稳定生产者价格和农业技术投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仓单系统是坦桑尼亚政府实现市场公平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鼓励农户使用仓储设施储存农产品,在市场价格升高之后再加以出售。这一体系通过农村初级组织(primary society)、农户协会及信贷合作社(SACCO)得以运作。初级组织先向农民支付产品价格的70%和其他红利(缓减农户支付来年生产资料和协会费用的压力),对农产品进行细致的称重和评级,向农户签发一式三联的收据。农户将农产品储存起来,几个月之后经由仓单管理系统进行拍卖,得到剩余30%的款项。这一过程降低了仓储、利息、运输和管理的成本而使农户受益。仓单体系旨在稳定生产者价格,向农户进行生产资料补贴和提供信贷(SACCO)而增加技术投入。
仓单系统提高了流动性,减少了大买家的反竞争行为,从而激励了市场竞争。在引入仓单系统之前,这些拥有银行金融渠道的大规模出口商和加工商占据着Mtwara、Lindi和沿海地区的大部分腰果市场。他们收买地方的私人贸易者(代理商或中间商),从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购买腰果。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出口商和加工商为数甚少,就有可能形成垄断。而地方贸易者之间也不有在竞争:他们只是这些大型企业的代理人,只为了赚取可观的佣金而已。因此,引入仓单系统:为农业部门带来了更多的银行资源(和流动性),使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能够获得独立的银行资金;迫使大规模的出口商和加工商无法直接从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购买腰果,而是只能参加拍卖,减少了它们的反竞争行为。
而这一系统对农户的作用又如何呢?来自腰果产区农业市场合作社组织和来自早稻产区信贷合作社组织的运作经验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工具,仓单系统能够通过设立市场终端、稳定及提高市场价格等方式,使农户得以受益。随着出口价格的上升,农场交货价格也有所上涨。例如,在Nchinga、Nkangala和Mtwara,在2007-2008年度引入仓单系统之后,农场交货价格从2000年的每千克250先令上涨到每千克800先令。在Tandahimba区,腰果的生产者价格从每千克150~410先令上涨到了每千克710~850先令(几乎翻倍),不但反映了生产者价格的上升,也表明价格波动得到了大幅度的抑制。
在Iringa和Mbeya地区,仓单系统是通过信贷合作社运作的。仓库从农户那里购买早稻,先预支他们50%的市场价格。在收获季节,旱稻的平均价格大约是每100千克50 000先令。这样,农户会通过信贷合作社得到每100千克25 000先令的首付款。随后,储存的旱稻被仓库管理者以75 000先令的平均价格(反季价格)出售。支付给农户的第二批款项会扣除贷款、生产资料成本和利息,这样农户大约能够获得每100千克60 000先令的总收入,也就是每千克600先令。由此,农户能够承担市场成本、生产资料投入,获得稳定的相对高价。
当然,仓单系统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户不喜欢分两期付款的形式,更倾向于在收获时拿到100%的价格,来支付劳动力成本、学费和其他必需品开支。可见仓单系统的运作不能“一刀切”,可以为部分农户保留其他的选项。还有一些农户希望在定价和拍卖中争取更多的代表性,呼吁审计、内部控制和透明度,并要求获得更多关于支付二期款项和红利的时间信息。对农户访谈时,他们大多以抱怨开始,又以积极的建议结束,他们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尽快扩展到其他作物,如木薯、玉米和豆类等,因为私人贸易者并不可靠。
(二)生产力促进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Nkasi和Rukwa的早稻和玉米产量要高于当前水平。1992年,水稻产量首次达到峰值(每公顷30袋,而之前的水平仅为每公顷5袋)。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数字继续提高到每公顷35袋。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期的时候,由于无法获得充分的灌溉,加上水流中断(如洪水)等原因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产量回落到每公顷25袋。
而畜产品产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北部Sukumaland的游牧民族Sukuma人。他们拥有许多牛,也就自然地享受了有机肥施用、牛耕犁、牛拉车等农业技术的裨益。养牛文化开始逐渐蔓延,意味着个人的资本存量和资产在增加。如果能够提供适当的管理、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养殖业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1995-1999年,国际小母牛在1999—2003年,香港明爱在2004-2005年,分别支持过坦桑尼亚的奶牛养殖,使其成为一些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项目并遵从项目原则的农户更是如此。例如,一个来自Rukwa地区Kalesa的受益者在1996年获得了一头奶牛,用出售牛奶所获得的收入购置了5公顷土地用于水稻种植,修建一栋有4间卧室的瓦房,将唯一的孩子送去私人中学,并邀来8位亲戚的孩子同住,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学费。虽然这些支出使她本人无法脱贫,但为亲戚提供支持在当地社区被普遍视为福祉的指标之一。
(三)信贷制度
农户能够更多地获得小额贷款,为他们扫除了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障碍。例如Mwandima的信贷合作社覆盖了整个Mwandima地区和Rukwa的所有4个村子(包括Kalesa)。自2006年引入的信贷制度目前已经吸引了417个成员,并拥有一个由6人组成的董事会和由3人组成的监委会。信贷合作社要求其成员进行储蓄以获得贷款资格,并鼓励他们购买股份。每股价值5 000先令,入社费则为2 000先令。一个人要想获得贷款,必须拥有至少50 000先令的股份和50 000先令的存款。
从Rukwa、Mwanza和Mtwara的生活故事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普通人要想加入信贷系统仍然困难重重。然而,一旦满足了初始条件成为信贷合作社成员,回报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在获得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尤其如此。确实,信贷渠道是农业生产力和减贫的重要决定因素。回归分析也表明(经济活动的)金融化、储蓄和信贷机构的成员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渠道,都是减贫和生计改善的重要决定因素,显著度为5%。
信贷制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其成员及社会大众过高的文盲率。其成员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储蓄和购买股份的传统,他们只是想贷款而已。如果贷款没有得到批准,他们会抱怨受到了歧视,声称信贷合作社只为富人服务。鉴于这种负面观点甚为风行,通过成员资格促进资源流动就无从谈起。
在网络方面,每个村庄大约20%的人参加了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ROSCA),其模式是将成员的所有储蓄贷给某一成员,在特定时间之后收回贷给下一位成员。一些焦点小组访谈受访者认为,信贷合作社比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所需花费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后者能够更快地发育成熟。在Rukwa的Nkasi地区,葬礼组织十分普遍,其成员会以现金和劳力的方式,在成员或其近亲去世时分担葬礼成本。这种组织或协会也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或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的筹资。
除了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另一种重要的非正式信贷制度:在亲属、邻居、朋友、商人和房贷者之间的财务安排。这是大部分农村人口获得信贷的主要来源,而获得的款额主要用于消费,如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和婚礼花费等,仅有部分投入到生产环节。这种贷款的额度一般比较小,大约在5 000~10 000先令。部分贷款不收取利息,也没有附加条件,还款的模式基于互惠原则而比较随意。在Kalesa和Rukwa,农户会以一袋早稻来偿还10 000先令的贷款,而其市场价格则在20 000~30 000先令。放贷者由于收取高昂的实物利息而被指责借机剥削农户。然而,非正式贷款促使农户能够获得不受约束的贷款,从而增加耕作面积,放贷者承担的风险反倒较高。农户能够耕种2~3公顷的土地,提高产量和生产力。另一方面,Kalesa村的放贷者因为缺少资本而无法满足当前的贷款需求。
五、 新的增长是否促进了减贫?
令人沮丧的是,上节所述的增长并未促进人民福祉。其原因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扭曲的农产品市场。
(一)基本需求成本迅速上涨
1. 2005-2009年的上涨
受访者认为,在2000-2005年,生活成本上涨并不显著。而到了2005-2009年,上涨之快已经抵消了仓储系统带来的所有收益。因此,在MKUKU-TA I时期人们反而感到更加贫困。虽然仓单系统使腰果的价格从250先令涨到500先令,又进一步涨到800先令,但仍然不及生产资料投入和生活成本(基本需求,如鱼、煤油、香皂、糖、盐和布)的上涨幅度。贫困人口被赶出了某些基本需求市场(例如牛肉、鸡肉、牛奶和鱼,即食物蛋白质)。生活成本的上升体现在几个层面。图7所示的指数在2002年以来在持续上涨,自2005年以来上涨速度甚至在加快,其中食物价格的增速最快(燃油价格次之)①。诚然,自2007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以来,食物通胀成为通胀中最为严峻的部分。

资料来源:NBS (2010)。
①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NCPI)根据坦桑尼亚大陆20个乡镇的价格计算,覆盖了207种产品。所有的价格都根据当前市场价格计算。NCPI是一个对城市地区居民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统计测量的工具,涵盖了所有的消费群体。NCPI测量价格(而非支出)的变化,而价格是影响生活成本的最主要因素。
图8为先令在不同时期的消费购买力。2002年11月100先令的价格/购买力下降到2009年11月的59.28先令。在Nkasi的城市地区如Newala、Magu和Kayumbe等地,基本需求成本的通胀导致的贫困现象更为明显,这里的居民更加依赖市场获得就业机会,而所需支付的价格也高于农村地区。

资料来源:NBS (2010)。
2. 必需品和临时性劳动力的价格上涨
临时工们更能体会到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一位妇女说,“如果我们去做临时工,比如做20天的甜甜圈,会拿到20 000先令的工资。但是20 000先令没办法从市场买到够20天吃的食物”(专栏6)。
根据一位受访者的反馈,表9对1999-2009年的价格变化幅度进行了粗略的估算。官方数据表明2002年以来,坦桑尼亚的物价水平整体上翻了一番,因此,表9的估算可能略有夸大,而该受访者在访谈中也十分生气。然而,表9仍然能够反映受访者对价格上涨的感受。 过去10年间,非食品类必需品(如肥皂和煤油等)的价格也翻了一番甚至两番。在坦桑尼亚,依赖市场获取食物的人口面临着最高的食品不安全性,临时性劳动力尤其如此。坦桑尼亚虽然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其食品不安全问题却可能会恶化。原因有三:人口增长过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加了2倍)、耕地面积减少、肥力降低等因素,导致劳动力数量增加;农业生产持续萎靡,减少了就业机会,限制了工资上涨;食品和非食品必需品价格上涨。
表9 1999-2009年间的食物价格估算
单位:先令
资料来源:de Corta和Magongo (2010)。
因此,虽然MKUKUTA进行了减贫的努力,但临时性劳动力的饥饿问题却在加剧。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饥馑早期预警网络(FEWSNET,2009)对坦桑尼亚2009年10月到2010年3月的预测表明,食品价格的居高不下导致了食品不安全家庭数量的增加。
3. 低收入缘何产生高成本
这是个困扰经济学家已久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对这些产品的有效需求缺失,应该会导致价格的降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运输成本。在坦桑尼亚,燃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食品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成本增加,最终提高了食品和非食品必需品的价格(FEWSNET,2009)。Newala地区位于一个高原地区,运输者不仅要承担较高的燃油成本,也要考虑在破损的路面上行驶的风险,于是他们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加以弥补。从Kalesa到Kayumbe的道路破损不堪,雨季更是寸步难行,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成本。
电力供应的持续缺乏也提高了生产成本,推动了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政府部分的扩员。政府雇员拥有永久性收入,并因稳定的工资而获得信贷渠道,成为少数有能动性的群体之一。这些带薪的政府雇员及为他们服务的人群(发廊、餐馆和旅店等)导致了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不受腰果价格波动的影响。非政府组织(NGO)也带来了稳定的客流(NGO工作人员、到访的官员、作物贸易商等),从而带动了商品需求。在Mtwara和Mwanza,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此外,近年来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导致现金量增加,也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二)服务成本迅速上涨:水、教育和健康
对贫困人口而言,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本增加来自于基础服务领域。在大部分地区,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水、教育和健康等方面。MKUKUTA旨在扩展基本社会服务,却因成本不断增加而恶化了贫困人口的处境。贫困人口由于无法负担成本,就只能承受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教育、卫生设施不足和不利的健康状况等后果。
例如,Nchinga人正在缺水。20世纪60年代,他们用水泵从Ruvuma河取水,再以管道通到各个建筑。这些设备已经年久失修,水泵所需的电力供应也不足。结果当地人只能选择买水或者远距离取水。每天,他们都要花6~8个小时来取水(早晨2点到6点或早晨6点到下午2点),而返程还是一段上坡路。年纪大一些的孩子能帮忙,却会因为过于劳累而不愿上学。或者,当地人还会雇佣临时工来取水,并支付现金。总之,缺乏免费或廉价的水资源,会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金融成本(500先令的工资支出),或间接降低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或是影响家庭的卫生状况和健康水平。在3个研究点,研究者都提到了许多孩子脸部和衣着的脏污情况。同时,购买力降低意味着昂贵的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品开支无法保障,而卫生设施不足又会进一步恶化营养不良。
另一个问题是学费成本和其他开支的增加。当问到Newala的焦点小组为何Nchinga和Nkangala的学校退学率高于坦桑尼亚其他地区时,得到的反馈令人无限伤感:“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让孩子上学!但是穷人没法交得起学费、校服费和其他的钱,只能滚蛋。”(专栏7)
比Asna和Samweli更贫困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送子女去上学。在当地的政府学校,一个孩子要交纳30 000先令购买桌椅,或者从家里自带桌椅,否则就不能上学。小学教师会强制学生交钱而不能自带。而买不起校服是最令人伤感的退学理由,在当地却十分常见。所以,能够上学(包括中学)的孩子一般都来自“非贫困”家庭。教育支出数据表明,极端贫困人口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的20%(图9)。贫困人口不送子女上学的主要原因是真实收入降低直接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资料来源:实地调研。
虽然药房、医疗中心甚至医院都十分便利,但享受这些健康服务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仍然过于昂贵而望而却步。X光检查需要花费25 000先令,“但很少有贫困人口能够在突然患病时拿出25 000先令,只能坐以待毙”(Mtwara地区Newala的焦点小组)。即使到了医院,贫困人口也会发现那里缺医少药,两三个病人只能挤一张床。MKUKUTA试图以税收调节这些基本服务的提供,特别是对健康、教育和水资源部分加大投资。然而,本地人的农业收入还是跟不上这些服务价格的涨幅。
六、 总结、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试图评估调查地区过去10年间是否实现了农业增长,而这些增长是否贡献于减贫。
(一)基本必需品价格迅速上涨
研究发现表明,农业增长速度长期以来无法显著地针对广大农业人口实现减贫、生计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当然,某些地区实现了适度的农业增长,有一系列指标可以证明,例如贸易机会(如跨边界贸易终端)、农畜产品、农业技术、仓单系统等。不幸的是,这些增长没能提高人民的福祉。
价格的上涨和农产品市场结构的扭曲是主要原因。通胀迅速地拉升了基本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包括农业部门临时性劳动力的成本。同样的,如水、教育和健康等服务的成本也在上涨,抵消了腰果、芝麻和非传统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此外,通胀持续压低了真实生产者价格。同时,市场结构也不利于农户。在本地市场积累起来的财富没有惠及生产者,相反地,少数贸易者有意压低本地价格,降低支付给农户的成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和地方农户都与外部市场脱节,也就无法享受有利的生产者价格。私人贸易者能够在外部市场上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农户的产品,获得巨额利润。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市场自由化以来,坦桑尼亚一直没能建立起市场扭曲的调解机制。市场结构需要加以调整,以反映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维持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并发挥有效的最小监管作用。政府对市场的最小干预必不可少。目前的市场结构存在漏洞(由于一些市场角色的不作为,特别是政府),导致收购商对农户的剥削,农户无法直接进入更加有吸引力的市场进行交易。
因此,制定一个有效的农业战略规划就迫在眉睫,才能推动小农农业转型,刺激农业活动以促进农业增长,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最终改善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生计。
(二)农业增长(和减贫)的阻碍
农业市场被少数私人贸易者主导,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加重了小农的负担。在9.5%的通胀率条件下,现有的市场结构并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仓单系统是矫正市场扭曲的手段之一,使农户能够间接地与外部市场相连接。要降低通胀的影响,需要为粮食生产者提供支持以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农户收入、降低食品通胀。
通过支持如Tandahimba农户腰果协会(UWAKOTA)和Newala农户腰果协会(UWAKONE)这样的农户组织,能够弥补仓单系统的一些弱点。它们借助仓单系统建立了新的市场渠道,向其成员收购腰果,再通过仓单系统进行储存和出售。据称,与初级组织相比,这些协会更透明、更负责。它们以需求推动,有更强的市场谈判能力,以成员利益为行动准则。在其他地区,特别是Newala和Masasi,对这类组织的需求十分强烈。
要扫除农业增长的阻碍,需要出台一系列干预措施。农业增长和减贫的阻力同样来自于以下方面:低下的土地生产力、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生产力;有限的资本存量和金融服务渠道;农业技术支持服务缺乏;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城乡联系;传统的性别关系;生产者组织能力不足;初级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价格劣势;不安全的产权;将商业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用于借贷抵押等。这些负面因素影响了农业生产力(渔业、畜牧业也未能幸免),是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也应该是农业投资的优先领域。因此,应当关注私人部门的参与,改善道路网络、信贷和教育条件,确保农业支持服务的及时到位。
与妇女及婚姻有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加上农村离婚妇女大多是法盲,妇女常常遭受离婚或被丈夫抛弃之苦。她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善现状。应当给予陷入这种困境的妇女更多的关心,并提供法律支持。
(编译者:唐丽霞 李飞)
中国包容性增长与减贫:进程与主要政策
黄承伟 徐丽萍
摘要: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其基本含义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素包括: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中国政府正在和即将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最大限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三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四是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但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理念一脉相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减贫;政策
2009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的理念。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的《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致辞中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并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其基本含义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包含以下基本要素: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
一、 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历程回顾及其主要特征
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推动全国大规模减贫(1978一2001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三分之一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普遍贫穷和落后状态。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首要目标是解决普遍贫困问题。1978年,中国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工作上来,并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阶段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缓解贫困。
①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新华网, www. xinhuanet. com,2010 年 09 月 16 曰。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到1983年,该项土地制度改革覆盖了超过98%的农村家庭。同时,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逐渐放开农产品的买卖价格。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中,国家首先削弱壁垒并打断城乡二元结构分隔,允许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贸易取代在城乡地区被国家控制的棉油统购,鼓励在大城市建立农产品市场。继家庭承包经营的成功,政府开始指导农民进行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并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为提高农产品产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科技研究并在县级建立了推广体系,为增加农业产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4年10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重点内容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内容主要有国有企业全面实行利改税,自主经营权的突破即逐步确立了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自身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逐渐暴露,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历了改革与脱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相应得到加强。1987年国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模式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并发展。自此,单一的计划经济格局开始转变,中国的市场主体开始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GDP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通过“渗漏效应”,经济增长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按中国政府贫困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1年的2 927万人,相应的贫困发生率由30.7%减少到3.2%。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加速增长时期,这期间国家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专项扶贫开发,并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贫困发生率由1993年的8.8%下降到2000年的3.4%。
(二)政策调整带动城乡统筹,促进均衡发展(2002-2010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期。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时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一阶段包容性增长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整,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均衡发展。2002年,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一2010年)中,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明确,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
 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减免农业税和支持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等
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减免农业税和支持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等
①张磊,中国扶贫开发历程(1949一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向“三农”倾斜。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保障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大病统筹机制。建立城乡公平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
为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农村乱收费现象的恶化,中央政府于2001年开始试点,2003年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直到彻底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已经全部取消了农业税。 这些惠农政策为农业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日常基本需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加速了农村扶贫的进程。这一时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分散化趋势,中国政府相应调整了农村扶贫的方式和策略,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将区域瞄准范围由贫困县向贫困村转移,实现让最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这一阶段,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5 825万(仅低收入人口)下降到2010年的2 688万。
 (三)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起)
(三)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起)
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一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资料,2010。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助推中国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非均衡发展机制也使得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仍然比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而消费动力不足;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不均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甚至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理念,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分享。为此,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一阶段包容性增长主要通过完善各项制度建设,把试点成功的政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具体包括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着力解决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未来10年,中国将扶贫开发提高到“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长期历史任务的战略高度,开始贯彻执行“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未来10年的减贫目标,即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证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由于目前剩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以武陵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为代表的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将这些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
二、 中国推进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政策
(一)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政策,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为稳固这一成果,实现更大的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程。
(1)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政策。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行业准入等经济和法律手段,引导更多资金进入薄弱环节和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制定实施,安排200亿元技改专项资金支持4 441个技改项目。预计到2020年,信息通信、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六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望达到20%左右①。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政策。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政策。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马骁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报告,2011年。
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采用8个约束性指标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能源和环保指标.还覆盖了人口控制、养老保险、农村医疗等民生领域,而将以往最被看重的经济增长等列入预期指标。
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初步转变,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趋于增强,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由2005年的31.4%上升至2008年的33.2%。2009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十五”末的40.3%上升至42.6%。
(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
1. 流动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分为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开始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转移就业,政府提供就业培训和服务。进入21世纪,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促进流动人口融人城镇发展(表1)。
对流动人口由控制向鼓励和提供服务的政策转变,加快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自主流向城市,成为在城镇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军。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亿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不仅为经济生产带来巨大效益,也为农民实现增收、加快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
①马骁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报告,2011年。
②段玉瑾,《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4卷第6期。
表1流动人口政策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劳动力转移与培训
中国在反贫困行动中,特别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使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利用,组织、发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同时,在反贫困行动中还特别强调人员培训,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培训。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是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和培训的两项主要的政策。
(1)阳光工程。为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实现稳定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农业部等6个部门从2004年起,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简称“阳光工程”。“阳光工程”首先在河南、四川等26个省区和黑龙江农垦总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2005年培训28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增加到4亿元①。该培训项目作为由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的政府项目,对中国西部广大输出劳动力的地区能力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对于贫困人口素质技能的提高和长期发展的作用尤为深远。
(2)雨露计划。为解决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矛盾,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2004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发出《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通知》,开始实施“雨露计划”。“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开展职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截至2010年年底,“雨露计划”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近500万青壮年贫困农民和20万贫困地区复员退伍士兵成功转移就业;通过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农户至少有1名劳动力掌握1~2门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农业生产技术。“雨露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由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阶段,发展到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并举的新阶段。
①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一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三)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1. 个人所得税政策
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个人所得税政策。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但是并没有出台一些具体的征税细节。1986年9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公民的个人收入统一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表明个人所得税政策开始启动。
随着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没有及时做出调整,越来越多的人群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截至2009年,个人所得税总额已达到3 949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5倍①。同时,个人所得税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开始阶段,由于起征点远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收入达到征税标准的人群比例很低,因此,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个人所得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高收人群体避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单项税特征(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综合税),因此,也没有充分发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②。为了减轻低收人群体的税赋,缩小收入差距,2011年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3 500元。
①李实,有利于减贫的收人分配政策:中国经验报告,2011年。
2. 农业税和农村税费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税赋重,所要缴纳的各种费名目繁多。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户负担的税费达到了很高水平,据调查某个县税费负担最高达到了28%③。面对农民负担日益严重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进行农业税改革试点,一些地方的税费负担开始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2.8%。2006年,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同时取消地方政府征收所谓的“三提五统”的权利。全国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后,共减轻农民负担约1 250亿元,每个农民减负140元左右④,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收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农村的税费政策具有很强的累退性,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年以后,采取的农村税费减免政策既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更加有助于减少贫困。据李实等估计,以1995年为例,如果农业税费全部减免,那么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会由2.47倍下降到2.34倍⑤。
 (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改善民生
(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改善民生
②李实,有利于减贫的收人分配政策:中国经验报告,2011年。
③陈锡文主编,《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人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
④黄维键.取消农业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及下一步政策取向,财经研究,www. cjyj. shufe. edu. cn,2007 - 10 - 23。
⑤李实,有利于减贫的收人分配政策:中国经验报告,2011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曾一度过分依赖市
场化手段提供,导致因病和因教育致贫的严重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1. 全面普及义务教育
教育方面的成功改革主要体现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支持力度和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等。198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施行,标志着中国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进一步确定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
为了缩小中国城乡的发展差距,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2005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逐步对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2005-2007年3年内全部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国家财政共安排227亿元资金①。
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方面,2005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从2006年起,各地政府承担了全部办学经费,农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政策对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发展了关键的作用。2003年,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人均8.1年;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2 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②;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70%(其中男、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99.68%和99.73%),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1%(图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87.5%③。
①张秀兰,利贫的社会政策:中国的经验与未来的策略选择报告,2011年。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
义务教育的实施在提高义务教畜普及率、隆低文盲率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农村义务教育的补贴政策对提高贫困人口素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完善医疗卫生设施与卫生服务
(1)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90年代医疗体制推行市场化。在城市,医疗体制改革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1994年开始试点,1998年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该制度正式建立。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体城镇职工,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并陆续出台医药分家、药品招标采购、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等一系列政策。2000年以后,政府开始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以促进医疗保障和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政府于2003年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政府投入为主,农民自愿参加,目的是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以及医疗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平性等问题。2004-2005年,政府相继推出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帮助弱势群体应对医疗负担的高风险。
②③教育部,2010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 //www. chsi. com. cn/jyzx/201107/ 20110706/219482079. html。
(2)完善医疗卫生设施与卫生服务。中央和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机构建设力度,进一步健全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其中,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400亿元,建设县级医院1 877个,中心卫生院5 169个,村卫生室11 2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382个①。同时,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型、改造以及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多种方式,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资源得到充实。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群众获得了方便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截至2011年4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94.1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3.3万个,乡镇卫生院3.8万个,村卫生室65.O万个,诊所(医务室)17.5万个②。2010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诊疗人次达到了30.2亿,占到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的51.7%。
(站)3.3万个,乡镇卫生院3.8万个,村卫生室65.O万个,诊所(医务室)17.5万个②。2010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诊疗人次达到了30.2亿,占到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的51.7%。
①张秀兰,利贫的社会政策:中国的经验与未来的策略选择报告,2011年。
②卫生部,2011年4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http: //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 mlfiles/mohwsbwstjxxzx/s7967/201106/52031. htm。
③卫生部,《2010卫生统计提要》,http://www.moh.gov.cn/。
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医疗机构和设施的改善,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孕产妇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00/10万下降至现在的30.0/10万(图2),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10年的13.1‰(图3),均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10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3岁,国民健康水平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①。

数据来源:《2010卫生统计提要》。

 数据来源:《2010卫生统计提要》。
数据来源:《2010卫生统计提要》。
①卫生部,2011年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工作简讯,http: //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 ness/htmlfiles/mohfybjysqwss/s7901/201104/51206. Htm。
3. 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首先由城市起步,1993年,上海市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志着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诞生。1997年,城市低保制度正式建立。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全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形成。
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 145万户、2 310.5万人(图4);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低保资金52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占69.7%。全国农村低保对象2 528.7万户、5 214万人(图5);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44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占60.4%①。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了城乡均等覆盖,并稳步向应保尽保迈进,为稳定、持久、有效解决农村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奠定了制度保障。2010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251.2元,人均补助水平189.0元②;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每月117元/人,月人均补助水平74元③。

 资料来源:《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资料来源:《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①张秀兰,利贫的社会政策:中国的经验与未来的策略选择报告,2011年。
②③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http: //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 201106/20110600161364. shtml。

资料来源:《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三、 中国继续推进包容性增长与减贫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
总的要求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一是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
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二是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三是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
(二)扩大内需,建设消费型社会
一是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人群体的收入增长。二是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穷人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三)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待遇
主要是健全法律法规,特别是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促进农民融人城市生活,增加进程务工人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四)调节分配结构,继续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我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为此,中国的税收需要做出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以增强其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功能和反贫困的功能。一是逐步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二是将个人所得税由现在的分项税改为综合税,前者是对每一项收入进行征税,而后者则是对家庭总收入征税。实行综合税可以避免低收人人群和贫困人口也交税的尴尬局面,可以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五)继续完善机制制度,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待遇水平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边缘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中国2009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6.16%。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助于缓解贫困。要坚持深化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不仅要让贫困人口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好处,而且要让他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或不付代价。
四、 几点启示
在中国,包容性增长从概念提出到全面实践历时并不长,但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与“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理念一脉相承,成为国家制定不同时期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是解决发展过程中谁受益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对中国,对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包容性增长理念始终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政府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三,需要不断探索并完善包容性增长的政策体系并有序推进制度化建设。
第四,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特征,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适合本国的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和措施。
印度尼西亚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新战略
Tulus T.H.Tambanan 印度尼西亚USAKTI工业、
中小型企业与商业竞争研究中心
一、 引 言
印度尼西亚在所谓的“新秩序时代”(1966-1998)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年经济增长率在6%~8%。政府还通过农业现代化以及经济工业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成功地降低了贫困率。因此,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新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宏观层面的经济成就掩盖了一些问题,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无效率和市场扭曲。此外,印度尼西亚还受到经济代价过高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的困扰。在此期间,经济发展实际上仅局限于政策制定者认为重要的特定社会团体和特定地理区域(如爪哇等)。
十余年前,印度尼西亚遭受了自1945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1998年经济衰退,年增长率为-13%。从此之后,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开启了深远的制度变革,成为该地区中最为动荡的民主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印度尼西亚也取得了很多进步。自2002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实际GDP年增长率为5%~6%。谨慎的财政管理和巩固战略使政府债务显著减少。通货膨胀基本在控制中,国际收支平衡,出口商品多样。过去5年中公共投资稳步增长。贫困率降低,公共服务部门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如新的社区发展项目等。商业、金融和工业等经济领域广泛的改革已经展开,经济发展战略也从“排斥”向“包容”转变。
本文旨在探讨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战略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秩序时代)的“排斥性”向“包容性”转变的过程。具体而言,本文讨论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目前制定和执行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在此之前本文首先需要简短地讨论印度尼西亚政府目前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二、 印度尼西亚经济成就简述
印度尼西亚在前总统苏哈托领导下的新秩序时代(1966-1998)是东南亚少数经历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可能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中极少数在工业化、农业发展(特别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推行)、GDP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和减贫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因为其轰动一时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继“原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之后在地区报告中将印度尼西亚称为“新亚洲四小龙”之一。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过程在5年经济计划(Repelita)的指导之下集中关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进口替代战略拉开帷幕,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转移到出口导向战略,在其他国家和世界银行的捐助和投资以及国外直接投资的刺激之下,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快速结构转型的增长过程。尽管印度尼西亚在多样化、结构深度、科技含量等方面的工业化程度与韩国、中国台湾相比要低很多,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的工业GDP份额已经高达43%,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继马来西亚之后位居第二位。
虽然农业GDP在此期间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经济发展进程一样稳步下降,农业经济部门随着“绿色革命”的进行在现代化和密集化程度方面发展良好。政府在此期间采用此战略旨在提高生产率和农民收入,进而降低农村地区的贫困率,降低国家对于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尤其是基本食物(如大米)的依赖。实际上,该战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甚至在特定的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仍然能够实现国家主要食物大米的自给自足。伴随着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产出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他部门如商业、建筑业和金融业产出的总体增长,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一直到1997年取得了年均8%的快速经济增长,并在1990年达到9.9%的峰值(图1)。人均收入从1970年少于500美元(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稳步增长到1996年略高于1 000美元。在地区经济危机即1997-1998年亚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年鉴(多年),BPS(www.bps.go.id)。
洲金融危机衰退之后,印度尼西亚经济在1999年重新开始并保持增长,人均收入预期将在2011年超过2 500美元(图2)。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年鉴(多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BPS) (www.bps.go.id)。
苏哈托时期经济发展成果的另一指标是以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所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衡量的贫困率持续下降。1976年贫困率约为40%,1990年降低至约为15%。受1997-1998年危机影响,许多公司倒闭,失业率大幅提高,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1998年贫困率骤然升至24%。但是自1999年之后,贫困率降低并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13.3%。世界银行预期2011年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在12.5%左右(图3)。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年鉴(多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BPS)(www.bps.go.id)。
然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自新秩序时代以来,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遭遇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是开始于1997年下半年并于1998年中期达到顶峰的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是由资本从泰国突然外逃引发的,导致泰国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随后不久,资本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外逃,导致上述国家货币相继贬值。印度尼西亚是受此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降为-13%,贫困率显著上升。第二次是2007-2009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范围远大于1997-1998年危机。此次危机是开始于2007年美国的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该危机的全球影响表现为支柱产业的失败、消费者数以10亿美元计的财富缩水、政府大量的金融担保、很多国家经济活动的趋缓。危机进一步快速发展和扩展为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引发大量银行破产、各种股票指数下降、股票和商品市场价值萎缩。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都受到该危机的很大影响。虽然多数亚洲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率只经历了轻微的减缓,但是由于危机的加剧和2009年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国内需求急剧萎缩,2009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活动大幅降低了。
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之外,当前存在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另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普遍认为这会波及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虽然与美国、日本相比传统上欧元区并不是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国家的游客和印度尼西亚货币与欧元的汇率。虽然如此,普遍认为正如面对2007-2009年危机,印度尼西亚已经充分准备好如何面对此次危机的可能影响。印度尼西亚经济相对于1997-1998年危机时更加具有弹性,并得到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健康的支持,例如国外债务/GDP比率、政府财政赤字总额及其所占GDP比率,还有银行指数如不良贷款率和资本/资产率。
三、 包容性经济发展
1. 概念
何为包容性经济发展?根据Ali和Zhuang (2007)、Ali和Son(2007)以及Rauniyar和Kanbur(2009),关于包容性经济发展没有一致和普遍的定义。该概念基于另两个概念:包容和经济发展,包容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目标。包容是指社会通过消除歧视和限制社会中特定的个人和团体的障碍而容纳差异存在。它将社会看成问题,而非人。Rauniyar和Kanbur(2009)指出包容性经济发展应该理解为经济增长同时伴随平等的经济机会,而且所创造的经济机会应该向社会所有层次人群开放,并非仅面向穷人开放。只有当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个人的环境和背景)都参与到并贡献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该经济发展过程才能称为包容。同理,包容性经济增长强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创造面向所有人特别是穷人的经济机会。因此,包容性经济发展是一个确保将所有边缘化或排除在外的社会团体纳入其中的社会发展过程。因为包容包括了社会中的所有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网络是实现包容的核心策略。
根据Sachs(2004),为了给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相同的机会,包容性发展战略需要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确保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所以正如Sen(1999)所强调的,民主是一项基本价值,能够确保发展过程所需要的透明和负责。Sachs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是包容性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到为残疾人、母婴和老年人等为弥补自然或身体不平等所设计的福利项目。补偿性社会政策还应包括支持救助失业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第三,全体社会公民具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健康、住房。
包容性经济发展的思想来自于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提出。千年发展目标针对以下事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了以高经济增长、高人均收入、快速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结构转型等为标志的长期经济发展成果,但是不少国家的贫困率依然很高,贫富差距甚至扩大。普遍认为可持续的减贫需要建立在快速经济增长基础上,但是二者的关系不是必然的。一些快速增长的经济未能降低贫困,而另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更加成功。甚至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2010)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根本问题在于缺少包容性经济发展战略来融合和支持“人类发展”的宏伟目标。
不难理解为何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南亚和非洲某些地区依然在贫困线附近挣扎(贫困率甚至上升),很大比例的公民生活在一穷二白的极端状况之下(特别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很多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HIV/AIDs携带者、少数民族、流浪者、战争难民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排除在外或被边缘化。贫困即是弱势的后果也是弱势的原因,因此,若非将贫困人口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困将无法减轻。
从上述讨论而言,包容性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贫困、参与、合作、协作。这意味着减贫是或者应该是包容性经济发展政策的中心,并且减贫甚至彻底消除贫困不仅需要直接的减贫政策,而且经济发展政策、项目、工程在不牺牲效率、生产率和竞争水平的前提下降低贫困。
2. 包容性发展指标的框架
在亚洲开发银行(2011)中,35种核心指标用来监测包容性经济发展或增长。Zhuang(2010)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或增长指标框架界定了这35个关键政策要素,即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社会包容、社会防护、良好政府管理和制度等。指标包括8个维度:①贫困和不平等(收入和非收入);②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③关键设施和禀赋;④教育和健康的渠道和投资;⑤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渠道和投资;⑥性别平等和机会;⑦社会安全网络;⑧管理和制度(表1)。根据Zhuang(2010),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增长有3个政策支柱(图4)。政策支柱1是创造生产性就业和经济机会;政策支柱2是确保经济机会的公平;政策支柱3是保障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以及应对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造成的暂时的生活冲击。当然,3个政策支柱必须基于良好的管理和制度之上。
表1 包容性经济发展指标的框架
资料来源:Zhuang (2010).ADB (2011)。

四、 印度尼西亚包容性发展战略
1. 基本发展战略
在1997-1998年,印度尼西亚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随后发生了社会政治动荡。这一系列危机导致了1998年5月苏哈托政府(新秩序体制)倒台。自此之后,印度尼西亚人民决定寻找新的道路,即民主。民主、分权的执行以及1945年宪法的修订从根本上改造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些旧的社会制度安排停止运行。
新秩序时代实施了很多反贫困项目,并且贫困率也曾大幅下降,这表明当时的政府慎重地对待和处理贫困了问题。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的贫富差距并没有显著改变。事实上,当时的发展战略倾向于“排斥”而非“包容”,很多规定、政策和措施仅有利于一小撮大型公司,并以中小型企业为代价。
在改革的新时代,政府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包容性经济发展轨道上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9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地区代表全体会议之前,从地区视角看待国家发展的发言中提出,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情,所有发展模式只有在采用以下6个基本发展战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SNRI,2011)。
(1)第一个是包容性发展战略,保证公平和正义,尊重和保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多样性。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经常阐释关于印度尼西亚发展的共识。该共识应该以印度尼西亚的中长期目标和使命为指导。2007年17号法律即国家长期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印度尼西亚2005-2025年长期发展方向,而印度尼西亚的中期发展方向每隔5年颁布一次,即中期发展计划(RPJMs)。每个五年发展计划都有一个阶段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组成长期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各个中期发展计划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总结如下(MNDP,2010,page l-23):
1)第一个五年计划(2005-2009)将改革和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所有领域,旨在为人口日益增多的印度尼西亚创造一个安全、和平、公平和民主的环境。
2)第二个五年计划(2010-2014)旨在全面巩固改革的成果,强调人口素质的提高,包括提升科学技术的能力建设以及强化经济竞争能力。
3)第三个五年计划(2015-2019)旨在进一步全方位巩固发展的成果,其途径是在自然资源领域竞争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基础上加强经济的竞争,提升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
4)第四个五年计划(2020-2025)在各地区竞争优势和人力资源质量及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巩固既有经济结构,通过多领域的加速发展,实现一个自立、先进、公正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社会。
每个五年计划包括前景、目标以及建立在国家长期发展计划上的总统项目。总统项目包括国家发展战略,一般政策、部门和跨部门项目、地区和跨地区项目,以及宏观经济框架。宏观经济框架是在管理和指向性资助框架构成的工作计划中包括财政政策方向在内的总体经济状况。五年计划是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构建各自战略计划的基础(Renstra-KL)。地方政府在建立或修改地区发展计划时也必须根据当前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向国家发展目标靠近。随着2005-2025年国家长期发展计划的执行,国家长期发展计划将被进一步纳入到政府年度工作计划(RKP)中,并且成为构建政府预算草案(RAPBN)的基础。
目前执行的是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2010-2014。与国家五年计划2004-2009 -致,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2010-2014分解为3个经济发展战略,包括“促增长,促就业,消除贫困”战略。通过“促增长”战略,经济增长加速,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增长、平等)。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2010-2014有14个优先省和优先地区,包括苏门答腊、爪哇一巴厘、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努沙登加拉、马鲁古和巴布亚,优先领域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政治、国防和安全、法律和国家机器、地区和空间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
(2)第二个基本发展战略是在全面发展框架中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必须存在领土维度。每个省、市都是国家增长的核心,必须将每个地区的全部潜力进行资本化,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地理位置。这正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鼓励边境地区发展合作的机会,如IMT - GY和BIMP - EAGA,以及与澳大利亚和帝汶岛开展合作。领土维度的发展同时意味着政府继续促进地区提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地区之间平衡一定要得到保持,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地区失衡。
(3)第三个基本发展战略是在全球化时代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经济。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开放性国家,所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不能孤立进行。而且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PEC和WTO的成员国,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联系,有义务消除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所有障碍。同时,印度尼西亚也要利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为人民谋求最大可能的利益。换言之,印度尼西亚需要在全球化的时代抓住经济融合的机会,避免经济融合的负面影响。
(4)第四个基本发展战略是地区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劲的国内经济。这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之一。强劲的国内经济是一国在全球化的凶猛浪潮之中繁荣富强的重要资产。印度尼西亚从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能够从容应对全球经济萎缩的国家才是一个国内经济强劲的国家。而且,国内经济强劲的国家能够保证国家的自足自立。这正是加强地区之间联系成为前提要求的原因。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在2004-2009年,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完成了连接爪哇和马都拉大桥的建设。爪哇一马都拉的联系将显著促进马都拉的发展及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同理,印度尼西亚正在计划建造一架连接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桥梁。一旦完成,发展利益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在爪哇岛,将扩展到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完成加里曼岛、苏拉威西岛、巴布亚岛的建设。除了加强地理上的联系,印度尼西亚试图加强地区之间功能上的联系。政府继续促进一个地区的产品能够作为下一个地区的原料投入或者作为最终产品。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努力消除地区之间的贸易障碍,例如政府收费站等。特别是非官方的收费站严重阻碍了相应地区之间投资和贸易的融合。
(5)第五个基本发展战略是增长和平等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增长,平等)。该发展战略是对上一个发展政策的矫正,即所谓的滴入论效应。滴入论效应假设经济增长的需求优先于经济平等的需求。实际上,滴入论效应在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很多国家为全民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成功。所以,为了同时实现增长和平等,印度尼西亚采用了一种“三管齐下”的战略,即在国家经济发展战中促增长、促就业、消除贫困。在“三管齐下”的战略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提高投资和国内外贸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通过实体经济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同时通过复苏农业和农村以及以人为本的项目消灭贫困。
(6)第六个基本发展战略是公平正义发展的本质,强调提高人类素质。该战略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仅是发展的客体,相反,是发展的主体。因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目标的重点,所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得以提高。因此,发展模式优先考虑教育、健康、收入以及更好的生活环境。此处的环境不仅指健康、可持续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有序、安全、安逸、民主的社会、政治和稳定的人文环境。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预期寿命从2004年的68.6岁持续上升到2009年的70.7岁。婴儿死亡率从2004年的3.39%下降到2009年的2.62%,妇女生育的死亡率从2003年的0.307%下降到2007年的0.228%。同时,文盲率(15岁以上的印度尼西亚居民)从2004年的9.6%降低到2008年的7.9%。一般认为,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发展指数从2004年的68.7%上升到2008年的71.1%。
2. 减贫政策
在包容性发展中,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战略,即“促增长、促就业、消除贫困”。就“消除贫困”战略而言,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前启动了多种项目直接或间接消除贫困。这些项目的执行不是替代而是补充经济增长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动力。这些项目中最普遍的一种是国家自力更生社区建设项目(PNPM),旨在直接地从社区和村庄层面促进人们摆脱贫困。在国家自力更生社区建设项目之下,村庄的人民可以结合各自地区在发展中的优先顺序进行决策。
其他消除贫困项目包括无条件直接现金资助项目(BLT)、公共健康保险(Jamkesmas)、学校管理支持项目(BOS)、生活补贴项目(例如大米、肥料、项目信用等补贴)、覆盖全国贫困家庭或接近贫困家庭的家庭希望工程(PKH)。家庭希望工程旨在当其无法自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时帮助其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一些项目采用所谓“钓竿”形式,如国家自力更生社区建设项目每年为每个社区提供30亿亚盾的资金补贴,而这些资金由人民在村庄层面自己决定如何使用。
此外,政府应该为中小型企业通过信用补贴的形式分配预算,银行部门应该为中小型企业信用分配资金。中小型企业基于以下3个主要原因很重要。第一,该类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且印度尼西亚企业的主体是该类企业(其中,小型企业是主体),因而中小型企业是印度尼西亚创造就业和收入的最大来源。第二,多数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主要是由贫困家庭和个人运营。因此,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减贫政策的有效工具之一是支持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发展。第三,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的女性企业家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中。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女性的发展对于减贫极端重要,为女性提供成为企业家的机遇是支持女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对于女性企业家的培养很重要。图5,表2、表3、表4、表5可以大致说明在印度尼西亚中小型企业信用的发展作为以人为本、消除贫困和包容性发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BI (www.bi.go.id)。
表2中小型企业分部门贷款
单位:万亿亚盾
注:* 12月,**8月。
资料来源:BI (www.bi.go.id)。
表3 中小型企业分银行贷款发展
单位:万亿亚盾
注:* 11月,**8月。
资料来源:BI (www.bi.go.id)。
表4 2008-2010年中小型企业分银行分类别贷款
单位:万亿亚盾
表5 2009和2010年小型企业分省贷款
单位:万亿亚盾
资料来源:BI (www.bi.go.id)。
最近,印度尼西亚政府引进了4个向中小型企业倾斜的特殊贷款计划。第一,Kredit Ketahanan Pangan&Energi(KKPE),旨在保障食物和能源。该贷款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农民合作协会向农民提供工作或投资贷款。贷款年利率为5%~7%,贷款时间最长为5年。第二,Kredit Pengembangan EnergiNabati&.Revitalisasi Perkebunan(KPEN - RP),旨在支持基于农作物的能源项目的发展。该贷款计划也是通过农民合作协会向农民提供工作或投资贷款。第三,Kredit Usaha Pembibitan Sapi(KUPS),旨在支持耕牛繁殖。该贷款计划通过农民合作协会向农民提供工作或投资贷款,年利率为5%~6%,时间最长为6年。第四,最重要的一项,Kredit Usaha Rakyat(KUR)即小额信贷,旨在帮助一些可行但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型企业项目,即无抵押贷款。该贷款计划为中小型企业个人生产者或所有者提供工作或投资资本,年利率为14%(KUR,零售)~22%(KUR,微型),贷款时间最长为10年。
不仅如此,政府还颁布了多种新政策法规,包括总统指令第6/2007号,2007年6月颁布的实体部门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制定了加强中小型企业信用贷款保障系统的任务;总统规定第2/2008号,即公司保障规定;总统规定第222/PMK.010/2008号,即公司贷款保障规定(CGC和公司保障规定。CGC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如下中小型企业:没有抵押物,没有足够抵押物,有抵押物但没有正规执照如土地使用许可证等。)
五、 选定指标的证据
本部分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数据(ADB,2011)描述和讨论印度尼西亚的选定指标的证据(其他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作为对比)。
1. 收入贫困和不平等
1976-2011年,印度尼西亚生活水平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比率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经展示(图3)。作为地区之间的对比,表6提供了基于当前国家贫困线和2美元/天的贫困率数据,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些国家(数据可获得)的收入/支出的平等程度。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相对于多数其他国家表现更好。不可否认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减贫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6选定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的收入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ADB (2011)。
2. 非收入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
对于非收入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本文该部分只提供了最重要指标的证据:①年轻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5~24岁)和成人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5岁以上);②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比率;③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表7)。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中几乎所有指标都表现地很好。年轻时和成人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上升了;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比率虽然仍然高于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但是已经相当低了。只有每千人生育死亡率印度尼西亚需要进一步努力,因为越南的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印度尼西亚,但是每千人生育死亡率却低于印度尼西亚。
表7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非收入选定指标
资料来源:ADB (2011)。
3. 经济增长和就业
5个指标的数据如表8:①人均GDP增长率;②人均收入/消费增长率;③15岁及以上就业率;④就业的GDP弹性;⑤每100名雇佣工人中自有工人人数。第一个指标,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增长率不仅随地区变化,而且还随百分位数变化,因为就业机会和通货膨胀在城乡之间存在差距。对于就业率而言,印度尼西亚依然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然而,就业的GDP弹性增长了意味着1992-2008年GDP增长的质量得以提高。
4. 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电力和浇筑道路,印度尼西亚相对于几十年以前和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较好,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表9展示了能够很好描述一国提供基础设施能力的4个指标,特别是①民用、商用和工用
表8经济增长和就业
注:①1993-1995;②2005-2007;③农村/城市。
资料来源:ADB (2011)。
表9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基础设施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注:*商业银行。
资料来源:ADB (2011)。
现代能源;②浇筑的道路基本设施,历程更长,运输速度更快;③移动网络的现代通信渠道;④金融融资渠道。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由于新增工业、家庭用电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用电途径,特别是城市/大城市地区1990年以来空调和做饭方面,人均电力消费量(kW·h)增长很快,印度尼西亚依然落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在浇筑道路(km)占总道路的百分比方面,印度尼西亚也落后于上述国家。虽然印度尼西亚在2000-2010年增长很快,但移动电话增长率在同类国家中相对落后。至于在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除印度尼西亚银行以外)的家庭存款,印度尼西亚并不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2276)、新加坡(2134)和泰国(1802)等国家表现优异。
5. 教育和健康的渠道和投入
教育和健康作为政策支柱2的一部分,即社会保证公平的经济机会渠道,表10展示了以下指标证据:①各教育层次预期受教育年限(男女)(PTR):给定当前的入学率,今天儿童的预期受教育年限;②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③1岁以下婴儿疫苗覆盖率(IC):白喉、破伤风、百日咳(DTP3);④卫生工作人员的数量(DHW),即每万人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人数,换言之获得经过训练的卫生工作人员的渠道;⑤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⑥政府在健康方面的支出在总支出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的这些指标发展快于其他国家且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中最好的国家之一。
6. 基础设施的渠道
基础设施的渠道也是政策支柱2的一部分,表11展示了4个指标,其中前两个是家庭层面能源贫困率的指标(IEA et al,2010),后两个是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指标:①通电人口比率(城乡一共)(EA);②使用固体燃料(木柴、碳、动物粪便)做饭的人口比率(SFC);③饮用经过净化的水资源的人口比率(DWS),这是使用安全饮用水的代理工具;④使用医疗卫生设施的人口比率(SF)。可见,印度尼西亚在清洁燃料方面表现较差,其他3个方面在该地区表现较好。
7. 性别平等和机会
表12展示了印度尼西亚在性别平等和机会方面变现不俗的4个指标(其中3个也是千年发展计划的指标):①教育的性别平等(GPE),或者小学(P)、初中(S)、高中(T)女性总入学率与男性总入学率的比率,衡量教育参与性别平等;②生育护理覆盖率(ACC)(至少1次),表示怀孕妇女健康护理的基本指标;③劳动参与的性别平等(GPLFP),15岁及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的比率,表示劳力参与劳动市场或者参与商品和服务生
表10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教育和健康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表11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基础设施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注:E-最早年份,L-最近年份。
资料来源:ADB (2011)。
表12 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性别平等和机会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产的机会性别平等的指标;④女性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比例,表示女性参与司法过程。
8. 社会安全网络
表13展示了社会安全网络(SSN)的3个指标:①基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社会保障(SP)和劳动力评级(LR),受劳动力市场规定影响,劳动力市场规定试图降低劳动力返贫风险或者维持一定最低的福利水平;②社会健康保障支出(社会保障计划和其他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占政府健康支出的百分比(GH);③政府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为生病、全部或部分残疾、老年、幸存者、儿童、失业等人群提供现金补贴)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9. 良好治理和制度
表14展示了评价良好治理和制度的3个指标:①话语权和责任(V&A);②有效管理(GE);③腐败指数(CPI)。这些指标不是基于国家数据,而是根据对企业、家庭、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进行的调查。前两个指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数值从-2.5~+2.5,数值越大表示治理越好;第三个指标,腐败指数,来自国际透明度,从0(极度腐败)到10(极度廉洁)(ADB,2011)。
表13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社会安全网络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注:*评级“1”一极差表现,评级“6”一极好表现。
资料来源:ADB (2011)。
表14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治理和制度选定指标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ADB (2011)。
六、 未来日程
印度尼西亚过去几年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在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需要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过去几年取得的成果包括基本资产的形成,而这到2014年需要一直提高。总统曾指出,到2014年印度尼西亚必须在人民的福利、公平正义、政府管理、民主程度以及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方面得以进步。为此,总统在2010年颁布了2010-2014年印度尼西亚发展目标。印度尼西亚发展目标是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根据2014年发展目标,实现繁荣、民主、公正的印度尼西亚,这些是必要的努力。此阶段政府的使命就是指导实现繁荣、稳定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2014年目标分解为政府的如下任务,即2010-2014年国家发展目标(MNDP,第1-31页)。任务1:继续向一个繁荣的印度尼西亚前进。繁荣不仅是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发展过程中追求理想,投身于一条原创性、建设性的道路。该任务的重要部分是可持续地维持和发展食物与能源的稳定、气候变化(森林与土地的复原、提高流域的管理、环境友好型能源与交通的发展、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控制)、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基本人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的创造。任务2:巩固民主的支柱。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民主改革开始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自那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进程大步前进,并逐步发展成熟。但是政治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以突出民主制度。任务2的核心政策是改革政治制度和国家稳定安全制度之间的关系;改革政治结构,政府制度作为要根据国会以及法律确定的目标和功能并贯彻和执行;权力分散、地区自治、地方民主等。任务3:强调社会正义。该任务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通过带动其周边落后地区的发展强调社会正义,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跨地区互动系统之下,强调工业生产产业链的地缘联系。该项任务的实现需要特别强调社会正气、公平和稳定以及地区扶持。政策扶持地区的相关产品发展;分配专门基金发展公共服务;开发外部小岛和边境地区;同时协调超大、大、中、小城市经济增长和工作机会创造;在部门、政府、商业和社会之间进行协调、同步、整合和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海洋产业导向的地区);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支持地区商业投资机会的开发;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包括贫困人口、偏远地区、自然灾害受灾区;扶持女性发展。
为了完成任务,印度尼西亚已经决定在2014年之前实施5个国家发展日程,即: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福利(日程I),改善政府管理(日程Ⅱ),巩固民主基础(日程Ⅲ),实施法律和消除腐败(日程Ⅳ),包容和公平发展(日程V)。
增进人民福利的日程在2014年之前享有政府的优先权。福利提高的最终形式反映在收入水平提高、失业降低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一些核心政策包括:①极度贫困、贫困和贫困边远家庭基本数据(姓名和住址)的编辑,这是指导社会保障和援助项目的核心;②减贫项目的分类;③PNPM Mandiri社区扶持项目的和谐统一;协调从中央到地方减贫的步调,包括实施的联合责任。实现目标的最重要项目是J amkesmas(社会健康保障):贫困儿童的教育、贫困家庭的食品,PNPM Mandiri(社区扶持项目)和KUR(小业主贷款)。
就第二个日程而言,机构改革将在所有部门和政府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展开。预算程序和基于预算系统活动的执行将全面实行。上述两项将巩固、扩展和加速机构改革,并与很多司法改革结合起来。由于改善政府管理的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部门,同时涉及包括国有公司的管理等私有部门,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了提高开放程度和运营责任,鼓励企业家向公共公司转型。这一步对于消除贫困、裙带关系和利益冲突十分重要,否则将阻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支持民主,应该特别强调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公平调查和平衡;尊重多样差异;依法治国;平等和公平;国家和地方的公平普选;保护公民的信仰、出身、阶层和性别。
就旨在消除腐败的执法而言,日程涵盖了法律制定、诠释、监督和已经颁布的法律的执行以及腐败案例。日程同时注意确保自由的司法过程。这将有助于巩固民主。通过增加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责任性、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以及司法系统的透明度和开放程度,法律结构的问题得以解决。因此,政党、商业团体以及全体司法队伍,包括警察、国家检察机关、法院和律师都必须一致执行法律规则和遵循法律系统。
就日程V而言,经济领域的正义主要体现在改革中或者扶持落后群体、残疾群体和边缘群体的项目中。在社会政治领域,公平参与(包容性)体现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政治活动中的性别平等和歧视的消除。在经济领域中,特别是就降低收入差距而言,通过直接项目将高收人群体资金向低收人群体资金转移,收入再分配是关键政策之一。将燃油补贴向教育和健康补贴转移是另一个关键政策。
就减贫的努力而言,采用了多项途径,包括自下向上发展策略,表现在多个项目如PNPM(国家社区发展项目)。此项目中,项目计划阶段、筛选阶段和评估阶段都涉及社区。发展阶段社区的参与是一项必要组成部分。通过此项目社区将获得所有权,在与项目合作的同时从中受益。
在2014年以前,在每个项目每个经济发展活动中都将强调正义和包容。例如,通过家庭希望工程(PKH),教育和健康的有条件现金转移将提供给极度贫困的社区。这项政策在短期将为贫困家庭提供额外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在长期将提高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此外,政府将提高社会保障的质量,并在社会援助系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家庭。
七、 政策建议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于包容性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值得高度鼓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印度尼西亚仍然面临着3个可能阻碍包容性发展的严重问题,即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特别是地方政府尤为严重;法律执行力度低下,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腐败自新秩序政府(1998)倒闭以来已经极其严重,在政府和社区的各个层面泛滥;基础设施缺失,不仅是道路、港口、电力、通信和交通设施,还有学校,以落后、前线、边缘和冲突地区为甚。
虽然很多其他直接或间接因素在包容性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解决上述3个问题,包容性经济发展只能是另一个政治口号,对于人民的福利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因此,机构改革、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的发展、法律的执行、腐败的消除等与落后、前线、边缘和冲突地区全体人民教育和健康的发展、减贫(全体人民的就业机会)、食物保障、能源和环境保护成为国家优先考虑事项。
(编译者:夏庆杰 赖海涛)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
地址:北京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86-10-84419655 传真:+86-10-84419658(电子地图)
版权所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京ICP备2020039194号-2